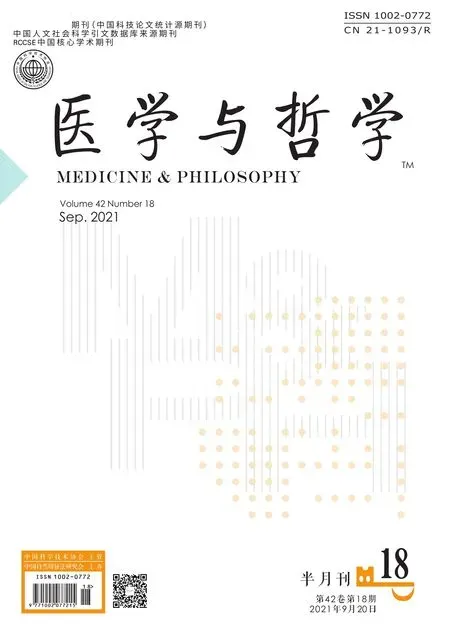痛苦如何走向哲学
——痛苦哲学的内涵、隐喻与范畴
王一方
1 从疼痛哲学到痛苦(苦难)哲学
痛苦是什么?它是人类的基本困境,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人类第五体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体验,也是人的社会化的必然代价,自从人类有了疼痛的体验开始,就萌生了疼痛的哲思,继而有了朴素的疼痛哲学,力求将痛觉的咀嚼升华到灵与肉的二元拷问上来,随着疼痛体验之上投射更多的社会、心理,乃至政治、经济、文化光斓,不仅只关注失控、失能、失智等躯体功能丧失之苦,还关注失意、失落、失重等心理之忧,更旁及失恋、失业、失独等社会事件之痛,疼痛哲学逐渐嬗变为疾苦哲学、苦难哲学。在哲学语境里,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痛苦的意义》一书中认为对疼痛的纵容本质上是拒绝轻而易举获得的快乐和幸福;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认定:痛苦是人生的“象征性交换”工具,由此来确立受苦的意义,它不仅是人生快乐与幸福的映衬与参照物,还是生命意志的磨刀石,是巅峰体验的前戏,是活力人生的源泉与进取人生的催化剂。维尔热里(Bertrand Vergely)[1]归纳:痛苦的意义不外乎生命信号(符号,符号即意义)、悟-道(智慧)、宿命回报(报应)、得救(救赎)。在尼采的直觉里,激起人们反抗的并不是痛苦本身,而是“痛苦的无意义”(悲剧性)。人生的真谛就是对苦难的穿越与超越,对死亡的直面与豁达。在医学语境里,一部疾病史就是人类的蒙难史、劫难史,一部医学史就是苦难的抗争史、抚慰史。苦难哲学本质上是患者的哲学,作为亲历者,穿越苦难、咀嚼苦难是患者的疾病境遇与疾苦体验,作为他者,同时又是关怀者,回应苦难、阻断苦难是医者仁心、临床疗愈的永恒诉求,而理解苦难、超越苦难,更是人类精神豁然、升华、觉悟、解放的阶梯。
痛苦哲学也是时代思潮的晴雨表,痛苦意识折射出时代的反思,从临床实务上看,患者至上(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文化必须建立在苦难哲学的基础之上。相反,技术至上、技术至善主义者常常以各种理由(虚玄,不被纳入循证医学的认知轨道)来漠视痛苦哲学,以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哲学来取代苦难哲学的价值深究。从因应疼痛(躯体)到回应痛苦、疾苦、苦难(全人),是当代医学必须完成的一次思想淬火,是人文医学不可或缺的自我警醒与建构,从关注疾病到关注疾苦,从关注病到关注病中被疾苦折磨的人,从止痛、镇痛到抚痛、抚慰,也是医疗行为必须要完成的价值拓展,是人文医疗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全人医学模式的兴起,叙事医学为契机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复兴为苦难哲学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航道。深究临床工作中的疼痛治疗,其位阶不高,它不是病因学干预,也不一定是发病学干预,只是症状学、安慰性干预,因此发掘不充分。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深知,充分止痛仅为初级干预,就疼痛的症状学处理而言,无论是末梢神经的局部阻断,还是中枢性阻断,都是权宜之计,而非根本性解决方案。高级干预更多的是关怀、关注、关切、关心、共情;倾诉、倾听、减压,医患之间就疼痛体验展开对话。深情告知:“你说出来,我在认真倾听”“别害怕,这份疼痛体验我也经历过……”
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关于疼痛的定义跳脱出单纯的生物学视野,认定疼痛是组织损伤或与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的一种不愉快的躯体感觉和情感体验,是一种与实际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包括了感觉、情感、认知和社会成分的痛苦体验[2]。近十年来,麻醉与疼痛管理逐渐由外科手术外溢到内科的过程疗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许多医院的麻醉科中分化出疼痛科来,他们脱离外科协同的使命,专注于恶性肿瘤晚期的癌痛、生命末期的整体性疼痛,以及顽固性痛经、痛风、慢性疼痛等,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止痛、镇痛与抚痛、抚慰的张力考验着这个新兴学科的价值位序,更需要从痛苦哲学的高度来提升疼痛科的精神海拔。
伴随着慢病时代与老龄社会的快速逼近,安宁疗护事业方兴未艾,慢性疼痛,衰老之苦、别离之苦正在不断聚焦,成为新的社会热点话题,仅仅基于生物学的疼痛干预显然不足以控制、管理好慢病历程,以及深度衰老境遇中的痛苦。究其根本,还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剪刀差”。1967年,西塞莉·桑德斯(Cicely Saunders)博士通过分析1 100个生命终末期病案,提出“整体疼痛”(total pain)概念,包括躯体疼痛、精神心理的痛苦、社会的和心灵的困惑[3]。因此,安宁疗护病房里仅有躯体镇痛是不够的,还需要心理疏导与心灵抚慰。随着人们熟知的特鲁多人文医疗纲领(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在安宁疗护中逐渐落地,正催生出新的干预哲学,那就是“有时,去止痛;常常,去抚痛;总是,去关怀”。
虽然痛苦哲学与死亡哲学都可归于人生哲学,但两者是一对孪生子,一只双头鹰,生之苦与死之苦息息相关,很大一部分的死亡恐惧、焦虑都源自疾病、衰老的过程痛苦,疾苦心理与死亡心理也存在很多“共轭效应”,甚至潜藏着某种“循环加速机制”,深入研究这些并行规律,可以为临床难题提供连环纾解方案。近年来,死亡哲学逐渐得到重视,有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但痛苦哲学依然沉寂,这不仅阻滞了痛苦哲学自身的进阶,也无助于死亡哲学的发展。
跳脱出临床实务来探究苦难的哲学化命题,需要对其进行哲学辨析,也就是按照哲学思辨的范式对疼痛、痛苦、苦难的语义、境遇进行哲学修辞分析,隐喻追问,范畴建构,才能勾勒出“苦难如何走向哲学化”的认知轨迹。
2 疼痛、痛苦、苦难的哲学修辞
疼痛(pain)、痛苦(pain and suffering)、苦难(suffering),无论在中文语境,还是英文语境,都不是一个内涵齐同的概念,痛苦偏重于遭逢疾苦的主体,而疼痛偏重于疾苦的体验本身,苦难则侧重于躯体之外的复合感受。即使是非医学专业人士,也能感悟到躯体到心灵的两分与递延。也就是说,当人们不再把疾痛-疾苦仅仅看作是一个躯体现象、医学事件,而是一个心理现象、社会事件时,哲学修辞就无可回避,劳特里奇公司2017年出版杰尼福·考恩斯(Jennifer Corns)[4]主编的《劳特里奇疼痛哲学手册》(TheRoutledgeHandbookofPhilosophyofPain),开篇就叩问疼痛的性质,以此作为建构疼痛哲学的基石(表现主义哲学、现象学哲学等),随后从神经生物学、心理学、意识与认识论、宗教、伦理、法律多个维度展开对疼痛的剖析,临床医学只是其中一个维度。2018年,米歇尔·布莱登(Michael Brady)[5]在他的专著《苦难与美德》(SufferingandVirtue)中将苦难与道德、品格作为一对范畴来阐释。2020年,劳特里奇公司推出大卫·拜恩(David Bain)联袂米歇尔·布莱登、杰尼福·考恩斯[6]1-17共著《苦难哲学:形而上学、价值与规范》(PhilosophyofSuffering:Metaphysics,Value,andNormativity)一书,很显然,三位作者是将既往的疼痛与苦难的哲思交互迭代进行深入阐析,追求更高层级的哲学化认知境界。
奥利维尔·马辛(Olivier Massin)在“遭受痛苦”(suffering pain)一节中做了一个三分法,疼痛、苦难、负面感受(negative affects)三个概念交互套叠,负面感受是疼痛与苦难的集合,而苦难是悲伤、疼痛的集合,疼痛是躯体、精神感受的集合,其中的精神体验就是苦难[6]77,疼痛感受常常有特定的部位(location),而苦难则是相对泛化的感受,没有特定部位,也就是说,苦难感受具有横断性、模糊性、隐匿性、混沌性、不确定性,难以言说,但会产生彼此的互动(interactivity)、丰富的表达(expression)、广泛的同情(compassion)[6]84,佛教的人生“七苦说”(生、老、病、死之苦,苦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基本上可以称之为负面感受,既包括疼痛,也包括苦难,但更多的是生命中的苦难体验。
在临床沟通中,每每会遇到“苦不堪言”与“难言之隐”的窘境,未受苦的“我”(医者)与正在受苦的“他”(患者)之间存在着词不达意的鸿沟,当主诉中出现“隐痛”一词时,一般具有不明原因,部位并不清晰,感受难以言说的特征,可以将其作为疾苦躯体化的例证,背后潜藏着两个可能性,一种是社会心理行为失序的躯体化表述,并无确切的疼痛,而是心理、社会、精神遭逢挫伤、挫折的迁移性表述;另一种则是躯体真实痛苦的生物与技术逃逸。其一,疼痛无法显影,既测不准,也不可测,且个体的疾苦阈值不一,疼痛量表(疼痛温度计)存在诸多的局限,临床上更多地依靠医者的观察记录与患者的疼痛叙事,如强迫体位,眉心紧锁,面目晦暗,表情痛苦,嘴角抽搐,撕心裂肺地嚎叫或低沉地呻吟,感觉如同针扎/刀割/火烧/烙铁烙/巨石挤压一般、如同锉刀锉神经一般、如同毒蚂蚁噬咬一般疼痛,“疼得我把脑浆都吐出来了……痛不欲生,痛得天昏地暗,此刻度日如年,顿觉人生灰暗”,萌生自杀念头(不想活了)。其二,痛苦无法还原:神经递质学说无法彻底解读疼痛机理,内源性镇痛内啡肽分泌有个体差异的或然性,那些试图将所有疾苦与苦难都置于生物学的魔镜之下,继而真相大白的外在化、客观化思维,难以契合存在的本相,难以驯服内在化、主体化、主客间性真实世界的疾苦境遇、苦难叙事。
总之,不同于一般的语义分析,哲学修辞更注重价值内涵的钩沉,展现语义背后的历史与逻辑张力。首先,“疼-痛”“痛-苦”“苦-难”都是一个二元复合词,囊括了躯体与精神、感觉与幻觉、个体与群体、结果与过程、存在与价值诸多范畴,从医学辐射到社会、心理、文化,最后归结于宗教、哲学。苦难的基质是躯体的“疼-痛”,继而延展为身心二元的“痛-苦”,最终抵达心灵的“苦-楚”、精神的罹难,汇合为人类无法摆脱的苦难宿命。
3 疼痛、痛苦、苦难的存在与隐喻
作为生命表情:从疾苦-呻吟到苦难-呼号,不仅是痛苦程度的递进,更寄寓着生命希望的残存与破灭之异,隐喻也无所不在。譬如,那一些刻画疼痛的词汇,字面上相近,寓意则差之百丈,如头疼与头痛,心痛与心疼,“头疼”是标识局部症状的特称概念,“头痛”则是饱含“隐喻”的复合概念,它是人生负面感受的集合,泛指一切烦恼,也包括了头疼;“心痛”既是一个特称症候,指心脏部位的疼痛,也是牵挂、惋惜的表达,“心疼”则是要亲缘关切的“隐喻”,充满了歧义,都会因语境变化而改变理解。“难受”(网络热词“蓝瘦”)、“想哭”(网络热词“香菇”)的症候并不跟某一具体的疾病接轨,但却是身心俱疲、生命力耗竭的指征,是心理纠结、精神压抑的“躯体化”象征。
关于疾苦与苦难的隐喻,在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中文名凯博文)的《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中归结于“疾苦的躯体化”,不仅关涉躯体-精神之间的张力,还旁及跨文化比较的境遇,当个体经历了严重的身心创伤,常常通过身体这一外在化的载体(容器)来解释、表达内心的精神、社会苦痛。凯博文[7]认为: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境遇中话题与行动的隐喻。身体苦痛决定并调节着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不公境遇的解读,前述的“头痛”“难受”(泛化的疾苦)不过是疾苦“躯体化”的特例,极端的案例莫过于已经截肢的战士嚷嚷着肢体疼痛,一部分痛苦的感觉来自感知惯性与幻觉,另一部分痛苦则来自截肢的罪感。
无疑,痛苦意义的精神化呈现出特有的“深井效应”,生命书写之外,依次呈现接纳痛苦、穿越痛苦、超越痛苦,苦难中发现意义(灵性)的人生真谛,苦难是人生的炼狱(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年礼),成功的阶梯(人生淬火);孟子在谈论“生于忧患(苦难),死于安乐”主题时的名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其中蕴含着苦难哲学的逻辑开阖,精神的升华必然以躯体痛苦作为代价,苦难与快乐是一体两面,相互转圜。
有一些睿智的临床学家,也加入了痛苦哲学的探索之中,其中就有保罗·布兰德(Paul Brand),他在自传体纪实《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与菲利普·杨西合著)一书中表达了“讴歌疼痛”的独特立场,他认定疼痛是造物主的“礼物”(隐喻),是人类的“卓越特权”,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是生命疗愈与个体健康的同盟军,这位印度裔(有着禁欲超世的宗教信念)手外科医生、麻风病医生,常常接诊末梢神经麻木(失去痛觉)的患者,在他的临床中,令他震撼的是一位先天性无痛症患者丹耶,他对自我摧残行为完全无感,后来,林林总总的麻风病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疼痛缺失症,由此失去了对于危险境遇的预警功能,这一切都引出他对传统疼痛观念的反思,于是乎,他大胆地提出了疼痛“礼物说”,以表达人类智者对苦难的别样渴望与感激。 临床上也有“以痛止痛”(转移说,如针灸将疼痛转变为胀麻感、酥热感)的悖论。因此,许多医者并不期望,甚至不曾想象“无痛的生活”,如果医者手中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除躯体疼痛”的特权,他将不会行使这个权利[8]。
与之类似,疼痛有益论(dolorist)的纷争也曾经甚嚣尘上,dolorist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19年法国《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作家兼记者朱利安·泰普(Julien Teppe)透过他的畅销书(《为失常辩护》《专横的疼痛》)与雄辩,将这个术语推入大众视野,成为当时的一个热词。不仅发表了《疼痛有益宣言》,还创办了《疼痛有益杂志》,其基本观点“我遭受疼痛,所以我在(我痛故我在)”有着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在他看来,疼痛是人性的宣泄,一种在冗余的、偶然的、虚伪的现代性中挣扎并获得净化的途径,是人类超凡脱俗的理想境遇。“在所有的生理状态中,疼痛是最普遍的也是最强劲的,既在精神方面,又在肉体方面控制着人的全部活动,它不容许欺瞒和妥协,而展现出真实与决绝,它一登场就足够抵消其他所有的意念与欲望,它是能够主宰我们生命和生活的因素,具有超脱世俗的功能与价值,疼痛可以激发人性中的同情与悲悯,反省人性中的自私与贪婪、敌意和战争。”“极度的痛苦,尤其是肉身的疼痛,就是为了在每一个个体中激发出绝对的理性主义信念,就人类创造与创新而言,它是完美的刺激”[9],医生的临床作为,一方面致力于减轻、消除患者躯体上的疼痛,更有义务激发患者穿越痛苦之后的精神升华。
若以更大的视野审视人生,苦难是命运与时代的机缘:历史是一架飞驰的过山车,战争、饥荒、瘟疫、动乱总是周期性光顾人类,而且常常是无征兆地降临,于是便有了“四骑士”的隐喻,其启示有二:一是人类终究无法摆脱苦难宿命的纠缠,尊重宿命是必然选择,二是在苦难与幸福的交替中确认人类对命运的挑战性、主体性,努力倡导并践行人道主义。医学作为人道主义信念的积极倡导者、笃定坚守者,必须见证苦难,在穿越中搏击苦难,继而驾驭、管理苦难,努力为人类造福。
4 疼痛、痛苦、苦难哲学的基本范畴
范畴论无疑是哲学化的高级形式,洞悉疼痛、痛苦,乃至苦难的基本范畴也是建构痛苦哲学的内在需求。古往今来,这份理性诉求一直没有停顿,但21世纪的苦难哲学范畴应该具有更高的学术境界,更深的思想与价值内涵,以便回应、解读更复杂的临床生活、更先锋的技术境遇。
自从人类咀嚼痛苦的生命意蕴开始,就将其置于快乐、幸福的对立面,分娩之痛与性爱激情何尝不是一种交换。因此,从互文性角度开掘痛苦-快乐,苦难-幸福的意义就成为苦难哲学的基本使命。生活中,痛苦与忍耐、个体痛阈差异常常呈现出不同的苦情反应与苦难表达,背后的支撑是信念(文化与宗教投射)、阅历(年龄与职业)的内在因素,以及医疗关怀与抚慰的外在因素,使得人文医疗的胜任力在痛苦与干预中的权重起起伏伏,医者对他者苦难的敏感、共情成为医患和谐度、满意度的重要关注点。苦难的人性纾解并非依赖药物,而是解读苦难来去的规律,面对疼痛、苦楚、罹难,患者同样也会有“罗斯五步”的拒绝、愤怒、讨价还价、沮丧的情绪、最后一刻的无奈接纳[10]。接纳痛苦之后的应对思路有三:其一,解决(抗争、制止,包括即时止痛);其二,直面(迎击、不回避、不放弃生命的目标);其三,解构(无意义的痛苦)与建构(重新赋予意义)。对于医者来说,面对躯体的精神化与精神的躯体化,抗争疾苦与接纳疾苦并行不悖,此时除了止痛剂的使用之外,还必然对患者施以痛苦觉悟、苦难解放的人生哲学启迪。以癌痛为例,常常引入基尔凯廓尔(Soren Abby Kierkegaard)的苦难寻因,着眼于罪与罚(报应说)、辜与伐(好人无辜受难)、蛊与惑(阴谋论)的除魅,旨在帮助患者把握生命感知与生命意志的张力,寻找希望的星光。由于人们常常在疾苦变化中遭逢乐极生悲(悲伤即痛苦),或苦尽甘来的人生转圜,模糊了不幸与有幸,憎恨/诅咒疼痛与热爱/礼赞疼痛的是非边界,一番归因分析,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诱惑与决绝)的思索也进入苦难哲学的范畴谱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信条的认同本质上是苦乐、祸福辩证法则的觉悟,既不用享乐主义的态度逃避苦难,也不用英雄主义的豪情去轻慢苦难。同样,医疗行为也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消除疾苦,另一方面增加苦难,究其原因,既有医疗事故(有技误施)、临床中突发的、不可抗力的意外与无奈(无技可施、有技难施),还有恶劣的医源性战争苦难,如731医生、纳粹医生,以医疗手段参与战争杀戮(背叛良知,其心可诛)。
如何认识并解读个体痛阈与疾苦体验的差异性,需悉心追问疾苦境遇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客体性与主体性,外在性与内在性,外感受与内感受,疾苦感受的集束效应与分散效应,躯体疾苦的凝视效应与社会心理与文化的泛化效应等各种范畴与张力,除此之外,别无门径。疼痛意识的特征十分复杂,一方面是无意识的、模糊的感受,另一方面又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临床上,疼痛患者既难以言说,又急于倾诉,呼唤认同与理解。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11]建构的“可见的不可见性”意念恰恰为破解疾苦感受的“精准与模糊”困境提供了哲学智慧,在他未完成的手稿中,提出“在场的肉身”(la chair du present)概念,揭示“正在知觉中的、活动(漂浮、游离)的、带着欲望的、痛苦着的躯体”,以及作为前客观存在的“身体间性”,人是实在(身体)的,也是存在(感知)的,痛苦本不是某一个或一组绝对值所标定的客观指征,而是实在经历的存在体验的交织。现象学家兼脊髓侧索硬化症患者图姆斯(Toombs)[12]在《病患的意义》一书中的呼唤:“医生,你只是观察,而我在体验!”揭示了医生世界与患者世界的两分,相对于医者“观察,故我在”,患者的“体验,故我在”更真切地抵达疾苦、苦难的渊薮与本质。临床上,从疼到痛,从疾痛到疾苦,从痛苦到苦难,就是一个不断背弃精准性,迈向模糊性的“返祖”过程,也是医学不确定性与诊疗艺术性的真实呈现,任何“刻舟求剑”的疾苦认知都是幼稚的,甚至是愚钝的。
在循证医学如日中天的当下,疾苦似乎与新兴的叙事医学有更多的不解之缘,把握疾苦、驾驭苦难更多的不是观察,而是聆听、分享患者的体验,疾苦体验虽有客观性,但主观感受与个体阅历、语言表达的偏好更占上风,相对于外感受的描述而言,患者对于疾苦的内感受,时间性、独特性、偶在性、因果偶然性、主客间性、伦理性依次凸显,这些内容在丽塔·卡伦[13]的《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一书中有专题介绍,疾苦叙事的重要性促使丽塔·卡伦要修正医学的目的,不再拘泥于救死扶伤,而是致力于“回应患者的痛苦”。相对于救死扶伤,“回应患者的痛苦”的使命更加期待苦难哲学的完善,也更加关注证据与故事的张力。阿瑟·克莱曼[14]的《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丰富了慢性疾痛哲学的范畴,譬如疾苦的“个人境遇与社会境遇”“疼痛的脆弱(疾苦人格)与脆弱的痛苦(疾苦的敏感性、漂移性)”“生活的痛苦(底色)与疾病的痛苦(叠加)”“慢性疾病中的痛苦:欲望与希冀、羞耻与罪感”“疾病境遇中的痛苦与死亡逼近境遇中的痛苦”“人类学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这些话题的释出不完全源自学术探索,也来自于他十年间照护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琼·克莱曼(Joan Andrea Ryman Kleinman,中文名凯博艺)的真实感受与开悟。在需要长期照护的慢病时代,疾苦的泛化弥散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生命的每一个节点,疼痛管理变得日常化、精细化、本土化。患者需要止痛药物,更需要陪伴、见证、抚慰、安顿,以及共情、关怀、呵护,这些有价值的照护技能却被排斥在医学教育的谱系之外,使得专业照护失去人情味,因此,痛苦哲学的新使命是反思以“数字化(证据、算法)”为特征的新技术主义,推动医学教育的改革进程[15]。
无疑,痛苦的哲学化之旅还在斜坡之上,本文对痛苦的哲思仅仅只是吉光片羽的序章,期待有更多的学人参与这一母题的建构,尤其希望一线临床医生奉献他们的疾苦叙事、分享他们的哲学洞悉。从而揭示痛苦对医学映射的丰富性,彰显痛苦与生命意志、痛苦与人类文明的永恒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