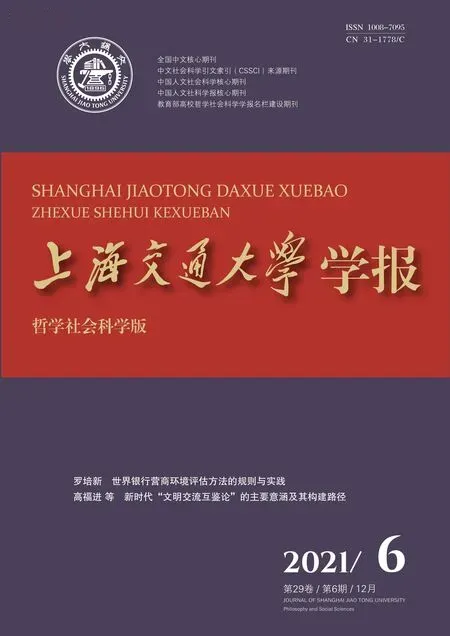论北方族群法与东亚法文化圈的关系: 以盗罪倍赃制的传播为中心
张春海
(南京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46)
本文标题所说的“盗罪倍赃”制指对犯盗罪者罚以一倍以上之物的制度,尽管它在各个国家、群体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复杂的形态,但它们在对盗赃罚“倍”(由一倍到多倍)这一核心做法上是一致的,且这一做法具有大致完整的演进脉络。而“北方族群”即学界从前所习称的“北方民族”,指主要由历史上各游牧部族组成的位于华夏族群北方的各族群,为了叙述方便,简称“北族”。本文之所以用“北方族群”替代“北方民族”,是因为“民族”乃是近代形成的与民族自决原则直接相关的一个政治概念,用之指称历史上的人类群体,难免有时代倒错之感。
引 言
关于古代东亚法文化圈的形成,以日本学者之研究为基础的通说,一般将其与“律令制”挂钩。所谓律令制就是“建立在律令法基础之上的支配体制”。(1)荒松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第6卷[M].东京: 岩波书店,1971: 41.日本学者赋予了律令制以如下特征: 中央集权的官僚性的国家体制,区分良贱的身份制,以及土地国有制。(2)荒松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第6卷[M].东京: 岩波书店,1971: 41.显然,这一模式是从日本大化改新之后到镰仓幕府成立之前约四百年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3)在法制史领域,泷川政次郎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继受法时代”。(泷川政次郎.日本法制史[M].东京: 角川书店,1969: 66-67.)在日本学者看来,东亚法文化圈与律令制的关系不言自明: 6—10世纪之东亚法文化圈的基本内涵就是律令制。质言之,受唐制影响的国家都是律令制国家,它们构成了东亚法文化圈。岛田正郎的说法颇具代表性——他把法文化圈理论、朝贡体系理论、律令制理论紧密结合,认为因唐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当时的东亚诸国皆以唐为宗主国,在和唐建立起朝贡关系的同时,也希望将自身建成与唐具有同样国家体制的国家;为达致这一目的,就必须移植作为唐之国家体制基础的法律体系,并通过这种法律体系,建立起理想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渤海、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4)岛田正郎.アジア: 历史と法[M].东京: 启文社,1962: 216-217.
且不说除日本以外的四个与唐同时代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唐的律令制,是否成了律令制国家,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学者将传统中国法局限于“中原文明”的范围,他们所谓的“东亚法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为取代“中华法系”提出的概念。尽管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这一概念基本均与“中华法系”等值,但它淡化了传统中国法在其中的核心地位。(5)文化圈的理论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2000年,日本山川出版社就出版了早稻田大学李成市教授名为《东アジア文化圈の形成》的专著。该书被认为是以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为依据,对东亚世界历史的各种相关问题均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并指出了西嶋定生学说中的不足之处,乃意欲从事册封体制研究者的必读书,因而被誉为是上乘之作。(金子修一.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隋唐史的研究[J].李济沧,译.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7): 19-25.)日本学者虽也有“中国法系”的说法,但实际多指中原文明,和我们理解的中华法系不同。(6)比如岛田正郎即云:“中国法系(从唐代开始),在以后之各个时代,在东亚诸地域得以广泛实施。将这些事实总括起来,设定一个东亚法文化圈是可能的。”(岛田正郎.东洋法史[M].东京: 明好社,1970: 160.)他们既不能正视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愿承认在此空间范围内,包括法律在内之各种文化间的内在联系,而多从冲突、对立的视角看问题。与此相关,他们忽视了比他们所说的“东亚”更广大的区域内诸文明在法制上的联系。(7)有学者在直到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还讲:“历史上的‘汉字/东亚/儒家/中华文化圈’,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不包括隶属于中国的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边疆游牧地区,却涵盖了朝鲜、琉球、越南、日本等深受传统中国的汉字语言、律令制度、儒学思想、佛教教义等至少四个方面影响的东亚国家。”这一说法不完全准确,明显受到了日本学界“通说”的影响。其提出者在文章注释中,也明确提示,此说来自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东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颜丽媛.国际礼法观: 清代中国的朝贡与条约[J].南大法学,2021(1): 86.)而在此更广大区域内的诸多法律文明,由于某些媒介与纽带的作用而形成的松散法律共同体,即本文所称的“东亚法文化圈”。质言之,我们所说的东亚法文化圈是一个较中华法系范围更大、联系也更为松散的法律共同体,北方族群法是这一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此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起着纽带作用。由于史料缺略,对北方族群法的这种作用,我们已无法做全面、综合性的探讨,只能以现在所知的某些具体制度为断面,一窥其间的某些脉络,盗罪倍赃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本文将通过对与此制相关信息的拼接、分析与解读,对北方族群法与中华法系、东亚法文化圈的关系进行探讨,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法律传播之一: 北方族群法影响下的隋唐法制
(一) 隋唐律典中的盗罪倍赃制与中原文明无关
《唐律疏议·名例律》“诸以赃入罪”条注云:“盗者,倍备。”律疏释曰:“谓盗者以其贪财既重,故令倍备,谓盗一尺,征二尺之类。”(8)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M].北京: 中华书局,1996: 328-329.“倍备”即盗罪倍赃,虽具有刑罚性质,但由于赔偿物归于受害人,赔偿性亦是其主要的法律特性之一。
当然,关于倍赃究竟归于国家还是受害人,学界有不同认识,占主导地位的是仁井田陞主倡的归于国家说。但必须注意的是,唐代法制有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不能以某一时期某个条款的规定概括有唐一代的整体状况。仁井田陞之说实际基于唐令。他说:“在唐律中,规定对于盗犯,除了应向被害者返还被盗物外,还要征收和被盗物同等数额的倍赃。可是,在此情况下,并不免除盗犯的实刑,倍赃也不是给予被害者,依据唐令,倍赃只应作为奖赏,给予揭发盗犯之人。”(9)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补订版)[M].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 303.
他所说之唐令,乃开元二十五年《捕亡令》。该令规定:“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10)仁井田陞.唐令拾遗[M].栗劲,王占通,译.长春: 长春出版社,1989: 658.这一规定乃开元后期制度,唐律却是承袭隋律而来,且在永徽之后基本未有大的改动。(11)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讨论,可参考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序论[M].北京: 中华书局,1996.因此,唐律中的盗罪倍赃制在隋代当已确立。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其《名例律》“诸彼此俱罪之赃”条律疏云:“假有乙盗甲物,丙转盗之,彼此各有倍赃,依法并应还主。甲既取乙倍备,不合更得丙赃。”(12)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M].北京: 中华书局,1996: 316.物的合法所有人有权获得倍赃,但不能再得到之后又转相盗窃的倍赃。开元《捕亡令》将倍赃作为奖赏,是对永徽律疏的修改。仁井田陞之所以未看到这种变化,当是由于他认为现存《唐律疏议》乃开元律所致。(13)20世纪30年代,仁井田陞和牧野巽著《〈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文,考定《唐律疏议》非永徽律疏,而是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新颁行开元律的律疏,至今仍是日本学界的定说。1978年,杨廷福在《文史》第五辑上发表了《〈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1982年蒲坚在《法律史论丛》第二辑发表了《试论〈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问题》,以详细、严密的辩证,证明了中国学术界关于《唐律疏议》的传统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关于此问题,还可参考岳纯之.仁井田陞等《〈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及其在中国的学术影响[J].史林,2010(5): 183-187,191.
敦煌文书中的《文明判集》就载有一个适用盗罪倍赃制的案例。案由如下:“豆其谷遂本自风牛同宿,主人遂邀其饮,加药令其闷乱,遂窃其资。所得之财,计当十匹。事发推勘……乃款盗药不虚。未知盗药之人,若为科断?”判云:“语窃虽似非强,加药自当强法。计理虽合死刑,挛脚还成笃疾,法当收赎……正赃与倍赃并合征还财主。”(14)刘俊文.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考释[M].北京: 中华书局,1989: 441-442.该判对于赃物,要求征倍赃,归于财主,而非国家,显示唐律中的盗罪倍赃制是一种个人指向的具有鲜明赔偿性的法律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周以来中原文明的类似制度。之所以如此,乃因它本来就非来自中原法律传统。
中原文明关于盗罪倍赃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周代金文。《散氏盘》铭文曰:“用夨践散邑,乃即散用田……乃卑西宫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湿田、畛田,余有爽变,爰千罚千。’西宫襄、武父则誓。厥受图,夨王于豆新宫东廷。”(15)王玉池.古代碑帖译注[M].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0: 24.胡留元.从陕西金文看西周民法规范及民事诉讼制度[J].考古文物,1993(6): 16.铭文讲到周王派遣大臣“夨”来到姓散的城邑,命出让土地者对大家发誓。誓词中的“爰千罚千”乃罚金一倍,交于官府。“罚爰”的惩罚色彩明显,国家指向突出,个人层面的赔偿色彩甚淡。
《周礼·秋官》:“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楬之,入于司兵。”汉代郑玄注曰:“入于司兵,若今时伤杀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县官。”(16)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20.这一记载可与《散氏盘》中的“罚爰”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由郑玄注可知,汉代存在“加责入官”制,其运作方式是先对盗贼之赃加倍处罚,然后没入官府,与西周的“罚爰”制基本一致,很可能是西周以来中原地区流行之制度的残余。
从种种迹象看,“加责入官”制在秦汉时期的适用范围并不广泛,除了郑玄注之外,与之类似的只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对伪造书证的规定:“诸诈增减券书,及为书故诈弗副,其以避负债,若受赏赐财物,皆坐臧(赃)为盗。其以避论,及所不当(得为),以所避罪罪之。所避毋罪名,罪名不盈四两,及毋避也,皆罚金四两。”(17)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M].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1: 135.该规定可看作罚金一倍入于官府,亦为国家指向,而非对个人的赔偿。
对于盗罪,未见《二年律令》有直接规定。日本学者堀毅著有《秦汉盗律考》一文,用相当大的篇幅揭示盗与赀罚的关系,(18)堀毅.秦汉盗律考[J].法制史研究,1983: 岛田正郎博士颂寿记念论集刊行委员会.东洋法史の探究: 岛田正郎博士颂寿记念论集[C].东京: 汲古书院,1987: 130-152.却未提及任何与盗罪倍赃相关的规定。关于对盗赃的处理,《秦简·法律答问》:“盗盗人,买(卖)所盗,以买它物,皆畁其主。”(1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8: 160.《二年律令·盗律》:“盗盗人,减(赃)见存者,皆以畁其主。”(20)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M].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 16.由这些材料可知,秦及汉初对于盗赃,以归还原物为原则,而非加倍赔偿。在直承汉魏的两晋南朝法律中,也不见类似制度。由这些迹象,我们基本可以推知,在早期的中原文明中,“罚爰”“加责入官”一类的制度应该过早地衰落了,(21)仁井田陞则指出:“政治权威在中国很早得以确立,对于违法行为的制裁,是向科以国家性质之刑罚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立场的赔偿制在中国刑法典中的规定是贫乏的。”(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补订版)[M].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 310.)不能成为隋唐法制中盗罪倍赃制的渊源。
(二) 北方族群法影响下的隋唐盗罪倍赃制
笔者认为,隋唐法制中具有鲜明个人赔偿性质的盗罪倍赃制乃是由鲜卑人带来的古夫余人的法律。这一制度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族群南下的浪潮,在族群与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进入了中原王朝的法典。
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夫余人曾经是东北亚地区经济、文化、社会最为发达的古族,其风俗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制度,都对我们称之为秽貊系的诸民族有过深远的影响;其开发松嫩平原所取得的成就,直到其亡国5个世纪以后,才为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所超越”。(22)杨军.夫余史研究[M].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1.同样,夫余人也发展出了一套独特而又相对完整的法律制度。《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用刑严急,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尤憎妒,已杀,尸之国南山上,至腐烂。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兄死妻嫂,与匈奴同俗。(23)陈寿.三国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63: 841.
赔偿制是这套法制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有“输牛马”的制度;其次,杀人者,需没其家人为奴婢;再次,在北方各族群中最早发育出了盗罪倍赃制,即“盗一责十二”之法。从性质上看,古夫余的盗罪倍赃制首先是一种与死刑并列的刑罚;其次,所罚之物要交给受害人,具有明显的赔偿性,与汉代的“加责入官”制完全不同。
夫余作为当时东北地区的文化中心,其文明对周边各族群,如鲜卑、高句丽、百济、勿吉(靺鞨)均产生过重大影响。(24)范恩石.夫余兴亡史·前言[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其中,鲜卑在夫余之西,紧邻夫余,在文化上与夫余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盗罪倍赃制亦为其所吸收,并随着鲜卑人的大迁徙被带到了北方草原地带。(25)张春海.论古夫余族“倍偿”之法对古代东亚法制之影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28-32.《魏书·刑罚志》:“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昭成建国二年: 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26)魏收.魏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2873.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原理上,鲜卑人的盗罪倍赃制均与夫余类似。
代国时期,昭成帝什翼犍将盗罪倍赃制以成文法的形式颁布,使之逐渐成为内亚草原地带各游牧族群的共有法,进而成为一种法律传统,这是内亚传统连续性的体现。罗新曾指出:“内亚历史上,一些政治集团消亡了……一些集团南迁进了中国传统农业地区了……一些集团西迁进入中亚了……然而,内亚草原上的游牧社会与游牧文化从未中断,内亚游牧政治体也持续涌现,尽管这些政治体规模大小有别,统治集团所说的语言各不相同,各政治体的历史认同(主要表现在部族名号与起源迁徙的历史叙述上)亦频繁改变,但内亚政治和文化仍然呈现鲜明的连续性。”(27)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M].北京: 海豚出版社,2014: 66-67.因此,不论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如何变换,(28)如罗新所言:“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所谓‘民族’,都首先是政治集团,是政治体……政治体是实质,血缘联系通常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历史叙述。内亚不同时期的统治集团固然有变动,但作为各政治体基础的民众,当然存在着政治权力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变化和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但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社会成员或后裔,与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并无两样。”(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M].北京: 海豚出版社,2014: 68-69.)盗罪倍赃制适用于草原地带,始终不变。比如,从现存回鹘契约文书可知,元代回鹘亦盛行赔偿制,其中一种即是一赔二,与唐代的盗罪倍赃制类似。(29)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见霍存福.古中国与古罗马契约制度与观念的比较[J].美中法律评论,2004(12-1): 49.
作为各北方族群共同法的盗罪倍赃制,由鲜卑人在中原建立的北魏王朝多次立法进入北朝的成文法体系。从隋唐法制的渊源看,(30)刘俊文指出:“隋开皇律系以北齐律为底本,兼采梁律和北周律而成。”(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M].台北: 文津出版社,1999: 72.)盗罪倍赃制显然是通过隋代立法而成为隋唐王朝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隋及唐初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法律必须轻简,史称隋文帝“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31)魏徵.隋书[M].北京: 中华书局,2000: 3.张伟国指出:“隋初急于修律,其原因是文帝欲行宽大之政,以收人心。”(32)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140.因此,《开皇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纵轻”。(33)魏徵.隋书[M].北京: 中华书局,2000: 710-711.这一立法原则亦为后世所继承。《大业律》“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是时百姓久厌严刻,喜于刑宽”。(34)魏徵.隋书[M].北京: 中华书局,2000: 716-717.《贞观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35)刘昫.旧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2138.在这一法律轻简化的浪潮中,盗罪倍赃亦当不断减轻,一直降到了二倍。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言,在隋唐法制中当有一些北方族群法的因子,但经过上百年与中原法的融合,发生了严重变形,使我们难以察觉它们的踪迹,只有盗罪倍赃制流下了一些可供追索的印痕。由这一线索,我们推测: 北方族群法之于东亚法文化圈的形成,首先在于它们对隋唐法制的作用,而隋唐法制文明的凝成直接导致了中华法系这一东亚法文化圈中最重要法系的成立。
古代中国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一部北方族群与中原人群反复互动的历史。在由秦到清两千余年间,至少有三次大规模北方族群南下征服华夏的浪潮。北方族群法随着此种浪潮大举进入中原地区,与该地区既有的法律传统相互碰撞并逐渐融汇,使中华文明具有了一些新特征。
二、 法律传播之二: 古代东亚诸文明对北方族群法的吸收
(一) 朝鲜半岛的盗罪倍赃制
盗罪倍赃制亦为和夫余人比邻而居的高句丽吸收,之后又随着高句丽帝国的扩张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北部。《北史·高丽传》:“高句丽,其先出夫余……其刑法……盗则偿十倍,若贫不能偿者及公私债负,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用刑既峻,罕有犯者。”(36)李延寿.北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310-3316.同夫余一样,高句丽的盗罪倍赃制也是一种刑罚。从“贫不能偿者”需“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的情形看,赔偿物给予受害人,具有赔偿性,与夫余、隋唐的做法一致。
百济上层统治集团为夫余族的一支,后来逐渐迁徙到位于朝鲜半岛中部的汉江流域,建立了百济王国,其原有法律亦被带入新居之地。古尔王二十九年(262年)正月令:“凡官人受财及盗者,三倍征赃,禁锢终身。”(37)金富轼.三国史记[M].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290-291.比之古夫余法,百济人的盗罪倍赃制有了很大改变。
首先,此制的适用范围,不再局限于盗罪,官员的受财行为亦适用此法。这应和当时官僚制的发展、王权的强化及王权对官僚集团强烈规制的愿望有关。就在律令颁布两年前,百济设置了六佐平、五率、十德的官僚体系,同时还制定了官品、服色制度。(38)金富轼.三国史记[M].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221.两者之间当有一定的关联。因此,我们看到,此法在适用范围上还附有“禁锢终身”的附加刑。
其次,所罚倍数大为减少,从之前的十二倍减到了三倍。之所以会出现此种变化,当与他们到达了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半岛中部,农产品有了更多剩余,人们对财产犯罪之社会危害性的评价随之降低,而文明程度又有了较大的提升有关。这和盗罪倍赃制在唐代发生的情形类似。
(二) 中南半岛的盗罪倍赃制
与朝鲜半岛通过高句丽和百济吸收北方族群法的情况不同,位于中南半岛的越南对以盗罪倍赃制为代表的北方族群法因素的吸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制度特别是唐律的移植实现的。古代越南的《黎朝刑律》(又名《国朝刑律》)共十五章722条,据学者研究,该律基本以唐律为模本制定,条文多直接移植唐律或对之做了微小修改。(39)刘仁善.黎朝刑律?.8497.0EFF3F9A863FA1BC485423A1BDC1D1D6AEB7A8A3ACC6E4C1F7CDBDD6AED7EFBDD4BCF5D7DDC7E1A1B1A1A3A1BC5A57A3A83B58A1BDA1BC5A4BA3A8A1BDCEBAE1E72ECBE5CAE9A3DB4DA3DD2EB1B1BEA9A3BAA1A1D6D0BBAACAE9BED6A3AC32303030A3BAA1A1373130A1BC43442A32A1BD3731312EA1BC5A4BA3A9A1BDA1BC5A57A3A9A1BDD5E2D2BBC1A2B7A8D4ADD4F2D2E0CEAABAF3CAC0CBF9BCCCB3D0A1A3A1B6B4F3D2B5C2C9A1B7A1B0C6E4CEE5D0CCD6AEC4DAA3ACBDB5B4D3C7E1B5E4D5DFA3ACB6FEB0D9D3E0CCF5A1A3C6E4BCCFD5C8BEF6B7A3D1B6C7F4D6AED6C6A3ACB2A2C7E1D3DABEC9A1A3CAC7CAB1B0D9D0D5BEC3D1E1D1CFBFCCA3ACCFB2D3DAD0CCBFEDA1B1A1A3A1BC5A57A3A83B58A1BDA1BC5A4BA3A8A1BDCEBAE1E72ECBE5CAE9A3DB4DA3DD2EB1B1BEA9A3BAA1A1D6D0BBAACAE9BED6A3AC32303030A3BAA1A1373136A1BC43442A32A1BD3731372EA1BC5A4BA3A9A1BDA1BC5A57A3A9A1BDA1B6D5EAB9DBC2C9A1B7A1B0B1C8CBE5B4FABEC9C2C9A3ACBCF5B4F3B1D9D5DFBEC5CAAEB6FECCF5A3ACBCF5C1F7C8EBCDBDD5DFC6DFCAAED2BBCCF5A1B1A1A3A1BC5A57A3A83B58A1BDA1BC5A4BA3A8A1BDC1F595642EBEC9CCC6CAE9A3DB4DA3DD2EB1B1BEA9A3BAA1A1D6D0BBAACAE9BED6A3AC31393735A3BAA1A1323133382EA1BC5A4BA3A9A1BDA1BC5A57A3A9A1BDD4DAD5E2D2BBB7A8C2C9C7E1BCF2BBAFB5C4C0CBB3B1D6D0A3ACB5C1D7EFB1B6D4DFD2E0B5B1B2BBB6CFBCF5C7E1A3ACD2BBD6B1BDB5B5BDC1CBB6FEB1B6A1A3AAA50D0AA1BC4A5032A1BDD3C9D2D4C9CFB7D6CEF6A3ACCED2C3C7BFC9D2D4B6CFD1D4A3ACD4DACBE5CCC6B7A8D6C6D6D0B5B1D3D0D2BBD0A9B1B1B7BDD7E5C8BAB7A8B5C4D2F2D7D3A3ACB5ABBEADB9FDC9CFB0D9C4EAD3EBD6D0D4ADB7A8B5C4C8DABACFA3ACB7A2C9FAC1CBD1CFD6D8B1E4D0CEA3ACA1BC4A5032A1BDCAB9CED2C3C7C4D1D2D4B2ECBEF5CBFCC3C7B5C4D7D9BCA3A3ACD6BBD3D0B5C1D7EFB1B6D4DFD6C6C1F7CFC2C1CBD2BBD0A9BFC9B9A9D7B7CBF7B5C4D3A1BADBA1A3D3C9D5E2D2BBCFDFCBF7A3ACCED2C3C7CDC6B2E2A3BAA1A1B1B1B7BDD7E5C8BAB7A8D6AED3DAB6ABD1C7B7A8CEC4BBAFC8A6B5C4D0CEB3C9A3ACCAD7CFC8D4DAD3DACBFCC3C7B6D4CBE5CCC6B7A8D6C6B5C4D7F7D3C3A3ACB6F8CBE5CCC6B7A8D6C6CEC4C3F7B5C4C4FDB3C9D6B1BDD3B5BCD6C2C1CBD6D0BBAAB7A8CFB5D5E2D2BBB6ABD1C7B7A8CEC4BBAFC8A6D6D0D7EED6D8D2AAB7A8CFB5B5C4B3C9C1A2A1A3AAA50D0AA1BC4A50A1BDB9C5B4FAD6D0B9FAB5C4C0FACAB7A3ACD4DAD2BBB6A8B3CCB6C8C9CFA3ACBFC9BFB4D7F7CAC7D2BBB2BFB1B1B7BDD7E5C8BAD3EBD6D0D4ADC8CBC8BAB7B4B8B4BBA5B6AFB5C4C0FACAB7A1A3D4DAD3C9C7D8B5BDC7E5C1BDC7A7D3E0C4EABCE4A3ACD6C1C9D9D3D0C8FDB4CEB4F3B9E6C4A3B1B1B7BDD7E5C8BAC4CFCFC2D5F7B7FEBBAACFC4B5C4C0CBB3B1A1A3B1B1B7BDD7E5C8BAB7A8CBE6D7C5B4CBD6D6C0CBB3B1B4F3BED9BDF8C8EBD6D0D4ADB5D8C7F8A3ACD3EBB8C3B5D8C7F8BCC8D3D0B5C4B7A8C2C9B4ABCDB3CFE0BBA5C5F6D7B2B2A2D6F0BDA5C8DABBE3A3ACCAB9D6D0BBAACEC4C3F7BEDFD3D0C1CBD2BBD0A9D0C2CCD8D5F7A1A3AAA50D0AA1BC4854A1BDA1BC485332A1BDA1BC485431322E48A1BDA1BC5354485AA1BDA1BC5754485AA1BDA1BC4A5AA1BDB6FEA1A2A1A1B7A8C2C9B4ABB2A5D6AEB6FEA3BAA1A1B9C5B4FAB6ABD1C7D6EECEC4C3F7B6D4B1B1B7BDD7E5C8BAB7A8B5C4CEFCCAD5A1BC5354A1BDA1BC4854A1BDA1BC5754425AA1BDAAA50D0AA1BC485448A1BDA1BC5354485AA1BDA1BC5754485A23A1BDA3A8D2BBA3A9A1A1B3AFCFCAB0EBB5BAB5C4B5C1D7EFB1B6D4DFD6C6A1BC5754425AA1BDA1BC5354A1BDA1BC4854A1BDAAA50D0AB5C1D7EFB1B6D4DFD6C6D2E0CEAABACDB7F2D3E0C8CBB1C8C1DAB6F8BED3B5C4B8DFBEE4C0F6CEFCCAD5A3ACD6AEBAF3D3D6CBE6D7C5B8DFBEE4C0F6B5DBB9FAB5C4C0A9D5C5B4ABB2A5B5BDC1CBB3AFCFCAB0EBB5BAB1B1B2BFA1A3A1B6B1B1CAB7A1A4B8DFC0F6B4ABA1B7A3BAA1B0B8DFBEE4C0F6A3ACC6E4CFC8B3F6B7F2D3E0A1ADA1ADC6E4D0CCB7A8A1ADA1ADB5C1D4F2B3A5CAAEB1B6A3ACC8F4C6B6B2BBC4DCB3A5D5DFBCB0B9ABCBBDD5AEB8BAA3ACBDD4CCFDC6C0C6E4D7D3C5AECEAAC5ABE6BED2D4B3A5D6AEA1A3D3C3D0CCBCC8BEFEA3ACBAB1D3D0B7B8D5DFA1A3A1B1A1BC5A57A3A83B58A1BDA1BC5A4BA3A8A1BDC0EED1D3CAD92EB1B1CAB7A3DB4DA3DD2EB1B1BEA9A3BAA1A1D6D0BBAACAE9BED6A3AC31393734A3BAA1A133333130A1BC43442A32A1BD333331362EA1BC5A4BA3A9A1BDA1BC5A57A3A9A1BDCDACB7F2D3E0D2BBD1F9A3ACB8DFBEE4C0F6B5C4B5C1D7EFB1B6D4DFD6C6D2B2CAC7D2BBD6D6D0CCB7A3A1A3B4D3A1B0C6B6B2BBC4DCB3A5D5DFA1B1D0E8A1B0C6C0C6E4D7D3C5AECEAAC5ABE6BED2D4B3A5D6AEA1B1B5C4C7E9D0CEBFB4A3ACC5E2B3A5CEEFB8F8D3E8CADCBAA6C8CBA3ACBEDFD3D0C5E2B3A5D0D4A3ACD3EBB7F2D3E0A1A2CBE5CCC6B5C4D7F6B7A8D2BBD6C2A1A3AAA50D0AB0D9BCC3C9CFB2E3CDB3D6CEBCAFCDC5CEAAB7F2D3E0D7E5B5C4D2BBD6A7A3ACBAF3C0B4D6F0BDA5C7A8E1E3B5BDCEBBD3DAB3AFCFCAB0EBB5BAD6D0B2BFB5C4BABABDADC1F7D3F2A3ACBDA8C1A2C1CBB0D9BCC3CDF5B9FAA3ACC6E4D4ADD3D0B7A8C2C9D2E0B1BBB4F8C8EBD0C2BED3D6AEB5D8A1A3B9C5B6FBCDF5B6FECAAEBEC5C4EAA3A8323632C4EAA3A9D5FDD4C2C1EEA3BAA1B0B7B2B9D9C8CBCADCB2C6BCB0B5C1D5DFA3ACC8FDB1B6D5F7D4DFA3ACBDFBEFC0D6D5C9EDA1A3A1B1A1BC5A57A3A83B58A1BDA1BC5A4BA3A8A1BDBDF0B8BBE9F82EC8FDB9FACAB7BCC7A3DB4DA3DD2EB3A4B4BAA3BAA1A1BCAAC1D6CEC4CAB7B3F6B0E6C9E7A3AC32303033A3BAA1A1323930A1BC43442A32A1BD3239312EA1BC5A4BA3A9A1BDA1BC5A57A3A9A1BDB1C8D6AEB9C5B7F2D3E0B7A8A3ACB0D9BCC3C8CBB5C4B5C1D7EFB1B6D4DFD6C6D3D0C1CBBADCB4F3B8C4B1E4A1A3AAA50D0ACAD7CFC8A3ACB4CBD6C6B5C4CACAD3C3B7B6CEA7A3ACB2BBD4D9BED6CFDED3DAB5C1D7EFA3ACB9D9D4B1B5C4CADCB2C6D0D0CEAAD2E0CACAD3C3B4CBB7A8A1A3D5E2D3A6BACDB5B1CAB1B9D9C1C5D6C6B5C4B7A2D5B9A1A2CDF5C8A8B5C4C7BFBBAFBCB0CDF5C8A8B6D4B9D9C1C5BCAFCDC5C7BFC1D2B9E6D6C6B5C4D4B8CDFBD3D0B9D8A1A3BECDD4DAC2C9C1EEB0E4B2BCC1BDC4EAC7B0A3ACB0D9BCC3C9E8D6C3C1CBC1F9D7F4C6BDA1A2CEE5C2CAA1A2CAAEB5C2B5C4B9D9C1C5CCE5CFB5A3ACCDACCAB1BBB9D6C6B6A8C1CBB9D9C6B7A1A2B7FEC9ABD6C6B6C8A1A3A1BC5A57A3A83B58A1BDA1BC5A4BA3A8A1BDBDF0B8BBE9F82EC8FDB9FACAB7BCC7A3DB4DA3DD2EB3A4B4BAA3BAA1A1BCAAC1D6CEC4CAB7B3F6B0E6C9E7A3AC32303033A3BAA1A13232312EA1BC5A4BA3A9A1BDA1BC5A57A3A9A1BDC1BDD5DFD6AEBCE4B5B1D3D0D2BBB6A8B5C4B9D8C1AAA1A3D2F2B4CBA3ACCED2C3C7BFB4B5BDA3ACB4CBB7A8D4DACACAD3C3B7B6CEA7C9CFBBB9B8BDD3D0A1B0BDFBEFC0D6D5C9EDA1B1B5C4B8BDBCD3D0CCA1A3AAA50D0AC6E4B4CEA3ACCBF9B7A3B1B6CAFDB4F3CEAABCF5C9D9A3ACB4D3D6AEC7B0B5C4CAAEB6FEB1B6BCF5B5BDC1CBC8FDB1B6A1A3D6AECBF9D2D4BBE1B3F6CFD6B4CBD6D6B1E4BBAFA3ACB5B1D3EBCBFBC3C7B5BDB4EFC1CBC6F8BAF2CEC2C5AFA1A2CDC1B5D8B7CACED6B5C4B0EBB5BAD6D0B2BFA3ACC5A9B2FAC6B7D3D0C1CBB8FCB6E0CAA3D3E0A3ACC8CBC3C7B6D4B2C6B2FAB7B8D7EFD6AEC9E7BBE1CEA3BAA6D0D4B5C4C6C0BCDBCBE6D6AEBDB5B5CDA3ACB6F8CEC4C3F7B3CCB6C8D3D6D3D0C1CBBDCFB4F3B5C4CCE1C9FDD3D0B9D8A1A3D5E2BACDB5C1D7EFB1B6D4DFD6C6D4DACCC6B4FAB7A2C9FAB5C4C7E9D0CEC0E0CBC6A1A3AAA50D0AA1BC485448A1BDA1BC5354485AA1BDA1BC5754485A23A1BDA3A8B6FEA3A9A1A1D6D0C4CFB0EBB5BAB5C4B5C1D7EFB1B6D4DFD6C6A1BC5754425AA1BDA1BC5354A1BDA1BC4854A1BDAAA50D0AD3EBB3AFCFCAB0EBB5BACDA8B9FDB8DFBEE4C0F6BACDB0D9BCC3CEFCCAD5B1B1B7BDD7E5C8BAB7A8B5C4C7E9BFF6B2BBCDACA3ACCEBBD3DAD6D0C4CFB0EBB5BAB5C4D4BDC4CFB6D4D2D4B5C1D7EFB1B6D4DFD6C6CEAAB4FAB1EDB5C4B1B1B7BDD7E5C8BAB7A8D2F2CBD8B5C4CEFCCAD5A3ACD6F7D2AACAC7CDA8B9FDB6D4D6D0B9FAD6C6B6C8CCD8B1F0CAC7CCC6C2C9B5C4D2C6D6B2CAB5CFD6B5C4A1A3B9C5B4FAD4BDC4CFB5C4A1B6C0E8B3AFD0CCC2C9A1B7A3A8D3D6C3FBA1B6B9FAB3AFD0CCC2C9A1B7A3A9B9B2CAAECEE5D5C2373232CCF5A3ACBEDDD1A7D5DFD1D0BEBFA3ACB8C3C2C9BBF9B1BED2D4CCC6C2C9CEAAC4A3B1BED6C6B6A8A3ACCCF5CEC4B6E0D6B1BDD3D2C6D6B2CCC6C2C9BBF2B6D4D6AED7F6C1CBCEA2D0A1D0DEB8C4A1A3A1BC5A57A3A83B58A1BDA1BC5A4BA3A8A1BDC1F5C8CAC9C62EC0E8B3AFD0CCC2C9A1BC4854A1B6426174616E67A1B7A1BD0EFF3F8497360F〗 唐律 继受 [J].法学史研究,2003(27): 334.因此,《黎朝刑律》中亦规定有盗罪倍赃制,其基本原理来自唐律和唐令。
不过,盗罪倍赃制在黎朝的变化较大。从总体上看,《黎朝刑律》规定的倍赃制远较唐律复杂。比如,其“强盗”条规定:“诸凡劫者,首斩,从绞;赃偿之外,田产入官;即得财杀人者,枭;从者,斩;追偿命钱即倍赃一分还主。”(40)杨鸿烈.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51.这一规定有两大特点。其一,对于强盗的财产性处罚,除了征倍赃之外,还要将其田产充公,此为唐律所无,惩罚的力度远远超过唐律。其二,追征“偿命钱”之制为《黎朝刑律》所特有,而此种偿命钱只有金额的1/5归于受害人,而非如唐代那样完全给予受害人。
从总体上看,在黎朝,北方族群法因素变形得十分严重,已越来越难以窥见其本来面貌。其中的一个明显表现便是这一制度在民事领域的渗透,并被运用到了法典的多个条文中。如其《户婚》《田产》之律中有一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俱亡,而宗人非理卖子孙田产者,杖六十,贬二资,追原钱还买主者,仍倍二分还买者。”(41)杨鸿烈.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53.《违制》《杂犯》之律的多个条文亦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其中一条曰:“诸毁伐人家树木、禾稼者,笞五十,贬一资,计其值,倍一分还主。”(42)杨鸿烈.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53.北方族群法中单纯的盗罪倍赃制在越南演变为一种复杂的惩罚性赔偿体系,成了法典的一项基本原则。
(三) 日本列岛的盗罪倍赃制
日本文明深受中国文明之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子文明,法制尤其如此。从公元7世纪开始,日本大规模移植隋唐法制,进入律令制时代,成为中华法系的一员。
在移植隋唐律令之前,未有明确证据显示日本列岛曾存在过盗罪倍赃制。目前,关于古代日本法制的最早记载是《三国志》卷三十《魏书·倭人传》:“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43)陈寿.三国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64: 856.当时的倭国实行严刑峻法,与“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的刑罚手段相比,盗罪倍赃制太过软弱,难有存在的余地。
到了相当于中国南北朝的时期,倭国法律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北史》卷九十四《倭国传》:“俗,杀人、强盗及奸,皆死;盗者计赃酬物,无财者,没身为奴;自余轻重,或流或杖。”(44)李延寿.北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136.虽然严刑峻法的局面依旧,但这一时期倭国的生产力与文明程度显然有了提升,赔偿制有了发展,法律对“盗”有了更细的划分,区分出了强盗与窃盗: 对强盗处以死刑,对窃盗则以赔偿为主。至于《倭国传》中所说的“计赃酬物”是否属于盗罪倍赃,由于史料缺略,已不得而知。从“无财者,没身为奴”的规定看,除赔偿的性质外,还有很重的惩罚色彩,这在东亚各文明早期,是一种常见现象。
大化初年,惩罚性赔偿制终于出现。大化元年(645年)八月,孝德天皇诏国司等曰:“判官以下取他货贿,二倍征之,遂以轻重科罪。”(45)国史大系编修会.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日本书纪(后篇)[M].东京: 吉川弘文馆,1974: 229-230.大化二年三月,又诏东国朝集使等曰:“以去年八月,朕亲诲曰: 莫因官势取公私物,可吃部内之食,可骑部内之马。若违所诲,次官以上降其爵位,主典以下,决其笞杖,入己物者,倍而征之。”(46)国史大系编修会.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日本书纪(后篇)[M].东京: 吉川弘文馆,1974: 229-230.从天皇的屡次重申可知,此种惩罚性赔偿在当时应属初创。
大化初年的惩罚性赔偿制针对的并非其他文明中常见的“盗罪”,而是针对中下级官员(判官以下)的受贿行为及各级官员因势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以官僚群体为主要规制对象。这应和“改新”的时代背景有关。众所周知,皇极天皇四年(645年),中大兄皇子联合贵族中臣镰足发动政变,诛杀了当政的豪族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登基,开始了所谓的“大化改新”。改新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引进中国律令强化皇权。大化元年六月,中大兄皇子和孝德天皇、群臣在大槻树下盟誓曰:“天覆地载,帝道唯一。而末代浇薄,君臣失序……而自今以后,君无二政,臣无贰朝。”(47)国史大系编修会.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日本书纪(后篇)[M].东京: 吉川弘文馆,1974: 217.“君无二政,臣无贰朝”是大化改新的前提。在当时官贵一体的情况下,法律加强对官僚的规制,就是强化皇权对贵族势力的控制。
日本学者井上光贞认为《日本书纪》所记的惩罚性赔偿制与《唐律疏义》规定的盗罪倍赃制有显著类似性,应是大化时期法律受唐律影响所致。(48)井上光贞.隋书倭国伝と古代刑罚[J].季刊日本思想史,1976(1): 20-21.同时,他认为这也是因公权力发达造成赔偿制定额化的结果,显示了中国法律在此领域的深入浸透。(49)井上光贞.隋书倭国伝と古代刑罚[J].季刊日本思想史,1976(1): 29.此说虽有一定理据,但从总体上看,该制与前文所论百济制度最为相似,应是以百济制度为基础,参考唐制的原理而成。质言之,日本大化初年的惩罚性赔偿制是唐制与百济制度在日本融合的产物。
大化以后,随着日本对唐代律令更大规模的移植,唐律的盗罪倍赃制被移植到了日本列岛。现存日本律《名例律》之“彼此俱罪之赃”条关于倍赃的规定与《唐律疏义》的规定大同小异:“凡彼此俱罪之赃,及犯禁之物,则没官。”注云:“所盗之物,倍赃亦没官。”夹注:“假有乙盗甲物,景转盗之,彼此各有倍赃,依法并应还主。甲既取乙倍备,不合更得景赃;乙即元是盗人,不可以赃资盗,故倍赃亦没官。”(50)井上光贞.日本思想大系3律令[M].东京: 岩波书店,1984: 41.
进入中世(967—1467年)以后,在镰仓幕府时期(1185—1333年)武家法的《新增追加》中亦有一些关于盗罪倍赃的规定。如宽喜三年(1231年)四月二十二日“贼盗赃物事”条:“右已依赃物之多少,并定科罪之轻重毕。假令钱百文若二百文以下轻罪者,以一倍令辨偿之,可令安堵其身。”(51)佐藤进一,池内义资.中世法制史料集第1卷镰仓幕府法[M].东京: 岩波书店,1969: 71.宽喜三年五月十三日“诸国新补地头沙汰事”条:“假令于钱百文以下盗犯者,以一倍令辨偿,可令安堵其身。至于三百文以上之重科者,虽搦取其身,不可烦亲类妻子所从,如元可令居住也。”(52)佐藤进一,池内义资.中世法制史料集第1卷镰仓幕府法[M].东京: 岩波书店,1969: 75.镰仓幕府法的盗罪倍赃制,在适用范围缩减的同时,仍保留了十分明显的赔偿性与个人指向色彩,维持了这一制度的基本特性。
三、 文明对照: 盗罪倍赃制与“西亚—地中海法文化圈”
在近代之前,地球上各文明虽相互阻隔,但亦有联系孔道。特别是,作为同一物种,人类具有大致相通的情感与思维,在类似的地理、气候、生产生活条件及实际需要的推动下,会“不约而同”地创制出某些“类似”的制度,不同文明间的对照乃至比较是可能的。(53)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类似的工作,如张文晶著有《罗马法之神圣物与唐律之神御物比较研究》一文,指出:“唐律之神御物与罗马法之神圣物,便是古代中国与罗马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类似的物的分类概念。”(张文晶.罗马法之神圣物与唐律之神御物比较研究[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2): 111.)
(一) 西亚—地中海诸文明的盗罪倍赃制
包括“盗罪倍赃制”在内的惩罚性赔偿,是“西亚—地中海”诸文明中的一项共有制度。正是以这一制度为代表的一些共同性制度,将这些法文明连接成一个松散的法律共同体,我们不妨称之为“西亚—地中海法文化圈”。
据现有史料,在西亚—地中海区域,最早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出自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汉穆拉比法典》中的多倍赔偿规定基本上是针对两类行为,一类即为盗窃,一类即为类似于委托的关系中当事人一方的抵赖行为。”(54)余艺.惩罚性赔偿研究[D].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2008: 1.由于论题的关系,本文仅讨论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的演进与第一种相似,限于篇幅,只能割爱。
关于对盗窃行为的多倍赔偿处罚,我们可以该法典第八条为例加以说明。该条规定:“自由民窃取牛,或羊,或驴,或猪,或船舶,倘此为神之所有物或宫廷之所有的,则彼应科以三十倍之罚金,倘此为穆什钦努所有,则应科以十倍之罚金;倘窃贼无物以为偿,则应处死。”(55)《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汉穆拉比法典[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14.在当时的巴比伦,全体居民分为自由民和奴隶两大阶层,自由民又按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分为“阿维鲁”和“穆什饮努”两个阶层,前者享有较充分的法定权利,后者的法律地位则较为低下。不难看出,由这类法条创立之制度的实质就是“盗罪倍赃”,与前文所论夫余人的法律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的只是因古巴比伦特有的社会分层结构而使此盗罪倍赃制更加复杂而已。
具体而言,《汉穆拉比法典》的盗罪倍赃制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性质上,与古夫余人的同类法律一样,倍赃乃是一种刑罚,与后世所理解的“罚金”不同。其次,此刑罚与古夫余人法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倍数的不固定: 按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有权的性质及物品所有人之社会等级等因素,可分为三倍、五倍、六倍、十倍,直到三十倍等多个等级,具有典型的身份制刑罚的特点,是国家本位、刑罚本位、身份本位的三位一体。
古巴比伦的法律对周边诸文明及后世法律产生了影响,乃“西亚—地中海法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古巴比伦后期,赫梯崛起,于公元前1595年夺取巴比伦城,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一个帝国。赫梯于公元前1600年或公元前1500年前后编纂了法典,该法典既有受古巴比伦法律影响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以盗罪倍赃制而论,《赫梯法典》第五十七条规定:“假如任何人盗窃良种的牛……则先前要交付三十头牛,而现在他应交付十五头牛: 他应交付五头二岁的牛,五头一岁的牛,五头不到一岁的牛,同时用自己的房屋担保。”(56)《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赫梯法典[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36.与《汉穆拉比法典》一样,《赫梯法典》的处罚倍数亦在5~30倍之间,是一种刑罚,故在交付罚款之后,当事人不需再承受其他刑罚。
当然,《赫梯法典》也有和《汉穆拉比法典》不同的一面。首先,《赫梯法典》对于盗窃牲畜规定的倍赃,是一组年龄不同的牲畜的组合。其次,惩罚力度比《汉穆拉比法典》有所减轻,这是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变异,但从“担保”等用语的使用情况看,《赫梯法典》盗罪倍赃制中的所罚之物交于被害人,而非国家,维持了《汉穆拉比法典》以来该制的基本特征。
《汉穆拉比法典》《赫梯法典》这些西亚早期文明中较为发达的法制,当对之后邻近区域的古罗马法制产生了影响。古罗马的代表性法典为《十二铜表法》,该法典于公元前451年前后完成。盗罪倍赃制也见于法典之中,如其第六表《获得物、占有权法》之第十八条规定:“对窃贼处以缴纳(窃物)价值之二倍的罚款。”(57)《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十二铜表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41.经过千余年的演进,盗罪倍赃制已由古巴比伦时代的主刑变成附加刑,所罚的倍数亦大为减少,基本固定为两倍。此种演变与从古夫余到唐代之盗罪倍赃制的演变轨迹相似,是生产力发展、人类文明程度提升的表征。和《汉穆拉比法典》相比,《十二铜表法》盗罪倍赃制的个人本位色彩更强,出于国家本位的惩罚目的退居其次。这也与东亚法文化圈中由北方族群法到唐律、百济法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点类似。
古罗马的法律传统一直延续到东罗马时期。在东罗马帝国(395—1453年)的《法学阶梯》中,有不少关于盗罪倍赃的规定,如该书第四卷第一题《产生于私犯的债》第五条:“不论是对奴隶还是对自由人,现行盗窃的罚金是盗窃物价值的四倍,非现行盗窃的罚金是两倍。”(58)优士丁尼.法学阶梯[M].徐国栋,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423.类似条款还有不少,所用词语虽均为“罚金”,但所罚金额归于受害人,在性质上主要是赔偿,刑罚的色彩转淡。
另外,《圣经·出埃及记》第22章1~4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出埃及记》第22章7~9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可见,与古巴比伦邻近的古犹太的法律同样有盗罪倍赃制。由此我们进一步确信,该制为西亚—地中海诸文明的一个共有法律传统。当然,犹太法中的盗罪倍赃制亦有自身的特点,倍赃在2~5倍之间,数额因被盗物的不同而异,处罚的目的既是补偿,又是刑罚,乃刑罚与赔偿的结合。
(二) 共同制度与法文化圈
由前两节的分析可知,北方族群法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文明传播,使古代东亚诸文明的法律有了更多相似性,东亚法文化圈因此而逐渐形成。在此东亚法文化圈之内,由于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同源性的制度又会发生变化: 盗罪倍赃制在气候寒冷、事农条件较差、财富不易积累、文明发育程度较低的东北地区及北方草原地带,赔偿的倍数高;当这一制度传入气候温暖、事农条件好、财富积累相对容易、文明发育程度较高的中原地区、朝鲜半岛中南部及日本、越南,便逐渐发生各种变形,总趋势是趋于轻简。这种既有同一性,又在同一性中逐渐发展出多元性的法律共同体就构成了一个法文化圈。
而本节的分析则显示,由此路径而形成的法文化圈,在世界范围内绝非孤例,“西亚—地中海法文化圈”的形成正好可以成为东亚法文化圈形成的一种对照性证明。我们之所以要做这种对照性研究,除了此两大法文化圈所处的时代相近,在古代世界文明中所占据的地位基本相当,文明的形态与内涵存在重大差异而足资对照之外,更为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是,作为我们分析断面的“盗罪倍赃”制在现代法学中被认为属于“惩罚性赔偿”的一种形态,而“西亚—地中海”文明较早发育出了这一制度,甚至被认为是这一制度的直接源头,我们的这种对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以正视听的作用。
通过本节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古巴比伦到东罗马帝国,它们的法律中有一些延续不绝的共同因子,这些因子由文明之间的影响与传递关系而形成。由于这些共同因子,一些联系紧密的共同体构成了一个法系,如美索不达米亚法系、希伯来法系、罗马法系,(59)这里使用的是威格摩尔的十六法系说,见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M].何勤华,李秀清,郭光东,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而它们彼此之间又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大、联系更为松散的法律共同体——“西亚—地中海法文化圈”。一些如盗罪倍赃之类的共同性制度便是这一法文化圈得以形成的纽带。这一法律共同体是一种共时性与历时性兼具的存在,故作为其纽带的共同性制度在其中亦呈现出或隐或显的演化脉络,在同一性中发展出了多元性。
总之,由某些共同制度形成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并存的历史联系,使某个更大范围内的各种法律文明组成一个松散的法文化圈,并非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古代东亚法文化圈与西亚—地中海法文化圈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存在罢了。大于法系或超越了法系之文化圈的存在,反映了文明波状扩展的历史事实。
四、 北方族群法、中华法系与东亚法文化圈
上文以盗罪倍赃制在东亚诸文明中的传播与演进为切面,分析并揭示了北方族群法与东亚法文化圈的内在联系,使我们进一步正视我们古老文明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渊源的多元性,及由此不断走向融合的历史事实与趋势。
从总体上看,盗罪倍赃制是在人类文明早期物质贫乏阶段流行的一种制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古代东亚,华夏族群聚居的中原地区较早进入了文明状态,故此类制度自西周以后就基本从华夏核心区消失。然而,在古代东亚这一多元文化环境中,它仍流行于处于后进状态的各族群,特别是物质财富创造力贫乏的北方各游牧、渔猎群体中,随着这些群体的迁徙、征服活动而散布四方,使整个内亚地区的法律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相似性与同源性,构成所谓“内亚传统”的一部分。(60)内亚传统的延续性也表现在法律上,比如辽代有“射鬼箭”的刑罚,即将死囚绑在柱子上,众军士向着军行的方向将其乱箭射死,据学者研究,可能是匈奴以来的传统;而辽代置于边远部族、投诸境外和令出使绝域的三等流刑,也可能是久已行之于北族的习惯法。《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书》云:“乌丸者,东胡也。……其约法……其亡叛为大人所捕者,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无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乌孙之东北,以穷困之。”(陈寿.三国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63: 832-833.)
鲜卑等北方族群对华夏地区的迁徙与征服,又使包括盗罪倍赃制在内的流行于北方各族群的法律向中原地区渗透,最终成为隋唐等华夏王朝法典的一部分。之后,这些“后进”因子又借助华夏高度发达的文明继续向四周的农业地区传播,使东亚各农业文明居然与在自然环境、文化状态与文明程度上迥异的游牧、渔猎文明的法律制度具有了一些共性,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广但内在联系松散的文化圈。(61)游牧族群的其他制度与法律也会以类似的方式散布与传播,只是由于史料不备,我们已无法得知其详情而已。这个文化圈就是本文所说的“东亚法文化圈”。(62)“文化圈”的概念是由德国传播论的代表人物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提出的,他认为重建各种文化圈是文化历史学家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关于此,参见赵敦华.古史研究中的“帕斯卡猜想”[M]//罗秉祥,赵敦华.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57-158.)如果说法系主要由系统性的法律移植所形成,一般由具有近似文明环境(包括生产与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念等)的群体与国家之法律体系组成的话,法文化圈则由零散性或非系统性的法律移植所形成,内部各群体与国家的法律在总体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即是说,一个法文化圈之内的不同法律体系并不一定能构成一个法系。
在制度传播的过程中,盗罪倍赃制不断发生变化。如前文所言,这一制度主要在文明后进群体中流行,是物质贫乏条件下的产物。一个文明愈是落后,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就越低,因而越将物质看得重要,对侵犯财产行为的处罚也越重。我们看到,在北方各族群中,盗罪倍赃制的基本形态为罚十倍,且为实刑;可当它随着“野蛮”的征服者来到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后,便逐渐降至二倍,且从主刑变为附加刑。其间变迁过程复杂,笔者将另文分析。
总之,盗罪倍赃制是特定自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本有其特定的适用空间与范围,然而,在各北方族群特别是游牧族群对事农群体的反复渗透、征服过程中,它及北方族群其他的一些制度作为征服者的法律被“带入”各个不同的地域与文化环境,成为在这些地域与环境中生活的群体的法律。由于传统的形成,即使这些文明程度更高的群体后来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未能将征服者留下的法律因子完全清除,而是将它们中的一部分收入自己的法典。
东亚(63)关于“东亚”的概念及其在古代史研究中的意义问题,可参考甘怀真.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M].台北: 台大出版中心,2007: 2-4.与东亚法文化圈的概念主要由日本学者所提倡,中国学者往往茫然地接受并使用。日本学者所说的东亚法文化圈,其实与所谓“律令制国家群”(64)“律令制国家群”是日本学者井上光贞提出的一个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建立在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基础之上的作为体系化之普遍法存在的律令法,为周边的农耕、游牧诸民族继受,从而形成了律令制国家群。”荒松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第6卷[M].东京: 岩波书店,1971: 41.“远东法”(65)关于“远东法”问题的讨论,可参考大木雅夫.东西方的法观念比较[M].华夏,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一样,是“中华法系”的替代物,故高明士称此文化圈为“中国法文化圈”。(66)高明士.也谈中华法系的特质[C]//张中秋.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4.日本学者不肯使用“中华”这一直指法系核心特征的词汇,更不肯将“中华”与“法系”相联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使用的是“中国法”或“中国法系”的说法。(67)“中国法系”之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亦为中国学人所使用。然而,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法系”便逐渐为“中华法系”所取代。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可参考赖骏楠.建构中华法系: 学说、民族主义与话语实践(1900—1949)[J].北大法律评论,2008(2): 438-446.这种做法有其深意所在——他们所说的“中国”实际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帝国主义为肢解中国而编造的“中国本部”,即长城之内的十八行省,而“屏满蒙回藏于中国之外”。(68)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答费孝通先生[M]//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 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73-83.质言之,在以“民族”话语肢解中国的语境下,日本学者所说的“中国法”或“中国法系”实际上仅指中原文明(华夏文明)。如同他们不承认“中华民族”而将满、蒙、回、藏等族群区隔于中华民族的范围之外一样,他们将古代中国法律文明中除中原文明以外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北方族群法在内)排除出中华文明,建构起一种“北方民族法”与“中国法”二元对立的学术话语与模式。(69)如岛田正郎所云:“和以实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中国法相对,在北方族群法中,赔偿制是一项基本原则,对于杀人、伤害、奸淫、盗窃等犯罪,均可以家畜赔偿……在女真、蒙古等北方族群侵入并征服中国后,两种固有法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在因执拗地坚持自身之固有法而发生对立的过程中,中国法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赔偿制的影响;而在北方族群法中间,也出现了不能以财物抵罪的不可赎罪,特别是,在中国法的影响下,实刑主义的范围扩大了。”(岛田正郎.东洋法史[M].东京: 明好社,1970: 90.)
与之相应,“中华法系”这一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也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冲击下在中华大地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有关。(70)具体论述,参见郭世佑,李在全.“中华法系”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08(6): 178-186.具体而言,“中华法系”可被看作“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在法律文明史上的投影,是论证并建构中华民族的一环。如学者指出的那样,从20世纪初开始,我国的中华法系研究大体走过了一条“中国法系—中华法系”的路径。(71)具体论述,可参看赖骏楠.建构中华法系: 学说、民族主义与话语实践(1900—1949)[J].北大法律评论,2008(2): 417-453.
“中华民族”与“中华法系”虽为现代学术话语,但我们又不能完全将之归结为“想象”与“建构”,中华法系在“法系”这一概念出现之前早已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在“中华法系”与“中国法系”这两个用语冲突与替代过程的背后,是如何认识北方族群法与中原法,再进一步,是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的问题。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认知与使用,涉及对现代“中国”是持建构立场还是持解构态度的重大问题。
如前文所论,北方族群法与中原法的关系相当复杂,有长久的融合历史,而日本学者却过于强调它们之间的“冲突”。他们将“中国”限于中原,将居住在中原以外的各族群称为“民族”,并将这些族群的本俗法与中原法的关系设定为对立、冲突,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受此种“民族”观念与话语影响而进行的研究,难免走偏。中华法系在近现代的所谓被“建构”,只不过是获得了一套符合现代学术话语的表述方式而已,这种表述形态的获得不能否定其历史存在的事实。
如果说中华法系是由母法与子法紧密联系而形成的一个整体,那么,相对而言,东亚法文化圈则是由一些历史性的纽带特别是一些共同的制度与文化因子以松散的方式联系起来,在范围上较中华法系更广。北方族群法便是东亚法文化圈得以形成的纽带之一。从上文所论盗罪倍赃制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看,这种纽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北方族群法对周边文明的直接影响;二是北方族群法不断影响中原文明,两者融合使中华文明面目一新,此种文明再向周边辐射而产生影响,这是一种间接的影响。通过此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个东至日本列岛,西至中亚,北到草原大漠,南至中南半岛的法文化圈便出现了。
东亚法文化圈之形成依靠的是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力量,其中,政治力的作用不可小视。诸多强大的北方族群政权对周边地区的征服是东亚法文化圈得以形成的重要动力。鲜卑人以其征服活动将北方族群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深度整合与融汇,这在古代东亚法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文明形成后,又通过文化的力量以和平的方式向周边传播与扩散,形成中华法系,使东亚法文化圈有了真正的基础与核心。
总之,与法系的形成不同,促成法文化圈生成的因子并不一定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成分,一些相对“后进”的成分,亦可被比之更发达的文明吸收,发展成一种普遍性制度,成为制度体系中的黏着剂,使法文化圈得以产生。北方族群法之于古代东亚法文化圈的作用就是如此。当然,包括盗罪倍赃制在内之“后进”的北方族群法因子,在与其他文明碰撞的过程中,不断变形——愈是深入气候温暖、事农条件较好的地区(通常也意味着当地的文明更“先进”),变形得就愈厉害——这样一来,东亚法文化圈内诸文明法制的差异开始增大,在同质化过程中又不断发生分化,从而呈现出另一层次的多元性。
古代东亚法文化圈形成与演化的历史为我们考查当今法律文明的走势,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对我们该如何合理地移植外国法制,更好地为当下服务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应当从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吸取智慧,获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