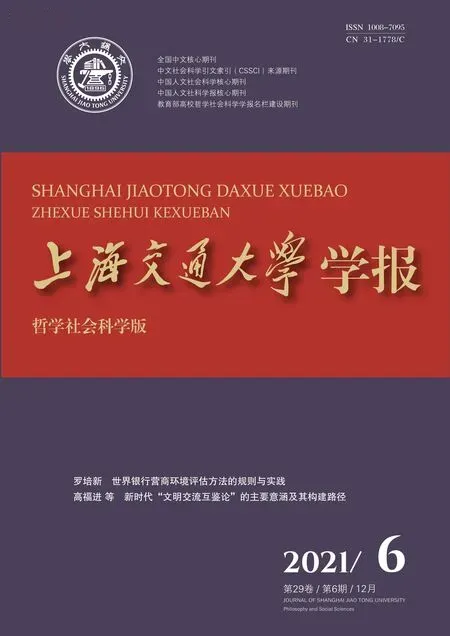风险社会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张劲松
(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 361021)
当代西方社会学家贝克和吉登斯等人把风险视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并指出风险社会是取代西方工业社会的一个崭新历史阶段,“现代性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得了解放,并缔造了一种新形态,也就是这里所称的(工业化的)‘风险社会’”。(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8: 前言2.风险的全球性和普遍性关乎人类的集体命运,其跨越国界且危及所有物种的特征促使人们形成共同体意识。由此,风险社会理论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同时风险社会也是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因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引领全球行动的意识形式和观念形态,也体现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而采取的人类共同行动。它反映了人类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和客观要求,是应对世界风险社会、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型全球发展道路。从世界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其实践,能够准确地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内生动力和历史使命,能够在对照分析中清晰地把握其所蕴含的中国制度优势及其世界意义。
一、 世界风险社会的内涵与表现
“风险”(risk)一词最初是指航海活动中由于悬崖、暗礁等因素而导致的危险,后被用来指所有冒险活动的不确定性后果。风险社会是指自然因素和人类实践导致的风险成为社会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它通过强调不确定性、未来预期等特征使之与工业社会区分开来。现代社会既与风险相伴而行,又与全球化同步成长。贝克指出:“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2)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4.在规模和范围上,风险从局部、区域性现象上升为整体、全球性现象;在影响深度上,从危及某一社会领域升级为影响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在风险的应对和治理上,亟待超越个别机构和单一民族国家而形成相互协作、互利共赢的全球风险治理体系。无论是产生源头、传播机制还是治理方式都充分表明风险已经具有普遍的全球性时空影响,它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整体特征和共同关切,“风险越来越成为现实并构成威胁,超越了社会的区隔和国家的边界”,“全球风险处境的客观共同体形成了”。(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8: 43.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生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科技、生态和经济三个领域,其中科技风险是直接推动力,生态风险是主要作用场域,经济风险则是直观的社会表象并揭示其深层的制度根源。
(一) 世界性科技风险
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然而科技带来的风险也对人类安全和生存形成巨大的威胁。吉登斯依照风险的不同根源区分了自然风险和人造风险,指出现代社会的内在风险是“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自然风险是存在于现代世界的外部风险,既包括自然界产生的洪水、沙尘暴等灾害现象,也包括军事对抗、暴力斗争等人类冲突引发的威胁。而现代社会的风险更主要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它是资本贪婪本性驱动下科技创新过度工业化的恶果,“在某个时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最近),我们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4)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3.
在全球一体化快速发展的20世纪,科技风险从核技术、生化技术、网络系统扩展到基因技术、航天探索等领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总体格局的重要威慑力量,核武器的总数量足以毁灭地球数次,已暴露的核辐射可能导致人体衰竭并影响数代人的健康。此外,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技术、人类胚胎的基因剪辑技术、各种新的变异病毒等极大地威胁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健康生存和持续繁衍。这些技术之所以产生风险是因为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潜在的、不可知的危险以无法明显感知的形式存在,迫使人们严重依赖于科学知识对客观环境和事物属性的界定。复杂的工业流程、机器体系或技术环节日益形成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脱离人类控制的客体世界,精密的机械化和高度智能化使得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科技活动的风险已经上升为一种高后果风险——一种会对极大量人口造成普遍性后果的风险,层出不穷的危机(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使得人的生活处于极端的不确定状况”。(5)刘大椿.在真与善之间: 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9.
交通、信息等领域的科技进步为开启全球化时代提供技术基础。然而,科学技术加剧风险的不可预见性、偶然性和破坏性,扩大了风险的影响范围并加快其传播速度。在私有制社会里,资本逻辑裹挟着科技创新,不断地提升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能力,其必然导致环境的日益恶化、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潜在风险的不断增多。科学技术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内在动因和重要中介,它既表现为基因、核技术、克隆技术等的越界使用而产生的人类自身的生存风险,同时又在资本增殖本性的驱动下,外现为自然灾难、资源枯竭等破坏客观环境的自然生态风险。
(二) 世界性生态风险
科技是风险产生的重要源头和内在动力之一,生态危机则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典型作用场,是最容易、最频繁发生的风险现象。生态风险既是科技风险的直接表达,又是资本扩张的必然后果。首先,生态风险是科技理性过度的张扬引发的负面效应。高度发展的技术理性借助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体系,使人们大肆地开发自然以服务于人类的需要,从而导致自然界以生态灾难的方式威胁人类的生存。马克思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2: 4.
其次,个体主义是生态风险产生的行为动因之一。人类中心主义将个体利益、民族利益凌驾于人类整体利益之上的自私行为,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21世纪以来,从SARS冠状病毒、MERS病毒到新型冠状病毒,攻击人与其他生物的各种病毒将所有物种置于危险的境地。这再次警告人类不能忘记自身乃万千生物中的一分子,必须建构共同体以应对世界性生态风险。
最后,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无限增长的欲求与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是生态风险形成的制度根源。在资本扩张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无止境地开发利用,必然导致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并危及人类的整体生存,从而引发现代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生态风险。
(三) 世界性经济风险
世界性经济风险既是科技风险、生态风险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直观体现,更集中体现为资本逻辑带来的阶级对抗、社会两极分化、金融体系不稳定等风险。资本天然就具有一种通过不断的扩张运动来实现剩余价值的内在必然性,马克思把资本逻辑引发的危机称为一种“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406.从制度层面看,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西方风险社会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并随着全球化步伐而使之演变为世界性经济风险。
世界性经济风险既表现为无限的资本扩张与有限的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生态风险,也表现为金融制度与工业生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脱节与矛盾。为了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繁衍和扩张,资本家通过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基金等金融衍生品将资产证券化。“在银行的操作领域,经济风险在二阶观察的层次上是自我指涉的”,这一风险的特性是“不可预见的效果积累、超过阈值、意外所产生的不可逆并导致不可控的灾难。”(8)尼克拉斯·卢曼.风险社会学[M].孙一洲,译,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 265,268.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体系逐渐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一旦资本运动的某一链条断裂或潜在的制度风险爆发,将造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系的整体崩溃。此外,世界性经济风险还表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和矛盾冲突。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时代被放大为大型跨国企业的高度组织性与全球资本无序流动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激化和扩散,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阶级对抗,“世界上最贫穷者将受到最严酷的打击。他们将极少有能力适应环境的变化”,“源于资本的内讧。这种内讧将‘工人的命运’转变为在更远的和基本范畴的‘命运’”。(9)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3,85.
二、 源于世界风险社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彼此关联、深度融为一体,科技、生态和经济等领域的突发风险给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贝克认为中世纪的人们处于“地位命运”之中,而当代人们面临“作为命运的风险处境”,“出现在这里的则是发达文明的风险命运。出生在发达文明的人,无论付出何种努力也难以从中逃脱”。(10)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8: 34-35.世界性的普遍风险必然孕育出人类命运与共的意识,滕尼斯把这种意识称为“共同领会”,“相互一致的、结合到一起的信念是一个共同体特有的意志”,“它是一种特殊的社群力,也是一种相通的感受,由此,它就把一个整体里的各个成员团结到了一处”。(11)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张巍卓,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 95-96.这种共同体意识既包含着消除焦虑和恐慌的团结心理,形成“民胞物与”的“类存在”思维,又体现为凝聚全球共识、促进协同行动的世界主义观念。
(一) 世界性风险社会外在地促成人类的团结意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心理学底座
人们在传统社会里依靠既有的经验和惯例获得确定性。在当代风险社会,资本增殖的本性、科技理性的膨胀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人类置于相同的风险境地之中。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心理状态普遍地体现为现代性这头猛兽引起的“本体性安全和生存性焦虑”。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无根性导致人们的焦虑和恐慌,个体犹如失去根基的浮萍,焦虑感、惶恐不安、“信任危机”等成为现代社会个体的生存常态和普遍心理特征。
从心理学角度看,世界性风险越是强烈地威胁着人类的整体生存,越是能激发人类团结一致、共同行动的心理倾向。滕尼斯认为“一个人受到外在威胁的时候,他就越会想起群体”,这种威胁“能使群体团结一致、共同战斗、一同发挥作用”。(12)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M].张巍卓,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 80.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个体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利益最大化并累积形成全社会的共同福祉。而在风险社会里,以往由利益需求而结成的社会联盟,现在转变成出于焦虑而结成的共同体。源于心理焦虑而形成的政治团结能够激发一个群体的内在凝聚力,它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驱动力。包括家庭、村庄、部落、国家在内的一切群体都要求其成员保持团结以维护共同体的存在,“团结内含着保护和安全的意味……在这一基本意义上,团结乃是最根本的社会要求,没有团结,就不会存在任何社会”。(13)雅克·布道.建构世界共同体: 全球化与共同善[M].万俊人,姜玲,译,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89.
共同风险取代单一的经济或政治利益而成为世界普遍交往的纽带,命运与共是全人类的广泛共识。世界性风险社会客观上将人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建构命运共同体夯实了心理土壤和情感基础。“命运还必然迫使我们在无意识的层面付出代价,因为它的核心意义是对焦虑的压抑。无意识中关于人类整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似乎充满了作为基本信任的对立面的恐惧感。”(1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3: 117.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普遍安全观试图建构一种超越国家疆界的多元安全体系,包括应对科技风险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网络安全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等。这些命运共同体力图通过增强集体命运感、强化共同体意识,促成消除普遍焦虑和内在恐惧的共同行动,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
(二) 世界性风险重新唤醒了人类的“类存在”,内在地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人类学意蕴
“类存在”首先要超越“物种思维”,它不仅体现为人类自身的物种属性,同时表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命运相连。马克思指出人具有“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作为自然界的高等动物,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把本质力量对象化,把自然变成“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界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共同体关系。诚如贝克所言:“文明发展对生命的威胁激发了有机生命体的共同经验,从而把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需求连接在了一起……由大地、植物、动物和人类构成的共同体变得清晰可见,这是一种‘生命体的团结’。”(1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8: 83-84.这种生命体的团结不仅是自然界的本性使然,更是应对世界风险社会的必然要求。面对可能使地球上所有生物毁于一旦的世界性风险,所有生命不分高低贵贱、位序差异,而形成一个命运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所有的自然界万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生活在一个硕大无垠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ary community)中,他们共同分享着彼此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彼此承受着共同的命运”。(16)王宁.新冠病毒肺炎突发与治理的人文反思[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9(5): 112-120.
“类存在”促使所有不同人群、不同民族国家都跨越隔阂而形成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学层面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根源。风险要求人们超越“人种思维”,唤醒所有人种和民族之间存续攸关、生死相连的“类存在”属性,“普遍的危险有一种相同的效果,它会削弱阶级、国家、人类和自然的其他物之间,文化的创造者和直觉动物间……人类和没有灵魂的事物间的被精心设立的边界”。(17)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87.世界性风险促使各民族国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建构一种跨越种族、区域而“同呼吸、共命运”的世界共同体。
(三) 世界性风险促成世界主义观念的孕育成型,从而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行动基础
为了应对危及人类生存的世界性风险,贝克模仿《共产党宣言》的语气呼吁“世界公民们,联合起来!” 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主义宣扬整体的世界公民观念,提倡世界主义的团结和人性,这成为世界主义观念的最初源头。康德以世界永久和平为目标,设计了包含共和制、联盟制和公民权利等内容的世界主义制度体系。在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交错融合中,在空间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性风险促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启蒙,贝克称之为“世界主义时刻”。“风险社会通过它所引发的威胁动力,瓦解了民族国家、军事联盟和经济集团的边界。当阶级社会还在以民族国家的方式来组织的时候,风险社会已经催生出客观的‘危险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最终只能在世界社会的框架中加以理解。”(18)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8: 45.贝克倡导的世界主义试图突破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一系列传统禁锢,形成一种独特的、可变的、多元的边界结构。赫尔德从制度设计上提出一种“世界主义共同体”,它建立在自主性的民族国家之上、体现了跨国界的多元权力和制度框架,由此“一种从城市、国家到区域、全球网络的民主社团的政治秩序将会出现……一方面,重塑传统的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在民主行为的跨国结构之内,新共同体的可能性得以建立”。(19)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 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M].胡伟,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48-249.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性的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兴起,这充分表明世界主义观念在实践中不断地孕育、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对世界主义观念的超越和扬弃,它们都具有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尊崇世界的整体利益和共同价值。然而,与基于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之上的世界主义观念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共同体优先于个体,尊重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在内在理念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视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共同价值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制度建构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建立一套世界主义的跨国制度和组织体系,“一个世界社会意味着一种世界性的管理、一套完备的具有意图和范围的法律法规之实体机构、一套解决各个不同领域的冲突并强制执行裁决决议的程序,以及对于批评性道德规范的共享性理解”。(20)雅克·布道.建构世界共同体: 全球化与共同善[M].万俊人,姜玲,译.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4.这一制度设想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疆界和主权的消失,而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国际协作和共同治理。
三、 应对世界风险社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才真正到来。英国政治学者巴里·布赞认为:“直到19世纪中期,一个较为完善的国际军事—政治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而全球性的国家间社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出现。”(21)巴里·布赞.全球化与认同: 世界社会是否可能[J].王江丽,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0(5): 5-14.自此,个体的、单一的民族国家的风险迅速地超出了特定的地理界限和国家疆域,成为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普遍性危机,共同应对风险的全球行动也逐步兴起并不断制度化。世界风险社会不但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产生,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建构这一共同体的议事规则和制度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是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协作和共同行动的延续和拓展,它使全球行动有了新的内涵、目标和行动主体。
(一) 科技风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核技术的和平利用开启了人类应对科技风险的共同行动。为了应对核武器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参与研发核技术的科学家们在1945年成立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生产核材料的主要国家在1957年成立国际原子能机构,之后又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些协调机构和通行规则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应对科技风险的初步探索。危及全球“类生存”的核安全风险推动了共同体实践,明确了人类整体利益高于民族国家个体利益的原则,“人类共同体的主权优先于其他任何组织、部落和民族国家的主权”。(22)入江昭.全球共同体: 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M].刘青,颜子龙,李静阁,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6.科技风险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滥用现代生物技术而导致危及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重大隐患。生物技术的越界与滥用、病毒样本的管理不当、基因剪辑技术的失控等已经成为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制止生物武器的全球扩散,1975年生效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截至2018年10月已有182个缔约国。这一公约为防止生物武器威胁和扩散提供了法律武器,初步探索应对科技风险的人类生物安全共同体。
21世纪以来,由科技风险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日趋严峻,世界亟待建构一个安危与共、协同合作、成果共享的科技共同体。在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将全球化视为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采取关闭边境、与邻隔离、限制流通等保护主义措施,从而导致疫情防控的全球合作迟迟未见成效。与之相反,在应对风险的对象和目标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化在核技术、重大传染性疾病、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协同合作;在应对风险的过程和路径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团结”“合作”“协调”等行为准则,强调各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创新交流合作,建立研发共同体来进行技术攻关;在科研成果的运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共享,强调科技创新成果不应该只成为服务资本增殖的工具,不能只服务于个别国家和少数人,“我们要提倡国际创新合作,超越疆域局限和人为藩篱,集全球之智,克共性难题,让创新成果得以广泛应用,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474.中国政府以身垂范,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并投入使用后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让技术创新成果惠及全人类。
(二) 生态风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1962年问世的《寂静的春天》警示人们全球性生态风险的日益临近。此后,一系列关注生态环境的全球行动兴起,如“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学运动、提出“盖亚(地球母亲)假设”的地球保护运动等。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首先使用“人类环境”一词,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类和自然界命运与共。1973年联合国设置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这是从组织制度上防范世界性生态风险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为了应对生态风险,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为主导的人类行动框架,这些全球行动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步探索和行动基础。
人与自然、人与人共生共存的生态共同体是人类应对生态风险的必然选择。生态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之一,它将生态文明上升为全人类共同的行动指南和价值指向。生态共同体首先要突显所有物种的“类存在”,筑牢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360,435.首先,它要求世界各国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共同保护绿水青山和万物生灵。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主体平等、权利义务对等的全球生态正义。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要求实现全球生态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少数发达国家在生态问题上坚持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退出环境治理的全球合作机制并拒绝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不确定性因素并阻碍了生态治理的全球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在自然资源分配和生态责任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尊重不同国家在历史责任、发展阶段、能力建设、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不搞一刀切,每个国家承担与自身国情和能力相匹配的生态义务,从而探索最适合共同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和全球治理模式。
(三) 经济风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均衡发展,促使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共享技术、资源和财富,联合国分别设立了经济发展特别基金、工业发展组织等,旨在改变“冷战”思维,促进各国经济协作和共享发展。此后,各类以发展为目标的国际机构纷纷涌现,“它们构成了一个致力于发展的个人和团体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它们相互密切地沟通交往。在它们看来,发展正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工程,需要跨国协作”。(25)入江昭.全球共同体: 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M].刘青,颜子龙,李静阁,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12.20世纪出现了以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性经济共同体,以共同体的方式促进本区域经济协作发展并共同抵御经济风险。21世纪以来,应对全球性经济结构失衡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在完成这一使命上,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截至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累计减贫超过7亿人,成为世界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2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52.中国的成就推动世界减贫事业的发展,有效地减少了由贫困引发的社会动荡和生存风险,推动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
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应对经济系统性风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另一重要任务。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少数发达国家重新强调国家利益的优先地位,不断挑衅通行的国际贸易准则,实施单边的贸易保护政策。这种逆全球化、单边主义行径破坏了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成为世界性经济风险的潜在源头之一。要规避世界性经济风险,实现全球经济共同发展,必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要不断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在专门领域内的协调和治理职能。近二十多年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成为克服全球性经济危机、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并在2016年杭州峰会上首次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此外,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金砖五国伙伴关系,在加强全球治理、共同应对挑战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解决南北发展失衡、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2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492.这些为应对全球性风险而形成的国际组织和治理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要的实践机制和创新探索。
四、 结 语
全球性风险引发的本体性安全和生存性焦虑推动着人类团结意识的产生,凸显了人与万物之间的“类存在”,促成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主义行动,它们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撑。世界风险社会带来的系统性危机和生存挑战,促使人类产生一种集体命运感,从而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共同体意识,因此,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原动力。此外,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科技风险、生态风险和经济风险,世界各国共同制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并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它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的践行者、推动者和实施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这些前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之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风险到命运,从国际行动到命运与共,这些理论与行动的发展和延续都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与反思。然而,风险社会理论的解决方案依然囿于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带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试图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系。与之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大同世界”“协和万邦”“民胞物与”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蕴含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彰显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对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体系的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自身的发展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动力,并且愿意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2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43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世界风险社会、实现全球共同繁荣的中国方案,它为实现人类永久和平和持续发展,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新变革提供了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