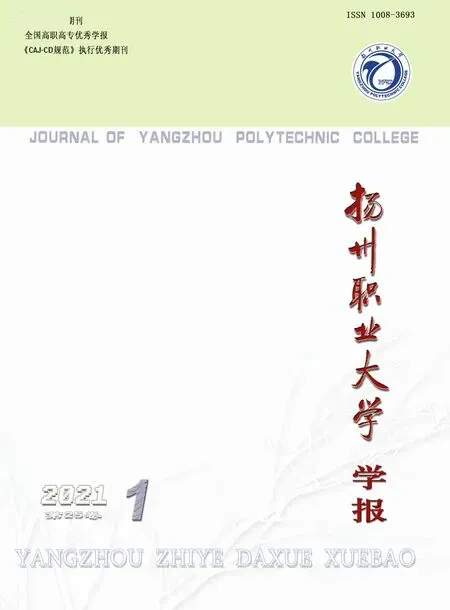沈廷芳早期交游考
王 静 沉
(安徽大学, 安徽 合肥 230601)
沈廷芳(1702—1772),字椒园,一字畹叔,号萩林,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由监生举鸿博,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历官山东道监察御史、山东巡漕使、山东登莱青道、河南按察使、山东按察使,为官有政声。沈廷芳一生往来南北,生于浙江仁和,深受浙派地域文化影响,后因其父沈元沧被征刑部,沈廷芳亦北上急父难,随即奉父命游学京城,结识方苞、刘大櫆等人。乾隆元年(1736),沈廷芳由当时的兵部侍郎杨汝谷荐举应试博学鸿词科,名列二等,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后又改山东道监察御史。乾隆九年(1744)冬,沈廷芳奉旨巡漕山东,他的京城生活自此告一段落,这也是沈廷芳人生交游的一大转折。沈廷芳早期所交往的文人,多为一时名士,沈廷芳与他们的交游情况大多可从其诗文集《隐拙斋集》中觅得轨迹。
1 家族亲友
1.1 查慎行、查嗣瑮
查慎行(1650—1727),原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武英殿总裁纂述,康熙五十二年(1713),乞休归里,人称初白先生。著有《敬业堂诗集》《敬业堂文集》等。查嗣瑮(1652—1734),字德尹,号查浦,浙江海宁人,查慎行仲弟。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官翰林院侍讲。著有《查浦诗钞》等。
沈廷芳年少好学,少即“受业于查浦、初白两先生之门,得其诗法”,[1]12初白、查浦即查慎行、查嗣瑮两兄弟。沈廷芳外祖查昇为查慎行族侄,因此沈廷芳与查慎行、查嗣瑮二人既为亲属,又为师生,情谊非同一般。沈廷芳入京前,与二人来往最为频繁,他既在查嗣瑮乔迁新居时赋诗向其道贺,亦在重阳佳节陪同二位师长登高豪饮。雍正元年(1723),沈廷芳与兄长觅得查慎行旧作《余波词》抄本,《余波词》集查慎行五年所作词一百四十余阙,原稿遗失近四十载,如今抄本得归,查慎行既惊又喜,不仅在《余波词》小序中表示“故物复出,殊出望外”[2],还特意口占两首绝句以谢,沈廷芳亦赋诗相和,由此事可见其对长辈之用心真挚非常。
雍正四年(1726),查慎行、查嗣瑮受其弟查嗣庭文字狱案牵连被征入狱。次年五月,查慎行蒙恩被释,沈廷芳十分欣喜,随即赋诗《喜初白先生出狱二首》[3]225送其归里,而查慎行则在临行前“尽授作诗之法”[3]225,也是对沈廷芳抱有无尽期望。查嗣瑮被判流放陕西蓝田县,未得归乡,廷芳亦作诗送之,并发出“飘零门下士,何日接慈颜”[3]225的感慨,惆怅不知何日才能再聚。八月三十日,查慎行卒于故里,是时沈廷芳仍客居京城,怅然闻查慎行死讯,遂过查慎行旧居樵沙道院,更觉悲痛难忍。其后沈廷芳寄诗查嗣瑮,有句“窳轩(查慎行室名)老去惟公在,撰杖无缘意独深”[3]228,别具怀念之痛。
1.2 沈德潜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编修,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辞官后又加礼部尚书、太子太傅衔。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编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
沈廷芳祖上出于吴兴竹墩沈氏,后迁浙江仁和,而沈德潜虽为长洲人,先祖亦是于明代自竹墩迁居至长洲,故沈廷芳与沈德潜可算同族。沈德潜与沈廷芳父沈元沧素有来往,他为沈元沧所作《墓志铭》有记“余与君以弟兄谊,而廷芳又从余游”[4],沈元沧与沈德潜有兄弟情谊,沈廷芳亦称沈德潜“家归愚叔”、“族叔归愚先生”,甚至还曾受业于沈德潜,二人自有渊源。沈廷芳十分敬重沈德潜,他既请求沈德潜为其父沈元沧编定诗集及作诗序[3]245,也曾在沈元沧下葬时“偕其兄廷怀、心具行状遣伻走三千里”,乞沈德潜“铭其墓中之石”。乾隆元年,沈德潜入都赴试词科,沈廷芳也在京预备应词科试,二人遂频繁交往游玩,春游丰台赏芍药,秋则登芙蓉楼观秋水,饱览山水之景。乾隆四年(1739),沈德潜再入京,沈廷芳为此欣而赋诗,是年夏,沈德潜还移居沈廷芳所寓隐拙斋,二人“日夕论诗,互有丽泽之益”[3]200。至沈廷芳离京前,两人的交往都可谓密切。
2 浙派同乡
2.1 厉鹗、杭世骏、齐召南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乾隆元年荐试博学鸿词科,报罢。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杭世骏(1696—1773),字大宗,号堇浦,浙江仁和人。雍正时受聘为福建同考官,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授编修,改御史,后罢归。著有《道古堂文集》《道古堂诗集》等。齐召南(1703—1768),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浙江天台人。乾隆元年举鸿博,乾隆十三年(1748),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宝纶堂文钞》《宝纶堂诗钞》等。
厉鹗、杭世骏、齐召南,皆为浙派文人,且三人及沈廷芳都于乾隆初被荐举博学鸿词科。厉鹗、杭世骏与沈廷芳可算同乡,因而沈廷芳入京赴试前即与二人相识相交。雍正十一年(1733),沈廷芳由京城归家奔丧,秋游秦淮水榭则有诗《柬厉太鸿征士》[3]234,除此之外,厉鹗为《隐拙斋集》所作诗序也有记,厉鹗从里中诗人符曾处闻沈廷芳诗名,只恨无缘得见其诗,癸丑年(1733)厉鹗客居维扬,沈廷芳则过宅到访,[3]198二人即相识于此。雍正十三年(1735)正月,厉鹗、杭世骏皆于浙省被选应试词科,其时沈廷芳居丧在籍,未得赴都,也未被荐举应试,友人相继被征入都求取功名,沈廷芳既真诚祝愿他们壮志得酬,雅怀得申,也想追随他们的脚步,不甘碌碌无为,故而发出“余岂愿栖息,长作蓬蒿人”[3]239的感叹,幸而沈廷芳入京后被杨汝谷举荐,三人才得以同试词科,沈廷芳终如愿以偿。词科试后,沈廷芳与杭世骏皆入翰林院,而厉鹗不第回乡,但沈廷芳并未与厉鹗断了往来。乾隆五年(1740),厉鹗移居杭州城东,作《移居》四首[5]9,四方友人交相唱和,形成了一次《移居》诗唱和高潮[6]。其时沈廷芳远居京城,却也于次年作诗四首寄和厉鹗诗,厉鹗亦依韵奉答,诗中细述二人初识之情,也愿待到沈廷芳公事尽毕,将“数椽渔舍”与其相分[5]21。
齐召南亦为浙派诗人,但因他是浙江天台人,故而入京之前,沈廷芳与其并无往来。词科试后,杭世骏列一等授编修,沈廷芳、齐召南列二等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散馆后,沈廷芳授编修,齐召南授检讨,三人则为翰林院同僚。雪夜春朝,每每同人酬唱集会,都可见三人身影。乾隆四年春,沈廷芳有诗《瑞竹诗为齐次风同年作》[3]266,竹本就有君子高风亮节之寓意,沈廷芳在诗中亦由齐召南庭前翠竹极言其品性高洁,才华殊异,堪为国之大器。
2.2 吴廷华
吴廷华(1682—1755),字中林,号东壁,浙江钱塘人。康熙举人,雍正年间任福州府海防同知,乾隆初荐修《三礼》。三礼馆隶属内阁,馆臣又以翰林居多,在京文儒诗酒集会,实属平常,[7]故而沈廷芳与吴廷华虽然入京前素无交集,但二人既有同乡之谊,又有同僚之情,相识相交并不出人意料。况且其时沈廷芳的老师方苞也担任三礼馆副总裁,二人还“同问礼于子方子之门”,这就更拉近了沈廷芳与三礼馆以及吴廷华的距离,无怪吴廷华在著《仪礼章句》时,频至沈廷芳之邸,“遇轇轕处,每属订正。”[3]503沈、吴二人不仅于经学上志同道合,沈廷芳与吴廷华仲子吴寿祺亦有师生之谊,更将长女许配给吴寿祺,关于这件事沈廷芳在《此君亭记》中有记:
吾友吴中林郡丞有仲子寿祺,好学善属文,余因以与筠字之,馆于室中。适兄自粤东来,每花月时偕余扶侍太恭人憩亭上,与筠必在侧听寿祺读书,琅琅应竹声。老人神为之怡,中林亦尝坐亭间,啜茗对竹谓余曰:“此境非荆蛮民画耶?”[3]562
长幼有序,其乐融融,沈廷芳与吴廷华的交往已经深入到家庭生活层面,双方的家庭成员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人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朋友”二字可以概括。乾隆七年(1742),沈廷芳患咯血之症,吴廷华“为视药饵”,病情加重后,沈廷芳即请吴廷华为自己书行状[3]593。所幸不久病愈,二人的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3 在京同人
3.1 刘大櫆、方苞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乾隆元年,应博学鸿词科,乾隆十五年(1750),再举经学,皆未被录取。著有《海峰先生诗文集》《论文偶记》等。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亦为桐城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任为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时为《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乾隆元年,充《三礼义疏》副总裁,擢礼部侍郎,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雍正三年(1725),刘大櫆入京赴顺天乡试,被贡入太学,其文才深得方苞赏识,故而拜入方苞门下。雍正五年(1727),沈廷芳因其父沈元沧被捕匆匆北上。一时事毕,沈元沧即令沈廷芳在京游学。沈廷芳、刘大櫆皆为太学生,此或为二人相识契机,雍正六年(1728)冬,沈廷芳由刘大櫆引荐学文于方苞,故而沈廷芳与刘大櫆又为同门。刘大櫆在为沈廷芳所作《沈椒园诗集序》中写道,“沈君累然太学生,尝工举子业,屡试不遇,而其心愈下,其气愈和”[8]73,而刘大櫆入京前多次童试败北,满心失意。由此看来,刘大櫆之所以愿意引荐沈廷芳,或出于对沈廷芳科举不第的感同身受,故而希望在他看来是“梅枝作骨”[8]427的沈廷芳也能得遇良师,得偿所愿。刘大櫆在京时间不算长,且期间断续往来于家乡和京城,在京期间沈廷芳与其交往游玩自不必说,二人也时与同人饮酒集会赋诗联句。雍正十二年(1734)春,沈廷芳正服丧在籍,至江苏游览,而刘大櫆此时由家乡再赴京师应举,北上途中二人得以短暂相见,沈廷芳即有诗送刘大櫆,感叹重逢又将分别,希望刘大櫆此次科考能够如愿。刘大櫆到京后,沈廷芳又写诗以寄,“远书不到心常忆,旧雨重逢话定长”[3]236,既表思念,又憧憬京师再次相见,可见二人情谊并不因时空距离而生疏。
雍正六年,方苞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而沈廷芳来谒,此为二人初次见面。但在此之前沈廷芳与方苞也并非毫无交集,沈廷芳外祖查昇、父亲沈元沧皆为方苞故交,也因为这层关系,沈廷芳初次拜见方苞后,方苞即于翌日“乘车曳杖”冒雪回访,分别之际不忘教导沈廷芳要勤勉治学[3]539。对于沈廷芳来说,方苞即为师长,又为亲长。在学问上,方苞多次言明让沈廷芳“以治经为务”[3]539,还教习沈廷芳作古文之法,不仅如此,沈廷芳在生活和做官为人上也多得益于方苞,雍正十三年(1735),沈廷芳服阕归京,复游太学,其时方苞正任《一统志》馆总裁,沈廷芳因而“为馆中官写书求补缺”,方苞于是令沈廷芳以国子生为《一统志》校录,更告诫他“馆中易荒业,生宜穷经著书,勿沾沾于是”[3]539,既为沈廷芳解决生计,又教导他治学之道。乾隆八年(1743),沈廷芳担任御史因言事被降职,方苞听闻此事则寄书沈廷芳,既肯定其为官“已得正路”,又劝慰沈廷芳多“默诵诸经”,以“养心卫生”,[3]540这些言语也是对沈廷芳坚持直言上书始终不改的有力支持。可以说,方苞是沈廷芳入京之后心中最鲜明“师”的形象,也是他的同道和榜样。
3.2 张栋
张栋(1705—1778),字鸿勋,号玉川,又号看云山人,江苏吴江人,工诗善画。张栋亦以贡生入太学,与沈廷芳同为太学生,此应为二人相交的由来,而在《隐拙斋集》中沈廷芳所记与张栋的第一次交集即是雍正九年(1731)为其《石公山画卷》题诗,其时沈廷芳已届而立之年,另乾隆六年(1741)沈廷芳所作《春夜止鸿勋宿》亦有句“与子十载余,人海浮两萍”[3]287,据此推算,沈廷芳与张栋相识的时间即是雍正九年前后。沈、张二人并非年少相识,也并没有重要相识契机,然而沈廷芳却频将张栋引为知己。雍正十年(1732)秋,沈廷芳于贞一斋集会送张栋归乡,即有诗称其是“知音”[3]232,其时距二人相识也仅仅一年的时间。沈廷芳其后的诗歌对于二人友情的描写亦是情真意切,张栋弱冠即游京师,诗画俱佳,因屡试不第,故而离京弃试,专研诗画,沈廷芳对于张栋这种潇洒使意的行为十分欣赏,认为“眼前衮衮富贵者,未有磊砢如君才”,也希望张栋即使怀才不遇,挂席南下,也一定“豪情莫叹知音稀”[3]271,即是愿为其知音的意思。张栋一生寄情山水,往来江湖之间,然而张栋每每入京,沈廷芳都与其有所交游往来,既同赏古画,也同游新春,二人的关系正是沈廷芳所说的“平生一知己,相于长忘形”[3]287,即使一人身在朝堂,一人身在江湖,知音挚友之情却常在心中,时时都可欣然对榻夜谈。
年少时期家族亲友的谆谆教诲奠定了沈廷芳好学善学的基础,浙杭同乡好友的互相交游唱和营造了沈廷芳的地域归属,而京城所结识的诸子同人甚至亦师亦友的诸位贤达,开阔了沈廷芳的文学和生活视野。因此沈廷芳这一时期的交游可以说对他的文学创作甚至人生态度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也是他离京后清白为官,任书院山长时辛勤执教的精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