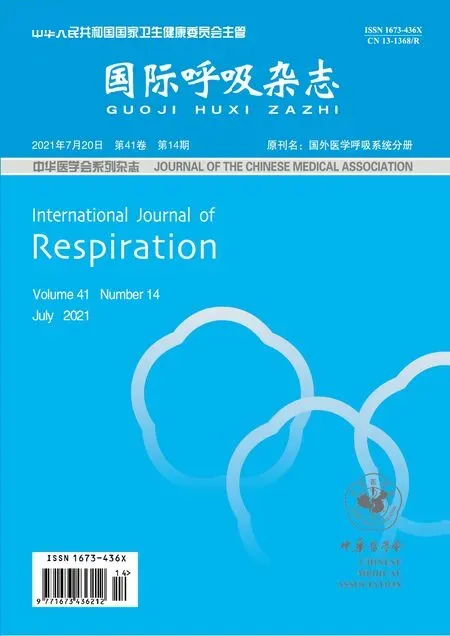气腔播散相关特征及对肺癌预后影响的研究进展
何帆 王华萍 柴荣 殷钢 韩一平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上海 200433;2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450000
2019年全球癌症负担报告指出癌症的疾病负担仅次于心血管疾病,位于第2位,肺癌是发病率第二,病死率第一的癌种[1]。国家癌症中心近期发布的 《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表明,我国肺癌的发生率与病死率均为各肿瘤的首位,与肺癌相关的病死率是美国的1.4倍[2]。肺癌的预后与其分期密切相关,早期有手术机会,可获得较好的预后[3],但仍有部分早期肺癌患者不久后又出现复发甚至转移。近年来,随着病理学的深入研究,发现了气腔播散 (spread through air spaces,STAS)这一新的肿瘤侵袭模式,而STAS正是早期肺癌术后复发和转移的高风险因素。本文就STAS的相关特征和对肺癌预后影响等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STAS定义及由来
根据2015年WHO 的肺癌病理分类标准,STAS被定义为 “微乳头状簇,实心巢或单个细胞散布在主要肿瘤边缘以外的气腔空间内”,是一种新的肺癌侵袭模式[4]。既往研究将肺腺癌侵袭方式分为三类,分别为:(1)间质浸润;(2)脉管浸润或胸膜浸润;(3)非贴壁的生长方式,例如乳头状、微乳头状、腺泡型、实性形式[5]。而STAS则被定义为肺腺癌侵袭的第四类。
在正式定义STAS之前,早期报道表明,肺腺癌引起的气源性肿瘤扩散、游离的漂浮细胞簇以及结直肠癌的转移都是导致肺癌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6]。除此之外,另有研究也发现此现象,并提出肿瘤岛的概念即存在于肺泡腔内的一个孤立的、大量游离的肿瘤细胞群。肿瘤岛以微乳头状结构为特点,位于主肿瘤灶周围,又与其间隔几个肺泡,常见于肺腺癌[7]。2015 年Kadota等[8]研究纳入了Ⅰ期肺腺癌患者411例,其肿瘤最大直径均小于2 cm,该研究证实了STAS是一种肺腺癌的侵袭模式,且大部分出现在邻近主肿瘤灶的第一肺泡层中,少数也可出现在远处肺泡腔中。在同一年Warth 等[9]研究收集了病理切片观察569例,该研究组将STAS分为两类,广泛STAS 和局部STAS,广泛STAS是指细胞簇与主肿瘤灶间隔大于3个肺泡腔;局部STAS是指细胞簇与主肿瘤灶间隔小于3个肺泡腔。而2017年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则将STAS分为3类,即高STAS (≥5个实性癌巢或单肿瘤细胞或微乳头样细胞簇),低STAS (1~4个实性癌巢或单肿瘤细胞或微乳头样细胞簇),无STAS[10]。这是首次对STAS 进行半定量评估,有助于预后风险评估,对临床指导意义重大。
2 STAS机制
由于对STAS 机制研究较少,我们对其认识尚浅。STAS发生可能与细胞-细胞间及细胞-基质间的相互作用有关。肿瘤细胞在基底膜上增殖,继而从基底膜上脱落,游离于气腔中,可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发现脱落的肿瘤细胞;随后肿瘤细胞再附着于另一处基底膜并在其上生长[11],可以用Liotta[12]的三步入侵模型来解释:黏附,降解和移动。此外,黏附分子、层黏连蛋白、基质金属蛋白酶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的表达,癌细胞与超微结构之间的松动,以及肿瘤浸润白细胞的刺激都可能与STAS有关[13]。多项研究表明,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可能受到其所处微环境的影响,该环境不仅由癌细胞组成,还包括多种基质细胞。基质细胞通过分泌可溶性因子,例如生长因子或炎症趋化因子,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有研究认为中性粒细胞可以诱发肺癌肿瘤细胞脱落,继而导致肺癌的气腔播散,致使生存期缩短,这可能是腺癌进展的一种重要因素。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和成纤维细胞是肿瘤微环境中的主要细胞成分,可以调控肿瘤的扩散和转移[14]。Qiu等[15]分析了208例α平滑肌肌动蛋白(Alpha smooth muscle action,α-SMA)阳性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和CD204 阳性血清肿瘤相关物质 (TAM)的Ⅰ~ⅢA 期肺腺癌标本,结果显示STAS的存在与较多数量的α-SMA 阳性CAF 和CD204阳性TAM 相关。STAS的精确分子机制尚不明确,还需要动物模型来分析。
3 STAS的病理特征及检测难点
STAS是一种病理学概念,包括3种形态学模式:(1)单个肿瘤细胞,是由肺泡腔内游离的单个肿瘤细胞形成的;(2)微乳头状细胞簇,是由缺少中央纤维血管轴心的乳头状结构形成的,偶可见环状结构; (3)实性癌巢,是由充满肺泡腔内的实性成团的肿瘤细胞形成的[16]。值得注意的是,单个肿瘤细胞或STAS 群不能沿肺泡间隔贴壁生长,必须位于肺泡腔内。此外,这些肿瘤细胞与主肿瘤灶边缘之间必须间隔一个肺泡层以上[8]。
虽然STAS的形态学模式很明确,但其检测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困难:首先,肺泡腔中的肿瘤细胞与肺泡巨噬细胞在形态学上不易区分,吸烟者肺泡腔中的巨噬细胞,其胞质通常含有黑色碳颗粒和淡褐色色素,而STAS阳性的肿瘤细胞通常无胞质色素,较易区分;但不吸烟者肺泡腔中的巨噬细胞通常也无胞质色素,区分二者难度较大,需要更细致的辨别,巨噬细胞胞核较小,核仁不明显,无核异型性,而肿瘤细胞核仁大而多,且有核异型性,此外还可借助免疫组化等其他方法加以鉴别[17]。其次,病理切片制作时,刀切割可能会使肿瘤破碎,而碎片堆积则看上去与STAS病变极为相似,难以区分[18]。有研究认为从主肿瘤灶起始的气腔就持续有肿瘤细胞簇的是STAS,而与主肿瘤灶无联系又远离的肿瘤细胞簇则是人工假象[8]。但目前的病理评价标准尚未统一,Shiono和Yanagawa[19]与孙平丽等[20]研究STAS的发生率分别为14.8%∶61.8%,竟相差4倍之多。综上可见,对于STAS的病理检测尚需要更多的实践。
4 影响STAS相关因素
STAS是早期肺癌术后重要的预后指标,那么STAS的发生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许多研究均表明STAS与性别、年龄及吸烟均无关[21-24]。部分研究认为肿瘤直径大小对STAS发生有影响,Uruga 等[10]认为肿瘤直径≥1 cm,Toyokawa等[22]认为肿瘤直径>2 cm,徐艳等[24]认为肿瘤直径≥2.7 cm 时,STAS发生率更高;而有研究则表明当肿瘤直径≤2 cm 时,STAS发生率与肿瘤大小无关[8]。另有部分研究发现STAS 与肺癌相关分子之间关系密切。Warth等[9]研究发现STAS 与EGFR 突变发生率较低,BRAF突变发生率较高相关,而与KRAS 突变,TTF1,Napsin或CK7表达无关。有研究也提示STAS 与野生型EGFR 显著相关[19]。而另有研究得出STAS与EGFR 突变或PD-L1表达无显著相关性[22]。Lee等[23]研究显示野生型EGFR 和ALK 重排的肺癌中更易出现STAS,Kim 等[25]研究也表明STAS与较低的EGFR 突变发生率和较高的ALK重排发生率有关。由于样本差异及病理检测标准不同,导致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STAS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尚需要更多大样本、前瞻性的实验去进一步证实。
5 STAS与影像学
STAS只能在手术切除的标本中检测到,而不能在CT引导或支气管镜活检标本中检测到,在手术前无法可靠地识别出该现象,因此术前对该现象的预测具有重要意义。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以实性结节为特征并行手术切除的肺腺癌患者80例,结果显示,STAS阳性结节,其固体成分占总结节的比例、结节直径大小均显著大于STAS阴性结节[26]。Kim 等[25]研究共纳入了接受手术切除的肺腺癌患者276例,以探索用于预测STAS的CT 成像特征,结果发现:(1)STAS在实体瘤中比在部分实体或磨玻璃样病变中更常见; (2)STAS还与中央低衰减、支气管造影和固体成分百分比 (percentage of solid component,PSC)有关;(3)PSC 是STAS发生的独立预测因子,其灵敏度为89.2%,特异性为60.3%。有研究根据术前CT 和术后病理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STAS与肿瘤直径大小、分叶征、血管征、毛刺征、胸膜牵拉相关,而与磨玻璃样结节无关[27]。由于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会导致CT 检查发生变化,因此无法在CT 上可靠地检测到STAS现象。
6 STAS与肺癌术后预后
许多研究发现STAS与肺癌术后预后密切相关,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在肺腺癌。Kadota等[8]一项纳入了手术切除的Ⅰ期肺腺癌患者411例的回顾性研究,得出结论,在局限性切除组中,STAS阳性患者复发的风险显著高于没有STAS的患者;但是在肺叶切除术组中,STAS阳性患者与没有STAS患者相比,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变量分析显示,STAS是肺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一项回顾性,纳入了研究接受局限性切除的早期肺腺癌患者508例,并得出结论,STAS是局限性切除的早期肺腺癌术后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且与手术切缘复发相关[28]。另有研究也表明STAS是行局限性切除但未进行肺叶切除术的IA 期肺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29]。Toyokawa等[22]研究也认为经手术切除的STAS阳性腺癌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 (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均短于没有STAS患者,特别是行局限性切除的STAS阳性腺癌患者术后生存率明显缩短。Eguchi等[30]对T1N0 M0 肺腺癌患者1 497例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在STAS阳性的T1N0M0肺腺癌患者中,肺叶切除术比局限性切除术会具有更好的结局。综上可见,STAS与肺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并建议STAS阳性的早期肺癌患者行肺叶切除。
为进一步探究STAS程度对肺癌预后的影响,有研究发现STAS的数量可能是影响肺癌预后的一个重要因素,STAS越高,RFS越差[10]。Warth等[9]则探究了STAS距离与肺癌预后的关系,结果发现,广泛STAS 与局部STAS相比,患者预后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但无论广泛还是局部STAS 阳性患者预后明显差于没有STAS 患者,这可能表明STAS阳性对肺癌预后有不良影响,但STAS距离与肺癌预后关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为探究STAS 和肿瘤大小对肺癌预后的影响,Dai等[31]研究发现在肿瘤直径>2 cm 的患者中,STAS阳性提示预后不良;当肿瘤直径≤2 cm 时,STAS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作用弱。Yang等[32]研究也表明在行根治性肺叶切除术的肺腺癌>2 cm 的Ⅰ期患者中,STAS阳性是预后明显较差的预测指标,而在肿瘤≤2 cm 的患者中无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如果STAS可以成为肺癌分期中的一个参数,尤其对于肺腺癌,可能会更准确地预测其预后。
尽管大多数研究都与肺腺癌相关,但研究人员还发现STAS也与肺鳞癌患者的复发和生存有关。Lu等[17]分析了切除的Ⅰ~Ⅲ期肺鳞癌445例,其中有30.0%的病例存在STAS征象,并且随肺癌分期增加,STAS发生率也随之增加,与STAS阴性患者相比,STAS阳性患者的复发率及病死率明显增高。在多变量分析中,STAS是复发和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另一项纳入肺鳞癌患者220例的回顾性研究,其中有42例 (19.1%)STAS阳性,研究发现STAS与Ⅰ期肺鳞癌的复发和不良生存相关 (5 年RFS:37.4% 比68.4%,P=0.000 6;5 年 OS:50.2% 比71.4%,P=0.007 8),而与Ⅱ~Ⅲ期肺鳞癌的相关性不明显,他们认为STAS是Ⅰ期肺鳞癌复发和预后不良的预测指标[33]。然而,Toyokawa等[34]分析了手术切除的30 例鳞癌患者的肿瘤标本,其中19 例 (63.3%)为高STAS,6 例 (20.0%)为低STAS,5 例 (16.7%)为无STAS,研究结果显示,STAS高的患者与STAS阴性/低的患者之间的复发率和总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因为样本较少,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综上可见,在肺腺癌中,STAS与患者预后不良密切相关,且STAS的数量越多预后越差,但STAS的距离对预后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等。除了肺腺癌,STAS也与鳞癌、多形性癌患者预后相关,且STAS阳性是其复发和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STAS阳性的早期肺癌患者建议行肺叶切除。
7 总结与展望
目前,在肺癌中越来越多地发现STAS,并且大多数研究表明,这种新的征象具有重要的预后价值,它是独立于肿瘤分期和生长方式的预后因素,也是Ⅰ期肺腺癌和Ⅰ期肺鳞癌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8,33],这将对临床治疗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STAS精确分子机制不明确,病理检测仍有难点,也没有良好的能够预测STAS的特异性指标,STAS是否可以成为肺癌分期中的一个参数,STAS阳性患者是否均需行肺叶切除,若行亚肺叶切除后化疗能否获益,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努力和研究的方向。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