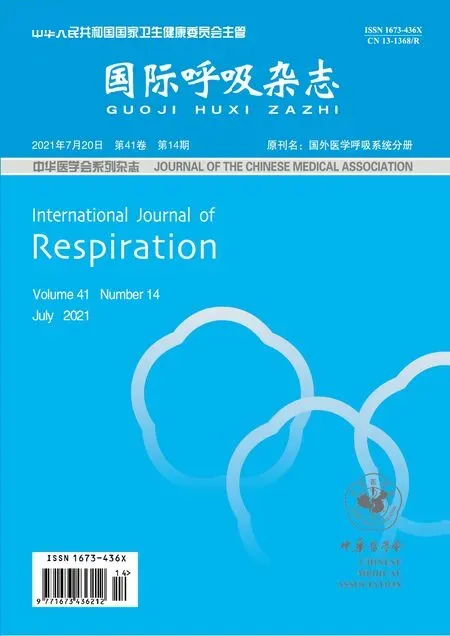肺微生物组群与肺癌相关性研究进展
刘启平 范运秀 韩鹏凯
1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404100;2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肿瘤放射治疗科呼吸病区 404100
微生物组群是指与人体共栖、共生和致病的微生物生态群落[1],包括细菌、古细菌、原生生物、真菌、病毒等。它们位于机体的各种部位,如皮肤、鼻咽、口咽、呼吸道、胃肠道和女性生殖系统[2],在不同的器官形成具有器官特异性的微生物组群。人体微生物群落的大小和组成,受宿主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因部位不同而各有差异,并能够影响疾病的发生和治疗效果。众所周知,微生物是感染性疾病的主要病因,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群落与许多非感染性疾病的发病密切相关[3],如癌症。
1 肺微生物群
微生物群落与癌症的关系是目前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得益于二代测序宏基因组学和16SrRNA 高通量测序技术以及生物信息学的快速发展,我们能更全面了解呼吸道微生物的组成。其中宏基因组学能够检测出呼吸道中所有微生物基因序列 (包括细菌、真菌以及病毒等),主要应用于微生物组分析;16Sr RNA 高通量测序技术是识别16S亚基,主要用于菌群的分析。新的测序技术大大推进了呼吸道微生物组的研究。众多研究发现,健康人的肺并不是无菌的,而是存在不同的微生物群落[4]。肺部微生物组群的种类和数量在气道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受到解剖位置和局部环境条件的影响,并通过人体吸入、咳嗽活动、黏液纤毛清除和免疫系统激活等来维持动态平衡。影响共生菌生长和生存的因素包括营养物质、温度、p H 值、氧张力、宿主免疫细胞丰度和激活状态等。健康的肺不适合细菌群落的发展,导致细菌繁殖速度相对较低。上呼吸道具有大量的厌氧菌和十倍以上的好氧菌[5]。下呼吸道中的菌群是比较固定的,在门、纲水平,以硬壁菌门、变形菌纲、梭杆菌纲和拟杆菌门为主;在属水平,则以假单胞菌属、链球菌属、普雷沃菌属、韦荣球菌属、嗜血菌属以及奈瑟球菌属为主[6-7]。
肺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多样性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迁移至肺部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肺部微生物的消除以及肺部微生物本身的繁殖速度[8]。当肺部发生病理性改变的时候,局部微生物生长条件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特定的细菌生长创造了合适的环境,使得这些细菌能够适应并改变肺部环境。研究发现,与健康状态下相比,肺慢性疾病时,肺部微生组群发生巨大变化,并且在疾病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亦具有明显差异。如链球菌的短暂侵袭能很好地预测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严重程度[9];囊性肺纤维化 (cystic fibrosis,CF)时,大量黏液聚集、炎症和微生物的变化 (特别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10]不同程度地影响患者的肺功能;另有研究表明,某些发酵性厌氧菌是CF加重的重要因素[11]。再比如,COPD的早期阶段,肺部微生物组群似乎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是随着疾病的进展,肺微生物组群发生包括链球菌、假单胞菌和嗜血杆菌在内的细菌属别变化[12];在COPD 急性加重期,以致病性细菌的增多最为明显,肺菌群的改变与COPD 加重等疾病状态密切相关[13-14]。与健康人相比,危重患者的肺部微生物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5-18],并且与肺泡和全身炎症程度相关。
2 肺微生物群与肺癌
已知某些微生物会导致人类癌症的发生。如某些致癌病毒,包括人类疱疹病毒 (HHV4和HPV8)、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人类T 细胞白血病病毒-I,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HPV 16 和HPV18)和默克尔细胞多瘤病毒。在细菌中,幽门螺杆菌和伤寒沙门菌是已知的可导致胃癌和胆管癌的细菌[1,19]。
肺癌是目前全球健康的重大威胁,每年有130万人死于肺癌。与其他癌症相比,肺癌早期无症状,诊断时多数已处于晚期,不同组织学类型有不完全相同的病因、进展模式和预后。尽管有手术、化疗、放疗、靶向、免疫及中药等不同的治疗手段,但肺癌5年生存率仍仅为约15%。
基因突变、空气污染、吸烟、过度的辐射、感染、某些慢性肺部疾病是目前已知的肺癌病因。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近年的研究发现,肺微生物群与肺癌的发病密切相关[20-22]。一项基于肺癌遗传模型的研究发现,抗生素治疗或无菌状态可以抑制小鼠肺癌的发展[23]。该研究还发现,肺部低细菌负荷与肿瘤生长速度减慢显著相关,揭示了局部微生物群丰度与肺癌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随着细菌负荷的增加和肿瘤相关菌群多样性的减少,IL-17介导的炎症细胞增多,进而促进肿瘤前中性粒细胞的增生和肿瘤细胞的增殖。将从晚期肺肿瘤中分离的细菌群,进行气管内灌注则加速了肿瘤的生长,而局部给于细菌菌体成分(脂多糖和肽聚糖)则可显著刺激肺内的T 细胞增生,并且在其他类型肿瘤模型中也有相似的发现。目前肺微生物群的研究,主要通过唾液、痰液、支气管灌洗液、肺组织的二代测序 (包括16sRNA 测序、宏基因测序等)进行。
口腔微生物群可通过吸入直接进入肺部。Yan等[24]研究发现,不同肺癌患者唾液中的微生物组群是不同的,特别是嗜二氧化碳噬细胞菌属、Selenemonas、韦荣球菌属和奈瑟菌属。通过靶向QPCR 技术,研究者发现肺癌患者唾液样本中嗜二氧化碳噬细胞菌和韦荣球菌属更丰富,而奈瑟菌属相对较少,这表明它们有可能作为一种肺癌早期检测的生物标志物,而且显示出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实验中,与对照组相比,在鳞状细胞癌和腺癌患者的唾液样本中,韦荣球菌属更为丰富,可考虑将此作为鳞状细胞癌和腺癌的诊断生物标志物。
与燃煤有关的家庭污染也可能是肺癌的致病因素,这可能与多环芳烃的产生有关。一项研究对中国的非吸烟女性肺癌患者进行了微生物成分分析,此小规模研究[12]采用全宏基因组的方法对肺癌患者痰液中的微生物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的痰液相比,肺癌患者痰中肉芽孢杆菌、非营养菌和链球菌显著增加。
Lee等[12]对28 例肺癌患者支气管灌洗液进行16Sr RNA 基因测序,在每个样本中均发现了大量的分类单元,且发现肺癌患者和非肺癌患者的运算的分类单位(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OTU)丰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肺癌患者韦荣球菌属和巨形球菌属显著增加,两者相结合,在预测肺癌可能性中显示出较高的ROC曲线下面积(Authentication Center,AUC)值 (0.888),这些微生物差异可能是肺癌的重要特征。该研究还表明巨型球菌属和韦荣球菌属可以作为肺癌的一种生物标志物。因此,这两个属有可能成为肺癌微生物治疗的靶点。
另一项研究[25]则针对肺癌患者 (手术切除单侧肺大叶团块癌变部位和对侧非癌变部位支气管灌洗液)和健康对照者支气管灌洗液,通过16SrRNA 测序分析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肺癌患者的微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alpha多样性从健康部位到非癌变部位再到癌变部位逐步下降。在癌症病例中,链球菌属明显多于对照组,利用链球菌属预测肺癌的AUC 为0.693 (敏感度为57.5%,特异度为55.6%)。链球菌属和奈瑟菌属的丰度在肺癌患者中呈上升趋势,而葡萄球菌和杆菌属的丰度从健康部位、到非癌部位、到癌边部位,则逐步下降。总的来说,肺癌相关的微生物群在肺癌与健康对照组之间存在差异,并且微生物群的改变并不局限于肿瘤组织。从健康部位到非癌变部位再到配对癌变部位的逐渐变化,提示了与肺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微生物微环境变化。
包括健康人、肺癌及良性肺部疾病患者在内的,共530例参与者的研究发现,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是所有参与者肺中最丰富的菌门,分别在肺癌患者中占17.5%、47.5%,良性肺部疾病患者中占28.2%、39.27%,健康对照组中占40.62%、32.09%。此外,与其他组相比,肺癌患者中有大量放线菌和厚壁菌门[26]。在属水平上,普氏菌属在所有参与者中占主导地位,但在癌症患者中的比例相对较低 (肺癌为25.74%,良性肺结节为35.59%,健康对照组为36.75%)。相比之下,链球菌在肺癌病例中更为富集 (肺癌为9.65%,良性肺结节和健康对照组为7.98%,良性肺结节和健康对照组为7.26%)。提示肺癌患者与健康人呼吸系统微生物群组成存在明显差异,有可能作为诊断肺癌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还有研究对比分析了165份不同阶段肺癌患者组织样本,发现特定细菌与肺癌临床分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热菌属在晚期患者 (ⅢB、Ⅳ)的组织中更为丰富,而军团菌在发生转移的[27]患者中含量更高。同样,非恶性肺组织比相应的肿瘤组织具有更高的微生物群多样性。另有一些证据表明,肺部微生物群的组成与肺癌预后之间存在潜在的关系。Peters等[28]研究发现,拟杆菌科、毛螺菌科和瘤胃菌科的丰度越高,无复发生存(relapse-free survival,RFS)和无病生存期 (disease-free survival,DFS)越短,提示肺微生物群可以作为预测早期NSCLC复发风险的生物标志物。如果肺部微生物群组成的预后价值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得到验证,也将成为改善肺癌患者RFS治疗的新靶点。
不同的流行病学研究,分析了肺部微生物群与肺癌的关系,发现微生物群的改变不仅参与肿瘤的进展过程,而且影响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性[21]。目前有关微生物群对不同药物疗效调控作用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肠道[29]中的细菌,肺部微生物群相关的研究尚未见报道。然而,由于许多抗癌药物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肺部,在这里,可以被共生细菌消化吸收。Cribbs等[30-31]观察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的肺泡灌洗液在代谢组学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柄杆菌科、葡萄球菌科和Nocardiidaceae。肺部微生物菌群可能是一个代谢活性联合体,能够改变治疗药物的化学结构,改变其药理活性 (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和/或影响其局部有效浓度[32-33]。肺部微生物群对的抗癌药物代谢的作用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3 肺微生物组群与肺癌发生的相关机制
3.1 促进致癌炎症环境的产生 肺癌的发生与慢性炎症密切相关,炎症细胞浸润和促炎因子 (包括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前列腺素)的积累,可以刺激细胞增殖、血管生成、组织重塑或转移[34]。研究表明微生物可以通过诱导炎症促进肺癌的发生。特定细菌在促进癌症发展中起着不同作用。已经发现结核分枝杆菌与肺癌的发生有重要关系[35]。这种关联可能的机制是结核诱发的慢性炎症导致癌变。其他细菌如嗜血杆菌、莫拉克菌、链球菌、葡萄球菌和假单胞菌也可引起肺部的慢性炎症[36]。微生物群致癌作用可能是微生物群及其代谢物激活免疫上皮细胞的TLRs导致炎症的发生,如果炎症持续,可能会导致正常细胞不可逆的损害,促进肿瘤的发生[21]。CD36可能与肺微生物群促进肺癌发展之间存在联系[37]。CD36与病原体衍生配体或毒素相互作用,是炎症通路的重要介质,CD36 可能通过影响多聚(adp-核糖)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 (PARP-1)来调节癌变,而PARP-1是细胞增殖和癌变的重要调节因子[38]。已有研究表明,肺组织中CD36表达的改变与肺癌发生有关[39]。Apopa等[37]观察到,除了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外,在肺癌患者肺标本中检测到蓝藻 (0.53%),CD36调节了肺泡中蓝藻源微囊藻体残基的内化和加工,这可能与肺微生物群促进肺癌发展存在联系。
3.2 微生物组代谢产物的致癌作用 微生物群影响宿主的新陈代谢,这种影响已经在肠道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微生物的变化与致癌物乙醛[40]和脱氧胆酸[41]的产生有关,脱氧胆酸是一种胆盐代谢物,已被认为与食管癌和肝癌有关。肺癌患者发生变化的细菌属存在一些共性,不同的研究报告了颗粒链球菌[7,12]、链球菌属[7,12,25]和韦荣球菌属[24,42]的变化。链球菌、肠球菌和颗粒链球菌是兼性厌氧菌,COPD 和肺癌患者发酵性兼性厌氧菌乳酸杆菌显著增加,生物膜形成明显。另外,宏基因组学方法提示肺癌微生物组的功能改变可能与肉芽肿的增加有关。特别是微生物组代谢产物腐胺及其多胺产物[12]的能力增强。肉芽肿形成可能是肺癌的一种特殊的微生物学反应。肉芽孢杆菌被认为是营养变异链球菌的一个例子,因为它需要如吡哆醛(维生素B6的一种形式)或L-半胱氨酸补充到培养基中,以便在实验室[43]中生长。这与平行代谢组学研究[12]中检测到的肺癌患者中腐胺含量的增加相吻合。多胺与吡哆醛代谢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这可能是肉芽孢杆菌丰度的增加是对这些代谢途径的响应[44]。影响细胞周期的腐胺和多胺已在几种癌症中被发现,包括肺癌[45]。因此,颗粒链球菌的生长和肺癌代谢物增加有关。
3.3 基因毒性 有几种细菌与基因毒性有关。例如,脆弱拟杆菌毒素与触发双链DNA 损伤有关[46]。细菌产生的化学物质,如超氧化物歧化酶,也是基因组不稳定的原因[47]。Greathouse等[48]研究也表明肿瘤的TP53突变和食酸菌属Acidovorax存在联系。所以TP53突变状态和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与吸烟导致的肺癌发生有关。
3.4 ERK/PI3K 通路上调。Tsay等[49]研究了微生物群促进癌细胞生长的可能机制。他们发现肺癌患者下呼吸道中有链球菌和细根杆菌的富集。支气管上皮细胞平行转录组分析显示ERK/PI3K 通路上调,体外实验表明Veillonella能够直接促进气道上皮细胞和肺肿瘤细胞ERK/PI3K 信号的激活。该途径被认为是肺癌发生的早期事件,从预防的角度来看,早期识别可能被肺癌微生物组调控的PI3K 是一个可作为靶标的事件[50-52]。如果PI3K 的激活确实是由微生物组驱动的,那么这可能为直接修饰微生物组的化学预防新方法打开了大门。
4 总结与展望
肺微生物组群和肺癌相关的研究结果,提示微生物组群研究可以作为肺癌诊治的潜在的生物标志物[21],可以早期诊断肺癌、判断分期、预后及可能的药物治疗效果。更好地了解肺微生物组与肺癌的关系,将有助于研究和开发潜在的肺癌阻断药物靶点。但需要更多的肺微生物样本(包括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来将各种微生物与肺癌发病机制中的保护性或致癌性因素联系起来,同时需要标准化的程序来一致地描述肺癌患者呼吸到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功能模式。此外,由于肺癌是由异质性亚群组成,未来的研究应探讨这些亚群 (如病理类型、疾病分期)与呼吸到微生物群之间的联系。但需要更大的试验样本量、标准化的检测程序、动态监测微生物组群变化、研究肺微生物代谢组学等,以进一步阐明肺癌的发生发展和呼吸到微生物群之间的关系。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