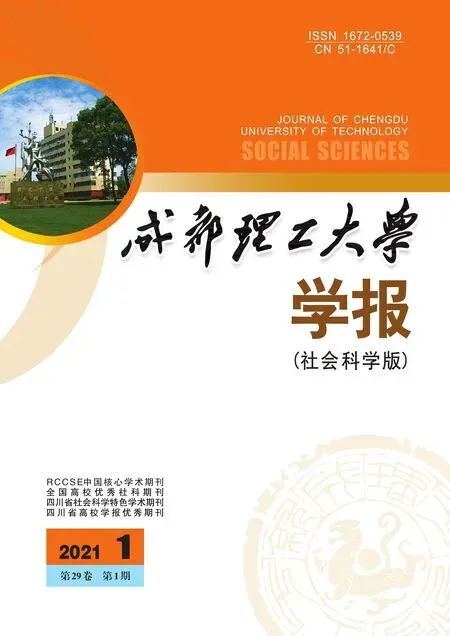朱熹经学诠释与楚辞学革新
庄 丹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郑振铎先生认为,朱熹“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1]531。《楚辞》研究曾一直停留在汉代学术的研究范畴中,直到朱熹的《楚辞集注》一书编成,才使《楚辞》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朱熹能自觉扬弃《楚辞》研究中的汉代经学标准,阐发《楚辞》作为文学作品的抒发情感、表现忧患意识的总体特征,开启了后世《楚辞》文学的正确方向及研究热潮,可谓功绩卓著。然而,对于朱熹如何将《楚辞》从汉、唐诸儒的经学注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学界对其内在的经学思想变革之原因探求尤为不足。事实上,朱熹的楚辞学研究新突破,却恰恰根源于其经学思想的变革。从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可以研究朱熹楚辞学研究及创作取得历史功绩的内在原因,同时结合朱熹楚辞文体学的历史贡献,可进一步认识朱熹楚辞学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一 、朱熹经学之“道”与《楚辞》之“文”
朱熹《楚辞集注》云:“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2]16
朱熹认为,《楚辞》的根本价值在“道”,在“增夫三纲五典之重”,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虽“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虽不能致力于经学研读以建立儒家之“道”,但“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能以“文”合“道”。朱熹正是在对“道”的根本价值的追求中,对屈原《楚辞》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思想意义阐发,“才使《楚辞》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而《楚辞集注》就成为楚辞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3]262-263。
自汉代以来,对屈原的评价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以班固的批评最为代表:“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4]5对此,朱熹坚守经学之“道”予以反击,其《楚辞集注》题序即指出,屈原作品“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2]16,那种忧时伤世、报国无门、矛盾痛苦的感情,正是作者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因此具有内在的感人力量,足以“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2]16。其《楚辞后语序》亦云:“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钜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至论其等,则又必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其或有是,则虽远且贱,犹将汲而进之。一有意於求似,则虽迫真如杨、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2]220-221朱熹认为《楚辞》是屈原“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辞也”,是“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感情的流露,是符合圣人之“道”的人格精神的。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曰:“《楚词》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於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5]4288朱熹认为,《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表达的是“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的遗憾,不是怨君。《朱子语类》亦载:“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褊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语意,所以如此。”[5]4241朱熹认为,屈原的怨君是出于忠君爱国,后人所理解的“骂怀王”是“从头被人错解了”。“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能以“怨君”而“枉屈说了屈原”,这就澄清了屈原《楚辞》的怨君之说,突出了屈原忠君爱国的本质。再次,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多次将扬雄与屈原对比,通过对比来反衬屈原的忠君爱国:“然则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雄乃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至于杨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即从“忠君爱国”的大“道”出发,通过批判杨雄的失节而反衬屈原的忠君爱国。故莫砺锋先生尝总结道:“从‘露己扬才’到‘忠君爱国’,这是屈原人格评价上的一个飞跃,是朱熹《楚辞》研究的最大功绩。”[3]271也正是由经学之“道”的思想出发,朱熹删除了王逸所注四篇作品,认为“《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就其中《谏》、《叹》犹或粗有可观,两王则卑已甚矣。故虽幸附书尾,而人莫之读,今亦不复以累篇帙也。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赋尤精,乃不见取,亦不可晓,故并录以附焉。”[2]183不从体裁形式来衡量,而从情感内涵来考察,正是从“道”研究《楚辞》“文”的佐证。
朱熹认为:“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6]3374在朱熹看来,文是道的自然外露。圣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因此“光辉发越而不可掩”,文章自然就会生成。而在作文的具体实践中,朱熹在强调“道”的根本地位的同时,能将文与道统一起来,既以道为本,又两不偏废。他指出:“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7]1305他认为,“道无适而不存”,文中都有道的存在,所以“即文以讲道”,将文与道统一起来,避免两者脱离,产生既害文又害道的“两失”结果。朱熹正是在吸收了“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与道俱”以及“文以载道”等文道观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文道合一”的文道观。朱熹的“文道合一”观是其文学理论的核心,既十分强调“道”的第一位的作用,又重视“道”与“文”、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朱熹不仅第一个使用“道统”这个名称,而且其“道统”之建构是建立在经学思想基础上的。曾经一度有人怀疑朱熹《楚辞》学作品的真伪。综合来看,朱熹将《楚辞》作为“文”,强调“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认为经学之“道”打通了,“文”自然就流出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朱熹也把《楚辞》当作经来阐释,他在《楚辞辩证·目录》云:“按《楚辞》:屈原《离骚》谓之经,自宋玉《九辩》以下皆谓之传。”[2]182《楚辞集注·序》亦云:“(屈原)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2]16,风、雅是经的六义之二,那么风、雅之末流亦当仍为经,可见朱熹还是把《楚辞》当作一部经学之作来解读。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云:“《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词,大氐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故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董子有言:‘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呜呼,岂独《春秋》也哉!”[2]87《九章》共有九篇,朱熹认为这是屈原在流放期间因为思念君国而创作的一组抒情诗。其中《惜诵》表达自己因为忠直而遭受谗言之意,《哀郢》则是由于“见君而不再得”生出的“恋恋于君”的不舍和哀怨,至于已经有沉江绝世之意的《抽思》《惜往日》《悲回风》等作品,屈原还在担心君王被小人蒙蔽,君德不显。朱熹根据屈原不同的作品所表达出来的不同情感,认为屈原是一个终其一生都“忠君爱国”的完美形象。朱熹特别引用董仲舒的“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这显然是有感而发,将《九章》之解读比照《春秋》经,说明如果不真正理解《春秋》经内在的微言大义,是不可能正确理解《楚辞》的,这也是朱熹作《楚辞集注》的主要原因。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沈圻刊本序中,明代张旭亦云:“窃惟朱子因《离骚》以删定《楚辞》,与孔子之假鲁史以修《春秋》同一心也。《春秋》既作,乱臣贼子知所惧。《楚辞》既行于世,忠臣义士其不知有所奋发哉!”[2]317这里亦将《楚辞》与《春秋》经进行比照,认为朱熹“因《离骚》以删定《楚辞》,与孔子之假鲁史以修《春秋》同一心也。”客观地说,朱熹《楚辞》之“文”确实是与其经学之“道”内在融合的。
二、朱熹经学“探求本义”思想与《楚辞》大义
朱熹云:“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荡旧说,诗意方活。”[8]2758朱熹《答吕子约》亦云:“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 此又是一种工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 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 不要留一宗先儒旧说, 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虫井蛙所以卒见笑于大方之家也。”[9]2213朱熹正是通过对《诗经》“尽去《小序》”“尽涤荡旧说”“唯本文本意是求”的阐释,才促成了《诗经》文学研究的蔚为大观。而在《楚辞》研究上,同样是通过其“探求本义”的经学思想,促使《楚辞》文学研究蔚为大观。胡适曾说:“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10]65对于《楚辞》,“唯本文本意是求”所求的便是《楚辞》自身本是文学的特征。任何对经典的阐释都应该依据文本本身的意蕴来解读,脱离文本的解释只能是“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
《楚辞辩证·九歌》云:“盖以君臣之义而言,则其全篇皆以事神为比,不杂它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则其篇内又或自为赋、为比、为兴,而各有所当也。然后之读者,味于全体之为比,故其疏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有其甚则并其篇中文义之曲折而失之,皆无复当日吟咏情性之本旨。盖诸篇之失,此为尤甚。今不得而不正也。”[2]195朱熹认为《九歌》被后之读者“其疏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更有甚者是对于《楚辞》文本“篇中文义之曲折而失之”,以致“无复当日吟咏情性之本旨”,所以他要“探求本义”以正之。在《九歌》中处处能体现朱子关注文本自身的本义,如《湘夫人》《东君》《少司命》《国殇》《礼魂》五篇的注或序里,均没有牵强比附及任何曲解,而坚持从《楚辞》本身的文本本意出发来阐释。又如《九歌》中《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句,朱子阐释时也是从文本本义出发:“此言湘君既不可见,而爱慕之心终不能忘,故犹欲解其玦佩以为赠,而又不敢显然致之以当其身,故但委之水滨,若捐弃而坠失之者,以阴寄吾意,而冀其或将取之。若聘礼宾将行,而‘于管堂楹间,释四皮束帛,宾不致,而主不拜’也。然犹恐其不能自达,则又采香草以遗其下之侍女,使通吾意之殷勤,而幸玦佩之见取。其恋慕之心如此,而犹不可必,则逍遥容与以俟之,而终不能忘也。”[2]51全文只是在描述湘夫人对湘君的“爱慕之心”和“恋慕之心”,没有一字语及君臣之义等比附之意,乃复“当日吟咏情性之本旨”。
朱子在论经学读书方法时云:“抑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6]2671这里朱熹一再强调他在解读经书时是“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即从文本本身的句读文义升华到“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如《湘夫人》篇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王逸注为“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五臣注为“喻小人用事则君子弃逐”,蒙上了牵强附会的说理气;而朱熹注:“嫋嫋,长弱之貌。秋风起,则洞庭生波而木叶下矣,盖记其时也。”[2]51其白描之文学画面铺现开来。《湘夫人》中“捐余袂兮江中,遗余篏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句,王逸解之为“屈原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犹求高贤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与共修道德也”,五臣注之为“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复背己,无所用也,故弃遗之,杜若以喻诚信:远者,神及君也,”而洪兴祖不仅没有予以纠正,还解之曰:“既治湘夫人以袂褋,又遗远者以杜若,好贤不已也。” 此四句本与《湘君》篇中的“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有异曲同工之妙,朱熹所以只是言简意赅地肯定其文本的真实价值:“此篇首末大指与前篇同”,这里却被各家注解得牵强附会,正体现了朱熹“解经不可乱说,当观前后字义”的解经思路。《楚辞集注·序》云:“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话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2]17可见朱熹肯定的是王、洪的训诂名物成就,不满的是“与其题号离合之间”,而洪兴祖却未能加以“是正”。这里的“是正”正是要还原文本的真实意蕴,也与其经学读书中一再强调切不可以己意来篡改经意,否则会导致把经典文本的本意给曲解的思想一致:“须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虚此心将古人语言放在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11]336
朱熹对文本本身意义的诠释,具体到对词语的解释上也坚持其本义。如《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中”之“内美”,王引五臣注释之为“内美,谓忠贞”,这显然是牵强附会;朱子更之为“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赋我美质于内也”[2]21,显然朱熹释义更贴近文字的本义。又如《湘君》篇:“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中的“吾”,旧注曲之为“屈原自谓也”,洪兴祖《补注》也因袭解为“屈原因以自喻”,而朱熹从文本本义指出:“旧注直以为屈原,则太迫。《补注》又谓言湘君容色之美,以喻贤臣,则又失其章指矣。”[2]196这里文本通篇讲祭祀,朱熹注之为“盖为祭者之词”更为恰当。又如《湘君》篇:“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中的“婵媛”,王逸释之为“女谓女媭,屈原姊也。婵媛犹牵引也”,且把所思念之“君”释为楚怀王,朱熹则指出其弊端:“‘女蝉媛’,旧注以为女媭,似无关涉,但与《骚经》用字偶同耳。以思君为直指怀王则太迫,又不知其寄意于湘君,则使此一篇之意皆无所归宿也。”[2]196旧注太偏离文章本旨,直以为是屈原所作该篇,直接针对的是怀王。所以朱子进一步解释道:“《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为详尽,而为说者之谬为尤多,以至全然不见其语意之脉络次第。至其卒章,犹以遗玦、捐袂为求贤,而采杜若为好贤之无己,皆无复有文理也。”[2]197王逸注附会颇多,而洪兴祖并未给予纠正。朱熹每从语意之脉络次第出发,探求其本来之“义理”。《楚辞辩证》亦云:“《九歌》诸篇,宾主、彼我之辞最为难辨,旧说往往乱之,故文意多不属,今颇已正之矣。”[2]197朱熹从文章本意出发解析《楚辞》,将“最为难辨”“旧说往往乱之”一一正之,足见其“探求本义”之功。
《朱子语类》云:“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是不好。”[5]4290“楚词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5]4291朱熹一再指出不“探求本义”,不真正理解楚词“只是平说而意自长”的文本本义,就反而会造成“文章务意多而酸涩”的不良后果,就会导致《楚辞》“反艰深了”的研究局面。“某患学者读书不求经旨,谈说空妙,故欲令先通晓文义,就文求意”[5]3823-3824,朱熹在其解读经书中一再强调通晓文本本义的根本意义:“探求经文之本义是朱熹平生治经所追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它是治经阐发义理的基础,舍本义而发明义理,为朱熹所不道。”[12]67事实证明,也只有“探求本义”,才能真正探求《楚辞》大义。
三、朱熹经学“沈潜反复”思想与楚辞学方法论
朱熹《楚辞集注·序》云:“然自原著此词,至汉末久,而说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盖未能免,而刘安、班固、贾逵之书,世不复传。及隋、唐间,为训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骞者,能为楚声之读,今亦漫不复存,无以考其说之得失。而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沈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2]16-17
朱熹认为,《楚辞》在汉代时就失去了它的原本“义趣”,甚至连司马迁都不能得其真趣,而刘安、班固、贾逵等人的注解更是不能流传。到隋唐时期,虽然有五六家注释,但也“漫不复存”,只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与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能行于世。综论《楚辞》大义“不见白于后世”的原因,正是因为没有做到“沉潜反复”,嗟叹歌咏,结果导致《楚辞》“性情”与“义理”未能阐发,屈原精神未能发扬光大。而“在研究楚辞时候,正是需要‘沉潜反复’,全身心投入,并且持久用心用力,才会有所得”[13]33。
“‘沈潜反复’是朱熹治学修道的总体原则与方法。”[14]25朱熹认为解读经书皆当“沈潜反复”:“观书,须静着心,宽着意思,沈潜反复,将久自会晓得去。”[11]337其经学著作更是其“沈潜反复”的结晶:“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后之君子。”[15]31朱熹《中庸章句》一篇即是其“沈潜反复”后的成果。而在经学基础上的理学探求也都一再强调“沈潜反复”之方法:“比来为况如何?读书探道亦颇有新功否耶?岁月易得,家理难明,但于日用之间,随时随处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随事观理,讲求思索,沈潜反复,庶于圣贤之教渐有默相契处。则自然见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谓学者舍是无有别用力处矣。”[6]2898只有“沈潜反复”,随事观理,才能与圣人“渐有默相契处”,“舍是无有别用力处矣”。
在朱熹看来,以往《楚辞》注疏之穿凿不通主要是研究者不能“沈潜反复,求其本义”所造成的。
《楚辞辩证》云:“大抵后人读前人之书,不能沈潜反复,求其本义,而辄以己意轻为之说,故其卤莽有如此者。况读《楚辞》者,徒玩意于浮华,宜其于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藴,故余因为辩之,以为览者能因是以考焉,则或泝流求原之一助也。”[2]210-211朱熹认为,“大抵后人读前人之书”,实因不能真正掌握“沉潜反复,以求本义”的方法,而“辄以己意轻为之说”,因此造成楚辞学“徒玩意于浮华”。在这里,朱熹一再强调解经方法的不正确是造成《楚辞》研究穿凿附会、曲证衍说、重复繁琐、不通大义的主要原因。《楚辞辩证》亦云:“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故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今王逸为《骚》解,乃于上半句下,便入训诂,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义而再释之,则其重复而繁碎甚矣。《补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误。今并删去,而放《诗传》之例,一以全章为断,先释字义,然后通解章内之意云。”[2]185自汉以来,注经者往往为解经而解经,牵强附会,以致《楚辞》大义不得其正。朱熹认为王逸注解《楚辞》即不得解经之正确方法,“重复而繁碎甚矣”;而洪兴祖《补注》既不能更正,并且同意其误。针对不正确的解经方法,朱熹注解《楚辞》时以“全章为断,先释字义,然后通解章内之意”。因为在朱熹看来,“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这事实上是朱熹反复涵泳文本,通过“沈潜反复,以求本义”的结果,“克服了他们的重复繁碎、穿凿附会之弊,彻底摆脱了汉儒注经的习气”[2]3。
朱子经学的“沈潜反复”思想,其弟子总结为文学上的“涵泳”说。“涵泳”说是从理学家提倡的解读经书及修养道德的方法脱胎而来的诗学理论。“二程”说: “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朱熹对此多有继承和发挥,其一再强调:
此语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论。且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16]113
如看诗,不须得着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16]2114
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 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16]2114
朱熹重视涵咏《六经》之文,强调“涵泳读取百来遍”后“久之当自有见”,也“方见得那好处”。
客观地说,“‘涵泳’说不仅是把握《诗》之大旨的方法,也是把握《楚辞》‘大义’的方法”[17]76。朱熹经学的“沈潜反复”方法,正是把握《楚辞》文学意蕴的主要方法。
四、朱熹经学“先体而后用”思想与楚辞文体学
汤漳平先生在《闽学视野下闽地的楚辞研究与骚体文学创作》一文中指出,闽地学者产生了一批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研究专著,“如谢翱的《楚辞芳草谱》、陈第的《屈宋古音义》、黄文焕的《楚辞听直》、林云铭的《楚辞灯》、李光地的《离骚经九歌解义》等,均对楚辞学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8]118。在传世的不到110种楚辞学专著中,闽地学者达13种之多。闽地楚辞学研究能有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与朱熹楚辞学创立的传统是分不开的。朱熹楚辞学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重视对楚辞文体学的研究与应用,而其楚辞文体学思想及研究同样源于其《诗经》学等经学思想。
朱熹《楚辞集注》首篇解题《离骚》强调:“按《周礼》:太师掌六诗以教国子,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毛诗大序》谓之六艺,盖古今声诗条理无出此者。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则朝会燕亨公卿大人之作,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其所以分者,皆以篇章节奏之异而别之也。赋则直陈其事,比则取物为比,兴则托物兴词。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属辞命意之不同而别之也。诵诗者先辨乎此,则三百篇者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矣。”[2]20朱熹引《周礼》经书观点证明诗学之六义,强调诵诗者应先“辨体”的文体学思想。在此经学文体学思想引领下,其进一步论述应分辨楚辞文体之“骚体”:“不特《诗》也,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至于语冥婚而越礼,抒怨愤而失中,则又《风》、《雅》之再变矣。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托物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属也。然《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要必辨此,而后词义可寻,读者不可以不察也。”[2]20朱熹认为《楚辞》与《诗经》一样,都运用了赋、比、兴等六义之体。他对《离骚》的所有章节,也都标明“赋也”“比也”“赋而比也”“比而赋也”等。同时从经学六义之“风、赋、比、兴、雅、颂”的思想出发,创造性地通过变风变雅说来诠释骚体的产生与文体特点,并得出“骚则兴少而比、赋多”的楚辞文体学结论。“兼体类以论楚辞者,朱子实为第一人。”[19]199
朱熹不仅强调“辨体”,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不因‘体’的出现的前后而有所偏重,‘体’就是体,形式的文体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20]348其认为:“古人作诗,体自不同,雅自是雅之体,风自是风之体。如今人做诗曲,亦自有体制不同者,自不可乱,不必说雅之降为风。”[8]2736正是朱熹这种不贬视“今曲子”等俗体文学的文体学思想,促成了“楚辞”文体的进一步独立与通俗化,为南宋以降的楚辞文学研究及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创作应用方面,朱熹的诗歌与辞赋创作即引用楚辞的体式、句式、用典以及风格等各个方面,体现了其楚辞文体学“用”的具体实践。如朱熹的《招隐操》《远游篇》《卜居》等作品篇名直接取自《楚辞》中的《招隐士》《远游》与《卜居》,《虞帝庙迎送神乐歌词》则借用了《九歌》的形式。朱熹诗歌中也常用与屈原及楚辞相关的典故来表达情感,屈原及楚辞中的众多篇目和词汇常被化用在其诗歌中:
《离骚》感迟暮,《惜誓》闵蹉跎。(《拟古八首》之六)
故应只有王摩诘,解写《离骚》极目天。(《奉题李彦中所藏俞侯墨戏》)
美人殊不来,岁月恐迟暮。(《秋怀二首》之二)
遥知水远天长外,更有《离骚》极目秋。(《夜闻择之诵师曾题画绝句遐想高致偶成小诗》)
此山岂不幽,何必赋《远游》?(《倦游》)
江妃定许捐双佩,渔父何劳笑独醒!(《江槛词》之二)
弱植愧兰荪,高操摧冰霜。湘君谢遗褋,汉水羞捐珰。(《赋水仙花》)
以上诗句化用与屈原或楚辞有关的典故,或取楚辞中的辞藻,或取其中的风格,都可见出楚辞文体学的内在影响。又如朱熹代表赋作《感春赋》《空同赋》《梅花赋》《白鹿洞赋》等,其中《感春赋》《空同赋》和《梅花赋》属于骚体赋,《白鹿洞赋》正文虽非骚体,但结尾“乱曰”等都带有骚体的典型特征。无论从体裁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可以看到楚辞文体对朱熹赋作的深刻影响。以《梅花赋》为例,其充分吸收了屈原及其骚赋的精髓,在辞藻、句式、体裁、创作因缘上都实得屈赋精义。《梅花赋》从开篇到全文都是对屈赋的吸收和化用:“夫何嘉卉而信奇兮,厉岁寒而方华洁。清姱而不淫兮,专精皎其无瑕。既笑兰蕙而易诛兮,复异乎松栢之不华。屏山谷亦自娱兮,命冰雪而为家。谓后皇赋予命兮,生南国而不迁。虽瘴疠非所托兮,尚幽独之可愿。”“谓后皇赋予命兮,生南国而不迁”,即是化用《橘颂》中“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一句。后如“既奇服之眩耀兮,又绰约而可观”,“与迟暮而零落兮,曷若充夫佩帏”等句中的“奇服”“迟暮而零落”“充夫佩帏”等词都出自屈骚,篇尾的“辞曰”也模仿《橘颂》《招魂》等篇而成,足见朱熹对楚辞文体学体用之深。
朱熹尝云:“来喻所云潄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淡,此诚极至之论,然恐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6]3095-3096其“‘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的提出是针对‘六艺’的”[21]29,即认为必须从经学根源出发把握古今文章体制才能创作好文章,才能挽救衰颓的文风。朱熹“在论理气、道器、无极与太极等理论问题时,往往从体用两方面进行反复论述”[19]185,且“以体用言之,有体而后有用”[22]1763,与其先对楚辞“骚体”进行“辨体”而后应用于诗歌、辞赋等创作的思想相一致。客观地说,朱熹楚辞文体学思想及应用是其楚辞文学的核心内容,并根源于其经学“六艺”思想的转变与成熟,促成了闽地楚辞学乃至中国楚辞文学的发展。
五、结语
正如蔡方鹿教授所说:“朱熹的经学思想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根基。”朱熹的一切思想,“都是建立在他的经学思想基础上”[23]638。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是其楚辞学得以树立新阐释原则和方法的根本原因;朱熹楚辞学研究的新突破,正是根本于其经学思想的新变革。其经学“先体而后用”思想的成熟促成了楚辞文体学的发展,实现了楚辞学从经学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的关键转折。朱熹经学思想与楚辞学的内在联系说明,将经学之“道”与《楚辞》之“文”融合研究,可以从根源上研究朱熹楚辞学的发展与内涵,并进一步认识其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作用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