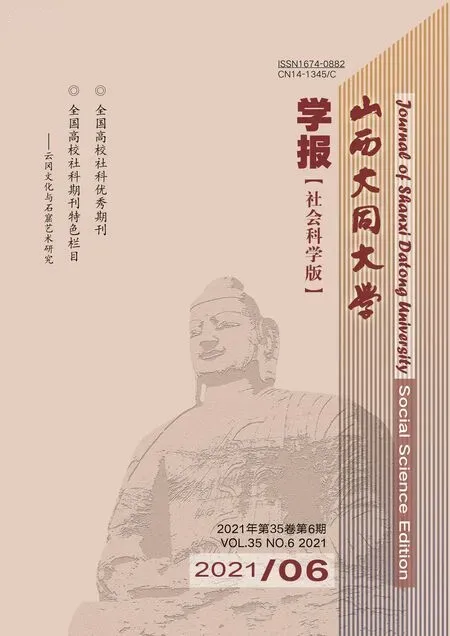语言建构视域下劳伦斯剧作《儿媳》的主题阐释
丁礼明,李照冰
(1.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英国作家劳伦斯以小说闻名天下,殊不知劳伦斯早年是以诗歌和戏剧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他终其一生创作的八部戏剧作品甚至可以比肩长篇小说代表作《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劳伦斯作为戏剧家的地位重新获得世人认可,于是在1965到1969年间劳伦斯的八部戏剧作品在伦敦的各大剧院陆续上演,其中《儿媳》和《霍家新寡》等经典剧目成为英国宫廷剧院的保留节目。2002年劳伦斯的剧作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汇编成集,《D.H.劳伦斯戏剧全集》(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D.H.Lawrence:The Plays)的出版发行足以证明劳伦斯剧作在英国文学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国内学者似乎特别钟情于劳伦斯的小说研究,忽视了劳伦斯戏剧作品的价值。正如黑马所言,劳伦斯的戏剧很难一概而论,他的一些剧本有的太写实,有的则太过先锋,加之被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光环所掩盖,所以一直难以受到切实的研究。肖丽君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劳伦斯戏剧研究专家,她撰写的论文和论著从专业的视角探索了劳伦斯戏剧的语言,却没有把戏剧主题研究和语言建构之间的结合勾勒出来。笔者以为《儿媳》最大的亮点是借助方言对作品展示的无政府主义、阶级观和性爱观主题成功地进行了语言建构,实现了语言和戏剧主题的无缝对接。其中的语言和语言变体为剧作家劳伦斯反映英国阴暗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母子、父女和夫妻)提供了必要的文本支撑。
一、戏剧《儿媳》的缘起和剧本建构
事实上,早在1912年劳伦斯就已经完成剧作《儿媳》的创作,但一直没有公演。劳伦斯去世后的1931年弗里达(Frieda)的妹妹,埃尔斯(Else)重新发现了该剧的手稿,并于1933年归还给弗里达。手稿后来由英国著名剧作家瓦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1903–1974)改编,他不仅改变了原剧本的结构,把原来的四幕剧改成了三幕剧,而且修改了故事的结局。至关重要的是“他修订了剧中的语言,使之更加通俗易懂。”[1](P298)最终该剧1936年以《我儿子的儿子》名字在伦敦各大剧院公演。事实表明,不管评论家针对的是哪个版本,他们发表的所有积极和消极的评论都指涉同一个方向:剧本中的方言口语的运用。不仅如此,评论家普遍认为该剧突出特点是借助方言对话传达出劳伦斯的阶级观和性爱观主题,而语言和语言变体则是剧本《儿媳》呈献给观众的最大艺术特色。正如学者保罗·珀普拉乌斯基(Paul Poplawski)所言:“剧本《儿媳》完全是用方言写作,以至于观众无法跟上劳伦斯的节拍。”[2](P31)无怪乎1936年《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如此撰文评论道:“剧本《儿媳》本身有所欠缺。剧本中贯彻全剧始终的张力让位于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张力,前两幕剧累积的情绪最终得以戏剧性的缓解。”[3](P255)文学界流行着有一种说法暗示着剧本《儿媳》的成功得益于格林伍德(Greenwood)对剧本的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对剧本中方言进行了必要的修饰。而从1967年到1985年间源于剧本的不同制作和上演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评论则集中在劳伦斯的自然主义观点上,同时也专注于剧本呈现出的浓厚家庭氛围,两者都是源于剧中方言口语的成功运用,其他一些评论则直接涉及到剧本中方言口语的运用技巧。罗伯特·威尔切(Robert Wilcher)曾经如此评价:“特里·瓦尔德非常惊讶地发现世人忽略了劳伦斯的剧本《儿媳》的价值。他认为剧中的德比郡方言弥漫着人性的光辉,这是该剧最闪光的地方。”[3](P256)
具体来看,该剧以1912年煤矿工人的罢工为背景,重点在于揭示西方现代生活中社会的阴暗面。作品营造出紧张的家庭气氛,并借助罢工隐喻暗示导致家庭关系紧张的原因,剧本的结尾却是家庭紧张气氛的烟消云散,生活重新恢复了平静。全剧围绕两男和三女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展开。两男是路德(Luther)和乔(Joe),路德和乔是兄弟俩。三女分别是盖斯康妮夫人(Mrs.Gascoigne),米妮(Minnie)和珀蒂夫人(Mrs.Purdy)。盖斯康妮夫人与路德和乔是母子关系,米妮与路德是夫妻关系;珀蒂夫人是波莎(Bertha)的母亲。与小说《儿子与情人》情节类似,剧中女性主宰着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盖斯康妮夫人是家中长者,她虽然出身矿工家庭,但是性格盛气凌人,她最大的优点是没有阶级和等级观念。
国内劳伦斯文学研究专家黑马在2005年的散文集《名家故居仰止》中大加称赞劳伦斯和他创作的剧本。黑马认为劳伦斯虽然以小说闻名于世,但是很有戏剧天分,根据他的剧本《霍家新寡》拍摄的电影实在是一部写实与心理剧的杰作。他的《儿媳》更是独树一帜的英国矿工生活剧。目前这两部话剧都拍成了电影,其浓郁的生活气息,特别是泼辣鲜活的底层百姓的戏剧对白,在英国的戏剧家中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比拟。黑马感叹道:“从方言俚语的角度看劳伦斯对矿工生活的挖掘,其实读他的剧本比读他的小说更有直感和质感。”[4](P298)其实,不管是西方评论家还是国内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劳伦斯剧本《儿媳》的优缺点都集中在作品的诺丁汉郡的方言口语的运用上。
二、《儿媳》中无政府主义、阶级观、性爱观的语言建构
剧本《儿媳》中语言和语言变体大量存在。劳伦斯借此处理剧中生活在阴暗社会背景下的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其中母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不断出现紧张气氛,反映出在无政府主义的外部环境下人们的阶级观和性爱观,由此构建了剧中的主要情节和事件。所以,剧本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阶级观和性爱观是紧密相关的三个主题要素:在不断变换的社会标准下无政府主义思想借助个人主义思潮的推动逐步延伸到阶级观和性爱观,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关联形成全剧主题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一)语言建构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展示 在论及《儿媳》剧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前有必要谈到作家劳伦斯的政治观。学者西蒙·凯西(Simon Casey)撰文指出,无政府主义思想绝不是劳伦斯政治思想的唯一标签。[5](P2)他主张看待劳伦斯无政府主义思想要从作家提倡的凡事应该“自然而然”(spontaneity)的人生观说起。西蒙借用马歇尔·肖慈(Marshall Shaltz)在《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作品》(1971)中观点说道:“作家劳伦斯的中心思想就是宣扬凡事要自然而然,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这与现代工业社会致力构建的有组织结构的规训社会背道而驰。”[5](P2)换句话说,劳伦斯在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所提倡的自然而然地遵从性冲动的主张与无政府主义的信条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剧中的确存在大量的无政府主义话语。剧中主人公盖斯康妮夫人(Mrs.Gascoigne),她的儿子和珀蒂夫人都曾经谴责过公司没有给员工上过保险;米妮(Minnie)指责路德依然是妈咪宝贝,责备他过分地依恋母亲,以及路德没能保持房间的环境卫生和没有努力工作等等。甚至母亲和儿媳之间也互相指责对方:妈妈指责米妮没有照顾好儿子,米妮认为母亲牢牢控制了儿子,路德没有任何自由而言。另一方面,作品中人物所做出的决定似乎都是出于自然而然的行为:米妮写信请求路德娶她为妻,路德立即答应了米妮的请求以及乔决定去澳大利亚的行动都是完全出于自发的行为,不受他人的约束和束缚。作家无意间营造了如此无政府主义话语,人物之间(米妮和母亲)的对话所形成的话语在标准英语和方言口语之间穿梭,由此建构了两个矛盾的世界:规训和有组织纪律的世界和嘈杂无序的社会,文明约束和束缚与原始冲动与本能之间形成的对抗局面。不仅如此,借助人物之间话语的矛盾和冲突剧本的紧张氛围也就顺理成章地建构起来,语言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的鸿沟也就逐渐地被抹平了,反之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联。作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借助剧本中的语言和语言变体逐步地展示给读者和观众。
家庭紧张关系的形成也与人物的话语构成紧密联系。作品中路德参与罢工的情节尤为重要。罢工在剧本中可以被视为隐喻,它暗示着剧中人物之间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本性。比如剧中有这样情节:米妮因故去了趟曼切斯特,回家后花完了所有积蓄。路德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气愤,他怒斥道:“家务活—咦!我们要家干嘛。家务活也参与罢工算了。”(Act III)[6](P59)如此对话表明无论是妻子米妮还是丈夫路德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践行者,他们无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忘记夫妻之间的和睦之道,甚至以罢工作为夫妻争吵的媒介,罢工成为文学隐喻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从人物的角度分析,路德的话语揭示出他的自由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心态: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环境都需要按照顺其自然的法则行事。米妮与妈妈盖斯康妮夫人之间的话语冲突也是剧本刻意渲染的细节。在剧中由于言语不和儿媳米妮可以随意顶撞和责备妈妈,她的大胆言行构成了语言反抗。她由此成为作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言人,她的言行削弱了盖斯康妮夫人的权威,宣布了自己绝对的自由自在,她甚至鼓动丈夫和她一起反抗母亲在家庭中的绝对地位和权力优势,去建构他们自己的自由王国。
(二)语言建构下的阶级观表露 从个人层面上看,作家劳伦斯本人在现实世界中就生活在不和谐家庭中:作家的母亲处在一个文明有序的知识阶层,劳伦斯的父亲所代表的是举止粗鲁和秉性自然的矿工阶层,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结合后矛盾和冲突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劳伦斯父母之间的冲突具体体现在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和言语表达上。同样在剧本《儿媳》中米妮和母亲等其他三个人物之间发生的阶级冲突也是借助语言得以展示的。儿媳米妮出生于上层阶级,言语之中透露出的是身份的特殊,她的标准英文与家庭中其他三位人物的方言口语式英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无疑是米妮和路德结合的唯一途径,也是婚姻把两个不同世界联系起来。
剧本交代了米妮和路德婚姻关系建立的巧合。米妮从路德年方23岁时就一直彼此相识和相恋,米妮出于冲动给路德写信希望路德可以娶她为妻。米妮写的求爱信在作家眼里也是一种话语,不仅揭示出米妮内心的冲突,也是作家阶级观展示的平台。首先,米妮的信件中语言规范,态度中肯,折射出一位出生上层阶级的优越感。这也是为什么她敢于在家庭权威母亲面前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原因所在。其次,作家劳伦斯借此形象弥补了他在小说《儿子与情人》中对母亲形象塑造的不足和欠缺。小说中的母亲与米妮出生相同,但是命运差异明显。剧作中的米妮也是一位年轻母亲,但是她所表现出的反叛勇气和反抗精神是劳伦斯所有作品中“最危险的和最有力量的。”[7](P458)劳伦斯借助米妮信中语言的规范和得体对比路德母亲诺丁汉郡方言口语的粗糙和鲁莽,目的在于揭示出米妮性格中的直爽和坚定。米妮在信中如此表达内心的渴望:“亲爱的路德,我思考了良久觉得我们最好把婚结了吧。我们拍拖了很多年似乎无需再多了解。我们最好现在做个了断,当然你要准确表达内心想法,如果你不情愿就不要勉强自己。”(Dear Luther,I have been thinking it over,an’have come to the opinion that we’d better get married now,if we are ever goin’to.We’ve been dallying on all these years,and we seem to get no further.We’d better make the plunge,if ever we’re going to.Of course you will say exactly what you think.Don’t agree to anything unless you want to.)(ActI,Scene I)[6](P78)路德母亲看到信件后的言语简直是语无伦次了,她冲着米妮大声说道:“恩,小姐,他是下班后拿到信的,我看到他有点犯难。”(Well,missis,he got that letter when he com whoam fra work.Iseed him porin’an’porin’盖斯康妮夫人对儿子路德吼叫:“……如果你想和她结婚你就去吧。”(……If‘er wants ter be married,’er can,an’doesna,’er nedna.)(ActI,Scene I)[6](P79)上面的例证清晰地表明,米妮和盖斯康妮夫人不属于同一阶层,语言表达的差异十分明显,重要的是路德的母亲没有阶级观的概念,这也就为后来米妮和路德的婚事铺平了道路。但是,另一方面这段引文暗示了米妮和路德母亲之间的潜在冲突还是存在的:语言表达的差异必然是思维的距离。而路德对米妮信件的反应是出于自然或者是出于摆脱母亲的控制的愿望,所以他并没有立即把信件拿给母亲看,顺其自然的做法并没有让路德和米妮很顺利地走到一起,也没有促使两个来自同一阶层的路德和巴萨结为连理。由此看来,剧本被营造在社会阴暗面的大背景下,劳伦斯意欲借助对家庭琐事的描述和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揭示潜在的家庭矛盾和冲突;此外,剧本中刻意凸显的1912年工人罢工的爆发暗示了剧本要揭露敏感的阶级冲突话题,凡此种种都在显露剧本《儿媳》的阶级观思想和主题。
剧本还有很多细节描写揭示出作品的阶级观主题。比如路德的阶级属性是通过他的洗浴习惯显示出来。剧中显示“他身上总是有股汗臭味”,不仅如此,他在生活细节上从不讲究。如在剧本第一场的第二幕有如下描写:此刻,路德很快从存放碗碟的地方进入厨房,用块大的搓手毛巾檫脸。他上半身裸露着,他后背的灰尘都没有来得及清洗就跪坐在火炉边开始吃饭,甚至他的头发都没有干,被他随便揉几下。再者,剧本中很多食物英语表达的使用也充分暗示了说话者的阶级身份。丰富的口语语言表达不仅证明民间生活的情调,也表明淳朴人民的智慧。在剧本第一场的第一幕有如下对话:
盖斯康妮夫人:……对男人或女人来说婚姻就像一个老鼠夹子。你很快就会吃光夹子上的奶酪。
乔:嗯,有总比没有好。(ha'ef a loaf's better nor no bread)(Act I,Scene I)[6](P86)
从上述对白可以看出阶级观的问题与性别差异之间形成内在的连接关系,当然也有性爱观的展现。站在盖斯康妮夫人的角度看,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多么的仓促和草率,无需资产阶级的爱情和婚姻来的那么优雅和高贵。老鼠夹子的比喻形象又生动地显示出劳动人民对神圣婚姻的朴素理解,婚姻有时是被迫的而非自愿的行为。而奶酪一词的妙用不仅鲜活地展示了作品的生活情趣,也再次证明了作品的阶级观:盖斯康妮夫人眼中的奶酪仅仅是家庭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它只是简单和普通物品的代言词;相反,有钱阶级眼中的奶酪通常被赋予美好的愿望,是用来表达赞美及爱意的礼物,他们秉承了古罗马时代的奶酪情结。
(三)语言建构下的性爱观呈现 罗伯特·吉利(Robert Kiely)曾经针对劳伦斯的阶级观做过如下评述:“作家劳伦斯并没有真正看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他只发现工人简陋的生活条件在方方面面确实影响了两性关系……在劳伦斯的作品里你不难发现任何一位工人角色在如此条件下不与性爱无关,你同时也很容易找到阶级和性别之间的内在联系。”[8](P91)反观劳伦斯剧本《儿媳》,我们发现性别角色存在于剧本的每个角落:男人对应着女人;妻子对应着丈夫;儿子对应着母亲。他们之间形成了令观众困扰的三角性爱关系:母亲、儿子、媳妇。盖斯康妮夫人独享家中的权势和地位,对儿子的身心垄断无可厚非。剧本中母亲的言语间处处透露出占领意识和控制欲,这导致儿子的独立性比较差和创造力比较弱。母亲甚至视儿子的婚姻对她而言是潜在的威胁。因此她极力控制住已婚的儿子路德和未婚的儿子乔,这些都在暗示男女之间性爱关系的不对称和不协调。国内学者陈新由此总结道:“劳伦斯作品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一种对偶性,相互对立的两极,如男和女、爱与法、太阳与月亮、自然与机械、有机的结构与无定的形状等等。”[9](P94)剧本中显然存在着类似的对偶性两极:儿子(男)与母亲(女)、儿子(男)与妻子(女)。
与此相对应的是剧本中的话语性别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母亲的话语透露出的是霸道和垄断性力量。如下文所示:
盖斯康妮夫人:我想这会儿要不是肚子饿了你是不会回来的。
乔:(坐在沙发上不回答)
盖斯康妮夫人:还不想吃晚饭啊?
乔:有吗?有就吃点。
盖斯康妮夫人:要是没有,那么你就可以不吃喽。小家伙,别说大话。你上午去哪了?
乔:为了钱,我去了办事处。
盖斯康妮夫人:在那你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10](P131)
以上对话选自劳伦斯剧本《儿媳》的第一幕的第一场。母亲在和儿子乔的对话中用了大量的方言口语式英语。(I s’d ha’thought thy belly‘ud a browt thee whoam afore this.)语言粗鲁和不规范性凸显人物性格的豪放和不羁。劳伦斯意在表明,现实生活中是女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性别的角色拥有强势力量,而男性的话语权显然是弱于女性的。如对话中母亲说话时盛气凌人的口气和语言表达的方式和气势都是与常人完全不同的。劳伦斯用在母亲身上的语法句式是有违常规的:Doesn’t ter want no dinner?(还不想吃晚饭啊?),An’if the’isna,tha can go be out?(要是没有,那么你就可以不吃喽),Gen thee nowt!(什么都没给!)
如果说母亲与儿子之间的话语只是性别上的差异造成的,那么夫妻之间的对话凸显的是性爱观的差别。第二幕有如下对话:
米妮:哼!你真的不适合娶妻。你只想让你妈妈哄你入睡。(Pah!-you’re not fit to have a wife.You only want your mother to rock you to sleep.)
路德:妈妈不要,老婆不娶,你也不稀罕,什么人都不需要-不需要。(Neither mother,nor wife,neither thee nor anybody do Iwant-no-no.)(Act II)
该对话发生在夫妻之间,话语简短而有力,显然是夫妻之间发生的激烈争吵时的气话。路德的话语明显表明他内心的态度:他拒绝一切女性的干涉。不管是生他的母亲,还是自己的妻子,甚至其他任何女性都被他抛弃和排斥。最后的两个“no”无疑揭示出他内心的痛苦,他已经受够了围绕在他周围的强势女性,他希望摆脱她们的控制。劳伦斯借助话语的作用不仅把两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凸显了出来,也阐明了自己的性爱观。劳伦斯自己这样表达性爱观:“爱是一种感情赝品。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更矫情,更缺乏真情实感,更夸大虚伪的感情。”[11](P78)所以,劳伦斯在剧本中展示的是最真实的两性关系,路德和米妮之间话语没有过多的言语修饰,更没有缠绵与悱恻,只是夫妻间真实情感自然而然的流露和传达。
借助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劳伦斯戏剧的最大特点是语言和语言变体的运用,尤其是方言口语的大量使用让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不仅如此,劳伦斯在剧本《儿媳》中擅长运用语言和语言变体去建构文本的无政府主义、阶级观和性爱观主题,由此最大限度地挖掘出语言的内涵。评论家认为剧本《儿媳》完成于劳伦斯小说《儿子与情人》,不仅延续了他小说中传达的两性关系的一贯主题,也试图发现解决家庭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方法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