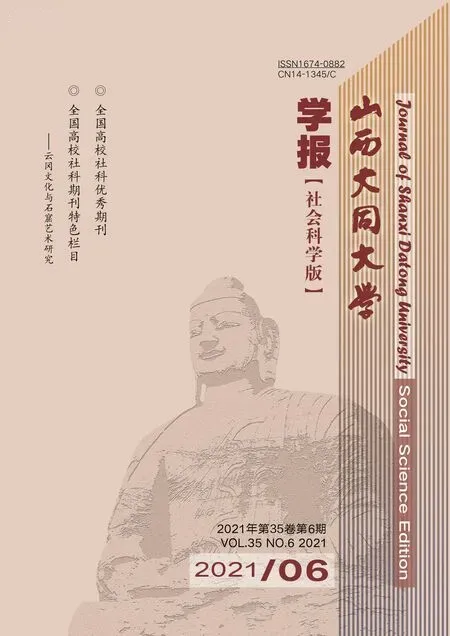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相近犯罪关系之辨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视角
段 丽,郭 辉
(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刑事治理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该罪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三种相近犯罪的适用存在区分难度。研究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三种相近犯罪的关系,厘定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它们各自发挥作用、准确适用的范围,对于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前规定相近犯罪适用的立法与司法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两高等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司法性文件及典型指导案例,使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成为打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主力军,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例,却未搜索到此罪适用于非甲类传染病的先例。即使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相类似的“非典”疫情期间,相关妨害疫情防控措施的犯罪也是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规制。应该说自从1997年修订刑法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本次新冠疫情期间才得以首次、集中、大量地被适用。相似疫情下适用罪名的不同源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前置法与司法解释的变化。
1997年《刑法》吸收了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第35条的内容,在第330条创设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此之前,依据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的规定,有《传染病防治法》第35条所列行为之一,从而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比照1979年《刑法》第178条违反国境卫生检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003年“非典”袭来,由1997年《刑法》第330条规定的结果性要件可知,只有当危害行为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才有可能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而在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中,并不包括“非典”肺炎及其他传染病,国务院也未将“非典”纳入甲类传染病的范围,这就使得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不能适用于“非典”肺炎疫情的防控当中。为解决该类犯罪无法可依的问题,最高法、最高检于2003年5月13日出台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以公共安全为切入点,在第1条中规定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传播“非典”肺炎,从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规制。《解释》的出台,使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规制“非典”疫情期间的妨害疫情防控措施犯罪的主要罪名。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修改,删除了第3条中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的规定,并在第4条创设了“乙类传染病的甲类管理制度”,即采用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来管理符合条件的乙类传染病。在此之后,最高检、公安部于2008年6月25日出台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追诉标准(一)》),第49条明确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可用于“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案件的追诉当中,自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于鼠疫和霍乱之外的疫情防控成为可能,但此规定有类推之嫌疑。
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国家卫健委第1号公告出台,第1条将新冠肺炎定性为采取甲类传染病管理措施的乙类传染病。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公安机关大多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相关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了有力打击犯罪、更快控制疫情,2020年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司法性文件《意见》。《意见》的第2条对罪名的适用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故意传播新冠肺炎病原体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规制,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其他的妨害疫情防控从而导致病毒传播或者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定罪处罚。
《意见》的出台,使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有了更加明确的依据,但也引发诸多争议。在当时的《刑法》第330条中,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所需的结果性要件仅包括“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就国家卫健委2020年第1号公告来看,新冠肺炎并未被定性为甲类传染病,而是被定性为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在这种情况下,《意见》直接将相关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置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制的范围之内,存在规范对应上的模糊性,与上文2008年的《追诉标准(一)》一样,有类推之意,并导致了《意见》的规定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争议。
为进一步规范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和解决争议,《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7条对该罪进行了修改,将“引起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或传播严重危险”纳入到《刑法》第330条所规定的结果性要件当中……将第1款第4项中“预防、控制措施”的制定主体卫生防疫机构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机构。
对于刑法中的自然犯的理解通常要侧重于其字面上所体现出来的含义,而对于法定犯的理解则要兼顾到前置法中的相关规定。[1]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作为典型的法定犯,对其的理解和解释当然要到前置法中去寻找依据。依据《刑法》第330条的规定可知,甲类传染病的范围由《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该表述自1997年被写进《刑法》,一直到新冠疫情发生未曾有过改动,但作为前置法的《传染病防治法》则经历了数次修改,关于“甲类传染病”的相关表述也发生了变化。这就导致《刑法》中的“甲类传染病”与前置法中的“甲类传染病”出现规范对应上的模糊性。
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在规定“甲类传染病”包括鼠疫和霍乱的同时,赋予了国务院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的权限,国务院可以根据相应的标准,将其他符合条件的传染病定性为“甲类传染病”,从而使得在鼠疫和霍乱之外,被定性为“甲类传染病”的其他传染病处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制范围之内。由于《国际卫生条例》中的甲类传染病仅包括鼠疫、霍乱和黄热病,作为《国际卫生条例》的缔约国,为加强与世界各国对传染病的共防共治,国务院不但没有增加“甲类传染病”的种类,还于2004年修改《传染病防治法》时取消了其调整甲类传染病范围的权限,也造成了诸如新冠肺炎这样的“乙类甲管”传染病是否是《刑法》中的“甲类传染病”的适用难题。
法律具有滞后性,但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当相关前置法受制于国际条约的制约不便于修改时,司法解释的扩大处罚必然引起理论界的争议,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刑事立法的及时跟进。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如果排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不仅违背刑法保障社会正义的理念,而且对于疫情防控也是极为不利的,从这一角度分析,《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是一场及时雨。
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认定为过失危险犯
关于该罪主观罪过的观点有“故意说”“过失说”和“混合罪过说”。笔者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只能是过失。然而,将本罪主观罪过认定为过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刑法》第15条第2款中的“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二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过失犯罪只处罚结果犯而不处罚危险犯”在新兴传染病犯罪领域是否仍然适用。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刑法》中“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表述是一种“提示性”规定,意在强调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显然要低于与该过失犯罪相对应的故意犯罪,并不是所有的过失行为都要被定罪处罚,只有当其社会危害性达到刑事可罚性程度时,才可以对其定罪处罚。虽然《刑法》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未做出明确规定,但将其认定为过失犯罪也不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障碍。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我国是否存在过失危险犯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与故意犯罪相比,过失犯罪本身已经降低了入罪要求,扩大了处罚范围。在此种情况下,又把过失行为导致的危险状态纳入到刑法处罚的范围当中,此种做法的后果会导致刑罚适用泛滥、刑法谦抑性原则受损。[2]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风险社会已悄然而至。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必须重新审视传统刑法理论在诸如传染病犯罪等新型犯罪治理中的作用。就新冠肺炎疫情来说,由于其传播的快速性、隐蔽性以及对人类健康的巨大危害性,已经使得其与传统过失犯罪的成立有所不同,一旦实害结果发生,后果非常严重而不堪设想,因此,有必要设置为危险犯,将成立犯罪的条件提前,以加大对犯罪的预防功能。加之传染病犯罪因果关系认定具有复杂性,妨害疫情防控措施与造成新冠肺炎传播的因果关系认定难上加难,设置为危险犯,评价危险的产生比证明引发传染病传播后果的难度有所降低,利于对此类犯罪行为的打击。
就“引起新冠肺炎传播严重危险”来说,这种具体危险状态也与传统犯罪中的具体危险状态不同。在传统犯罪领域中,具体危险状态只是造成了一种现实紧迫的危险,最终并未转化为实害结果,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只要有“引起新冠肺炎传播严重危险”的具体危险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转化为“引起新冠肺炎传播”的实害结果。《刑法》未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害结果和具体危险结果规定不同的法定刑,足以表明该罪具体危险状态与实害结果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如果仍将“过失犯罪只处罚结果犯”的观点应用于传染病犯罪领域,危害的将不单单是司法效率,更是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罚适用的不得已性,而非要求刑法体系只减不增,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刑法必须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调整。[3]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认定为过失危险犯并不违背谦抑性原则,这正体现了刑法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的机能。
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适用
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行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一致性,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容易混淆两罪的适用,因此需要对两罪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做出辨析。有观点认为,《意见》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格主体须为经医疗机构根据诊断标准所确定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病原体携带者和疑似病人,除此之外的主体不能以该罪进行规制。[4]依据该观点,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格主体也应是经医疗机构依据诊断标准所确定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病原体携带者和疑似病人。此外,《意见》规定了两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结合该观点,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行行为也应限于《意见》规定的这两种行为。由于过失犯罪需要造成法定的危害结果,所以在新冠疫情中,除了要符合上述主体与行为条件外,要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需造成新冠肺炎传播的实害结果,并且该实害结果危害了公共安全。
笔者认为,在新冠疫情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体并非只限于经医疗机构确定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病原体携带者和疑似病人,还应当包括那些在医疗机构诊断前就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的行为人。上述观点表面上看是在限缩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实际上与刑事法理和疫情防控需要相违背。对于那些在医疗机构作出认定前就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的行为人,其人身危险性并非只有在医疗机构做出确诊通知之后才会产生。在新冠肺炎爆发的初期,由于多方面客观原因的限制,出现了感染新冠肺炎却不能被医院收治的现象,这类“新冠肺炎患者”只能自我居家隔离。在自我居家隔离期间,若其怀着“若我是新冠肺炎患者,我也要传染给其他人的心态”进入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故意接触不特定多数人,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然已经达到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处罚标准。我国《刑法》中的身份犯,指的是在行为时具有该身份,那些在医疗机构确诊前就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的行为人,在客观上完全符合“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身份,故不能因为“程序上未确诊”而将其排除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处罚范围之外。在疫情防控中,由于医疗机构对确诊和疑似病例所采取的是定点隔离收治的措施,通常这类主体反而是没有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机会,而那些未经医疗机构确定前就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的行为人,却因其未被隔离收治而可以出入公共场所。《意见》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体的规定并非全部罗列,其更多意义上应视为是一种提示性条款。况且2003年《解释》并未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体进行限定。所以在新冠疫情下,只要故意传播新冠肺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就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与此相一致的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体亦并非仅包括经医疗机构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体携带者和疑似病人,还应包括在医疗机构确诊之前就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的行为人。
由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主体、主观罪过和实行行为相同,并且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要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所以在新冠疫情下,“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的行为人若因实施违反疫情防控要求的行为而过失导致新冠肺炎传播,并且被感染者是危重症患者或因感染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这两个罪名的处罚标准。也就是说,在上述情形下,两罪出现竞合关系,并且是交叉型的竞合关系。有学者认为,由于公共安全法益重于其他法益,故适用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为合理。[5]笔者认为,由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两罪所侵犯的法益在实质上并没有区别。由于传染病犯罪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证明方法的特殊性,适用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规制将产生因果关系证明上的困难。此外,虽然两罪的最高法定刑一致,但刑法第330条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有“后果特别严重的”规定。该处的“后果特别严重”应当包括传播的危险与传播的实害两种结果,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结果只限定为严重的实害结果,由此推知,前罪比后罪量刑更重,所以,对于两罪的竞合处理,笔者建议应按照“重罪优于轻罪”的原则,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规制。
四、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区分适用
在1997年的《刑法》之前,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行为是比照1979年《刑法》第178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的。现行《刑法》第332条对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作出了规定。在疫情发生后,为加强国境口岸的防控力度,最高法、最高检等五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五部门意见》),其中第2条对该罪的适用情形作出了细致的规定。由于立法层面的缘故,两罪在诸多方面存在交叉,所以新冠疫情下,两罪在适用中容易出现混淆,故需对两罪的异同点进行区分。
《五部门意见》规定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主体为检疫传染病染疫人和染疫嫌疑人,对于该类主体的认定,是否需要经过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笔者认为是不需要的,通常关于犯罪主体身份的界定是以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的时间为节点,如果在实施危害行为时不具备特定的身份,而在之后的时间具备该身份的,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备犯罪所需要的特定身份。同理,如果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就已经具备了特定身份,只不过该身份需要在后续的程序中所认定,那也应当认定该行为人具备犯罪所需要的特定身份。故该罪的主体应当是在实施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时,在客观上就已经感染新冠肺炎或者接触过新冠肺炎的感染环境并可能传播新冠肺炎的人。故在这一类主体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具有一致性。除此之外,两罪主观罪过都为过失,即对行为“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持过失心态。
由于两罪都属于法定犯,故构成犯罪都需要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前置法的行为。两罪的主要前置法分别为《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境卫生检疫法》。在行为类型上,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不同的是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行为人主要是实施了违反海关依照国境卫生检疫法提出的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包括拒绝执行健康申报、体温监测、疫学排查或隔离、留验、就地诊验等抗拒行为以及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等隐瞒行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客体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和“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客体为“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和“国境卫生管理秩序”。
由以上分析可得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主要适用于出入境传染病检疫过程中,然而,那些实施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而进入境内的行为人,若其在境内隐瞒疫区停留史、密切接触史以及违反规定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若发生法定的危害后果,是适用前罪,还是适用后罪?抑或是用两罪进行数罪并罚?有观点认为,由于两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同的,所以应将两罪名合并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相关犯罪行为一律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6]笔者认为,在传染病防控领域,国境检疫与境内防控是两个不同的防控环节,《刑法》之所以规定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是因为国境关口作为传染病输入与输出的第一道门槛,对防控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当两罪互相配合,对疫情防控中的不同领域进行全覆盖,才能达到不遗不漏的防控效果。上述问题中的行为人,实际上其犯罪行为触犯了这两个罪名,但由于造成同一个法益侵害结果,故只能在两罪名中,择一重罪处罚。
在丁某某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7]中,丁某某在填写《入境健康申明卡》时隐瞒自身咳嗽、乏力等症状的行为是对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违反,其后多次乘坐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具有引起新冠肺炎传播的严重危险。由于其隐瞒自身咳嗽、乏力等症状的行为发生在海关对其检疫的过程中而非发生在境内新冠肺炎防控过程中,所以丁某某只涉嫌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在郭某鹏妨害传染病防治案[7]中,公开资料未显示郭某鹏在入境时实施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但在其回到郑州后违反《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第21号》中关于“隔离观察”的规定,进入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并在民警核查时未“如实申报”,造成了新冠肺炎严重传播危险。由于郭某鹏、郭某玲违反“隔离观察”和“如实申报”的行为发生在境内疫情防控过程中,故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若郭某鹏在入境前就已经出现发热、咽痛等症状,并在入境时隐瞒自身症状,就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由于前罪的法定刑高于后罪,故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