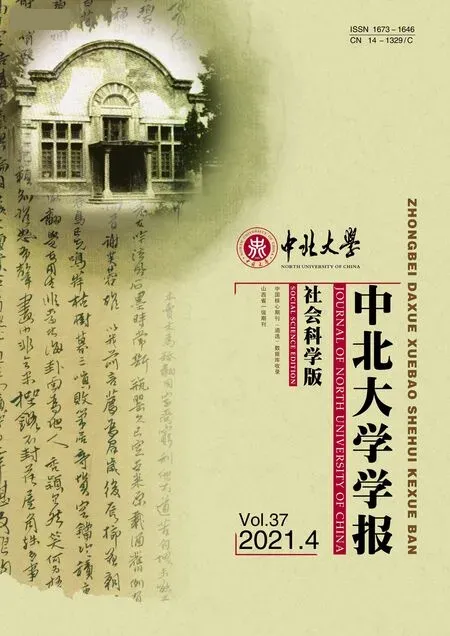“古淡”范畴的诗学内涵及其嬗变
邵康慧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古淡”最早出现在韩愈的《醉赠张秘书》一诗中:“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1]215但在其流传过程中,真正使它得到充分阐释并进入更宽广的批评视野,是在有宋一代才逐渐完成。先由北宋前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在论梅尧臣诗时指明,开启了其后绵延不断的讨论。然而,在学界对宋代尚“淡”的审美取向有所共识的背景之下,“古淡”的涵义往往被“平淡”“淡泊”等习语所模糊和掩盖。本文拟将此作为论述起点,探讨“古淡”范畴的诗学内涵。
1 从“平淡”到“古淡”:梅尧臣的个人诗学
元人龚啸谓梅尧臣诗“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 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2],对梅尧臣诗歌的艺术特点与文学史地位都作了较为客观的界定。刘克庄《后村诗话》亦云:“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 尹之下。”[3]22梅尧臣与欧阳修、 尹洙等人对矫正五代诗风、 复古明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作方面,他受到欧阳修的推重,二人唱和不断; 而对梅诗最为精准的评语,也正来自于欧阳修。
梅早年学韦,南宋朱弁《风月堂诗话》云:“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世人咀嚼不入,唯欧公独爱玩之。”[4]2951及至晚年,仍有肖似之作。其诗底色清淡,取道便与昆体区别开来。严羽《沧浪诗话》云:“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5]8这是看到了梅诗萧散闲远的一面。但梅尧臣若仅止于“学唐人平澹处”,未免不足以称其为宋调的“开山祖师”。
自景祐元年(1034年),梅尧臣开始在诗中更多地表现日常题材,学古的范围也变得相当广泛。[6]250-251《答裴送序意》:“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曲曲物象磨穷年。”[7]300梅尧臣承认作诗的过程艰苦,语辞简陋,但是自己学古的眼光要深远得多。他在多首诗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如《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梅尧臣对近世空摹物象的纤巧经营持否定态度,并上溯诗骚传统,欲以此振兴诗道,用心可谓专深。
在梅尧臣逝世后的第二年,欧阳修作《梅圣俞墓志铭》,对其诗风的嬗变过程作了相当准确的概括:“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7]1157《宋史·文苑传》评梅“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7]1159,亦本欧说。到了晚期的成熟阶段,梅尧臣诗歌臻于老境,变“平淡”为“古淡”,向艺境高处更迈进了一步。从其个人诗学的历时角度来看,变化相当明显,“古淡”范畴的内涵较“平淡”更具深意,单纯地将二者混为一谈,显然不妥。朱东润先生认为“把尧臣的作品归结为平淡,不但不符合梅诗的实际情况,也是违反尧臣的主观要求的”[7]29,当包含这方面的思考。
正如他所言,梅的性格其实颇具斗争性。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7]845论者多引此句为其创作主张,却忽视了这句诗首先是对邵不疑诗作的评价,诗末的落点则是在“既观坐长叹,复想李杜韩。愿执戈与戟,生死事将坛”[7]845。《正仲见赠依韵和答》云:“我愚希六义,将使鬼神感。譬彼捕长鲸,区区只持罯。青天挂虹霓,踊跂不可揽。太华五千仞,妄学巨灵撼。”[7]717这使我们联想到韩愈的“险语破鬼胆,髙词嫓皇坟。至宝不雕琢,神功谢锄耘”[1]517。“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1]517梅尧臣辗转多师,在崇古、 学古的过程中所树立的典范,助其在闲肆平淡的基调上,从深沉古意中更翻新声。后来,着力仿梅的陆游就曾说“歌诗复古,梅宛陵独擅其宗”[8]2113,更独具只眼地标举梅诗律“雄浑”[8]545。其《读宛陵先生诗》云:“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锻炼无余力,渊源有自来。平生解牛手,余刃独恢恢。”[8]1452可以说是把握住了梅尧臣在学习前人时的一部分自我期许。
总之,要想准确理解“古淡”的内涵,首先需要意识到:它是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中获得其自身阐释力的,在平和淡远之上,还有着对雄奇诗风的复古与学习。
2 融入“平淡”的“古淡”:诗学范畴的历时演进
最早使用“古淡”一词来评价梅尧臣诗歌的人即欧阳修。庆历四年(1044年),他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中并举苏梅:“近诗尤古硬(淡)(1)“硬”,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 《四部丛刊》影印元代刻本校:“一作‘淡’”。此处宜作淡。一来,如李逸安先生在《欧阳修全集》前言中所说:“欧阳修著作中的异文较多,主要是他对自己的作品常反覆修改的结果。对这些异文,尤其是欧阳修亲手编定的《居士集》中的大量异文,周必大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基本上予以保留。”二来,如下文《再和圣俞见答》,唯“古淡”而未见异文,可与此处互见。,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9]29他以橄榄回甘作喻,“古淡”起到桥梁的作用,连接诗歌的阅读体验与感官上的味觉经验,形成生动的印象,揄扬梅翁诗艺精进,传情达意越发老到。皇祐二年(1050年)《再和圣俞见答》:“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虀。”[9]82可见,欧阳修使用“古淡”一词论梅诗,不一定直接来源于韩愈,很可能也受到梅尧臣观点的影响。此时的梅尧臣年近半百,诗名早已遍传,“古淡”在诗学上的审美价值是他所褒扬的,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也得以较好地呈现。
欧梅之后,苏轼留下大量理论文字,进一步深入阐释了“古淡”的诗学内涵,以其形象、 精当等特征,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苏轼先以书喻诗,“予尝论书,以谓钟、 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于诗亦然……李、 杜之后,诗人虽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 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10]2133。又引司空图诗论“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10]2133。这与“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虀”的意思有相通之处,真味不在味中,而在味外,在“无味”——即“淡”之中。后人承苏轼之语,多有阐发。但在这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古淡”之“古”,多谈“淡”之一味。追溯其源,较有代表性的两则分别是“平淡”与“枯淡”。
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11]348
——周紫芝《竹坡诗话》
中国的文论传统对“味”的引入始见于六朝。从生理层面的经验到心理层面的认知,逐渐成为一个囊括深广的批评范畴。钟嵘《诗品》称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联系他在《诗品序》中所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是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这里的“平淡”实含贬义。[12]115而到苏轼,则指向臻于老境后的浑成。过尽千帆,方自绚烂归于平淡。梅尧臣《依韵和晏相公》云“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7]368,便描述了欲达于此境的艰难不易。宋人李纲有诗:“秋髙气倍清,夜静舟初泛。露华浩如洗,月色寒可鉴。林峦与邑屋,左右入轩槛。晶荧星影揺,崷崒山光蘸。风微烟羃羃,溪远波湛湛。端疑客乘槎,坐使云河犯。观梁且停桡,恋月愁系缆。景幽费摹写,思妙造古淡。吾方久于此,胜赏岂云蹔。愿同二三子,险韵时得探。”[13]147系与友秋夜泛舟,即目所感,分题得一泛韵。用语素朴,“景幽费摹写”说得老实,直到最后三联无景可写,以“思妙造古淡”自白,并表达了时与诸人切磋诗艺的愿望。明人姚广孝读韦应物诗,云:“交游泉石间,感物自成诗。古淡岂易学,五字真吾师。”[14]618同是感物成诗,然而“古淡”难成。稍不出于自然,不可谓古淡,若露一毫牵强,便落了下乘。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站在接受者的立场来看,若诗耐咀嚼,可以含玩不尽,那么,读者亦能收知言之乐。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 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乾枯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10]2124
——苏轼《评韩柳诗》
苏轼称道的“枯淡”,外枯中膏,需分中、 边。清初贺贻孙更进一步品评陶诗“真而不厌”。“何以不厌,厚为之也。诗固有浓而薄,淡而厚者”别出心裁地点出“浓而薄”与“淡而厚”这两种“似浓” “似淡”之诗的深层不同,很是恰切。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这段文字更大程度上是站在了“食客”的角度,或者说对鉴诗者提出了区分“中边”的要求,更直言有此品味者的数量之稀少。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记东坡语云:“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15]71俗人不爱,而对于有能力的读者,自放于其余味和远韵,不失为适心娱性的快事,所谓“借得新诗连夜读”是也。钱锺书指出,《邵氏闻见后录》所云“圣俞诗到人不爱处” 即用此语。[16]116
反面言说,难知难造,淡而有味——就上述的几个特点而言,“古淡”自然与“淡”这一批评序列的其他术语共享类似的感官体验。但“古淡”的“古”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批评对象的替换:“淡”开始更多地偏向对陶诗的评价。一来陶渊明之“古”不必强说,二来宋初文坛的复古反拨也为本朝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朱自清先生认为:“平淡有二,韩诗云‘艰宕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梅平淡是此种。朱子谓‘陶渊明诗平淡出以自然’,此又是一种。”[16]167欧阳修曾记梅尧臣即席赋河豚,云:“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难。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9]265对梅诗古淡诗风的界定显然属人为一类,而与天然之作拉开距离。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苏、 李之天成,曹、 刘之自得,陶、 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 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10]2133这与他所说的“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 刘、 鲍、 谢、 李、 杜诸人,皆莫及也”[17]1402,若合符节。问题是,当自然神奇作为一种风格特点被置于历史中考量时,其往而不返的走向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尽管苏轼的铨论背后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理论依托,人们对“平淡天成”这样的结论,其接受度之高,在某种程度上盖过了推究其所以然的兴致。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引《西清诗话》云:“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18]403崇陶已极。此后“古淡”除了不时以梅诗定评的面貌出现,主要便被用来形容陶诗。北宋黄裳《书子虚诗集后》云:“趣古淡则为陶潜,趣飘逸则为李白、 杜牧。”[19]272南宋赵善括《赵清献帖跋》云:“陶彭泽之诗,发言古淡,诵其言,则知其忘机械,脱风尘,邈乎其远矣。”[20]9元人邓雅《读姚子深寄娄良器诗因述古作者之意次韵》云:“坡翁学陶得三尺,古澹中含温润色。”[21]元好问《闲闲公墓铭》云:“至赵秉文之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22]269刘仁本《送物元阜上人序》云:“其所作五言诗多清适古淡,得陶靖节体。”[23]316清人纪昀在《瀛奎律髓刊误序》中指出:方回“选诗之大弊有三:一曰矫语古淡……夫古质无如汉氏,冲淡莫过陶公。然而抒写性情,取裁风雅,朴而实绮,清而实腴。下逮王、 孟、 储、 韦,典型具在。虚谷乃以生硬为高格,以枯槁为老境,以鄙俚粗率为牙龈,名为尊奉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是可以为古淡乎”[24]1826,其实取义仍近于“平淡” “冲淡”。
至此,再回头看发端于韩、 梅的“古淡”。一方面,江西诗派将苦心锤炼发挥到了极致,并以杜甫为尊,梅尧臣已经不显。另一方面,梅尧臣的“古淡”风格,尤其是在他对创作进行实验与过渡的时期中写就的一些苦硬涩重之作,后人并非一片叫好。朱熹就认为:“圣俞诗亦不得谓之好……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25]3113从《与程允夫书》中拈出的可法典范来看,朱熹也只推重“冲淡”:“某闻先师屏翁及诸大人先生皆言: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耳。盖不如是,不足以发冲澹萧散之趣,不免于尘埃局促,无由到古人佳处也。如《选》诗及韦苏州诗,亦不可以不熟读。近世诗人,如陈简斋,绝佳,吴兴有本可致也。张巨山愈冲澹,但世不甚喜耳,后旬当录寄一读。”[26]4878就这样,“古淡”随着代际推移,被赋予着新的外延,其涵义侧重也由之发生偏转。
3 元明清三代的“古淡”批评
前文已经谈到,“古淡”在有宋一代基本完成了它在内涵上的变迁。宋末文人姚勉在《汪古淡诗集序》中就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古淡”的所指。
“张籍学古淡,轩昂避鸡群。”退之语也。武宁汪子载善诗,乡之邢吏部,以古淡名之。盖以其似张籍,虽然诗而已哉。有道味,有世味,世味今而甘,道味古而淡。今而甘,不若古而淡者之味之悠长也。食大羮,饮玄酒,端冕而听琴瑟,虽不如烹龙炰凤之可口、 俳优郑卫之适耳而饫则厌,久则倦矣。淡之味则有余而无穷也。为今之人甘可也,欲为古之人,其淡乎。惟古则淡,惟淡则古。周子曰:“淡则欲心平。”子欲追古人之淡,夫苟无欲,则于道庶几矣,诗安足论哉?张籍岂足为哉?[27]430
汪子载以古淡自推,姚勉便针对“古淡”谈论了自己的观点。这段文字一是突出了世味、 道味有别,古与今有别:“世味今而甘,道味古而淡”“为今之人甘可也,欲为古之人,其淡乎”。二是指出甘、 淡给人带来的审美感受不同,淡者余味无穷,而珍馐美馔、 郑卫之音,美则美矣,日久易生厌倦。三是强调了“古”与“淡”的关系,“惟古则淡,惟淡则古”,二者间是充分且必要的关系。最后姚勉引周敦颐“淡则欲心平”之说,发挥其理学思想,复将“道”郑重提出。老子有云:“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庄子主张:“游心于淡,合气于漠。” 姚勉说:“子欲追古人之淡,夫苟无欲,则于道庶几矣,诗安足论哉?张籍岂足为哉?”[27]430与韩愈所谓“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 通其辞者, 本志乎古道者也”[28]305含义相近,体现的都是对道统的追求。因此,可以说这段话实际上只是以谈诗为引,但他提出的几个观点都值得注意。首先,是对现时所处环境的不满,“世好竞咸辛,古味殊淡泊”。道丧文弊,浮靡不振。其次,是对淡而有味的辨析,前文已作讨论,在此不赘。最后,对“古”与“淡”的关系有充分关切。姚勉言此二者同时并存,相互对应。很少有其他人作如此直接明了的判断,可备一说。
宋代之后,“古淡”开始受到广泛运用。作为一个风格论的范畴,它不再停留于对具体某一位或极个别诗人的指认。
首先,在进行古淡批评时,于诗体层面自然显现出上溯古体的倾向,多与五言并提。如元人邓雅以“五言推古淡”论陈尚泰诗。[21]且“古淡”一词本身即非常直观地体现出复古、 崇古的倾向,有时评论者基于其所处时代或流派,对此“古”所论范围有更进一步的规定。如仇注杜诗《寄高三十五书记》:“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一联云:“三百篇为诗法之祖,嗣后作者继起,文以代新。而诸体各出,莫不有法存焉。” 随后,又引徐祯卿所言诗之各体:“吟咏情性,总而言志,谓之诗。苏李而上,髙简古澹,谓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谓之律。”[29]194以“高简古澹”为古诗之法,对诗歌时代及体裁有明确的指向。清人王士祯编《古诗选》,其中汉魏六朝的五古入选作者达百位以上,而唐代入选的仅五人,他在“凡例”中说:“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 晋之风骨,变梁、 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贞元、 元和间,韦苏州古淡,柳柳州峻洁。今辄取五家之作,附于汉魏六代作者之后。”[30]93盛极之后,五古逐渐显现出衰微之态,而批评者对“古淡”的使用也趋向这狭隘的一条道路。清人朱庭珍云:“五古以神骨气味为主,愈古淡则愈高浑。”[31]2334较之五言,七言一般更为曲折多姿,要求气力贯之,便较少用到“古淡”作批评。胡应麟就屡以“壮”“丽”评论七言律,且明确提出“淡”与之不相谐合。其言:“七言律,壮者必丽,淡者必弱。唐孟襄阳、 张曲江,明徐迪功、 高观察,诗皆以淡为宗,故力皆屈于七言。古今七言律,淡而不弱者,惟陈无己一家。然老硬枯瘦,全乏风神,亦何取也。”[32]218谓陈师道用力过度,滑向硬语枯淡的极端,反失丰采。又云:“宋之为律者,吾得二人。梅尧臣之五言,淡而浓、 平而远; 陈去非之七言,浑而丽、 壮而和。梅多得右丞意,陈多得工部句。”[32]206
其次,“古淡”开始被用来品鉴诗歌中具体的某一句或一联。元人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便屡屡使用,如评陆游云:“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云:“三四古淡。”[24]496胡应麟评张耒“更老心犹在”云:“第五句最古淡。”[24]507明人胡应麟所编《诗薮》中多处以“古淡”评储孟、 老杜,如评老杜云:“杜七言句……壮而古淡者,‘百年地僻柴门回,五月江深草阁寒’。”[32]93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评《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物役水虚照,魂伤山寂然”云:“五六古澹有味。”[33]473
胡应麟评王维云:“右丞五言工淡、 丽闲,自有二派。‘楚塞三江接’ ‘风劲角弓鸣’ ‘杨子谈经处’等篇,绮丽精工,沈宋合调者也。‘寒山转苍翠’ ‘寂寞掩柴扉’ ‘晚年惟好静’等篇,幽闲古淡,储孟同声者也。”[32]66先言“工淡”“丽闲”为王维五言之“二派”,随后各举三篇来充实论点。但此时他使用的形容词“绮丽精工”和“幽闲古淡”,分明是将“工淡”“丽闲”拆散后重新糅合,“工”与“丽” “淡”与“闲”组成了新的范畴,体现了论诗的含混之处。不过工者可以丽,亦可以淡; 丽者亦闲淡皆可。本出于一,未尝不能自圆其说。古淡批评的操作显得愈加灵活、 自如。
清代佚名所著《杜诗言志》注《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一诗云:“此诗无寓意,只质言其事。然简洁古淡,求之汉魏,惟靖节能之。学者当观其情致之绵邈、 描写之灵秀、 用笔之骀宕、 琢句之整洁、 炼字之工稳。如入武夷九曲,纤尘不到,应接不暇。”[34]31诗歌直指陶靖节,渊源有自。原诗通篇言事,意象串联。注者将其风格概括为“简洁古淡”,随后一一点出后生可学之处,从情致、 写意到笔法、 字句,实指颇多。至此,“古淡”作为诗学批评中的常见范畴,其内涵之丰富,已不待明言而呼之欲出。此外,“古淡”在被用以进行诗学批评而逐渐上升为固定短语的同时,有意无意间也被赋予了体现诗人人格气质的作用。明末吴嘉纪诗效孟郊、 贾岛幽峭冷逸,王士祯称其“苦吟不交当世。予见其为五言诗,清冷古淡”[14]2865。实际上,唐初已用“淡”或“平淡”论人,如《晋书·杜夷传》之“夷清虚冲淡”,《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之“袁翻才称淡雅,常景思标沉郁,彬彬焉,盖一时之俊秀也”[13]116。而“古淡”则要到中唐乃至有宋一代后才加入以“淡”为核心的系列范畴之中,直接用以论人的用法也不多见。例如《唐阙史》中“路舍人友卢给事”一则,云:“路舍人群,与卢给事弘正,性相异,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尝言朝市; 夕拜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35]241又如《北梦琐言》云:“陇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质气古淡。”[36]48
4 馀 论
由于淡味难以言表,古人欲表现味之淡薄时,常援用味之浓重,以其反面辩证言之。苏轼“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议论看似对立,本质上却含着由此及彼的可能。《明诗别裁》选皇甫冲诗,称其“以造诣古淡,无一点秾纤之习”[37]169,则通过否定更易辨认的浓艳纤丽,来衬出对古质淡泊的体悟。南宋吴子良在《石屏集后序》中评戴复古:“诗清苦而不困于瘦,丰融而不豢于俗,豪杰而不役于粗,闳放而不流于漫,古澹而不死于枯,工巧而不露于斫。”[38]其中“古澹而不死于枯”虽亦语本苏轼“枯淡”之论,但也点出了古淡的另一个对立项,即枯槁。
追摹“古淡”绝不靠亦步亦趋,而在于学习,然后出新,所谓“淡薄虽师古,纵横得意新”。在这样的用心下,有出尘之姿,但过犹不及,又易陷入苦涩乏韵的一端。《唐才子传》云:“时韦应物以古淡矫俗,公尝拟其格,得数解为贽。韦心疑之,明日,又录旧制以见,始被领略曰:‘人各有长,盖自天分,子而为我,失故步矣,但以所谐,自名可也。’公心服之。”[39]68这是比较正面的例子,但比较少见。相较而言,反面的例子则更多。钱锺书先生评论梅尧臣诗时说:“都官力避昆体之艳俗,而不免于村俗。”[16]170“圣俞诗力避巧丽轻快,沦为庸钝村鄙。”[16]507“力避”二字见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用功,但难免矫枉过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唐诗,李、 杜之外,孟浩然、 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则孟为尤胜。储光羲有孟之古,而深远不及。”[40]38它指出储诗有古意,但殊少远韵,不能称大家。宋人黄彻《巩溪诗话》云:“孟郊诗最淡且古,坡谓‘有如食彭越,竟日嚼空螯。’”[41]1862后来费衮在《梁溪漫志》中说得更清楚:“自六朝诗人以来,古淡之风衰,流为绮靡,至唐为尤甚。退之一世豪杰,而亦不能自脱于习俗。东野独一洗众陋,其诗高妙简古,力追汉魏。作者政如倡优,杂沓前陈,众所趋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绅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屡叹而谓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过,盖矫世不得不尔。”[42]215论者的赞赏、 惋惜之情俱形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