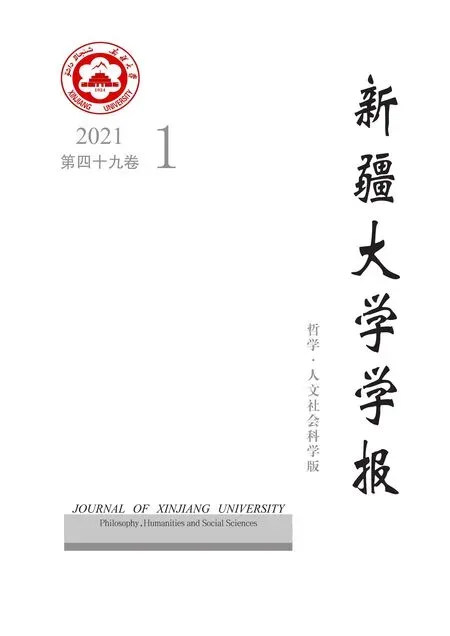义素析出视角下的“大+指人名词”结构研究*
焦 浩
(兰州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一、引 言
本文所谓的“义素析出”是指义素从词义、语素义中析出并参与“大+指人名词”结构定中关系建构的语言现象。义素(语义特征)属于语义范畴,是将词义、语素义进行切分后得到的更小的意义单位。义素是词义、语素义的组成因素,义素分析主要用于比较词义异同。一般认为,义素只是静态地储存于词义、语素义之中,不具备“独立运用”的特性,即不作为词法、语法层面的语言单位使用。但以下两种语言现象及其研究表明,义素是可以参与短语语法关系建构的。
(一)副词修饰名词
汉语中存在副词直接修饰名词的现象,如“很淑女”“很绅士”等。邢福义、于根元、桂诗春、张谊生、储泽祥与刘街生、施春宏等多位学者都对此做过研究①参见邢福义《关于副词修饰名词》,《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第215-217页;邢福义《“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语言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0页;于根元《副+名》,《语文建设》,1991年第1期,第19-22页;桂诗春《从“这个地方很郊区”谈起》,《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第24-28页;张谊生《名词的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4期,第57-75页;张谊生《名词的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续)》,《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第135-142页;储泽祥、刘街生《“细节显现”与“副+名”》,《语文建设》,1997年第6期,第15-19页。。
“副词+名词”属于一种超常的状中结构。施春宏曾经从名词的语义特征角度探讨副词和名词组合的可能性,区分出了名词的关涉性语义特征和描述性语义特征。②参见施春宏《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中国语文》,2001年第3期,第212页。施春宏指出:“描述性语义成分指对名词内涵起到描写、修饰等形容作用的评价性内容,它显现出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即具有描述性”[1]212,“描述性语义特征是副词与名词组合显现的客观基础”[1]212,如“绅士”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为:“文雅的,有礼貌的,有风度的”[1]215,因此可以说“很绅士”“十分绅士”“最绅士”。施春宏还指出:“副名组合中,语义特征决定语用状况,语用状况显示出语法分布”[1]223,“词语之间的组合从根本上说可以看成是语义之间的组合,语义特征之间的组合是词语组合显现的客观基础”[1]223,“语义特征对语法表现有一定的制约作用”[1]223,“副词与名词的组合实际是副词的语义特征与名词的语义特征的组合”[1]216。因此,“副词+名词”结构中,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参与了状中关系的建构。
(二)义素外现
在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过程中,有类义素从单音节词中外现并与单音节词构成定中、动宾关系双音词的语言现象。车淑娅研究团队将这种现象称为“义素外现”,认为外现的义素由“潜语素”变为“显语素”。①参见车淑娅、李秀芳《义素外现:“头发”的复音化研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47页。其中,吴婉淑研究了义素外现类复合动词,如“眨”的义素“眼”外现构成“眨眼”;②参见吴婉淑《义素外现类复合动词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2011年,第7页。墙峻峰研究了“树”类类属词、地名类类属词、动物类类属词、颜色类类属词的类义素外现现象,如“松” 的类义素“树”外现构成“松树”,“崤”的类义素“山”外现构成“崤山”,“鲮”的类义素“鱼”外现构成“鲮鱼”,“红”的类义素“色”外现构成“红色”;③参见墙峻峰《“树”类类属词的类义素外现》,《安徽文学》,2012年第11期,第99-100页;墙峻峰《动物类类属词的类义素外现》,《语文学刊》,2012年第7期,第11-13页;墙峻峰《地名类类属词的类义素外现》,《剑南文学》,2012年第9期,第314-315页;墙峻峰《颜色类类属词的类义素外现》,《黑河学刊》,2013年第9期,第48-49页。墙峻峰还以“俯”“仰”为例探讨了对象义素外现现象,指出其中的对象义素“首”外现构成“俯首”“仰首”“仰头”等词;④参见墙峻峰《以“俯”“仰”为例谈对象义素外现》,《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59-61页。王佳分析了“水”义素外现现象,如“泪”“池”中的义素“水”外现构成“泪水”“水池”;⑤参见王佳《“水”义素外现类复合名词研究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3页。李秀芳研究了人体器官类义素外现复合名词,如“掌”的义素“手”外现构成“手掌”,“眉”的义素“毛”外现构成“眉毛”;⑥参见李秀芳《人体器官类义素外现复合名词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7页。车淑娅认为“头发”的复音化是“发”的领属义素“头”外化的结果⑦参见车淑娅、李秀芳《义素外现:“头发”的复音化研究》,《山西师大学报》,2014年第1期,第147页。;谢淑娟研究了自然事物类义素外现的复合名词,如“虹” 的类义素“彩”外现构成“彩虹”。⑧参见谢淑娟《自然事物类义素外现复合名词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60-63页。以上现象都是外现的义素与其所从出的单音词复合成双音词。因此,以上义素外现现象主要是单音词的类义素外现并参与了定中、动宾关系的建构。
二、“大+指人名词”结构的义素析出
(一)考察对象的范围限定
汉语“大+指人名词”结构主要包括两类成员:一类是普通成员,如“大姑妈”“大孩子”,其中的“大”是指年龄、体型等方面;一类是特殊成员,如“大教授、大学者、大专家、大律师、大诗人、大傻瓜、大笨蛋、大烟鬼、重大嫌疑人、重大嫌疑犯”等,也包括带定语标记“的”的,如“最大的嫌疑人”。其特殊性在于,其中的“大”不是体型、年龄方面的“大”,更不是规模、形制、数量、尺寸等具体性的“大”。特殊成员是本文的考察对象。
特殊“大+指人名词”结构中,指人名词可以是褒义的,如“大才女、大才子、大善人、大美人”,可以是贬义的,如“大傻瓜、大土匪、大强盗、大流氓”,也可以是中性的,如“大教授、大专家、大学者、大商人”。当其为褒义或中性时,整个结构分为两种:恭维性的和事实性的。恭维性的“大+指人名词”是说话人的恭维之言,常带有调侃、玩笑之意,“大”多指职务、职称之高,或对某种职业、工作的羡慕之情,而不是某方面的成就或才能“大”。“大+指人名词”与“小+指人名词”对比使用可以表明此意,如“人家是大院长,我只是个小讲师”;事实性的“大+指人名词”则是事实性的描述或评价,无恭维之意。试比较以下两例⑨例(1)(2)引自杨同用、刘惠瑶《“‘大/小’+职衔性称谓”组合情况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第84、87页。:
(1)妈妈的邻居老是夸奖我妈妈说,“你女儿都当大局长了,你还住在这儿”。(《追忆我的姐姐任长霞》)
(2)乾隆年间,中国出了一位大学问家,名叫段玉裁。(孙云晓《解放孩子》)
例(1)中的“大局长”显然是恭维性的话语,并不强调该局长的政绩、功绩、成就等方面的“大”,更不是说局长的年龄大或身材高大;例(2)显然是事实性的陈述,清代小学家段玉裁是公认的大学问家,不带有恭维性意味。
单说“大+指人名词”结构,不能判断其是恭维性的还是事实性的,要根据具体语境来判断。试比较以下两例⑩例(3)引自杨同用、刘惠瑶《“‘大/小’+职衔性称谓”组合情况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第86页。:
(3)毛毛一听乐了,说:“大记者也有胆小的时候呀?”(《近访中国001号记者》,《大连日报》2002年6月22日)
(4)率先在《纽约客》上披露这一报道的是赫赫有名的大记者西摩·赫什,所获得的渠道是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例(3)的“大记者”是恭维性的;例(4)的“大记者”是事实性的,“赫赫有名”可佐证。
“大+职衔性称谓”结构与“大+指人名词”结构有交集,杨同用、刘惠瑶分析了“大/小+职衔性称谓”结构(本文所论“大教授”“大学者”等亦属此类),他们认为:“这种称谓只用于非正式场合。用于叙述,经常与其他职衔对比使用,带有更多的评价性意味和更多的主观感情色彩。”[2]杨同用、刘惠瑶显然未对“大+指人名词”结构的不同性质进行区分。恭维性的“大+指人名词”属于汉语的主观性情态、评价等方面的内容,与汉语的本体研究范畴有较大区别。而事实性的“大+指人名词”都带有公允的、可信的评价性质,是由汉语语法、词义的内部要素形成的语言现象,其在语法、语义上的特殊性及形成机制才是应该着重研究的内容。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特殊性的“大+指人名词”结构,但不包括恭维性的“大+指人名词”结构。
(二)义素析出与定中关系的建构
义素析出与义素外现不同,义素外现是义素由潜到显并参与语法结构建构,且外现义素以汉字形式显示出来,而义素析出则是义素从词义、语素义中析出并参与语法结构建构,但析出义素不一定以汉字形式显示出来。如“大才子、大才女、大善人、大美人、大傻瓜、大笨蛋”等词语析出义素以汉字形式显示出来,“才、善、美、傻、笨”就是析出义素,而“大教授、大专家、大律师、大商人、大土豪、大土匪、大强盗、大流氓”等词语析出义素则不以汉字形式显示出来,详见下文。义素外现产生于汉语词汇从以单音节为主向以双音节为主转变的过程中,是属于词这一层面的语言现象,其结果是形成双音词;而义素析出则是词组、短语层面的语言现象,其结果是形成定中关系的特殊性“大+指人名词”结构。
罗琼鹏曾分析过“大笨蛋”“大傻瓜”“大英雄”“大丈夫”“大天才”“大怪胎”等词语,认为:“‘大笨蛋’指某人‘笨’的程度很‘大’,与该人的实际尺寸或者年龄无关”[3]44,“‘大酒鬼’表示某人的酒瘾很大”[3]44。这说明“大”修饰的不是指人名词的整体,而是其义素,“笨”是“笨蛋”的义素(同时也是语素),“酒瘾”是“酒鬼”的义素。本文所讨论的“大+指人名词”结构也是如此。如“大教授”指有很大学术成就的教授,“大学者”指有很大学术成就的学者,故从语义关系上说,“大”修饰的是“教授”“学者”的义素[+学术成就]。换言之,在“大教授”“大学者”语义的建构过程中,义素[+学术成就]从“教授”“学者”的词义中析出并参与了定中关系的建构。
具体来说,指人名词的共有类义素是[+人],但“大”不直接修饰[+人],而是修饰可析出的义素。除了“大”以外,“重大”“最大”等词语也可以修饰某些特定的指人名词,如“嫌疑人”“嫌疑犯”等,从而构成特定类别的“大+指人名词”结构。现将常见的“大+指人名词”词语及其析出义素列出:
大教授:[+学术成就];大学者:[+学术成就];大专家:[+专业成就];大律师:[+善于诉讼];大诗人:[+诗歌成就];大商人:[+长于做生意];大才子:[+才学];大才女:[+才学];大善人:[+善良];大美人:[+美];大傻瓜:[+傻];大笨蛋:[+笨];大烟鬼:[+烟瘾];大土匪:[+坏且善于抢劫];大土豪:[+有钱];大强盗:[+坏且善于抢劫];大流氓:[+不务正业、为非作歹];重大嫌疑人:[+犯罪嫌疑];重大嫌疑犯:[+犯罪嫌疑];最大的嫌疑人:[+犯罪嫌疑]。
析出义素可以是名词性的、动词性的、形容词性的,都可以受“大”修饰。“大”是形容词性或副词性的,副词性的“大”相当于程度副词“很”。从语义构成上来讲,“大”直接修饰析出义素,二者一起构成类义素[+人]的定语,定中关系由此建构而成,“大”仅是类义素[+人]的定语中的一个形容词性或副词性成分;而从语法单位的关系上来讲,“大”就是整个定语,修饰整个指人名词。语义与语法关系的不一致正是该结构的特殊性之所在。
(三)义素析出的原因
造成特殊“大+指人名词”结构中指人名词义素析出的原因,主要是该结构语法关系与语义关系不一致,表层的语法关系类型不能涵盖深层的语义关系。目前,偏正、并列、动宾、述补、主谓等几种表层的语法关系类型,不足以涵盖汉语深层的所有语义关系类型。汉语的意义系统十分复杂,汉语语法的研究不可能完全抛开语义,语义对语法影响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此不赘述。“定中” 一般描述的是词与词之间或语素与语素之间的语法关系。如“蓝色的天空”是词与词之间的定中关系,“飞机”是语素与语素之间的定中关系,其语义与语法关系是一致的。
“定中”着眼于两个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这种概括性的语法关系是表面的、笼统的,不能细致地表明所有“大+指人名词”结构的语义关系。①不只定中关系如此,并列式等其他语法类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焦浩曾探讨过同义并列式双音词的内部语义关系,指出同义并列式双音词的两个语素地位并不是绝对平等的,并根据这种不平等性,将此类双音词分为后限定式、前限定式、附加式,前、后限定式的不平等同义并列双音词分别与偏正式、动补式在表义上有相同作用,这种跨结构的表义上的一致性,归根到底是为了适应汉语双音化和表义精确化的要求。参见焦浩《汉语不平等同义并列式双音词研究》,《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20-24页。语法单位由大到小依次为:词组>词>语素。词组是词的组合,所以实际上句子层面最重要的语法单位就是词和语素。同时,词和语素也都是语义的单位。汉字是词和语素的表现形式,所以语法单位层面的关系最深只能触及到语义的语素层面。若从语义单位来说,语素却不是最小的单位,因为词义和语素义还可以切分出义素这一更小的意义单位。一般来讲,义素不是语用层面的意义单位,也就是说义素不能在句子层面作为语言单位来使用,不具备“独立运用”这一特性。汉字只能是其描述形式而不是表现与记录形式。因此,语义单位比语法单位多了义素这个更深的层级。现代汉语的语义表达已经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这种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精确的语义表达需求会造成语法关系与语义关系的不一致,此时义素就会析出并参与语法关系的建构。
三、义素析出的反向过程——义素内化
(一)可析出义素的隐含与显现
根据可析出义素是否显现在指人名词的语素层面,可将特殊“大+指人名词”结构分为两类。一是可析出义素隐含型,主要有:大教授、大学者、大专家、大律师、大诗人、大商人、大烟鬼、大土匪、大土豪、大强盗、大流氓等,这类“大+指人名词”结构中的可析出义素不显现在指人名词的语素层面,也就是不以汉字的形式体现出来;二是可析出义素显现型,主要有:大才子、大才女、大善人、大美人、大傻瓜、大笨蛋、重大嫌疑人、重大嫌疑犯等,可析出义素直接显现在指人名词的语素层面,以汉字的形式体现出来,如“大傻瓜”中的“傻”,“大笨蛋”中的“笨”,“重大嫌疑人”“重大嫌疑犯”中的“嫌疑”。“傻”“笨”“嫌疑”既是义素又是语素,二者在形式上重合了。
不管是隐含型还是显现型,大都由“大”和指人名词直接按照定中关系复合而成。而“重大嫌疑人(犯)”的形成过程还可以在现代汉语的共时层面找到痕迹,分析其形成过程可以更清晰地说明义素[+犯罪嫌疑]是如何析出的,也可以很好地展现“大+指人名词”结构的内部语义关系。
(二)义素内化——以“重大嫌疑人(犯)”的形成过程为例
1.不是所有的内化都能找到形成轨迹
可析出义素隐含型和大部分显现型的“大+指人名词”结构,是由“大”和指人名词直接复合而成的,复合的基础是“大”能修饰指人名词的可析出义素。可析出义素在指人名词形成(或词汇化)的过程中就已完成内化,故其形成过程大都不能在现代汉语的共时层面找到轨迹,甚至不存在这一过程。如“大”与“教授”早就共同存在于汉语史中,但其并未很早就结合在一起。其结合是在“教授”成为高校教师职称之后,也就是[+学术成就]这一义素内化于“教授”之中后,这是在现代汉语阶段才发生的。虽然大部分“大+指人名词”结构不能找到可析出义素的内化轨迹,但其形成机制可以用义素内化和义素析出来解释。
我们在现代汉语的共时层面找到了“重大嫌疑人(犯)”的形成过程,这个形成过程就是可析出义素内化的过程。内化是与析出相反的过程,展现内化过程就是从反面证明义素是可以析出并参与语法关系建构的。
2.义素[+犯罪嫌疑]的内化
“嫌疑”常以“大”言之。例如:
(5)弟子的公公死得不甚明白,村中人无一不知,但嫌疑最大的,就是公公扶正的姑嫜。(清代《八仙得道传》第六十回)
(6)您现在的处境非慎重考虑不可,您犯了极其重大的嫌疑,可能引起极严重的后果。(李丹译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卷)
(7)老陈昨晚跟老婆在周公馆的门房说话是真的,这就是十分之十的重大嫌疑。(夏衍《上海二十四小时》之七)
(8)专案组又将现场提取的痕迹鉴定材料与凌卫朝案卷中的有关鉴定材料比对,也认定一致。显然,凌卫朝有重大嫌疑。(姚云海《捕影神探》)
从例句可以看出,“大”与“嫌疑”可以构成定中关系词组。“嫌疑”还可与“有”一起作“人”“人员”的定语。例如:
(9)蕊玲回来了,这个最有嫌疑的人回来了,他实在不知道她回来的目的。(于晴《红苹果之恋》)
(10)在出事之后的两天,警察曾审问过一些有嫌疑的人,但是审问了十来个人之后,他们便失去了对这桩案件的兴趣。(北京大学CCL语料库高尔基《母亲》)
(11)车站谣言更多,说从北京到天津这一段要经六次大检查,检查出有嫌疑的人来,立刻拉下火车去枪毙。(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12)该市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连日来还主动出击,逮捕了一批有恐怖嫌疑的人员。(2003 年12月24 日新华网洛杉矶电《洛杉矶国际机场进入“911”以来最高戒备状态》)
(13)对有犯罪嫌疑的人不仅不让他们出国看比赛,甚至连国内的比赛也不让他们进赛场。(2001 年10 月19 日新华社伦敦电《英国收拾足球流氓》)
例(9)—(13)中的定语标记“的”表明“有……嫌疑”与“人”之间为定中关系,而“有……嫌疑的人”之“嫌疑”可以受定语“大”的修饰。例如:
(14)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15)王松年和干警们通过现场分析,很快就确定了侦查方向,对有重大作案嫌疑的人员可能的藏身之处进行堵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有嫌疑的人”即“嫌疑人”,“有恐怖嫌疑的人员”即“恐怖嫌疑人”,“有犯罪嫌疑的人”即“犯罪嫌疑人”。前者是后者的释义,也是后者的义素的组合。例如:
(16)格鲁吉亚内政部29 日宣布,格鲁吉亚军队当日在潘基西山谷地区逮捕了一名持法国护照的恐怖嫌疑人,并怀疑此人属于本·拉丹的“基地” 组织。(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17)河南省有20 多万群众参加了“严打”斗争,直接扭送犯罪嫌疑人1300 多人。(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例(10)出自高尔基《母亲》的译文,其他译者将“有嫌疑的人”译为“嫌疑犯”。
(18)案子发生几天后,警察曾经传讯过一些嫌疑犯,但在审讯了十来个人以后,他们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徐志伟译高尔基《母亲》)
释义或义素组合式的表述方式中,“大”可以修饰“嫌疑”,但当释义或义素组合式的表述方式词汇化为“嫌疑人”“嫌疑犯”时,定语“大”就只能修饰“嫌疑人”“嫌疑犯”的整体。例如:
(19)随着案情的逐步明朗,警方确认李荣健系枪案重大嫌疑人。(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20)2001年12月10日,专案组在厦门抓获了重大嫌疑人刘良艺,使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21)2004年11月24日,公安部悬赏通缉刘招华等五名在逃重大毒品犯罪嫌疑人。(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22)试想,舜的非正常死亡,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是象母子,因为之前他们就有种种对舜不善的恶名传于外。(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23)特别重大的犯罪嫌疑人,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也不能超过30天。(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24)得克萨斯州贝勒大学篮球选手帕特里克·邓尼被枪杀,队友被认为是最大的嫌疑犯。(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25)我这么大的嫌疑犯他们能不来找吗?(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例(19)—(25)中,尤其是定语标记“的”的位置可以清楚地表明,表层关系中“大”是修饰整个“犯罪嫌疑人”“嫌疑犯”的。“重大嫌疑人”“大嫌疑犯”意思与例(14)(15)中的“有……大嫌疑的人” 相同。实际上,后者就是前者的义素分析,“嫌疑” 是“嫌疑人”“嫌疑犯”的析出义素。
3.“重大嫌疑人(犯)”的形成
“重大嫌疑人(犯)”的形成过程为:
(重大+嫌疑)+的人→重大+(嫌疑+的人)→重大+(嫌疑人)→重大嫌疑人(犯)。
“嫌疑”与“人”未词汇化时,“重大”修饰“嫌疑”,词汇化为“嫌疑人”后,“重大”只能修饰“嫌疑人”这个整体。从语感上来说,“重大嫌疑人”是“重大”修饰整个“嫌疑人”,但从语义上来说,“重大”仅是修饰“嫌疑”。这就是语法单位与语义单位定语的不同,即表层语法关系与深层语义关系的不一致,也就是语感与实际语义不统一的原因所在。
“重大嫌疑人(犯)”义为“有很大犯罪嫌疑的人”,“嫌疑人”的语素“嫌疑”含有义素[+犯罪嫌疑],本处于中心语的语法位置上,而从语义单位上说,却属于定语部分。“大教授”中,“教授”的义素[+学术成就]实际上是受定语“大”的修饰,只不过该义素隐藏于“教授”的语义内部,不以汉字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实质与“重大嫌疑人”相同。因此,“大教授”“重大嫌疑人(犯)”等定中结构中有义素从中心语的词义中析出,并在词组、短语层面发挥了语法作用,参与了定中关系的建构。
四、结 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义素可以从词义、语素义中析出并参与定中语法关系的建构。若无义素析出,则特殊“大+指人名词”结构的定中关系就不能成立,义素析出是定语与中心语能够结合的基础。义素本是隐含在词义、语素义中的,而词义、语素义要借助汉字记录的语法单位来表现,语法单位之间的直接联系是语法关系,深层联系是语义关系,这就使义素参与语法关系的建构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义素是沟通语法与语义的桥梁。义素的析出是以语法组合为前提的,定中关系是激发义素析出的根本原因。特殊定中结构“大+指人名词”中,因为有定语“大”才有中心语“教授”“学者”“嫌疑人”的义素析出。
本文讨论的特殊“大+指人名词”结构具有不对称性,即相对的“小+指人名词”结构大都不表达相反的意义。如“小教授”一般并不着眼于其“学术成就”,而是其职称或社会地位,常与表示职务高、社会地位高的恭维性“大+指人名词”对比使用;“小傻瓜”一般是指其年龄小,“小酒鬼”也是指年龄小,不能表达“不太傻”“酒瘾小”的意义。
汉语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的外在形式是由语法关系控制的语法单位建构起来的,本质内容则是庞大而复杂的语义系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语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语义控制的。本文对义素析出现象的讨论也表明,语义对语法有一定的影响与控制作用。义素作为深层的语义因素,就像“基因”一样,深刻影响着语法关系的建构。特殊“大+指人名词”结构以及副名组合、义素外现、不平等同义并列式双音词等方面的研究都表明,偏正、并列、主谓、动宾、动补等五种基本语法类型难以涵盖汉语复杂的语义关系,对每种语法类型内部更细致的分类以及对其语义与语法关系更深入的探讨,都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