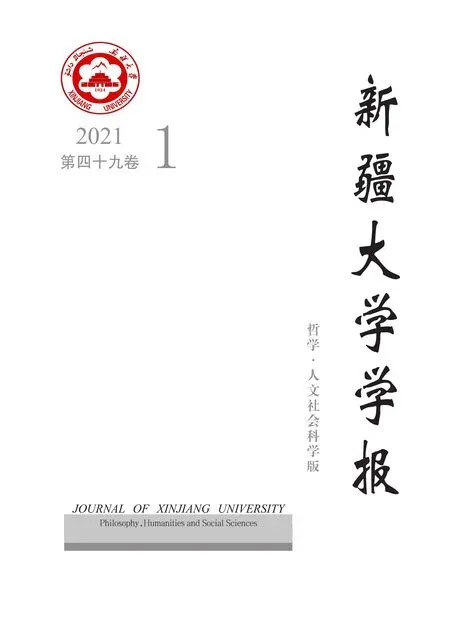矛盾、空间与解脱:论明中期吴中文人的仕隐困境*
都轶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明代吴中文化繁盛,文采风流,才子辈出。然明代吴中文化氛围、文人境遇与心态有明显分期。明代前期,由于政治迫害与科举压制,吴中学子极难考中进士,①据统计,整个明代276 年间,苏州府进士共有1055 人,而明代前期百年间录取人数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参郑彩娟、傅蓉蓉《明清苏州府进士数量及分布特征探析》,《文史月刊》,2012年第8期,第241页。对政治的恐惧与仕途的无望,使得元代以来的隐逸之风延续。天顺以后,国家承平既久,政网松驰,吴中徐有贞、吴宽、毛澄、王鏊等相继身居高位,吴中地区科举之风日炽,隐逸名士的子侄辈纷纷科考入仕,“人材辈出,岁夺魁首”[1]。自成化至嘉靖初年,即本文所讨论的明代中期,正处于吴中地域文化由隐逸向入仕的转型过渡期,也是吴中文风最盛的时期。也正在这一时期,社会价值与个体生命、在朝之功名利禄与在野之诗意生活之间,构成了充满矛盾、困境的舞台,使得身处其中的文人在仕与隐、进与退之间反复踟蹰、徘徊。
仕与隐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常态问题。然而在明代中期吴中文人这里,基于特定时空界限的政治环境、地域文化传统及士人群体特征,这一问题表现出复杂、微妙的情态,具有特殊性。对这一复杂而重要的现象及其成因做细致深入论述,无论对于挖掘吴中文人群体的心灵史,还是对我们藉此知人论世地理解和把握其诗文及艺术创作的心理与情感动因,都很有必要。而前人对他们之于科举出仕态度的复杂性认识尚不足,对其成因也主要从商业繁荣、城市世俗生活发达的影响等外部因素讨论,而缺乏对以文化、文学与文人为本位的内部因素的探寻。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加以推进、再做考察。
一、吴中文人对科举出仕的矛盾态度
明中期吴中文人大多有参加科举的经历,但同时他们在诗文中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反思和批判又是十分突出的。如文徵明《凤峰子诗序》批评科举以经义取士对文艺的戕害,导致诗歌创作不兴,诗道浸弱。又如陆粲《赠训导严用文之官宁海序》批评科举制度压制、埋没人才;桑悦《桂阳州新建儒学记》批判科举考试内容空洞无物。即使是以进士出身而至高位的吴宽、王鏊,也在吴中文人批评科举的潮流之中,对科举制度不乏抨击之论。如王鏊《拟罪言》指出:“国家设科取士之法,其可谓正矣密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轶前代,卒未闻有如古之豪杰者出于其间,而文词终有媿于古。虽人才高下系于时,然亦科目之制为之也。”[2]批判态度最激烈的要属祝允明。他在《贡举私议》《容庵集序》等文章中,反复论及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特别在《答张天赋秀才书》这一长文中,痛陈天下学术、士风“一坏于策对,又坏于科举,终大坏于近时之科举矣”[3]227。并对科举之害与程文之弊作了全面翔实的阐述,此文之深透有力,可谓吴中文人反思科举的代表作。上述种种可见,在观念层面上,针砭科举、贬抑时学已是当时吴中文人群体之共识。
明中期吴中文人对待科考本身也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长年奔走科场,希望博取功名;另一方面又不力务于科考,既不苦读钻研,更不曲意迎合。祝允明就曾坦言:“读书学为仕,亦从世格举,不加力务,亦弗矫而去之。”[3]271文徵明“数试不利,乃叹曰:‘吾岂不能时文哉?得不得固有命耳。然使吾匍匐以求合时好,吾不能也。’”[4]1724钱孔周“早岁思以功名自奋,稍敛锋锷,以就文场矩矱,亦惟涉猎训故,涵泳道腴而已,于世所谓括帖关键,皆不之省”[4]723-724。唐寅表达得最为直率,科考在即,他直言曰:“诺。明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弗售,一掷之耳。”[3]306这虽似狂生之语,却也符合这些吴中文人的真实心态。唐寅能够高中解元,大半归功于他天资聪颖,即所谓“信步闱场,遂录荐籍”[3]460,而非勤习程文、积极备考之效。总之,他们虽也顺应当时吴中科举大盛之时潮,科考不辍,但又都不愿为了应试而真正用功致力于帖括时文之艺,似乎对参加科举的结果成功与否并不在意。
他们虽然对科考本身并不愿勤苦用功,但又始终不愿彻底放弃科举出仕的机会。在谋求出仕的漫漫长路上,他们时而表现出对功名恋恋不舍,时而又欲将功名看穿,隐居乡间。文徵明《病中遣怀》诗云:“潦倒儒冠二十年,业缘仍在利名间。敢言冀北无良马?深愧淮南赋小山。病起秋风吹白发,雨深黄叶暗松关。不妨穷巷频回辙,消受罏香一味闲。”[4]243既感叹自己功名业缘难消,又欲穷巷回辄,享受乡居生活的悠闲。祝允明在弘治五年(1492)中乡试之后,便欲弃考归隐,自云“浮名虽或就,夙尚乃弥坚。漆雕有风期,恒虞终邈然”[3]49。援引漆雕开拒绝出仕之志自比,不去参加次年的会试。但就在这一年,祝允明又力劝唐寅参加科举。之后的二十年间,他自己也又七次参加会试。可见,这些吴中文人对科举没有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与急于出仕的迫切渴望,他们用一种几近敷衍的态度,反复赴考,所以遭受屡试不售的挫折,也就不足为怪。既非志在必得,又不甘心放下,在这样的矛盾、徘徊的心态下,文、祝等人也无法全身心投入乡居生活,像前辈杜琼、沈周等恬然自守,而常常陷入“壮志乡心两无着”[4]276的困境。在诗文之中,他们常常流露出仕途困顿、岁月蹉跎的悲伤与无奈。如文徵明《失解东归口占》,祝允明《述行言情诗·其一》等,均是发自肺腑的深沉叹息。
然而真正踏上了仕途,吴中文人往往又是浅尝辄止,常任职不过数年就辞官回乡。如杨循吉于成化二十年(1484)中进士,授礼部主事,弘治元年(1488)三十二岁即致仕,乡居五十多年。张安甫于弘治三年(1490)中进士,授祁州知州,四年之后就致仕不复出,乡居三十五年。一些任职时间较久、官阶较高之人,也在致仕之后有长时间的乡居生活。如祝允明之祖父祝灏累官山西布政司右参政,成化元年(1465)致仕,乡居十九年。他如文森、钱贵、王榖祥、汤珍、张寰等都有多年的致仕乡居经历。且吴中文人的仕宦政绩也并不显赫,除了徐有贞曾在天顺初年位居权力中心,多数人在政治事功方面并无多少建树,即使如吴宽、王鏊官拜尚书,位高权重,也仍以文名。尤其是吴宽,热衷于文事,身在朝廷,而仍如吴中乡居隐逸文人般过着诗意、闲适的生活,所以“坐令功业为文掩”“空令海内尊韩子,不见朝廷相仲淹”[4]160-161。这种出仕后又得之即弃、眷恋乡居的现象,充分说明科举出仕并非他们真正的人生追求和价值所系。而这一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科举出仕在吴中文人那里究竟是何种定位,值得深思。
总之,明中期吴中文人对科举与出仕的问题,呈现出既追随时潮又批判贬抑,既热衷执着又敷衍鄙夷,既难舍功名诱惑又得之即弃的多重矛盾。这种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情态,在中国古代文人心态史中是相当特殊的,其背后必有多元的成因,归结起来,大致可以从进取的阻力与退守的空间两方面切入。
二、进取的阻力
明代吴中地域文化中,隐逸传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前人对吴中隐逸传统已有关注和介绍。本文从立论角度出发,则着重阐发隐逸传统所导向的文化性格与价值观念。元代由于仕进之路不畅,隐居乡间的吴中文人寄情于文艺,文人交游、诗文书画创作都十分繁盛,名家辈出。入明之初,吴中文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出现了闻名天下的吴中四杰,他们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并皆不得善终,于是将个体精神与满腔情怀托于诗歌。以高启为代表,他是一位典型的将诗歌融入生命的诗人,自言“凡可以感心而动目者,一发于诗;盖所以遣忧愤于两忘,置得丧于一笑者”[5],说明他将内心的情感都发抒于诗中,并因此而获得了忘忧解愁、遗世独立的个体价值感。
明代前期对吴中文人的政治高压和科举压制,导致他们出仕热情不高,隐逸传统得以延续,或终身布衣,或有数年中下层官僚的经历。文学创作虽不及明初之辉煌,但也出现了一批诗文、书画兼长之人,如刘珏、沈澄、谢缙、沈贞、杜琼等。天顺之后,逐渐形成了以沈周为中心,以史鉴、朱凯、朱存理等布衣为常客的文人圈子,以诗文、书画创作活动为中心,追求简淡自适、崇真尚情的吴中地域流派重又走向复兴。沈周作为隐逸文化、诗酒风流的代表,将元代以来吴中地区凝聚的审美艺术精神发展到了极致。钱谦益序沈周诗云:“有三吴、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览,有图书子史充栋溢杼以资其诵读,有金石彝鼎法书名画以博其见闻,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写其神情。烟风月露,莺花鱼鸟,揽结吞吐于毫素行墨之间,声而为诗歌,绘而为图画,经营挥洒,匠心独妙。”[6]钱氏之言实是以沈周为代表,生动准确地描绘了吴中文人诗情画意的生活传统,即由吴地的灵秀山川、浪漫风物、鼎盛人文所营造构成,远离庙堂政治,亦无关宏大抱负、深邃思想。
成化、弘治以来,科举之风兴起,终生远离科场、无意仕途的隐逸行为在吴中地区逐渐消歇,但是隐逸传统的流风余韵,浸润既久,已经潜移默化成一种地域文化性格。以祝允明、文徵明、唐寅为代表,明中期的吴中文人多富有诗文、艺术才能,精神上注重真情、张扬个性,适志、贵我的思想更加突出。如唐寅云:“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7]524祝允明云:“遐览天地间,何物如我贵。”[3]56在诗文创作上,也推崇语出天然、情由心生。如都穆《南濠诗话》之《学诗》一诗言:“切莫呕心并剔肺,须知妙语出天然……但写真情并实境,任他埋没与流传。”[8]这正是吴中文人诗歌观念的代表,强调诗歌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不必刻意雕琢苦吟,甚至仅将作诗视作抒发性情的一种方式,而非旨在创作经典的文学作品。
总体来看,明中期吴中文人的精神世界仍延续先辈的传统,崇尚感性、审美的生命体验,追求个体生命的舒展与超越。翻阅这一时期的吴中文人文集,不难发现此一总体特色:他们很少关心政治,没有干预现实政治的热情;同时也缺少理性的思考,除了祝允明的著作较富有思想性之外,多在思想、哲学领域无甚成就,也不感兴趣。他们普遍对程朱理学抱以反感态度,其时浙东新兴的心学思潮也没有在吴中地区产生明显影响。故对于出仕,明中期的吴中文人既无兼济天下的抱负,与吴中前辈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相去甚远;又无理学家们企图得君行道的宏愿,不以圣贤自期。因此对于明中期吴中文人而言,科举出仕也就只是一种求名获利之手段。时人黄省曾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竞以求富为务。书生惟藉进身为殖生阶梯,鲜与国家效忠。”[9]“鲜与国家效忠”六字已将科举在吴中文人心中的定位说得很明白了,也与同时期具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与家国意识的前七子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在祝允明、文徵明等人的诗文中,每每以“富贵”“名利”“功名”“浮名”等来代指科举出仕,如“业缘仍在利名间”[4]243,“痴人只理闲文字,不读人间富贵方”[3]573等诗句。前引祝允明诗云“浮名虽或就,夙尚乃弥坚”[3]49;他劝唐寅参加科举时亦谓“子欲成先志,当且事时业;若必从己愿,便可褫襕襆,烧科策”[3]306。这里“浮名”与“夙尚”,“先志”与“己愿”,都是外在价值和内在心意之间所存在的强烈冲突的写照。这种矛盾冲突对向来追求自适、个性的吴中文人构成了长久的束缚,所以他们会不时对科举出仕表现出排斥、反感的态度,对科举的功用、意义都在不断质疑和反思,不断进行批判。
文学思潮方面的推崇古文辞,是明中期吴中文人群体的又一大特色,前人就其古文辞之文体观念及特征已有论述。①参见黄卓越《明中期吴中派的诗文体统观》,《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第34-37页。但本文要强调的是,吴中文人推崇古文辞的初衷及目的,除了文学审美上的因素,更直接、更重要的就是对科举时文的批判。明中期吴中文人群体中,首先倡导古文辞的应是吴宽。据吴宽《旧文稿序》:“宽年十一入乡校习举业,稍长有知识,窃疑场屋之文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之使人笔势拘絷,不得驰骛以肆其所欲言,私心不喜。时幸先君好购书,始得《文选》读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读《史记》《汉书》与唐宋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颇属之。”[10]365吴宽开始属意于古文辞应在天顺、成化年间。至弘治初,影响扩大,年轻一辈的吴中文人纷纷投入古文辞写作中。据文徵明记载,“弘治初,余为诸生,与都君元敬、祝君希哲、唐君子畏倡为古文辞。争悬金购书,探奇摘异,穷日力不休。僩然皆自以为有得”[4]1219。稍晚的黄鲁曾、王宠等人也皆受影响,以古文辞为尚。明中期吴中地区兴起的这场古文辞运动,较前七子的复古运动要早。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差异,其中关键在于,从宗旨上看,复古派主要针对台阁体诗文,要从格调法度上恢复汉唐的古典审美,而吴中文人主要针对的就是科举时文。除上引吴宽之序外,如文徵明亦云:“以亲命选隶学官,于是有文法之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而中心窃鄙焉。稍稍以其间隙,讽读《左氏》、《史记》、两《汉书》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时时窃为古文词。”[4]571黄鲁曾亦是“弱冠并充弟子员,窃鄙时义,博综群籍,探古文辞,好奇纵谲,为文闳衍,莫能加焉”[11]。从这些叙述来看,吴中文人所谓古文辞就是与时文相对的古体散文,其取法对象也不限于秦汉文,而是从汉至元的“古今人文集”。他们对时文的批评侧重于文法格式,特别反对时文“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之使人笔势拘絷”[10]365,并从文法自由、文势闳肆的角度提倡学习古文辞。
同时,吴中文人的古文观念,与唐宋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不同,他们提倡文、道并重,尤其突出“文”的重要性。如祝允明论六朝之文,提出“即如今人所病,魏晋之浸衰,陈隋之极靡,道其理气,斯诚然矣。然皆按规而造轮,持矩以构室……谁非拟诸经籍者哉!所以为是萎迟者,良由其理局气猥,乃至音澌步踬,非过文之罪也”[3]779-780。唐宋古文家贬斥六朝文,主要在于六朝文过度强调文学形式之美,而弱化了载道功能。祝允明却认为六朝文之缺陷在于“理局气猥”,而非“过文之罪”,其旨在维护六朝文章文学性的价值,提高“文”的地位。可以说,注重文辞、文采是吴中文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举考试以论说经义为主,要求“取书旨明晰而已,不尚华采也”[12]1689,跟提倡文辞、注重文学审美功能的吴中文风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在明中期吴中文人看来,科举是戕害文学的罪魁祸首。如文徵明云:“惟我国家以经学取士,士苟有志用世,方追章琢句,规然图合有司之尺度……今之为是言者,良由其卫道之深,而不知语言文字,固道之所在,有不可偏废者。是故文章之华,足以润身;政事之良,可以及物。”[4]1228-1229指出科举以经学取士,文章全为卫道之作,以致完全忽略了语言文辞本身的价值。
吴中文人以古文辞对抗时文的态度是激烈的,不仅在观念层面批判,而且付诸了行动。吴宽就曾一度“欲尽弃制举业,从事古学”[13]。唐寅在乡试之前的提学考试中,答卷竟采用了与八股要求不符的古文辞,以至于“文法诖误”[3]460,险被取消乡试资格。文徵明于科考一再失利,友人劝其放弃古文辞,专攻程文,他却回答:“就而观之,今之得隽者,不皆然也,是殆有命焉。苟为无命,终身不第,则亦将终身不得为古文,岂不负哉?”“用是排群议,为之不顾。”[4]572他们为坚持古文辞写作,或欲放弃举业,或临场犯禁,甚至屡试被斥也在所不惜,足见明中期吴中地区的古文辞运动尽管未能如前七子复古运动那样在文学领域掀起巨大的浪潮,但从科举出仕角度来看,确实构成了进取的阻力,其对吴中文人群体本身的命运是影响至深的。
三、退守的空间
从退守的角度说,物质经济条件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明代吴中经济发达,为吴中文人提供了多样化的世俗治生之途,他们一般不会因科举失利引发严重的生存危机。但除了外在的优越的物质条件,我们认为明中期吴中文人群体的交游活动和文化好尚所营造的精神空间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内在因素。
弘治、正德年间,老一辈沈周、朱存理、文林等尚且活跃,年轻一辈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蔡羽、都穆等也已逐渐成长起来。一时俊彦荟萃,互相交游唱和,热闹非凡。文林曾这样记述一次饯别宴会:
戊午春,将赴温州,杨君谦礼部邀饯于虎丘。同集者沈启南、韩克赞,二老複巾杖䉫;韩从子寿椿与朱性甫青袍方巾;唐子畏、徐昌国并举子巾服,而余与君谦独纱帽相对。会凡八人,人各有侣,适四类,不杂。[14]
这种超越了年龄、身份、穷通之界限的交游,以诗文、书画为共同好尚,以追求自适、真情为精神内涵,达到一种和乐融洽的境界,正是吴中文人圈特出之精神。吴中文人不论仕途穷达与否,都可因诗文、书画才能进入交际圈中,并受到赏识和推崇。如祝允明在年轻时,“发为文章,崇深钜丽,横纵开阖,茹涵古今,无所不有。或当广坐,诙笑杂还,援毫疾书,思若泉涌,一时名声大噪”[15]。唐寅更是以风流才子之名享誉江南。
在明代文人之间倾轧剧烈,文学流派之间、流派内部论争不休的背景下,明中期吴中文人在交游往来、文学创作上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包容和谐的关系。虽多具有鲜明个性,主张保持自我本色,但亦尊重他人的个性。王世贞《文先生传》曾记载:“吴中文士秀异,祝允明、唐寅、徐祯卿日来游。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祯卿诗奕奕有建安风。其人咸跅弛自喜,于曹偶无所让。独严惮先生,不敢以狎进。先生与之异轨而齐尚,日欢然无间也。”[16]文徵明平和温厚、醇正高洁,却能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等性格放浪张扬之人异轨齐尚、欢然无间。四人能共揽“吴中四才子”之名,一定程度上正是缘于求同存异的互相尊重。当然,他们在思想、言行上也不免会有冲突。如唐寅在科场蒙冤之后,更加放纵任诞,文徵明致信规劝,而唐寅在回信中却道:“山鹊莫喧,林鹗夜眠;胡鹰耸翮于西风,越鸟附巢于南枝;性灵既异,趋从乃殊。是以天地不能通神功,圣人不能齐物致……寅束发从事,二十年矣;不能翦饰,用触尊怒。然牛顺羊逆,愿勿相异也。”[7]223完全是在强调自己的个性与选择,不愿从友人文徵明之规劝,且言辞尖锐激烈。然从二人后来的交往来看,文徵明并未因此心存芥蒂,依然相处融洽。唐寅晚年向文徵明吐露:“寅长徵仲十阅月,原例孔子以徵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7]224言辞恳切而谦卑。狂傲无忌如唐寅,若非出于真心,岂能如此?故袁宏道曾对此叹曰:“真心真话,谁谓子畏徒狂哉!”[17]此足见二人一生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徐祯卿曾赞赏文徵明“含和而不同,圣哲所称焉”[18],正是吴中文人之间宽容和合的交游关系的真实写照。在文学创作上,相较同时期前七子内部的李何之争、李徐之争,以及之后闽派、公安派、竟陵派等各流派之间不断的批判攻讦,明中期吴中文人圈内部具有地域自守性,不注重向外扩张和攻击,与外部争论不多,内部更没有什么利益纠葛和观念论争,没有争魁首、争观点的情况,呈现出一片和谐气象。这一点在对待徐祯卿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徐祯卿北上进入前七子复古一路,并未因此受到吴地故友的排挤和非议,祝允明有诗云“遑遑访魏汉,北学中离群”[3]71,对徐祯卿非但没有指责,反而有些赞赏,也有对离群友人的怀念。而同为前七子的李梦阳对徐祯卿诗文中保留的吴中风格则大为不满,认为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19],双方一再辩论、批评。两相对比,区别判然可见。正是这种具有包容性的良性关系,使得吴中文人的真性情可以更加自如地展现,彼此之间也能建立起更纯粹牢固的情谊。
不仅身处吴地的文人之间通过交游建立起了真挚牢固的情谊联结,当时在朝的吴中官员,以身居高位的吴宽、王鏊为代表,也都积极提携乡邦文人,宣扬吴中文化,与吴地在野文人互为应和,有意识地进行地域文化建设和弘扬。一方面,他们开始大规模编纂地方文献如地志、故实、传记、总集等。这些文献中无不大力鼓吹吴中风土、人物、文化之盛。而这种大规模的地域文献编纂本身,正反映出明中期吴中文化发展到高潮阶段,当地文人共襄盛事、以垂青史的文化自豪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吴中文学经历了明代前期的低落,成化以后开始复兴,吴中文人自感可以媲美明初的文学鼎盛时期再次到来,十分振奋,极力宣扬文坛之盛况。如陆师道对明中期吴中文人之数量、声势都做了高调评价:
英、孝之际,徐武功、吴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当钧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向风景服,靡然而从之。时则有若李太仆贞伯、沈处士启南、祝通判希哲、杨仪部君谦、都少卿元敬、文待诏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国、蔡孔目九逵,先后继起,声景比附,名实彰流,金玉相宣,黼黻并丽。吴下文献,于斯为盛,彬彬乎不可尚已。[7]593
已有学者指出,陆师道所言,实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其目的是通过集体自守的方式共同抵御外域文学的影响,重塑吴中昔日的辉煌。①参见李祥耀《论明中期吴中文学的集体自守性》,《社科纵横》,2009年第4期,第125页。但如此夸耀乡邦文学成就,对于吴中文人群体心态也有其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自我认同树立起地域文化自信,鼓励时人和后辈坚守、弘扬吴中的文学传统,进而对于乡居在野的风雅生活感到自足和自豪。
上述几方面,最终都直接内化为明中期吴中文人对待科举出仕问题的坚实的心理缓冲区,为科举落第之人、致仕还乡之人都提供了精神上强大的退守空间。这样,在出仕之外,就有另一种精神空间可供他们逃遁和徜徉,科举和仕途对他们的绑缚就不会那么紧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科场落魄不幸的影响。这使得吴中文人不会像吴敬梓笔下的范进那样,将所有的精神、情感完全维系于科举,乃至彻底为之疯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退守空间的存在,又会淡化功名心,削弱进取意志,在进与退的拉锯中提供了一股退后的力量,造成一种选择的困境,使得吴中文人在科举仕进的路上多年徘徊踟蹰,蹉跎光阴。他们不会像寒门士子那样将科举出仕作为鱼跃龙门的唯一途径,不会全力以赴、孤注一掷地投入,这正是其多年不第的原因之一。
四、解脱之道与无望之殇
有研究者指出:“生活在明清时代的作者,只有赢得科举的成功或彻底放弃科举,才能走出举业的阴影,步入自由写作的阳光地带,才有酣畅发挥性灵和天才的文学创造。”[20]的确,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在生活、心态和精神层面上同样如此。明中期吴中文人亦难免被这种普遍风气裹挟其中。虽然上述吴中地域文化环境为文人提供了退守空间,但是,到了科举之风日炽的明代中期,这已不足以完全抵消出仕的压力。科举出仕在明中期吴中文人那里,除了在外在价值层面上是一种求名获利的手段,更已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社会评价标准,成为一种巨大的必须背负的压力强势进入了吴中文人的生活轨迹。不管是否与他们内心意愿相符,都以一种无法超越的姿态存在,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
文徵明和祝允明的求取进士之路都以失败告终,在多次科考不第之后,得到了贡举出仕的机会。据《明史·选举志》:“至弘、正后,资格始拘,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12]1717以贡生、举人出仕,因出身低微,其地位和前途都远逊于进士。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接受。受职之后,文徵明作《谢李宫保书》云:“若夫怀藏道德,抱节守贞,某实非其人;即其人,将自韬约远引,不令公知矣。”[4]578祝允明作《答人劝试甲科书》言:“(友人)又曰:‘然则曷不遂行遁?’夫不仕无义,度力而趋,乘田委吏,莫非王臣。”[3]222皆表明不甘就此归隐的态度,足见出仕之念仍萦绕于心。
与多数出仕为官的吴中文人一样,祝允明、文徵明在仕途上都无甚作为。祝允明在兴宁知县任上虽然有一些政绩,但他却志不在为官。他在兴宁期间,经常游览山水胜景。从赴任到辞官归乡,历时很短,这期间他写下了一生中为数最多的山水诗和山水游记,却极少有文字言及政事和民生,更从未提及自己的政绩。对于为官,他总结道:“仆诚不善仕,其故大率不能克己,不能徇人,不能作伪,不能忍心。视时之仕者若神人然,安能企及之哉!”[3]226数年之后,虽升迁到应天府通判这个更重要的职位,但祝允明当年即决意辞官回乡,归隐不出。文徵明赴京供职翰林院。赴任不久,即遭遇了震惊朝野的“大礼议”事件,官员纷纷卷入站定立场。然而文徵明却以跌伤手臂为由,未曾参与其中。其父文林与张璁有旧谊,张璁因“议礼”获胜,骤然权势熏天,欲让文徵明党附于他,文徵明却并未遵从。①事载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25页。所以他虽然身在朝中,却仍然对政治不感兴趣,主动保持距离。或许正是这种与政事、权贵都表示疏离的态度,让他在朝中难有立足之地,“同事太史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滥竽木天”[21]。原本备受推崇、处于吴中文人交游圈核心的文徵明,受到嘲弄和排挤,其孤独和郁闷结成了大量的思乡诗。故文徵明在京仅三年就再三请辞归乡。
对于祝允明、文徵明而言,数年的出仕经历既不成功、也不愉快,并未给他们的人生增添多少光彩,似乎应算生命的低谷时期。然而这段出仕经历对他们而言却又是十分重要的,其意义并不在于仕途的显赫与否,实仅在于出仕这一事实本身。因为在科举时风影响特别是家族责任的巨大压力下,经历多年科考,已使出仕在他们那里变成一种求而不得的心结,即使再三在仕隐、进退之间踟蹰、徘徊,似乎聊能排解,却依旧欲罢不能,只有获得出仕之机,卸下背负的压力,方能真正解开这一困境,得到精神上的超脱。可以说,出仕在他们那里已近乎一种必要的仪式,因为一旦入仕,他们在仕途上就不再是求而不得的失败者,而是高姿态的主动弃官者,就能获得极大的心理平衡。在中国古代,仕与隐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如果不曾出仕,某种程度上都不能算作真正的隐士,而只是庶民或者布衣。所以出仕不但对于隐士身份的构建是必要的,而且也只有摆脱了仕隐、进退的矛盾心态,才能完全在精神上享受致仕归乡的隐逸生活。
过去通常认为,祝允明、文徵明等人主要是因为出仕之后看到官场黑暗,仕途受挫,心灰意冷而归乡的,②较为典型之例如富路特、房兆楹《明代名人传》第二册《祝允明》,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533页;杭春晓《文人理想的幻灭与重建——文徵明的出仕、致仕及其心理辨析》,《方法论与美术史个案叙事》,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84-93页。其实不然。无论官场境遇如何、仕途顺逆与否,他们对官场的不适应和退隐都是必然的,这主要源于他们对科举出仕在内心意愿层面上的排斥。他们既非真有用世之志,辞官归乡之后,也自然不会因为官场失意而感到挫败,而是以一种轻松自在的心态,完全融入了吴中文人充满诗意和快意的生活中。文徵明返乡之后便自称“老归林下”[4]1725等语,其实他不过被授予从九品的翰林院待诏,基本都谈不上真正的入仕为官,但他仍然以致仕还乡的官员自诩,显得从容而自得,一扫之前怀才不遇的愤懑和仕途困顿的嗟叹。晚年的文徵明,书画更为精绝,又因其品行醇厚、德高望重、提携后辈,主盟文坛数十年,成为了吴中文化的象征。晚年的祝允明,“益事著述,洞观天人,或放浪山水间,翛然乐也”[22],也全然没有了之前的压抑和痛苦。一方面能全情投入著述之中,写出更为犀利、更为洞彻的文字,一方面又诗酒风流、纵情快意,精神上皆归于“乐”境。总之,文、祝二人最终走出了科举、仕途与本心、人生的矛盾与困境,实现了表里如一的真诚。
而唐寅是彻底不幸的。这种不幸,主要应在于他陷入了出仕无望的境地之中。他在参加会试之际因牵涉舞弊而下狱,自此失去了参加科举的机会和举荐入仕的可能。但他依然心存念想,在宁王招取幕僚之际,还是希望能借此机会在功业上有所作为。入幕相对贡举更次一等,文徵明就拒绝了宁王的邀请,而唐寅仍选择了前往,可见其不甘之心。然而,未等他有所施展,宁王已密谋造反,他靠着装疯而勉强保命逃离,这令他陷入更加不堪的境地。自此,出仕之路彻底断绝,也没有了任何弥补的可能。生命最后十年中,唐寅表面上放浪形骸,纵情酒色,实际上是无比痛苦、绝望和幻灭的。袁袠《唐伯虎集序》中如实展现了唐寅晚年心态①参见唐寅《唐伯虎全集》附录,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24页。,也说明其放纵的生活方式,都是笼罩在科考无望、入幕遇险阴影之下的自我放逐和麻痹而已。相较文徵明、祝允明,唐寅似乎更为浪荡不羁、沉湎声色,这是因为他需要更强烈的刺激来消释痛苦。他晚年诗作中颇多沉痛的自悼之词,其中夹杂着心有余悸、空幻、失望等复杂的情感,读来着实令人悲叹。在彻底的绝望中,无论寄情山水、放浪行迹、纵情声色,甚至信佛、信道,各种超脱的手段都无法完成自我度化,始终感染着悲伤的底蕴。与祝允明、文徵明一样,唐寅本无心于仕途,也并未怀抱用世、成圣贤之志,只是他对于出仕的阴影,终生未能走出。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士人的基本处世原则,使士人在进退出处之间维持心态平衡、立身不失。然随着物质经济、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变化,又基于吴中地域文化和文人交际圈本身的特点,明中期吴中文人在立身、处世上已经打破了传统儒士的规范,进不愿“兼济天下”,退也不能“独善其身”。吴中地域文化环境为他们建立以个体生命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土壤,同时,科举时风的裹挟与家族责任感的压力,又迫使他们必须进入作为传统社会标准的科举出仕的评价体系中。在科举与出仕上的种种徘徊和矛盾,也可以归结为外在的社会价值体系与内在的以个体生命为中心的精神世界失衡而产生的困惑与焦虑,这也正是其仕隐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