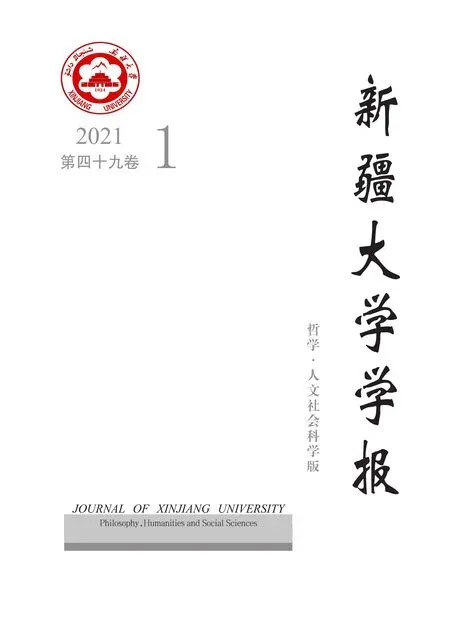从借词看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
——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曹利华
(攀枝花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四川 攀枝花617000)
吐鲁番地区自古是民族汇聚融合之地,位处丝路要冲,各民族往来不绝。晋唐时期曾存在过车师、匈奴、柔然、敕勒、吐谷浑、突厥等漠北和西北游牧民族,龟兹、焉耆、鄯善等西域诸族,粟特、波斯、天竺等异域外族,以及主体民族汉族,民族构成非常复杂。大量域外民族入籍此地,编户为民,与汉族百姓杂居相处。交流交往中他们的语言、思想、饮食生活、风俗习惯等必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涵化。有民族交往就有词语借用发生,借词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民族交往的见证。
而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研究,多从政治、人口、民族通婚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语言接触角度来考证的几乎尚属空白,我们则选取这一独特视角开展实证性研究。对吐鲁番出土文书①本文所言吐鲁番出土文书,主要指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1992—1996),所收文书年代最早为前凉升平十一年(367),最晚为唐大历十四年(779),所以我们的研究限定在4—8世纪这一历史时段,文字上表述成晋唐时期。中汉语的借词,一方面从语言角度分析其怎样一步步进入汉语进而汉语化的,另一方面从民族交往视角透析一个个借词所蕴含的广阔历史时空及民族交往的历史波澜,最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分析该地区民族交流交往的特点与动因。这对当今新疆地区各民族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吐鲁番出土文书借词例析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主体居民是汉族,出土文书也多为汉文文献,我们研究该地区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借词,也以汉语为主体,对汉语的粟特语、印度语、突厥语及西域语言借词分别从商业、生活、军事、宗教方面各选1例进行分析,以小见大。
(一)商业类借词——萨薄(萨宝)
高昌国特别是唐西州时期的吐鲁番已取代敦煌成为重要的国际物资集散中心,民族间商贸往来频繁,商路畅通,馆舍店肆林立,商品种类繁多,交易场所固定,且交易量大,②参见殷晴《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与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99-105页。名贵香料一次交易达800斤,三分之一左右的交易在100斤以上③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54号墓所出《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记录了麹氏高昌某年1—12月高昌市场中货物交易双方向官府所交的称价钱数。该文书共71行,记录进出口交易37笔,涉及人数49人。其中昭武九姓41人、龟兹白姓2人、翟姓2人、车姓1人,突厥1人,汉人1人,不明身份1人。买卖的商品中金、银、鍮石、硇沙来自波斯、粟特地区,香料主要来自印度,丝则产自中国。名贵香料一次交易达800斤,丝达80斤,硇沙达240斤,三分之一左右的交易在100斤以上。见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第450-453页。。该地区还出现大量的专职经商人员,掌握至少两种语言的译语人、双语人①参见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城研究》,1995年第1期,第97-103页。等。高昌国对外来胡商也有一套规范且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并利用自己的商业地位获取利润,如对胡商收取称价钱、藏钱等。该地区还采用当时丝绸之路上统一的货币标准,以波斯银币、罗马金币作为重要的货币流通手段。②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13页。
“萨宝(萨薄)”是丝绸之路上最具商业特色的词语之一,指粟特这个典型商业民族政教合一的商队大首领,后成为中国的官职名称。
“萨薄”一词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两见:其一,《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卅日祀部班示为知祀人上名及谪罚事》(1-136)③吐鲁番出土文书用例,引自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的,在文书名称后采用“(册数-页码)”格式标注,这里指该文书见于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1册第136页,《吐鲁番出土文书》之外的用例,则直接注明。该标示方法借鉴了王启涛先生《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虎牙孝恕,萨薄□□,虎牙孟义,(缺)”;其二,《高昌义和六年(619)伯延等传付麦、粟、㲲条》(1-355):“萨薄□□传粟□斛给与车不六多。”
从以上两则出土材料的完整图版可知,第一件文书是高昌国祀部长史虎威将军麹顺签署的参与祭祀者名单,名单中“萨薄”与“虎牙、参军、中郎、主簿”等官员并列,尤其是文书第9行“虎牙孝恕,萨薄□□,虎牙孟义”,“萨薄”前后,皆有虎牙将军,无疑这里的“萨薄”为高昌政府授予之官职。第二件文书显示“萨薄”具有传令的权力,亦即具有官员的权利。文书中之“萨薄”与史籍中出现的“萨宝”“萨保”等书写形式表意相同,应属一词之异写。④姜伯勤等先生持此观点,荣新江先生则认为“萨薄”“萨宝”各有所指。具体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27-234页;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收于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8-143页。以下论述过程中统一写作“萨宝”。
“萨宝”一词是随着粟特商队进入西域、吐鲁番,进而到达中原的。粟特这个典型的商业民族为满足丝绸之路上远途跋涉和大宗物资运输的需要,以及抵御丝路上的自然灾害和人为劫持,他们组成规模浩大的商旅队伍,动辄几百人,在丝路沿线城镇留居,形成粟特聚落。商队首领在粟特语中称为“萨宝”,他们不仅管理日常事务,还管理商队中的祆教祭祀活动,于是便形成了典型的宗教首领与商队首领合一的“萨宝”管理体制。
这种体制为高昌国和中原统治者所认可,并使用这一名称设置相应官职,主要负责外来聚落事物管理,甚或国家宗教事物和外来事物管理。于是,“萨宝”逐渐成为唯一一个进入隋唐王朝官职系统的外来词。⑤参见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48-279页。《隋书·百官志》载:“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1]《通典》载:“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2]1103;视流外官职载“四品,萨宝府率;五品,萨宝府史”[2]1105-1106。《旧唐书·职官志》载:“开元初唯留萨宝、祆祝及府史,余亦罢之。”[3]1803可见,至迟在隋朝中原统治者已启用“萨宝”一职,并且在使用上有所改造,职责范围上有所扩大。
语源上看该词源于粟特文“s’rtp’w”。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等均持此观点,⑥参见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8页;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9-92页;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72-173页;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5页、第78页。此不赘述。
关于“萨宝”源于粟特,隋唐时期的墓志碑铭也可提供有力支撑。“无论是在北朝、隋唐,实际担任萨保或萨保府官职的个人本身,抑或唐人墓志中所记载的曾任萨保的其曾祖、祖、父,绝大多数是来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4]例如:
君讳元敬,字留师,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乐,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仵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5](《唐康元敬墓志》)
君讳诃耽,字说,原州平高县人,史国王之苗裔也……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师萨宝。[6](《唐史诃耽墓志》)
康姓、史姓是粟特大姓,这些墓志材料历史再现了粟特人由原居地康居等地迁徙至中原,并在中原担任官职,逐步融入汉人社会的历史。从材料可以看出墓志主人的曾祖一代已经在中土为官,四代之后他们应该已经完全融入汉人生活,在这个小范围内实现了民族交融。
总之,“萨宝”这个粟特词语进入汉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汉民族与粟特民族历史交往的见证。“萨宝”被借入汉语和被广泛使用的过程,正是汉粟民族交往不断加深的过程。“萨宝”一词的借入和广泛使用,可以折射出当时粟特商队历尽艰辛来到吐鲁番和西域各地进而辗转中原的情景,折射出粟特人入朝为官而逐渐受汉族文化融入汉族的过程,这只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一个微小缩影。
(二)生活类借词——迭(㲲)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有胡瓜、胡饼、葡萄等西域食物,有龟兹锦、波斯锦等西域锦缎,有“迭”“氍毹”等印度引进的生活用品。以下我们以“迭”为例,探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生活类借词。
“迭”,或写作“疊”,在晋唐之际用来指棉花,是音译词。后来“疊”增加形符写作“㲲”,或借用汉语固有词“绁”表示。①为更好体现“疊”“㲲”的对比和变化,这里“疊”我们没有写成简体字“叠”。使用过程中不断本土化,最终被“棉”“棉花”替代。
吐鲁番出土文书关于“迭”的最早记录一般认为是吐鲁番阿斯塔那39 号墓出土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升平十四年(370)残券》(1-2),该文书残存两行:
1 升平十四年□□□九日宋永(缺)韩小奴□瓜地二亩
2(缺)迭四尺
“宋永□”买或租了“韩小奴□瓜地二亩”,以“迭布四尺”作为土地卖买或租借的条件。
高昌国时期“迭”的使用明显增多。如:《高昌章和十八年(548)缺名随葬衣物疏》(1-288)中有“罗迭百匹”,《高昌延昌二年(562)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1-145)有“迭千五百匹”。“迭布”在当时已被当地百姓广泛使用,如《高昌缺名随葬衣物疏》(1-443)记有“细迭衫一具”,《高昌作头张庆右等偷丁谷寺物平钱帐》(2-109)记有“迭被一,平钱八文”,《高昌僧道瑜斛斗疏》(1-462)“智谦”下小字标有“六月卅日迭袴”等。唐西州时期的文书中普遍用“绁”来代替“迭”,如《唐景龙二年(708)西州交河县安乐城宋悉感举钱契》中,宋悉感“陆拾肆文作绁花贰拾斤”(3-553),《唐宝应二年(763)西州高昌县周义敏纳布抄》记“周义敏纳三月番课钱绁布壹段”[7]。
史籍中相应时代也有关于“迭”的记载,并且对其性状用途有所描述,字形上作“迭”或“叠”。《梁书·高昌传》载,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迭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8]811。《南史·高昌传》记载与此完全一致②〔唐〕李延寿《南史·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3页。。《旧唐书·高昌传》载:“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3]5294从以上记载和描述,基本可以推知“迭”当指我们现在所言之“棉花”。
语源上“迭、㲲、绁”乃梵语之音译。印度种植棉花历史悠久,与中国交往源远流长,棉花从印度引进非常自然,且典籍记载可资印证,又有语音上的很好对应,这都为“迭”源于梵语提供了充分证据。
印度河流域是世界上种植棉花最早的地区之一,“印度河两岸是草棉的老家,种植以供纺织。尼罗河两岸被认为是亚麻织物的发祥地”[9],该流域已发现公元前2000 年左右的棉花及棉织物残片③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55-156页。。而中国和印度的交往源远流长,《史记·大宛列传》:“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10]可见至迟在公元前2 世纪时,中国蜀地产品已远销印度,又辗转他地。而中国之丝绸,至迟在公元前3 世纪已传入印度。④参见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3-164页。印度从中国引进丝绸、蜀布、邛竹杖,中国从印度引进棉花,自然而然。
从典籍记载看,一般认为最早记录棉织品的中国史籍是《宋书》。⑤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7-36页。《宋书·夷蛮传》载:“呵罗单国治阇婆州。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迭古贝”[11],言“白迭”产天竺国。同时,佛教典籍中对“迭”“㲲”等多明确其借词性质,如慧琳《一切经音义》“㲲缕”条云:㲲,“音牒,西国草花萦也……本无此字,译经者权制之”[12]1120。“㲲”条:“《切韵》:细毛布。今谓不然,别有㲲花织以为布”;“㲲衣”条云:㲲,“西国草木花布也。经作叠”[12]1438。
从语言学角度讲,“迭”上古音属定母质部,拟音为kiět;中古音则属见母入声屑韵,拟音作kiet,与梵语karpasi(或karpasa)在语音上有明显对应关系。综上“迭”源于梵语无疑。
可见,汉语的印度语言借词不仅仅停留在影响最大的佛教层面,随着印度文化、西域文化的影响,民族交往的深入,印度日常生活类词语也被引进汉语。
另外,“焉耆、龟兹”等西域地名,以及“葡萄、胭脂”等日常生产生活词语,都是借词。就葡萄而言,不仅仅引进了物种、借来了词语,而且葡萄物种作为民族交往的见证,在吐鲁番地区广泛种植,并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支柱产业。据估算麹氏高昌时期吐鲁番地区有葡萄田3 063亩,约占高昌垦田的3%—4%之间,①参见卢向前《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葡萄酒及葡萄酒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0-120页。有学者通过对文书《北凉承平年间(443—460)高昌郡高昌县赀簿》的分析,估算葡萄园种植亩数达总耕作亩数的10%之多。②参见殷晴《物种源流辨析——汉唐时期新疆园艺业的发展及有关问题》,《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第17-26页。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葡萄园的租借买卖、雇佣作人在葡萄园从事劳作等,亦见葡萄种植的普遍和规模,可知至迟在晋末葡萄种植在吐鲁番地区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之一,延续至今。
(三)军事类借词——胡禄
“胡禄”,指以兽皮为材料制成的盛箭的袋子。《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胡禄”见3 例,均和弓箭同现。《唐唐幢海随葬衣物疏》(2-20)记有“胡禄弓箭一具,攀天丝万万九千丈”;《唐缺名随葬衣物疏》(3-110)记有“白银刀带一具,胡禄弓箭一具”;《唐某府卫士王怀智等军器簿》(4-5)记有“王怀智,弓一,并袋,刀一口,胡禄箭卅支”。
“胡禄”一词见于汉语典籍最早在南北朝时期③参见张永言《汉语外来词杂谈》,载《语文学论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年,第239 页;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442页。,该时期汉人骑兵已开始使用“胡禄”④参见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4-102页;杜朝晖《从“胡禄”说起——兼论古代藏矢之器的源流演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第90-96页。,后来唐代军队的配置中也常见“胡禄”,如“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觽、毡帽、毡装、行滕皆—”(《新唐书·兵志》)。一般认为“胡禄”为音译词,是突厥语Külüg 的对音。⑤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28页。汉文典籍中“胡禄” 还有“胡簶”“胡箓”“胡簏”“弧箓”“箶簏”“葫芦”等多种写法,也是“胡禄”为音译词的重要证据。
吐鲁番地区何时使用“胡禄”并借用其读音,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我们认为应该不晚于中原及江南地区。南北朝时期,高昌与柔然、高车、突厥等游牧民族政权交往甚多,高昌往往为其所役属,受其封号,并与之联姻,客使往来不绝,并且在经济文化上受到明显影响。高昌男子往往“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袴”[8]811。高昌王麹伯雅朝隋归来曾下令“解辫削衽”,“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1]1847。高昌男子“胡服”“辫发”,尚骑射之风,所以“胡禄”在该地区较早被引入是非常自然的,并且吐鲁番出土文书也证明,高昌国时期男子的随葬衣物疏中均有弓箭出现。⑥参见裴成国《论高昌国的骑射之风》,《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2页。总之,“胡禄”的引入是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交融过程中,积极吸收外族文明的结果。
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有大量的突厥语借词,拙文《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突厥语的汉字译音看6—8 世纪西北方音声母之特点》列汉语的突厥语借词46 组,⑦参见曹利华《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突厥语的汉字译音看6—8世纪西北方音声母之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82-188页。多地名、官职,也有器物类音译词,此不一一分析。
(四)宗教类借词——胡天
语言接触交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超越单方向的词语借用,出现两种接触语言的成分共同构成一个词语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构成的词一般称为“合璧词”。⑧参见游汝杰《合璧词与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语言研究集刊》(第九辑),第183-195页。就汉语与其他语言构成的合璧词而言,指一个汉语语素和一个非汉语语素构成的词。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大量的以“胡”为构词语素构成的词语,如胡豆、胡瓜、胡床、胡椒、兴生胡、作胡等。“胡本匈奴(Huna)专名,去na 着Hu,故音译为胡。后世以统称外族。”[13]历史上,春秋战国之后匈奴往往被称为“胡”,如“粤无樽,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郑玄注:“胡,今匈奴”(《周礼·考工记》)。匈奴人也常自称为“胡”,《汉书·匈奴传上》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14]西域各族对匈奴也称为“胡”,《汉书·西域传》载鄯善、疏勒、龟兹、焉耆等国都有“击胡侯”“击胡君”“击胡都尉” 等官职,这些西域小国屡为匈奴所犯,专设击胡官职,这里的“胡”特指匈奴。后“胡”的使用开始泛化,泛称西北诸族,甚至可指称所有汉族以外的民族,如干宝《搜神记》卷二有: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①〔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页。
以下我们选取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常见的宗教类合璧词“胡天”简要分析。
“胡天”,是一种敬奉“天神”的外来宗教,故称“胡天”。《魏书》《北史》《隋书》的《高昌传》均记载,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史书之“天神”应是出土文书所言之“胡天”。
“胡天”一词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有出现,如吐鲁番县城郊安伽勒克古城出土《金光明经卷第二题记》:“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15]阿斯塔那88号墓所出文书《高昌高干秀等按亩入供帐》(1-200):“十二月十五日,一斛,付阿(缺)祀胡天。”另外《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1-238)记有:“面六斗,供祀天”;《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1-400)中“祀天”字样六见。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从外族传来而为当地百姓所认同和接受,并最终在语言文字中沉淀,期间的民族交往和认同是不言而喻的。
该教传入吐鲁番地区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载。《魏书》载: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神龟中(518—520)其国王居和多遣使上书贡物。”[16]《梁书》载:滑国“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陁始遣使献方物……事天神火神”[8]812。当为记录该教最早的正史文献。陈垣先生推断该教于5 世纪传入我国,并考证该教所信仰的神为天神,至唐初缩写“天神”二字始创“祆”字,“祆者天神之省文,不称天神而称祆者,明其为外国天神也”[17],以后史书多称该教为“祆教”或“火祆教”,我们赞同此观点。
公元前6 世纪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吸收波斯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崇尚火和日月星辰。该教不久开始向外传播,而重要传播地之一就是粟特地区。资料显示,在公元前6世纪已经有粟特人信仰该教了。②参见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页。萨珊波斯时期(前224—625 年)该教被定为国教长达400 年。这一时期该教在粟特继续发展,并且进一步与粟特民族文化碰撞交融而有了明显的粟特文化特征。③参见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吐鲁番地区的祆教应该是由粟特聚落带入的,因为四到八世纪粟特人基本垄断了中亚到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④参见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明在唐朝的交融》,载《中国学术》第1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6-67页。并且吐鲁番是粟特商队的一个重要聚集地。祆教不仅被粟特人随着他们庞大的商队带入吐鲁番地区,同时还被带入了西域的于阗、鄯善,带给了北部的嚈哒、突厥等民族。《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于阗“好事祆神”,《魏书·西域传》载:焉耆“俗事天神”。又《梁书·滑国传》载嚈哒“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记:“突厥事祆神。”[18]突厥与粟特关系密切,突厥文便是在粟特文基础上创制的,⑤参见牛汝极《从借词看粟特语对回鹘语的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01-112页。粟特人在给突厥人带来其他文化信息的同时带来宗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粟特人给西域带来敬奉天神的祆教之后,自己却在民族交往的洪流中改信了佛教,至少部分人改信或兼信了佛教。高昌国时期的吐鲁番地区“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尤其是麹氏高昌时期礼敬佛教尤为虔诚,玄奘法师停留高昌期间,每将讲经麹文泰则“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隥,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19]21及别高昌,麹文泰“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19]21。可以想见,佛教在当时的地位和盛行程度。随着粟特人大规模长期定居高昌国和后来的唐西州,编户为民,在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进一步接受了佛教。①当然该时期佛教可能通过其他渠道传入粟特本土,《隋书·康国传》有“俗奉佛,为胡书”的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40页;《旧唐书·康国传》云:“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0页。粟特人信奉佛教在姓氏名籍中也有很好体现,如曹佛儿(1-281)、康僧祐(1-324)、曹僧居尼(2-33)、安僧迦(2-42)、史仏住(2-107)等佛教特征尤为鲜明。据文书年代可知,这些姓名都出现在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一般在公元7 世纪左右。另外,敦煌文书中的50 余种粟特语文献,多是佛教经卷,②参见吉田丰《敦煌胡语文献》,载《讲座敦煌·卷6》,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第187-204页。时代已到晚唐五代,亦能很好说明佛教在粟特人中流传之广。宗教信仰属一个民族的观念层面、意识层面,一般不会轻易改变,粟特人宗教信仰的改变,除粟特人适应能力极强之外,只能解释为该地区民族交融程度之深。
二、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的特点及动因
(一)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的特点
1.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全面深入
通过对借词的分析,可以看出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的民族语言借词,不仅有反映政治和军事交往的职官名称“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多波旱、鍮屯发”“将军”“都督”“公主”及军事用品“胡禄”“乌骆马”等,还有商品交往方面的“萨宝、兴胡、兴生胡、波斯锦、疏勒锦”,生产生活类的“葡萄、胭脂、胡瓜、胡饼、氍毹(毛毯)、迭(棉布)”,以及反映人们宗教信仰的借词“胡天”等。可见,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各族人民既有物质层面的交流又有精神层面的交流,既有军事政治层面的交流又有生产生活方面的交流,民族交往已深入到政治、经济、生产生活、饮食服饰、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
2.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双向互动特征明显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具有明显的双向互动特点,即一个民族在同化其他民族的同时也受到影响,民族的交流融合是双向互动的。这种双向互动,既对交往双方产生影响,又对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
该时期吐鲁番地区的主体民族为汉族,统治者为汉族,通用语言为汉语,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独立小王国。入居此地的各民族多受汉文化影响,他们改用汉姓、取用汉名,如具有鲜明汉文化特色的姓名“康阿狗、康善憙、康善财”等,该地区民族交融的主流应该是其他民族的汉化。不过也应该看到,不管是麹氏高昌还是阚氏高昌基本都依附于突厥、柔然等北方民族,受其封号,汉族衣着服饰等多从突厥,男子皆辫发左祍,着胡服,善骑射。可见汉族在影响其他民族的同时自身也受到影响。
又如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粟特人本信祆教,敬奉天神,“萨宝”既是他们祆教信仰的领袖祆教仪式的主持者又是粟特商队的主宰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维系粟特人商业特色及其生存的根本所在。但是随着粟特人大规模的长期定居高昌国和后来的唐西州,在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中进一步接受了佛教。粟特人给西域带来敬奉天神的祆教之后,自己却在民族交往的洪流中改信了佛教,至少部分人改信或兼信了佛教。粟特人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文化的接受者;同化其他民族的同时也受到影响,民族间的交往是双向的,影响是相互的。另外,汉语中有大量的粟特语、突厥语、印度语借词,相应的其他语言也有大量的汉语借词。这些都是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涵化的结果。
3.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多元文化交融特征明显
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借词的分析,我们发现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文化多元,形成了中原文化、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交流融合、兼收并蓄的景象。
首先,表现出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该地区居民以汉族为主体,政治体制上也基本与中原政权一致,这里的官私文书基本上全部以汉文拟定,并且出土了大量儒家经典抄本,尤其是唐西州时期,改高昌国为唐西州,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受中原影响更进一层。可见该地中原文明的特征明显,中原文化是这里的主体文化。
其次,具有明显的游牧文化特征。高昌国与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突厥有长期交往,并且接受其封号,出土文书保留了“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多波旱、鍮屯发”等系列音译借词。不仅从突厥语借来箭矢之器“胡禄”,借来良马“乌骆马”,最主要的是接受了北方民族的骑射之风,以及与之相应的“胡服”。“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袴”[8]811成为高昌男子的典型装束,虽高昌王下令“解辫削衽”[1]1847而不能禁。一个汉族为主体,汉文化为代表文化的社会,社会民众皆着胡服,辫发垂之于背,并具骑射之风,足见汉族与北方民族的交往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汉文明对北方草原文明的认可与接受。
第三,西域文化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文化。波斯锦、龟兹锦、棉布(迭)等各种商品在丝绸之路上往来贩运,高昌国及唐西州客舍馆驿的设立,以及藏钱、称价钱制度的执行,显示了该地区作为丝路商品集散地的商业性质。另一方面高昌与西域诸国交往频繁,粟特、龟兹、焉耆、鄯善等西域国人皆有入籍高昌(西州)者,各民族交错杂居,共同劳作,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对当地必有影响。波斯锦、龟兹锦、粟特锦不仅仅作为商品输入,还带来他们的审美和绘画艺术,如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在当地建筑、绘画等方面皆有鲜明体现。
第四,多元交融的宗教文化。祆教由粟特人带入,敬奉胡天,“胡天”一词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有出现,对“胡天”的信仰既有个人行为,也有国家行为,可见高昌国对胡天的重视,以及民众对祆教的接纳程度。佛教在高昌地区更为流行,上至高昌王下至普通百姓信众更为广泛。玄奘法师停留高昌期间,每将讲经,高昌王麴文泰则“躬自迎引,低跪为隥,日日如此,不胜虔诚”。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在出土随葬衣物疏中有很好体现,一般都会在死者姓名前冠以“佛弟子”,或有“持佛五戒”字样。同时在随葬衣物疏中还融合了中原传统宗教道教的成分,如道教咒语、符咒等。可见,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宗教信仰是丰富的多元的,粟特人信奉祆教而兼信佛教,汉人在本土宗教道教基础上不仅接纳了佛教,还接纳了祆教、摩尼教等其他民族宗教。这些都只能在民族成分复杂、民族交往频繁、民族交融深入的区域进行。
总之,吐鲁番地区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并存的局面,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同时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交融动因分析
吐鲁番的交通区位、政治地位决定了其为多民族交融之地。该地位居丝路要冲,处于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同时与北方高车、突厥、铁勒等游牧民族仅有一山之隔,又自然地成为南北交流的必经之地,高昌为东西南北交流汇合之处,为该地区的民族交流文化融合提供了先天的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加上该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光热充足,水资源丰厚,可以作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提供充足的物资资源。所以历史上不管是中原王朝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对该地区的争夺都比较激烈,或实行羁縻政策,对该地区都有重要影响,在语言、文化等各个层面留下了历史剪影。
交往需要是民族交往的根本动因。从政治地位看,高昌乃绿洲小国,处在中原政权、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之间,为保全实力,维护国内安定,需依附于更为强势的政权来寻求保护。一方面与中原政权长期保持联系,一方面又臣服于高车、柔然、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甚至在北方民族间周旋。社会经济方面,加强交往的愿望十分迫切。高昌国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商业贸易,从中获取商业利润,获得马匹等必需品。而大漠南北方游牧民族也不能单靠牧业生存,需要大量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不断通过战争及政治等手段对绿洲国家进行控制,主要是通过双方和平贸易以获取源源不断的生产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源。西域、中亚诸国尤其是粟特,为获取利润,以该地为重要的中转市场,形成大的聚落,定居吐鲁番地区。
三、小 结
我们选取“萨薄”“迭”“胡禄”“胡天”4 词分别代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汉语的商业类、生活类、军事类、宗教类借词,考证它们在汉语中的使用、流变及其所折射的民族关系。发现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文化多元,形成了中原文化、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交流融合、兼收并蓄的景象;民族交往全面而深入,各民族长期交错杂居,融洽相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涵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期和谐共处。长期交往中,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格局不断巩固,休戚相关的一体化观念与意识不断形成与强化,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