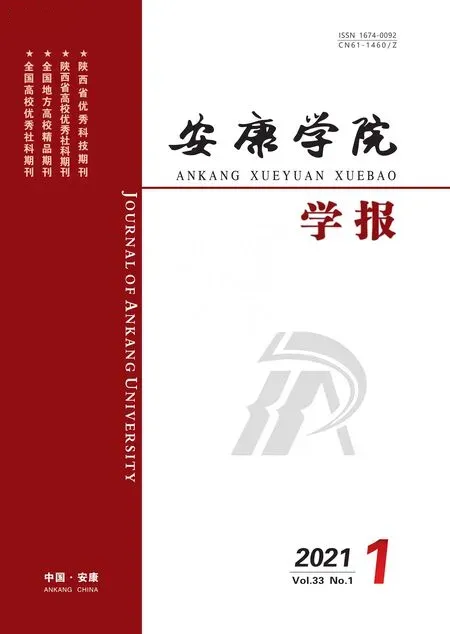佛教的弱者伦理关怀思想与实践及其启示
孟凡平
(淮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1]马克思的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宗教的产生源于被压迫者对现实苦难的反抗。佛教的产生即是如此。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有感于古印度奴隶社会中底层民众的悲苦生活,创立了以引导众生脱离“苦海”为目的的佛教。印度佛教传入我国后,一方面保留了小乘佛教注重个人自我解脱、自我觉悟的精髓;另一方面不断与传统中国文化相调适、相融合,日渐发展成为自利利人、自觉觉人、自度度人的大乘佛教,凸显了佛教伦理对众生的深切关怀,为救助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弱者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2020年之后,虽然我国的脱贫攻坚事业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社会生活中依然不乏弱者存在,如残疾人、孤寡老人以及流浪人口等,他们仍然需要伦理关怀。在扶助弱者的工作中,大乘佛教的伦理关怀思想与实践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佛教的弱者伦理关怀思想
佛教是一种伦理型宗教,其全部教义和实践都是以人为中心、围绕人的苦乐悲喜展开的,如“众生平等”“慈悲利他”“福田”和“布施”等思想学说,包含着对弱者的深切关怀。
(一)众生平等:弱者伦理关怀的思想基础
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源于佛教的基本理论——缘起论。“缘起”指世间万法相互依存,因缘和合而生。缘起论认为,世界上没有独立存在的事物,万物的产生、存在和消灭都是相互关联的——“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2]杂阿含经,卷十因此,众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其他条件而存在。既然众生皆是因缘和合而生,那么众生在缘起上就是平等的,所以,“众生平等”意即因缘和合而生的万物就是平等的。“众生平等”不仅仅是缘起平等,而且在成佛的可能性方面也是平等的,即“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通过修行成佛,达到与佛平等的地位。
在佛教教义里,“众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众生”指有情众生,即有生命、有情感的事物;广义的“众生”指因缘和合而生的万物,既包含有情众生,也包含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等无情众生。“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2]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一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肯定了一切生命的价值,在客观上冲击了古印度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反映了社会底层民众反对不平等制度、渴望消灭痛苦、获得幸福的心声。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都倡导平等,但佛教对平等的追求超越了儒家和道家。与儒家立足于血缘亲情的等差之爱不同,佛教的缘起论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也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自我存在,即所谓“无我”。所以,佛教因“无我”而对众生一视同仁。这种无我之爱在外施的过程中,不掺杂任何私心,以拔除众生痛苦、使众生获得快乐为己任,表达了佛教关心、怜悯芸芸众生的深切情怀。概言之,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包含了生命权的平等和成佛权利的平等,既是关怀弱者的逻辑起点,也是关怀弱者的思想基础。
(二)慈悲利他:弱者伦理关怀的核心精神
依照缘起论的观点,既然万物都是因缘际会,那么人就不可能主宰自身的命运,人生无常,而且面临着诸多痛苦,如生老病死的痛苦、求而不得的痛苦等。于是,如何摆脱痛苦、拔除痛苦并求得快乐就成为人们的必然需要。在佛教中,满足这种“拔苦得乐”需求的佛法就是“慈悲”。
“慈悲”是佛教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是佛道的根本,是佛法中最重要的原则。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萨见众生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后世苦等诸苦所恼。生大慈悲救如是苦……一切诸佛法中慈悲为大。若无大慈大悲。便早入涅槃。”[2]大智度论,卷二十七此处之所以说“大慈大悲”,是因为慈悲有层次之分——人我有别的慈悲是小慈悲,平等无差别的慈悲是大慈悲,是最高层次的慈悲,即“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其中,“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2]大智度论,卷二十七。“慈悲”的展开即“四无量心”,也即“慈悲喜舍”。慧远所著《大乘义章》有云:“爱怜名慈,恻怆曰悲,庆悦名喜,亡怀名舍”,又进一步解释道:“谓以菩提起于慈心。以救众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于喜心。以摄智慧行于舍心”[2]大乘义章,卷十一。“四无量心”内在地具有利他精神,“慈心多缘无乐众生。悲心多缘有苦众生。喜心多缘得乐众生。舍缘究竟解脱众生”[2]大乘义章,卷十一。广为人知的观音菩萨就是“四无量心”的化身,其不仅对众生一视同仁,而且能够以大慈大悲之心开示教化,解救众生度脱苦厄。概言之,“慈悲”是众生成就佛果的解脱心愿和精神力量,其主旨就是爱护众生,给予众生以欢乐;怜悯众生,拔除众生痛苦,蕴含着对生命个体的关怀。这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必然成为佛教散发慈悲心的主要对象。
以慈悲利他为根本宗旨,佛教提倡“诸善奉行”。佛教所说的善行通常指“十善”,即“永离杀生偷盗邪行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邪见”[2]十善业道经,卷一,也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此“十善”有两重内涵,“一是要尊重众生,不侵犯众生,不损害众生,进而要帮助众生,乃至度脱无限众生,也就是慈悲博爱;二是排除一切不利于自我修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也就是说,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行为都要有利于修行成佛”[3]。其中,尤其以“不杀生”为首善,认为不杀生“即得成就十离恼法。何等为十。一于诸众生普施无畏。二常于众生起大慈心。三永断一切嗔恚习气。四身常无病。五寿命长远。六恒为非人之所守护。七常无恶梦寝觉快乐。八灭除怨结众怨自解。九无恶道怖。十命终生天”[2]十善业道经,卷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教视生命为宇宙间最高价值,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因此,历史上的佛教高僧多深怀大慈大悲之心,致力于赈济、养老、育婴、医疗等慈济事业,表达了对受苦受难的众生的悲悯之情,显示了佛教为众生的幸福而忘我的慈悲利他精神。
(三)福田布施:弱者伦理关怀的实践举措
部分佛教思想在传播过程中日渐与中国本土伦理思想相融合,在化解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冲突的同时,也增强了佛教伦理自身的功利性和世俗性。例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道赏善而罚淫”等相契合的“因果报应论”就在流布过程中以种“福田”和“布施”为举措,践行了佛教关怀弱者的慈悲精神。
种“福田”意即播种可生长和收获福德之田。大乘佛教的经典之作《佛说诸德福田经》有云:“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2]佛说诸德福田经,卷十六佛家将“福田”分为“敬田”和“悲田”:受恭敬之佛法僧等为“敬田”,受怜悯之贫病者为“悲田”。此“二田”中,佛家认为关怀贫病孤老等社会弱者比恭敬佛陀更重要。《佛说像法决疑经》有述:“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2]佛说像法决疑经,卷八十五此外,佛教中还有“三福田”“四福田”“七福田”“八福田”之说,但无论哪种说法,提倡悲悯与救助贫弱病苦之人的“悲田”思想的影响都是最为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是佛教慈善救济事业的直接理论依据。
“布施”意即以福利施予人,是一种出于怜悯、同情和慈悲心的自利利他之举。《大乘义章》有曰:“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于他名之为布。辍己惠人目之为施。因其布施缘物从道名布施摄”,并解释说:“布施摄中差別有四。一者财施。二者法施。三无畏施。四报恩施。菩萨思愿与无贪俱起身口业,舍所施物济慧贫乏名为财施。以法授予名为法施。济拔厄难名无畏施。菩萨先曾受他恩慧,今还以其财法无畏酬报彼恩名报恩施”[2]大乘义章,卷十一。因此,依据佛教的因果业报理论,人人都应该以善业求善果、以善行求善报,因此,佛教要求教徒们以自己的智力、财力、体力去救助处于苦难之中的人,或者满足有需求的人,甚至不惜损失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去“布施”。
综上所述,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为关怀弱者奠立了思想基础,慈悲利他精神则直接指向社会弱者,福田观念和布施观念植根于佛教对因果业报的认识,推崇大慈大悲,劝导人们弃恶从善,倡导社会成员平等友爱、扶贫济困,体现了对弱者的伦理关怀,也为佛教的慈悲精神找到了实践路径。
二、佛教思想影响下的弱者伦理关怀实践
佛教传入我国之后,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积极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干预社会生活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佛教的慈善实践就是其关怀弱者的历史印迹。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战乱频繁,老百姓流离失所,饱受贫病之苦,急需救助。在佛教慈悲精神的推动下,一些佛教寺院开始在赈灾、济贫、救病、护生等方面发挥作用:北魏文成帝时建立了由国家控制的“僧祗之粟”制度,“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4],一方面用于供养僧尼,维持他们的宗教活动,另一方面用于赈灾消困,救助百姓;齐武帝之子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5]。梁武帝曾下诏:“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创办“孤独园”,要求“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6]除了这些具体的慈善制度和机构外,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界人士还成立了“无尽藏”,专门用以救济贫穷困苦之人,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基金会。
隋唐时期,慈善机构逐渐规模化,佛教慈善在整个社会慈善事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中尤以唐代的“悲田养病坊”为典型。“悲田养病坊”最初是设置在寺院内的一种半官半民的疗养所,旨在“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7],包含了救济贫困、疗养疾病、抚慰孤独等功能,后来逐渐演变为寺院的慈善事业。长安年间,朝廷还专门设置了负责监督佛教寺院病坊的“悲田使”,并确立了“寺理官督”的“悲田”管理体制。及至后来,在政府的经济资助下,唐朝各州道的佛寺都普遍设有“悲田养病坊”,对于救助弱者、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朝延续唐朝旧例,创办了慈善机构“福田院”。《宋史》有记载:“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8]这类“福田院”在北宋的救助机构中影响很大,通常由僧人主持院内事务,政府派官吏定期巡视,指导工作并统计救助人数、上报开支等。此外,宋代比较有影响的慈善机构还有收容“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之人的“居养院”、收养救济贫病之人的“安济坊”、收养弃婴和流浪儿童的“慈幼局”和“举子仓”、安葬无主尸骨及家贫无葬地者的“漏泽园”等,有些寺院还储备了名为“长生库”的慈善基金,在灾害救济、疾病医治、恤孤济贫、捐资助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出现了由僧侣主持的仿效唐代“悲田养病坊”的“惠民药局”“养济院”等慈善机构。这一时期,随着儒释道合流趋势的加强,佛教慈善观与儒家伦理和道教伦理进一步结合,特别是随着“劝善书”的广为流布,慈善布施、恤孤救寡的观念进一步向社会推广和渗透,僧尼、道士及士绅、商人纷纷响应,民间慈善力量大增,使得这一时期涌现了众多的善会和善堂,如“从施济内容看,有对贫民的施衣、施米、施粥等,有对病人的施药、诊治,有对死者的施棺、代葬及义塚;从施济对象看,有收容孤老贫病者的安济堂,有收容流浪者的栖流所,有收养婴儿的育婴堂、保婴堂、恤孤局等,有救济贞女节妇的恤嫠会、清节堂、儒寡会等,有管束不肖子弟的洗心局、归善局、迁善局等,有综合性实施救济的芹香堂、同仁堂、博济堂等”[9]。
及至近代,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曾号召将寺庙财产十分之二的部分用于办理慈善事业,其提出的“人间佛教”一词更是彰显了对弱者的伦理关怀精神。另一位佛教领袖圆瑛法师不仅强调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还强调“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并且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佛教的慈悲精神,先后兴办“宁波白衣寺佛教孤儿院”和“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以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筹办了“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十六省水灾赈济会”“上海灾区佛教救护团”以及“上海难民收容所”等佛教慈善团体。在一定意义上,“人间佛教”把人们对传统佛教的信仰与社会慈善结合起来,为佛教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提供了理念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佛教慈善组织秉持“弘法利生”的使命感,继续弘扬佛教慈善事业。目前,我国(主要是中国大陆)的佛教慈善组织有“救济型慈善”“服务型慈善”和“弘法型慈善”三种基本类型[10]。其中,救济型慈善主要以财物救助为主,如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服务型慈善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还帮助受助者解决实际问题,如上海玉佛寺觉群慈爱功德会;弘法型慈善以弘传佛法为要务,如中华佛陀文教基金会,主要活动是放生护生、印经音像、佛寺佛学院建设等。在这些慈善事业中,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是救济型慈善,如新中国第一家佛教慈善机构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事业基金自1994年12月成立以来,“通过捐资希望工程、资助病残、扶贫济困、安老慰孤、义诊施药、放生护生、赈灾救急、祈福消灾等具体方式进行各项慈善活动,服务于社会。截至2008年底,发放各类善款总额超过4500万元”[11]。
应该说,传统社会中的佛教慈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阶级矛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在社会救助和保障方面的不足,其彰显的伦理关怀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团体通过具体的慈善事业帮助弱者摆脱痛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因此,可以说佛教的发展历史本身也是一部关怀弱者的实践历史。
三、佛教弱者伦理关怀思想与实践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弱者救助事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部分弱者的不利地位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特别是物质方面都有了一定保障。取得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后,如何合理恰当地满足弱者的不同需求,我们可以从佛教的弱者伦理关怀思想和实践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维护弱者的人格尊严
“慈者多缘贫穷众生。”[2]大乘义章,卷十一佛教的“慈悲”精神直接指向社会最底层、最弱势、最无助和最可怜的人群。如果说“无缘大慈”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那么“同体大悲”就是对身处困厄之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从而产生悲悯之情,然后衍生出对他人的同情并愿意以自己的所有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实施“予乐拔苦”的慈悲行为。而且在佛教教义中,相对于“慈”,佛教更重视“悲”,提出要“常生悲心”。这是因为,佛教认为人生“苦海无边”,宣扬佛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引导众生脱离“苦海”,即“拔苦”。所以,在“慈悲”二者中,“悲”是“慈”的基础,“慈”是“悲”的延伸和扩展,即所谓“慈从悲来,悲必为慈”。“先就慈悲明相资助。慈欲与乐无悲拔苦与乐不成。由悲拔苦与乐方熟。故悲资慈。悲欲拔苦无慈与乐苦终不去。由慈与乐苦方可离。故慈资悲。次用慈悲共喜相资。慈欲与乐悲欲拔苦。”[2]大乘义章,卷十一对社会弱者而言,要想获得幸福快乐,首先就要脱离痛苦,脱离痛苦是获得幸福快乐的逻辑前提,“佛家的‘予乐’并非衣食住行满足之后的愉悦,在人们没有通过‘觉悟’真正从精神压力或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前,那些旨在通过外力施加的‘予乐’不会激发无忧无虑、发自内心的‘大乐’。所以,佛家慈善的德心,虽然表现在‘予乐之慈’,却立足于‘拔苦之悲’”[12]。慈悲的精神实质不仅仅是在物质上使他人摆脱困境,而且要在精神上使人获得做人的尊严。正因为如此,佛家要求布施者在布施时态度要友善,要尊重恭敬接受布施的人,不让受施者感到压力和不安,并且要不怕艰难困苦,亲自及时布施,布施时不损害第三人。概言之,在众生平等的观念基础上,佛家对受助者的真实需要一视同仁,对弱者的关怀是源自本心的悲悯和尊重,没有居高临下,没有态度歧视,维护了弱者的人格尊严,实现了物质救助与情感关怀的合二为一。
(二)注重精神关怀和心灵关怀
佛家“布施”尤其强调“法施”。“法施”即佛家向凡夫俗子讲解人情事理之真谛,目的在于使凡夫俗子摆脱“三毒”,即“贪、瞋、痴”三种烦恼状态,达到心灵和谐,离苦向乐。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觉醒法师在“佛教慈善与社会服务”研讨会上指出:“佛教慈善以其无私的济世思想引导和调节道德行为,对每个不幸者给予必要的关怀和帮助,这种关怀和帮助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鼓励。作为物质慈善的重要补充,精神慈善值得积极并大力提倡。”[13]佛教伦理关注人的心灵成长,在帮助弱者消除烦恼,减轻痛苦的同时,能够给予弱者更多的精神关怀和心灵关怀,帮助他们获得精神的安宁和幸福,这是佛教伦理关怀的精神核心,比世俗的物质关怀更具有道德感召力和超越性。比如,汶川地震之后,佛教界开展了以“安身、安心、安生”为宗旨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救济工作,特别是举办各种消灾祈福法会,对遭遇巨大灾难的同胞进行心理安抚和精神抚慰,帮助灾区群众重新树立了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发挥了佛教伦理的精神关怀和心灵关怀功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关怀弱者是一项需要爱心和慈悲心的事业,特别是当弱者在精神、情感方面陷于困顿时,精神关怀和心理关怀就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伦理关怀。我国的部分弱者不仅表现为物质上的贫困,而且在情感上也较为贫困,特别是一些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他们由于缺乏情感慰藉而觉得孤独痛苦,社会各界在关怀这部分弱者时不仅要给以应有的物质关怀,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情感需求,给予精神关怀和心灵关怀。
佛教慈善事业在赈灾、助学、扶贫、医疗、养老、环保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佛教的慈善功能毕竟是有限的,不能满足当代弱者的多样化需求,也不可能代替中国共产党成为关怀弱者的决定性力量。就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看,社会工作业已成为各国救助弱者的重要力量,我国也应该紧跟世界步伐,建立和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制度的保障下更好地关怀和维护弱者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