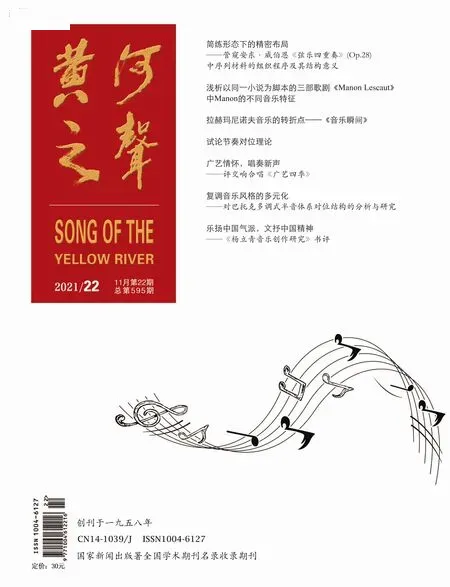荒芜的“原野” 自由的渴望
——探索歌剧《原野》的独特艺术魅力
李 琪
20世纪初,随着西洋音乐的传入,学堂乐歌的兴起,中国歌剧开始萌芽,黎锦辉的12部儿童歌舞剧开创了中国歌剧的先河,中国歌剧创作开始进入探索与发展时期,随之产生了不少优秀代表作品。1987年,一部用西方作曲技法呈现中国本土故事题材的歌剧——《原野》在北京天桥剧院上演了,并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国歌剧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作品。1992年,歌剧《原野》走出国门,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连演11场,震惊了全世界,作曲家金湘也获得“东方普契尼”的美誉。
这部歌剧是中国歌剧发展较为成熟时期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走出国门的歌剧作品。歌剧脚本选自中国现代戏剧家曹禺的同名著作,由曹禺女儿万方担任编剧,作曲家金湘编曲。作品共分为四幕,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我国北方农村的故事:主人公仇虎逃离被困八年的监狱回到家乡复仇,与曾经的爱人金子重逢,经历一番抗争后,仍旧未能逃离封建社会的枷锁,将生的希望留给金子,自己选择勇敢赴死。笔者在本文中从人物形象的多面性、故事情节的悲剧性、角色唱段的戏剧性以及创作技法的融合性四个方面来探索歌剧《原野》的独特艺术魅力。
一、人物形象的多面性
(一)美与丑
本剧中男女主角的人物形象呈现强烈反差的视觉冲击。荒芜的原野上,经历了牢狱之灾与逃亡之苦的仇虎变得面目全非,脸上深深的刀疤,手上沉重的镣铐,驼背又瘸腿,丑陋且粗鲁。而他青梅竹马的爱人金子充满激情活力,风流魅惑,美艳而动人,连白傻子都被迷得魂不守舍。这样两个外在形象强烈对比的两人却拥有同样的灵魂,他们不堪封建社会的压迫,敢爱敢恨,野性自由,为爱付出一切,毅然决然走到了一起。
(二)善与恶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性的多面性,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焦母是一位失明的老妇人,封建古板,对儿媳妇金子极其不满,觉得她既不安分也不贤惠,还夺走了焦大星对自己的关注,甚至用封建迷信的手段“扎小人”对付金子。而这样一个看似恶毒的老妇人,对儿子焦大星和孙子小黑子却是关怀备至,无所不从,全心全意守护着焦家;纯真的焦大星性格懦弱却充满善意,他对儿时好友仇虎热情友好,对媳妇金子百依百顺,可没想到却被二人背叛了,他悲愤交加地举起刀,人性的恶在此时爆发;仇虎满怀恶意回来复仇,却在复仇后愧疚不已,精神崩溃;金子厌烦焦大星,痛恨焦家,但仇虎要杀大星时,她却几次三番为大星说情。在这部剧里,每个人都在善与恶之间来回挣扎,没有真正的好人,也没有完全的坏人,这就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故事情节的悲剧性
歌剧《原野》是一部悲剧性的作品,以仇虎复仇为主线展开,他的复仇之路也是他的悲剧之路。第一幕开头仇虎一身伤痕、戴着镣铐站在舞台上时,鲜明的悲剧性人物形象赫然呈现,满心回来复仇的他却得知仇人已死,爱人已嫁,他痛恨命运不公,被仇恨蒙蔽双眼的他继续他的复仇之路,最终将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杀死,又设计使焦母误杀小黑子,自己则在内疚与恐惧中自杀而亡。
在故事情节中总共发生了三次悲剧行动,设计得非常巧妙,得到了极大的悲剧效果。古希腊戏剧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中对亲属之间发生的悲剧行动划分了四种方式,作曲家在此借鉴。“第一类,认识自己企图害死的人是亲属,也确实把他害死了;第二类,不认识对方是自己的亲属而把他杀害了,杀害之后才发现真相,因而极其痛苦;第三类,原来不认识对方是自己的亲属,由于及时发现,对方得救;第四类,认识自己企图害死的人是亲属,进行杀害,但最后却又不去完成。”①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三类悲剧杀人的呈现方式是最好的,第一、二类次之。仇虎一直在是否让儿时好友焦大星“父债子偿”的矛盾中痛苦挣扎,焦大星得知金子背叛后恼羞成怒地举刀冲向仇虎,于是仇虎趁机说服自己杀害了焦大星,这时作者选用了亚里士多德悲剧论中的第一类方式;焦母想置仇虎于死地,准备在侦缉队捉拿之前先杀掉仇虎,却没想到被仇虎算计错杀了小黑子,这次悲剧行动作者选用了第二类方式。杀害了焦大星的仇虎并得偿所愿的满足感,而是被内疚与恐惧充斥,精神恍惚最终崩溃;误杀亲孙的焦母更是绝望到了极点,踉踉跄跄跑出屋外却发现焦大星已死,她最爱的两个人的死导致她疯了;金子想冲破封建的牢笼,与青梅竹马的爱人仇虎逃离焦家,她以为自己获得了自由和幸福,仇虎却因为杀害无辜焦大星陷入深深的愧疚与恐惧中,金子仍然失去了自己最亲切的爱人。结局出现在仇虎身边的“老朋友”镣铐与开头呼应,就像他逃不脱的封建社会枷锁,将悲剧情节推向高潮。
焦大星无辜被杀,小黑子被焦母错杀,仇虎自杀,所有人都在得与失的纠缠中以“失”收尾,人性的善恶在此时得到赤裸裸的展现,呈现出巨大的悲剧效果。
三、角色唱段的戏剧性
歌剧《原野》共有六个重要角色,作曲家为其分配了不同的声部,并创作富含人物性格的念白、宣叙调、咏叙调、咏叹调以及合唱与重唱片段,充分展现角色个性,丰富戏剧冲突,推动剧情发展。
焦母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却也代表着封建资产阶级,第一幕半念半唱的宣叙调将她古板又狡诈的人物特点展露无遗。她对毫无三从四德的金子很是摒弃,对她的至亲骨肉却疼爱有加。她担心仇虎回来复仇霸占家产,于是报告侦缉队前来捉拿仇虎,夜色中她神色慌张地唱起了《黑色摇篮曲》,音调诡异,声音颤抖,预示着悲剧即将来临。
剧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应属焦大星,金子被掳来当填房,导致他被怨恨;父亲作恶多端,导致他被杀害;母亲狡诈算计,导致儿子被误杀。他害怕失去金子却又懦弱无能,《哦,女人》这首咏叹调将这矛盾的心理充分展现,他万般无奈地唱道,“…原指望一家人和和睦睦,…可现在…不是你哭,就是妈闹,难哪难哪,叫我怎么办?”既可怜又可恨。而作为介绍剧情、情节连接以及预示作用的白傻子,他头脑傻痴却心灵自由。大多为念白式唱段,如介绍金子时“新媳妇好看,傻子看了直打转,新媳妇美,傻子看了流口水。”不但将故事情节巧妙地交待,又将人物性格准确地表达。
仇虎与金子作为这部作品中的主线人物,他们充满着斗争和反抗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向往着幸福和自由。金子在焦家整天被焦母刁难,懦弱的焦大星也只会两方讨好,日子过得暗无天日,《哦,天又黑了》将她无奈又无助、心如死灰的心情表露无疑;后重遇心爱之人,心中爱情的火焰熊熊燃烧,她热情大胆地唱出《啊!我的虎子哥》,流露出对仇虎的浓浓爱意。而陷入仇恨的仇虎一直无法摆脱对焦家的忿恨之情,面对儿时的好友焦大星,《现在已是夜深深》生动地描绘了经历抉择时内心的痛苦挣扎;杀了大星后他逃入黑森林,心中五味杂陈精神恍惚,又看到自己好不容易摆脱的镣铐,唱起了《呵!老朋友》,他感叹命运的玩弄与不公。除了独唱唱段,合唱、对唱和重唱唱段在作品中占了更大的篇幅,展现戏剧情节的冲突。如剧末,仇虎为了保护金子和孩子,决定舍身赴死,两人相拥一起唱道“生下他,他就是天。生下他,他就是地。”(二重唱《你是我,我是你》),剧情也因此推向高潮。他们自己虽然没能携手冲破封建的牢笼,但是他们相信希望就在不远处,孩子代表着希望、生命,更是自由。作曲家在剧中通过不同风格的唱段来呈现截然不同的人物性格,表现角色丰富的戏剧性。
四、创作技法的融合性
歌剧《原野》中,作曲家金湘主要采用西方作曲技法呈现作品,如表现主义、浪漫主义、无终旋律、偶然音乐等等,同时融入丰富的中国民族元素,中西方音乐的融合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一)中国民族元素
1、民族乐器
序幕,大七度的震音率先登场,中国民族打击乐器小堂鼓、板鼓等融入,接着人声哭腔式依次喊出,“黑呀!恨呀!天哪!冤哪!…”似乎是阴曹地府的冤魂哭泣,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氛围,奠定了全剧的音乐基调,更预示了悲剧性结局。
2、民歌唱腔
常五爷受焦母之托来到金子家中监视,聪明的金子用一壶酒套出了实话。她想让仇虎带她离开,于是唱起了她梦中期盼的美景,“大麦呀,麦穗长,漫过那汕头的是那红高粱哪…”这段带有纯朴民谣风的唱段借鉴了辽宁民歌《瞧情郎》曲调,采用“换头合尾”的技法,舒缓的民歌唱腔带有强烈的画面感,表现了金子对今后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3、戏曲韵白
焦母对金子这个儿媳妇很不满意,一上场便阴阳怪气地唱道,“…好看的媳妇,败了家哎,娶了个美人就丢了妈!”,作曲家采用无调性的音乐布景,怪诞的曲调塑造焦母封建古板、阴险狡诈的形象。唱段中充分借鉴了中国戏曲韵白的语调,半说半唱,句尾加上鼻腔哼鸣,将焦母可恨又可怜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二)西洋创作技法
1、偶然音乐
序幕与第四幕中,作曲家都采用合唱与乐队呈现了无调性和声音乐布景,念白和宣叙调部分音调运用偶然音乐的技法,只画出大概音区和时值,实际表演时由演员在谱面范围内即兴发挥。昏暗的舞台灯光效果,哭腔式的念白,爱恨情仇糅杂在一起,将悲剧性的音乐氛围烘托得淋漓尽致。
2、“无终旋律”
“无终旋律”由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率先提出,他想打破意大利歌剧“分曲”形式,让旋律连续不断向前推进,使作品的整体音乐性更强。金湘在《原野》中巧妙地采用了此技法,如第二幕第一首仇虎与金子的对唱,天色已晚,金子催仇虎离开,金子又爱又气地甩了仇虎一巴掌:“滚出去!”,话音未落,又立马撒娇“回来!”,采用念白结尾淡化调性,左手的快速震音紧接进入下一曲咏叹调——《啊!我的虎子哥》。“无终旋律”的使用让这两首曲子自然地过渡连接,也让角色情绪得以保持,保持剧情发展的整体性。
3、表现主义
仇虎与金子逃出焦家,被困黑森林,此时的仇虎为焦大星和小黑子的死内疚不已,一时恍惚产生幻觉。表现主义手法呈现的音乐布景阴森可怖,合唱队员模仿古希腊悲剧中歌队的形式,分散铺满舞台,先是扮演森林当中的树,紧接着化成阴曹地府中的小鬼,分成四个声部先后在不同的调式上唱出主题旋律,“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多调性的和声背景让本就昏暗的场景更加阴森恐怖,使舞台效果更具感染力。
歌剧《原野》作为中国歌剧的经典作品,在中国歌剧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散发出耀眼的艺术光芒,更蕴藏着深刻的人文价值。这部作品以复仇为主线,爱与恨,悲与喜,得与失,对比性的戏剧冲突贯穿全剧,它是多元的,民族与西洋的技法丰富了音乐效果;它是戏剧的,人性的善与恶在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它是悲剧的,又不是完全悲剧的,仇虎以一人之力始终没有逃出封建社会的枷锁,“生下他,他就是天,生下他,他就是地。”孩子是他生命的希望,更是对自由的渴望,被封建社会压迫的农民终将对的命运奋力抵抗,立于天地之间,是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望,更是对获得自由的坚定信念。■
注释:
① 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原野》中焦母命运倒错的三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