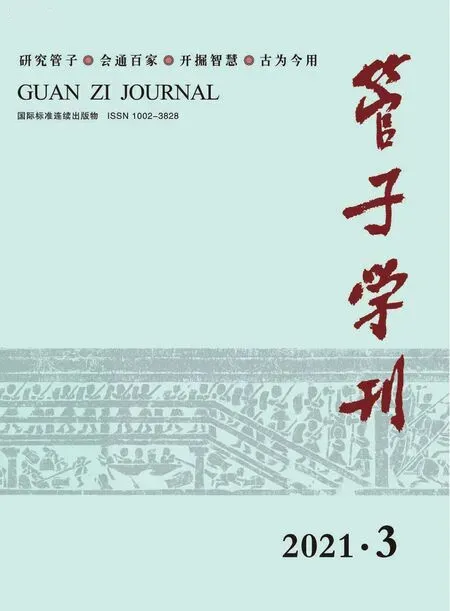先秦法家“俗”思想研究
曲祯朋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说文》言:“俗,习也。”“习,数飞也。”(1)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3、69页。“俗”是反复练习并以此形成稳定的文化传统,即习俗。另,郑玄注《周礼》言:“俗,谓土地所生习也。”(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所以“俗”即是具有地域特色的风俗与产物。从这两个定义来看,“俗”具有稳定性和独特性等特征,所以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礼俗志》中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3)黄遵宪:《日本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384-2385页。另外,瓦拉纳克在对民俗定义时指出:“民俗是没有教条的集体信仰,没有理论的集体实践。”(4)瓦拉纳克(Andre Varagnac):《民俗的定义》(Definition du Folklore),Paris,1938,18.转引自[美]丹·本-阿默思著,张举文编译:《民俗学的概念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没有教条与理论,这体现“俗”的民间性和自发性特点,因而民俗学者认为:“‘俗’应该是以口头、物质、风俗或行为等非正式和非官方的形式创造和传播的文化现象,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它不是什么人宣扬和倡导的内容,也不是人们自我标榜的东西,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和无意地遵循和维护的一种行为规范、道德伦理、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5)王娟:《民俗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自古以来,“俗”对于早期国家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6)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73页。。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周天子通过设有 “小行人”一职,负责四方采集风俗善恶,以此了解和监督各封国的治理状况。《汉书·艺文志》载:“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7)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8页。这也是《诗经》国风之所由来。毛诗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可见“俗”对于早期国家治理之重要性,而如何对待“俗”,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社会治理理念。
法家对“俗”的认识,与儒家、道家等并不相同。民俗学者多重视研究“礼”“俗”之争(9)参见杨世文:《论先秦儒家礼俗观》,《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期,第78-84页;蔡锋:《先秦时期礼俗的发展历程及其界说》,《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65-70页;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第14-24页;等等。,对法家“俗”思想研究多集中在“俗”“法”之争或“法”“术”“势”的讨论上,对“俗”思想本身的关注却不充分。有学者对齐法家和晋法家的“俗”思想加以区分,认为齐法家有“重俗”“因俗”的特征,而晋法家无此特征(10)杨玲:《中和与绝对的抗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194页。。的确,在《管子》思想中,“俗”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和“法”地位相当。梁启超认为,管子的所有政治举措都是为了化民成俗,至善至美的俗是其政治理想(11)梁启超:《管子传》,上海: 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37页。程关松:《礼法合治传统的两种法学范式——以管商为例证的现代解释》,《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5-30页。。但是,所谓齐法家主要是指以《管子》为代表的相关文献,其思想特征、学派属性等尚有讨论的空间,《管子》中的一些篇目是否可以归入法家文献也待考察,所以将《管子》一些篇目所体现的“俗”思想定义为法家思想是有待商榷的。有学者讨论了韩非子政治思想体系中“移风易俗”的重要性,认为“打击当权重臣及其党羽”“贯彻君臣之间的商卖原则”和“移风易俗”是规范和引导政治治理和社会道德形成的重要内容(12)宋洪兵:《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330页。。也有学者认为“俗”与“法”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如吕思勉提出“法俗”概念,“法俗指无形者言,有意创设,用为规范者为法,无意所成,率由不越者为俗。法俗非旦夕可变,故观于今则可以知古也。”(13)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杜文忠认为从风俗可进一步为法俗,从法俗进一步即是法律(14)杜文忠:《法律与法俗——对法的民俗学解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程关松有相似的看法,“礼法同源,根基在俗。在先秦法家中,俗的本体地位提升于太公,阐发于管子,成于商鞅,毁于韩非子”,从法学角度言,“‘俗法同构’才是中华法系的制度论根基,也是礼法合治传统得以形成的决定性机制”(15)程关松:《礼法合治传统的两种法学范式——以管商为例证的现代解释》,第15-30页。。诸说言简意赅,寥寥数语便点明法家“俗”思想若干特征,可惜尚未见专门之研究,“俗”思想之阐发并不系统,也未能将法家“俗”思想以及战国时期的变法活动相联系。故本文试以先秦法家“俗”思想为例,梳理战国时期变法活动中对待“俗”的不同态度,分析法家主导的变法活动的实质及其对治理思想之启示。
一、法家对“俗”的否定性认识
在谈论变革时,我们一般都提到“移风易俗”一词,如荀子言:“乐者,圣王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16)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1页。《说苑·政理》:“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17)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0页。这里,“风”和“俗”似乎是作为偏消极的对象而存在。但总体而言,儒家对“俗”是持肯定积极态度的,与“移风易俗”相比,儒家更主张“不求变俗”,如《周礼·土均》云 :“礼俗、丧纪、祭祀。”郑玄注云:“礼俗,邦国都鄙民之所行,先王旧礼也。君子行礼不求变俗,随其土地厚薄,为之制丰省之节耳。”(1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第409页。《礼记》亦多言“俗”不可变,如“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入国而问俗”“修其教不易其俗”“化民成俗”等(19)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91、358、956页。。荀子更是将“俗”与“道”并提,主张万世不可改易,“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万世不能易也”(20)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76页。。《周礼·大宰》记载治理“都鄙”的八种方式,其中就有“礼俗,以驭其民”,贾公彦疏曰:“俗谓昏姻之礼。旧所常者为俗,还使民依行,使之入善。”(2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第28页。所以儒家不是一味地要求“移风易俗”,而是要因势利导,依从“俗”,美化“俗”,以“俗”来引人向善。所以在治理思想中,儒家虽然强调“礼”的价值与作用,“但在推行‘礼’的实践过程中却往往是礼俗合一的”,“礼”与“俗”始终处于一种“互动互补”的状态(22)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第14-15页。。
与儒家重视“俗”不同,法家对“俗”持相对否定的态度。从法家经典文献来看,“俗”在法家思想中并非必要的、正面的,而是负面的、被改易的对象。法家多认为“俗”代表传统,与当下时事不相吻合,是落后的旧习惯、旧制度,也是前进道路上需要破除的“障碍”。所以法家主张“变法”也就要去除旧俗,也就是“移风易俗”。法家对“俗”的否定认识主要体现在对“俗”与“法”“德”关系的讨论中。
其一,“俗”与“法”对立。《商君书》多次提及“俗”,提出“观俗立法”“立法化俗”的思想。《算地》云:“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23)祝鸿杰:《商子校本·温州古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2页。与之相似的还有“度俗为法”,《壹言》云:“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24)祝鸿杰:《商子校本·温州古甓记:外二种》,第49页。圣人治理国家,关键就在于“观俗立法”。所谓“观俗立法”,就是根据“俗”来制定治理国家的“法”。但需指出的是,这里的“观俗立法”并非体现“俗”与“法”的一致性,恰恰相反,而是体现出“俗”与“法”的对立。因为根据“俗”来制定“法”,而制定“法”的目的却是来化“俗”,“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25)祝鸿杰:《商子校本·温州古甓记:外二种》,第47页。。圣人治理国家需要依据“俗”来制定“法”,制定“法”然后就可以“化俗”,而“化俗”的结果则是民皆“依法从制”,从而摆脱对“俗”的依附。因此,这里的“俗”似乎是作为社会“病症”而存在。针对这个“病症”来制定“药剂”,这个“药剂”就是“法”,通过“法”去除和矫治“俗”。显然,“俗”并没有得到法家的肯定。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对“俗”亦是持“法”“俗”对立的态度。《奸劫弑臣》篇云:“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2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3页。显然,要想国家得到好的治理,圣人就必须采取人民所厌恶的严刑重罚策略,也就是以“法”治国,这样的策略是合乎“德”、合乎“义”的,但同时却是人民所不喜欢的,是与世俗相违背而异于“俗”的。这也表明,在韩非子思想中,“法”是与“德”和“义”相一致的,却是与“民”和“俗”对立的。
其二,“俗”与“德”对立。上文言“法”与“德”相顺,而与“俗”相异,这也说明“俗”与“德”的对立关系。除此,还可以从“俗”的变动性与不可信赖的角度说明二者的对立关系。与荀子所言“成俗”不同,法家主张“俗”是因时而变的:如《商君书》批评当世之君时云:“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27)祝鸿杰:《商子校本·温州古甓记:外二种》,第48页。君主要明察世俗之变化和百姓之情实,才能使刑赏得其宜。和《商君书》相似,韩非子也认为“俗”是处于变化中的,是因时而变的。“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2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45-446页。既然“俗”本身就是变动的,那就不存在荀子所谓的不可易的“成俗”。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在上者要根据时局变化来采取相应措施,要依据时局需要来制定政策,这种情况下,处于变动不居的“俗”不可作为评判的标准,甚至是不值得信赖的,“易俗”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甚至是必然的事情。
法家的“德”是怎样的呢?一般认为法家的道德论乃是一种典型的客观道德论,其道德基础在于客观的“法”“术”和权力,那么这种道德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强制性。有学者指出,韩非子的“德”可分为“私德”“公德”和“官德”,与政治相关的“‘公德’的构建与通过制度性的‘法’和程序性、技术性的‘术’来治理国家不仅并行不悖,而且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29)徐克谦:《私德、公德和官德——道德在韩非子法家学说中的地位》,《国学学刊》2013年第4期,第73页。。因此,在法家思想中,“德”意味着制度化、程序化的模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客观规范,这种规范是值得信赖的。显然,这是与随时变动的“俗”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法家不但主张“易俗”,同时也对“俗”作出了根本性的否定判断,即“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30)祝鸿杰:《商子校本·温州古甓记:外二种》,第18页。。“俗”是与“德”完全对立的,想要达到“至德”的境界则不能合乎“俗”,所以要“易俗”。“俗”是作为一个消极面的存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俗”。对于“俗”与“德”的这种变与不变的矛盾,还可以从法家“变法”与“定法”的角度去分析。前者讲“破旧”,即“根据不同时代制定不同法律和制度”,是为“变法”;后者意指“新制度基本确立后,法律和政策不断改变,甚至朝令夕改,对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实际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不重“变法”,是为“定法”(31)林剑鸣:《法与中国社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2页。蒋重跃先生由此总结出“变法”与“定法”的两重含义。参见蒋重跃:《论法家思想中的变法与定法》,《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第61页。。这里的“变”与“定”正体现出“俗”的变动不居与“德”的客观规范二者之间的矛盾。
另外,《管子》成书较为复杂,既有法家思想,也有黄老道家等思想,不可概而论之。从对待“俗”的态度来看,其与法家具有相似之处,如其主张“立法治俗”,“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32)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19页。。《正世》又言“俗”因时而变的特征,“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33)黎翔凤:《管子校注》,第922页。,《管子》一些篇目也明确主张“变俗”,如:“故法而守常,尊礼而变俗,上信而贱文,好缘而好驵,此谓成国之法也 。”(34)黎翔凤:《管子校注》,第661页。
总而言之,不同于儒家,法家总体上对“俗”是持相对否定的态度,所以法家多是从“法”的角度看待和利用“俗”,认为“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上者要“观俗立法”,根本上是要“以法治俗”。法家的这一思想在其政治实践中多有体现,其变法活动的展开可视为“易俗”思想的实践。
二、法家“俗”思想实践与战国变法活动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封建的束缚已经解除,大一统的专制的压制尚未开始;七雄相互间的竞争激烈,人类各种智能的活动,皆可得到尝试与鼓励。所以这又是一个大自由、大开放,民族的生命力得到空前发展的时代”(3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同时,自由也带来了混乱,诸侯混战,社会陷入困境,进入社会大变革时期,学者称其为“一场罕见的社会革命”,“其兴起之普遍、历时之久长、根源之深厚、内容之丰富、成效之卓著、使命之重大、经验之深刻,实为中外历史所少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社会革命,为后世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36)黄中业:《战国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第5页。。同时,这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也是法家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法家“俗”思想也在这场运动中充分体现。而某种程度上,法家主张“易俗”“治俗”,与“变法”是同步的、一致的,简言之,所谓“治俗”,其实是以“易俗”为主,而“变法”也就是“易俗”(37)黄中业先生认为移风易俗是战国变法的一项总体目标,参见黄中业:《移风易俗是战国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学术月刊》1991年第1期,第53-54页。。
从历史事实来看,战国时期的历次法家主持的改革都与“易俗”有直接的关系,如秦国商鞅变法和楚吴起变法等。商鞅颁布的变法命令涉及许多移风易俗的内容,“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38)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42页。。“变法”是改变古制,商鞅变法即是“更为严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39)石光瑛:《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53页。,“自古帝王之法,至商鞅而变”(40)陈澧:《东塾读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变革古制也就是变革旧“俗”,也就意味着其面临来自世俗的阻力,“变法在一个层面上实际表现为守俗与革俗之争”(41)晁福林:《谈先秦时期的“民”与“俗”》,《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第148页。。对此,商鞅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42)司马迁:《史记》,第2229页。因而,国要强盛则需变法,也就必须变易“俗”,脱离“俗”。具体而言,法家对于“俗”的变革可从四个层面讨论。
首先,就整体而言对“俗”的统一。商鞅变法中“移风易俗”即是整顿“俗”,使“俗”统一。“俗”的一大特征就是形态各异,所以荀子讲“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43)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页。,“俗”是各具形态的,也就是“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44)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4页。,但这对于要求政治秩序整齐划一的法家而言,是不被允许的,而商鞅变法的一大举措就是整顿“俗”,使其整齐统一,因而蔡泽在见到范雎时说:“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45)司马迁:《史记》,第2422页。与统一货币、度量衡等相似,“一其俗”恰恰体现了法家对制度统一的强烈要求。相似的还有蔡泽对吴起变法的描述:“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46)司马迁:《史记》,第2423页。由此可见,“变法”的一大相通之处就在于对“俗”的统一。
其次,从政治层面对君臣之“俗”的改造。从韩非子对商鞅变法的评论也可以看出变法对“易俗”的要求。《奸劫弑臣》篇云“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这个“俗”恰恰就是商鞅变法所要改易的对象。“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4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01页。可见,“古秦之俗”乃是一种废除公法的“人治”,有罪却可以免除,无功却可以占据高位,而商鞅改之,使之“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48)司马迁:《史记》,第2230页。。商鞅实行“斩一首者爵一级”的军功爵制(49)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99页。,使得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秦爵二十等起于孝公之时,商鞅立此法以赏战功”(50)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207页。。与之相似的还有吴起变法。《韩非子·和氏》记载:“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5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96-97页。楚国之“俗”与“古秦旧俗”相似,吴起变法也是改变旧的选任制度,实行新的升迁体制。韩非子对商鞅和吴起“变法易俗”的肯定,也再次体现出法家思想中“变法”和“易俗”的一致性。
再次,从社会层面对家庭之“俗”的改革。《史记·商君列传》载秦之旧俗:“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而商鞅所谓更其制,指的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52)司马迁:《史记》,第2234、2230页。。商鞅此举意在鼓励小家庭增加生产,客观上却打破了原有的宗法大家庭习俗,这也被后之儒者所批评,如汉贾谊对此评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钅且,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53)班固:《汉书》,第2244页。贾谊认为,因为重视经济利益导致家庭疏离,致使亲情淡薄,妇姑相讥,父子好利,从儒家仁义而言,则与禽兽无异。贾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秦俗日败”,即认为商鞅改变了原有的良好的大家庭生活的“秦俗”。相似的还有吴起在楚国的变法(54)关于吴起的学派属性,一般认为:与孙武并称时,属于兵家;和商鞅并提时,属于法家。郭沫若认为商鞅与吴起“说不定还有点师弟的关系”,参见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3页。高华平教授认为吴起为先秦法家的“开山祖”或法家思想形成的代表人物,参见高华平:《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27页。,吴起“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5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0页。,具体对生活习俗的变革,如《吕氏春秋·义赏》载:“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高诱注曰:“变其两版,教之用四,楚俗习久见怨也。”(56)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328页。
最后,从军事层面对战法习俗的变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赵国赵武灵王和楚国吴起的变法中。《战国策·赵策二》记载赵国的守旧大臣反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理由是“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改变合乎传统的“俗”会产生混乱,而赵武灵王则反驳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57)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0页。可见赵武灵王改革的核心即是“易俗”,具体而言就是改为“胡服骑射”,改变赵国旧有的军事技术,按照胡人习俗进行改革,当然这也引起守旧者的强烈反对。
综上而言,在战国的社会变革中,法家也从政治、社会以及军事等多个具体领域对“俗”实现了变革,也同样引起诸多传统势力的反对。在变法者的政治设计与实践中,“易俗”都是其主要的变法内容,甚至是变法标志,可以说,所谓“变法”即是“易俗”。
三、法家的历史意识与秩序模式
上文已具,“俗”是一种具有持久性、自发性和独特性特征的民间文化。简而言之,“俗”即是习俗,也就是传统。那么,法家思想和变法理论为何要求“移风易俗”呢?这和法家的历史意识有关。与儒家复古的历史意识不同,法家主张“不法古”。儒家、阴阳家、道家倾向于把人类历史视为周而复始的循环,法家则把人类社会认定为直线的变化过程,“儒家和墨家加入到法先王的行列中,法家则成为法后王的一面旗帜”(58)魏义霞:《循环论与直线论、法先王与法后王:先秦历史哲学研究》,《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第30页。,也就是“法古”与“不法古”的区别。
法家经典文献明确提出“圣人不慕古”的观点,如《管子·正世》云:“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59)黎翔凤:《管子校注》,第922页。《商君书》也提出“圣人不法古”的思想,“‘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60)祝鸿杰:《商子校本·温州古甓记:外二种》,第19页。,“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61)祝鸿杰:《商子校本·温州古甓记:外二种》,第44页。。以上皆明言圣人“不法古”“不慕古”,因此,作为传统之代表的“俗”在法家思想中自然没有太多的理论价值。
进而究之,为何不可“法古”呢?这就涉及到法家另一个重要理论,即“时变”。《商君书·画策》言:“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62)祝鸿杰:《商子校本·温州古甓记:外二种》,第72页。其分“昊英”“黄帝”“神农”三世,三世各异,是为“时异”,针对“时异”,则应“时变”。就此而言,“法古”意味着不变,“时异”而不能“时变”,势必不能长久。这一思想被韩非子所继承,《五蠹》:“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6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42-443页。这里韩非子并不是否定圣王和圣王之道,而是反对以先王之道治理当今之世、以先王之政治理当世之民。时代变化,风俗变异,古今异俗,“世异则事异”,先王之道政已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事异则备变”,所以韩非主张“变”的历史观或“应时史观”(64)宋洪兵:《“应时”与“复古”之间——共识视阈中的儒法历史观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第48页。,批评固守先王之道的儒者为“邦之蠹”,“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6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56页。。韩非子要求“便国不法古”,要“变古”,“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6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20页。。这是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正因此,其对作为传统的“俗”持一种否定态度,而“俗”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易俗”也就是理所应当的选择了。
既然法家反对“法古”,也就对传统经验的有效性表示质疑,并进行否定判断,这是法家秩序模式的一大特征。须知,儒家秩序是一种经验模式,是在不断试错中逐渐进步、发展,所以十分重视传统,主张“法古”,这也就是哈耶克所言的“自生自发的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self-organizing order)。法家与儒家注重“法古”的传统不同,法家主张“所有社会制度都是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是一种“组织秩序”或“人造的秩序”(artificial order,directed order)。一派“主张有机的、缓进的和并不完全意识的发展,而另一派则主张教条式的周全规划;前者主张试错程序,后者则主张一种只有经强制方能有效的模式”(67)[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除了对传统经验加以否定的特征之外,法家秩序模式的第二个特征即是对“民”的自主能力的否定。儒家“从俗”“美俗”是基于对“俗”的信任基础上,重视“俗”本来之面貌,遵从“俗”并加以引导,而法家则是采取直接改造甚至消灭的方式,简单粗暴,体现的是对“俗”本身具有的自发向上的可能性的抹杀,也就否定了“俗”自身能够发展成为一种良好秩序的可能性。此处“俗”代表的是一种基层的、源自“民”自身的力量,否定“俗”,也就否定了“民”的自主性。因此,与“以法治俗”“以法化俗”相对应,法家主张以法“制民”“胜民”“塞民”。
进一步追问,法家为何对“民”如此不信任呢?这源自其对“民”这一群体的认知水平和性情的两重判断(68)宋洪兵先生称之为对国民性的知识与性情的两层判断,参见宋洪兵:《先秦诸子“愚民”论考辨》,《求是学刊》2008年第6期,第132页。。一是知识层面的“民愚”,即《商君书·更法》言:“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69)祝鸿杰:《商子校本·温州古甓记:外二种》,第18页。《韩非子·显学》称:“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7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64页。“民智不足用”,也就是说民不具有自主学习向善的能力。二是性情层面的“民性喜乱”,即《韩非子·心度》言:“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7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74页。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民”具有向善的自主性。那也就说明,秩序的实现不可避免地有赖于外在的客观规范,且这种规范是具备完全强制性特征的。也就是说,法家秩序模式必然有赖于强有力的权力和强制性的规范才可实现,这也就是“法”的实行。对此,史华兹在讨论作为术语的“法”时即已提出:早期“‘法’这个术语主要意义还是指模型或技术。‘法’这个词内蕴的强制性涵义很可能随着法家的兴起,随着刑法以及所有的强制性模型都朝着强制性的方向转变而得到了强化”(72)[美]史华兹著,程钢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上,作为被治理的对象,“民”并不具有任何自主性的能动作用。法家已经将“俗”的自主性完全抛弃,而以“法”的绝对外在强制性取而代之。
综上,法家之所以对“俗”采取直接改易、抹杀的方式,原因在于法家对以“俗”为代表的传统和经验的不信任。在法家历史意识里,时事是变动不居的,传统和经验也就不具有指导当下的价值,所以主张“不法古”。既然不可“法古”,那么法家思想中的秩序则是一种全盘规划、深思熟虑的产物,其实现有赖于强有力的强制性规范的实行,也就是“法”的实施。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言法家“俗”思想,乃是一种概括的表述,所谓“易俗”,也是从整体上讨论,至于细节之处,法家对“俗”也不是完全否定,如《韩非子·五蠹》讲“称俗而行”(7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45页。。虽然这里的“俗”有其特定语境,但也可见法家并不必然否定“俗”的正当性。但从整体上言,尤其是在与“法”的比较中,法家以“易俗”为主,“称俗”为辅,这是大致无疑的。
四、法家“俗”思想与社会治理启示
对法家思想与战国变法的成败评论很多,如对商鞅变法的评价:从商鞅个人的命运而言,认为这次变法是失败的一次政治活动,但从政策的延续以及对秦国的影响而言,此次变法则是成功的(74)对于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学者研究颇深,历史经验总结也十分丰富。如齐思和先生《商鞅变法考》文中“变法成效考”节,从秦国成就霸业角度认为“商君事业大成功”,参见齐思和:《中国史探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275页。郑良树先生对商鞅变法及其思想的影响和效应进行细致说明,参见郑良树:《商鞅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325页。黄中业先生对战国社会变革进行了十个方面的总结,参见黄中业:《战国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第5-13页。高专诚先生对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进行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认为只有商鞅变法是比较成功的,参见高专诚:《战国前期的变法活动及其历史教训》,《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6-9页。以上都从个体到总体对变革进行了深入分析。。整体而言,法家思想引起了战国时期的变法思潮,秦、赵诸国通过变法富强起来,在兼并战争中占据主动,最终秦国一统天下。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法家思想是成功的,但若是放到中国历史整体中去考量,即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以法家思想为主却二世而亡的秦制并不能算得上成功。当然,法家与秦政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厘清。自汉以后,儒家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而法家思想逐渐从台前走向了幕后,但无论怎样,法家思想及其变法实践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也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地方。法家思想中的“俗”思想,对当下社会治理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从“俗”的特征而言,法家“易俗”思想为何不被接受呢?主要有两点。其一,“俗”本身具有自发性的特征,更容易被接受。不同于被圣王制作的“礼”,“俗”本身就具有一种自发性与非强制性的特征,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基本概念》中指出:“‘习俗’是一种外在方面没有保障的规则,行为者自愿地事实上遵守它,不管是干脆出于‘毫无思考’也好,或者出于‘方便’也好,或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且他可以期待这个范围内的其他成员由于这些原因也很可能会遵守它。”(75)[德]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编:《韦伯文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当然,当个体不遵循“俗”行事时必须忍受“或大或小的不快与不利”,但却不是强制性的、暴力的威胁,“人们依循民俗一般并非迫于民俗的暴力威慑,或由这种暴力威慑产生的恐惧,而是民俗给人一种社会安定感和相互亲近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秩序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传统的依恋”(76)万建中:《民间文化的多维视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其二,“俗”是在民间流行的小传统(77)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 提出 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大传统指少数具有思考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士绅所代表的文化,是在学堂或庙宇之内培育出来的;小传统指一般社会大众所代表的文化,是自发的萌发出来的。参见[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著,王莹译:《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与“民”关系紧密,“俗”被接受与“民”之地位的提升密不可分。叶国良指出:“礼是在较大范围内施行的,俗是在较小范围内施行的;礼是大传统,俗是小传统;礼往往经过国家的规范成为法律、制度,俗只在民间施行,不具强制性。”(78)叶国良:《中国传统生命礼俗》,上海:上海书店,2017年版,第1-2页。“俗”在先秦诸子中逐渐被重视,恰恰体现了“民”的地位被重视的过程。许嘉璐指出:“随着封建制度的完善,奴隶的数量在减少,自由人的比例渐渐增大,与之相适应,‘民为本’的思想不断明确,在无伤政治制度之大体的前提下的民之俗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79)许嘉璐:《礼、俗与语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65页。以“俗”为表现的 “民”已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因而,儒家重视“民”的地位,顺应“俗”的自发性,既是对传统的认同与继承,同时也增加亲近感,减少施行障碍,这也是为何儒家的“从俗”被历史所采纳,而“俗”文化一直作为小传统在中国稳定存在并持续发展。儒家也并非完全顺从“俗”,对不符合儒家教化思想的“俗”也是持“移风易俗”的态度,但是其方式较为温和。与之相反,法家建立在“以法治俗”的基础上的“易俗”则更具有强制性,“人民对于自己固有的习俗总是恋恋不舍的,凭借暴力让他们放弃习俗与风尚,就会给他们带来不幸。所以,不要去改变他们,而要引导他们自己去改变习俗和风尚”,而用“法”来改变风俗的做法则“太专横”,不如“借助另一种习俗和风尚去改变原有的习俗和风尚”(80)[法]孟德斯鸠著,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62-363页。。
其次,从传统、秩序与法家主导的变法的关系来看,法家“俗”思想在社会治理上具备哪些价值和启示呢?可从社会治理中对传统的认识以及秩序构建中人民的自主性这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其一,尊重历史传统。任何变革都不是凭空产生,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汲取营养并逐步完善的。对于社会文明的改善,应当“旨在点滴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的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81)[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第37页。。当下我们必须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必然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哺育与滋养,一味地对历史传统加以否定,改革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基础也会变得不牢固。
其二,秩序建构要注重人民的自发性,思想也要经受人民的检验。徐复观指出:“任何好的学术思想,根据任何好的学术思想所产生的政策,若是为人民所不好,为人民选择所不及,则只好停止在学术思想的范围,万不可以绝对是真、是善等为理由,要径直强制在政治上实现。”(82)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从法家“俗”思想来看,显然其违背了“俗”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性特征,也没有与“民”相结合,没有重视“民”的意愿,“严而少恩”,其结果也必然如徐氏所言:“极权主义者可以假借任何学术思想为名以实行残暴的极权统治,亦即是任何学术思想在此种情况之下皆可能变为杀人的工具。”(83)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第138页。秦亡于苛政或是其最佳的注脚。工藤元男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容认为秦要“彻底清除各地在原有价值体系上存在的风俗习惯,全面施行秦的法律”(84)[日]工藤元男著,莫枯译:《云梦秦简〈日书〉所见法与习俗》,《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第111页。。陈苏镇先生对此表示认同,认为秦律与各地风俗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而秦律的强制推行,势必引起各地人民对秦政的极大反感,这也成为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85)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37页。。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当人们希望改变习俗和风尚时,就不应该求助于法律,否则可能太专横。不如借助另一种习俗和风尚去改变原有的习俗和风尚,这样可能较好。”(86)[法]孟德斯鸠著,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第362-363页。与其强硬给予,不如引导其自发生成。
总而言之,相较于儒家重视并借助“俗”在社会治理与教化上的作用,法家“易俗”思想则显得消极许多,原因主要在于法家历史意识和对国民性的判断,使其对传统经验的有效性以及对普通“民”之自主能力加以否定。进而,在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家无法信任传统带来的经验,也无法给予“民”足够的自主权,而只能依赖于强制性的、规范性的“法”,这也是最终导致法家思想及其主导的变法活动走向失败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尝试,法家“俗”思想及其历史实践都是十分有益的经验,值得当下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