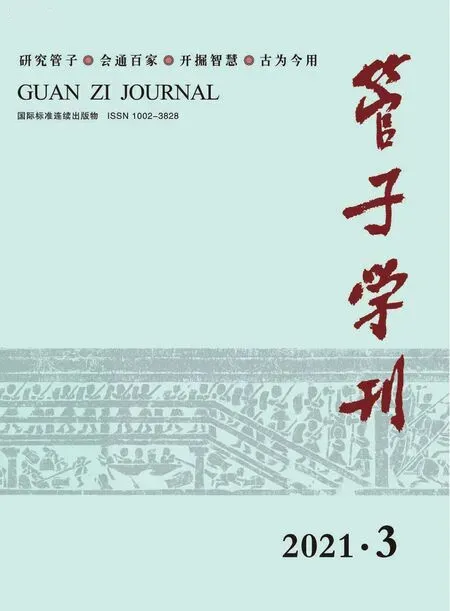韩非子的人论:性情之变常统一
张 娜
(燕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0)
一、问题的缘起
人性是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人性论不仅规定了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方向,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宗教、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礼俗、人生态度等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论断之后,战国时期诸子对人性问题展开积极讨论,提出了几乎所有的可能性。孟子倡言人性善,告子则认为人性无善无恶(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4页。,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3)杨宝忠:《论衡校笺》(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荀子力主人性恶。韩非子作为荀子的弟子,诸子的后劲,面对前贤对人性问题的论争,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有人认为韩非子和他的老师荀子一样,是性恶论者,如冯友兰指出:“法家多以为人之性恶。韩非为荀子弟子,对于此点,尤有明显之主张。”(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61页。韩非子持性恶说的观点在学界曾一度流行,目前的拥护者也不在少数,细读其相关论述,不难发现儒家思想的印迹与影响。如果用儒家之仁义道德为标准来衡量韩非子的思想,性恶说似乎是必然的结论。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认同以一种外在的标准,有时候甚至是某种对立并充满敌意的标准作为尺度得出的结论呢?自然,标准的选择难免受到主观成见的影响,无法做到完全的合理与公正。然而,坚持以儒家之仁义道德为标准来判断韩非子的思想,结论的可信性必然大打折扣。判断标准之外,性恶说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从《韩非子》的文本中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所谓的性恶不过是有意识地推论得出的结果。
围绕以上问题,一些学者指出韩非子对人性只有事实描述,并未做出善恶判断。张申认为韩非子和荀子的人性论有原则性的区别,韩非子的人性论既不是性恶论,也不是性善论,而是无善无恶的自然人性论(5)张申:《韩非是性恶论者吗?》,《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第86-93页。。张申的观点影响很大,与性恶说几乎形成二选一的局面。即使有一些看似新颖的观点,如“自为”人性论(自利人性论)、二元结构论以及人性三类型说(6)赵如河认为韩非子不是性恶论者,而是持“自为”人性论,且追求新的伦理价值,见赵如河:《韩非不是性恶论者》,《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4期,第50-52页。韩孟英明确提出韩非子的人性论是自利人性论,见韩孟英:《论韩非所处的时代及自利人性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81-84页。宋洪兵认为韩非子的人性论是由“圣人”之聪明睿智之性、虚静无为之心与“众人”之好利之性、欲利之心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见宋洪兵:《善如何可能?圣人如何可能?——韩非子的人性论及内圣外王思想》,《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72-81页。詹康指出,韩非子所论的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自己至上的放肆利己观、在礼法规范下求利的审慎利己观、追求美善与利他的高贵利己观,见詹康:《韩非论人新说》,《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26期,2008年9月,第97-153页。等,事实上都是在张申观点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上述观点避免了以儒家为标准进行研究带来的弊端,比性恶说具有明显的解释优势,更贴近韩非子思想的实质。尤其是后两种观点,大致将韩非子所论及的各种人性表现都囊括在内。但是,韩非子为什么拒绝对人性之善恶做出判断呢?韩东育认为,“好利恶害”的人情是客观自然的而非想定自然的,是后天的反应而非先天的预设,所以很少见到法家往人情身上贴“善”或“恶”一类的价值标签(7)韩东育:《徂徕学与日本早期近代化的思想启蒙》,《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19页。。刘亮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认为韩非子主要以人行为的效果作为考察角度,加之评价标准不一,无法为人性善恶提供一致的答案,只能停留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层面(8)刘亮:《〈韩非子〉为何不评价人性善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123-124页。。或许韩非子强烈的政治实用主义使得他认为,人性善恶与否并不影响政治家对政策的制定,只要了解人性的普遍表现并善加利用、诱导即可。
目前来看,韩非子人性恶说与韩非子人性非善非恶说两种观点的论争,基本成为韩非子人论研究的范式。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在关注同一个话题,即沿着孟子、荀子的思路,对韩非子的人论做出性善、性恶的道德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然而,人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首先,人性与人情应该明确划分开来,分别考察。从性恶说观点的论证来看,不少论者实际上是将人情当作了人性。而詹康的三分法将人性与人情混合在一起,宋洪兵的观点实质上是分离了人所具有的精神性与生物性,将这两者分别给予了圣人与普通人。因此,有必要对人性、人情进行清晰地界定,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来考察韩非子的人论。实际上,在韩非子看来,人情可变而人性不变(9)由于对人性与人情的认识不够精确,某些观点认为人性即人情,对二者的使用不加区分,并以为人性会发生变化。如王立仁:《论韩非的“因情而治”》,《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54-60页。。由此,韩非子的人论具有变常统一的特点,与他的历史观和道理论保持着理论上的一致。其次,人性之善恶问题之外,还有思想家对人性持有乐观或悲观的态度问题。或许,思想家对人性之态度,更能决定其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的圣人情结反映了古人对人性的乐观态度。由此,思想家们选择了君主制和精英政治,没有认真地思考如何从制度上防范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腐败、作恶的问题。他们希望借助掌握最高权力的圣人,来改造普通人的人情,从而实现治世目标,只不过所看重的路径不同而已。实质上,圣人与普通人在性情方面的特点,也是一种变常统一的辩证关系。
二、韩非子的人论:性情之变常统一
韩非子对人的论述,侧重于其实际的外显行为表现,可以将他的人论称之为“人情论”。情,《说文解字》曰:“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段玉裁引董仲舒、《礼记》、《左传》和《孝经》的话来解释“情”字。《左传》与《礼记》皆将“情”解释为人的各种情绪或情感,董仲舒解释为人的欲望,《孝经》认定性属阳而情属阴(10)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2页。。先秦时期,“情”字除上述含义外,常用的还有“实际情况”的意义(11)这一点也得到出土先秦文献的佐证,见李天虹:《〈性自命出〉与传世先秦文献“情”字解诂》,《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第55-63页;丁四新:《论郭店楚简“情”的内涵》,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儒学与当代文明——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8-1058页。。如《左传·庄公十年》记载:“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12)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孟子·离娄上》记载:“声闻过情,君子耻之。”(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74页。《墨子·尚同下》记载“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14)孙怡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89页。等。《韩非子》中也多有这种用法,如“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群臣之情不效”(15)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116页。等。准此,人情即指人的实际情况,也就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表现出来的行为与基本倾向性。韩非子对人情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陈深在《〈韩子迂评〉序》中感慨:“今读其书,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至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16)张觉:《韩非子校疏》,第1368页。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民夫民妇,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在韩非子的观察范围之内。概言之,韩非子的人情论颇类似于环境论,即人的行为表现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在《奸劫弑臣》篇中,韩非子指出,官员是结党营私还是一心为公,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如果君主“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官员们就“清廉方正奉法”;如果君主昏庸,放任重臣擅专政柄,官员们就“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历史阶段的不同,对人情亦有显著的影响:“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7)张觉:《韩非子校疏》,第1203页。与当今相比,古人看起来似乎更讲道德,在韩非子看来,主要是因为古代的物质资源相对于较少的人口来说比较丰富,人们不用付出多少努力就可以满足基本的需要;而当今之世,生齿日繁,货财相对不足,人们之间出现了残酷的生存斗争。可见,人情是会变的,还似乎呈现出智力上的进步和道德上的退化,《忠孝》篇说:“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18)张觉:《韩非子校疏》,第1272页。古代的人朴实到了愚蠢的程度,因此可以用道德的虚名来哄骗;现在的人则狡猾聪慧,不愿意再听从在上者的摆布。这与《商君书·开塞》所言“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的论述几乎如出一辙,显示出韩非子对商鞅思想的借鉴和吸收。
一些常被用来证明韩非子持性恶论观点的材料,如“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和父母出于利害的计算而杀害女婴(19)张觉:《韩非子校疏》,第729、1129页。,其实都是人的实际行为即人情而非人性。另外,父母、子女之间因物质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以及父母杀害女婴的行为,所表明的不是人性之恶,而应该是社会之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或许才是真正的原因。这也提醒我们,人类生活中的罪恶并不仅仅来源于人性,还有制度、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原因。因此,不能基于韩非子揭露了社会上的罪恶而认定其为性恶论者。值得深思的是,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礼法等措施来“化性起伪”,矫人之恶。如果韩非子也认为是人性之恶造成了这些罪恶,为什么没有提出针对人性的改造措施,而却汲汲于改造社会制度呢?或许在韩非子看来,罪恶的根源并非仅仅在于人性,而更应该归咎于外在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管子·牧民》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与韩非子的观点遥相呼应。如果能够通过善意的合作得到满足,人并不反对像天使一般行善,而一切使人向善的文明之物,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如果只能通过侵略和掠夺得到满足,人也绝不介意像魔鬼一般作恶,而那些教人及逼人向善的文明之物,在此情形下发挥的效用很难得到保证(20)谢红星:《法家“刻薄寡恩”笃论——从“刻薄寡恩”看法家的治理理论》,《法律史评论》2016年总第9卷,第107-130页。。正是因为看到了环境对于人之行为表现的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韩非子才认为孟子所提倡的以自我修德为主的内在途径是不可行的,才坚决要求实施法治,以外在规范作为引导人的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法也好,术也好,实际上都是针对改变环境而提出的策略。法能给人们创造公平正义而有序的环境,术能够通过对执法官员的合理任免与监督来保障法的顺利实施。
不过,细究之下即可发现,在变化的人情之下,其实都有不变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个不变的因素就是自为自利、趋利避害的人性:人“皆挟自为心也”“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21)张觉:《韩非子校疏》,第730、982页。。如果道德能够带来名誉和权势,那么就“竞于道德”;如果智谋能带来更多实惠,那么就“逐于智谋”;如果赤裸裸地以力相搏能称霸诸侯,统一华夏,统治者也会竞相去做这种事情。就普通人来说,父子间的不满与怨恨,也根源于人的自为之心,《外储说左上》篇说:“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22)张觉:《韩非子校疏》,第729页。韩非子通过大量观察人情而总结认为,人性是自为自利、趋利避害的。归纳所得的结论很可能不是纯粹的真理,不能包含所有的事例。事实上,在韩非子的认识中,没有将这种人性绝对化,而是坦然承认这只适用于大多数情况下的大多数人(23)普通人所具有的自为自利、趋利避害的人性与少数“太上之士”和“太下之士”的特殊人性,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变常统一的关系。。对于政治治理来说,这已经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可以成为其出发点。韩非子认为,人性的自为自利与趋利避害,根源即在于人有一个身体,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人必须求得基本欲望的满足,《解老》篇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24)张觉:《韩非子校疏》,第386页。虽然思想家们竭力强调人的精神性,认为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强调人的高贵,但是人之受制于肉体或生物性是无可辩驳、不可更改的事实。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25)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78页。如果人没有身体而只剩下精神性的存在,人类的欲望及由此引发的罪恶恐怕将消失许多。不独中国古人如此认为,古希腊哲学家也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性与非理性的部分,基本上对应于精神性与生物性。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理性、激情与欲望。激情与欲望是生物性的,理性是精神性的。苏格拉底在饮毒酒身亡之前,怀抱着灵魂高贵而不灭的信念,坚信脱离了肉体的羁绊,他的灵魂才能与那些不朽之物为伴(26)[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4页。。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由两部分组成,即理性部分与非理性部分(27)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59页。。理性部分对应于精神性,非理性部分对应于生物性。
在韩非子的思想中,人之精神性与生物性的对立,通过圣人与民众的对立表现出来。宋洪兵认为,韩非子的人性论是由“圣人”之聪明睿智之性、虚静无为之心与“众人”之好利之性、欲利之心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28)宋洪兵:《善如何可能?圣人如何可能?——韩非子的人性论及内圣外王思想》,《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72-81页。,深刻地揭示出这种对立。不过,“聪明睿智”是否可称为“性”,还有待商榷。和普通人一样,圣人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生理欲望。不过,圣人懂得“知足”,这说明精神性完全彻底地控制住了生物性,《解老》篇说:“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故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则不忧矣。”(29)张觉:《韩非子校疏》,第386页。民众与此不同,他们汩没在物质欲望之中而任凭生物性主宰精神性,精神性中唯一能发挥作用的不过是为了逐利所必需的理智计算之心罢了。无论君臣之间还是陌生人、亲人之间,都不过是“以计合”(30)张觉:《韩非子校疏》,第345页。的利害关系。但是,人之自利性虽然可以像荀子相信的那样导致争夺,亦可以促使人们互相合作以求得双赢的利益满足(31)张觉、马静:《论韩非的人性“自利”观——兼驳对韩非思想的种种误解》,《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18-25页。。理智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必须首先或同时满足别人的欲望与利益需求,而且合作能够带给人们比之于争夺或单打独斗更多的利益,这就使人们之间的合作互利成为可能,成为常态化的行为方式。换句话说,人要切实满足自己的欲望,实现自己的利益,离不开别人的合作与协助,因而有可能在自利的基础上,通过互利合作的方式,出现双赢的结果。具有不同禀赋、从事不同行业的人们必须通力合作,各自为社会、为他人付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才能获得相应的利益。那些认为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一定会导致互相争夺之恶果的人们,实际上是将人完全降到了与主要靠本能生活的禽兽相同的水平。这也说明,精神性与生物性之间还有合作相容的另一面。
韩非子对个人私利以及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采取了理解包容的态度,甚至鼓励人们通过国家认可的方式去追求私利。这可以说是韩非子乃至法家诸子的显著特点之一。战国时代,儒墨号称显学,徒众遍布天下。尽管儒、墨在不少问题上观点尖锐对立,但他们在反对个人追求私利方面则有相当的默契。墨子倡导“兼爱”,希望人们能够“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32)蒋伯潜:《诸子学纂要》,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7页。。孟子严“义利之辨”,有将义与利绝对对立化的倾向。孟子虽然大力宣传仁政,希望底层百姓能够从中获利,得以温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仁政的实施完全依赖于统治者个人之仁心的推扩,而无制度上的保障,这就使所谓的“仁政”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一定意义上来说,仁政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对庶民百姓的恩赐,其隐含的内容是仁政所带来的利益并不是百姓应得的,乃是恩赐的结果,故而庶民应对统治者感恩戴德。韩非子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正当的、合理的,因此必须得到制度的保障。人们可以靠主动积极地为国出力(耕战)获得应得的利益,而不必消极地等待统治者的恩赐,《六反》篇说:“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33)张觉:《韩非子校疏》,第1137页。韩非子对个人私利正当性的肯定,具有重大的意义。长久以来,由于受到儒家对个人逐利的敌视和价值低估,个人私利的正当性无法确立,人们即使在追求自己的正当合法利益时,也有一种心理上的不安感。
韩非子的人论包括两个方面:人性与人情。人性自为自利,趋利避害,而且永恒不变;人情则会随着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人性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精神性与生物性。精神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生物性是人与生俱来、不学而能的欲望与本能。人性论的两方面内容,与性字的字义有密切关系。性是生的孳乳字,生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象草木生出地上之形(34)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3版),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页。。《说文解字》云:“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姓、性等都是从生之字,是生字的各种义项分离分化的结果。姓,《左传·隐公八年》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说文解字》云“姓,人所生也”。那些古老的姓皆从女,如姜、姬、妫等,就是明显的例子。性,《说文解字》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许慎对性字的释义,明显受到阴阳五行思想与孟子性善论的影响,并非性字的原义。根据徐复观的研究,性字的原义是指人生而即有的欲望与能力等。性字从生,既系标声,同时亦即标义。欲望与能力乃生而即有,且具备于人的生命之中;在生命之中,人自觉有这种作用,非由后起,即称此生而就有的作用为性。到春秋时代才开始出现作“本质、本性”解的性字新义(3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6-7、53-54页。。性字的原义与春秋时期出现的新义,分别对应了人性论中生物性与精神性这两方面的内容。人的精神性与生物性并存、相容又时而对立,精神性完全控制生物性的是少数圣人,民众则任凭生物性的主宰。如此,圣人之性与民众之性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变与常的辨证关系:如果说民众之性乃是常,那么圣人之性即是变。
人情作为人外显的行为表现,受到内在动机即自利之人性以及理智之心的计算选择这两个方面的制约。无论对人性还是人情,韩非子都没有做出善、恶的道德评价。《备内》篇记载:“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36)张觉:《韩非子校疏》,第308页。内在的人性决定了外显的人情,人们对人性的认识需要通过外显的人情。但是,人性与人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直线对应关系,如同道德意愿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实际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背后的动机也许并不值得称赞。韩非子曾列举一些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这些看似颇具道德意义的事情,从动机上来说都是为了一己私利。质言之,自私自利的动机不仅没有表现出自私自利的行为,反而引导人们做出利他的道德行为。基于人性与人情的区别,可以发现,詹康所提出的人之三类型说(37)詹康:《韩非论人新说》,《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26期,2008年9月,第97-153页。,实际上是将人性与人情拼合在了一起。自己至上的放肆利己观、在礼法规范下求利的审慎利己观、追求美善与利他的高贵利己观三种人性观,前半部分是人情,后半部分是人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因为人情可变;而人性不变,永远是利己的。不仅韩非子,孟子与荀子也注意到了人性与人情的不一致性。孟子固然认为人之性善,但他绝对不会糊涂到认为性善能够使得人所有的行为自动地都是善的,他对人情可能的邪恶表现有着清醒的认识。人如果不能悉心保护培育人性中的善,那么将如《孟子·告子上》所说的那样,“违禽兽不远”(3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10页。。荀子认为人之性恶,但又匪夷所思地提出正是因为人性中的恶,人们才热烈地向善,从而表现出道德的追求与行为,《荀子·性恶》说:“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39)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9页。当然,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40)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354页。。
韩非子的人论具有变常统一的显著特点。他认为人情可变,而人性不变,是常。当然,性情仅在理论上是可分的,实质上统一于人这一整体之中。人情是人性的表象,以内在人性为根基,受外在环境的深刻影响。因此,韩非子不满意于孟子、荀子抽象地谈论人性之先天道德善恶,而是转入历史领域,试图在社会发展的客观环境中认识人的本质(41)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这就使得韩非子的人论与他的历史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他恰恰认为历史是变常统一的。《五蠹》篇记载:“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历史的发展(变)是绝对(常)的,但历史有阶段性,在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发展(变)是缓慢的、不为人所察知的、潜伏的,因此表现出一种稳定性,即“常”。当发展(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质变的点,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变),就进入下一个阶段,再次稳定下来(常)。事实上,变常统一的历史观与人论,均决定于韩非子的道理论,与之保持着理论上的一致。道本身即是变常统一的。道永恒存在,是常,《解老》篇说:“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道虽然与天地共生,但与天地不同,道是不会消散灭亡的,它永恒存在。另一方面,道永远处于流变之中,变即是常:“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常者,无攸易,无定理。”(42)张觉:《韩非子校疏》,第393、388、393页。道肩负着生成万物的责任,而万物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理),因此道也必须随物变化,柔软灵活,不能囿于某种固定的形式。从道与理的关系来看,道是常而理是变。道理论在韩非子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使得韩非子的历史观、人论以及政治思想,无不带有变常统一的色彩。
韩非子的人论大致如此。韩非子人论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人之阴暗面的揭露与深深的警惕。正是因为这些内容,人们把韩非子看成一位悲观主义者。不过,韩非子对圣人的无限信心和他的盛世理想,则彰显了他的乐观主义。
三、韩非子的态度与对策:乐观主义与圣人强权
韩非子对人之阴暗面的揭露可谓血淋淋、赤裸裸,他之所以被人憎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敢于说真话。人们能够勉强做到心平气和地面对与接受陌生人之间、君臣之间的利害争夺关系,而韩非子毅然剥去骨肉亲情之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揭露其中令人不忍正视的残酷斗争,则让人不寒而栗,使人深深地感到韩非子对人的悲观绝望。然而,仔细辨析即可发现,韩非子对人的批判以及悲观态度,一般多围绕当时之世,对于遥远的过去与即将到来的将来,则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这与他的人情可变论事实上是一致的。
上古三代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有意识地塑造、美化为人类曾经有过的黄金盛世。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言必称尧舜”(4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2、234页。,《礼记·礼运》称三代为“大同之世”,墨子亦推尊三代,“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44)孙怡让:《墨子间诂》,第49页。,荀子言“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45)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99页。。韩非子也接受这种共识,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上古盛世不是由于道德而是由于法治带来的结果,《有度》篇说:“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46)张觉:《韩非子校疏》,第97页。《饰邪》篇说:“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47)张觉:《韩非子校疏》,第331页。盛世之时,人们遵章守法,竞于道德。人性虽未变,人情之表现却值得称道。与之对比,韩非子生活的社会却是一个政治失序、不义横行的“大争之世”,人们的表现令人失望:“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官员以贪赃谋利为能事,百姓以因循风俗故事、乱中取利为当然。当世之君主更是韩非子重点批判的对象,《十过》篇尖锐地指出君主的十种重大过失,其他篇章中也随处可见对当世君主的批评。或许正是黑暗的现实激发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殷切企盼,韩非子多次饱含深情地谈到自己的治世理想。《奸劫弑臣》篇说:“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48)张觉:《韩非子校疏》,第264页。《大体》篇说:“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49)张觉:《韩非子校疏》,第560页。在这样的治世环境中,人们远离罪恶,乐于为善:“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在保证法律底线不被突破的前提下,人们的道德水平逐步提高,最终必然出现“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的道德盛世。这样的治世并不是不可期望的遥远的梦,而是近在咫尺。只要圣人掌权当政,强力实施法治,理想很快就会变为现实,《难一》篇说:“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50)张觉:《韩非子校疏》,第939页。从韩非子对法治的信心以及他的盛世理想来看,韩非子乐观地相信人情能够得到转变,人类的罪恶假如不能根除的话,也能够被压制住。
韩非子对理想盛世的实现抱有乐观的态度,儒家三子亦然。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5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6页。若有君主践行自己的治国之道,最多三年就可以见到成效。孟子的信心更为充足,他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5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2-213页。如果此时施行仁政,必然事半功倍,收效迅速。荀子认为只要“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的王者在位,就能够“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53)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87页。。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人们尤其是士人在对现实极度失望的同时,也不可思议地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与希望。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还是韩非子,都为自己设立了一个伟大的治世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策略,并宣称只要当时的君主切实严格地实施这一套策略,就必然能够在短时间内拨乱反正,天下太平。这反映出思想家们的乐观精神,而这乐观精神又与圣人观念联系密切。
韩非子的治世理想与他的圣人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圣人话语是中国思想史中引人注目的话题,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战国诸子无不借助圣人标榜自己的学说,甚至以之作为辩论的利器。王世贞曾言:“凡刑名游说,诸家立说,必牵扯圣人以骇世。”(54)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韩非子也不例外,“圣”在《韩非子》中共出现107次,涉及29篇;“圣人”出现71次,涉及22篇。由此可见,韩非子具有明确的圣人观念,圣人在韩非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儒家诸子相比,韩非子的圣人观念具有明显的不同。儒家所颂扬的圣人,主要是道德上的完满;韩非子认可的圣人,不仅道德完满,智慧超群,更重要的是圣人有能力解决人们最为关切的时代问题,能够造福国家和人民(55)有观点认为韩非子是非道德主义者,他的圣人观念剔除了道德的因素;或以为韩非子的圣人仅指君主。如孙旭鹏、赵文丹:《韩非的“圣人”观及其现代意蕴》,《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95-100页。窃以为,这些观点无法得到《韩非子》文本的有效支撑。事实上,韩非子的圣人观念对儒家、道家之圣人观念进行了扬弃,吸取了其中的合理内容,而又具有鲜明的法家特色。具体而言,韩非子圣人观念中的道德性可以说来自于儒家,哲学性来自于道家,而政治性则来自于商鞅等法家先贤。在韩非子看来,只要符合条件,君主和大臣均可成为圣人。。可以说,韩非子理想中的圣人兼具道德性、哲学性与政治性。政治性是核心,哲学性是前提条件,道德性是光环。圣人的哲学性或者智慧来自于对“道”的体悟。老子最早提出“道”的概念来代替上帝天命,之后“道”成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时也是最高境界(56)金岳霖:《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17页。。体道的圣人能够见微知著,预测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势,并能够果断地采取措施以顺应之:“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圣人体道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透彻地理解这个世界,更在于有效地改造这个世界。对于人类来说,政治乃是有效改造社会最有力的途径。这就凸显了圣人的政治性。事实上,韩非子把伟大政治业绩作为判断圣人的标准,将政治性看作圣人的核心属性,这也是古人一致的观点,《礼记·乐记》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5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89页。“作者”是指那些缔造国家并创造礼乐制度的政治家,是视听言动足以形成政治凝聚力的领袖人物。这一点,先人创造“聖”(圣)字时确实有过充分的考虑。“聖”字字形由人的耳朵与嘴巴组成,表明这样的人既有敏锐的听觉,又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他通过有利于民生的制度安排来“使民养生丧死无憾”(58)韩东育:《道学的病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页。。从儒家的圣人系统来看,孔子之前的圣人均为一代王者,他们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创建了不朽的功业。于此,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不轻易许人为圣,亦从不以圣自居的原因。此外,圣人还是道德完善的人,《功名》篇说:“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59)张觉:《韩非子校疏》,第556页。不论圣人的人性是否仍然自为自利且趋利避害,其人情已经达致完美的程度。少数得道的圣人,不仅能够控制自己的外显行为,还能够借助国家强制力的帮助,以“法、术、势”这一套完整制度有效地引导并改造民众的人情表现,从而造就一种理想盛世。
毫无疑问,韩非子的圣人观念表明了他对人的乐观态度。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人的乐观态度,包括对民众和圣人的乐观态度,决定性地让韩非子选择了精英主义与强权政府的道路。在韩非子的理论设计中,没有明显的、有效的对君主或者说对最高权力的制约。韩非子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对人之阴暗面的揭露,及对权力负面影响的警惕众所周知,毋庸置疑,而最终对人的乐观态度让他没有认真考虑对最高权力的限制。这一点,常常被误认为是韩非子对君主极权专制的狂热所致。值得一提的是,鼓吹君主绝对权力的英国学者霍布斯对人抱有悲观的态度。他认为在原始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处于战争状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等权利没有任何有效的保障。因此,人们订立契约组合成国家,这样的国家就是“利维坦”。在利维坦式的国家中,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君主运用强力控制臣民。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遵守“丛林法则”,处于战争状态(60)[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4-132页。。这说明,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人类的共同体,霍布斯均持有不信任的、悲观的态度。换言之,对人的悲观与乐观态度,均有可能使人们倾向于君主制和强权政府。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考察儒家与法家诸子的差异性,而对其思想共性不够重视。从对人的态度来说,他们的看法实际上具有一致性。表面上看,孟子与荀子更加乐观,而韩非子则较为悲观。孟子倡言性善,并且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6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17页。;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对人之改恶从善信心十足,“涂之人可以为禹”(62)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23页。。孟子、荀子都乐观地坚信,人们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即都能从根本上坚守住本有的善性或改恶迁善,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韩非子则不然,他从来没有认同过民众人性的改变,他只认可少数圣人可以做到让精神性完全控制生物性。至于普通民众,只要他们外显的人情在圣人与外在规范的制约、引导下发生符合理想的变化即可,韩非子并不抱有从根本上改变普通民众人性的希望。不过,这只是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不同。无论是孟子、荀子还是韩非子,最终都寄希望于圣人来整顿乱世,权力的腐蚀作用似乎对圣人无效,他们几乎都没对圣人的最高权力认真地提出制约。这在理论上无可非议,但在实践上则极易造成君主滥用权力以致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这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性乐观有余,对其阴暗面却警惕性不足。如果换一种参照体系,就能看得更为清楚。基督教对人的认识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由此人具有一定的神性和理性;另一方面,人有原罪,有着根深蒂固的堕落性,靠着人自身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可以得救,但永远无法像神一样完美无缺。后一方面的认识,决定了基督教对人的彻底悲观态度。基督教不相信人可以在现世建立理想的社会,不相信人可以成为道德完善的圣人。基督教对人的不信任,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张灏指出,正是这一份深重的“幽暗意识”开创出西方的民主传统,而不像中国的儒家、希腊的柏拉图那样,将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归结到追求完美人格的人作为统治者上面(63)张灏:《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58页。。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这些人本主义者对人性的信心与乐观态度。
结语
思想家对人的认识直接决定了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人的问题既包含性善、性恶之道德判断问题,也包含思想家对人之悲观、乐观的态度问题。韩非子把人性与人情分开考虑,认为人性自为自利,趋利避害,而且永恒不变;人情则会随着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人情作为人外显的行为表现,受到内在动机即自利之人性以及理智之心的计算选择这两方面的制约。韩非子的人论具有变常统一的特点,这与他的道理论和历史观保持了理论上的一致性。韩非子对人的关注更侧重于其阴暗面,貌似对人抱有悲观态度。不过,从韩非子的圣人观念以及对理想治世的阐释来看,他对人实际上抱有乐观的态度。由此乐观之态度和理想主义,韩非子选择了精英主义和强权政府的政治模式。韩非子拒绝评论人性之善恶,主要是基于他对圣人和合理制度的无限信心,相信在圣人的领导与制度的强力约束之下,人性虽不能改变,但完全可以使之外在的行为表现即人情,符合道德和社会正义。
韩非子等战国诸子对人的认识,基本上都看到精神性与生物性这两个方面,并相信少数人可以通过努力让精神性完全控制生物性而成为圣贤,相信圣贤的完善道德与超群智慧,能够免于被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侵蚀。这里不无怪异之处,尤其是对韩非子而言。韩非子一方面对人之阴暗面有深刻的认识与较高的警惕,另一方面又对圣人完全信赖而不设防。如果说基督教对人抱有彻底悲观的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则对人抱有乐观的态度,虽然其中必然存在量的差异。对人的悲观或乐观态度,并不能完全解释不同民族和国家对政治制度的选择,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缺少民主的思想,对人尤其是对统治者乐观有余而对人的阴暗面重视不足,警惕性不强,及对权力的腐蚀力掉以轻心,无疑是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