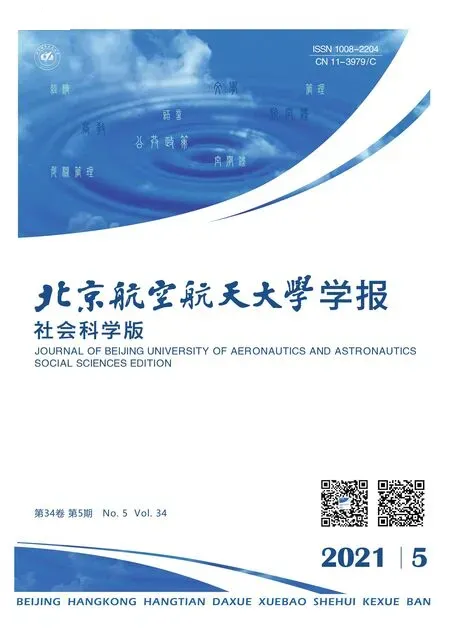《〈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意识形态观
赵翌妍, 孟宪生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吉林 长春 130017)
一直以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很少被视作意识形态的经典文本,主要原因是《导言》通篇都没有出现“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确,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问世,意识形态概念才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而亮相,并且一经亮相就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系统论述。但是,这并不表明《形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意识形态问题都是蔽而不明甚至未有涉及的。就像乔治·拉雷恩所讲,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所应有的基本内容都已具备,只是“尚缺乏一个正式的命名而已”,特别是在《导言》中,“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内涵在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以及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中已然呼之欲出”[1]。《导言》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意识形态观,集中体现着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形成根源、意识形态克服途径、意识形态转化功能的理论揭示和思想要旨。
一、意识形态形成根源:颠倒的世界产生颠倒的世界意识
就像马克思所讲,在德国“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3,《导言》也是从“宗教批判”开篇的。或许有人会指出,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宗教进行的批判,基本是在德国已经结束和完成的,特别是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理论成果。应该说,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马克思宗教批判同近代以来唯物主义宗教神学批判之间的联系和一致,却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后者的超出和区别,也就没有领会到马克思在《导言》中以“宗教批判”作为起手的理论意图。即便《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没有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超出和区别也已经表明,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因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批判,在吸收和反思唯物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向着完备的意识形态观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或者说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最终形成和系统提出,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因素”。
但是,马克思宗教批判能够超出费尔巴哈的关键环节,正是因为发现并抓住了这个“物质因素”,才能从“德国的现状(Status Quo)本身出发”来思考宗教与现实,特别是“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才能第一次把宗教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同产生这种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结合起来。不仅指出宗教和意识形态本身代表了一种精神颠倒,而且指出这种颠倒并非认识论的误区,而是由颠倒的现实条件决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2]3。在宗教批判的名义和前提下,马克思揭示出了意识形态作为颠倒意识的发生根由,并且告诉人们,只要还处于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只要现实基础还是颠倒的,那么“颠倒的世界”产生“颠倒的世界意识”这种社会现象就不可避免。
指出宗教是一种颠倒意识,并非马克思的独创,而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宗教批判取得的基本成果。“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3。在费尔巴哈那里,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对象化、客体化的结果,是从人自身分离出去并投射到上帝那里的虚幻想象。这个虚幻想象导致了根本性颠倒,作为产品的上帝变成了造物主,明明是人创造出上帝,却被颠倒为上帝赋予人生命和意义,人反而成了上帝的产物。作为客体的东西成了主体,作为结果的东西成了原因,作为结论的东西成了前提,对象化变成异化,支配变成被支配。这种颠倒以及为这种颠倒进行粉饰和辩护的神正论,在唯物主义宗教批判和自然科学、工业革命的连番冲击下,被扯下罩袍、露出本相,就像马克思所说,“谬误在天国为神邸所作的雄辩(Oratio pro Aris et Focis)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2]3。不过,揭露和驳倒这种“颠倒”容易,但是克服和消除这种“颠倒”却很难。这就涉及宗教产生、意识形态颠倒产生的根由缘起问题了。从这里开始,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区别开来,比起后者仅仅把这种颠倒现象归结于“人类理智的迷误”来说,马克思走得更远、看得更本质。
马克思不满足于揭露颠倒现象,更关心造成颠倒的根源,以及如何消除这种颠倒。“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2]3“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2]4。宗教既是人们在“有缺陷的现实”中获得的“精神上的补偿”,又是人们不得不在头脑和灵魂中针对“现实的苦难”做出的回应和抗争。宗教作为“人民的鸦片”,让人们既解毒又中毒,因而宗教里的抗争不过是“无情世界的情感”,充斥着“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正像它就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2]4。
可见,宗教里的压迫与反抗,基本是对尘世生活里压迫与反抗的真实反映。造成这种压迫与反抗的是苦难尘世的生产方式、物质条件,在其中,少数人无情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剥削阶级奴役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生产与分配、劳动与财富的自然联系和正义规律。这种构筑于颠倒现实之上的阶级统治,为了维系和扩大自身利益,就会尽力掩盖和粉饰这种颠倒关系,于是在宗教和意识形态中,一切又都被颠倒过来:人的力量被说成是神的威力,人的创造被说成是神的恩赐,此岸的苦难被说成是通往彼岸的自我救赎,历史的进步被说成是观念的自身运动,如此等等。经过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正反颠倒,人们把“虚幻幸福”理解和追求为“现实幸福”,不是“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而是围绕“虚幻的太阳”来转动,只能采摘“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并将之视若“神圣光环”[2]4。支撑这个“神圣光环”的,不过是宗教意识形态编织出来的“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贯穿其中的基本关系仍是普遍颠倒。“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那么他只能找到“他自身的反映”,而且是“他自身的假象”,也就是“非人”[2]3。然而,由于人们对这种颠倒全然不知,确切说是对这种精神颠倒同现实颠倒之间真实联系的全部不知,导致即便人们对颠倒世界中“现实的苦难”感到憎恶厌烦、不堪忍受,也丝毫不会影响到构筑其上的宗教意识形态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个体思想灵魂与生命活动进行教化支配,并且一旦到了革命的十字路口,往往还会造成似乎人们仅仅只是在承受来自某种“观念的统治”的政治假象。
二、意识形态克服途径:对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
既然弄清了颠倒的真相,是否在观念领域将意识形态颠倒的关系正立过来,人们就能克服意识形态呢?显然不能。即便“上帝死了”的口号和宣言人尽皆知,也没有影响到人们信仰“上帝”的虔诚。人们懂得溺水原理之后,再怎么宣称“重力思想”是迷信观念、宗教观念,也不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因为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罢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误会和幻想”的“标本”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杰出代表是“黑格尔的幻想、思想、观念、想法”,以及不论“问题的提出”还是“问题的解决”,都不曾真正走出“黑格尔体系地基”一步的“青年黑格尔运动”。
这个“青年黑格尔运动”及其形成的“青年黑格尔派”,曾经带给马克思迷惘与苦恼。在185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过,“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3]588-591。
分析这段颇具思想史和心灵史意味的学术独白可知:其一,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和重视,既是引发“苦恼的疑问”的现实缘由、物质动因,也是马克思破解这个“苦恼的疑问”,最终走出和清算“青年黑格尔体系”的逻辑起点、关键环节。“善良的‘前进’愿望”渴望“依照思想建筑现实”,推进“世界的哲学化”,但是这种“愿望”由于德国社会“时代错乱”而不断落空,结果是“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4]547。这让马克思意识到一方面,脱离“物质利益”的概念思辨和词句批判,并不能切中德国历史的根本困难与真正出路;另一方面,仅仅在理论思维中批判宗教、批判德国现存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是断然不能在“政治解放”中寻求和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让用思想所无法摆脱的那种现实的、感性的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2]288,终究无法摆脱“乌托邦式的梦想”和“政治解放”的片面性、局限性。
其二,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结果,没有停留在词句革命和逻辑胜出层面,而是将思辨哲学产生的根源以及对这种思辨哲学的批判本身,都置于“市民社会”的总体历史框架之中,指出迄今为止的政治意识形式连同其为之服务的国家制度全都构筑在一定“市民社会”的物质条件之上,这就是他在阐述自己同黑格尔国家观的根本区别时所强调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591就是说,《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这个基本原理的“物质前提”和“理论内核”已经初步具备,尤其在对“市民社会”同“法的关系”“国家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之间“联系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上,已经达到了超出以往的“原则高度”。凭借这种高度和优势,马克思进一步超出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观,关于如何克服和消除意识形态的颠倒现象,提出了一个闪烁着唯物主义真理光芒的经典论断:“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2]11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宗教和意识形态的颠倒,是现实中的颠倒的真实反映,就像马克思后来在“照相机”“视网膜倒影成像”[2]525比喻中阐述的道理那样,颠倒的现实是真实的关系,不是想象的联系,颠倒的现实不会因为颠倒的意识在头脑中的再次颠倒而被直接正立过来。既然颠倒是真实事件,那么克服和消除颠倒也只能是现实革命。克服一种意识形态,消除这种意识形态在人们观念领域造成的歪曲和颠倒,固然需要理论清醒和前提批判,但最为有效的“解决办法”还是“实践”。要想拿走镜中花,就得把花从镜前拿走;要想取下镜中面纱,就得把面纱从头上摘下。宗教和意识形态所反映的苦难与抗议,是由实践造成的,因而只有在实践中消除了这种苦难与抗议,才不需要到宗教和意识形态之中去寻找,人们才能抛弃“虚幻幸福”而追求“现实幸福”。这里除了说明实践是推翻一切不合理关系的根本手段之外,同时也说明,随着实践推进“彻底的革命”,造成歪曲和颠倒现象的宗教和意识形态都将逐渐消失。就是说,消除颠倒的意识形态,跟消除颠倒的现实关系具有一致性和同步性,根本都在于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用“武器的批判”磨砺“批判的武器”,用“物质力量”摧毁“物质力量”。萌生于此的这个观念原理,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形态》中被明确起来,并且得到了最系统的阐述。但是,尽管还是萌生和初现,这个观念原理也已经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批判逻辑中显示出本质重要的理论意蕴。
三、意识形态转化功能:理论解放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
实践作为“原本”,是克服和消除“颠倒的世界”及其“颠倒的世界意识”的根本所在,全部“副本”问题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01。那么,在德国,“实践”应当专注于怎样的“课题”?这就是马克思紧接着提出的,“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2]11马克思在这里关于革命理想做出了明确的性质区分:“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政治解放”,旨在建立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国家”,“人的高度的革命”则是“共产主义革命”,指向“彻底的革命”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旨在“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都回归于人本身”[2]46,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认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只不过是说明,德国的历史“就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只承担着一项任务,那就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2]8。德国的现状,既是“旧制度(Ancien Régime) 的公开的完成”,也是“现代国家的未完成”。因此,如果革命实践仅仅要求“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无非是向前迈了一小步,确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但是,这个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它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为“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2]28,结果必然导致“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的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2]5。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与结局充分说明了这点,第三等级发起了革命的冲锋,成为推倒法国王庭的主要力量,却也扮演了这个革命的“炮灰”角色,成为革命的牺牲等级,没有享受到革命的真正果实,只能在目睹复辟与反复辟、资产阶级与王公贵族的拉锯大戏中见证启蒙学说、天赋人权的彻底破产。资产阶级革命实行的“政治解放”不会带来“普遍的人的解放”,无非兑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革命承诺。
因此,马克思追问到:“(德国)怎么能够一个筋斗(Salto Mortale)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呢?”[2]13这个“障碍”就是“彻底的革命”的障碍。能否越过这个障碍,一是取决于有没有“彻底革命的需要”,二是取决于有没有“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在这里出场。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是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这个阶级“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去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2]17。所以,无产阶级自身“存在的秘密”就是“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2]17,它是彻底革命的被动因素和物质基础。
不过,无产阶级要想推进“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还需要哲学,需要“使哲学成为现实”,需要从宗教和思辨哲学的意识形态支配关系中把人的头脑和心灵解救出来。对此,马克思写到:“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2]12这就进入到意识形态功能批判了。“宗教改革”的理论性在于“宗教批判”和“神学批判”,揭露和批判“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d’honneu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2]3,进而引起披着“宗教外衣”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混杂其中的君主统一运动,造成了“僧侣统治”“神权时代”的政治终结。理论解放、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意义”要求无产阶级,要想终结现存国家制度,就要“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2]9,要对代表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垄断根本利益的思辨哲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清算,把人们从“立宪国家制度的一切幻想”和“乌托邦式的梦想”中警醒并解救出来。
到这里,马克思意识形态(功能)批判的辩证品质进一步显示出来:其一,马克思虽然揭露和批判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颠倒性,并且指出造成这种虚假和颠倒的现实关系,但是并没有因为“实践”是解决一切问题(“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中的颠倒)的关键,就看清或否认意识形态的理论辩护和精神引导功能,实际上是承认了意识形态具有反作用性和相对独立性,所以他才说“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2]4-5。其二,虽然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掩盖和粉饰“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指出它们“求助于伪善和诡辩”来“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假象来掩盖自己的本质”,进而“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2]7,炮制了“人民处境的幻觉”和“人民的鸦片”,但是并没有迁怒于“哲学”和“理论”,像庸俗唯物主义那样把人的心灵和精神贬得一文不值,似乎“人的解放”不过是“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4]503。
与之相反,马克思在肯定理论解放具有根本“实践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先进思想、彻底理论对于塑造和动员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指导作用,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11。
综上可知,《导言》可谓是较为完备地记述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理论的“第一个 文件”。在其中,当马克思在讲“宗教”以及“宗教批判”,在讲“思辨法哲学”以及“迄今为止的一切政治意识形式”时,都是在实指“意识形态”,所以他不仅批判了宗教意识形态,而且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更是揭露和批判了意识形态本身,确立了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不仅作为内容,而且作为方法,告诉人们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克服和消除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是什么”,“为什么”要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不断强化“理论的解放”。由此表明,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概念就已经达到了“原则高度”,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已然呼之欲出,其所欠缺的一是正式命名,二是来自唯物史观的系统论证和重新表述。
如果说《导言》是马克思清算“旧时哲学信仰”的开始,那么《形态》则是“新哲学信仰”的最终确立,随之确立的还有马克思在《导言》中批判和破除“旧时哲学信仰”时提出来的意识形态基本原理。这种从《导言》到《形态》的最终确立表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获得了自己的总体原则和基本范式,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内核与思维方法,同时也获得了一种使命和信仰,那就是意识形态批判总在路上,面向人心、嵌入生活、涤旧生新。特别是对于当今时代的中国社会来说,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具有特殊重要性,在做好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也要抓好意识形态建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