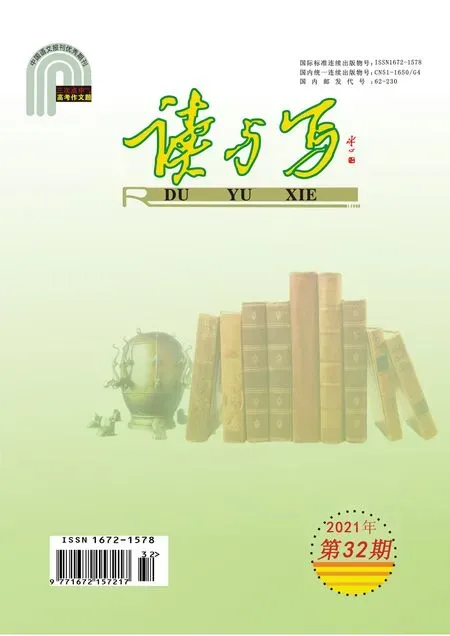我们怎样认识“儿童”
王奕璇
[浙江省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团(总校) 浙江 杭州 310000]
小学语文,乃至整个小学教育,是建立在对儿童的理解基础上的,当前教育追求短期效益,许多教师不考虑儿童的真实兴趣与需要,把儿童当作自己课堂教学的展示板,但是,儿童始终就是儿童,儿童始终要要成为儿童,那么当前课堂中的儿童究竟是如何的呢?什么才是儿童呢?
1.课堂中的儿童
在一次小学见习活动——批改试卷时,三年级语文组的教师为扣分标准进行了讨论,对于某教师提出的错一个标点符号就算全错,另外每个错别字扣半分的评分标准,另一个教师提出了异议,说这个标准不符合常规。但其他教师的意见很明确、一致,主张就是要让儿童“痛”,因为“痛”了,儿童才会印象深刻,才会改正错误,才会下不为例。根据我所学的强化学习理论,我想到了一种假设:如果有足够的刺激强化,儿童就会规避风险,避免低分的惩罚,从而改进学习行为。教师这样的评分标准以及意图,带着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极端地忽视了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只看到外部环境的作用。
华生曾经说过,给他一打健康婴儿,让他在可以完全控制的环境里去培养,他能使任何一个婴儿变成任何一种人物。当然,现在的教师不太会完全相信华生的话,但现实中教育却大行其道。表现在课堂上,就是教师强调课堂过程的控制,儿童被当作被任意塑造的“物”,符合教师预设的回答都是值得被表扬的,偏离轨道的回答一律被无视,公开课也会经过完美的预设以及N次的排练,只为了呈现教师非凡的教学技能,而儿童只是教学的展示板。
我相信,在那些被忽视的回答中,一定会有金子,然而,大多数教师没有发现金子的眼睛,也不会站在儿童的角度想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回答,只抓住了符合自己要求的那一种思想,最后每个人变成了思想一致的“机器”。我想到了李润洲老师的《作为人的儿童》一文中提到的“印刷术”,凡是超出了正轨的儿童都应该通过谴责唤回理性与服从的大道,如果劝告没有效力就必须惩罚,最后,儿童逐渐变成了教师眼中可以任意变形的“物”。
2.儿童是什么?
那么儿童究竟是什么呢?何谓儿童?关于这个问题,卢梭在《爱弥儿》中是这样说的:“儿童是人”,“儿童是成长中的人”,“儿童是儿童”,让儿童成为儿童,这一观点贯穿于卢梭的教育体系始终;李润洲老师在他的《作为人的儿童》中提到儿童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儿童,并且与人一样都是生成的,并不是能够预设的,应该以人的方式对待儿童,把儿童视为具体的、完整的、生成的人来筹划教育;关于“儿童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儿童”这一点,林梅梅在《儿童是自由的人》中也有借鉴,她同时认为自由是儿童存在的本性,儿童是按照自然的普遍发则而自由发展的,我们应以自由的态度对待儿童。除此之外,李润洲老师还在《作为儿童的儿童》中提到了作为儿童的儿童应该是怎样的,用儿童的方式教育儿童,就是成长即目的,生活即学习,行动即存在。
其实,儿童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每个人都是从儿童时期走来的,童年的时光会给每个人留下独特的印记,我们都有自己的儿童观,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走进成人世界之后,尤其是小学教师,充当儿童教师的角色,促使我们要学习和思考儿童问题。那么,儿童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的儿童观念和儿童实践,使我们拥有许多可贵的有关儿童的“知识”,诸如:古代认为“儿童是小大人”,中世纪认为“儿童是生而有罪的”,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种子论”,启蒙时代有“白板说”等等,还有一些长远流传下来的说法,儿童是花朵,儿童是快乐的天使,这包含着人类对儿童美好生活的寄托;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人们对儿童学习发展的劝诫;棍棒下面出孝子、不打不成材,这仍然是不少人依然坚信儿童教育方式;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是预测儿童成长的基本定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对构建适合儿童成长环境的基本信念……
综上种种,我认为,儿童是有自己独特地位的,我们应该把成人看作成人,儿童看作儿童,每一个儿童应该有三个“唯一”。这个“唯一”表示的是“一去不复返”,儿童不同于产品生产,是不可重复的,因此,我们对儿童需要倍加细心;在一个群体中,每一个儿童也是唯一的,这个“唯一”表示的是每个儿童都“与众不同”,儿童生而“与众不同”;儿童的快乐也是唯一的,这个“唯一”表示的是儿童的快乐与成人的快乐是不同的,作为成人,同时也作为教师,我们不应该用成人所认为儿童应该有的快乐去覆盖儿童“唯一”的快乐,让这份“唯一”变成“千人一面”、成人世界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