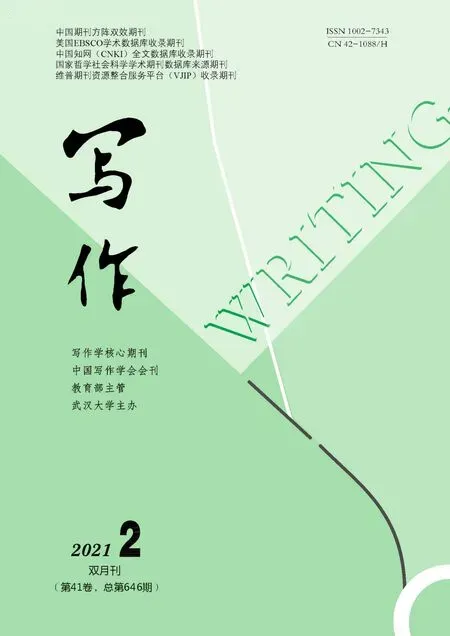梦的叙事:一种先锋写作谱系的考察
徐兆正
笔者曾在《文学的同质,或先锋的意义》①徐兆正:《文学的同质,或先锋的意义》,《福建文学》2020年第3期。一文中分析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这对范畴的消极作用,譬如我们经常会谈起“现实主义复兴”或“现代主义从未过时”这类话题,但这种谈话又往往近于空谈,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概括也近乎无效。与之相比,“传统与先锋”反倒更容易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经由历史,我们得以指认现实。在本文中,笔者打算接续这个话题,进而考察“先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写作谱系:梦的叙事。如果说先锋是为了对抗趋时的文学保守主义,打碎同质的文学趣味,那么这种梦的叙事,则更为具体地表现在它要同现实主义去争夺一种更高意义的真实。
一、现代主义的真实
(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跖
韦勒克曾经从一种否定神学的角度谈论现实主义,他并非直接追问“现实主义是什么”这个几无可能解决的难题,而是尝试着厘清下面这一问题:“现实主义不是什么”。在《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一文中,韦勒克的回答很简单:现实主义不是浪漫主义,它是继浪漫主义之后并且为了反对浪漫主义才提出的美学信条——“它排斥虚无缥缈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斥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神话,不需要童话,不要梦幻世界。它还包含对不可能的事物,对纯粹偶然与非凡事件的排斥。”①[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由此一来,所谓“现实主义”就通过排除法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规定,即它是对“一个19世纪科学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由因果关系统治的世界,一个没有奇迹、没有先验存在的世界”②[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进行的描述;而先前为韦勒克所回避的“客观性”“真实”等等难题,也同时转换了它们自身的形式:不再是“何为客观性”“何为真实”等问题,而是在这个外在的世界,“客观性与真实对于写作意味着什么”③[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在韦勒克看来,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与真实意味着“丑陋、骚乱、低贱的东西都成了艺术的合法题材,性与垂死这类忌讳的题材(爱与死是能够被接受的)现在也被允许进入艺术的殿堂”④[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
韦勒克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已然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看法。不过,此时的他还只是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跖意义上来界定后者,而现实主义中尤其令人感到绝望的悖论——虚构与真实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根据谢俊《在文本细碎处描写真实——谈谈如何通过“虚构”达到“真实”》(《今天》杂志2017年第3期)一文的看法,“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首先即是对小说(fiction)的另一重含义“虚构”进行的反拨,“现实主义”试图在小说/虚构的框架内,通过摒弃浪漫主义的高蹈玄思,进入到一种强调自身“非虚构”的倾向。所以在谢俊看来,此后的现代主义无疑类似于浪漫主义的回潮,现代主义的小说作者又开始倾向于召回为现实主义抛弃的事物。然而,他认为现代主义力图达到一种“文本即制作”或者说“小说仅仅是一种虚构”的自觉,则不免是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者的误认。以笔者之见,现代主义仅仅当它是一种“超级现实主义”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这就意味着它将现实主义拒斥不用的事物一一召回的目的(如韦勒克所列举的“寓意与象征、高度的风格化、纯粹的抽象与雕饰、梦幻世界”),仅在于追求更大意义的真实(如潜意识的真实、表象以下的真实)。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笔者所理解的现代主义是此前诸种文学思潮的一种混合。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后序》中有云:“这‘真实与诗’乃是歌德所作自叙传的名称,我觉得这名称很好,正足以代表自叙传里所有的两种成分,所以拿来借用了。真实当然就是事实,诗则是虚构部分或是修饰描写的地方,其因记忆错误,与事实有矛盾的地方,当然不算在内,唯其故意造作的这才是,所以说是诗的部分,其实在自叙传中乃是不可凭信的,应该与小说一样的看法。”⑤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其实“诗与真”已经区分了现代主义它所混合的两大文学思潮,“诗”的部分即是浪漫主义,“真”则指向了现实主义。这样说,无非是为了强调现代主义不曾反对过现实主义追求真实感的目标,它反对的仅仅是后者那刻板的反映论而已。
(二)日神艺术与酒神艺术的对跖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跖,也合乎日神阿波罗(梦)与酒神狄俄尼索斯(醉)的对跖,这两个希腊神灵是尼采早期诗学中的两个重要神话形象。日神代表着理性的赋形之力,酒神则是非理性的打破形式与限制的冲动。尼采毕其一生都更亲近后者,其思想气质也被打上了鲜明的酒神烙印,但在他运思的开端,日神却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牵制力量。日神的美学意义,即是令酒神艺术(音乐)中那些无法付诸言语的感知,具象为一种视觉形态(雕塑);日神的现实意义,则是它庇佑了一种脆弱又疯狂的个体免于丧失其个体的形式。日神艺术是为现实赋形,而非复制现实;它的赋形,也在于它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刻板教条,不同于现实的因果律与能量守恒原则,而如同白日梦一般,是一种审美意识,“是一种‘幻觉’,它提供的是一种叙事形式,我们以此将一系列毫无分别的动机组织成清晰的话语和图像”①[英]斯平克斯:《导读尼采》,丁岩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简单地说,在最激烈的浪漫主义者身上或可隐约看到酒神艺术的影子——根据鲍默在《尼采与狄奥尼索斯传统》一文中的看法,“尼采之前真正的狄奥尼索斯传统,是由一批古典与文学家完成的浪漫主义哲学和神话学,诸如施莱格尔、舒伯特、格雷斯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克罗伊策、谢林和巴赫奥芬三位学者”②转引自孙周兴:《未来哲学序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日神精髓之间却很难草率地划上等号。现代社会不仅未能重现古希腊悲剧中将酒神与日神融合的完美,甚至连两者都予以抛弃,从酒神艺术(音乐)到日神艺术(雕塑)再到长篇小说(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正是从迷狂到幻觉再到清醒的理性进阶。因此,当先锋文学用梦似的语言和氛围充实了清醒的现实叙事时,它只是在用酒神艺术去调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尝试。进一步说,它是从清醒复归于迷狂,将迷狂视为被清醒所压抑的另一部分的真实,由此让文学达到一种“现实”的层面,令它得以把握到自身的虚构本质。以余华为例,以此观照他的那些梦境般的叙事,说到底也不是为了要反对真实——梦一般的故事框架反倒接近了另一种精神的真实——其实恰恰如莫言所说,这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
二、格非的梦境叙事
因为这个原因,笔者始终将余华——也包括八十年代的大部分先锋文学作家——看成是一批有志于革新现实主义的作家群体,而且他们在叙事上对梦境的接纳事实上并未随着“新写实”浪潮的兴起而告终(不仅未曾终结,反而延宕至今)。关于这一点,可以举格非2007年的一个短篇小说《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例。在这篇小说里,格非毫无疑问地启用了现实主义的笔法,不过文本层面却始终存在着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现实维度,即“我们”的大学生活;第二个维度是梦境维度,即“我”与胡惟丏的交往。无论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其原型,亦无论胡惟丏是否投射了作者关于80年代的回忆,他都既是小说叙述者在现实世界交往的对象,也是现实世界里的一个阴影似的存在,而作为两者重叠的胡惟丏——他的身世与居住环境、他的沉默、归隐与无由殁世——已然奠定了小说中两个叙述维度交错互映的关系。可以说,这种交错互映的梦似的氛围一直延伸到了小说结尾,并且落实成为一个真实的梦:在西藏讲学的“我”有一天收到了一个名叫“旺堆”的喇嘛寄来的信,信中他邀请“我”到热振寺做客。小说叙述者在看到明信片上的蒙娜丽莎图像时,当即意识到这封信之不同寻常,于是夤夜赶往热振寺与旺堆见面。见面之后,“我”果然见到了胡惟丏,不过,眼前的这个人已经剃去了满头白发,我们就此坐在桌边谈起了这二十年来的往事。谈话之后,梦中的“我”入睡了,直至醒来之后才发现原来一切是梦。
《蒙娜丽莎的微笑》是一篇在很长时间都让我深受感动的作品。胡惟丏这个人物,无论是他身世的隐秘、性情的古怪抑或大学期间给“我”留下的印象,严格说来都不免有些单薄;它之得以成立,得以成为现实世界里一个阴影似的存在,令读者在读过之后受到一种后知后觉的深刻撼动,完全是由于梦境维度的介入。梦境与梦醒的交错安排,本身让胡惟丏变成了一个在两个世界同时存在的人。首先,胡惟丏曾经存在于世,尽管他是一个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甚至看起来不太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但他毕竟曾经存在。其次,他的殁世直接让这种“不太可能的存在”变成了实然的不存在,也由此使得他成为了与现实世界截然对立的象征:既在价值上同卑湿重迟对立,也是存在与不存在的对立。这也正是小说最后格非所写到的细节由来:“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降落的时候,不知怎么,我忽然又想起在拉萨做过的那个奇怪的梦来。看着窗外肮脏、昏暗的大地,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它是一种矜持的嘲讽,也含着温暖的鼓励,鼓励我们在这个他既渴望又不屑的尘世中得过且过,苟安偷生。”①格非:《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页。阿乙:《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这个看起来毫不真实的人物,毕竟曾经存在,而他对于苟安尘世的我们既是嘲讽,也“含着温暖的鼓励”。
将梦境楔入现实笔法的叙事,《蒙娜丽莎的微笑》之后还有《隐身衣》与《月落荒寺》。后两本小说也都被一种扑朔迷离的解谜氛围笼罩(如时间的回溯、细节的重复)。《隐身衣》中,最大的谜团来自于“我”的那位神秘顾客丁采臣,他虽是小说后半部分的发端,其真实身份自始至终停留在阴影里,作者像是在用一处留白来牵引着整个文本的叙述向前行进。这个名字一旦出现,《隐身衣》便从写实主义直接僭越到了稍显哥特风的不太真实的段落。《月落荒寺》里则是由楚云取代了“丁采臣”的位置。对格非而言,采用这种形式也许只是为了表达那些在寻常生活里看似不可能而人们又着实期盼的存在。小说叙事在这里并未丧失它观照日常现实的本质,但作为一种微型、弥散的乌托邦式的梦境,则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氛围和节奏,亦如萨特所言:“对生活体验的最高形式能够锻造它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总是不充分的,而它往往具有梦似的隐喻结构。一个人若能用梦本身的语言来表达梦,梦就是可理解的。”②[法]萨特:《萨特思想小品》,黄忠晶、黄巍编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如何去描述一个不可能存在于当下的80年代的缩影?除了“具有梦似的隐喻结构”,似乎别无他途,而且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梦境的楔入旨在于充实、完整了那纯粹的现实主义所无力表达的现实。对格非近年来的写作而言,梦境实质上都是为了强调存在一个尽管并不存在却应当存在、虽然毫无现实性可言却关系着当代人精神救赎的价值标高。
三、阿乙的梦境叙事
格非、余华以降,启用梦境叙事的另一位作家,是阿乙。在他的短篇小说《对人世的怀念》中,两个毫不相干的时间片断——一个是“我”的祖父走到阮家堰的汉友医生家里吃板鸭(由于担心食物中毒而考虑汉友医生便于搭救之故),另一个是“我”在梦里重返故乡(与堂兄老细哥聊天的“我”,因为醒来后想到几年前老细哥便出车祸亡故而怅然不已)——被并置在一起。第一个时间片断,是记忆中祖父当初描述的那种濒死一瞬之感,勾联起了过去与当下;第二部分与之相仿,却是梦境与梦醒的交错:梦中与老细哥恳谈至夜深,梦醒之后老细哥已然不在。因此,在第一部分,过去与当下的相似构成了它叙述的合理性;第二部分叙述的合理性则来自于梦境与现实的反差,而这两者之所以能够并置在一起(这个小说文本谋篇的合理性),来自于它们都勾勒出了某些难以言传的氛围,包括人世的似是而非、置身时光的恍然等诸种因素。同时,在这篇小说里也隐隐约约能够看见一种由消失所象征的遗忘的焦虑:祖父曾经描述的感觉在早已将那段时光遗忘许久之后,如同闪电一般冲击了“我”;梦醒之后老细哥亡故的事实则否决了梦境中的现实。或许是出于这种遗忘的痛苦,阿乙在不少随笔中都记录了自己造访梦境的经历,其中多数是醒来后遗憾于梦中世界的消失。在《记忆》一文,作者写道:“人重新进入过去,情况类似于救火,能记录下来的财物有限。有时烧掉的废墟太难看,还需进行拙劣的重建。无论怎样,从离开事情的那一刻起,你就失去对原貌的掌握。这是做人痛苦的一部分。”①格非:《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页。阿乙:《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过去可以指代梦境,也可以指代逝去的现实。梦与现实在遗忘这一点上都表现为经验的丧失,这就是为什么梦醒后的怅然与现实生活里经验的匮乏,对写作者而言是无差别的痛苦。遗忘的梦总是经验匮乏者的梦。
对应于此,同样是收录于作者第四部小说集的《忘川》便提供了两个故事。小说明处是写王杀了失忆的继承人,暗处则是写梦醒了的人试图重返梦境的徒劳无获。故事起始于王子春卿对一个喑哑国度的造访。春卿“从他们的目光中分辨出,自己并非什么偶经此地的陌生人”②阿乙:《情史失踪者》,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6、111、100页。,不过这个国家的人民只是热切地关注着这个闯入此地者的一举一动——他们似乎掣于某项纪律无法开口,也不同春卿解释他的境况——放任其苦思冥想。在某个短暂时刻,春卿会怀疑起自身所处,并且出于疲倦与懈怠,怀疑稍纵即逝。最终他还是骑上了马嬉戏起来,被远方高楼下达的判词“他没有通过测试”拍马赶上。没有通过测试与春卿停止思考自身的处境有关,亦即他只是一个不知国耻家恨,贪图享乐的白痴。但这篇小说尚不止于此,它实际上还包含了一个更隐秘的暗处,暗处的故事是由明处对太子春卿的定语(小说结尾春卿乳母的太息之语:“太子自从坠马以后,就变得什么也不记得了”③阿乙:《情史失踪者》,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6、111、100页。)引出来的。凭着这个细节重读小说,由“他怀疑起自己所处的实际环境来”始,至“思索啊,它让人是如此焦虑”一段终,我们读到的便是另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同样是春卿,只不过发生在他怀疑自身所处的时刻。春卿看着那些因为纪律无法向他吐露情形的子民,怀疑他们陷入喑哑,并非是因为某项国王下达的命令禁止他们讲话,而是源于自己此时此刻就在梦中,是梦的法则迫使人们沉默。如若我们延展这一逻辑,那么春卿闯入的就是他曾经做过的梦,他亲手铸造的王国,只是这个王国被创造出来随即便遭受了楼兰、庞贝一样的命运,一如春卿彻底遗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曾在梦中应允一人请求,醒来后不复记得,惟当倏忽想起,尝试多次终于重回那一梦时,“在奔向那仍旧伫立的等待者后,他发现对方死了,苍白干燥的皮肤已经坼裂,眼中曾经充满的血如今萎缩成眼窝内的粒粒红土”④阿乙:《情史失踪者》,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6、111、100页。。这些实际都是对遗忘作出的譬喻,作者尝试着说明遗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至此我们可以说:明暗两个故事的交合之处在于春卿与那个无法抵达的记忆之间的距离(明处是现实的失忆——经验匮乏的极端表现,暗处是梦醒后对梦的遗忘)。于是,由这两个故事架构起来的关联便归结为一条同尼采相对立的命题:对遗忘的遗忘才是存在的真正沉沦。《忘川》的写作直面了遗忘的命题,《对人世的怀念》则加以弥补,它写的是人置身于时间之中的恍然。
阿乙晚近以来的这一批小说,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首先,它们标明了“逃离”这一主题写作的结束;其次,它们都是作者反身清理内在疑难,以困惑作为隐喻完成的作品;再次,在梦与虚构的相似性维度上,它们开启了另一种力图打破梦境与现实、自传与虚构壁垒的异质写作。将这三者总括起来,作者近来的创作即呈现为一种回指于当下和自身的写作形态。这一创作的源头出于随笔集中收录的那些似真似幻的小叙事,并且再次于最近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它们是《用进废退》《大坝》《思想者》这三篇小说。以《用进废退》为例,相比《情史失踪者》一书收录的小说,这一篇大概是一个更加难解的作品。读过这篇小说后,我们甚至无法像对《忘川》或《对人世的怀念》那样做出可靠的叙事分析,因为在这个文本中,梦境与现实已经难分难解,明面上它写的是一次平凡无奇的下午茶,也近似于非虚构的笔法,但是其中又有许多蹊跷的地方,如“我”并没有将约会地点告知对方,而对方已经知道了“我”临时的决定,“我”在服务员将啤酒端过来的路上已经抽出了三张纸,预备擦她那“必然”要倾洒的啤酒,后来啤酒果然洒在桌上,而几乎就在同时,“我”已经将桌面清理干净。又如“我”正在与拓跋晓春谈话,却恍然觉得“有两个晓春,在相同的咖啡馆,相同的时光,面对相同的听者,说了相同的话”。在返程的地铁上,“我”莫名哭泣起来——这又是莫名其妙的一个情节,哭泣的原因在于“我”已经看到了五六年后拓跋晓春的结局:“我在一个四面墙都刷成乳白色的美术馆,看见身体两侧被割开很多伤口的晓春,被关在密闭的水箱内,正在游泳。”①阿乙:《用进废退》,《江南》2019年第1期。某种意义上,虽然这篇小说涉及的题材(人工智能)或题旨(没有革命和解放的可能。一旦囚禁,永远囚禁。所有不肯放弃肉身形式的人类都被人工智能处理成可供展览的艺术品)是作品的新颖之处,但是作品真正独具匠心之处,却无疑是阿乙将过去、现在与将来三种事态融合在一起的做法,如此安排时态,叙事便直接在日常生活中飞升到了一个可能性的存在(它甚至不必依赖梦境的叙事手段)。
四、宋尾的梦境叙事
阿乙在《用进废退》中叙事的娴熟,已然超越了《早上九点叫醒我》中对梦境的简单借用。梦境如今已经渗透到了文本的所指层面。换言之,它仍然是现实主义,却又不止于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阿乙与宋尾相遇了。准确地说,宋尾的写作在许多方面都与格非、阿乙不谋而合,譬如他对侦探小说文体的偏爱,对现代人精神疑难的关注等等。在宋尾已经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与小说集中,同样有一篇借用了梦境,并且令人印象深刻。这篇小说即是发表在《人民文学》2019年第2期上的《大湖》,它所采取的是一个俄罗斯套娃式的叙事形式:故事的最外层,是“我”与几位朋友在一个私家园林的聚会,聚会上我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自己知道的那些离奇事件,如张尹讲了一个托梦破案的故事,这则讲述勾引起了席间一位警察的回忆;故事的内层,便是这个警察的自叙,这一部分占据了小说的绝大篇幅。通过他的讲述,我们大体知道这个警察生命中的某些奇异经历,譬如在他年幼时父母即离婚分家,他独自一人跟随父亲生活,后来由于生病,而父亲又工作繁忙,他被送到了乡下的祖母家。在祖母家康复之后,有一次他在湖边溺水,被湖水偶然地冲到了一个陶渊明式的渔村,并且在翌日被渔民送回家中。祖母知道这件事,慌忙地叫父亲把他领走。然而这段经历又先后被表兄与母亲否认,表兄否认的原因是“我”凭着记忆指认的渔村,在表兄的记忆中从未有人在那里居住,而母亲则断然地否认了“我”曾在幼年时去过祖母家的经历。在她的记忆中,“我”是被送到了省城的铁路总医院,并且在那里康复的。
在这位警察的讲述中,此后几年他又从自己的母亲那里知道了父亲的一些旧闻,譬如他总是在夜晚做噩梦,“问他梦见什么,他就说回了趟家”。纵使如此,他又从不愿意回家。关于这一细节,后来“我”又在表兄、表姐那里得到了一些关联性的佐证。表兄对“我”的父亲为何从不回家的解释是他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而表姐则直接告诉了“我”家族几代人的隐秘:并不是父亲害死了“我”的祖父,而是“我”的奶奶将自己日日酗酒的丈夫捅死了,但这件事最终莫名地由父亲背负了污名。“我”也对表姐讲述了幼年那个离奇的梦,表姐的解释是梦具有遗传性。换言之,“我”所做的这个梦很可能便是母亲口中父亲经常做的那个噩梦。事情至此也许全部得到解释,然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些不可解释的因素:在父亲留下的物件中,“我”看到了自己梦中被渔村的伙伴赠予的五枚小石子儿……《大湖》的另一个外层,重又回到了作为倾听者的“我”的角度:那次聚会的私人园林在两年后被拆迁了,这件事让“我”想起了这个离奇故事的讲述者刘警官——下面这一段是最让读者感到震惊的地方:“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否认了这个人的存在。他们凭借记忆,认定那天“我”喝得不省人事,并且悄悄离开了酒席。简单地说,《大湖》这篇小说纯粹是一幅由一连串对梦境的描述以及对这些描述的否认完成的拼图。刘警官的讲述,以他自己的“现实”经历与将这种经历指认为不可靠的梦境结束;作为主人公的“我”,则又经历了他人对于“我”对刘警官回忆的回忆的否定。
如果说前者是现实被指认为梦境,那么后者就是在指认梦境的现实中又一次地被指认为此乃关于梦境的梦境。既然如此,是否还存在着一种真实呢?这便是问题的关键。在《大湖》的创作谈里,宋尾曾坦承自己更偏爱那种“虚实相间”的小说,这种小说的特点在于:它发生“在可能(真实)和不可能(非真实)之间。更准确地陈述:你说它是非现实的,但逻辑上它又是现实的,在这种交融中,一个故事产生了”。作者的许多小说都是如此,如《大湖》的故事,落笔于“我们活着,往往就为这种根本不知其所来也不知何所去的屈辱”;《聋哑人集会的地方》的故事,落笔于即将殁世的主人公在等待着一个已经殁世的女性;《完美的七天》,则是落笔于一个蹩脚的侦探感知自己与世界的距离愈发遥远。这些故事中都存在着一种“真实似乎并不存在”的强烈惶恐,无论小说是否严格地采纳了梦境的叙事,宋尾的写作对于真实与现实本身都构成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而这一点也正是谢俊在那篇论文中提到的地方:“也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下,马原才会写作小说《虚构》,余华才会写《虚伪的作品》。余华说,‘经验’是缺乏想象力的,实事求是的,它被日常、习俗、科学常识等规定、操纵了。……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先锋一代是以‘虚构’的形式到‘现实主义’那里去争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