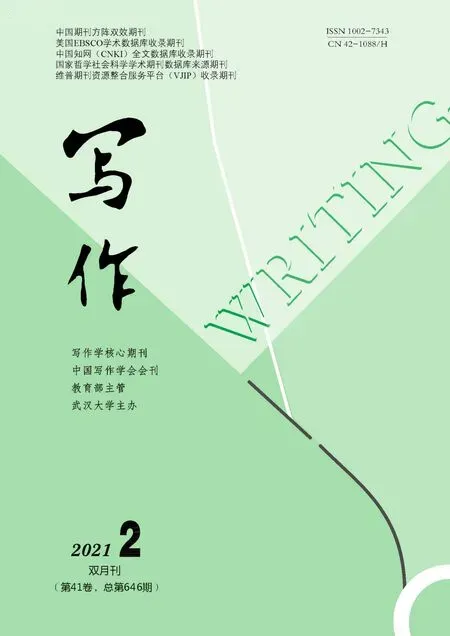从《再击壤歌》看写作中的二律背反问题
胡 亮
一
要谈诗人陈先发的匠心之作《再击壤歌》,当然,就要先谈某个上古初民的即兴之作《击壤歌》。《击壤歌》的作者以及时代,都已经渺不可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心横跨的斜拉桥,永远看不到桥头堡。同样的道理,还当有更加晚来的“陈先发”。想想,就觉得很有意思。就觉得,好多东西都新得可疑。却说《击壤歌》,首见于《论衡》。鉴于此处及下文多处需要,必须引来这段古老的文字:“尧时,五十之民击壤于涂。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①王充:《论衡·感虚第十九》,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论衡》作者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生活于公元1世纪。到了公元5世纪,范晔著《后汉书》,对王充下了一个评语:“好博览而不守章句。”②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99页。这个评语很奇怪,似乎在说,王充既是学问家,又是自以为是派。尧之于王充,恰如王充之于我。我今目击王充之旧籍,恰如王充当年耳闻尧之逸史。可信度,也许会两次打折。如果王充的记载属实,那么《击壤歌》就应该是汉诗的“元典”。“元”者,“始”也。“原始”,如今已是一个双音节词。杰出的古典诗学者朱自清先生,似乎就采信了王充。他当年编纂《古逸歌谣集说》,置于卷首的一篇作品正是《击壤歌》。
《论衡》算得上是一部哲学散文,与诗无涉,后来才有人从中摘引出并修订为传世单行本《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从哲学散文,到诗,变化并不大。然而,却是高手所为。为何这么讲?哲学散文在“吾”后连用五个四字句,已然板滞,几乎让人难以忍受。诗将“尧何等力”,改为“帝力于我何有哉”,一则语气更加有力,再则句式更加多姿。这个细小而微的文字调整,甚至预言了汉诗的大趋势:从四言,到七言。你说奇妙不奇妙,重要不重要?这是闲话休提。
对于陈先发来说,《击壤歌》既是汉诗的“元典”,也是《再击壤歌》的“原典”。“原”者,“本”也。“原本”,如今亦是一个双音节词。那么可否这样讲,《再击壤歌》,本于《击壤歌》?这个问题却不能轻率作答。即便《击壤歌》关乎劳动(稼穑之劳动),《再击壤歌》亦关乎劳动(诗之劳动),也不能强行将前者看作是后者的绝对上游。况且,着眼点如果只是劳动,是不是太皮表了呢?至于王充,在这个问题上,那就显得更加皮表——他在《论衡》里引来《击壤歌》,不过是为了证明“尧时已有井矣”①王充:《论衡·感虚第十九》,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二
《击壤歌》被视为劳动之歌,或田野之歌,其实却是游戏之歌。“壤”,并非土泥,而是一种古代玩具;“击壤”,并非劳动于田野,而是一种古代游戏。却说有个浪子回头的周处,生活于公元3世纪,著有《吴书》,又著有《风土记》。这部《风土记》,已佚,幸而被其他古籍征引而保留下这样一个片段:“壤者,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三寸,其形如履。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②转引自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0,转引自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可见击壤游戏共有两个壤,手中壤,地上壤,前壤击中后壤,就算是取得了胜利。手中壤与地上壤,既有排斥力,又有吸引力,既是一对充满敌意的矛盾,又是一对充满爱意的雌雄。
而陈先发的《再击壤歌》,已将这个击壤游戏,看似巧合般地落实为诗学隐喻。这首新诗当然是一首“元诗”(Metapoem或Metapoetry),更狭义地说,是一首“论诗诗”(The Poem on Poetry)。诗人抛出了写作的二元论,却又企图皈依于更加高妙的一元论。何谓写作的二元论?一元是“我渴望在严酷纪律的笼罩下写作”(全诗第一行),一元是“也可能恰恰相反,一切走向散漫”(全诗第二行)。对于任何诗人的青年时代来说,对于多数诗人的一生来说,这都是一对矛盾;而对于杰出诗人的中晚年来说,反而是一对雌雄。何谓写作的一元论?“在严酷纪律和随心所欲之间又何尝/存在一片我足以寄身的缓冲地带”(全诗最后两行)。“严酷纪律”,进阶也;“散漫”,化境也。两者有可能反复交手,反复擦肩,反复红脸,此消而彼长,也有可能前者最终重叠于而不是绕开了后者。矛盾冰释,雌雄齿合。“月亮,请映照我垂注在空中的身子/如同映照那个从零飞向一的鸟儿”——这首诗只有此处所引之两行,好比半首绝句,却偏要无愧地叫做《绝句》。这是闲话休提。
笔者早就注意到,前述想法,于陈先发可谓由来已久。诗人讲过一个数学坏故事,或者说,一个诗学好故事:他诱导五岁的儿子,做算术题,得出了丰富的错误答案,故意违悖了老师的努力和教育的要义。为何这么做?在孤独的黑池坝,诗人如是说:“但我要令他明白,规则缘于假设,你要充分享受不规则的可能性,要充分享受不规则的眩晕与昏暗,要充分享受不规则的锯齿状幸福感,才不致辜负大自然在一具肉体成长时所赠予的深深美意。”③陈先发:《黑池坝笔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61页。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许稍异于诗人——对于算术题而言,答案越多,机会和幸福感越少;对于诗学而言,答案越多,机会和幸福感越多。诗人故意混淆两者之差异,不过是明里牺牲数学而暗里成全诗学。“规则”,“严酷纪律”也;“不规则”,“散漫”也。这是两座看似对峙的昆仑,而诗人并非如他恰才所说,总是罔顾“规则昆仑”(亦即“严酷纪律昆仑”),而只想登上“不规则昆仑”(亦即“散漫昆仑”)。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多么地矛盾重重——有时候,他会钟情于“两岸的严厉限制”,以其“能赋河水以自由之美与哺育之德”④陈先发:《黑池坝笔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61页。;有时候,他会迁怒于“逻辑所要求的某种严谨”,以其“毁掉了我们最美的旋律、呓语和棺椁”①陈先发:《黑池坝笔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7、165页。;有时候,他欲罢不能地想要化身为一条鱼,这条鱼乃是击壤游戏的高手,以其深知“二分法之谬”,故而能够“同时寄身于钢铁之疲劳与河水之清冽”②陈先发:《黑池坝笔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7、165页。。有正,有反,有合,诗人恰在捶打诗学的绕指柔。这且不提;却说这条鱼如果洄游,不出意料,最终将会重返巨河之源(亦即人类文明之源)——佛家所谓“不二法门”③赖永海、高永旺译注:《维摩诘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0、152页。,道家所谓“抱一为天下式”④朱谦之:《老子校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2页。,抑或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⑤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页。。
三
从数学到诗学的跨栏,其“风险”,可能远逊于从诗学到佛学的通犀。《维摩诘所说经》怎么讲?“若有缚,则有解;若本无缚,其谁求解?无缚无解,则无乐厌,是为入不二法门。”⑥赖永海、高永旺译注:《维摩诘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0、152页。那么,佛学如何引导心猿?——其下境为“有缚”,其中境为“有解”,其上境为“无缚无解”。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不二法门还意味着无受无不受,无垢无净,无相无无相,无善无不善,无罪无福,无世间无出世间,无生无死,无尽无不尽,无我无无我,无色无空,无身无身灭,无取无舍,无暗无明,无实无不实,最终归于无言无说。那么,诗学如何引导心猿?——其下境为“诗”,其中境为“非诗”,其上境为“无诗无非诗”。如汝所见——“风险”逐步升级,佛学最终孵化出一种远在天外的乌托邦诗学,或一种近在眼前的虚无主义诗学。如果诗学盲从了佛学,诗与诗人,最终难免自割头颅。
笔者很早就意识到,学佛不可学诗。但是呢,学诗不妨学佛。怎么学佛?只到中境,勿入上境。诗人的特种行囊过于沉重,装满了词和妄念,那就正好在中境送别燕子般的和尚。且容诗人漫步于“有缚”与“有解”,而让和尚纵身于“无缚无解”(尽管这于他们也甚是艰难)。“有缚”,“规则”与“严酷纪律”也;“有解”,“不规则”与“散漫”也。诗人与诗不必——不可——也不能臻于“无缚无解”的佳境,究其实,正是为了小心翼翼地避开“无诗无非诗”的困境。
这里,且以民国的一次著名唱和为例——周作人《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以其“有分别心”,故而“有缚”;蔡元培《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何分袍子与袈裟,天下原来是一家”,以其“无分别心”,故而“有解”;然则两者都是诗人说话,而非和尚说话;临到和尚说话,既无“袍子”,亦无“袈裟”,甚或也就“无言无说”。“有分别心”,“无分别心”,或许对应了陈先发所谓“从一到二的写作”与“从零到一的写作”——这对有趣的写作学术语,出自组诗《居巢九章》中的《零》。《再击壤歌》当是两种写作的一个结晶,既是“周作人”说话,又是“蔡元培”说话,既是“有缚之诗”,又是“有解之诗”,却绝非“无缚无解之诗”。此乃和尚之残局,却是诗人之胜局,且容笔者后文从容讲来。
四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一个罕遘之机遇,来鉴赏这样一种诗之状态(或思之状态)——“有缚”是个车站,“有解”也是个车站,“袍子”与“袈裟”亦当如是观,“有分别心”与“无分别心”亦当如是观,乃至“精确度”与“即兴性”亦当如是观。诗人在前者与后者之间反复往返,从而源源不断地为诗提供了发生学意义上的“核动力”。此乃诗人之使命,亦是诗人之宿命。倘若往而不返,诗人或将真个做了和尚。陈先发抢购了一大把“往返票”,因而这首《再击壤歌》,无论是从“语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诗形”的角度来看,都呈现为剪刀般的两刃相割式结构,或麻花辫般的缠绕状结构。
首先,从“语义”的角度来看——第一行,“我渴望在严酷纪律的笼罩下写作”,初说“有缚”;第二行,“也可能恰恰相反,一切走向散漫”,初说“有解”;第三至第六行,“鸟儿从不知道自己几岁了/在枯草丛中散步啊散步/掉下羽毛,又/找寻着羽毛”,随手取譬,细说“有解”;第七行,“‘活在这脚印之中,不在脚印之外’”,以画外音方式,再说“有缚”;第八至第九行,“中秋光线的旋律弥开/它可以一直是空心的”,随手取譬,巧用通感,细说“有解”;第十行,“‘活在这缄默之中,不在缄默之上’”,以画外音方式,再说“有解”;第十一至第十二行,“朝霞晚霞,一字之别/虚空碧空,祼眼可见”,随手取譬,借“朝霞”异于“晚霞”,“虚空”异于“碧空”,初说“有分别心”;第十三至第十四行,“随之起舞吧,哪里有什么顿悟渐悟/没有一件东西能将自己真正藏起来”,忽视两种方法论——“顿悟”与“渐悟”的不同,突然将“有分别心”变频为“无分别心”;第十五至第十六行,“赤膊赤脚,水阔风凉/枫叶蕉叶,触目即逝”,随手取譬,借“赤膊”无异于“赤脚”,“枫叶”无异于“蕉叶”,再说“无分别心”,“触目即逝”亦即诗人所谓“完整地消失是我们在现象上最终的胜利”;第十七至第十八行,“在严酷纪律和随心所欲之间又何尝/存在一片我足以寄身的缓冲地带?”,最终归结于“有缚有解”。全诗起句(前两行)的“严酷纪律”复见于结句(末二行),这是长蛇衔尾的一般句法;起句的“散漫”在结句中换成“随心所欲”,则是长蛇衔尾的花式句法。花式,“花”得特别好,否则就会平添至少两吨重的板滞。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全诗总十八行,由肯定而否定,由否定而否定之否定,构建了令人目眩而又如此理所当然的“自反”(self-negative)风景。诗人独以个我之生命,接通世界之生命,就渐次进入了大自如的境界。这个风景,堪称绝景。
上述观点还将易如反掌地引出另外的观点,比如,这首诗交替展开了两套同义词系统。而这两套同义词系统,合成了一套反义词系统。先来看第一套同义词系统——从“严酷纪律”,到“脚印”,到“中秋光线的旋律”,到“一字之别”,到“祼眼可见”,到“渐悟”;再来看第二套同义词系统——从“散漫”,到“散步啊散步”,到“空心”,到“缄默”,到“随之起舞”,到“顿悟”,到“水阔风凉”,到“触目即逝”,到“随心所欲”。显而易见,第一套同义词系统的规模,远逊于第二套同义词系统。这说明,就总体向度而言,这首诗由“有缚”奔向了“有解”。而在所有这些词与词组里面,最为突兀的,不是“中秋”,而是“缄默”。“中秋”,经笔者采访诗人证实,或为必然,或为偶然,乃是此诗的成稿时间。而“缄默”,似乎更像是一个中性词,随时都有可能出离第二套同义词系统,甚至可以加入第一套同义词系统。这个发现,甚是奇妙,可以说令笔者大为惊讶。在孤独的黑池坝,诗人曾多次自释“缄默”。一次,他如是说:“感官雷动,有默为基。默中之默,犹巨枝生于微风之中,不解己之为枝,不知风之为动。相互咬合,无技可分。”①陈先发:《黑池坝笔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8页。一次,他如是说:“假设某种‘永恒沉默的部分’可以成为我们的目的——我们创立语言并不断地写作,是为了加速让它显现——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实上又在否定着它。像卑微的鸟鸣与附于其上的深不可测的宁静,执著于鸣之清越、鸟之短暂,忘乎所以,又不知其忘;处其短而不以形役,闻其声而不计其鸣。”②陈先发:《黑池坝笔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8页。可见“缄默”也者,乃是《维摩诘所说经》所云“无言无说”——这样一座文字的断头台,超越了理性边界,既绞杀了“严酷纪律”,又绞杀了“散漫”。这说明,就某个瞬间而言,这首诗由“有解”奔向了“无缚无解”(这是这首诗的一个虚无主义边陲)。可见佛经也罢,新诗也罢,谁又没有陷入过烂泥般的“文字障”?
现在,从“诗形”的角度来看——第一至第六行,第八至第九行,第十三至第十四行,第十七至第十八行,都用散句;第七行和第十行,中间隔着两行,组成了一对骈句;第十一至第十二行,组成了一对小骈句,第十五至第十六行,组成了一对小骈句,两对小骈句中间隔着两行,组成了一对更大的骈句。当然,骈句不一定服务于“有缚”,散句不一定服务于“有解”——可见“诗形”与“语义”,有时候心心相印,有时候则同床异梦或背道而驰。散句与骈句的反复往返,不太顾及“所指”(Signifié),而颇为任性地打造了能指(Signifiant)层面上的视觉节奏和听觉节奏。这首诗的形式感或仪式感,可谓用心良苦,绰乎有余地响应了艾略特的反面立论——“自由诗并不存在”①转引自[美]斯蒂芬妮·伯特:《别去读诗》,袁永苹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97页。,也响应了桑塔格的正面立论——“一切艺术皆趋向于形式”②[美]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五
前文一再谈到的“往返”,也可以译为“争论”。那就让我们从耽溺太深的《再击壤歌》,回到冷落有时的《击壤歌》。准确地说,是回到由后者引发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一方是籍籍无名的鲍敬言,一方是鼎鼎大名的葛洪(也就是抱朴子)。葛洪与鲍敬言,生活于公元3世纪到4世纪。到了4世纪,葛洪著《抱朴子外篇》,曾如是介绍鲍敬言——“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③葛洪:《抱朴子外篇》,张松辉、张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93、1112、996、1003、1006页。又曾如是介绍自己——“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④葛洪:《抱朴子外篇》,张松辉、张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93、1112、996、1003、1006页。归纳一下两段文字的意思:鲍敬言喜欢争论,葛洪不喜欢争论(除非棋逢对手)。然则,两者终于发生了一场争论:针锋相对,而又几乎不为人知。
鲍敬言与葛洪都是道家人物,这场争论,却几乎把葛洪逼成了儒家人物。《抱朴子外篇》的相关记载,甚为翔实,此处且引来双方主要论点。鲍敬言说:“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⑤葛洪:《抱朴子外篇》,张松辉、张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93、1112、996、1003、1006页。鲍敬言暗引《击壤歌》,将“凿井而饮”,改成“穿井而饮”,又将一二行与三四行对换,由此递进而立论,颇近于今人所谓“无政府主义”。葛洪则说,“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设官分职,宇宙穆如也”⑥葛洪:《抱朴子外篇》,张松辉、张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93、1112、996、1003、1006页。,“是以礼制则君乐,乐作而刑厝也。若乎奢淫狂暴,由乎人已,岂必有君便应尔乎!”⑦葛洪:《抱朴子外篇》,张松辉、张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93、1112、996、1003、1006页。葛洪所谓“明辟”“良宰”,还曾表述为“明王”“圣人”或“皇风”。鲍敬言提出了一种“无君论”,缘于“无为论”,乃是道家思想之正脉;葛洪则提出了一种“有君论”,缘于“有为论”,乃是儒家思想之正脉。除了《抱朴子外篇》,鲍敬言不见于任何古籍。他会不会是葛洪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呢?这个假设过于大胆,那就不妨更加大胆:这场争论会不会是葛洪的此我与彼我的一次或若干次争论呢?
《抱朴子外篇》的政治学命题,或思想史命题,预演了《再击壤歌》的诗学命题。“无君论”之“君”,暴君也;“有君论”之“君”,明君也。道家儒家,相反相成。“有君论”与“无君论”的双向修补,“有为论”与“无为论”的相互修补,就像“严酷纪律”和“散漫”的双向修补。葛洪本是道家人物,却转而提倡礼乐,亦堪称道家修正派。而陈先发,则堪称儒家修正派。诗人之急需不是道家修正派,而是绝对道家,只有后者才有可能封堵他的儒家思想的蚁穴。诗人赋有一首《深嗅》,结尾时,曾发出过极为虔敬的诗学吁请,“等这场小雨结束/‘无为’二字将在积水中闪光/葛洪医生/请修补我。”这位葛洪医生,反而等于鲍敬言,正是所谓绝对道家。
六
笔者已经反复谈到《再击壤歌》,反复谈到《击壤歌》,现在正好由两者之关系,谈到“传统与个人才能”之关系。前文曾有提及的艾略特,曾从两个维度阐述过这个问题:其一,“理解过去的过去性”;其二,“理解过去的现存性”①《传统与个人才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杨炼所谓“同心圆”②参见《同心圆》,杨炼:《鬼话·智力的空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20页。,有证据表明,也是对这种观点的重释。而陈先发,似乎另有一番见解。在孤独的黑池坝,诗人曾多次自释“传统观”。他用得最多的词组,就是“共时性”——“我确知自己能找到‘某个时刻’——在它之内,不管有着往日的隐士,还是明日的变形战士;不管是庄周在喂养母龙还是希梅内斯在种植石榴树。”③陈先发:《黑池坝笔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再击壤歌》与《击壤歌》,既平行,又交叉,故而不免参差。借用艾略特的观点,或许可以说,《击壤歌》催眠了《再击壤歌》,前者呈现出一种倔强的“现存性”;按照陈先发的观点,或许可以说,《再击壤歌》唤醒了《击壤歌》,后者提供了一种令人喜出望外的“共时性”。“现存性”与“共时性”有同有异,其异,导致了大相径庭的结果:艾略特的诗学旅行,投宿于一种安全的“非个人性”;而陈先发的诗学冒险,立锥于摇摇欲坠的“个人性”。已知与未知,名胜与秘境,端看诗人如何取舍或搭配。
艾略特与陈先发似乎都没有致力于某种条分缕析,在这里,笔者乐于稍作尝试。如果将中国古典诗——当然包括《击壤歌》——视为“赋能者”,从而察看新诗之反应,就会厘出好几种大异其趣的“接受模式”。第一种,“貌合神离”,可以鲁迅先生为例。比如《故事新编》各篇,亦即《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和《起死》,其“原典”,包括《尚书》《左传》《庄子》《墨子》《山海经》《淮南子》《史记》《列异传》和《搜神记》。“今典”之于“原典”,全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滑稽模仿”(parody)。除了短篇小说,还可以举出鲁迅的新诗。比如《我的失恋》,其“原典”,乃是张衡的《四愁诗》。来读《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再来读《我的失恋》:“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后者,居然步前者之原韵。这样的“滑稽模仿”,正是所谓“貌合神离”。第二种,“貌神俱离”,可以穆旦为例。比如《饥饿的中国》(其三),其“原典”全是“西典”,既包括叶芝的《再度降临》(The Second Coming),又包括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还包括奥登的《西班牙》(Spain)④参见《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江弱水:《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34页。。既然无涉中国古典诗,那就毋须引来原文。这样的“非中国”⑤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正是所谓“貌神俱离”。第三种,“貌神俱合”,可以张枣为例。比如《何人斯》,其“原典”,乃是《诗经·节南山之什·何人斯》。来读《诗经·节南山之什·何人斯》:“彼何人斯,其心孔艰。”再来读《何人斯》:“究竟那是什么人?在外面的声音/只可能在外面。你的心地幽深莫测。”这两件作品,正是所谓“貌神俱合”。第四种,“貌离神合”或“遗貌取神”,可以陈先发为例。比如《再击壤歌》,其“原典”,乃是《击壤歌》。单就标题而言,两者确已建立显而易见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而就正文而言,两者既可以说是毫不相关,也可以说是心心相印于某个肉眼看不到的隐形峰顶。这两件作品,正是所谓“貌离神合”或“遗貌取神”。陈先发与张枣另有一个不同:后者的《何人斯》,标题沿袭自“原典”;前者的《再击壤歌》,标题改窜自“原典”。陈先发有意添上去的这个字——“再”,似乎预示着这两位诗人,或这两首新诗,将在不同的半径内分头完成各自的蹀躞。
鲁迅和穆旦正当一个弑父时代(亦即破坏时代),前者正当弑父时代的初期,后者正当弑父时代的后期。张枣和陈先发或值一个拯父时代(此乃笔者杜撰,亦即建设时代),前者正当拯父时代的初期,后者正当拯父时代的中期(谁知道呢,也许仍属初期)。鲁迅的“故事新编”,穆旦的“西诗东渐”,张枣的“古典今译”,乃至陈先发的“旧题重写”,可谓各自夺取各自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时代的自觉与个人的自觉,两者,有时候是水推沙,有时候是金镶玉。从当年的“大破”到如今的“小立”(尚不是“大立”),诗人或已迎来转机,可望攀上那如此崔嵬的“共时性”。陈先发已经用个人的自觉,响应或强化了时代的自觉。所谓传统不再是外在的甲胄,而是内在的气息。如盐入水,半穿袈裟。这个意义,应该放到新诗史上去总结。闪转腾挪,莫非偶然。偶然也者,莫非必然。所以说,从新诗的苗头,也就可以见出百年中国文化的趋势。
七
笔者已经借道于或者说受教于《击壤歌》和《再击壤歌》,论及至少两对“二律背反”(antinomies):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乃是“离”与“合”的二律背反;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乃是“严酷纪律”与“散漫”的二律背反。哲学家康德所谓“二律背反”,已被如此笃定的陈先发而非气喘吁吁跟上来的笔者,三申为以不变应万变的诗学之锁与诗学之钥。
因而,谢天谢地,本文的起步点以及落脚点都是“诗”,都是“诗学”,而非广义上所谓“文化”。笔者无意于展开过于洋溢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然则看起来有点儿缭乱的东挦西扯,或许也曾误入过艾柯所谓“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那就真是前有狼,后有虎。好在,诗人陈先发从来就不反感“过度诠释”。在孤独的黑池坝,诗人早已预支给笔者一根如此如意的定海神针——“小说家自身容量大于他的小说之和,而诗人小于他的任何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