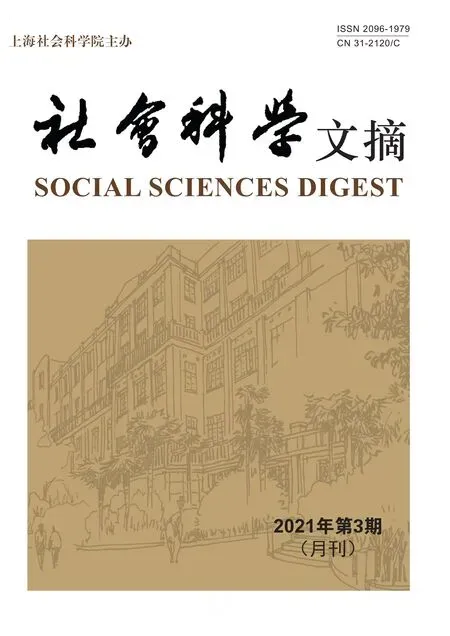自有住房陷阱与中国住房因城施策
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奥斯瓦德提出了著名的“自有住房陷阱”假说,他通过经验研究认为:购买房产会降低劳动者的流动性,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和经济活力的下降。这一假说对英美大力补贴自有住房的制度提出了质疑,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持续的讨论和验证。国内学界目前鲜少有相关的研究,“自有住房陷阱”是否适用于中国亟待展开研究。
自有住房陷阱:概念及争议
(一)概念与理论
1996年,英国学者奥斯瓦德发表了会议论文《对工业化国家高失业率的一种推测》,文中运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1960—1990年失业率和住房自有率数据建立简单的一元二次OLS回归模型,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住房自有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当时正值欧洲失业率大幅上升时期,许多学者都试图探究高失业率的成因及对策,奥斯瓦德也是其中之一,他本人也承认“自有住房陷阱”是假说不是结论,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去验证。
奥斯瓦德对失业和自有住房之间关系的主要解释是:当房主考虑搬家来接受新工作时,由于购买和出售住房而通常面临比租客更高的交易成本,这些费用也意味着房主相比于租房者更可能选择不搬家,接受更长的通勤距离,这会导致经济成本上升,对工作的激励减少。交易成本增加的另一个后果是:一些房主在求职时会接受完全不适合他们的工作,这种不匹配降低了经济效率,会使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恶化。
(二)争议
奥斯瓦德的研究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的英国刚刚完成大规模的公共住房私有化改革,他的研究结果对住房私有化改革是一种讽刺。如果“自有住房陷阱”确实存在,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住房制度需要再次改弦更张。随后一些学者运用宏观数据验证并支持了奥斯瓦德的假设,然而这些宏观研究和长久以来对购房者与流动性及失业关系的微观研究相悖。个人层面的研究表明,相比于租客,业主的失业风险更小,失业持续时间更短且工资收入更高。同时,奥斯瓦德的研究也和家庭自有住房优势的大量经验研究相违背。在英国及大部分英语国家,长久以来存在对私人产权的偏好,拥有产权被认为可以带来财富积累,为子女带来更好的教育和收入,更多邻里的社会资本以及居住的稳定性等正面效益。许多研究者认为自有住房是值得鼓励的,政策补贴是必要的。
(三)住房自有率究竟是高好还是低好?
微观层面的研究显示,房主比租房者在就业市场有更好的表现,这是否意味着高住房自有率就会带来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现实的经验又显然不是,从宏观的国家和城市层面都不支持这一假设。微观的经验和宏观的数据存在矛盾,主要原因在于住房自有率和失业率、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等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存在极强的内生性,需要控制一定的前提条件来分析因果关系。
转型过程中的住房市场对家庭自有住房的准随机分配,被认为可以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者对欧洲社会住房私有化的研究发现,自有住房促使家庭更加努力工作,增加劳动收入,并促进家庭的流动性,没有证据表明相对于租房者房主的失业风险更高。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要考虑自有住房带来的外部性,住房自有率增加带来失业率上升可能是由房主消费减少和就业竞争增加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导致的。Sodini的研究也证实,在购房的第一年,家庭消费支出会显著下降,但随后这一影响会逐渐降低,当房主选择卖出房产时,家庭的消费又会随之大幅上升,房产具有抵御家庭风险的正面作用。
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是美国相对低收入区域,这里的住房自有率较高,主要原因是不动产价格偏低,迁出的资产转换成本过高,自有住房确实“锁住”了这一地区的房主。次贷危机以来,美国住房违约增加房主的流动性,住房价格下跌导致房主流动性下降,正负影响相互冲抵,结果显示房主和租客的失业率没有明显差异,自有住房并没有锁住购房者带来的结构性失业。
中国大城市:自有住房陷阱是个伪命题
虽然奥斯瓦德的“自有住房陷阱”假说从概念到方法都存在较大争议,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为我国住房调控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一)购房行为与人生态度
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产属于稀缺资源,房价本身就是对新移民的一种筛选。大城市购房的主要门槛为购房资格、首付款及贷款资格,这本身就是对购房者受教育水平、个人能力、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原生家庭财富等的一种正向筛选。
购房行为背后更折射出人生态度的差异,购房者通常对自身及所在城市发展前景看好。购房也是个人对家庭责任担当的具体表现,因为在中国城市,自有产权住房通常与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挂钩。购房后的人生态度和家庭行为也易发生积极的改变,包括:家庭的满意度、幸福感、凝聚力增加。买房会促进个体更积极努力地工作,提升职业能力,增加收入。购房会促进家庭消费理性增加,减少奢侈型和冲动型消费,还会增强个人及家庭的风险意识,从长远看有利于家庭的财富积累。
(二)购房行为、流动性与就业
从短期看,购房可能导致家庭流动资金大幅减少,但并不等于流动性降低和就业机会减少。就流动成本而言,只有当购房者选择出售本地房产时,才可能面临比租房者高的流动成本,这一成本主要来自房产交易的佣金和税费。同时,租房者的流动也会面临经济成本,例如可能违约而带来的押金损失、更高频率的搬家带来的成本等。除了考虑经济成本,更需要考虑经济收益。对于购房者而言,大城市房产流动性和增值性较好,在卖出时通常能获得一定幅度的溢价。无论是购房者还是租房者,流动的目的地多是发展机会更多的城市,大城市的房产会帮助希望流动的购房者获得更多金融、财富的支持与保障。
从长期看,随着大城市房价的上涨,购房者财富因此而增加,迁移时卖出房屋所获得的收益也会随之增加,购房者陷入“自有住房陷阱”可能性更小,反而会增加购房者迁移流动的可能性。从长期的劳动力市场均衡以及失业和搜寻理论来看,“自有住房陷阱”也很难成立。假设租客会迁移到失业率更低且工资更高的地区,这会推动各个地区失业率和工资最终趋于均衡。如果自有住房造成失业和工资的下降,公司会选择迁移到购房者更多的地区,最终由竞争推动各个地区的失业率和工资达到均衡。
(三)大城市自有住房与城市发展的外部性
1.大城市自有住房的负外部性
拥有房产是否会带来负外部效应,首先是消费的下降?住房消费有三大特点。一是住房消费会动用大额家庭储蓄,通常需要动用夫妻双方及父母共三个家庭六口人的储蓄。购房本身还具有杠杆效应,住房贷款有利于扩大消费甚至提前消费。二是住房消费不仅会拉动后期消费,如家具家电消费等;由于房地产产业链很长,还会拉动包括水泥、建材等在内的前期消费。三是房产具有财富效应。当房产增值时,购房者财富扩张,消费信心也因此而增加,会扩大消费;当房产缩水时,消费会因此而缩减。
购买住房具有投资和消费双重属性,在收入既定或者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住房消费的结果是促进消费,并对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带来很大影响:与住房相关的消费增加,而与住房消费关联不大的消费可能因此受到抑制。当然,家庭在计划购买住房时,为购房积累必要的资金,对当期消费会带来负面影响。
家庭住房消费杠杆是否会带来债务风险和房价泡沫?2019年中国一二线城市首套房首付比例普遍大于等于30%,二套房首付比例在50%—80%之间。即便考虑首付贷、二押、众筹等加杠杆的情况,中国家庭部门购房杠杆率也并不高。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城市因房价高、人员流动性大等原因,总体而言,大城市住房自有率并不高,中小城市则相反。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不同住房制度国家的城市都呈现出相同规律。
2.大城市自有住房对城市发展的正外部性
自有住房对于大城市发展的正外部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世界范围内的不动产相关税收构成了地方政府税基的重要来源,为城市发展与居民福利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第二,由于房价上涨,生产与生活成本增加会导致部分对租金与劳动力价格敏感的企业因成本上升而选择外迁,对低附加值产业造成挤出效应,同时也会迫使留下的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客观上促进城市产业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第三,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带动土地价格上涨,使得土地财政成为可能,政府有更多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民生改善。产业空心化和高房价并无必然联系,例如美国中部铁锈地带城市衰落的主要原因并非房价过高,产业外迁后导致房地产价格大幅下挫,但没有带来产业的回流。
中国中小城市:自有住房陷阱与贫困陷阱
收缩型城市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无法避免的现象,以齐齐哈尔、鹤岗、玉门等为代表的收缩型城市,其典型特征表现为人口外流、GDP与房价的持续下降,且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以及民生和基础设施凋敝,城市发展进入恶性循环,在未来更有可能导致当地拥有产权的家庭被困在其中,无力迁徙到机会之地。
中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收缩型城市,城市收缩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和经济的衰退、房地产价值降低、空间品质下降、犯罪率提高等。只有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收缩型城市才有可能安然度过城市生命的收缩期,甚至有机会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否则极可能步玉门、鹤岗等急速衰败城市的后尘而沦为废城,结果是家庭财富的毁灭和留守居民的贫困,不利于人口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区域发展更加失衡,对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造成负外部效应。
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奥斯瓦德的“自有住房陷阱”假说,在中国的大城市并不成立,拥有房产会帮助大城市希望流动的购房者获得更多金融、财富的支持与保障,不会给购房者带来“锁定”效应。大城市的购房行为给城市发展带来正外部效应,表现为带动更多消费,与不动产相关的税收增加会为城市发展与居民的教育、医疗、安全等福利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还将有助于城市的创新与产业升级。
在以鹤岗、玉门等为代表的收缩型城市,奥斯瓦德的“自有住房陷阱”假说确实成立。城市在收缩与衰落过程中,房价下跌导致城市发展进入恶性循环,拥有房产的家庭因房产严重缩水导致资产无法转换或转换成本过高,被困在原地陷入贫困陷阱,这将对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外部效应。
(二)思考:中国区域发展前景与住房因城施策
房屋具有不动产特点,空间上不可移动。流动性较差的房屋会面临资产价格贬值,最终可能只剩下居住属性而不具备资产属性。我国一线城市的住房流动性最强,投资价值最大,二线城市次之。在个人和家庭层面而言,自有住房是应对未来可能风险和变化的物质保障。在国家和社会层面,自有住房还具有与社会保障相互替代的功能,这都是住房资产属性的体现。
以英美等为代表的欧美国家鼓励自有住房的住房制度,和以德国、瑞典等为代表的对自有住房持中立态度的住房制度,通常对应福利国家分析框架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社会民主主义”住房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住房的资产属性,政府提供全面的住房福利;在“自由主义”住房制度中,政府提供最基本的“安全网”“救护车”式的住房保障,剩下的住房需求交给市场,通过鼓励住房的资产属性以实现住房需求的满足及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平衡。近期的研究显示,为了更好地应对老龄化、贫困等社会问题,荷兰、瑞典等正从“社会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住房制度转变,普遍削减住房保障补贴。因此,一旦自有住房失去流动性和保障功能,就需要政府大幅增加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否则个人和家庭面临的贫困、健康等风险将可能大大提高。
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两大不可避免的趋势:一是收缩型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二是住房自有率在不同层级的城市间出现分化。两大趋势相互作用,将对中国城市未来前景产生较大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通常城市规模越大,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流动性越大,住房自有率相对越低,反之则越高。我国由于1998年前城市普遍施行福利住房体制,因此目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住房自有率普遍较高。未来大城市住房自有率将逐步降低,中小城市住房自有率维持较高水平。住房自有率水平较高的中小城市,相当部分将会沦为收缩型城市,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应对。大城市住房自有率逐步降低意味着租房市场不断扩大,购房门槛不断提高,需要解决的是购房难和租房难的问题。基于两种住房制度各自的优缺点,结合我国住房市场及城市化进程,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租购并举,公私合作。为了增加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给,同时实现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两种模式下的住房制度都从政府直接主导的住房建设转向了公私合作的间接补贴,例如英国、德国、法国等较为普遍的社会住房,德国、北欧国家较为流行的合作社住房以及美国政府通过补贴私人机构、开发商以及购、租房者个人的住房保障体系。这些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形式都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第二,逐步放松直至取消大城市的限购、限贷、首付比例较高等限制购房政策。住房政策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改善和纠正市场的负外部性,提升市场的正外部性,以此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促进城市和经济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未来大城市购房门槛会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不断提高,行政上的购房限制政策会进一步提高购房成本,导致更多大城市新移民只能在租房市场解决住房需求。租房供给一是来自私人市场,包括拥有多套房屋的个人房东及自如等长租公寓机构;二是由政府提供廉租房。目前租房市场中私人提供的租房受到限购等政策的限制,压力会转嫁至政府供给的廉租房,租房数量的缺口将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财力进行补贴,这有悖于租房市场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第三,适度加大对大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租购补贴。由于大城市购房和租房成本的不断升高,住房政策不仅需要逐步解除对大城市购房的限制,同时还应适度放低门槛,加大对大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租购补贴。
第四,加大对有收缩风险的中小城市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转移支付。有收缩风险的中小城市居民,未来很可能面临自有住房陷阱及贫困风险。政府宜保持并增加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不宜也不需要在住房尤其是购房政策上过多倾斜。面临收缩风险的中小城市的财政收入也是捉襟见肘,应当适度加大对这些城市的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