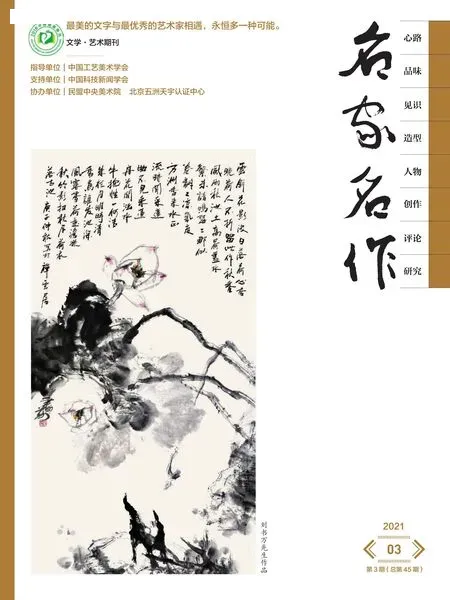中国宗祠的起源与当代发展—传统宗祠研究系列之二
张 锋 张桂红
一、引言
宗祠,就中国设计史,特别是中国建筑设计史而言,其设计直指独特信仰命题,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宗祠从出现到遍及天下,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历时数千年的伟大创造。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宗祠才不断地激发学者的学术兴趣,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考察与论述。笔者长期致力于对中国传统宗祠的研究,有鉴于学术界对宗祠源流演变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的现状,力求从历史与文化艺术的角度对中国宗祠的起源与发展做整体梳理,同时从文化空间角度审视传统宗祠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价值与启示。
二、文献中所见宗祠起源
宗祠作为民间祭祀祖宗而建立的场所,由来已久。关于中国宗祠的起源,相关史料有详细记载。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称谓,如宗庙、家庙、祖庙、私庙、宫室、祖祠、墓祠、家祠、庙祠、寺庙、食堂、斋祠,以及宗祠等。名虽不同,理实一也,都是祭祀的场所。本文所论宗祠事实上以涵盖四民在内的民间宗祠为主体,兼及统治者的宗庙。
明代以后出现的祠堂与古代文献记载的祠堂含义有所不同:古代为名人祠堂,明代以后的祠堂主要是宗族、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即民间宗祠。明代嘉靖之前,官府禁止民间私立宗祠。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献末议请明诏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礼疏》,建议准许民间设立祠堂,明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准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遍天下”。这就破除了以往的限制。由此,宗族祠堂实现了建制上的突破性发展,出现了明清宗祠遍布天下的局面。
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的上书和嘉靖帝“推恩令”的诏颁,是造成明清宗祠遍天下的直接原因。当然,这也与明清统治者教化为先、孝治天下的理念吻合,宗祠的不断发展,更符合统治者的意愿。
“祠堂空间的神圣性是群体(或个人)在地方变迁过程中,通过对祠堂的主观认知,在祠堂的主体空间经验以及客观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变迁中不断得到建构和再生产。”社会建构促成宗祠神圣性的形成,宗族社会变迁成为宗祠神圣性的内在动力。简言之,宗祠神圣性的建构与族众的日常行为,是宗祠及其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元代是宗祠兴起的关键时期。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国家,统治下的汉族各阶层受此刺激,血缘与地缘的凝聚力、向心力得到了充分增强。在北方,连绵的战乱导致北方汉族各阶层几经迁徙。南方汉族虽然亦经大乱,但社会环境在离乱后迅速恢复较为稳定的状态,宗族组织得以获得较快发展。庶民阶层悄然突破礼制限制,自建祠堂的现象较多出现。乡野村庄开始按照《朱子家礼》的设计理念修建本族祠堂。兴修祖祠由此而兴,故有“近代祠堂之称,盖起于有元之世”。此处所指的“近代祠堂”即为宗祠,由此可知宗祠的起源为元朝时期。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的上书和嘉靖帝的“推恩令”的颁诏,使宗祠建设更加合法化。
元代是家祠向宗祠演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当宗祠的创建受到世俗政治权力与资本力量的双重压迫之际,村民往往采用迂回抵抗战术,在特定的时空与政策环境下实现“避让但不逃离”的策略目标。既回避正面对抗避免毁灭性打击,又在表面服从与实质性建设中实现平衡,从而得以在小规模的改变中巧妙地实现自身意志的宣示与表达。
在权力压迫体系下民族意识兴发,推动汉民族血缘和地缘凝聚力增强。元代宗祠的兴起是汉族各阶层自我保护意识的反映。迂回抵抗战术体现了汉民族群体在文化压迫状态下的双重性特征,即一方面这是抵抗外界文化压迫的主动性回应,彰显自身作为权利主体的积极主动性;另一方面则由“迂回”行为表明了权利宣示的弹性与服从,说明其不能硬抗的局限性。不过这也恰巧就是智慧之所在,也在弹性中取得了自身文化特征的延续。
士大夫是元代宗族势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不断的战乱导致许多人弃家逃亡,几经迁徙方流落到相对安定的环境,不少士大夫在新的统治秩序中获得某些政治权力。由于元代重视家世“根脚”的选官理念,所以他们的权力由此得到较为长久的传递。他们开始反思现实政治、理学秩序与宗族的关系,试图构建一个符合“一本万殊”的“理”世界秩序。而同根同源的同姓世系族众正好就是这种聚合体系的集中体现。理学观念与现实政治需要推动士大夫自觉地关怀宗族势力,演化出宗族自建祠堂的现象。此风播之下,一般乡里、村落也开始兴建墓祠或者祖祠,并进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祭祖制度。
如果说南宋时期出现了家祠向宗祠转向的趋势,那么,元代则是开始在宗族祠堂上形成系统的祭祖制度,为向明清过渡打下了重要基础,因此,元代是中国宗祠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宗祠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更早,如果从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来对宗祠加以考察,则是更为深刻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等。汉朝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于是“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天问》。由此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这段话是对“祠堂”一词最早的记载。虽记载于东汉,但是事实大体上与战国状况不远。
更早一点的如《礼记·曲礼》记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另外,《礼记·王制》也明确规定:“周天子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士为一庙,庶人不准设庙。”这是关于统治者宗庙的较早记录。统治者宗法制度下的家庙事实上三代均皆有之,故此,这里的“宗庙”算不上是对民间祠堂的记载。事实上,古代所谓的三礼,大多成书于汉代,反映了秦汉时代的思想印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祠堂的礼仪,制定了详细的典制。西汉的《礼记》、唐代的《开元礼》和朱熹的《家礼》,则是两千年来论述祠堂礼仪典制最为规范、影响最大的历史文献。
朱熹《家礼》对祠堂形制作出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君主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位。”“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复之,令可以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卓。”“神主兼藏于犊中,置于卓上,向南。龛外各垂小帘,帘外设香桌于堂中,置香炉香盒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卓亦如之。”由此可见,《家礼》对于祠堂形制的深入思考和详细规划,虽参酌古典,但事实上是朱熹自身对礼制观念在家族场合落地的综合现实考虑。出于理学观念,《家礼》特别强调祠堂在家族中的崇高地位。《朱子全书·家礼卷》关于祠堂的系统论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家族祭祀与宗祠建筑提供了可供资鉴的理论与实操体系。
当然,用于祭祀的宗庙,后世文献记录将其延伸到上古的五帝时期(即原始社会晚期)。如《古今图书集成·宗庙祭典》就有“帝喾高辛氏始立宗庙”“帝尧作七庙以享先祖”“帝舜立七庙”及《夏制因唐虞立五庙》《殷制七庙》等记载。这些都是后世记录,很难说在当时有什么实质性的考古遗迹作为佐证。
阐明历史关联是认识建筑风貌及其发展的前提,这一点在研究中尤其重要。作为家族文献的重要物质载体,家谱中收录了大量的祠堂,祠堂是家谱章节中间的重要内容。家谱中关于祠堂的记载,通常两部分组成:一为祠堂图画,二为文字注释。一般是图主文辅,文字主要是用以注释祠堂图像,以便更清楚地说明祠堂分布等情况。囿于篇幅,此不赘述。
三、当代中国宗祠的发展
中国的宗祠家庙已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发展,20 世纪以来更是表现出以往所不具备的独特而复杂的发展态势。具体而言:其一,我国20 世纪中期对祠堂有过三次重大打击,由此发展受到重挫。此后,出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民间自发创建, 20 世纪后叶宗祠又取得了新的发展。其二,港澳台宗祠由于未受冲击,所以继续沿着固有轨迹向前运行、发展,旧有的宗祠建筑和传统得到了较好的保存。
作为民俗古建筑的代表——历时四五千载的中国古典宗祠,现存数量众多,发展盘根错节,民众敬祖习惯又绵绵流传,不大可能就此绝迹。以绩溪县为例,当地文献对宗祠发展历程记录得很详细,现存宗祠也有可观之处,宗祠保护可称得法。该县乾隆时期即有宗祠115座,到嘉庆年间发展到189 座,民国后期的1947 年达到了340 座之多。在1982 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该处仍然保有旧祠堂160 余座。再如广西贺州临贺宗祠,最早创建于明代,发展到高潮于清代,现在仍然保有24 座姓氏宗祠,其中多数为旧有的宗祠建筑,形成难得的宗祠建筑群落。
尊天敬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于传统政治文化中则形成了崇“圣”的信仰现象。“圣”根源于原始氏族的信仰体系,表达的是对姓氏祖先的尊崇,反映了不同氏族的精神境界,足以划分不同氏族,与姓氏一道成为氏族的独特符号。在历史发展的历程中,演化出“圣”“天”和“祖”等地方信仰符号体系,并内发地演化成族众的内在思想习惯,成为构建地方政治生态和文化体系的重要思想内容。
该信仰体系事实上不只是民间的,亦是官方和上层的,是上下一体的信仰体系。就后者而言,宫殿、坛庙等体现神权现实化的礼制建筑,在古代中国城市建筑空间布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深刻体现着文化理念对于地理空间的改造。于民间而言,则让宗祠成为村落的神圣空间,以此作为传递代际宗族记忆和孝亲敬祖观念的建筑载体。由此,宗祠在乡土中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生活与乡村空间发展的形塑上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民众来说,民族和精神层面的古迹遗存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民间修谱、建祠活动渐次展开,各地姓氏宗族组织也不同程度地重建。该时期的宗族组织不同于以往传统,主要是宗亲联谊性质的组织,大多剔除了封建族权等内容。他们的作为主要表现为修缮宗祠和续编族谱。旧有的宗族传统形态实现转型。这时宗祠的作用已经不再是宗族内部司法处所,也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族祭祀的场所,更多地保存了孝亲敬祖的精神内涵,成为村落中的公共文化空间。
“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父母与先祖死后就会消失,而是相信逝者的灵魂对家族来说仍然重要,还能够显灵。”在当代,宗祠更多呈现的是文化形态。当代宗祠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因应新时代出现新情况,产生新的价值观念,如文物价值、教化价值、寻根价值、文化娱乐及旅游价值等。
即便出现新的时代特征,但是毋庸讳言,宗祠的排他性与一姓私有仍然是存在的。祠堂中商讨的宗姓事务虽然也属于乡村公共事务,但是与现代公共事务还是有很大不同。为了解决此类议题的偏好与现代公共事务的偏差,需要用妥善的办法加以解决。宜疏不宜堵,为此广州市三水区政府设立了议题上的政社协商机制。不是单纯地用行政命令直接禁止,而是提倡在保留祭祀祖先传统功能的基础上,对本村其他公益事业开放使用,如果能做到,将根据《广东省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给予申请总投入的30%作为奖励补助。这就有利于宗祠的功能的现代改造,促成宗祠由单一姓氏活动空间向现代公共活动空间的转化,政社协商机制获取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不少宗祠在保留旧有传统文化的同时,成为党的建设、基层自治、文娱活动和社会组织孵化的重要阵地。代表性的如修葺后的陈氏大宗祠,当地结合祠堂的场地与凝聚力优势,汇聚了文化娱乐、体育运动、议事决策等新元素,进驻了舞蹈协会、醒狮协会、龙舟协会、老年人协会等14 个文体类协会。这既优化了社区环境,又融洽了居民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搞好了党群干群关系,有效破解了宗族势力与村庄治理的传统难题,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建设提供了新的良好范例。
广东省通过活化保护宗祠建筑,发掘宗祠优秀传统文化,开启了宗族文化的门扉,弘扬了岭南地区传统文化,展示了固有宗祠文化魅力,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化强省”。广东经验提醒我们:乡村也应该具有和建立自己的品牌,那就是把握乡村文化的核心。
宗祠不仅是村落姓氏宗亲的活动场所,还是既有传统文化延续的符号象征、凝聚族众的心理场域,诚如一位宗祠堂长所言:“祭祖、喜庆等族中大事都在祠堂里举行,自古以来祠堂在我们村的地位是最高的,没有祠堂的存在,村子就不是村子了,(村民)变成一盘散沙。”宗祠理所当然地成为村落文化的“精神空间”。
乡村振兴既是空间生产,又是村落品牌建构,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发现和探究村民潜意识中的具有共性的综合反映,并通过抽象化的、特有的、能识别的心智概念表达出来,宗祠才能更彰显时代价值。
四、结语
通过对宗祠起源和发展的梳理可以发现:在显性层面上加强传统宗祠的文化遗产保护,即尊重传统宗祠在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并对其不断完善,以丰富和发展民族艺术理论,走出传统宗祠保护的困境;有利于在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与促进民族大团结等方面实现创新。在隐性层面加强传统宗祠的文化交流作用,即抓住东南亚国家华人宗祠文化和宗亲社团这一认同的载体,加强国际交流,改观各国对于华人的认知,使宗祠和宗祠文化在进一步凝聚族群与华人意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和促进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夯实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也将是今后中国传统宗祠研究发展的主要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