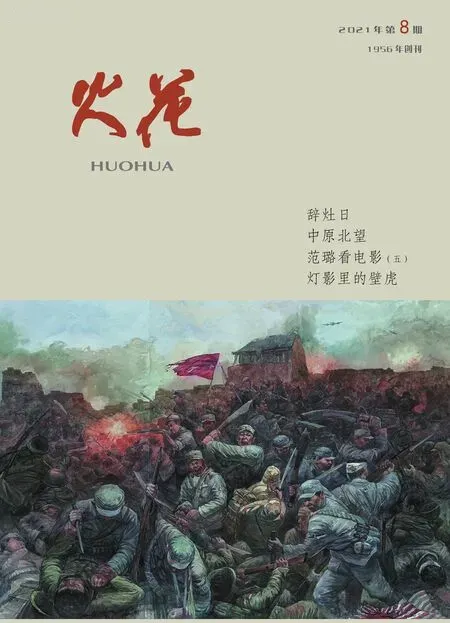烟 火
胡兴法
第四个早上,我醒来。
我背着手,在寻找烟。
有人的地方就冒烟,所以叫人烟。
人还有,可不怎么冒烟了。
整个村子藏了起来。
我闭上眼,细数,那时村子里的烟大致有六种,粗的、细的、浓的、淡的、硬的、软的。当然还有黏的、稠的、滞重的、飘逸的、阳刚的、狐媚的、恬淡的、满怀心事的。
烟如人,最有个性。每家的烟有每家的个性。那时村里的人还不时兴模仿。
小时候,我还能分得更细。根据烟的聚散、体态、胖瘦、浓淡、硬软,判断出主人家的大致秘密。
烟是每家的心事。
因为烟,整个村子在我眼里再没有什么秘密。
一股子一股子的黑烟,直往房顶窜,像人发脾气用头撞墙。准是这家的男人出门了,家里的存柴烧没了,女人只好将就点,塞点湿松树枝。
冒出的烟一离开烟囱口,就没了形状,丢了魂,跌跌撞撞,黑中带灰,铺天盖地,欲盖弥彰,像懒惰的女人一年没洗过的头发,披散在后脊。烧的定是松树或杉树皮。回头清点下自己的林子,看近几个月黑风高夜,是否少了几棵已能做檩子的杉树。树皮在晚上,用刀刮掉。第二天一早,一不做二不休塞进灶膛,裹上干柴,烧掉,毁尸灭迹。有啥用呢?还是会被第二天早上放牛的我,顺着这家屋顶冒出的炊烟,逮个正着。
遇上这事,我从不告诉大人。小孩子的事不能说给大人,就像大人的事不屑于说给小孩子:小孩子家懂个啥。
也有屋顶的烟冒得飘逸的,如祥云,丝丝缕缕,漫不经心,飘飘然,似云卷云舒,不绝如缕。这大多是日子过得轻松的。一个村子,一个屋场,总有几户过得滋润的,像几块能得到及时灌溉的田,长势总是高过别人一头。他们家冒的不是烟,冒的是尖。灶里烧的,多半是刨花,经常请得起木匠打家具嘛;或是干栎树柴,火质硬,经得起熬。火与烟一样,表面看是一样的,其实有软有硬。
有屋顶冒麻花烟的,一拧一拧的,两股或是多股缠在一起,好得不得了,绞得很死,打着旋子,扶摇直上。化蝶我没见过,化作青烟的缠绵,这便是。
冒这种烟,有两种情况:一是柴烧得不专一,几样柴烧混了,烟就冒杂了;一样柴一样烟,一人一脾气。二是这户住在风口上,风干起了见风使舵的事,搅得这家的烟走了形,变了样,原本直的,成了弯的;原本分开的,成了抱在一起的。这种情况下,风可以改变烟的走势,奇观出现,如命运扭转人的走向。当然,殊途同归,烟与人最终都踏向虚无。
那时早起,我们在山坡上放牛。朝阳观山高,我们闲得无事,就开始盯着看各家屋顶的烟囱。只要风不乱刮,不搅和,不见风使舵,我绝对不会看走眼。
徐青家的烟囱像是长了一条长腿,总是第一个跑向屋场上空。它是整个徐家屋场准时升起的第一面旗帜———黑旗。其他家的炊烟,在这股烟的引领下,好一阵才跟进,软沓沓地冒上来,冒得不持久。谁家的早饭也没徐青家的丰盛,他家的菜炒得多,多出别家两到三个。菜多烟冒得久,烟引导着柴,柴烧动着菜,菜牵动着媳妇的手。烟、柴、菜、媳妇是四件事,其实是一件事。他的媳妇是全屋场最能干的,起得最早的,劳力最好的,干活最多的,收工最迟的。所以,他家的烟囱,早上第一个冒烟,晚上最后一个收烟。
徐元家烟囱的烟冒得最迟。一个屋场,冒烟有最早的,就有最迟的。媳妇有最勤快的,就有最懒散的。他的媳妇生得老实,他当年娶她时穷得没底。没底时,人自己心里也没底,什么都可将就了。
他们常睡到太阳醒过来,升了好几竹竿高还不起床。此时,徐青家的两口,加上十三岁的大儿子,已将村东头三分地的草锄完了。看着徐元家屋顶的几根细烟,我也看到了他家生活的细节:起床了。媳妇抱着个夜壶,从稻场钻进茅厕,倒掉。回到灶屋,胡乱塞两把柴,热点剩饭。扛上锄头,这才出工。
一家人有一家人的烟囱,没两户是一样的。炊烟是村民盖在天空的印章,烟囱是直戳天空的一截手臂,村民们总想和天空有个接应。
原来一溜儿三间房,兄弟俩分家了,一人一间半。早上细数,会发现整个屋场上空,果然又多出一股子烟。我数过,原来是二十一股,连夜长了一股,成了二十二股了。兄弟分家了,烟也分出了一份。这股刚刚分出的烟,要瘦瘦弱弱地冒上起码五个月,之后,才能与其它炊烟一样壮实。
烟囱的形状也不一。最好的烟囱,是个子最高的,还用水泥糊上厚厚一层的烟囱。有了这个高高的基座,炊烟刚一冒出来,就比别人高出了一截。好比烟中贵族,有款有形,高傲得像穿高跟鞋回到村里的姑娘。
也有的在屋顶用石头随便砌一个的,乍看像个大鸟窝。
也有的干脆将就在土墙上斜着挖上一个的,像个大鼠洞。挖到外墙沿,胡乱扣上一个没了底的破瓷盆,一来免得雨溅进去,呛灭了烟。二来凡是烟,总得有个出路。这样给烟拢了个口,又收了个腰,让寒碜的烟尽可能冒得有气势,有形状。
儿时放学路上,就有一截这样的烟囱。我们那时就知道,寒碜的烟囱连接着寡味的锅台,寡味的锅台连接着寒酸的家。
天落雪了,放学了,有娃娃爬到这家屋后的土坎,用雪堵他家的瓷盆烟囱,堵得死死的。这家做饭时,冒不出来烟。烟掉个头依然退回来了,委屈得很,退回灶屋,呛得他们泪流满面。饭实在是做不熟了,出得门来,才看到竟是这帮娃娃们干的,把烟道堵死了。烟可是一家人呼吸吐呐的另一个大器官,堵烟囱就是堵灶台,堵灶台就是堵吃食;堵吃食,就是堵人命,把人家的活路连根子都堵死了。
这还了得!
这家最年长的人是一个老头儿,跳起来,跺脚大骂,冲起的雪渣与口水溅得四飞。我们吓得跑了。
没下雪时,有娃娃们就向这家倒扣的瓷盆烟囱里扔石子,叮叮当当作响,好听得很,大家都没听过。有一个小名叫牛娃子的,一次石子扔大了,他想听更大的更好的声音。石子从瓷盆砸进烟囱,飞了一截,突破靠近铁锅上沿的烟囱壁,径直砸进铁锅里。一口不知用了几辈人的大铁锅,让一个娃娃一块石子给毁了。
老头儿从灶屋出来,撒腿就追,可哪跑得过一个娃娃。娃娃跑得就像一股强劲的烟,一会儿就没了影儿了。娃娃们都是过眼云烟啊,一个愣怔就长大了。
老头骂了一回娘,算了。
几年后,我初中毕业那年,听说老头儿没了。那年夏天出奇的大旱,从没断过炊的屋场,有那么几户,一天冒三次烟的,只冒一到两次了。老头儿家的破瓷盆,一天顶多冒一次烟。
没粮了,断炊了。他吃多了红薯叶,喂猪的青红薯叶在肚子里持续发酵。一个老人,胀得不行了,几天后去世了。
当年我有没有堵过他家烟囱,有没有让他家的烟因一个孩子少冒一次,我始终充满着负罪感。
他在那头,有一个气派的烟囱吗?是破瓷盆的,还是高高的水泥基座的?
或粗或细,或高或矮,或屋顶,或屋旁,就让我家的烟囱为他再冒一次烟吧。
可他,终归已不食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