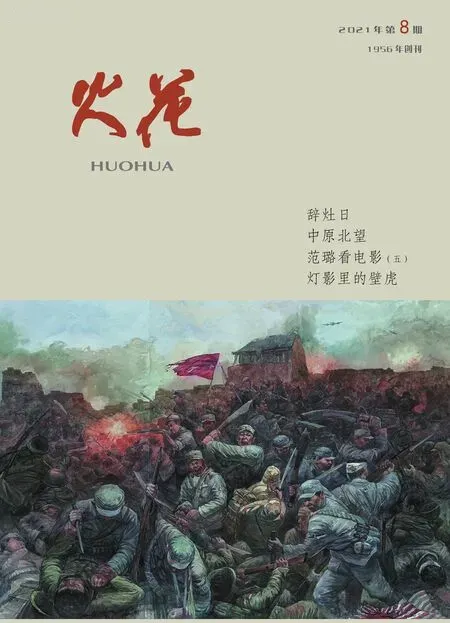万千悲喜,终归一梦
——《红楼梦》的悲剧美学
柯晴雯
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一首《作者题绝》这样叙说作者的一片无人能解的“痴心”:“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是这样一场大梦,在梦醒与入梦间沉醉徘徊,无法辨明究竟何为真实,何为梦幻。《太虚幻境楹联》如此道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情是梦,是假,似真;富贵荣华如过眼云烟,待曲终人散,酒尽狼藉,才惊觉人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悲剧。
《红楼梦》的悲剧或许是一早就注定的,从文字埋下的线索,可以牵引出一场巨大而彻底的崩溃。判词暗示的结局,聚时诗社作的诗句体现的人物性格与命运,待回头望时无一不深显它悲剧的内里。黛玉“玉带林中挂”,宝钗“金簪雪里埋”,元春“虎兕相逢大梦归”,迎春“一载赴黄粱”,探春“千里东风一梦遥”,惜春“独卧青灯古佛旁”,湘云“湘江水逝楚云飞”……在这场巨大的家族溃散的浩劫中,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于世事之外。每个人都被裹挟至这个洪流之中,在花落满地之时成为流水中随波而行的浮花,落到脏泥水沟中,在昔日繁华、美好、洁净的花期之后,也只剩臭乱与萧条。
王国维曾写过一篇《<红楼梦>评论》,指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是彻头彻尾之悲剧。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悲在欲望之不可解脱。“而解脱之道,在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那些自杀的人如金钏、司棋、尤三姐,皆非解脱之人。“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他们的解脱,或是“观他人之苦痛”,或是“觉自己之苦痛”。他们的痛苦不是常人的痛苦,他们的悲剧是出于一种清醒的认识、一种觉醒、一种哲学化的思考,而非仅仅局限于自我的阅历,个人的经验。而解脱的三人中,惜春与紫鹃的解脱,可以看作是超自然的、宗教的、平和的,而宝玉的解脱更偏向于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文学的、悲感的、壮美的,宝玉是实实在在见识到了人类世界中的“大悲”“大幻”。
宝玉的悲剧,在于他认识到了所有人的悲剧。他亲历了晴雯死前的时光,经历了黛玉死亡的悲痛,失去了一众曾经要好的姐姐妹妹,看到了各人离散的结局。家族败落、繁华散尽,而曾经那么好的、“干净”的“女儿们”,却都没有一个好的归宿。他的悲,正在于他用情对待他人,却无法挽回他人的命运;在于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无法左右自己的婚事。不自由的人是悲剧的,而内心纯净者目睹他人之不自由时,油然生起了同情、悲悯、却无能为力之时,是最悲剧的,也是最令人无法释怀的。
宝玉的悲剧或许还在于他“有欲望”。原有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被弃的一块石头,是女娲补天之时炼成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中唯独多出来的那一块,自经锻炼后灵性已通,却自怨自艾。听一僧一道说起人间的温柔富贵乡,便心生向往,也想下凡体验一番,遂化作宝玉出生时口中衔着的通灵宝玉。虽说宝玉是神瑛侍者下凡化身而成,但通灵宝玉或也可以成为宝玉的一个象征。他由石头变成,那石头向往人间,是因为他有“欲念”,有“欲望”。石头因为自己没有被用到而自怨自艾,石头向往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都体现了他被欲念所钳制的事实,一切恶、妒、恨、悔,皆是由欲望而生,可以说,欲望实在是一切悲剧开始的根源。
叔本华这样说人生的悲剧:“无论是从效果巨大的方面看,或者从写作的困难这方面看,悲剧都算作文艺的最高峰。”人的悲剧来自于痛苦,而痛苦实生于欲望。“一切生命,在其本质上皆为痛苦。”人的一切欲望的根源在于需要和缺乏,而人生,皆消耗殆尽于欲望与达到欲望这两者之间。痛苦最初的形式是缺乏,人们成功消灭了这种形式的痛苦,旋即又会有多种多样其它形式的痛苦席卷而来。最后,当痛苦再也找不到其它形式后,就以烦恼和无聊的方式向人们袭来,人们于是又要千万百计消除空虚和无聊。人生,即抛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
顽石来到人间,化作通灵宝玉,源于欲望无法被满足。而来到人间后的悲剧,叔本华将其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恶人“肇祸”,二是盲目的命运、偶然和错误,三是“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同时还不能说单是哪一方不对”。这第三种悲剧是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他们为这种地位所迫,互为对方制造灾祸。
《红楼梦》的悲剧正在于这第三种悲剧,同样,这也是宝玉的悲剧。“金玉良缘”的结局,是王夫人、王熙凤、贾母站在她们的立场做出的选择,并非宝玉的选择。而“木石前盟”中的黛玉,与其他几人的关系又不可简单而论,失去父母的庇佑,在自我的话语权上始终缺少力量的支持。黛玉的立场,始终不是王夫人的立场,由于各人立场的不同,各人都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关系脉络,为自己考量,最终也就造成了结果的冲突,也因此事与愿违。这是宝玉、黛玉的牺牲,同时也是宝钗的埋藏,实属人生的一大悲剧。
面对人生的悲剧,面对世界的虚空,宝玉的解脱方式是出家。其实他的性格本身即有出世的因素。在宝玉听曲文悟禅机的情节中,他几乎已经接近了遁隐的边缘。《寄生草》一曲,唱词为“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心有所感,写下偈子:“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这首偈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你认为你领悟了,我认为我领悟了,但只有通过内心的意会交融,才能真正达到领悟的地步。等到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领悟的程度,才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彻底的觉悟了。达到了彻底觉悟的地步,也就是没有什么再需要证验的时候,才算是进入了思想的最高境界。
看破红尘如《好了歌》,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悲剧的美。悲剧之“看破”,或许正是美的摇篮,从中孕育的“空”“无”,是一种洞晓的美,理智美,清醒美。《好了歌》如此唱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那些追求功名、金银、娇妻、儿孙的人,渴望长生富贵,渴望有朝一日变成神仙,永远留住这繁华快乐。人都是希望享乐的,可人生之乐哪能长久?执着于乐不肯松手的人,终究会在大厦倾倒,万事转头成空的那一刻,体会到更为彻底的悲哀,轰轰烈烈,无法化解,不可排遣,再难收场。
宝玉选择了“出家”,选择了“大地白茫茫真干净”,他转身走入白茫茫天地的孤绝背影,暗藏着多少人间的爱与恨,多少的心事,多少的不可得。可是那都有什么用呢?你吃再好的佳肴,穿再好的丝绸织衣,用再好的器皿,哪一样是能够永存的呢?哪一样你能够长久带在身边,保证它不会离你而去呢?所以宝玉选择了放下执着,放下欲念,放下“得之心”,那么也就不再惧怕“失之心”,辛酸可以化解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天地这时竟能生出一种超脱的美。
悲剧有如此大的魅力,如此深的美感,不是因为悲剧教会了人什么,使人懂得了什么。教化是一种冰冷的东西,而真正美的是情。是真情使得悲剧如此柔软,柔软得能够容下流不尽的眼泪;也是真情使得人在痛彻心扉后有了力量,有了能够支撑人继续活着的坚硬外壳。柔软与坚硬之间,有生命的美。
黛玉的《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深味人间之悲凉。“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侬今葬花人不知,他年葬侬知是谁?”黛玉的发问是有力量的,是美的,因为她将自己所有的情感、整个的生命都融入到了诗词之中,每一个字都是她真心实意的呐喊,是她痛苦的宣言,拯救的希望。这是如此的美,美到把人的精神整个地收归,用以对抗人生的悲剧。
《红楼梦》是一场大梦,梦幻是美,荒诞是美,虚无也是美。人在美中照见了自我灵魂的厚度,实现了自己意志的升华,这是真正的自由。如痴如醉,万物虚空,万千悲喜,终归一梦。“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悲剧是美的,因为悲剧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美的。哪管什么空啊,痴啊,美永远在最真诚干净的情感之中,永远发光,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