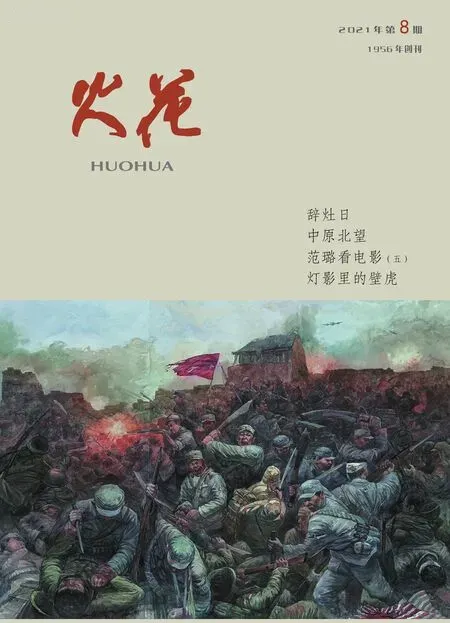灯影里的壁虎
徐玉向
多年之后,当我已为人父时才发现,自己如同一只壁虎,永远走不出父亲和母亲的那片灯影。
一
天刚擦黑,母亲已张罗起晚饭了。家中唯一的煤油灯被母亲安置到灶台最上一格。待天全暗了下来母亲才从灶膛里取出豆秸点着灯。朦胧的水蒸汽从热着馒头的锅上升起,慢慢包裹着灶台上微弱的灯光,母亲的身影在这片光线中忽然高大起来。
母亲吆喝我们把饭菜端进堂屋,她一手把着煤油灯一手端着碗筷引在前头。灯放定,人落坐,晚饭开始。饭后母亲举灯独自回灶台收拾。
我在院外直玩到一身大汗才肯循着窗下暖暖的昏黄的灯光跨进家门。堂屋门没有闩,月光跟我挤进一片黝黑所在。西头屋透出一抹淡淡的亮光,我伸头一瞅,母亲正坐在床边纳鞋底。她左手握着鞋底,右手上的锥子向鞋底上扎个眼后顺势把针从针眼处穿过去,反手一扯线接着再用锥子扎了下去。母亲见我进屋连眼都没抬一下,就这样一针一针地纳着鞋底,她要在入冬之前给家里每人都添置一双新棉鞋。父亲伏在写字台上,正给淮南的大姑妈回信。被窝里,弟弟已经睡熟。
写字台上靠床的一侧,煤油灯的火苗忽闪忽闪地跳动着,时而向上伸出一截,时而向左右两侧扭转。据说这盏灯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之一,原有个挡风用的玻璃罩,早不知去向,就连调节灯芯的旋钮也被一片中间用钉子打了孔的圆铁片代替,灯芯仅有半拃长荡在灯肚子的煤油上。整个煤油灯恐怕只有圆鼓鼓的灯肚子是原件了吧。
母亲见我洗完脚上了床,就把手中家什搁在床头的箩筐里,伸头吹灭了煤油灯。夜像一个幽灵悄悄走来,零星缥缈的狗叫声伴着我们一家人沉沉睡去。
二
在故乡,我们称壁虎为歇虎子,许是因它动作太慢,有事无事便挂在墙上,从不主动出击,直到猎物送到嘴边才会伸伸头。在农村,人们天生对生性懒惰的物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轻视,我也总以为歇虎子是对这种生物的蔑称。
儿时,每逢夏日的晚饭时,煤油灯总把父亲的背影无限放大,并高高投在山墙上,从堂屋门口向里看,他的背影仿佛就是一面墙。石灰抹的山墙总会脱落几处,仿佛老年人脸上斑点一般,无论你用雪花膏怎么抹,岁月的痕迹总也抹不掉。在这或明或暗的山墙上,歇虎子总是如约而至。于是,常常在我吃晚饭时,耳朵里灌进的是父亲的谆谆教诲,而眼睛里早从案桌咸菜盘上生生挪到了山墙上。那里,正在上演着一幕幕生死存亡的大戏,主角无一例外都是歇虎子。
一只蛾子被玻璃灯罩阻在灯外,于是,它停在山墙上喘口气。然而,它却没有发现半尺之外的歇虎子。歇虎子看到从天而落的美食,却一动不动,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势。
少顷,歇虎子确认自己没有暴露后,轻轻地抽动四肢交替着前行,悄悄逼近了蛾子。在朦胧的灯影下,我分明瞅见它乌溜溜的眼睛里闪起一丝光亮。蛾子并没有意识到危险降临,翅膀有一下没一下地扇动着。它在距蛾子一拃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微微摆下头,全身保持到蛾子刚落在山墙上的姿态。
就在我无比纳闷的时候,歇虎子飞扑了过去,一口咬定蛾子的头颅。蛾子仅仅翅膀急剧扇动几下便不再动了。它微微仰起头,从容地将蛾子吞入腹中。之后,扭动着腰肢向另一个方向爬去,然而,它始终在灯影里打着转。
我盯着歇虎子小巧的身躯,狠狠咬了口馍,却发现父亲收回马上点到我额上的筷子。忽闪忽闪的煤油灯,将父亲的背影装扮得更加神秘。
三
父亲一直用部队的作风来教育我,他从部队带回的三件纪念品就成了教育我的法宝。我的童年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军用皮带。
冬天出去玩时,小孩们总须裹着厚厚的棉衣,而我的腰间必定会被系上一条军用皮带,既压风又保暖,更可得意洋洋地从村东头慢慢踱到村西头,任凭小伙伴们投来羡慕和嫉妒的目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孩子们非常崇拜解放军,以得到部队用过的物品为荣,如军帽、五角星、军用皮带、红领章甚至绿色军装等。谁若能得到一样,便可在抓特务游戏时当一回解放军和好人。
待开春甩掉棉袄,父亲一手提着称粮食的大秤,秤钩上必是军用皮带拦腰套着的小孩儿,另一只手仔细地拨拉着秤砣。他双眼盯紧了秤星,歪着头嘀咕着,似自言自语又似跟母亲讲话,“四十八,过个年才重三斤!这饭吃得不照闲啊!”我们吊在秤上,笑嘻嘻地转着圈,直到双脚踩实地面,又一窝蜂跑到锅屋翻馍吃。
伯伯家的院墙拐角有一个蜂窝,一大群黄蜂每日飞进飞出。每次经过总觉不顺眼,尤其是只能远远地瞅着蜂窝边上熟透了的无花果。耐不住几个堂哥的撺掇,我决定为民除害。围巾裹了头脸,一只长竹竿便是我的武器,猫着腰悄悄过去,看准蜂窝连捅数下。黄蜂嗡嗡盘旋而起,我丢下竹竿就往村子外面跑。一气跑到村西再回头时,黄蜂早没了踪影,抹了把汗,我加入了去野外烧豆子的队伍里。
傍晚赶回家时发现院子里站了一群人,陆陆续续还有小孩的啼哭声。奶奶正用家里的七叶一枝花给一个小孩涂擦,他的脑门上有几块包,耳垂肿得快赶上菩萨了。原来我捅了蜂窝后,黄蜂没捉到我,也不肯进巢,在附近乱窜,路过的小孩却遭了大罪。当天晚上,可怜的我与父亲的军用皮带又见面了。
读小学时,父亲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三大步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他的基本教材,就连我写作业时也要把腰挺直。我的外套大多是绿色,大多是几个哥哥的旧物。一年冬天气温很低,母亲翻出一顶火车头的棉帽,父亲把身边存着的唯一一颗红五星别在了帽子上。清晨我戴着棉帽踏着积雪上学时,正遇到学校西面当公安的张叔叔披着军大衣走出家门,他竟然望着我笑了起来。站在门口的张家婶婶笑着说:“你看,他比你还要醒目呢!”放学回来我跟父亲说了,他也默默地笑了起来。
十六岁那年我外出读书,父亲特意抽空教我打背包。父亲说打背包是他在新兵连时学的技能,我马上要住校过集体生活了,以后还要参加工作,学好打背包对于培养我的纪律观念和生活作风会有很大的帮助,凡事不能丢了他这个老兵的脸面。
我一听来了劲,不就是打背包吗?电视里见得多了。从抽屉里取出父亲珍藏的背包带,向扫净的水泥地上扔一床被子,我便当着父亲的面鼓捣起来。
盯着绑得像粽子一样的被子,父亲直摇头。他利索地解开背包带,将被子捋平后对折再对折,然后用双手向边角一抹就完成了叠被子。素日早晨醒来时常被扭成麻花一样的棉被,在父亲的手中竟然呈现出不亚于电视里看到的“豆腐块”。
“打背包有两种办法,都要求背包的面上是三横压两竖。”父亲一边解说一边将细背包带拉直平放在被子上,而另一条宽背包带则被夹在了被子中间。一翻双手,被子旋转调了一个面,他在靠近没有开口的一侧打了一个结,再用力一拉。背包带抽紧后接连让被子再翻两个跟头,背包正面出现了“三横一竖”。最后一次旋转被子后用背包带穿过三横,呈现出了“三横压两竖”的效果。背包带在侧面打了个结,把多出来的带子塞进了被子。待被子和背包带的褶皱抚平,他拉出了夹在被子中间的宽背包带。穿过背包两端,宽背包带的两头打了个结,形成两个背带。父亲站直身子拎着背带向我面前一扔:“看清了吗?”
说实话,父亲在打背包时,我看得眼花缭乱。他放慢动作演示了两遍之后才开始让我练习。直到我能熟练地独立打背包,父亲才将两根打包带盘成圆饼状郑重递到我手里。
四
待我们匆匆赶到秧母地,老皮塘周边的几块田里有人担了满满两筐正往外面走,更多的人则弯着腰在拔秧苗。
乌云仿佛就罩在大片的葱绿的田野之上,风在大雨倾泻之后悄悄离开了,只留下空气中的漫天水汽。雨点停了一会儿又止不住往下落,只是雨丝越来越细。轻轻的雨点落进浑浊的秧母地,连一个小小水花也没有溅起。周身碧翠的秧苗盈盈立着,一株挨着一株,叶片挽着叶片。此时,它们仿佛不知自己即将告别这片温床,依然在雨丝中轻轻摆动。
劳动的人呢,有的人披着短雨衣,顶着一面旧草帽。有的人仅在身上绑了个塑料袋,从顶上掏了洞钻出头来,拦腰扎根细绳子。他们大都把裤子卷到膝盖下面,露出捂得有些白的小腿。很少有穿胶鞋,秧母地的水齐着小腿,很容易灌进短筒雨鞋,齐着膝盖的深筒雨靴一般人家很少用。拔秧的人除了向新来的熟人简单打个招呼之外,全都如比赛一般埋头干活。整个老皮塘下面,除了沙沙的雨声,便是田间沟渠里积水急呼呼地向下奔跑的喘息声。池塘中,一只花皮青蛙的叫声凭空就能传得很远。倘在素日,没有雨,人们少不得会将底部绑着木板的四脚凳子垫在屁股底下,一边不紧不慢地拔着秧,一边与隔壁田里的人叙话。
我跟着家人跳进微微带着凉意的秧母地,学着他们的样子拔起秧苗。拔秧苗其实也是有技巧的,手直接插到秧的根部,用力往身子方向一掰即提起,这样就不会伤到根须。待拔够一把时,用几根稻草束成一捆,在手中荡一下根上的泥,再随手向埂上一丢。父亲隔了一会儿就到埂上,用两个柳条筐担着几十捆秧苗走向大秧田。
五
每年秋末冬初,村子里就开始腌辣菜。老家的腌辣菜做法与别处略有不同,辣菜的主材以雪里蕻为上,其它青菜次之。
常去菜地割上一捆,或是逢集兑来几十斤,偶有推着架车来村里卖的,几家人便合伙包了车。青菜弄回来后就在各家院子里先除去死叶、黄叶和被虫子啃过的,菜刀剁去菜根。家里有井的就用大木盆或水桶端来清水,把收拾好的菜一颗颗清洗。没井的只好多跑几趟东塘和大井沿了。
经过最后的洗礼,青菜摊在凉床上,有的挂在晾衣绳上,一排细线串着青色沿着院子各个角落延伸开去。没了根,远离大地的滋养,它们的精神已大不如以前,一颗颗耷拉着脑袋缩小了身躯。干爽的西风呼啸着带走它们茎叶底下最后的一丝湿润。偶尔路过的喜鹊停下来瞅两眼又拍拍翅膀飞远了,房檐下的麻雀却是连正眼都不会瞧一下。
菜刀再次亮出它们的獠牙,它们的眼睛只盯着大个子的青菜,小块头的直接忽略。也有懒惰的做法,连码刀的环节也省了,直接把青菜摁进了大木盆里。
粗犷的海盐被细细敲成均匀的颗粒,阳光下一个个闪着狡黠的光亮。在一双双粗糙有力的大手反复地揉搓下,海盐渐渐失去身影,原本膨胀着的青菜仿佛没有筋骨的面团,软搭搭地偎依成一团。在它们的身子底下漫溢出一丝丝墨绿色的盐水混合物。
腌辣菜的最后一步就是装缸。浸过盐的青菜一条一条一层一层从缸底往上码,最上面必定压上块石头。这石头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多是从河滩或山边找到,大小方圆不拘,但一定要有份量。老人们也常说腌菜缸里的石头是块宝,有的人家用了几十年。装缸之后缸口会再压上一顶木锅盖,有的也用塑料布封口。
村里人在腌辣菜时常会往青菜里埋上几捧青辣椒。每次腌好的辣椒总会抢了腌辣菜的风头,成了餐桌上待客的稀罕之物。
六
伴着“啪”的一声脆响,蒜薹应声而断。我捏着薹苞下面的左手顺势一提,一根新鲜的蒜薹便被抽出了蒜苗。
刚剥离母体的蒜薹,周身色彩呈渐变色,薹苞与蒜苗包裹的薹茎部分是鹅黄色,底端泛着白,伸向空中的薹茎则是青色。蒜薹被抽出的刹那,我鼻子里钻进一股甜中带辛的清新气味。
来不及细品,我再度弯下腰,左手揪住另一根蒜薹,右手里的家伙顺着蒜薹往下滑去。裹着蒜薹的蒜茎被工具剖开,直至跟部两三寸的地方。这种工具非常简陋,就是一尺长的竹片,宽约两指,前端用火烫出一个铲状的凹槽,中间缠上一根粗铁丝,粗铁丝的一端事先被锤子锤平,磨出尖儿,呈锋利的刀刃状,再固定到凹槽中间。当工具顺着蒜薹下滑时,铁丝前端的刀刃便很轻松地剖开蒜茎。
抽蒜薹的最后一步,就是用铁丝前端的刀刃轻轻旋转,抵着蒜薹往前一送,蒜薹便断了。被抽了薹的蒜苗立刻瘫软下来,仿佛周身没了力气,原本挺拔的身体与尖子已发黄的蒜叶一起,软软地搭在泥土上。
儿时的记忆里,母亲每年都会带着我们在北塘底下点一大块蒜。春天,母亲把蒜地里的一大半蒜苗分批拿到集市卖,另一半则留下长蒜薹。也许是因为长得慢,亦或是被蒜苗培养得久些,集市上蒜薹的价格总高过蒜苗刚出街的时候。
但凡长出蒜薹的蒜,它埋在泥土里的蒜头也在慢慢膨胀。直到抽去蒜薹之后,蒜头才会慢慢成熟。这时,残存在地面的蒜苗会彻底枯萎,变成一抷败叶,回归大地。
母亲一早背着大蒜苗去东站的集市了,锅里已煮好早饭。中午放学回来,我们发现堂屋桌子上放着一袋小笼包,而母亲正在厨房忙碌着。
刚揭开塑料袋,一股诱人的香气直钻进鼻子里。一个个小笼包子如一个个白嫩嫩的胖娃娃挤挤挨挨地抱在一起,每一个仅有婴儿拳头般大,还冒着热气,挺着圆鼓鼓的肚皮,顶上微微翘起的部分是一圈花纹。每一个小笼包子都似一个有表情的小生命,直勾勾地盯着你,让你想下手却又难以张口。
小笼包对于乡下孩子来说是个稀罕物,偶然去集市上见到却未必能吃到。记得上次吃小笼包子是半年前了,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组织的比赛得了奖,家里用一笼包子作奖励。那可是整整一笼包子,吃得我满嘴是油,忍着口水,我数了一下,刚好六个。一笼包子是八个才对呀,弟弟不信,数了一遍也是六个。昨天晚上我们早已入睡,母亲还在堂屋点着灯收拾一捆捆大蒜苗。今天一早去集市时母亲一定没来得及吃早饭。从家到集市要翻过一座小山,约三四里,但要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赶路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通常要挨到蒜苗全部出手,母亲才会去买笼包子给我们打牙祭。小小的一笼包子,母亲仅仅吃了两个就全部带回家来。
就在我们分小笼包子的时候,在厨房做好午饭的母亲走了过来:“少吃两个,一会儿吃中饭了。”我们快速各吞下两个,剩下的放进篾篮里。
整个下午我都惦记着猪肉大葱馅的小笼包子。放学到家我们打开篾篮却发现剩下的小笼包子不翼而飞。母亲不紧不慢地向灶里填着柴禾,一边笑着说被老鼠偷走了。开饭时那两个包子竟然奇怪地出现在盘子里,原来母亲怕包子太冷,我们吃了会闹肚子,就与馍一起加热了。
时隔多年,我早已离开了农村,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地。每逢抽蒜薹的季节我就会想,蒜苗之于蒜薹,乃至蒜头,与人间母子的际遇是多么相似啊。试想,又有哪一位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越自己呢?在有限的生存资源里,她们每每面临着种种艰难抉择,最终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孩子能活得更好。
七
父亲喝酒时很惬意,一定要细细地斟,一口一口地喝,慢悠悠地夹菜,时光如窗棂上垂下的蜘蛛丝,被扯得又细又长。在温情的阳光下,一切仿佛都闪着光亮。
每当父亲喝酒,我和弟弟便可分吃下酒菜。有时取过他喝过的杯子用鼻子猛地一吸,一股辛辣之气直冲脑门,浑身不由一个激灵。再看一眼父亲,他的眼睛已眯了起来,是因为我们的表现,还是酒,这倒成了我们回忆时的一个不解之迷。
父亲好酒,但量不大,每日两顿,每顿两三盅,天天如此。酒算不得佳酿,两三块钱一瓶,每次去大队部边上的老小店买酒,夏家奶奶老远就把一瓶濉溪大曲搁在柜台上了。我以为他是自祖父去世后才开始喝酒,那年我六岁,弟弟四岁,他自己却说在村委当会计时就开始喝酒了,那时大概只有十八九岁,高中刚毕业。
印象中,父亲有一次喝醉了。当时外面下着雨,同他一个单位外号叫瘦子的表叔载他进了院子。耷拉着脑袋披着雨衣的父亲坐在车后座上,待被扶上床不久,便开始回酒,再之后便沉沉睡去。
舅舅是个嗜酒的人,不但喝得勤,且量大。每次去外祖母家他就嚷着“让小外甥来陪酒”。于是,我便有机会人模狗样地端起斟满的酒杯喝起来,喝完第一口就已满脸通红,忙着往嘴里夹菜。待我勉强将第一杯透底时,五六杯酒早已落到他的肚中了。他边夹着菜边笑着说:“小外甥真行,快赶上我了。”当我喝完第二杯时眼皮已重似千斤,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转动。我不知道是如何到的床上,迷糊中只听见舅母大声喝斥他的声音。
我发现,父亲在喝酒时眼里闪着光,舅舅在喝酒时眼里也闪着光,当他们从桌上端起酒杯的刹那,这光便钻进了我的眼睛。
多年之后,当我能稳稳当当地端起一杯酒时,我已远离故乡,去千里之外的南方闯荡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