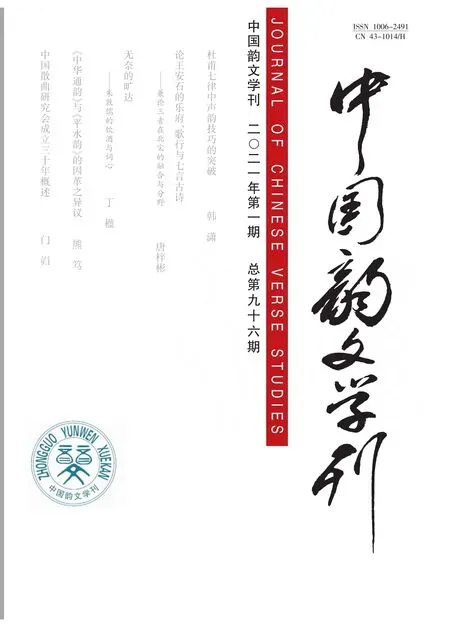陆游《钗头凤》本事及若干意象再辨析
高利华,丁雨秋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关于《钗头凤》的本事,最早见于宋人刘克庄《后村诗话》、陈鹄《耆旧续闻》和周密《齐东野语》三家笔记。三家大致具言陆游与唐氏伉俪情深,由于母亲的压力不得已与唐氏仳离,各自嫁娶,后二人相遇于绍兴沈园,陆游遂于沈园题壁,作《钗头凤》。时至清代,吴骞《拜经楼诗话》、王渔洋《带经堂诗话》、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均对宋人笔记所载的《钗头凤》本事提出质疑,但并未深究。20世纪50年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在为陆游词编年时,曾推断《钗头凤》作于乾道九年至淳熙五年(1173—1178)之间,是陆游寓居成都期间的冶游之作,与唐氏无涉。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钗头凤》本事问题的研究,词作中的红酥手、宫墙柳、东风恶等意象也成为讨论的焦点。本文拟从陆游诗词文本、《钗头凤》词调的来源、流行路径进行新证,就《钗头凤》本事以及诸意象问题,略陈己见。
一 《钗头凤》词本事再辨析
《钗头凤》本事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该词是何时、何地、为何人而作,对此目前大约有四种说法:一、绍兴年间,沈园题壁,为唐氏而作;二、乾道淳熙年间,蜀中冶游的赠妓之作;三、蜀中,为小妾杨氏而写;四、乾道八年,南郑,为唐氏而作。
宋代的笔记小说有“野史”之称,或可补正史之缺。宋人三家笔记是探究《钗头凤》本事绕不开的文献材料。刘克庄《后村诗话》言:“旧读此诗,不解其意,后见曾温伯,言其详。”曾黯,字温伯,是陆游老师曾几的曾孙,也是陆游的学生,陆游有《赠曾温伯邢德允》《除宝谟阁待制举曾黯自代状》等作品传世。作为学生的曾黯绝不会去附会一段子虚乌有的往事强加给自己敬重的老师,因此曾黯所说基本可信。曾黯与刘克庄曾有交往,刘克庄在《跋放翁〈与曾原伯帖〉》中记录了向曾黯几番索帖的往事,并赞其“人物高雅,词翰精丽,有晋唐风韵”。二人既有往来,那么曾黯为刘克庄一解放翁《沈园》二首背后故事也就合情合理。退一步讲,除非确有其事,否则刘克庄不可能在书中指名道姓、信誓旦旦地说“曾温伯言其详”。由此,《后村诗话》这一段记载可谓实录,大家的认可度高。陆、唐二人仳离后又在沈园相遇确有其事。
陆游曾于沈园题词也是事实,这在陆游的许多诗歌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如“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故人零落今何在?空吊颓垣墨数行”(《禹祠》),“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城南》),“绍兴年上曾题壁,观者多疑是古人”(《禹寺》)。晚年定居三山的陆游常常跑到城南一带,去凭吊、缅怀他逝去的爱人和爱情。而那一首曾经题写在沈园墙壁上的“小阕”就是一曲爱情的悼歌,是他一生情感伤痛的症结所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陆游的沈园诗总要喋喋不休地提起那坏壁颓垣上的“墨数行”。
既然沈园相遇和沈园题壁都是既定事实,那么问题就转变为那一首沈园题壁的“小阕”是否就是《钗头凤》?
《耆旧续闻》和《齐东野语》都提到《钗头凤》就是题壁沈园的“小阕”。《耆旧续闻》作者陈鹄其人,据学者考证,大约生活在1140—1225年,或更晚一些,他与陆游的兄长陆淞相熟,对陆氏兄弟都比较熟悉。据《耆旧续闻》所载,陈鹄曾亲眼看到过题壁沈园的《钗头凤》,不仅时间、地点、词作内容、唐氏和词残句都非常明确,而且连题词的“笔势飘逸”之态这样的细节都提到了,若非亲眼所见恐不至此。或以为《耆旧续闻》“系抄撮而成者,故所谓余者,不知是何人?”笔者认为,纵然这一段记载非陈鹄自述,而是录他人之文,那么在抄录的源头,必然有一个“余”存在,这个“余”曾目睹过书于沈园、笔势飘逸的《钗头凤》。此外,《耆旧续闻》所记的题壁时间与陆游自述高度吻合。陆游本人在宋光宗绍熙壬子年(1192)秋天,曾游沈氏园,作《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据此向前倒推40年,是1152年,与《耆旧续闻》所记的“辛未”(1151)仅差一年,这一年可能是由于月份或算法上的差异造成的。
《齐东野语》所记《钗头凤》的题壁时间是“绍兴乙亥岁”(1155),比《耆旧续闻》所记晚了四年。两家笔记在时间上的抵牾成为后来许多人质疑甚至反驳《钗头凤》本事真实性的重要依据之一。然而,《齐东野语》比《耆旧续闻》晚出,作者周密(1232—1298)与陆游生活的时代相去约百年,所记题词时间有误差也是情理之中。亲见亲闻也好,传抄杂录也好,《耆旧续闻》和《齐东野语》在题壁时间上的不同记载恰好说明他们的信息材料是来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出处,两个不同的出处都不约而同地表明《钗头凤》就是沈园题壁词,其实正是反证了《钗头凤》即沈园题壁词这一论断的真实性。
在三家笔记的记载中,关于陆游、唐氏仳离的原因、沈园相遇的具体细节等的描述上不尽一致,甚至相去甚远,但三家所记的本事大意是一致的。陆、唐仳离的原因、沈园相遇的细节等都是个人隐私,除了当事人,谁也无法明确知晓。三家笔记的作者(即使陈鹄、刘克庄都与陆游有间接的联系)毕竟都不是当事人,他们在听闻故事之后再将其转化为文字时,在故事整体脉络不变的基础上,难免带入一些主观性甚至是创造性的描述,尤其是《齐东野语》的叙述,颇具传奇色彩。
此外,陆游曾在严州删诗定稿,但于词,并无删削一说。他在淳熙十六年(1189)作《长短句序》曰:“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可见陆游虽对年少所作之词非常后悔,但并没有对其进行删削,而是编为一集,以识其过。从陆游晚年沈园诗中表现出的对唐氏的悼念与深情,以及诗中多次提及壁间“小阕”来看,这“小阕”他一直记在心里,是记了一辈子的,因此他在编词集时是绝对不可能忘记或者漏收沈园题壁词的。从现存词稿看,沈园题壁词非《钗头凤》莫属。从《钗头凤》词调的来源、流行路径看,应该写于绍兴。
二 《钗头凤》词调的来源、流行路径
《钗头凤》,本名《撷芳词》,又名《摘红英》《玉珑璁》《惜分钗》《折红英》《清商怨》等,“钗头凤”一名取自无名氏词“可怜孤似钗头凤”一句。关于词调,《花草粹编》卷六引宋杨湜《古今词话》:“政和间,京师妓之姥曾嫁伶官,常入内教舞,传禁中《撷芳词》以教其妓,人皆爱其声,又爱其词,类唐人所作也。张尚书帅成都,蜀中传此词,竞唱之。却于前段下添‘忆忆忆’三字,后段下添‘得得得’”三字,又名《摘红英》。其所添字又皆鄙俚,岂传之者误耶?《撷芳词》之名非擅为之,盖禁中有撷芳园、擅景园也。”张尚书即张焘,政和八年进士,因上书反对议和,得罪秦桧,于绍兴十年(1140)以宝文阁学士出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在蜀四年,绍兴十三年(1143)乞祠归,卧家十余年,直到秦桧死后才再次出仕。据此可知,《撷芳词》本是由皇宫内苑传出经歌妓演唱而流行于民间的曲调,张焘帅成都之后,此调在蜀中盛行开来,并且体式、名称都有所变化,用这种蜀中新调来作词的,有程垓、无名氏、曾觌等。
程垓是眉山人,其词名《折红英》:
桃花暖。杨花乱。可怜朱户春强半。长记忆。探芳日。笑凭郎肩,殢红偎碧。惜惜惜。 春宵短。离肠断。泪痕长向东风满。凭青翼。问消息。花谢春归,几时来得。忆忆忆。
无名氏词名《玉珑璁》:
城南路。桥南路。玉钩帘卷香横雾。新相识。旧相识。浅颦低拍,嫩红轻碧。惜惜惜。 刘郎去。阮郎来。为云为雨朝还暮。心相忆。空相忆。露荷心性,柳花踪迹。得得得。
曾觌(1109—1180)是宋孝宗的宠臣,根据《宋史》记载,曾觌不曾到过蜀地,其词名《清商怨》:
华灯闹。银蟾照。万家罗幕香风透。金尊侧。花颜色。醉里人人,向人情极。惜惜惜。 春寒峭。腰肢小。鬓云斜亸蛾儿袅。清宵寂。香闺隔。好梦难寻,雨踪云迹。忆忆忆。
在三叠字的蜀中新体之外,还有一种与之相似的二叠字体式存在,吕渭老的《惜分钗》词二首都是二叠字体式的:
春将半。莺声乱。柳丝拂马花迎面。小堂风。暮楼锺。草色连云,暝色连空。重重。 秋千畔。何人见。宝钗斜照春妆浅。酒霞红。与谁同。试问别来,近日情悰。忡忡。
重帘挂。微灯下。背兰同说春风话。月盈楼。泪盈眸。觑著红裀,无计迟留。休休。 莺花谢。春残也。等闲泣损香罗帕。见无由。恨难收。梦短屏深,清夜悠悠。悠悠。
与程垓、无名氏词中的三叠字结句相比,吕渭老《惜分钗》的上下阕末都是以二叠字为结句的,显然这是一种比蜀中新体更为简单、初始的状态。吕渭老,字圣求,浙江嘉兴人,有《圣求词》一卷,赵师屷《吕圣求词序》云:“当宣和末,有吕圣求者,以诗名……归老于家云。”吕渭老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宣和年间,经历过“靖康之难”,是典型的南渡词人,晚年在故乡嘉兴渡过。
根据词体演进由简单到繁复的一般规律以及吕渭老的大致生活年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吕渭老的《惜分钗》二首创作时间要早于程垓、无名氏等人的蜀中新体。也就是说,《撷芳词》最早是由浙江嘉兴人吕渭老改造,在原词调的上下阕末尾加二叠字。而张焘在帅成都之前,曾除文林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提举台州崇道观等职,任职范围均未出浙江一带,“张尚书帅成都,蜀中传此词,竞唱之”,显然《撷芳词》在蜀中的流行与张焘有密切关联。据此我们不妨大胆推测,《撷芳词》由吕渭老改造后在浙江一带流传,后由张焘带入蜀中,该曲调进入蜀地之后在吕渭老的基础上又被进行了第二次改造,由二叠字变成了三叠字,三叠字的新体从此在蜀中广为流传。这种三叠字的新体很可能在张焘离开成都时被带回浙江一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宋孝宗的宠臣曾觌不曾涉足蜀地,却也依着蜀中新体作有《清商怨》一首。
绍兴十三年(1143),张焘离蜀还家,三叠字的《撷芳词》传入浙江一带应当是本年前后的事情。大约七八年以后,陆游与唐氏相逢于沈园,陆游按此曲调题词壁间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上,《钗头凤》就是陆游与唐氏仳离后相逢于沈园时的题壁之作。
三 “红酥手”“宫墙柳”“东风”诸意象的内涵
围绕《钗头凤》本事,词中的“红酥手”“宫墙柳”“东风”三个意象的内涵也成了探讨的焦点。
目前关于“红酥手”的解释大致有三种:一、红润白嫩的手;二、红酥指唐宋时期妇女们制作的一种果品兼工艺品,陆游所谓“红酥手”乃是赞许唐琬有一双点制红酥的巧手;三、食品红烧猪脚。
笔者以“红酥”为关键词检索《全唐诗》和《全宋词》,得到结果如下:
(唐)两楼相换珠帘额,中尉明朝设内家。一样金盘五千面,红酥点出牡丹花。
(王建《宫词一百首》)
(唐)春冰消尽碧波湖,漾影残霞似有无。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
(元稹《杂忆五首》)
(唐)莺锦蝉罗撒麝脐,狻猊轻喷瑞烟迷。红酥点得香山小,卷上珠帘日未西。
(和凝《宫词百首》)
(宋)恰则小庵贪睡著。不知风撼梅花落。一点儿春吹去却。香约略。黄蜂犹抱红酥萼。 绕遍寒枝添索寞。却穿竹径随孤鹤。守定微官真个错。从今莫。从今莫负云山约。
(毛滂《渔家傲》)
(宋)红酥肯放琼苞碎。探着南枝开遍未。不知蕴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 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
(李清照《玉楼春》)
(宋)推愁何计,车下忘乘坠。日上南枝春有意,已讶红酥如缀。 儿童缓整余杯,芒鞋午夜重来。素面应憎月冷,真香不逐风回。
(李弥逊《清平乐》)
(宋)十月小春天。红叶红花半雨烟。点滴红酥真耐冷,争先。夺取梅魂斗雪妍。 坐待晓莺迁。织女机头蜀锦川。枝上绿毛幺凤子,飞仙。乞与双双作被眠。
(李石《南乡子》)
(宋)一番飞次春风巧,细看工夫。点缀红酥。此际多应别处无。 玉人不与花为主,辜负芳菲。香透帘帏。谁向钗头插一枝。
(王炎《采桑子》)
(宋)香摇穗碧。梅巧红酥滴。云涴宝钗蝉坠翼。娇小争禁酒力。 绣窗芳思迟迟。无端又敛双眉。贪把兰亭学字,一冬忘了弹棋。
(石正伦《清平乐》)
(宋)谁染深红酥缀来。意浓含笑美颜开。误认浣溪人饮罢,上香腮。辨杏疑桃称好句,名园色异占多才。折得一枝斜插鬓,坠金钗。
(无名氏《添字浣溪沙》)
由此可知,在唐代,王建、和凝诗中的“红酥”都是指点酥工艺,元稹诗中的“红酥”是形容女子红润的面庞。在宋词中,基本上都是用“红酥”来喻花的。以此为基础可以帮助我们辨析“红酥手”的确切含义。
在诗词中,用“红酥”来形容女子的面容是有先例可循的,然未见以“红酥”喻手。所谓的“酥”,是从牛、羊等乳汁中提炼出来的精华,为细腻的莹白色。这种白酥若加入红色染料,就成为“红酥”,用白酥和红酥制作食品,相关的技艺,称为“点酥”。点酥工艺在唐诗宋词中常常被提及,如“暖金盘里点酥山”(和凝《宫词百首》),“天应乞与点酥娘”(苏轼《定风波》),“手点酥山,玉筋人争莹”(王安石《蝶恋花》)。陆游本人也在《月上海棠》(斜阳废苑朱门闭)写道:“淡淡宫梅,也依然、点酥剪水。”因此,以“红酥手”来赞女子手巧、点酥做得好是合乎情理的。此外,类似“红酥手”一类的词,即“技艺或本事+手”这样结构的词语,我们在宋词中可以找到很多,比如丹青手、调羹手、擎天手、补天手、平戎手、丝簧手、匀妆手等等。
《钗头凤》中的“红酥手”其实是指唐氏那双点酥技艺高超的巧手,并非“艳笔”。至于将“红酥手”解释为红烧猪蹄的,实在不符合唐诗宋词的雅致特征,也与词作的意境、情感等格格不入。将“红酥手”解释为红润白嫩的手,虽不如点酥的巧手来得确切,也是符合词意的。陆游晚年所作沈园诗在怀念唐氏时称其是“惊鸿”“玉骨”“美人”,唐氏早已香消玉殒几十年,但是她最美的模样永远定格在了陆游的记忆中。既然唐氏是这样一个冰清玉洁、青春美丽的女神形象,那么她的手自然也是非常美丽的。综上,笔者更倾向于将“红酥手”解释为一双又美又巧的手。
“宫墙柳”的解释有以下五种:一、故蜀燕王宫,即五代时蜀王孟知祥燕宫;二、古越国宫墙的遗址;三、庙宇之墙(沈园旁有禹迹寺);四、禹迹寺西南有唐浙东节度使董昌所建的“第四宫”;五、“宫墙柳”是喻体,指唐氏;六、指龙瑞宫(道观)。
第一种说法由吴熊和先生在《陆游〈钗头凤〉词本事质疑》一文中提出,吴先生以“凤州三出:手、柳、酒”的俗谚与“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相对应,认为《钗头凤》作于成都,词中的“宫墙”就是陆游在成都时经常宴游的故蜀燕王宫,燕宫多柳,故曰“宫墙柳”。按此说,“宫墙柳”是实写,由此推论“红酥手”和“黄縢酒”也应当是实写。凤州在陕西省的西南部,与燕王宫所在的成都相隔千里,身在蜀地的陆游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想到凤州三出,还将其写入词中。若说是凤州“三出”同时在燕王宫、在陆游面前出现,未免太过巧合。
至于第二种说法,古越国的宫殿宫墙已不复存在,陆游题词时不可能莫名其妙地思绪遥接到千年前的古越国。况“宫墙柳”是一个整体,墙若不存,柳又何依?第三、第六种说法可归为一类,将道观、庙宇之墙称为“宫墙”的,除了杜甫的“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塔劫宫墙壮丽敌,香厨松道清凉俱”(《岳麓道林二寺行》)两句,其他诗词中都找不到相同的表述。且在诗词中,当“宫墙”和“柳”这两个意象同时出现的时候,“宫墙”一般指的是宫殿之墙,如“日映宫墙柳色寒”(张祜《长门怨》),“迟日犹寒柳开早。……千条万条覆宫墙”(刘商《柳条歌送客》),“御沟柳,占春多。半出宫墙婀娜”(毛文锡《柳含烟》)。因此将《钗头凤》中的“宫墙”视为禹迹寺或者龙瑞宫之墙,并不合适。
第五种说法言“宫墙柳”喻唐氏。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韩翃的《章台柳》。纵观这些以柳喻美人的诗词,往往显得轻浮艳丽,描写对象一般是歌女、妓女,将唐氏比作“柳”是对她的贬低与亵渎,以陆游对唐氏的深情,是绝不可能将其比作“宫墙柳”的。
第四种说法与词意环境比较符合。明代的徐渭在寓居禹迹寺内的“一枝堂”时自撰堂联曰:“宫墙在望居三卜,天地为林鸟一枝。”禹迹寺西南有唐浙东节度使董昌所建的“第四宫”,“宫墙在望”说明“第四宫”至明犹存,并且从禹迹寺可以望见其宫墙,那么南宋时期的陆游自然也能从沈园望见宫墙。
人们在诠释“宫墙柳”时,都将其当作陆游题词时的实景,因此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在寻找题词地附近的宫墙,以便与词中的“宫墙”相互印证。其实词的上阕包括“宫墙柳”在内的所有描写都是虚写。从“春如旧”可以看出,词中其实隐含着一个今与昔的对比,上阕是对往昔的追述,下阕是对如今的描摹。“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这三句当是陆游对唐氏以及与唐氏曾经一起做过的事情(如采菊作枕囊等)的整体概述。然而,强劲的东风突然吹来,吹醒了沉浸在美好春天里的有情人,吹散了彼此相爱的夫妇二人。一对爱侣被强行分开,带着相思离愁,一别就是好多年。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钗头凤》的上阕带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它是陆游对往事的一种整体性的描绘。没必要找出与之相对应实体。
关于“东风”恶的解释有以下四种:一,姑恶,指陆游母亲;二,指封建礼教;三,指王氏;四,“恶”在此句中是表示事物程度的“甚辞”。
对于第一种解释,笔者以为颇荒谬。对于陆游这样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可能去公然指责母亲“恶”。“姑恶”恐怕是我们后人出于对有情人不能眷属、唐氏香消玉殒的陆唐爱情悲剧的无限同情和惋惜所做出的解释。至于陆游的十几首姑恶诗,都是退居山阴所作。民间传说姑恶鸟是一个被婆婆虐待至死的媳妇所化的怨鸟,所以叫起来总是“姑恶姑恶”。陆游关注姑恶鸟这个意象是与其居住的自然环境有关,山阴是南方水镇,是姑恶鸟喜欢出没的地方,目之所见,下笔成诗,姑恶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诗歌中。陆游笔下的姑恶鸟有的只是田园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是借鸟之哀鸣抒发内心的不平,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许多人以此诗作为“东风恶”是陆游暗喻陆母恶的证据。但是陆游作此诗时陆母早已故去多年,普天下绝没有儿子会一直记恨已故的母亲,还要不依不饶地作诗加以指责。因此此诗应当是对民间姑恶鸟传说的一种感慨,我们不必对它作太多牵强附会的解说。
如何去对待已往历史以及以往历史中的人和事?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出:“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第二种说法很显然是站在了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我们现代社会所谓之万恶的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都是当时社会合情合理合法的存在,是包括陆游在内所有人从小耳濡目染并且内化为一种价值观的东西,在他们眼中,婚姻就是这个样子的、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一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生活,终身受其教化、熏陶的人是绝不可能去质疑社会制度、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的。
按照上文《钗头凤》为沈园题壁词的结论,第三种解释已然是个伪命题。或以为“东风恶”是陆游责怪妻子王氏拆散他与杨氏,这是一种缺少前提的推测。
第四种说法是目前最为妥当的一种解释。“恶”是程度副词,表示东风很强劲,这在诗词中是很常见的说法,如“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周邦彦《瑞鹤仙》)、“酒恶时拈花蕊嗅”(李煜《浣溪沙》),同时还与下片的“桃花落”形成一种因果的联系。进一步深究,这股强劲的东风也是命运之风,它说来就来了,吹落了繁花,吹散了爱侣,喻指的是人生的无常、命运的不可捉摸。
综上所述,《钗头凤》确是陆游与唐氏相遇于沈园所作,陆游正是借由题壁沈园的这一小阕追忆了少年时与唐氏相依相伴的甜蜜时光,诉说了世事无常、恩爱夫妻劳燕分飞的伤痛往事,记录了昔日爱侣再相见却咫尺天涯的无奈场景,也道尽了他一世的眷恋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