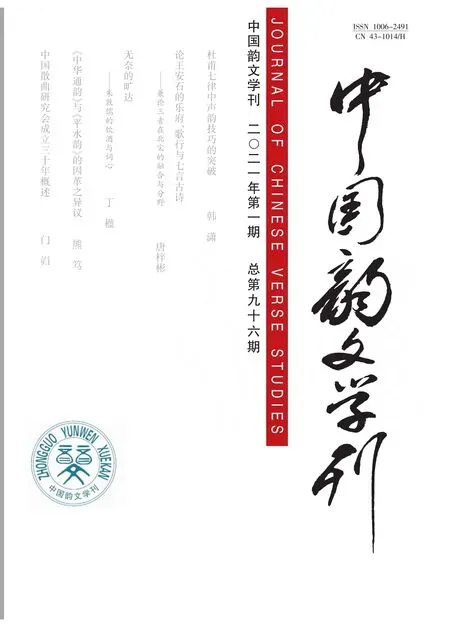杜甫七律中声韵技巧的突破
韩 潇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
对声律的严格要求是七言律诗的重要特点,这使得诗人们在创作中受到很大的限制:平仄和粘对规则,使得音节的排列不能够随心所欲地纵横起伏;平声押韵且不能换韵,也使得平仄交替用韵、随着内容变化而自由转韵等前代诗人常用的声韵技巧失去了用武之地。被明代诗论家视为“正宗”的初盛唐七律,在风格上和平浑厚、壮丽高华,甚至有时过于单调、缺乏变化,都与严格的声律规范有着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严苛的限制往往能催生高超的技巧,杜甫在七律中对声韵技巧的运用正是如此。
对于杜甫七律中的声韵技巧,前人已有一定的研究,但几乎都集中在拗体这一个方面。先有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将杜甫“好作拗体”列为“诸家所无”的特点之一,而后更有诸多学者集中探讨杜甫拗体七律的成就:江裕斌的《试论杜甫对诗歌意象结构与音律的开拓与创新》指出杜甫在七律中通过打破格律,实现情感内容与音律形式的和谐一致;孟昭诠的《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试论杜甫的七律拗体》则提到杜甫以不合律的“拗调”写有悖常理的“拗情”;刘占召在《“以古为律”与杜甫七律艺术的革新》一文中论及杜甫在声律上的“古调入律”及其对律诗的变革;王硕筌的《论“子美七言以古入律”——杜诗拗格试析》则进一步细致分析了杜甫七律中拗句的形式及其在声韵、结构层面所起到的作用。以上诸家都认识到了声韵技巧对于杜甫律诗情感表达效果和风格特点的影响,但他们都将视野局限在拗体之中,没有能够全面反映杜甫在七律中运用声韵技巧所达成的成就。
也有学者关注到了杜甫七律在拗体以外的声韵技巧,如郭绍虞的《关于七言律诗的音节问题兼论杜律的拗体》指出,“律诗的律到杜甫而细,他能在仄声中再严上去入之分,又能在平仄律中再参以双声叠韵之美,所以‘细’到极点”,但文中接着提到“可是律诗之拗也到杜甫而极,别人只做到变格,他则创为拗体,这才是他的不可及处”,还说“律细见杜诗工处,破律更见杜诗奇处。这种拗体比正格更难做”,可见他仍然认为杜甫七律运用声韵技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拗体。
对上述强调杜甫拗体七律成就的观点,叶嘉莹持相反的见解,她在《杜甫七言律诗演进的几个阶段》中说道:“这种成就,虽然避免了七律之缺点,做到了完全脱出于严格的束缚之外的地步,但另一面却也失去了七律之长处,而未能保持其形式上之精美,因此杜甫在拗律一方面之成就,终不及其在正格的七律一方面之成就的更可重视。”这一认识为更客观地评价杜甫七律声韵技巧成就开辟了道路。
美国学者高友工、梅祖麟在《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实践》一文中,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秋兴八首》的语言艺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文中指出,“杜甫驾驭音型的能力是非常杰出的,他能通过改变音型密度以加快或放慢语言的节奏。在有限的范围内,音型的密集或不同音型之间的强烈对比,会使诗的内部出现分化”,同时结合具体文本,揭示了杜甫对音型特质的灵活掌握和巧妙运用,对深入研究杜甫七律的声韵技巧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所谓的音型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声音与情感之间的关系。语言是音与义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并非随意的。章太炎在《语言的缘起》中说:“语言者,不凭虚起……诸言语皆有根,先征之有型之物,则可睹矣。”并举例说明了不同声音要素对于事物本身有描摹、象征的功用。黄侃也说:“太古人类本无语言,最初不过以呼号感叹之声表喜怒哀乐之情,由是而达于物。于是见水之流也,则以杳杳、泄泄之声表之;见树之动也,则以萧萧、索索之音表之。”同样解释了特定的语音形式与相关物态、情感之间的联系。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丁邦新、向新阳、申小龙、周世箴、竺家宁、朱晓农等语言学者,对不同声韵要素的语音形象进行了相对细致的分析,为更进一步分析诗歌声韵技巧奠定了语言学基础。
对于声韵与情感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朱光潜在《诗论》第六章中说道:“声音与情绪的关系是很原始普遍的”,“作者的情绪直接流露于声音节奏,听者依适应与模仿的原则接受这个声音节奏,任其浸润蔓延于身心全部,于是依部分联想全体的原则,唤起那种节奏所常伴的情绪”。更进一步揭示了音义关系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原理。
在前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固然杜甫的拗律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但杜甫对声韵技巧的掌握和运用并不局限于此。能把握汉语语音的象征性功能,运用不同语音形式与特定情感的对应关系,在七律中巧妙地调动声韵要素,以增强意境与情感表达效果,才是杜甫在七律中发挥声韵技巧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这也使他不必打破七律的格律,同样能自由地表情达意,做到情感内容与音律形式和谐一致。
二
杜甫在七律中对于声韵要素的调动和布置,主要体现在押韵、双声叠韵、叠音词等方面,其他音韵要素的排布有时也能体现出他的独到用心,这些技巧在杜甫之前的诗人诗作中已经普遍有所运用,但能够结合语音要素的象征功能,在声音、韵律的和谐之外,追求表情达意效果的强化,并广泛运用在七律之中,则是杜诗所特有。
1.押韵。
韵是音韵要素中最为明显的特性,对于诗歌节奏的形成、意境的营造和情感表达效果的强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杜甫在用韵上的讲求是细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的,比如在韵的区分上更加细化。
在《切韵》音系中,“支”“脂”“之”被分为三个韵部,但事实上,自唐代起“脂”“之”二韵已经同用,到了开元二十年左右修成的《唐韵》中则“支”“脂”“之”三部同用。这样的语音变化也反映在盛唐诗人作品的押韵中,高适、王维、崔兴宗、岑参现存的七律中,均为三部同用;李颀、李白虽无押“支”“脂”韵的七律,但他们现存的五律中,也是“支”“脂”韵同用。而杜甫作为开元后期步入文坛的诗人,其所处的语言环境与余人无异,亦无方言语音影响,而他于“支”“脂”二韵却绝不同用,体现了在押韵中更细致的追求。进一步分析杜甫押“支”“脂”二韵的作品:押“支”韵的两首(《紫宸殿退朝口号》《秋兴八首·其八》)皆表达有相对乐观积极的情感,反之押“脂”韵的七首作品中,则有六首(《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秋兴八首·其四》《咏怀古迹五首·其二》《立春》《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其二》《晓发公安》)明确表达出悲观失意的情绪。不难看出,杜甫对韵部功能选择的独到用心。
杜甫在七律中利用独特的用韵技巧增强情感表达效果,其主要表现为:利用韵的音响特性与适当的情感搭配,营造出更为浑然的诗境; 在诗篇内部,利用韵字的开合、等呼等要素的变化与思想情感脉络相配合,形成明暗两条线索,增强诗歌的韵律感和张力; 在联章组诗中运用情韵的配合,显示出篇章之间情感、意境的连贯性与变化趋势,使得组诗整体意境和谐,且局部情感更加鲜明。以上结论,我在《论杜甫律诗中情感表达效果与用韵技巧之关系》一文中已做了详细论述,可供参考。
2.双声叠韵。
双声叠韵同样是诗歌中常见的声韵技巧,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双声叠韵,大抵皆口中状物之词,及用之于诗,则口舌相调,声律有不期其然而然者。”其中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双声叠韵应用于增强诗歌表达效果的原理在于语音的象征功能,二是早期双声叠韵的使用是无意识的自然天籁,即“不期其然”的。
对双声叠韵技巧有意识的的应用始于齐梁,不但王融、萧衍、庾信等诗人写作了一批“双声诗”“叠韵诗”,进行了实践层面的尝试,《文心雕龙》《四声指归》《文镜秘府论》等理论著作也集中对双声叠韵的技巧有所探讨。至初唐,上官仪更是明确提出了“双声对”“叠韵对”的理论,对唐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总的来说,前代诗人对双声叠韵的探索和运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杜甫在七律中使用双声叠韵具有先导和启发作用。
但不同的是,前代诗人运用双声叠韵主要是追求音韵的和谐,如刘勰在《声律》篇中探讨“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是对永明声病说中“傍钮”“小韵”二病的阐释;上官仪“六对”“八对”中的双声叠韵同样是为了追求形式技巧和声辞之美;李重华也说,“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串联,取其宛转”,强调语音和韵律上的呼应。而杜甫则在声韵回环之美的同时,还尤其注重发挥双声叠韵的象征意义,以增强其诗歌意境和情感表达效果。
杜甫早期的七律仍然沿袭前人对双声叠韵用法,多注重其在音韵和谐方面的效果。如《赠田九判官梁丘》一诗中,连用“崆峒”“降王”“苜蓿”“嫖姚”四个叠韵词和“争长”“见招”“麾下”三个双声词,语如连珠,以达到骋才干谒的目的;《紫宸殿退朝口号》一诗颈联,“昼漏希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中,“昼漏”“天颜”“近臣”叠韵,“高阁”双声,四个词语句间相对,句中各自又对,工整精丽,体现了杜甫在盛唐体七律创作中达到的水准。
到了杜甫后期的七律中,双声叠韵的使用则更加注重其在意境营造方面的效果,既借助声母韵母本身的象征意义描摹物态情感,还能够在对仗中形成反差,使得双声叠韵的作用尤为突出。
如贬官华州途中写作的《望岳》,首联写“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上句“崚嶒”阳声叠韵,以较大的共鸣强化华山的巍峨之感,下句“罗立”则为“来”母双声,以其流转的特点状出群山相对低矮连绵的样貌,双声叠韵相对,使得华山与诸峰的对比更为鲜明,强化了西岳独尊的地位;再如《白帝》一诗,颔联写“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上句“高江”为“见”母双声,其势壮大干脆,与江间波涛翻滚、雷霆万钧的气势相合,下句“古木”合口上去声叠韵,听感细弱低回,更能表现出山峡林中幽凄昏沉的景象;又如出峡后作的《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之芳》,颔联写“大水渺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云升”,上句“渺茫”为“明”母双声,正状出水天相接,一片苍茫浑融的境界,下句“硉兀”为入声叠韵,与山峰参差交错、暑气喷薄的画面又正好贴合。诸如此类,在七律中运用双声叠韵的象征作用,以听感的对比强化情感的反差,极大地强化了诗歌的意境,体现了杜甫对双声叠韵功能的开拓。
同时,杜甫在七律中使用双声叠韵的方法也是极为灵活的,不像前人一样,拘泥于中间二联自然音步之间的对仗,而能够做到“或二句中,或四句中,参差多寡,其变不一”,这就更加扩大了双声叠韵技巧的应用范围。
杜甫一方面借助律诗中属对严密、章法变换的特点,安排多层次的双声叠韵对仗,实现多重复杂的对比效果。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颔联中“怅望”与“萧条”叠韵相对,均为响度较大的元音,但分别用去声和介音进行听感上的削弱,从而形成沉响的特质,共同强化抚今追昔的历史沧桑感;“千秋”双声对“异代”叠韵,前者为擦音声母,后者为细弱元音,均表现凄苦衰朽之感,而本组与前组相对,又强化了诗人面对历史兴亡只能徒增伤感的无奈之情,进一步增强了诗歌表达的张力。颈联之中,“江山”叠韵,既与下句“云雨”双声相对,反差出境界的大小之别,又与当句“故宅”双声相对,烘托出盛衰变化之意;尾联以“明”母双声的“泯灭”统摄前篇,抒发出强烈的历史虚无感。本篇堪称杜甫七律中运用双声叠韵技巧强化意境的典范。
另一方面,杜甫在一些作品中打破双声叠韵属对的传统,通过声母韵母的集群效应强化意境和情感的表达。如《白帝城最高楼》中“城尖径昃旌旆愁”一句,通过集中使用擦音声母,借助其尖利的听感,营造出白帝城楼高耸崎岖的意境;再如《阁夜》中写到“五更鼓角声悲壮”,同样通过集中出现的爆破音模拟鼓声,点染峡中长夜的悲壮气氛。
3.叠音词。
叠音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特殊的双声叠韵,也是诗歌中重要的声韵技巧。在《诗经》、“古诗十九首”等早期诗歌中,叠音词已经十分常见,它们往往能够本乎天籁地表达出特定的声情效用,使得诗歌形象生动、音韵悠长。但在近体诗中,叠音词起初是不被提倡的,如胡震亨说:“律诗忌犯叠音字,固也。”胡应麟也说:“第叠字最难。”方回在品评徐俯律诗时更是直言:“师川诗多爱句中叠字,十首八九如此,可憎可厌。”可见叠音词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破坏律诗凝练的语言风格,影响表达效果。在杜甫之前的七律中,叠音词的运用的确成就不高。大多数诗人在作品中使用的“年年”“处处”等词,往往只起到填充音节的作用,对于意境的营造和表达的强化没有太多效用;也有一些作品,虽然努力以叠音词描摹物态,但却失于凡俗或牵强。
而杜甫对叠音词的使用则远胜于初盛唐诗人,这是历代诗评家所公认的,仇兆鳌称其“声谐意恰,句句带仙灵之气,真不可及矣”,并举出了大量例证。如“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一联中,“泛泛”“飞飞”同为唇齿叠音词,都模拟出轻盈的样貌,但不同的是,前者以鼻音收尾,写出了渔舟在波涛中周流荡漾之感,而燕子在长空中自由翩跹的姿态则配合短促的音节更加形象。再如“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云石荧荧高叶曙,风江飒飒乱帆秋”等,皆与物态相合,见其匠心独运,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4.其他声音要素。
除了押韵和双声叠韵,诗句中其他位置象征性音韵要素的排布也能够影响到诗歌的意境营造和情感表达效果。
比如上声的使用就别有心意,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上声属于升调,适于表现亲密的情感倾向。古人已对此有所认识,如释处忠《元和韵谱》中说:“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前文也提到郭绍虞评价杜甫“能在仄声中再严上去入之分”。但在律诗中,因为押韵限用平声,上声的作用只能在其他位置加以凸显。在杜甫的七律中,在每联的上句末尾中使用上声,常常能增进情感的表达效果,如《客至》一诗:
用染色序列对P进行着色,实际上是对m(2n+1)+2n-1条边进行着色,而图4中色集合的个数有个,根据上述染色算法,当k是奇数时,有当k是偶数时,有因此恒成立,此时求得最小的整数k满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在这首表现宾主相得,村居生活其乐融融的田园欢歌里,四联上句之中,有三句以上声结尾,首句“舍南舍北皆春水”表现自己与自然的亲密,三句“花径不曾缘客扫”则凸显对来客的热情欢迎,七句“肯与邻翁相对饮”更是以问句的形式进一步拉近彼此关系,显得亲切备至,三个上声句尾都很好地起到了表现亲密情感的作用。
再如《又呈吴郎》颔联“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体现了对贫妇人的急切关怀,以及对吴郎的殷切嘱托;另外如《江村》末句“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言语之间流露出与故人亲密无间的友情,上句有版本作“多病所须唯药物”,读之则亲切之感失其大半。
除了上声之外,声母、韵母的象征效果也往往在串联中形成特殊的韵律,从而发挥特定的效用。有时通过声母的听感特点形成节奏的舒促变化,如《阁夜》中写“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上句以集中的爆破音营造出国家动荡的氛围,下句则归于平缓,表现诗人身处边地的无奈之感;有时又能通过韵母的抑扬开合配合境界大小的转换,如《黄草》一诗中“万里秋风吹锦水,谁家别泪湿罗衣”,上句多开口一三等字和阳声韵字,营造出秋风萧瑟之感,下句则多细微的三四等字,表现漂泊凄苦的情绪;有时甚至还能够以韵律的连缀弥补诗境跳跃带来的割裂感,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将这一联中所有字的韵母排列下来,分别是“阳皓觉鱼耕麌缉,陌模齐皓送唐支”,在图中观察音响效果的变化,则正好呈现出一条“由大转小继而变大”的和谐曲线,与此联诗境中所描绘的“香稻众而鹦鹉少,碧梧低而凤凰高”的物态特征、视野转换以及感知顺序是一致的,故而能够以听觉的和谐贴合情感意象的发展脉络,串联起诗境变化的线索,从而减弱因语法倒置而造成的意义曲折。
综上所述,杜甫对音韵要素的象征功能有着远超前人的深刻认识,并在七律中对声韵技巧加以灵活的运用,通过押韵、双声叠韵和其他音韵要素的排布营造意境、强化情感,这也是他能够在不打破格律的前提下,利用律诗讲求声韵的特点,开拓七律新境界,扩大其表现力的重要基础。
三
七律发展至杜甫在风格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胡震亨评价“少陵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其中“篇制多”与“诗料无所不入”是就杜甫对七律题材风格的开拓而言。的确,七律的篇制、风格、面貌自杜甫之后而蔚为大观,这意味着七律在杜甫手中真正走向了成熟,而在这一进程中,声韵技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充分认识汉语语音象征性功能的基础上,巧妙运用声韵技巧,通过听觉的感官传递增强所表现事物的形象性,更贴切地营造独特诗境以表达出细腻的思想情感,正所谓“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这种声情相谐的境界是中国古典诗歌所一直追求和提倡的。在早期诗歌中,人们往往能够自然吟咏出这样的歌诗。然而随着文学和声律的自觉,尤其是近体诗创制的初期,诗人们却陷入了“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的困境,这一方面是因为严整声律规范限制了情感的自由表达,另一方面也与语音发展过程中其象征意义变得曲折模糊有一定关系。而在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探索之后,诗歌终于还是迈上了“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的新高度。
就七律这一体裁来说,在盛唐诗人手中,已经能够充分利用其诗歌声调平和优雅、悠扬流畅的特点,恰到好处地表现或清新雅致,或高华壮丽的诗歌境界,其中,频频有声韵技巧的妙用上演点睛之笔。如崔颢《黄鹤楼》诗,以极强的音乐性和整体感,将情绪都融化进自然悠扬的吟唱之中,营造出周流婉转、深远绵长的境界;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以昂扬的声调和韵律,将境界扩大到了极致,十分贴合朝会的盛大威仪和诗人的得意情绪;又如张说《氵邕湖山寺》借助叠韵词,形象地表现出山林的寂静清空之境和鸟鸣的玄远回环之声,突出了氵邕湖山寺超凡脱俗的清雅意境;王昌龄《万岁楼》连用五个平声阳声字,极状境界之远,又以明母叠音词作收束,强化乡关之思。
相比于盛唐诗人在七律中运用声韵技巧取得的成就,杜甫有着进一步的突破。他能够运用和调动不同风格的声音要素,极为细致精到地描摹各种物态,赋予描绘的景物对象以主观人格化的精神,最大程度地发挥诗中每一个字的表现力度。
他在七律中使用声韵技巧的频率远超前人,同时在风格上营造出更为广阔丰富的诗歌境界。前文中已提到杜诗的清新雅致者,如《江村》《客至》,壮丽高华者,如《紫宸殿退朝口号》等,足以说明杜甫在盛唐七律已有风格中取得的卓越成就;而《望岳》《白帝城最高楼》之奇崛险拗,《阁夜》之雄浑悲壮,《黄草》《咏怀古迹五首·其二》之萧瑟凄紧,又体现出杜甫在七律风格上的开创。
而杜甫七律的风格仍不仅于此,还有沉郁悲凉的作品,如《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诗歌押“侵”韵,是平声韵中的闭口韵,最为含蓄细微,适宜表现忧伤的情绪。首联之中,“万方多难”的壮烈愁情,与“此登临”的卑微身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在音韵上也是开合变化,掷地有声,上声的“此”字曲尽其意地表达出了苍茫天地间诗人只身漂泊的孤独感;颔联境界开阔,而又在句尾以上声和闭口韵尾加以收束,使其不破坏整体诗境;颈联上句“终不改”写朝廷不可变易,既有上声带来的亲切之感,又可见出牙喉音所蕴含的恳切与坚决,下句“莫相侵”则以细微的听感,流露出诗人内心对于寇盗入侵的悲叹与无奈,将所思所感具象为人格化的倾诉对象,使情感流露更为真切,而在前后对比中,更见出其伤心的根源在于信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这便是通过声韵反映出来的言外之意。
再如《燕子来舟中作》,首联先写在潇湘舟中再度见到春燕飞来,感慨漂泊生活又经过一年;接下来则写到“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前半句“识主”用轻微的入声和上声,营造出亲切的语气,配以一个鼻音的“尝”字,在亲切之中造出疏离之感,而后半句“看人”则鼻音叠用,本为疏远之意,再加上一个“远”字,更凸显其无情之态,加深了作者孤单悲凉情绪的表达;颈联“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中,“处处”二字虽下得平常,却以去声表现出屡次迁居的沉重足迹,相对而言,平声的“飘飘”则加剧了漂泊之路的漫长和悠远,既细致刻画出了燕子的生活姿态,更写尽了自身的辛酸历程。
其昂扬奔放者,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用“阳”韵,听感十分响亮,自然铺垫出欢乐激越的情绪。首句仄声居多,以顿挫的节奏营造出捷报初闻时惊愕、振奋的心情,而下句则多三四等字,听感的削弱暗示着情绪的内转,作者集中以个人的心情绾结家国豪情;颔联中“却看”二字“溪”母双声,短促有力的节奏写出妻子愁绪的骤然消散,而“漫卷”阳声叠韵,则烘托出狂喜之情的长久;颈联承接狂喜的情绪,从放纵的喜乐,转入对回乡路程的思索,“好还乡”三字双声皆带有回环的语气,引出后文;尾联的路程更见杜甫在音韵要素排布上的功力,上半句为峡中行程,密集的塞音和入声字营造出重重关山阻隔的环境,而擦音从中穿插则表现出破除障碍的坚定决心,下句为出峡后的路途,连用六个平和流转的声母,写出对悠然回乡之路的期许,杰出的声韵技巧俨然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山水图卷。
其平白质实者,如《示獠奴阿段》:
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
郡人入夜争馀沥,竖子寻源独不闻。
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
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首联之中,“苍苍”以强大的共鸣状出境界之广大,擦音声母又描绘出树木萧森的景象,“袅袅”则因其介音的影响而显得细弱,符合水流的样态,鼻音声母则增强了水流连绵不尽的意味;颔联上句多爆破音和入声字,激烈的音感与人们争夺水流的喧闹之态相呼应,下句则全为细微的字音,写出阿段独自探寻水源的轻幽身影;颈联上句多牙喉音,表现出士人病中对饮水的迫切渴望,下句在鼻音之间插入两个塞音,既写出了水流乍来的惊喜,也渲染出了得到水流后的滋润之感。声感与情感的高度贴合,使得这首诗读之令人感同身受。
还有急切激愤者,如《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其颔联写“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先用集中错杂的入声模拟毒蝎杂乱众多的样貌,又以鼻音和平声的连绵模拟出其声音的连续纷扰,将读者带入了早秋苦热的环境之中;颈联则写到“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上句三仄尾,顿挫之间表现出内心愁绪的深切,下句先以四个急促的音节写出文案到来的频繁,又以连续的三个平声强调出其源源不断的态势,一个鲜活的急躁的诗人形象就这样展现在了读者眼前。虽然这首诗的整体格调不高,但却代表了杜甫在特定诗歌风格上的开拓,也体现了其运用声韵技巧的出色水准。
通过以上作品,不难看出,杜甫不但发展了盛唐杰出的七律诗人巧用声韵要素,贴切地描摹物态、营造诗歌意境的技法,还能够突破他们相对统一的审美情趣,对听感不同、效果各异的声韵象征要素都能够做到灵活运用,使得七律的风格走向多元化。
四
一般认为,杜甫在夔州时期的创作最能代表其七律的最高成就。反映在声韵技巧上亦是如此,尤其像《登高》《秋兴八首》这样公认的佳作,更是在谨严的格律之中,综合运用各种声韵技巧,并配合严密的句法、联法、章法结构,以其精巧的构思,将声韵要素的象征性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反映出杜甫对声韵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以《登高》为例: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杨伦称赞其:“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胡应麟更是将其标举为“古今七律第一”,并肯定了元人对其“一篇之内,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的评价。浦起龙更是称其:“望中所见,意中所触,层层清,字字响。”这里的“奇”“响”应当包含技巧之奇、声韵之响。
全诗押“灰”韵,属于较细微的韵部,适于表达相对细腻含蓄的个人情感。而在韵字的安排上,则很好地体现了与诗歌境界变化相配合的开合转换。首句写天高峡深,秋风疾劲,是一片苍凉开阔的景象,远处传来的猿鸣声将诗境引向更深远处,故而配以开口的韵字“哀”;视野不断延展,见到“渚清沙白”之后,又随着回巢的飞鸟收束回来,则与合口韵字“回”相配,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峡中图景浑然一体。而颔联则以眼前的秋风落木、江水奔流,将诗境再次扩展到无限的高远之处,同时蕴含着世事无情变迁的沧桑之感,承载着宇宙时空的厚重,韵字变为开口的“来”字,悲凉境界随之扩大为悲壮。
颈联是被誉为“十四字之间含八意”的千古名句,由个人的老病漂泊,到国家的衰颓动荡,悲情层层递进、越发凝重,情绪的加深又与前一联中的时空延展遥相呼应,故而“台”字也以开口韵,体现愁思之深切。最后一联,将前文努力铺展开的无边宇宙和无涯愁绪极速收束,聚焦在细微的双鬓、酒杯之中,蕴含着一发千钧的张力,以合口的“杯”字作结,达到了“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的效果。八句之中,五个韵字同在细微的“灰”韵基调上,随着表现内容与情感特点的变易,产生了“开—合—开—开—合”的相应变化,与诗境的大开大合形成了很好的搭配。
在双声叠韵和叠音词的使用方面,声母中对爆破音和牙喉音声母选用独具匠心。一般来说,爆破音(尤以浊声母和不送气清声母为主)的听感相对阻滞、凝重,易于形成顿挫的吟咏节奏,烘托出厚重、沉郁的诗歌境界。《登高》通篇56字之中,有多达32个爆破音,其中24个是浊声母和不送气清声母,且这些字多处在篇中、句中重读的位置(每句第二、四、六字和句尾)上,这就使得全诗在听觉上掷地有声,与诗境中浑融的孤城秋景和厚重的满腹愁情相得益彰。而在具体的排列上,还能配合情感变化形成相应的音韵节奏。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句,愁情最为浓烈,爆破音也最为密集,而且前疏后密,正与层层加深的愁绪形成双线的呼应,将愁情一步步推向顶峰。
相对而言,牙喉音的听感则比较低沉、细微,适合表现低调、苦闷的情绪。首联中的“哀”“回”两个喉音韵字的使用,强化了诗境中哀愁悲伤的色彩,为全诗奠定了韵律和感情基调。结尾处“艰难苦恨”中三个牙喉音字的集中出现,使得诗人心中的苦痛形象化为可感的音节,令读者感同身受,再与上一联集中出现的爆破音相对比,则愁绪之大、苦痛之深与诗人之无奈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声韵上的反差与情感上的冲突再一次产生了契合。
再看叠韵。尾联上句“艰难”分属“删”“寒”邻韵,下句“潦倒”同属“皓”韵,乃叠韵相对,强化了久客之“艰难”与病多之“潦倒”之间的呼应,更贴合多重愁绪交织的整体情感基调。
而叠词“萧萧”和“滚滚”,也能够高度贴合物态,具有强化诗境的功能。“萧萧”为心母字,听感尖锐锋利,正像枝叶枯落之态,与“落木”这样的炼字技巧相配合,强化了萧瑟之感,使得秋林肃杀的景象如在眼前;而“滚滚”则为合口阳声韵字,听感圆转浑厚,像长江奔流之状,句末“来”字为“来”母,更添周旋流转之感,同时也通过鼻音共鸣营造出时空的沧桑感和厚重感。两个叠词处在相对的位置上,尖利与圆浑的听感也在对比中更加鲜明,使得相应的诗境更为突出。
短短七言八句之中,既不打破格律规程,还能巧妙地利用律诗凝练和追求意境的特点,而在声韵技巧方面作出如此文章,被称为“古今七律第一”,当之无愧。
同样,《秋兴八首》在声韵技巧上也极具创造力。在押韵方面,其一的“侵”韵,写尽了秋日峡中的凄紧之感;其三的“微”韵则在宏大的篇章中恰到好处地贴合本首伤叹自身浮沉的细微诗境;其七的“东”韵,更是烘托出了盛世长安铺张秾丽的景况。而八首之间的用韵组合,更是配合着诗境、情感的变化,形成相应的波折、起伏,宛如一篇完整的乐章,不但使总体意境更为浑然,同时也使各单篇的情感、境界表现得更加鲜明。
双声叠韵方面,其一中“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一联,上句用四个送气擦音强化撕裂的听觉效应,模拟出剪裁衣料的迫切之感,下句则以五个不送气爆破音营造出强烈的节奏,极像石杵撞击捣衣砧的声响;其五中“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联,则集中使用零声母和边音声母,营造出宫扇徐徐展开的流动、雍容之态;其七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一联,上句全为细微韵字,营造出“摇荡凄凉机丝徒具之悲”,下句则多响亮的阳声韵字,表现出摇荡不安麟甲欲动之感; 其四中“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一联,“金鼓”双声,且与“振”同为爆破音,像鼓角争鸣之声,“羽书”邻韵,且与“驰”同为细微韵,表现出援兵不至的无力之感,对比之中更凸显出战事的紧急与朝廷的衰朽。诸如此类妙用,以及叠字方面的例证,组诗中还有很多,前文已有所论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由此可见,杜甫对于律诗声韵技巧的探索,可谓细致入微,他在七律中有限的自由空间内,仍然能发挥声韵技巧的功能,充分调动音韵要素的象征作用,从而使得情感内容与音律形式和谐一致。且与拗体律诗不同的是,这些诗篇能够发挥七律自身的体式特点,极大地激活了七律在意境营造和议论抒情方面的优势,提升了七律这一体裁的表现力,并为后世树立了极高的艺术典范。
综上所述,杜甫的七律创作,不仅能在格律之外横放杰出,更能在格律之内腾掷跳跃,借助声音要素的象征意义,运用声韵技巧为表情达意服务。这不是一朝一夕达成的成就,就连杜甫自己也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在杜甫人生各阶段的七律创作中,可以清晰地见出其声韵技巧,从初涉创变追随盛唐诗人“以古入律”的脚步开始初涉创变,进而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开辟出声情相偕、变化万端的诗歌境界,最终臻于化境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