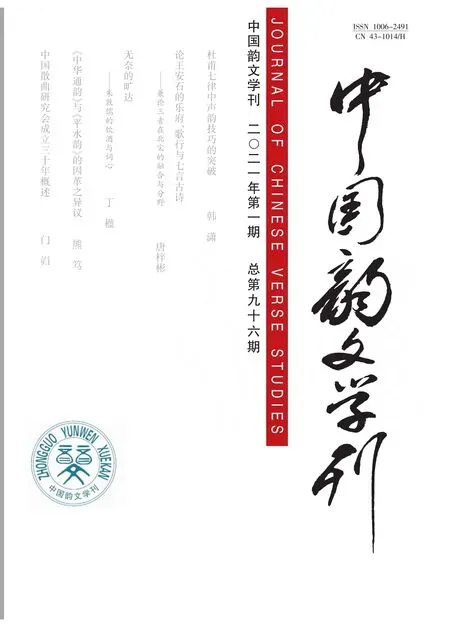刘禹锡刺吴、赐紫、立祠:多维视角下的文官行迹与价值碰撞
余 琳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有唐一代,大批文官在地理空间中的迁徙成为著名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官行迹的移动,不仅改写了唐代文坛的书写面貌,也关涉到唐代政坛深层的权力斗争及价值判断,同时文官行迹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流动与重塑。刘禹锡入吴任苏州刺史便是这一文学、政治、文化综合视域中的典型个案,事件本身如投石入水,澜表方圆,在个人、中央、地方等多个层面均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力,体现出不同角度下的言说形态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价值立场,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着碰撞与对话,具有当下、即时与跨越时空的综合意义。
一 刘禹锡刺吴:以“才”为中心的文官坚守
约在大和五年(831),刘禹锡离开了长安,出使苏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离开京城,此前两次离京,皆因获罪受贬。此次情况与之前有所不同,这是刘禹锡在受朝廷政治斗争排挤之后,主动选择的离京。《旧唐书·刘禹锡传》:“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唐代苏州经济发达、文化昌明,刘禹锡曾在江南一带度过漫长的青少年岁月,此番刺吴可谓回归故地。刘禹锡虽然在京受人排挤,胸有不快,但从长安南下,经洛阳等地时,受到旧友热情的接待,心境渐趋旷达。白居易在《与刘苏州书》中写道:“去年冬,梦得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吴。仆方守三川,得为东道主。阁下为仆税驾十五日,朝觞夕咏,颇极平生之欢,各赋数篇,视草而别。”并做《送刘郎中赴任苏州》与《福先寺雪中饯刘苏州》二诗,表达了挚友相聚之乐,而刘本人则写作《赠乐天》“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座听”用以回应。此外,在同期《苏州酬别乐天》等诗中,他运用了二南风化、梁鸿孟光、二陆等典故表达出对吴地的欣赏向往之情,加上挚友白居易曾在此为官,故有“承遗爱”“蹑后尘”之感。元人方回在《瀛奎律髓》卷四中评价道:“梁鸿、孟光尝客于吴,机、云二陆昔为吴人,今到苏之后,凡寄寓之客,及在郡之士人,与太守相追游,当共忆乐天为旧太守,即旧主人也。”可见,刘禹锡上任苏州之时,其心境是较为复杂的,既有受朝廷权力斗争排挤的苦闷,又有伴随离开权力中心而来的轻松、解脱之感。然而,赴任之时的轻松心境很快被到任后的严峻考验所取代,刘禹锡入吴之时,正逢苏州遭遇严重水患,他立即投身到紧张的治水救灾中去:“到任之初,便逢灾疫。奉宣圣泽,恭守诏条。上禀叡谋,下求人瘼。”后因治水有功,被赐紫金鱼袋,成为他后半生最大的殊荣。
紫金鱼袋,是古代朝服制度之一种,在唐代原为三品以上官员所佩戴。皇帝将紫金鱼袋赐予品级较低的官员,有着表彰功勋、荣誉嘉奖的含义,更多是一种精神鼓励,并无事实上的职权授予。“唐制,官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视其阶官品级而不视其职事官,其阶官不至三、五品而皇帝特恩赏赐者,称为‘赐紫’或‘赐绯’。”虽无实际封赏,但天子赐金紫对于官员,尤其对品级较低的官员而言,仍是非常值得向往的。如文宗即位后,征拜白居易为秘书监,赐金紫,刘禹锡贺诗:“久学文章含白凤,却因政事赐金鱼。……旧来词客多无位,金紫同游谁得如?”在他看来,获得金紫是比文人才学之名更值得庆贺之事,是文人难得的荣誉。在刘禹锡撰写的碑文中,一旦所记之人获紫金鱼袋,也必要明确书之。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苏州为上州,刺史从三品,但他其时阶官为礼部郎中,从五品,因此,当其因政绩突出被赐紫时,自然表现出极其喜悦的心态。《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诏书,加臣赐紫金鱼袋,余如故者。恩降重霄,荣霑陋质。虚黩陟明之典,恐兴彼己之诗。宠过若惊,喜深生惧。”《苏州加章服谢宰相状》:“顾逢掖之腐儒,被华章之贵服,有黩陟明之典,诚招彼己之讥。”
从刘禹锡本人角度来看,这一事件是他自我价值被证明的标志,同时他也借机抒发多年来政治上被打压的郁闷之情。受赐金紫后所撰《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与其说是谢恩,不如看作陈情,在开篇程式化表达感恩之后,即刻笔锋激转,陈述了自己半生坎坷,“臣起自书生,业文入仕。德宗朝为御史,以孤直在台。顺宗朝为郎官,以缘累出省。宪宗皇帝后知其冤,特降敇书,追赴京国。缘有虚称,恐居清班。务进者争先,上封者潜毁。巧言易信,孤愤难申”,表达了自己受排挤的冤屈之情。随后,又以“曾经诬毁,每事防虞。唯托神明,更无媒援”暗示自己遭人诋毁,孤立无援的艰难处境。刘禹锡此时已至晚年,在频频被排挤出朝后,终于获赐“金紫”,得到了来自皇权的肯定,他在谢恩表中流露的辛酸,不仅是对大半生命运的回顾,还有对自己失意仕途的总结。他将自身不得志的原因归纳为两点:一是才高于人,二是受人诋毁。
这一认识首先来源于刘禹锡对自身才华的强大自信。刘禹锡天赋极高,青年时代的仕途之道颇为顺利,他在《子刘子自传》中回忆:“初,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官司闲旷,得以请告奉温清。是时年少,名浮于实,士林荣之。”后参与王叔文政治革新,平步进入到当时核心统治集团:“愚前已为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余日,至是改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等案。”八司马事发后,刘禹锡被贬朗州、连州、夔、和二郡,在外坎坷三十余年,但他仍然坚持自身政治理想:“常谓尽诚可以绝嫌猜,徇公可以弭谗愬。”即使身处下州,也竭力尽职:“刘禹锡到夔州后,仔细考察当地各方面的情况,于长庆三年(823)和长庆四年(824)分别向朝廷进呈了《夔州论利害表》和《论利害表》。……希望穆宗效法前朝,纳言听谏。”同时深信自身政行并无瑕疵:“小人之善否,不在众人。”在苏州水潦之际,刘禹锡竭尽全力,解决当地民生问题:“臣发迹书生,以文为业。出身入仕,四十余年。顷自集贤学士,出守吴郡。面辞之日,亲承德音。念百姓水潦之余,示微臣政理之法。臣祗膺圣旨,夙夜竭诚。闾里获安,流庸尽复。猥蒙朝奖,锡以金章。及迁同州,又遇歉旱。悉心绥抚,幸免流离。”后至同州,又遇旱灾:“忝为长吏,敢不竭诚?即须条疏,续具闻奏。”因而可见,刘禹锡不仅具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还有具体实际的理政才能,加之其文学上的造诣在当时已有盛名,白居易赞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政治与文学上的双重才华,使他有足够的自信,确认自己是不可多得的治国良才。
在“有才”这一前提下,对于自身命运多舛的解释,刘禹锡将之归结于人言诋毁。中国文人对命运不济的思考,或为时运不济,或受人毁谤,往往从天命与人祸两方面寻找原因,而刘禹锡则明显倾向于后者。在谈及自身仕途生涯时,刘禹锡早期的《上杜司徒书》、中期的《苏州谢上表》与晚年的《子刘子自传》可分别视为其人生三个阶段自抒心志的陈情之作,充分体现了他对自身遭际的认知。《上杜司徒书》是王叔文被贬、八司马事发,刘禹锡远刺朗州后向宰相杜佑自剖心志之书,其时他政治生涯一落千丈,人生陷入谷底,这一切在刘看来,实乃人祸所至:“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他认为自己是他人猜忌嫁祸的牺牲品:“以内咎为弭谤之具,以吞声为窒隙之媒。”而他致书杜佑,目的是获悉宰相对他有所同情,期望蒙冤之事可得自杜佑的理解与护佑:“余闻初子之横为口语所中,独相国深明之。”刘禹锡第二次蒙召入京,后又受排挤出朝,刺苏州,在苏州获赐金紫时所撰《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其中提到“务进者争先,上封者潜毁。巧言易信,孤愤难申……曾经诬毁,每事防虞。唯托神明,更无媒援”,这既是对既往生涯受挫的总结,也是对自己委屈离京、无奈出使苏州的申述。而刘禹锡晚年所作《子刘子自传》,叙述生平之后自作铭文:“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悲叹平生空有才华却无法得以充分施展,根源就在于受人妒忌离间。从刘禹锡本身的价值观来看,他不仅对于自身才华格外自信,对但凡有才之人,也尽都爱惜珍重。在《天论上》中,他阐述道:“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新唐书·刘禹锡传》记载他曾上书宰相呼吁恢复学校:“言者谓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才之道,郁堙不扬,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叹癝庾之无余,可乎?”他的思想观中充溢着朴素的理性主义精神,对人的本质力量进行了有力的肯定,这是刘禹锡人才观的基础。他从自身及历代文人不幸遭际中总结出嫉妒中伤、打击陷害是人才蒙冤、国无贤才的根本原因,因此一以贯之地讽刺、批判这一人性之恶。在《苏州谢上表》中,刘禹锡写道:“伏以水灾之后,物力索空。臣谨宣皇风,慰彼黎庶。臣闻有味之物,蠹虫必生;有才之人,谗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在其七言古诗《百舌吟》中,以“天生羽族尔何微,舌端万变乘春辉。南方朱鸟一朝见,索漠无言蒿下飞”讽刺多言善妒、搬弄是非之人。因此,赐“金紫”一事,对于刘禹锡而言,是一个迟来的肯定,他也借此抒发了半生零落的感慨况味,并从当事人的角度,对自我及他者在价值与人性层面的功过进行了评判。
二 正史书写:“性”为中心的文官考量
《旧唐书》中,对于刘禹锡赐紫一事,仅一笔而过:“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这源自唐史的撰写体例,对官员赐紫仅记载而已,对赏赐原因则不加以说明。从这一角度来看,官员个体引以为荣的御赐金紫,从朝廷角度而言无非嘉奖称号而已,并无实际利益上的授予,同时从唐史记载来看,赐紫在当时颇为普遍,仅与刘禹锡有密切联系的王叔文、白居易、裴度等人,都先后受赐金紫。赐紫金鱼袋虽是恩宠的象征,但却算不上罕见的荣耀。当时文武官员,包括僧人道士均有可能被赐紫:如《新唐书》记载“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
一般情况下,朝廷颁赐金紫,多为对官员政绩的综合评价,并无某一具体原因,但刘禹锡受赐金紫却有明显的直接原因,因赐紫发生在刘禹锡入吴之后,正当其走马上任之际,遭遇水潦,刘禹锡治水有功,被评为“政最”,紧接着朝廷直接颁赐金紫,因此本次赐紫确实事出有因。那么,地方官员本对于本地天灾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皇帝为何此次又特别嘉奖刘禹锡,成为其八司马事件之后政途上最显赫的时刻呢?
刘禹锡多次在《苏州谢上表》中陈述,自己初到吴地,便遇水患,治水是他成为地方官后最为迫切的任务。对于此次苏、湖大水,新旧唐书中也有记载:“戊寅,苏、湖二州水,赈米二十二万石,以本州常平义仓觚斗给。”这条看似简单的记载,在唐文宗统治时期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翻检《旧唐书》,文宗时期是唐代自然灾害的高发期。“文宗一朝共发生自然灾害72次,发生率高达553.8%。相当于每2个月,就有一次自然灾害发生。”在诸种自然灾害中,水灾尤为频发,《旧唐书》记载,从大和三年开始,几乎年年、月月受灾,如“(大和四年八月)丙辰,鄜州水,溺居民三百余家。太原柳公绰奏云、代、蔚三州山谷间石化为面,人取食之”。同年九月:“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县水,溺民户六百八十,诏以义仓赈贷。”同年11月,“是岁,京畿、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等道大水”,“(大和五年六月)辛卯,苏、杭、湖南水害稼”,“(七月,)剑南东、西两川水……是岁,淮南,浙江东西道、荆襄、鄂岳、剑南东川并水”。
接连而来的天灾,不断震荡着帝国的神经,除对社会物质、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外,还直接威胁了文宗的统治权威。在古人的信仰观念中,君王乃上天垂象,是天命的承载者,而巨大的自然灾害直接质疑了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可以看到,自大和六年(832)以来,治理水患成了文宗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于大和六年下昭:“朕闻‘天听自我人听,天视自我人视’。朕之菲德,涉道未明,不能调序四时,导迎和气。自去冬已来,逾月雨雪,寒风尤甚,颇伤于和。念兹庶甿,或罹冻馁,无所假贷,莫能自存。中宵载怀,旰食兴叹,怵愓若厉,时予之辜。思弘惠泽,以顺时令。”文宗以刻苦己身表明理政的精诚之心,而赈灾也成为其在位时期重要的行政考验,关系其统治根基的牢固。这一年二月,刘禹锡刚刚就任苏州刺史,就遭遇了空前的水患,《旧唐书》对此虽一笔带过,但其中提到本州常平义仓所赈之米达到二十二万石之巨,较之同期的赈米数量,如大和五年杭州灾疫,赈米七万石、大和五年春太原旱,赈栗十万石等,苏州赈米的数量是空前巨大的。《唐会要》中有关于大和四年常平仓纳粮量的记载:“大和四年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宜于关内七州府及凤翔府和籴米一百万石。”一般来说,政府每年收入常平仓的纳粮量基本是固定的,大和四年关内七州一府的纳入量为一百万石,而二年后苏州仅一地的水灾即耗去二十二万石,这一比例之大,可直观地反映出这次水灾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刘禹锡到任后对赈灾的执行力度是极其到位的。
刘禹锡在《苏州谢赈赐表》中表达了自己就任以来的所作所为:“伏以臣当州去年灾沴尤甚。水潦虽退,流庸尚多。臣前月到任,奉宣圣旨,合境老幼无不涕零。询访里闾,备知凋瘵。方具事实,便欲奏论。”他具体的工作,是使赈米二十二万石“据户均给”,在《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中,他自陈心志:“自领大郡,又逢时灾。昼夜苦心,寝食忘味。”可见刘禹锡在任期间始终处于相当繁忙的状态,苏州治水给他此后的生活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后至同州,在《同州谢上表》中也回忆道:“臣顷任苏州之年,亦遭大水之后。面辞之日,亲奉德音。至于抚绥,皆承圣教。二年之后,百姓获安。”刘禹锡夙夜操劳理政,治水有功,在关键节点上维护了文宗的统治权威,被赐金紫,实乃朝廷对其多年疏离、提防后抛出的带有肯定意味的橄榄枝。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文宗并未在刘禹锡治水立功后将其召回,反而又刺汝州、同州,前后约4年才回到洛阳,分司东都,授太子宾客。事实上,太子宾客虽官阶三品,官俸优厚,但并无重权:《新唐书·百官志》:“太子宾客四人,正三品,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宴会则上齿。”总的来看,唐代统治层对刘禹锡的态度是颇为暧昧不清的:一方面,肯定刘禹锡的政治才能;另一方面,对其不能充分信任,不给予重用。究其根源,直接原因可归于刘禹锡革新的政治理念在保守的中晚唐政治氛围中并不受欢迎,深层原因则是以正史为代表的封建正统价值观在官员评价上面拥有强大的官方话语权,即品评官员的价值标准是处事谨慎、为人低调圆通,刘禹锡锋芒毕露的个性及强烈的自信使其必然不能成为统治阶层最心仪的臣僚。
《旧唐书》对刘禹锡的评价,可谓褒贬兼有,而批评更甚。首先,《旧唐书》引王叔文赞刘禹锡有“宰相器”,并对其文才进行了肯定,如引白居易评价:“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但对刘禹锡个性、行事,则多有批评,以“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作为史传对其的定论。《新唐书·刘禹锡传》也评价其“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褊心,意指心胸狭窄,气过于人,言行任意,如《旧唐书》记载宪宗在裴度为刘禹锡远刺播州求情时回应道:“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宪宗所论刘禹锡更重于他人之罪,即指其与王叔文结党革新一事,以中央集权为中心的朝廷,各类势力暗流涌动,暗中角力,而公开结党无疑会触及或挑衅到各个集团利益,锋芒太盛,是为官之大忌。从这个角度来看,刘禹锡并非无才,而是缺乏中庸圆通、韬光养晦的政治心机。故《旧唐书》评价:“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缙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对于封建社会最高权力集团而言,文才并不是官员的首要素质,处事能力则更为重要。如《旧唐书》评价韦辞,将之于刘、柳进行比较,认为前者“辞素无清藻,文笔不过中才,然处事端实,游官无党”。又如白居易,《旧唐书》对其天赋之文采及文学成就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对其做出了正面评价:“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壸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而这与白居易“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的谦和个性及悠游的处事态度是相关联的。戴伟华在《才性论与裴、李“初唐四杰”才性之争》一文中,引裴行俭“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作为官员任命的标准,裴行俭以此判断王勃“浮躁炫露”不适宜为官:“所谓‘器识’,主要指人的性格,并由性格而生的认识水平和情绪,裴行俭认为王勃等四人‘浮躁炫露’,只是杨炯‘稍似沉静’。四人‘器识’不及‘文艺’,而选材任人必须以‘器识’为重。”这一论断可准确解释新、旧《唐书》对刘、柳等人的评价。沉稳有度、深思屡远、谨言慎行等品性是唐代官员的首要素质和考核标准,在这个前提下,刘禹锡被颁赐金紫,只是朝廷与之表面和解的符号而已,并未根本上扭转中央政府对其的基本评定,因此也不能改变刘禹锡后半生再也无法进入权力核心的仕途命运。
三 立祠:地方立场及“贤”为中心的价值回响
刘禹锡入吴治水、赈米救灾、获赐金紫、惠及民众,在吴地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具体表现在苏州当地为其建祠,岁时供奉。此祠最早可追至宋代,由其时郡守蒋璨建。修祠始末记载在范成大所撰吴地方志《吴郡志》中。“思贤堂,旧名思贤亭,以祠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后改曰三贤堂。绍兴二十八年,郡守蒋璨建。”三贤祠在宋、明、清朝不断扩建,在修祠的过程中,立祠目的从最初的感念郡守政行,上升为吴地地方价值理念表达,是从方志角度出发,对以刘禹锡为代表的文人政客做出来自民间士绅阶层的价值审视与评判。
在三贤祠立祠暨修祠的过程中,首先反映出来的是吴地较为强烈的地方文化自信。苏州在历史上为东吴胜地,经济发达,称为上州,与下州相比较,文教昌明,人文素质极高。可以看到,吴人为历代郡守立祠,虽包含感恩政绩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也力图彰显本州文教兴盛,文化底蕴深厚。如“二公(白居易、刘禹锡)共生大历壬子岁,真辈行也。晚益相厚,世谓刘、白。白之去郡,刘以诗遗之,有‘(千)(门)万户婴儿啼’之句。虽三代遗爱,何以加焉。后六七年,当大和中,刘亦继来。乘郡荒疫之余,抚摩安辑,免民于转徙,文宗锡服以宠之。白公时在河南,犹以诗为刘贺。三贤平时道义相先,分相好,诚相与也。而文声政绩,兼优并著,且俱为有意于民者。名藩巨屛,得一师帅吾民,幸矣。乃接踵来临,岁月未远。声名风采,炳乎其辉,一时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可见三贤祠的修建,有强烈的地方文化认同感,与韩愈出使潮州“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不同的是:韩愈牧守潮州,使得当地文化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是先进的儒家文教对落后的岭南文化的全面洗礼;而白、刘、韦等文官的苏州行迹,则是名邦上州强大文化虹吸力影响所致,是同质相吸,反映出吴地文脉的悠长与兴盛。绍兴三十一年,其时郡守洪尊在三贤堂外新建瞻仪堂,“吴俗贵重太守,来者必绘其像”。越年,又在三贤堂内增益苏州历史上另外两位有名刺史唐人王仲舒与宋人范仲淹之像,改三贤堂为思贤堂。范成大在“瞻仪堂”条下加注:“吴自置守以来,仍古大国,世为名都。又当东南水会,外暨百粤,中属之江淮……窃尝观郡国方志,与耆旧、风土之书,既备载山川、土疆、郭郛所在,必论次前世贤守长爵里、姓字之大略,著于篇。谓君子尝居之,其地政僻陋,犹借此以为宠。今吾州不独能志其人,而肖貌具在,章绶相辉,凛凛如对生面,他郡未闻有此。”在范成大行文中,表现出对东吴文化的自信及高度赞誉,不仅名人纷纷而来,当地对其行迹、相貌都详细记录,他反复强调这一现象是“他郡未闻有此”,从中也隐约表现出对其他郡县“借此以为宠”攀附名人心态的不以为然。因为高度发达的经济、重要的政治地位及文化上的强势心态,地方太守为刘禹锡等历代郡守修祠立祠,这种行为不仅超越了铭旌感念的纪念意义,体现出彰显名邦文化的宣传意味,甚至还表现出相对独立的地方价值评判标准,虽不足以质疑中央统治集团的核心价值观,但却代表了与中央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独立思考并以广大士绅认同为基础的价值衡量体系。
在蒋璨始立三贤祠之初,范成大就对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合立为祠进行了解释,除交代刘白二人相好,先后牧守苏州外,特意为韦应物鸣不平:“并每独怪唐史如《文艺》《儒学》《循吏》三传,几二百人,韦公法当处一焉。乃独不为立传,亦史册之遗恨也。”并对韦应物政行、才德做出了很高的肯定:“公正元初,由左司郎得郡于此。清德临民,民乐其政。暇日,宾礼名流,与之酬唱。于时白公客游郡下,盛称公风流雅韵,播于吴中。至有诗仙之目,自以不得与公游宴为不满。已而罢郡,寓永定僧庐,羁旅萧然,欲求田课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扫地而坐。清风峻节,可想而知。其后白公自杭移苏,实宝历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诗镵之石,酷爱慕之,每自谓不及。韦公大概,可见于此。”范成大这段论述,既为韦应物未录于正史感到抱憾质疑,也体现出吴地士人乡绅对文官的价值衡量标准。
从三贤堂至思贤堂,其中对祠主的评判标准,都是围绕“贤”来展开的。贤是古代以乡为单位的基层宗法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乡是天子推行政令的最小单元,是最基本的社会缔结体,如乡有乡学、乡大夫,而一乡之中对大众具有教育垂范意义的人物可称乡贤。如苏州专门建有祭祀乡贤之祠堂:“蒋氏三贤祠在史家巷。祀明乡贤育馨、灿、若来。”吴地以“贤”立祠的传统悠久,从以白、刘、韦为核心的三贤堂到思贤堂,一直延续至清代发展成为囊括历代贤人的吴郡名贤总祠,以贤为主题的祠堂屡建不衰。仅以乾隆《苏州府志》卷二一至二三中对明代苏州乡贤专祠数量的记载,就有43座之多,为一时之最。贤成为该地区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和始终奉行的行为准则。从上述祠堂选择所祭祀之祠主来看,基本可对吴地“贤”的内涵做出理解。
首先,贤者需是有才之士,可为文学之才,也可为政治之才。如三贤祠主人白、刘、韦,均为文学之士,形成本地区郁郁乎文的文化氛围。又如明万历中修建五贤祠,供奉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王禹偁、苏轼,皆为历代著名文人,《吴越访古录》著录五贤祠诗文:“平远堂开枕碧流,群山遥拱各低头。名贤自昔多遗迹,异代相思半旧游。诗格漫区唐宋界,宦途永洗古今愁。危祠记是登临处,江令文章重虎邱。”表明此祠所祭祀五位贤人,皆以文章成名不朽。另与宋代三贤祠同时期的还有韦苏州祠,虽非以贤题名,但韦应物后进入三贤祠与刘白同祠供奉,说明吴人也给予其贤的评价。韦苏州祠题诗:“漫说文章僭左司,即论风雅亦吾诗。三吴名宦羊碑颂,七字清吟燕寝知。”表明韦应物的文才,是其成为贤者代代纪念的重要原因。又如韦苏州祠祠联:“斯可以从政,何莫学夫诗。”表明韦应物政才、文才兼美。清代所建吴郡名贤总祠,共祠群主三千八百余人,其中有文学之才,也有政治之才,其中多人非吴人也非吴地太守,皆能入祠而祀之,说明贤人的选择标准之一即为才干之士。这是贤的早期内涵之一。《谷梁传·文公六年》“使仁者佐贤者”,范甯注:“贤者,多才也。”《淮南子·修务》“周室以后,无六子之贤”,高诱注:“贤,才也。”
其次,贤在“才”之外的另一早期内涵为“德”。如《尚书·咸有一德》:“任官唯贤才,左右唯其人。”孔颖达义疏中,将这里的贤与《诗·大雅·烝民》序中“任贤使能”同解,即“有德谓之贤”。《书·仲虺之诰》“佑贤辅德”,孔颖达疏:“贤是德盛之名,德是资贤之实。”《论语》中孔子对颜回“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肯定也认为他为贤者,即有德之人。自宋以来,在对三贤、五贤及历代名贤进行评价时,吴地对其中所祠贤者的评价均在向“贤之为德”方向倾斜。如范成大对三贤祠得名时总结到:“韦、白、刘之余爱,邦人既已俎豆之。语在旧碑,尚矣。王、范风烈如此,且有德于吴,宜俱三贤不没,以为无穷之思,此堂之所为得名者。”明代松江人士何良俊曰:“乡贤则须有三不朽之业,谓立德立言立功三者是也。”首重即为德。又如清代名贤总祠祠联:“复古溯汉唐以降,有废必兴,重傍黉宫分俎豆;表微祔文行诸贤,无德不报,长留珂里作楷模。”可见德是贤的重要内涵。贤之为德的具体表现,在于“有德于吴”,对于地方乡闾而言,施善于民、造福流芳、教化垂范,是地方人文精神的核心构成与长久的价值守望,体现出地方文化的认识共同体。从这个意义来讲,吴人认为贤德比贤才更为重要,贤才囿于己身,贤德施于他人。如范成大讲到宋代苏州郡守蒋璨之子重修思贤堂目的时指出:“公既以道学文章命一世,顾有羡于五君子者。意将迹其惠术,讲千里之长利,以膏雨此民。”贤德与贤才比较,具有更广泛的时空影响力,对民众也具有更多的福祉与教导意义。在此基础上,一种来自吴地乡绅阶层的有关贤的全新理解产生了:“夫才高而不自贤,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可以看出,吴人对贤的理解与诠释,洋溢着经世致用、关乎民生的人文精神,这与之前刘禹锡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对自身才华的强调、正史为代表的封建中央统治集团对官员品性的关注是有所不同的。吴地文化并不单纯重视文官的才干,也不以性情为评价官员的基础尺度,而是注重其用才之道,以及才行在更长远的时空中所昭示出的意义。吴地乡绅阶层甚至对传统仕途之道所强调的韬光养晦、独善其身的政治智慧表现出批评态度:“尝谓士才高必自贤,位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而对不恃才自傲、积极治世之官员(如洪公忠宣公之子)表示了极高的赞赏:“邦人度公且上朝谒,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因此,自刘禹锡刺吴之后,宋、明、清人不断立祠修祠,文官本身的功绩已转化为一种跨越时代的价值衡量准则,与地方文化相互回应,成为吴地特有之人文精神与价值操守。
刘禹锡牧守苏州、受赐金紫、为其立祠,本为不同时间点上三则独立的历史事件,从表层来看,三者处于单纯的因果联系之中,刘禹锡因治水有功而受赐金紫,又因惠泽吴地而被立祠纪念。但表层看似简单的事件之下,却涌动着来自文官自身、中央统治阶层与地方乡绅阶层多元的价值尺度,并在彼此交流之中构成价值观的碰撞与角力,成为古代社会丰富的政治、文化生态之一角。这则个案也揭示出对于古代文人行迹的分析,具有极大的可深入挖掘的空间,文人空间行迹的背后,具有复杂的行动动因,并可在后来的时空范围内产生持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