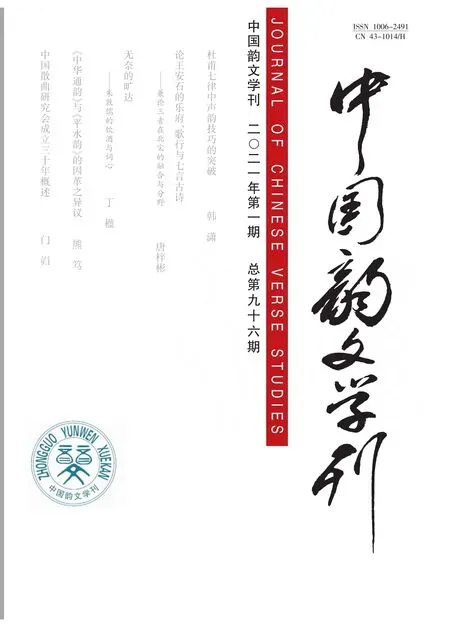苏轼诗歌中造物形象的诙谐意趣
郑韵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文学系,北京 102488)
在苏轼诗歌中,“造物”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这一概念源于《庄子·大宗师》:“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指的是主宰万物、命运的力量,后来还经常指自然及其创造者,具有相似意义的还包括“造化”“化工”“天公”“天工”等词。诗人对造物的书写不仅显示了对这种超越自我、支配万物的抽象力量的关注,更蕴含着他们观照自然外物与认识自身的方式,在不同的时代和诗人笔下,造物的形象及其与人的关系也会呈现很大不同。苏轼诗歌中的造物具有极为丰富的形象,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经常体现诙谐的意趣,这种意趣既包含了苏轼对造物严肃性的消解,也包含了他对自我与造物严肃紧张关系的消解,并深刻影响到后世诗人对造物的表现。本文拟对苏轼诗中的造物形象进行梳理,探讨其诙谐意趣的表现方式、形成过程和精神内涵,分析苏轼对古代诗歌中造物形象艺术表现的影响。
一 “造物本儿嬉”:苏轼对造物的诙谐表现
苏轼乐观旷达,幽默善谑,他用诗笔刻画造物形象时,也充满诙谐的意趣。现有研究在分析苏诗诙谐意趣时,多侧重现实经历和人际交往层面,尚少从自然特别是造物层面的探讨,因此有必要认识苏轼对造物的诙谐的表现方式。
首先,苏轼擅长以人格化的手法表现造物具有人的心理、局限和弱点,消解造物的严肃性和权威感。由于造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传统上诗歌刻画造物,总是用笔颇为严肃,突出其高大和理性,如“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王羲之《兰亭诗二首》其二),“天公高居鬼神恶,欲保性命诚难哉”(韩愈《感春五首》其四),“上帝设号令,隐其南山下,震发固有时,曷常事凭怒”(梅尧臣《冬雷》)。而苏轼偏偏喜欢让高大庄重的造物具有平凡随意的人性特征,形成反差。一个最典型和独创的体现是将造物比作小儿,即“造物本儿嬉,风噫雷电笑”(《曹既见和复次韵》),又如“造物何如童子戏,写真聊发使君闲”(《和人假山》),“老人大父识君久,造物小儿如子何”(《赠梁道人》),高大的造物却如小儿游戏,形成诙谐的效果。苏轼还经常表现造物具有任性、偏私、厌倦等与理性相对的情感,如《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其二又云:“花开时节雨连风,却向霜余染烂红。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这两首诗被认为有讽刺新法烦苛的意味,这是牡丹与政令两种本不相干的事物奇妙相联造成的幽默讽喻效果。而从造物的形象看,苏轼一时言造物一味呈新弄巧,冬天也不容牡丹稍歇,一时又言造物是偏私牡丹才令它冬日开放,恰恰反映了造物如人情随意任性和反复无常,与造物本应具有的公正秩序形成反差,由此形成诙谐的表达意趣。又如《次韵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其一:“省事天公厌两回,新年春日并相催。殷勤更下山阴雪,要与梅花作伴来。”元日与立春重合的历法现象被苏轼视为造物在图省事。《次韵范纯父涵星砚月石风林屏诗》说“天工与我两厌事,孰居无事为此形”,造物和自己一样厌倦于事,这类题材的常见主旨本是惊叹造物的奇伟精妙,在苏轼的写法下却有了轻松诙谐的意味。这种人格化的反差写法还常以细节取胜,如《中秋见月和子由》中:“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万丈生白毫。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显然,在苏轼笔下“天公”不只是造物的拟人化代称,而有相应的人格细节,他为天公添上了具体的器官眼眸,天公洗眼要用的自然是银河水,澄澈壮阔的月色银河与洗眼这一平凡行为相对应,就形成了谐趣。诙谐感得以成功在话语中显现,经常来自各要素的反常规组合,苏轼对造物随意和严肃的反差塑造正是这一原理。
其次,苏轼既然塑造平凡人性化的造物,与造物也会有相对亲近的交流,无论是对造物还是其创造的具体自然物,他都怀着一种平等友善的视角天真互动,这种亲近感成为诙谐的前提,而诙谐则是对亲近感的一种更为独特的表达。正如苏轼与朋友交往的诗作里经常充满友善的雅谑,他也善于在与造物及自然物的亲近互动中营造诙谐意趣。如《越州张中舍寿乐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时不肯入官府。
高人自与山有素,不待招邀满庭户。
卧龙蟠屈半东州,万室鳞鳞枕其股。
背之不见与无同,狐裘反衣无乃鲁。
张君眼力觑天奥,能遣荆棘化堂宇。
持颐宴坐不出门,收揽奇秀得十五。
才多事少厌闲寂,卧看云烟变风雨。
笋如玉筯椹如簪,强饮且为山作主。
不忧儿辈知此乐,但恐造物怪多取。
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
苏轼将屋外高耸的青山拟作与张中舍性情相投的高人隐士,既提炼了外形,又象征了精神,较之一般模拟表象或比附道德的拟人修辞,本就更生动风趣。又指出张中舍独窥造物用意,才能注意到常人忽略的奇景,人本是单向地观看山,被描述为亲密的宾主交欢,显得格外愉悦。而在诗人的想象中,造物对其创造和赐予的美景,竟然有些许吝惜,会责怪人过度占有它,这并非对造物形象的直接描写,却以层次丰富的情感交流令人会心一笑。作为有创造力的诗人,诗歌与造物是何种关系、能否影响造物,也是经常会思考的问题,比起前辈诗人经常表现诗歌“与造化争功”的肃穆、艰苦、紧张的互动关系,苏轼更乐于描绘诗歌令造物展现温暖、明媚、喜悦的一面,所谓“愿君发豪句,嘲诙破天悭”(《祈雪雾猪泉出城马上作赠舒尧文》),“诗成天一笑,万象解寒窘。惊开小桃杏,不待雷发轸”(《李公择过高邮,见施大夫与孙莘老赏花诗,忆与仆去岁会于彭门折花馈笋故事,作诗二十四韵见戏,依韵奉答,亦以戏公择云》),“谁信诗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三),戏谑的态度可以化解造物的悭吝严肃,而造物面对诗人的创造也会轻松一笑。即使对造物并不友善的一些行为,苏轼也倾向以某种轻松游戏的眼光看待,并以诙谐的口吻述说。如《次韵答刘泾》说“吟诗莫作秋虫声,天公怪汝钩物情,使汝未老华发生”,作诗穷人,未老白头,本是值得悲叹的命运,称为造物对诗人的责怪就显得不那么严肃,而诗人作诗本就受物情感发,造物却责怪诗人勾引物情,如此无理,在诙谐中实现了对友人的规劝。又如《次韵黄鲁直赤目》说“天公戏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眼疾是造物对人的戏弄,是假象的蔽障,是幻翳遮掩了明珠,也体现了诙谐乐观的开解。关于诙谐幽默的研究中,一个共识是良好的幽默能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我们也可以推广到自然造物,并反过来说,与造物的亲近互动往往能够形成诙谐的意趣。
更为可贵的是,苏轼对造物的诙谐表现并非一味出以弄巧调笑,还与经过省思的自嘲相联系。广义的诙谐与“可笑性”大致相当,而深层次的诙谐实际上是一种“诉诸理智的可笑性”,也就是说要经过思考,越是智慧和长于反思的人,越能创造诙谐的意趣。这种思考在苏轼面对造物时又常表现为消解自我庄重感的自嘲。由于一般人眼中的造物是高大万能的,人也会对造物有许多期望,苏轼却能看到这种期望的不切实际甚至荒唐可笑,也善于表现这种荒唐。如《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三:“种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不如种丛彗,春种秋可倒。阴阳不择物,美恶随意造。柏生何苦艰,似亦费天巧。天工巧有几,肯尽为汝耗。君看藜与藿,生意常草草。”苏辙原唱言“蓬麻春始生,今已满一丈。柏生嗟几年,失意自悽怆”,因此苏轼也承此言柏树生长艰难,这似是造物刻意,但他随即以“天工巧有几,肯尽为汝耗”否定。造物并不会那么专注一物,而藜藿没有被着意照管也生机健旺。如果将柏树视为自身生命的写照,其自嘲意味就更明显,一己人生在造物之下本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也不需要太失意怨尤,只要顺应自然。又如《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
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
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
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
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
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
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
这首诗的诙谐感也是通过思考和自嘲“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的荒唐可笑传达的。行舟阻风,向造物祷告立刻遂愿,按常情自要为造物满足自己感到高兴,苏轼却清醒地认识到造物的变化本是无心无私的,并且不掩饰自己心存私念,与至人有着相当的差距,才会欣喜造物满足了自己。进一步说明,即使是相同天气,人们也会因需求不同而感受不同,所以造物不仅不会一日千变地满足所有人,若是自己事事有求于造物,造物也会感到厌倦。从另一角度说,造物无法事事满足自己,最好的应对方式当是来去都无牵挂,行止都能安适。在与前人的对比中更能看出苏轼自嘲心态对造物表现的独特影响。由于苏轼惯于消解自我庄重感,他并不过分看重自己对造物的施力,更乐于设想造物的善意。如《登州海市》说“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这是针对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中“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而发的。同样是见到了时节反常的奇景,韩愈认为是自己的正直感动造物,苏轼更倾向于理解为造物对人的哀怜,并且当他感受到造物慷慨赐予了他快乐,“伸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精妙的语言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重要,“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诗歌没有与造物争胜,而是同海市一样变化幻灭。正是因为苏轼在省思中消解超越了自我的得失、利害、难易等种种拘执,才能面对造物不再严肃紧张,而以更亲近随意的态度看待,这是他诙谐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其诙谐意趣的深度所在。
二 从“游于物之外”到“我亦儿嬉作小诗”:苏轼对造物认识的变化过程
诙谐既是文学表现和风格,也可以是一种“对宇宙万物区而不隔性质的把握方式”。苏轼对造物的诙谐表现就源于他独特的观照自然和认识事物的视角,这种视角如同他深受世人喜爱的性情和观念一样,有在人生中一以贯之的部分,同时也经历了一定的形成过程,比如他如何能将造物视为小儿,并与之一同游戏,或许可以从他观物视角和心态的发展中寻找到一些线索。
苏轼诗歌很早就表现对观物的重视。虽然诗歌表现自然万物,自《诗经》就有传统,历代文论家也都很重视心物交感对诗歌创作的作用,但诗中明确和大量地出现“观物”一词甚至直接以此为题,以示对物普遍而主动的观照,是宋代的事。《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一中说:“煌煌帝王都,赫赫走群彦。嗟汝独何为,闭门观物变。微物岂足观,汝独观不倦。牵牛与葵蓼,采摘入诗卷。吾闻东山傅,置酒携燕婉。富贵未能忘,声色聊自遣。汝今又不然,时节看瓜蔓。”虽是写苏辙,也反映苏轼自己的价值取向,即使是微小事物的变化,也值得观照不倦。这组诗歌就多是细致入微地描写种种微小普通的植物的形态和生长变化,并从中感悟物理,虽然没有特别新奇的观点,却显示了观照微物能使人超越名利纷扰,对比貌似放情丘壑、实则难忘富贵声色的矛盾心态和刻意行为,更显得清醒难得。
随着苏轼在政治风波中浮沉,在地方生活实践中整合儒道思想,他对万物和物我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观物视角更加成熟,尤为明显的是对事物的美恶大小性质有了明晰的认识,以熙宁八年(1075)作于密州的《超然台记》最具代表性: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关于这段文字,学者已指出苏轼这种态度继承发展了欧阳修的“达理乐物”观念,“有助于诗人积极乐观地对待一切,从而在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现人生的趣味”,也对苏轼超然思想的内涵有丰富的论述,注意到超然物外的心灵是苏轼幽默文化个性的重要方面。从观物和认识造物的角度还可以做一点发挥:首先,苏轼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这也是为何他善于并乐于观照“微物”。其次,人情本是求福避祸,但如果心存物的美恶区别又患得患失,能满足欲望的物就少,更多令人悲哀,反而像求祸避福,这是物蒙蔽了人心。而对于如何克服蒙蔽,苏轼提出关键的“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超然观物,物本无大小之别,是观照视角的不同导致了人的感受不同,若拘执于物的表象差异和利害,只会感到处处被挟裹阻碍。对待本就比万物“高大”的造物更是如此。如果只关注造物的权威掌控和任意变化,只会感到“眩乱反覆”,具有飘零无定的情绪,例如“此身随造物,一叶舞澎湃。田园不早定,归宿终安在”(《韩子华石淙庄》),“书生例强狠,造物空烦扰”(《与客游道场何山得鸟字》)。而一旦跳出这种变幻不定来看,就能够超然自适地应对造物,如《百步洪二首》其一,一方面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千变万化的水势,感到“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觉来俯仰失千劫”,仿佛陷入造物裹挟,无法自主,另一方面“回视此水殊委蛇”,跳出纷乱变化之外冷静反思,于是悟到“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这一时期苏轼还从其他方面探讨了人对待外物应有的态度,如《宝绘堂记》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也提到了物能否令人快乐不在于美恶大小,而在于人的态度,不过强调的是不可耽溺于物;《醉白堂记》的“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也赞扬了超越名利、齐物自适的理想境界,不过还强调了“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的德行修养。其内核则有一致性,也就是超越表象差异,坚守内心安定,自物外超然观之。之前所举的苏轼对造物的诙谐表现,也往往拥有这种超脱的视角,如“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就是跳出个人私欲来理解造物,“不忧儿辈知此乐,但恐造物怪多取”,则体现了享受造物馈赠但不耽溺的节制。这种视角帮助苏轼消解了造物的高大权威,经常能从造物的行为中体验并表达乐趣。
苏轼观物的独特的“大小”观,为将造物视为小儿形成了必要的铺垫,但将造物小儿化并不必然具有诙谐意趣,还需要将人生反思更进一境界。学界对苏轼将造物视作小儿游戏关注已久,笔者认为对此语的产生语境还可细析。颇有意味的是,苏轼最早在诗中表达造物如儿戏,是黄州时期吊友人李台卿的挽诗《曹既见和复次韵》:“造物本儿嬉,风噫雷电笑。谁令妄惊怪,失匕号万窍。”苏轼因贬谪黄州才与李台卿相识,可谓患难之交,不料李很快去世,一个“妄”字深刻传达了人与造物的力量差异和面对造物戏弄的无可奈何。事实上,这段时间他所作挽诗提及造物格外频繁,也屡屡采用造物如儿戏(“戏剧”亦此意)的表达,如“人间得丧了无凭,只有天公终可倚”(《任师中挽词》),“家庭拜前后,粲然发笑色。岂比黄壤下,焚瘗千金璧。若人道德人,视此亦戏剧”(《邓忠臣母周氏挽词》),“平生无一女,谁复叹耳耳。滞留生此儿,足慰周南史。那知非真实,造化聊戏尔”(《叶涛致远见和二诗复次其韵》其一)。揣测苏轼的心态,当其遭受人生重大打击,政治前途和理想面临幻灭时,这样的困境或许令他倍加深刻地感到造物不可抗拒的力量,而生死又是最让人感到人力无能为力的事,对造物来说却显得十分轻巧、毫无理由,于是有了造物像小儿游戏、甚至是刻意作弄的看法,可以说基调本是悲哀而非幽默的。而苏轼之伟大也在于终能超越痛苦。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苏轼自贬谪黄州后,自嘲类的诗歌增多,正所谓“盛衰阅过君应笑,宠辱年来我亦平”(《和致仕张郎中春昼》,体验过苦难才会真正懂得诙谐,而自嘲谐谑又是他化解苦难的方式,自嘲即意味着对自我庄重感的消解。苏轼这一时期观物思想的发展也实现了某种自我消解,在《赤壁赋》中有集中体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人面对造物最大的悲剧感或许就来自“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而如果说此前苏轼从“内”与“外”、“大”与“小”的角度强调以恒定的内心看待物的表象差异,尚有物与我的分别,也只是能尽量减少物的“可悲”,那么此时他直接从“变”与“不变”的角度切入观物问题,不仅更深地触及造物的运作规律,而且发现了物与我的共通之处,由此达到物我界限消解、融化为一的“物化”境界,生死、荣辱、盛衰这些最验证自我存在感的要素不再困扰诗人。此外,造物一方面令人困厄,另一方面又将“无尽藏”分享给人,诗人不仅感受到自身超越了瞬间而获得了永恒,还能享受造物的永恒善意,这也消解了自我与造物的紧张关系。
所以,当苏轼解决了瞬间与永恒这一人与造物的最大隔阂,并且与造物和自然万物实现了一种更为亲密自由的关系,摆脱困境之后再回看造物的驱使,会觉得既然造物如同儿戏,自己也不妨以游戏的乐观心态看待,甚至与造物一同游戏。于是他会劝说他人“愿君付一笑,造物亦戏剧”(《次韵王郎子立风雨有感》)。又如“造物何如童子戏,写真聊发使君闲”(《和人假山》),“天公戏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次韵黄鲁直赤目》),不管是奇巧有趣的事物还是困扰人的病痛,他都能视为造物小儿的游戏。苏轼也会与造物一同游戏,如《蜡梅一首赠赵景贶》中:“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天工变化谁得知,我亦儿嬉作小诗。”他为蜡梅和蜂蜡建立关联,视为造物随意莫测的游戏,自己也以作诗的方式与造物一同游戏。“我亦儿嬉作小诗”还具有两层特殊意味:一者,虽然造物变化难测,但苏轼似乎并不为此费神或彷徨,而是感到诗人作诗就像造物创造万物一样随意,既然具有相似的功能和心态,只管一起亲密游戏;二者,在苏轼之前很少有诗人明确将作诗视为一种快意的游戏乃至愉悦的生活方式,这是对诗人身份庄重感的消解。如果苏轼不曾发现自己与造物的诸多共通之处,未能以游戏心态看待造物对命运和自然的驱使变化,以及缺乏对自我身份的解嘲,也就很难随时通过“作诗”营造造物的诙谐意趣。造物亲近诙谐的形象和诗人看待造物戏谑随意的态度,是苏轼对诗歌造物表现独到的贡献。
三 苏诗造物形象诙谐意趣的诗歌史影响
中国古代诗学很早就与自然有紧密联系,在本体论层面,认为文学是天地自然的文采的对应,“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文心雕龙·原道》);在创作论层面,也强调外物的感发作用,“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作为自然万物包括人的主宰者,造物在诗中的地位当然也十分重要。从诗歌史上看,在苏轼之前,造物形象尚不具有明显的诙谐意味,自苏轼之后则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诙谐的特征,以及造物与诗人亲近戏谑的关系,这种诙谐意趣正是苏轼对造物形象开拓性的贡献。
造物在诗中内涵的丰富和形象的发展,都经历了漫长过程。汉魏六朝诗中的造物,尚多为抽象的概念,诗人笼统地感叹造物主宰万物的力量,如“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虚盈”(潘岳《思子诗》),“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王羲之《兰亭诗二首》其二)。初盛唐时,此种感叹有了更具体的情境,最主要的就是赞美造物创造了奇伟景观,如“嵥起华夷界,信为造化力”(宋之问《早发大庾岭》),“昔闻乾坤闭,造化生巨灵”(王维《华岳》),“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李白《望庐山瀑布水二首》其一)。值得注意的是,个别诗人提到了绘画创作可比肩造物之功,如岑参“始知丹青笔,能夺造化功”(《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杜甫“乃知画师妙,功刮造化窟”(《画鹘行》)。这可能是因为绘画作为视觉艺术,描摹的形象很容易与造物创造的真实自然对应,而作为语言艺术的诗与造物的关系,还要到中唐才被充分发现。中唐诗中,随着诗歌世俗化、日常化的萌芽,诗人对造物功绩的关注也由宏大景观遍及更微小的事物,如“念汝小虫子,造化借羽翼”(卢仝《蜻蜓歌》),“犹知化工意,当春不生蝉”(元稹《春鸠》)。更关键的一个变化即川合康三指出的,诗人与造物以“与造化争功”的敌对形态出现,诗歌可以创造世界甚至破坏造物的秩序,韩孟诗派对自然怪奇激烈的书写也与此相关。从另一个角度看,诗人能够匹敌造物,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造物具有了某些与人交流的特性,于是出现了质问造物、向造物许愿等情感,如“足知造化力,不给使君须”(李贺《感讽五首》其一),“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白居易《牡丹芳》)。
北宋时期,造物形象的一大变化是与诗人关系更为紧密,不乏深度的精神互动。总的说来,北宋诗人也有匹敌造物的信念,但不是像中唐诗人激烈的对抗破坏,而是怀着强烈的探究精神,试图建立逻辑解释造物的运作,并发现自己与造物的相似性。苏轼之前,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中已出现大段围绕造物的讨论,如梅尧臣《韩钦圣问西洛牡丹之盛》说“君疑造化特着意,果乃区区可羞耻。尝闻都邑有胜意,既不钟人必钟此”,“天意无私任自然,损益推迁宁有彼。彼盛此衰皆一时,岂关覆焘为偏委”。他并不认为牡丹之盛是造物格外偏爱,而强调造物自身的运作规律,盛衰也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又如欧阳修《紫石屏歌》中明确表示对探究造物与物理的兴趣:“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穷探。欲将两耳目所及,而与造化争毫纤。”其《吴学士石屏歌》有一段造物与人关系的精彩表述:“虢工刳山取山骨,朝镵暮斫非一日,万象皆从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化之初难,乃云万物生自然。岂知镌镵刻画丑与妍,千状万态不可殚。神愁鬼泣昼夜不得闲,不然安得巧工妙手惫精竭思不可到,若无若有缥缈生云烟。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虢山深处石。惟人有心无不获,天地虽神藏不得。又疑鬼神好胜憎吾侪,欲极奇怪穷吾才,乃传张生自西来。”虢州工匠终日辛苦,才令石屏能映射万象,由此想到造物创造万物也极尽艰难思虑,还因怜惜将奇石珍藏,诗人一面坚信人只要有心探求就能获得,一面又怀疑造物是故意让人得到,好让自己为赋咏石屏耗尽才能。这类诗歌从题材、手法到风格都受韩愈很深影响,对造物形象的塑造显然更为复杂生动。苏轼诗歌中也有对这种探究造物的尚理精神的继承,其对造物和自我的思考,也可以说有时代的特色。
而属于苏轼自己独创的充满诙谐意趣的造物形象,从前文已知,一方面表现在消解造物的严肃性和权威感,另一方面则是在省思自嘲中消解自我与造物严肃紧张的关系。这也是苏轼认识外界和自身的一种重要观照方式,这种视角,与他超然乐观的性格气质相辅相成,令造物的诙谐意趣内蕴丰富,也深刻影响了同时及后世诗人对造物的表现。苏门文人的交游酬唱以雅谑擅戏著称,而以诙谐的笔法刻画造物,以超脱自嘲的态度看待造物的影响,也成为他们诗中的某种共识。如前文提到苏轼曾以“天公戏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开解黄庭坚的眼疾,黄庭坚便也说“化工见弹太早计,端为失明能著书”(《子瞻以子夏丘明见戏聊复戏答》),埋怨造物为了让自己效仿左丘明著书,竟然急着让自己得了眼病。又如黄庭坚《书蔡秀才屏风颂四首》其三:“此翁家世印累累,平生俯视造物儿。堪笑痴人不省误,犹说此翁真个痴。”也采用了造物如小儿的表达,赞扬了蔡秀才俯视造物的超然大智。张耒《二十三日晨欲饮求酒无所得戏作》:“张君所欲一壶酒,百计经营卒无有。夜来客至瓶已空,晨起欲饮还戒口。努力忍穷甘寂淡,人间万事如反手。百壶一醉有底难,造物戏谑君须受。”全篇以自嘲的口吻描述求酒不得的艰难,然而无论求酒还是醉酒本来都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此反差只能视为造物的戏谑,人对此也无可奈何,一笑置之。
至南宋时期,诗人更是经常用轻松诙谐的笔调去表现造物形象,包括细腻刻画造物人性化的行为和情态,以及表现诗人与造物戏谑调笑的情感交流。其中以杨万里最为典型,诚斋体以对自然生动灵性的描写和天真新巧的机趣著称,与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诗人与造物的关系也是如此,如“天公要饱诗人眼,生愁秋山太枯淡”(《夜宿东渚放歌三首》其三),“天公念子抄诗苦,借与朝阳小半窗”(《戏赠子仁侄》),“我欠天公诗债多,霜髭撚尽未偿它”(《送彭元忠县丞北归》),可以看出杨万里继承了苏轼对造物亲近诙谐的态度。又如“造物那能恼我曹?软红尘里漫徒劳。是中却有商量处,且道青原几许高”(《题王季安主簿佚老堂二首》其一),“也知口业欠消磨,造物嗔人奈口何”(《野望二首》其一),“造物嗔侬先遣去,遣侬侬去不须嗔”(《问涂有日,戏题郡圃》),杨万里笔下的造物仿佛更加情绪化,常常对诗人嗔怪着恼,不过造物又并未真能因为嗔怪就随心所欲地支配诗人,纵然它会责怪人、驱使人,人却也可以轻松地回应自己也很无可奈何,或是与造物商量,呈现出平等随意的伙伴关系。杨万里同样善于消解造物本身的严肃权威,诙谐地描绘造物创造万物的过程,如《题桄榔树》:“化工到得巧穷时,东补西移也大奇。君看桄榔一窠子,竹身杏叶海棕枝。”《观张功父南湖海棠杖藜走笔三首》其三:“天工信手洒明霞,若遣停匀未必佳。却得数株多叶底,殷勤衬出密边花。”造物可以是有些捉襟见肘的,要靠补救拼凑,还可以是信手挥洒的,又像真正的画家一样有着高明的艺术安排。当然,由于杨万里和苏轼的观物方式和创作观念仍有很大不同,二者对造物的诙谐表现也有些许差异,总的说来,杨万里在以细腻生动的笔法发掘造物的行为、情态和心理方面有着长足发展,而在自我省思方面则不似苏轼那么强烈明确。此外,苏轼独创性的视造物为小儿游戏的表达,几乎成为习用语,如“造化小儿真薄相,市朝大隐亦长贫”(陈与义《谢杨工曹》),“但将生死俱拈起,造物从来是小儿”(陆游《五月初病体益轻偶书》),“中有天下险,造化真儿嬉”(范成大《燕子坡》),“造物小儿真恶剧,痴顽老子久摧颓”(方岳《病起木犀已谢》),“造化小儿不耐闲,阿兄阿姊一似颠。两手双弄赤白丸,来来去去绕青天”(杨万里《行路难五首》其五)。无论是对自然还是人生命运,诗人纷纷用这一形象描述造物的轻松随意,和调侃造物与自身的关系。有时诗人还出以新奇的表达,比如杨万里说“万事乘除里,千年瞬息中。请君明著眼,造物一狙公”(《阻风泊舒州长风沙二首》其二)。狙公朝三暮四,造物反复无常又本质恒定的特性都浓缩在这一语词中,其诙谐意味又与小儿游戏的表达一脉相承。总之,在宋诗对造物的认识和书写中,除了尚理的特征持续发展,还有诙谐戏谑感大为加强,苏轼在其中具有关键性地位,他基本奠定了造物形象的诙谐意趣及其主要表现方式。
诗人对自然和外物的认识和表现方式是一个复杂深广的问题,作为思想丰富、性格鲜明、才华横溢的文化巨人,苏轼的观物方式形成也有很多因素影响,本文难以一一辨析。不过,苏轼诗歌如何表现造物的形象及其与人的关系,无疑是认识他思想性格和诗歌艺术创新的一个有效角度。苏轼以人格化的手法表现造物具有人的心理、局限和弱点,在反差中消解造物的严肃性和权威感,怀着平等友善的视角与造物亲近互动,并在省思自嘲中消解自我与造物紧张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富有诙谐意趣的造物形象。正如苏轼达观幽默的人生态度深刻影响了后人的文学和精神世界,他塑造的诙谐造物形象也在后世诗歌中被发扬光大。这种创造及其深远影响,从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角度,反映了宋诗艺术内涵和精神内涵的深入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