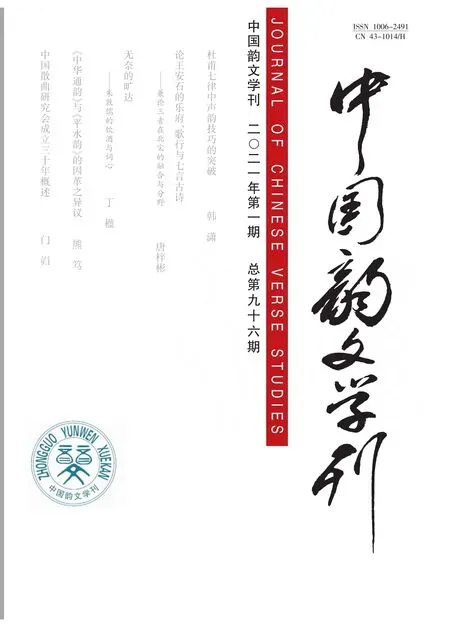唐代青海军城的文学价值
邓小清,李德辉
(1.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2.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一 引言
唐朝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在北边置八个节度使,下辖多个军镇,每个军镇所在地各有军城一座,用于驻军防守,《旧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唐会要》《册府元龟》所记累加多达二十多个。以上是作为军镇的军城。此外又有作为军事防御堡垒的军城,如朔方三受降城、灵州赫连城、泾州连云堡、陇右石堡城,都是史上有名、唐诗有载的。而西北沿边灵、夏、泾、原、邠、宁、鄯、河、廓、兰诸州州城,都高大坚固,更是重要军城。这些军城建置以后不久,就为文人所瞩目,到过的和未到过的,都来写作。基于此,在唐代,出现了一类题材类型和思想内涵都很特别的诗文,曰军城诗文,包括写军城本身的,写军城人物、事件、生活的,名篇有王昌龄《山行入泾州》、严武《军城早秋》、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张籍《筑城词》、白居易《城盐州》、李涉《题连云堡》、许棠《题秦州城》、罗隐《登夏州城楼》等。诗之外,还有纪功碑铭等。但由于作品零散,对这些作品过去从未从军城文学角度探讨过。至于专论某个节度军城诗文的,更是闻所未闻,这就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这些军城牵涉到唐史和唐文学,其研究基础相应地也有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史学研究开展较早,基础较厚。学界以严耕望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对唐河湟青海交通地理已有详尽考证,但文学研究基础尚弱。目前能看到的都是从某个意象或作者入手的,总体印象仍不清晰,价值也不清楚,本文可以稍稍补救这些不足,并引领进一步的探索。
二 唐代青海军城三个层面的文学价值
青海军城指唐前期陇右道驻军防守之城。《旧唐书·地理志一》所载,有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九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新唐书·兵志》所载,有镇西、天成、振威、安人、绥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临洮、莫门、神策、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积石军十八,平夷、绥和、合川守捉。而据《唐会要》及《太平寰宇记》等,这份名单还不齐全,颇有遗漏。估计各个时期所置累加,多达二十多个。作为文学研究对象,其价值不仅在于军城本身,还在于以它为中心,连同下面的烽燧、镇戍、堡垒、馆驿,都进入唐代文学视野,成为表现对象,拓展了唐代文学题材、主题和表现领域。析而论之,青海军城的文学价值在于三个方面:
(一)唐诗今典、军事意象
首先是作为唐诗今典、军事意象,供文人驱遣。陈寅恪先生认为,典故原有古典和今典之分。古典咏古事,今典写今事,但其具有的特殊含义和各自的适用面则是一致的。十多年前,有学者指出,研究古代诗文,既要能溯源而上,准确找到作者所用的前代典实,挖掘其文本含义,也要结合作者身世及时代,探究其所用词的情境,发现作品中隐含的今典,包括作者自身的和所在时代的。若是借鉴这一观点来看问题,则唐陇右道军城,有多个作为当代典实而进入唐诗,于写实叙事之外,还带有诗歌意象特征,能概括不同的事物和现象。其中表现突出的当数临洮、河源。临洮甚至还进入晚唐两宋诗,变成沦陷区的象征,表达不能收复失地的国耻,具有多个象征意义。这里拟以临洮为例略做说明。
临洮唐以前就有,但仅仅是个西北州县名。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晋书·地理志上》等,秦汉魏晋间,临洮是一个县名,在陇西郡临洮县,秦长城最西端。北周到隋为临洮郡,古西羌之地,非军城地名,更未进入文学领域。唐诗中的临洮则是陇右道军镇,一座军城,全称临洮军,在唐鄯州城。因而有先唐边疆地名临洮和唐代军事意象临洮之别。军事意象临洮兼具军事地名意象和当代典实特征,有数十首唐诗提到过。最早始于开元中,如王昌龄《塞下曲四首》其二:“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写日暮黄沙中所见临洮军城的黯淡身影,性质跟卢纶《晚次鄂州》中的“云开远见汉阳城”一样,都是远望所见。王昌龄开元中期曾北出萧关,前往河西。后又游历陇右,前往鄯州,到过临洮。《国秀集》卷下收此诗,即作《望临洮》。《国秀集》编成于天宝时,用的应是原题,表明此诗是纪实的,“黯黯见临洮”乃写实之笔。由于诗人意在借此边地渲染战场气氛,故临洮还有地名意象特征。属于写实的还有高适《送白少府送兵之陇右》:“践更登陇首,远别指临洮。”《送蹇秀才赴临洮》:“料君终自致,勋业在临洮。”这是因两位友人要前往鄯州军城临洮,才举以为实。其中的临洮作为陇右军镇的代表,有文化地标意义,内涵实中有虚。李白《白马篇》:“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
诗中的临洮则是虚拟,泛指游侠少年所历西北边镇,诗人想象的那里的情形。其《子夜四时歌·冬歌》:“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以临洮指夫婿从军的西北边地,主旨则在抒发闺思,同样属于象征泛指。其《胡无人》:“十万羽林儿,临洮破郅支。杀添胡地骨,降足汉营旗。”写唐代禁军远赴西北边地杀敌卫国,临洮在诗中不过作为边地象征物。《文苑英华》卷一九六题作《塞上曲》,其前为吴筠诗,这个诗题更表明临洮代表塞上,二者同义。杜甫《喜闻官军巳临贼境二十韵》:“花门腾绝漠,拓羯渡临洮。”亦是为了对偶而提炼的措辞,不过借临洮形容回纥的骁勇、迅猛。时当肃宗朝,为了尽快消灭叛军,朝廷征用安西、回纥之兵入援。据《九家集注杜诗》卷一九,花门代表回纥,拓羯代表安西。但其自安西入援,乃走河西驿道,并不经陇右临洮,故杜诗这里的临洮也是一个象征地名、军事意象。“腾绝漠”“渡临洮”云云,不过借以言其自安西前来助唐军之路,表意的意图明显,也有这方面的功效。
这些诗中的临洮都不是指唐前古临洮,也不是普通地名,而是指唐军城临洮。除了高适、王昌龄诗偏于写实外,李白、杜甫诗都不是。他们笔下的临洮是西北战地,唐蕃争战之场,是有背景、有故事的地名,其使用可看成是用典。其中李白《子夜吴歌》《白马篇》还是乐府诗,这更值得注意,因为乐府诗一向重模拟,喜泛写,一般不指向实际人事。一旦进入乐府诗被反复使用,那就意味着意义由实转虚,大家可以共享,普遍性要大于特殊性。临洮具备了上述特征,因此是一个代表性的军事意象。
以杜甫为界,唐人对临洮的使用就由实转虚,泛指边镇。杜诗作于至德、大历间,此后至于贞元、元和、大和、大中,作者相继。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近闻》:“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侵临洮。”前诗中的临洮子指临洮一带骁勇善战的羌胡少年,不一定来自临洮。后诗中的临洮则为实指,指唐蕃交战前线,因临洮军城首当其冲,故举以为言。到元和、会昌中,文士就将临洮摄入乐府诗,作为常用语,泛咏不同的人事。令狐楚《从军词五首》其三:“却望冰河阔,前登雪岭高。征人几多在,又拟战临洮。”李德裕《寒食日三殿侍宴奉进诗一首》:“楛矢方来贡,雕弓已载櫜。英威扬绝漠,神算尽临洮。”皆以临洮指代与外族有争战的西北边镇,脱离原意。此后是这一用法的延续。陈陶《陇西行四首》其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临洮本在陇西,唐前临洮更是陇西郡下属县,故陇西在这里跟临洮义近,扫匈奴实指战吐蕃。钱珝《春恨三首》其二:“久戍临洮报未归,箧香销尽别时衣。”二诗作于僖、昭宗朝,一个抒写夫婿久戍不归的春恨,一个虚拟唐蕃陇右争战,都是虚拟,临洮在诗中都是陪衬之物,象征战地,固化情境,并不在乎实际地望为何。以此二诗为收束,唐诗中的临洮完成了由军镇地名到文学意象的转换。令狐楚以下的四诗中,有两首是泛咏人事的古题乐府诗,更表明其虚化程度之高。
再看河源,其情形与临洮有同有异。唐前文献中的河源指在青海的黄河源头,见《山海经》及《汉书·张骞传》、《西南夷传》,不过云河出昆仑而已。唐人所记亦呈两分状态,虚拟的多为辞赋、送别诗,用古典,指传闻之地河源;写实的多为叙事,用今典,是军城地名,性质不同。天宝以后的唐诗中,河源更多地脱离古意,转向写实,指青海河源军,具有地理意象特征,用来概括唐代文官的边地生活,事主经历的某种境界。如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贾至《送友人使河源》:“河源望不见,旌旆去悠悠。”李端《奉送宋中丞使河源》:“部领河源去,悠悠陇水分。”都是写官员出使河源军,与古义无关。此外又有写出使吐蕃的,因河源军地当唐蕃交通要路而在诗中提到。如皇甫曾《送汤中丞和蕃》:“陇上应回首,河源复载驰。”郎士元《送杨中丞和蕃》:“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汉垒今犹在,遥知路不迷。”所写均为出使吐蕃的使臣路过河源。尽管内涵是虚拟的,但还是昭示了河源作为一方山川代表的意义。这是它的文学价值之一。这就如同华阳、黑水代表北方,玉门、阳关代表河西、西域一样,汉唐青海最有代表性的地理景观确是河源。它本来就是传说中的黄河源头,加上在地理方位上还有代表性,代表青海这个战略方向,故唐人诗文举以为言。
河源在唐室建置陇右节度使后被军事化,唐代军人及幕府官员往来陇右,练兵备战,并与唐蕃外交活动结合。因而还有一部分作品写唐代边镇军人和文人出使青海,奉使吐蕃,具有远戍、远使、远役之义。但作者多未亲历,只是在作品中提到它,这又是实中有虚。如景龙中送金城公主赴吐蕃和亲的《奉和圣制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作者为李峤、崔湜、刘宪、张说、沈佺期等十三人,即是如此。闺情诗如皎然《拟长安春词》:“春信在河源,春风荡妾魂。”咏物诗如万楚《骢马》:“朝驱东道尘恒灭,暮到河源日未阑。”边塞诗如张仲素《塞下曲五首》其四:“乡关万里无因见,西戍河源早晩休。”赠别诗如法振《河源破贼后赠袁将军》:“蔓草河原色,悲笳碎叶声。欲朝王母殿,前路驻高旌。”都是泛指。中晚唐河源早已不为唐有,河源在这里都是作为象征地名,代表京西边镇。
除了临洮、河源两个最著名的军城书写较多外,唐诗中写到的青海军城还有积石(赵彦昭《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洪济(高适《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莫门(高适《同吕员外酬田著作幕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等五六座。部分诗歌,不写军城本身,而写军镇内的村落、集镇、古迹、驿站、桥梁、津渡、堡垒、戍楼。比如戎昱《塞下曲》:“上山望胡兵,胡马驰骤速。黄河冰已合,意又向南牧。嫖姚夜出军,霜雪割人肉。”“塞北无草木,乌鸢巢僵尸。泱漭沙漠空,终日胡风吹。战卒多苦辛,苦辛无四时。”“晩渡西海西,向东看日没。傍岸砂砾堆,半和战兵骨。单于竟未灭,阴气常勃勃。”从内容看,都是青海西的古战场景色,但以形象化的写景抒情为主,故而并未出现军城之名。吕温也有《经河源军汉村作》《题阳人城》《题石勒城》等,均作于其贞元二十年出使吐蕃途中。《经河源军汉村作》:“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作汉村。樵采未侵征虏墓,耕耘犹就破羌屯。金汤天险长全设,伏腊华风亦暗存。暂驻单车空下泪,有心无力复何言。”《题河州赤岸桥》:“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钟受恩者,谁怜被发哭东流。”这也是一种写法,一种表现形态。前诗中的旧河源、千家汉村、征虏将军古墓、破羌屯,后诗中的左南桥、河州,均在青海境内,所以仍属对青海军城内部地域文化景观的一种趋于细化的书写。虽然和二十多个军城相比,这样的书写仅占少数,但这只是基于现存5.2万余首唐诗所做的判断,仅占唐人实际创作的三分之一不到。考虑到唐诗亡佚过多,现存唐诗只是其中少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再加上还有部分唐诗,虽然内容涉及某座陇右军城,但在诗题中仅以陇右、青海、边城等词来泛指和概括,而不直接以军城本名出现,所以仍不妨碍这一结论的成立。鉴于唐人对青海军城题材的多样化处理,唐诗文献的亡佚过多,同时考虑到唐诗文献记载的复杂性,我们仍可认定,唐青海二十多座军城,丰富了唐诗的描写对象和题材内容。
以这些词汇的使用为标志,形成了一个西北边疆文学语汇的新体系,拓展了唐诗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这是其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这些词语虽然也有虚拟想象意味,但跟六朝初唐边塞诗还是不同。六朝初唐边塞诗,过于重视模拟前代作品,泛咏前代人事,从人名、地名到事名都是虚拟的,缺乏现实生活的根基,感情浮泛,语气夸张,文人意气过重,减损了它的价值。唐人笔下的河源、临洮、积石等,则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实实在在的军事化地名,有着大量的唐蕃交战的历史背景和事件做支撑,其虚拟是虚中有实,以实带虚,不是完全的虚拟泛咏。六朝初唐边塞诗,绝大多数使用唐以前就有的乐府诗题目,从标题、题材、主题、意境、辞藻、人物、事件,都是袭用前代,驰骋文辞,绝少和实际生活挂钩。唐代青海军城诗,则多为边地纪行,写景,写人、送别、酬赠、唱和之作,多数都有具体的人事指向,有着很实在的现实生活背景和内涵,这跟六朝到初唐边塞诗那种惯见的后代人模拟前代出师征战还是有很大不同的。由于只是适度的想象虚拟,所写皆以西北边防军镇生活为基础,人物和地域、史事的关联度较高,结合较紧,这样就一定程度上祛除了凭借想象手法带来的泛咏色彩和浮夸意味,可以增添作品的象征意义和概括生活的面,对于这种做法,应予肯定。
唐诗今典方面,则可举哥舒、石堡为例。哥舒指哥舒翰。他自天宝中立功陇右后,就声名鹊起,成为诗中的文学题材。李白在天宝后,有《哥舒大夫颂德》《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颂其军功。二诗中的哥舒翰都带御史大夫官称。哥舒翰加官御史大夫,是天宝十三载后之事,故李白此二诗亦天宝十三至十四载所作。十五载冬安史乱起,哥舒翰在潼关出战,投降叛军,李白态度立即转变,说“函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批评其身为名将,不能为国死战,却开门纳敌,实在不该。杜甫的态度也是先褒后贬。他天宝十三载,率先写出《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极力称颂其人品军功,并无半句不满。安史之乱中作的《潼关吏》则说:“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树为反面典型。《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二亦提及哥舒翰攻拔石堡城事,以为有副作用,不利和平安定。其《送高三十五书记》:“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表达反战态度。前后之间,判若两人。思想观点看似进步,实则不顾边防实际,是迂腐见解。对此,宋人早有议论针砭。王观国《学林》卷七《言行》条即曰:“圣贤言行,要当顾践,毋使自相矛盾……杜子美《投赠哥舒开府翰诗》曰:‘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先锋百胜在,略地两隅空。’又作《潼关吏》诗曰:‘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此所谓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者耶?”讽刺杜甫以贵贱论人,持论前后矛盾。高适的立场则前后一致,均为赞扬称颂。其《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对哥舒翰破黄河九曲胡及破洪济城二役大唱赞歌。以上表明以哥舒为中心的话题,已构成盛唐军事文学的热点,在不同文人、不同时期激起不同反响,引发较大争议,具有丰富含义。
到了中唐,随着河西陇右万里江山的相继沦陷,哥舒翰及其陇右军城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变成中晚唐文人怀念、追忆、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表达各种主题,思想内涵深广,格调沉重悲怆,一改从前的高昂。元稹有《西凉伎》:“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哥舒在他笔下成为盛世的象征,并被用来和衰落了的唐朝对比,表达今夕盛衰的感慨。薛逢《感塞》:“满塞旌旗镇上游,各分天子一方忧。无因得见哥舒翰,可惜西山十八州。”将哥舒视为能守边御敌的名将,感叹晚唐西北边将无能,不能替天子分忧,导致州郡沦陷。可见哥舒一词李杜以来即为今典,文人多用,含义由实转虚,具有典故和意象特点,文人出于各自目的,赋予不同含义。而自天宝乱离之后,以贬义居多。哥舒翰是唐陇右军城的符号。尽管是个人名,但价值等同于军城,视为同类名词,未尝不可。
石堡是和哥舒、陇右相连的另一关键词。最早用例也是李白诗。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指天宝八载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晋升陇右节度使。天宝以来,石堡成为著名今典。同类作品有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石城与岩险,铁骑皆云屯……唯有关河渺,苍茫空树墩。”写天宝十二载哥舒翰在陇右道击破吐蕃,收复洪济、大漠门等城及九曲部落。西鄙人《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作者不可考,作年亦当在天宝八载哥舒翰收复石堡城后数年中,当和前引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及高适诗等量齐观,属于同一性质、同一批次作品,乃今人写今典,歌咏盛唐名将的显赫军功。这背后的典实是,哥舒翰天宝六载擢陇西节度副使、河源军使,在积石军大破吐蕃,此后军功日盛。天宝八载六月,擢陇右节度使,攻拔吐蕃石堡城。十二载,封凉国公,加河西节度使。因事迹突出,天下传扬,他和他所在的陇右军城被视为唐代武力达到极盛的代表。唐朝政府天宝十二年七月为他颁布的授官进爵诏,称赞他“屠城拔垒,靡有孑遗。收九曲之旧疆,开千里之沃壤。亭障卧鼓,既成禁暴之勋;屯田馈军,以益封财之用”。也正是因为这种非凡军功激发了自豪感,哥舒翰本人也写这类题材。其中写到石堡、雕窠等城,言及这里的战事。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一批作品就是代表。据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卷二《杂曲》,署名哥舒翰的《破阵乐》,不署名的《定乾坤》《春光好》《定西蕃》等,或明或暗都有对陇右军城的题咏。如哥舒翰《破阵乐》:“西戎最沐恩深,犬羊违背生心。神将驱兵出塞,横行海畔生擒。石堡岩高万丈,雕窠霞外千寻。一唱尽属唐国,将知应合天心。”为少见的六言律诗,中间出现了石堡城和雕窠城两座军城,都外形高大,形势险要。石堡城在西宁边外,鄯州河源军西百余里。本吐蕃铁仞城。开元十七年信安王祎攻拔之,二十九年为吐蕃所陷。天宝八载哥舒翰攻拔之。雕窠城则是河西军城,在天成军西百余里。天宝十三年,哥舒翰攻吐蕃置,再振威军,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此诗乃将陇右石堡城和河西雕窠城合而言之,主题转为杀敌立功,和传统的边塞诗接近。据《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黄进德《说哥舒翰破阵乐》考证,《破阵乐》乃初盛唐军乐,用于献俘奏凯,国宴时演奏。哥舒翰用此调写歌词,肯定含有借此弘扬国威之意。
这表明到天宝中,以临洮、石堡为代表的陇右军镇已从军城名晋升为文学意象,脱离原意,具有象征性,指远在青海、接近吐蕃的陇右军城,当从文学意象和典故类型上去把握它。
(二)唐代西北边镇纪实文学的关键词
自从唐朝在青海设陇右边镇后,这里就受到文人关注,出现了与之相应的纪实文学,写真人实事,现实感和地域性都很强。关于青海的战事很长时间内都是唐人诗文记述的重点和讨论的热门话题,题材和趋向上呈一致性。类似这种重写实、多讽谕的特点,与同在西北的以河西、西域为对象的边塞诗大异其趣。只因这种文学不重虚拟,所写过于实在,导致今人不大关注。古来确实只有边塞诗的提法,很少见到边镇文学的说法。只是不提并不等于没有,高人雄等学者早在十多年前即提出了这一概念。结合学界论述来看,边镇文学属边地文学的一种,记载西北部边地军镇自然、社会、人居生活,是一种纪实文学,跟边塞诗不同。边塞诗为文人意气之作,以驰骋想象为之,并不跟现实直接挂钩。边镇文学则为纪实之笔,平凡琐碎,想象和虚拟派不上用场。唐代在北部和西北建有八个节度使,中晚唐又从中分立出十多个节镇。如此多的军城镇戍,还存在过两百多年,又处在唐代这样一个“诗的国度”,自然就产生了与之相应的边地文学,以纪实诗为主,兼及其他体裁。写作对象则是史书记载的唐陇右道二十多个边镇。这么多军城,必然对唐文人和文学发生影响。这数十个军镇及守将、镇戍、堡垒、馆驿,如唐蕃交通路上的莫离那录驿、众龙驿、刘驿、婆驿、勃令驿,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军事文学价值,是唐青海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
析其内容,一为写边镇之作,重在描写地域、塑造人物、叙述事件, 如写陇右道名将哥舒翰、王思礼。其中写王思礼的为杜甫《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司空岀东夷,童稚刷劲翮……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敌。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马鞍悬将首,甲外控鸣镝。洗剑青海水,刻铭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转深壁。飞兔不近驾,鸷鸟资远击。”写王思礼武艺不凡,拔石堡城,征九曲,建立军功,兼河源军使。核之以两《唐书·王思礼传》,可证杜诗所述可信。相比之下,写哥舒翰的要多得多。最早将其纳入文学的是王维。其《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曰:“上将有哥舒大夫者,名盖四方,身长八尺。眼如紫石稜,须如猬毛磔。指扌为而百蛮不守,叱咤而万人俱废。髬髵奋髯,哮吼如虎。裂眦大怒,磨牙欲吞……然孤烽远戍,黄云千里。严城落日而闭,铁骑升山而出。胡笳咽于塞下,画角发于军中,亦可悲也。”据陈铁民《王维集校注》,此文作于天宝十二载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后。尽管是想象之词,但在外貌描写上是成功的,跟韩翃诗可一比,而且有对河陇军城环境和社会面貌的描绘,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却写景如画。至于人物形象塑造,最好的当推韩翃《寄哥舒仆射》:“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腰垂紫艾缦,手控黄金勒。高视黑矟公,遥吞白骑贼。先麾牙门将,转斗黄河北。帐下亲兵皆少年,锦衣承日绣行缠。辘轳宝剑初出鞘,宛转角弓争上弦。步乂(《唐诗品汇》卷三二作“人”)抽箭大如笛,前把两矛后双戟。左盘右射红尘中,鹘入鸦群有谁敌。杀将破军白日余,回旃舞旆北风初。”是一首出色的歌行,塑造了哥舒翰忠勇无双的英雄形象。核之以新、旧《唐书》之《哥舒翰传》,发现所言不虚,故可纳入边地纪实文学范畴。
另一种写法则是以叙事为主,兼带写景写人。这方面,高适堪称典型,他有五首诗写哥舒翰破吐蕃战功。其中《九曲词三首》为七绝组诗。《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云:“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连弩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写陇右道战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二载五月壬辰条云:“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高适诗所记即此事。他的另一首诗《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则为五古,写天宝八载破吐蕃洪济城,作年略早。以上史事都轰动全国,众多名将参与。唐史中反复提到的洪济城、大漠门城,就是两个有故事、有来历的青海军城,唐代史籍、唐人诗集及行记均有记载。《旧唐书·吐蕃传上》:“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张忠亮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与吐蕃接战,大破之。俄而积石、莫门两军兵马总至,与忠亮合势追讨,破其大莫门城,生擒千余人,获马一千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二年三月“丁亥,皇甫惟明引军出西平,击吐蕃,行千余里,攻洪济城,破之”。句下胡三省注:“杜佑曰:廓州达化县有洪济镇。周武帝逐吐谷浑所筑,在县西二百七十里。长庆中,刘元鼎为盟会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济西行二千里,水益狭,冬、春可涉,夏、秋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历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他水并注,则浊。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隐测其地,盖在剑南之西。’”这段引文就是写黄河源头河源地理情形的。从文学上讲,也是青海边镇写实文学富有时代、地域特色的部分。
边地纪实方面也不乏佳作,但都是在纪行框架中展开的。高适《同吕员外酬田著作莫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就是如此:“碛路天早秋,边城夜应永。遥传戎旅作,已报关山冷。上将顿盘阪,诸君遍泉井。绸缪阃外书,慷慨幕中请。能使勋业高,动令氛雾屏。”用五古体式,将田著作在青海莫门军西盘山旅馆夜宿的情景生动描绘出来,附带写田著作的生平和为人,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情形。吕温《临洮送袁七书记归朝》:“忆年十五在江湄,闻说平凉且半疑。岂料殷勤洮水上,却将家信托袁师。”写他出使吐蕃途中,在临洮军城送别使府掌书记袁同直自陇右归京,托其带回家信,顺带言及平凉之难。平凉之难和吕温使蕃都是唐朝大事,对这类事件的记述增强了诗歌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其《青海西寄窦三端公》亦作于青海西的使蕃路上,云:“时同事弗同,穷节厉阴风。我役流沙外,君朝紫禁中。”写远役的辛苦、流沙的空旷、阴风的惨厉,境界独特,内涵实在。以上均写时事。此外,未到过陇右但接近陇右的诗人亦偶有涉及。如杜甫《东楼》:“万里流沙道,西征过北门……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写通吐蕃的驿路从秦州经过。戎昱《泾州观元戎出师》:“朔野长城闭,河源旧路通。”写代宗朝泾原节度使出师作战,从交通地理涉及河源。
二为其他题材诗,一般不正面描写,而只顺带提及。送别诗如崔日用《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俗化乌孙垒,春生积石河。”张谓《送卢举使河源》:“故人行役向边州,匹马今朝不少留。”以上二诗,分别作于中宗、代宗朝,河源在这里是边镇名称。使边诗如员半千《陇头水》:“路出金河道,山连玉塞门。旌旗云里度,杨柳曲中喧。喋血多壮胆,裹革无怯魂。严霜敛曙色,大明辞朝暾。尘销营卒垒,沙静都尉垣。雾卷白山出,风吹黄叶翻。将军献凯入,万里绝河源。”接连出现八个军事意象,当为作者使边途中所亲见。游边诗则写中晚唐文士漫游边塞,如朱庆余《自萧关望临洮》、李昌符《登临洮望萧关》,写边镇路上景色。诗中的临洮跟玉关、萧关具有同等的美学价值。
三是纪实文章和纪行著述,主要有碑铭、行记、表状三种体裁。碑铭可考的有两篇,均为陇右纪功碑铭。一件是《哥舒翰纪功碑》,出盛唐文士之手,天宝中立。《通志·金石略》最先著录,云在熙州。尽管现存不到百字,但历来受重视,当代学者亦加以研究。另一件为现藏美国菲尔德博物馆的八棱碑,题为《石堡战楼颂碑》,天宝八载七月立。1906年在甘肃洮城出土,后被美国人劳费尔获得。碑文记录了唐朝收复石堡城的战役,现仍有部分文字完整。所记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相合,但有其中所无之细节。如其中谈到,唐军收复石堡城后,在城内修建战楼,“三旬而成”,即他书所无。
行记则是出使吐蕃的外交官撰写,记载跨境交通,政治意义重大,外交色彩浓厚。由于涉及敌国外交,其中含有民族情绪。只是今存残文已被前人改写,删去了那些主观色彩强烈的部分,只剩客观叙述文字。《存研楼文集》卷七引中唐贾耽《皇华四达记》,略云,由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为吐谷浑界。又经暖泉烈谟海,四百四十里乃渡黄河东北,距振武凡八百十里。此即其中的一段残文。其行文格式采用道路里程+地理景观的模式,每段行程自为一个单位,每个单位选择几个代表性景观记述。其中最具实感的,恰恰是那些军城、驿站。更完整的记载则见《新唐书·地理志四》陇右道鄯州鄯城条,云城为“仪凤三年置。有土楼山。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吐浑界也”。两段引文提到的军城、古迹,多达九个。最引人瞩目的,恰恰是那些有故事、有地域特点的军事地理建置,正是这些荒废了的军城、堡垒、驿站作为古迹,引发行人驻足停留。依照当今学者研究,凡是出使敌国外交官所写行记,都有家园温情、本国美景、故国颓败、敌国蛮夷等多重意蕴,及民族、国家意识。这种情绪在生成机制上,恰恰都是触景生情的,景点是否有历史感、现实感、时代感,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彰显出青海军城在外交行记中的地位作用。又唐德宗朝张荐出使吐蕃行记,亦属此类。原书虽亡,但《旧唐书·张荐传》存有残文,云:“(贞元)二十年,吐蕃赞普死,以荐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吊祭使。涉蕃界二千余里,至赤岭东被病,殁于纥壁驿。”所引即其行记残文。其中提到的驿站,在《册府元龟》中还可见到,属唐陇右道交通地理建置。《太平广记》卷四九七引《(大唐)传载》:“张荐自筮仕至秘书监,常带使职。三入蕃,殁于赤岭。”既然他曾三使吐蕃,按照当时外交制度,必有行记记其使事。类似这种出使西北行记,也是边地纪实文学的重要品种和边镇文学的重要方面,当对其存亡加以考述,对其价值合理地评估。
表状也是出使吐蕃外交官撰。如吕温永贞初使吐蕃,在陇右路途撰的《代都监使奏吐蕃事宜状》:“右臣前月十四日,至清水县西,吐蕃舍人郭至崇来迎,便请将书诏先去。臣以二十一日,到薄寒山,西去蕃帅帐幕二十余里,停止……加以接待殷勤,供亿丰厚,竭诚归化,形状可知。臣亲睹蕃情,不胜庆跃。绮里徐等固欲令臣与薛伾领蕃使却归奏事,臣当时苦争,请赴衙帐……即于今月五日,令臣与张荐分背便发,彷徨中路。”所述内容就有多处提到陇右道地名,而且和其出使吐蕃路途所作之诗,在写作对象和情感内涵上具有同一性,可以互相映照,诠释对方,将其纳入陇右边镇文学加以探析,未尝不可。
以上三类作品,在性质和写法上都与边塞诗不同。边塞诗多虚拟概括,不写具体人事,以河西西域为对象,青海军城则始于唐,故未进入边塞诗境域。青海军镇,仅青海一词因汉以来旧有,唐诗中多见,其他的都不见踪迹。查《乐府诗集》,更可确证此点。如河源,即呈两分状态。谢朓《从戎曲》:“选旅辞车睘辕,弥节赴河源。”以河源指军士所赴西北边地。沈彬《入塞曲》其二:“生希国泽分偏将,死夺河源答圣君。”以河源指河源军,唐代典故,“死夺河源”指与吐蕃争夺河源军。沈彬是五代诗人,诗为乐府,其所用河源军已乐府化。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可知在乐府诗中,凡提到陇右军城的均为泛用,实用的例子则分布于其他领域,表明用于纪实仍是陇右军城的重要价值,偏于写实仍是陇右军城诗文的重要特性。
(三)中晚唐陷蕃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
陷蕃文学是书写陷入敌国的中原王朝土地、人民生活和情感的文学,盛于宋代,但其起点则是中唐河西陇右。中唐前期,随着河陇万里江山陷落吐蕃,成千上万唐国子民成为沦陷区遗民。五代北宋随着契丹崛起,国土沦陷,大批中国士人被俘。随后的对峙讲和及遣使交聘,更让中国士人深入外国,备尝艰辛。包羞忍耻成为其诗文的鲜明特点,隐痛感和忧愤感成为普遍的抒情基调。这批文学最早的源头,即在青海。陷蕃文学历来以悲伤愤激为特征,常用对比反衬手法突出中外华夷差别,表现沦陷区人民对故国的怀念。而这种悲愤感、隐痛感的触媒,有很大部分就是陷落蕃中的地理景观。前朝的军城镇戍陷蕃以后,都被荒废。如有中华士人路过,必然触景生情。从创作成因和机制上讲,地名、人名、事名是陷蕃文学纪事抒情议论的三个基础。唐陇右道军城及其管内的镇戍、堡垒、烽燧、馆驿,就有这样的价值。唐顺、宪宗朝吕温使吐蕃诗,唐穆宗朝刘元鼎使吐蕃行记,就是陷蕃文学最早的作品。其诗文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作者过路所见的故垒。刘元鼎行记已佚,但佚文仍可考见。《旧唐书·吐蕃传下》:“是时,元鼎往来,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新唐书·吐蕃传下》:长庆二年,刘元鼎使吐蕃,“踰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元鼎踰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过石堡城,崖壁峭竖,道回屈,虏曰铁刀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而信安王祎、张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独虏所立石犹存。”三段引文,提到七个地名。其中属军事建置的有哥舒翰故壁、石堡城、封石三个。刘元鼎作为唐朝使节,路过此地,见到陷蕃的唐朝子民,百感交集。陇右道的军城、堡垒、烽燧、馆驿、关津、道路、桥梁、界碑、封石,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抒情的触媒。历史和现实在这里对接,理智和感情在这里碰撞。作者面对这些古迹,不能不激发出关切、焦虑、痛苦、矛盾、渴望恢复、感慨边事、有心无力等复杂情怀,于是在纪行文字中叙事感怀,发表议论,一改唐人西北行记单纯叙事、平面客观描述的固有风格,变得有个性,有内涵。其中出现的场面,我们在宋人出使辽金行记、诗歌中多次看到。其中“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一段,跟陆游词《关山月》“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范成大使金纪行诗《州桥》“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所绘情景神似,可视为此类场面的唐代版本。类似这方面的作用,就与陇右军城的性质、特点有关,是唐陇右道军城文学价值的重要侧面,将其纳入唐代陇右文学体系,十分必要。
三 结论
综上,唐代青海军城是有独特文学书写价值的军事地理建置,由此产生的唐代作品,偏重于写青海地区的人物、事件、古迹、山川、城郭,带有边地色彩和军事意味,题材、词汇、境界都不同于传统的边塞诗,属于西北边地文学的新境域,其出现弥补了边塞诗偏重虚拟,不重写实的不足。文学视阈中的唐代青海军城,价值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唐诗今典和军事意象,丰富唐代文学的内涵、意象、题材和主题;二是作为唐西北边镇纪实文学的关键词,从不同层面反映唐青海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政治军事态势和外交形势;三是作为唐后期陷蕃文学的书写对象,表达陇右道百姓渴望恢复失地,振兴国家的意愿,为这方面主题思想的表达起到奠基作用。这批军城作为一个历史存在,凸显了唐青海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其内涵既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一面。实在的地方是能反映社会、政治、时代、地域特征,虚的一面在于文化上的象征性:既作为唐代国力军力强盛的表征,见证了大唐帝国的强盛;也作为被遗弃的前朝古迹,见证了大唐帝国的衰落,沉淀了历史、国家记忆和民族意识,其文化意蕴和文学价值都值得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