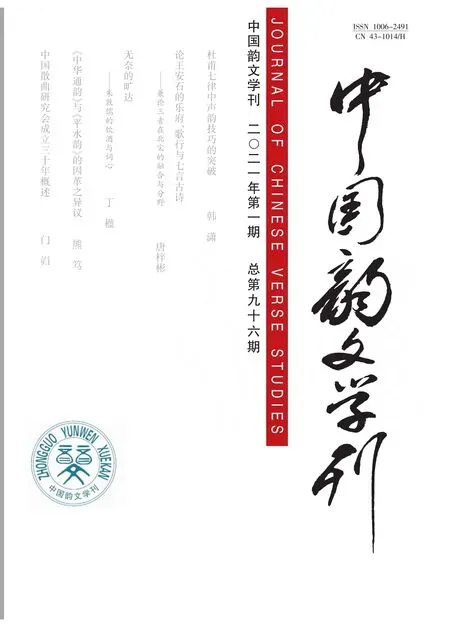篇章转句与诗境生成
——论陶渊明诗歌的“转势”效应
汪雯雯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将陶诗置于现代学术语境中,则可发现,学者对陶诗的文献版本及流传、诗史考证、陶诗哲学内涵及其背后的人格范型等方面,已有较为全面的探索和揭示。然而,诗歌给予读者的整体上、直觉性的感受,直接诉诸其间的话语体系、纹理脉络、结构层次等形式特征。当前的陶诗研究主要着眼于诗作本身“反映了什么内容”,对“如何反映”关注不多。反观历来的陶诗评点及诗法、诗话等传统诗歌批评理论著作,颇多以诗歌体式为核心,以诗歌句法、篇法、结构等为对象的审美分析。虽然此类评点式分析往往不够重视理性的逻辑建构,但因其建立在对审美对象进行深入观照的基础上,故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准确性。本文拟以传统诗话诗评中有关陶诗“转势”的论述为基点,尝试对陶诗“转势”的表现、风格的生成做出论述。
一 早期五言诗的篇章结构及“转势”的提出
“转”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范畴,涉及文本内部结构的形制特点。西晋陆云《与兄平原书》首次论及篇章中的转句:“文中有‘于是’、‘尔乃’,于转句诚佳”,“云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这里涉及两个层面,一是通过虚词的使用来顺承语意,二是通过四句一组的形式来强化节奏,推动文章的内容转换。陆云此处论及《登楼赋》《感丘赋》《吊夷齐文》等文、赋,尚未触及诗歌。事实上,篇章结构的承接与内容的转换关系着诗歌的写作,并影响着诗歌风貌的形成。
文人创作五言诗,大盛于建安时期。建安五言诗内容主要包括出行、观景、宴会、相思、游仙、人生感伤等经典话题,在篇章展开上则以历时性线性顺序为主。大量的建安五言诗在篇章形制上通过四句一转来实现场景内容和叙述方式的转换。如曹丕《杂诗》(漫漫秋夜长)前四句提供时空场景,交代夜中出行的背景;其下四句总写月夜所见,后四句又具体分述所见之物象;随后,秋夜之物候感发了思乡的情绪,诗人化用乐府古辞“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来深化悲伤情绪;最后两句以直抒胸臆作结。除最后两句外,全诗基本上以四句为一个语意单位,诗歌的展开以时间流动及“外在物感——内心体验”为逻辑层次。陈琳《诗》(节运时气舒)以登高远望开篇,转入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而后又进入建功立业的主题,以“外在”至“内在”的逻辑展开,主题的转换较为明显。晋代以来,诗歌篇章层次较汉魏诗丰富,但部分诗作在内容、话题的转换方面依然层次分明。如陆机《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主要由构建离别场景来交代缘起,其后进入建安诗歌中常见的出行主题,最后由景至情,层次了然。
出行主题的诗歌中,魏晋诗人在表现自我行迹时,常直接点明诗歌展开的逻辑结构,并形成对举,如西晋枣据《诗》中“徙倚凭高山,仰攀桂树柯。延首观神州,回睛盻曲阿”四句,将诗人的活动顺序一一点明;陆机诗中“南归憩永安,北迈顿承明”、“朝游忘轻羽,夕息忆重衾”、“朝游游曾城,夕息旋直庐”等用以交代行迹;东晋梅陶《怨诗行》中“晨悦朝敷荣,夕乘南音客。昼立薄游景,暮宿汉阴魄”,将时间落实为“晨”“夕”“昼”“暮”,并以此作为诗篇连缀的时空逻辑。虽在外在形态上获得了齐整与统一,表现手段和句式的重复却增加了诗作的繁赘之感。
与魏晋诗在语意推进和切换上呈现出的线性推进与对举式并列相比,陶诗利用“转”,使诗歌在内容表现和技艺上至于新境。陶诗的“转势”建立在诗人高度的艺术自觉中,通过变化及转换构成“势能”,叠加诗境。“势”的提出,首先在于书法领域,旧传蔡琰记载其父蔡邕的言论“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说明势是书写行为的主要推动力量。卫铄在《笔阵图》中,列举了七种笔画形象,将一笔一画同自然势能联系起来。可见,势能蕴含了结构方面如生发、照应、起伏、开合等多重关系。《文心雕龙·定势》对文学领域中的“势”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刘勰称写作需“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即认为势作为文本的表现形貌,构置于“情”“体”的结构框架之中。运用恰当的规则和方法,适应体的内在需求,因势利导,而致“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规,矢激如绳。因利骋节,情采自凝”的艺术境界。势包孕着运动、变化,黄侃称《定势》篇中所言,“皆言势之无定也”,说明势既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审美规范,又在变化中腾挪跌宕,无固定准则。
古人对陶诗善于利用“转势”早有揭示,这些评论涉及陶诗语意的转换和推进、诗歌内容展开次序的变化等层面。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称:“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析之以炼字炼章,字字奇奥,分合隐现,险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黄氏主张去掉概说和印象式的结论,从字、句、章等层面入手体察陶诗,方可体察陶诗结构上分合隐现、险峭多端的特点。其弟子沃仪仲评陶诗,也注意从章法承接的角度分析评说,如评《杂诗》(其八),谓其“一句一转,古诗之最变幻”。王夫之《古诗评选》评价《读山海经》(其一),称“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二句“安顿尤好”,说明句意的安顿、诗篇的结构直接关系着诗歌意境的生成。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对陶诗句意的转换揭示得最为明显,评《还旧居》诗称:“陶公诸感遇诗,都说到极穷迫处,方以一句拨转,此所以为安命守义之君子也,而章法特妙。”在评价《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时,邱嘉穗着眼于陶集,提出陶诗的“转势”:“陶公诗多转势,或数句一转,或一句一转,所以为佳。”除以上所列各处外,对陶诗“转”的说明散见于各类诗话诗评著作中。陶诗的标题、小序等副文本与正文本之间的转换与补充,古人也有涉及。本文在讨论时,也尽量将生成诗境的各个要素纳入研究视野,以期对陶诗“转势”的讨论能较为深入。
二 逐层转折:思想的驳诘与语意的推进
陶诗的转势,首先表现为语意的逐层转折及诗歌末尾骤起转势。陶诗以思想的驳诘与融通贯穿于诗作的内在叙述理路当中,因为前后句意都围绕着一个问题申述陈说,语意上形成层层转折之势,诗思向更深度推进。相当一部分陶诗在内在语意的转换推进中,消解了外在主题转换的痕迹,同时生成文本跌宕起伏、诗思深刻精炼的特征。
以咏史诗《咏三良》为例。该诗开篇即谓:“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通过写士人在时间、出仕、功名之间取舍的矛盾心迹,来表现三良与秦穆公君臣关系背后的复杂意味,“乘通津”“但惧”“服勤”“常恐”等处,通过语意的迂回转换,真实地描摹出三良殉葬背后的复杂心理。《陶诗汇评》对此体察尤确:“起六语愈折愈深,愈深愈危,一结主知,不得不以身殉,《黄鸟》之诗,所以哀且怨也。”《采菽堂古诗选》称:“将写遇合之情,起四句先作两折,以见结主知之难,用意深曲如此。孰谓陶诗为近?”更加揭示出语意的转折构成情感的“深曲”。《岁暮和张常侍》一诗,袁行霈将其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此年刘裕弑安帝于东堂而立恭帝。细味此诗,开篇的“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将生命之暮年融于岁暮之悲中,同时暗含时事,具有多重情感内蕴。然在表现时,诗人并未作平面单一的抒发,而是通过层层转折来表现情感的深沉:“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吴瞻泰《陶诗汇注》评价曰:“前曰‘凄’曰‘感’,曰‘愁苦’,曰‘无以乐’,穷通之虑深矣!忽又曰‘靡攸虑’,故作一折,以归于‘迁化’。结又曰‘增慨然’,自悲自解,已复自悲。”诗人在“靡攸虑”和“由化迁”的自我慰怀后,仍不免“增慨然”,使得情感的刻画极有层次。这几句依凭诗人的情绪感受向前推进,外在主题的转换几乎消失,读者仿佛也被裹挟进了层层叠叠的情感体验当中。《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也有此类转折,该诗从“丧室”至“乌迁”,叠写苦况,后忽截一语曰“在己何怨天”,似无可怨;“何怨”后,复说“忧凄目前”,又无一不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在“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后,转为对现实处境的体认:“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经历了“无一可悦”的情绪低潮,诗人又复振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流露出对古代高人志士的追慕;“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遗烈之崇高德操非己所攀求,仅谬得其固穷之节操,此处又作一顿挫;“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则在顿挫之中复又扬起,反问隐居于衡门之下岂为拙乎,意谓对自己隐居生活的认定。《陶诗析义》称此诗最后几联章法跌宕而富有张力:“无一可悦,俯首自欺;时见遗烈,昂首自命。非所攀,又俯首自逊;苟不由,又昂首自尊。章法如层波叠浪。”
陶诗善于通过交织的情感矛盾,来体现思想上的复杂性,其语意的层层转折也使诗歌摆脱外在逻辑的架构,因而呈现出更高的融合度。《东山草堂陶诗笺》在点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时,称“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四句“逐句作转”,而“其他推类求之,靡篇不有”,也说明陶诗善用语意的转换来推进诗歌议论的深度。《连雨独饮》是诗人对外在之身、永恒之天运、系于俗世之情等多重客体的一次深刻思索,开篇称:“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人生处于运行不息的天地之间,如同匆匆过客,终究会走向尽头。故老赠酒,却言“饮得仙”,此与开篇形成转折,也蕴含了一重可能性。诗人饮酒的感受正如故老所言——“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这使开篇的生命焦虑有了些许的消释;然而继又以问句锁接:“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此处构成第二重转折,从内在主体出发独守任真之心,才能达到与自然运化合一的境界。《陶诗析义》称:“曰‘忘天’,曰‘天岂去’,曰‘无所先’,三语三换意,生尽之感,天实为之,一觞未能忘也,重叠则忽忘之矣。”由“运生会归尽”转至“忘天”,又由“忘天”引至“任真无所先”,在肯定与否定的交织中,最后归于生命主体顺应自然的精神境界。
陶诗语意上的层层转折,多体现为陶诗对身、名、情等哲学命题的思索。陶诗往往叙写诗人“如何解决思想感情上的种种矛盾”,最终“由矛盾趋向和谐”。如《杂诗》(其八)开篇谓:“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从自身原本的期望与当下所从事的田桑之业入手,形成一重转折;第二重转折集中在农事活动与实际收获之间的反差上,“未曾替”和“常糟糠”构成一重带有戏谑意味的对举;第三重转折则建立在第二重基础上,意谓只希望果腹而已,并无更高之奢求——诗人在重重转折中坚定自己的志愿,故沃仪仲评价此诗曰:“一句一转,古诗之最变幻。”对身、名、情等的探讨在陶集中十分常见,“我躬谅不阅,身后欲何处”“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等处,均体现出陶诗对以上哲学命题的思索。因为身之短暂,渊明对名是看重的,其隐居于衡门之下的人生选择与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不冲突;而又因身之短暂,渊明对名又不执着,“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等处,诗人乃至完全在否定“名”的意义。陈寅恪论渊明的思想属性为“外儒而内道,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渊明处于儒家、道家以及佛教空无思想的交织当中,作为寒素士人,其对自我人格的植立与认同又使他表现出对“名”的豁达态度。在陶集中,我们常可见诗人在反问、诘问、设问中表达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如: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
(《己酉岁九月九日》)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己酉岁九月九日》)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饮酒·清晨闻叩门》)
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
(《影答形》)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影答形》)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神释》)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拟古·日暮天无云》)
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
(《饮酒·子云性嗜酒》)
方与三辰游,寿考岂渠央。
(《拟挽歌辞》(其一))
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
(《咏贫士·荣叟老带索》)
陶诗在不断否定与肯定、设问与反问、申述与陈说中讨论生命存在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类命题。陶渊明的思想具有多重维度,在思想的困境中往往做到入而能出。对于生活,诗人有躬耕实践和对于苦难的体验,有对人事的深情,这种思想和认识上的深刻性及复杂性实现了议论的层层递进和抒情的委婉曲折,构成了陶诗层层转折的实质。
三 骤起转势:视角转换、结构突破与语意变化
陶诗骤起转势,主要指诗歌打破惯常叙述方式,利用视角转移、语意情感转换、篇章结构跳跃等方式,与前文构成转势,从而扩大诗歌内涵,增强诗歌兴味。如果说陶诗中的层层转折主要表现为语意的转换推进,在于诗歌的深度,骤起转势则使诗歌通过时空的转换增强诗歌表现力和范围的广度。以下拟分述之。
1.视角转换增强文本张力
松浦友久称中国诗的节奏是在“一字一音”的“音节节奏”的基础之上,“二字一拍”的“拍节节奏”在律动着。除此之外,诗歌的“意义节奏”引领着读者遨游于诗歌所表现的意义时空当中。以视角的转换方式而言,则有时空方位的变化(由近转远、由远至近、由今至昔、由古至今等)、实与虚的转换等。以《停云》为例,全诗开篇写“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天空中凝聚不散的乌云和蒙蒙如网的雨丝投射在人的心灵上,带来压抑的感受。“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则将一种似乎近在眼前的实景无限推远和扩大,呈现出尺幅万里的广阔境界。魏晋大量诗歌通过“仰观”“俯视”“朝”“夕”来加以变化,但其对偶属性则使其意义限定在两句构成的语意圆环内,难以延展。
诗人在创作中,一方面控制文本,使其超出读者的惯性意识领域,另一方面又将其统一在一定的逻辑框架中,从而构成文本的腾挪变化之势。《答庞参军》是诗人和庞参军相识不久后所作,诗云:“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二人虽相处不久却志同道合,情谊深厚。诗人借答庞参军阐明自己的心志:“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唯旧,弱毫夕所宣。”开篇至此,诗人娓娓道来,颇有“散缓”之致。其后,诗人从实景实境中跳脱出来,宕开一笔,“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从近处实境推向远处,更从高处落笔,将二人友情渲染得高远深沉。此后接“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又回到二人的对话世界中,充满深厚的离情别意。陶诗善于通过镜头的拉伸或时空范围的转变来升华情感,《和郭主簿》(其一)结尾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从美好闲适的居住环境开始写起,继而写生活条件,园中蔬菜和旧日稻谷,虽不富裕,但诗人已然知足,加之“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故曰“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该诗最后一联将视角从当下推至远处,“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诗人遥望白云,思绪也随之远去,遥想古人之高迹,“其意远矣”。由于陶诗根植于生活的实境之中,尾联的转势得以凸显出更多的意味。
伴随着空间距离的拉伸转换,从生活实境中提炼而来的诗思使诗歌形成由实至虚的转势。《还旧居》写渊明于六年后返回昔日上京故居,诗人首先在旧迹中怀想往日,感慨今夕:“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此后,诗人突然将视角拉至人的生命长河之中,“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以宏观俯视的视角来看待人生的流迁幻化,诗人复又感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比起诗歌前半部分实写,此处明显作一转。《归园田居·其四》写归田园后同子侄辈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诗人由“步荒墟”所见之浔阳一带农村的残朽破败的遗迹,即景就事,“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用语质朴,当日之情景宛然在目。如果说其后“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是针对前面与薪者的对话而产生的感慨,是具体的、有特定所指的,那“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这句则是建立在对人生透彻领悟基础上的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称:“彭泽虽承汉、魏骨法,至夫叙实情有从容深远之妙,则前后无匹俦矣!”汉魏古诗中也常常有以“人生”开头的,抒发普遍性悲剧意义的诗句,但与之相比,陶诗更讲求从生活场景中脱化而来。陶诗从对实情的刻画中显示出深远之境,则需要自然地转换远与近、当下与追忆、情与理等多维视角。
2.语意情感的顿转形成诗意回味空间
除通过设问、反问、诘问来表现语意的层层转折外,陶诗常常在最后一联调转语意,打破读者预期的文本秩序,使文本的可联结性粉碎,“展现出一种数目不断增多的可能性”。如前文所列举的《还旧居》,当诗人由在旧迹中怀想往日的实境转向“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的人生观照后,诗末又一转,将视角从宏观俯视中拉回,“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又回到当下触手可及之处,让人重新体会到生命的真实无奈。陶渊明对酒的执着毋庸赘言,它们常集中在诗歌的最后一联,表现出和前文不一样的情感况味。《拟挽歌辞》(其一)设想自己“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的死后场景,发出“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的感慨,诗意已经完整,诗人却一转,以近乎诙谐的语言想象死者的遗憾:“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这样,对生命的达观就充溢于此诗当中,方东树称“结句收转,倒具奇趣”。《责子》一诗也是以轻松诙谐而略带责备的语气历数生活之不如意,不仅“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五个儿子也都无法让人称心,在事实面前,诗末转言:“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诗中的酒帮助诗人从尘世中超脱出来,获得平静自足。再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此诗描绘的是晋安帝义熙四年(408),一场大火烧毁了诗人住所后的情景和诗人的所思所感。“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写火灾情景,诗人由火灾引发心灵的触动而表达自己的心迹,其后开始遥想上古理想社会,“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东户”指的是尧时的诸侯东户季子,其时民风淳朴,衣食无忧。当意识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后,诗人立马转向现实世界,“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既然遇不到那样的时代,那还是种我的菜,浇我的园吧。结句的拨转体现出诗人面对现实的态度,其人格境界和诗歌境界也随之自然流露。这种“厚积薄发”式的蓄势转换打破了与前文的惯性联系,从而生发更多的空白及可能性,又因为此类句子常处在诗末,故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诗意回味空间。
3.篇章结构的跳跃与转换叠加诗境
传统五言诗的展开主要依赖的是历时性线性推进的方式,这形成了五言诗尤其是汉魏五言诗的古意。陶诗在主要保持汉魏五言诗特质的同时,又通过内容的跳跃,及其对传统写作顺序的突破获得了不同的诗歌风貌。《读山海经》(其一)就有语意的切换和层叠。诗云: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诗人从幽居的自然环境开始叙写,“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物我情融,充满情趣。诗人继写自己的耕读生活,“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王士禛认为“车大辙深,此穷巷不来贵人。然颇回故人之驾,欢然酌酒而摘蔬以侑之”,颇贴合此处诗意。“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在写乐趣无穷的生活实境后,诗人没有继写读《山海经》的情景,而是转接“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与汉魏以来五言诗景与情往往分并的写作方式不同,“微雨从东来”二句夹在“摘我园中蔬”和“泛览《周王传》”之间,正使诗再宕一层。《古诗评选》称“微雨从东来”二句,“兴会佳绝,安顿尤好”,若系之“吾亦爱吾庐”之下,则作“两分两搭,局量狭小”,正是从篇章结构与诗境生成的角度来看待其艺术效果。《古诗评选》曾批评潘岳《悼亡诗》《河阳县作诗》等诗作“一情一景,一今一昔,自以为经纬,而举止烦扰”,王夫之认为潘诗的展开顺序因过于落实而略显呆板,其从诗歌内容的展开方式与诗境生成的角度批评潘岳之作,正可帮助我们理解陶诗之佳处。
《岁暮和张常侍》《与殷晋安别》《拟挽歌辞》(其三)等诗同样体现了景的布置与内容切换对于诗篇意境层叠的影响。《岁暮和张常侍》中“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洌洌气遂严,纷纷飞鸟还”,两联紧扣诗题中的“岁暮”而发,置于整首诗的议论当中,打破了魏晋惯常的诗歌写景结构。《别殷晋安》中,诗人在感慨与殷晋安“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后,转而去描摹天空中的风和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古诗赏析》称:“‘飘飘’四句,透写到路途迢递,后会难期,忽插风云两喻,势更展拓。”风与云既是实写,又暗喻二人,在其渲染下,诗的意境再度升华。《拟挽歌辞》(其三)开篇设想自己出殡的途中环境,“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此后诗人直接点出事件——“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以保证诗歌意脉更为流畅。在“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后,诗人复转写环境的凄凉肃杀,“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也是对魏晋五言诗写作景情分并的突破。方东树评价此曰:“‘风为自萧条’一句,在俗手定将‘风’字夹写在‘荒草’二句之内,只是一层惨”,陶诗的处理方式使得“其惨又加一层矣”。就人综合的心灵感受而言,外在世界的物象和人的主观意识并非直线式、机械地由景到情、先景后情,“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交织层叠的情况或许更加符合人的审美感受的逻辑。
陶渊明的组诗创作尤为丰富,将组诗看成一个整体,考察其间的结构层次,则可体会组诗的结构构思和转换。在124首陶诗中,五言组诗8组共72首,占陶诗五言诗的六成。当诗歌专注于探讨一些哲学命题时,采用组诗形式就会起到叠加层次,变平常为奇崛的效果。如对生死的探讨,本来是玄风影响下诗歌的常见主题,陶渊明采纳组诗形式写作《形影神》,合理安排结构层次,将此类主题推向新的哲学高度。《陶诗析义》称:“诗心之妙,在三首互换,腐理恒谈,顿成幽奥。‘得酒莫苟辞’,若从《影答形》言之,有何深味,移置形赠,观影以耽酣酒,幻致奇情,层叠无限。”诚如黄氏所言,“得酒莫苟辞”追求的是形体之乐,置于《影答形》中,则不能体现“形”与“影”不可调和、互为矛盾的关系,也就不能表达“人类面对死亡时所遭遇的矛盾、困惑与多维性”。组诗的结构性意义极有可能是诗人自觉结撰的结果,《咏贫士》《读山海经》《杂诗》等组诗的第一首与其他各首有别,也呈现出其间的照应生发关系。如《读山海经》(其一)写的是幽居自得的读书生活,十分具有田园风味,而其余各首则是就具体的读书内容所发感慨。第一首既统摄组诗,也与其他各首互为变化,更添组诗神采。
余 论
陶诗以议论或情感表达的需要来架构诗篇,在语意、句序、结构等方面通过转势达到诗思精炼又张力无穷的艺术效果。陶诗的诗题大量地采用纪实的方式具体记录写作时间、事由,如《戊申六月中遇火》《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等,客观上与陶诗以大量议论抒发日常生活的哲理互为转势,彼此中和。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开篇即阐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的生存哲学,将“道”与“衣食”并举,意义极不寻常,但照应标题,则有议论源自生活实践之感。钟伯敬评价陶诗《有会而作》“妙在有会而作,命题旷远,而序与诗,句句是饥寒衣食之言,真旷远在此”,也说明诗题与正文本之间呈现的转势能生发更多的诗意。陶诗常通过小序来交代创作背景,小序帮助读者理解诗歌的正文本,也与正文本形成照应。《陶诗析义》评价《停云》小序称:“序曰‘初荣’,诗曰‘再荣’,序曰‘不从’,诗曰‘靡从’,意义同异,互相阐发。”《游斜川》序中“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与正文本中的“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情感上互为补充,均体现出陶诗的灵动与多维。
陶诗较少对外在逻辑结构的确认和说明,诗作本身也难以用层次分明的主题内容进行分隔,其融合度和整体性较高。“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陶诗以更高层次的内在逻辑关系统摄全篇,因而诗作即便因“转势”而获得丰富与层叠的诗境,也不会流于芜杂。《古诗评选》称:“平者,取势不杂,淡者,遣意不烦”,以此概括陶诗的“平淡”,可谓独具只眼。叶嘉莹称《咏贫士》(第一首)从孤云到贫士“有三层的转折跳跃”,可见诗人心中的情思意念“在沿着这样的轨道跳跃流动”;葛晓音也认为陶诗“以感情逻辑贯串丰富的内容”,从而“消解了复杂结构的层次感”,以上均是对陶诗这一内在特征的揭示。事实上,陶诗所体现的变化并非凭空而来,其对汉代古诗有所继承。如《古诗十九首》往往通过诗歌的第一句交代场景或缘起,如“今日良辰会”“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等,但在其后的展开中,作者并没有把相关场景安排成明显的叙事序列来加以表现,而是选择“描绘对这些场景的情感反应来表达内心体验”。另外,阮籍《咏怀》诗从语意上看,比起魏和西晋的其他诗作,句与句之间的跨度已经拉大,也有诗思的跳跃。但陶诗与以上二者相比,更注重通过对生活实境的描写蓄势,故能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以议论为主体的陶诗,则注重通过对哲学命题的多面考察以及在肯定、质疑、否定中推进议论的深度,又注重通过生活画面和主观真情的交织,来丰富诗境。
从五言诗的发展过程来看,陶诗的展开总体上遵循着魏晋诗的特征,但同时在容纳度、跳跃性及诗思精炼度上,均有进一步的推进。陶诗通过转势使诗歌呈现出动态的多维面相,并将诗歌预留的空白、诗境的层叠及丰富、诗歌展开的跳跃性最终上升为浑融无迹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