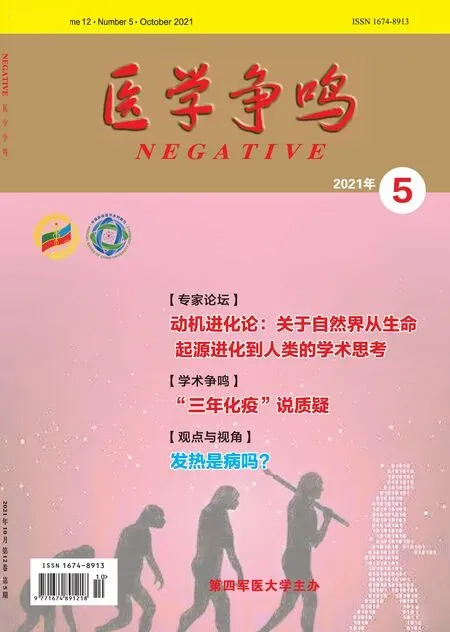象思维与《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的构建研究
王 冕,邢玉瑞(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陕西 咸阳 7046;西安理工大学,陕西 西安 70048)
《伤寒论》创立三阴三阳辨证体系,以阐释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及传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辨病证、断转归、论方药,被后世医家泛称为“六经辨证”。三阴三阳是中医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也是中医理论体系构建的模式之一[1]。《素问·五运行大论》提到:“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笔者认为,“象”不仅是研究三阴三阳本质的关键,更是构建六经辨证体系的基本元素。本文将从象思维的方法出发,对《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加以动态解读,分析其基本元素及构建过程,探究六经辨证的实质。
1 象思维及其路径
象思维是中医学区别于西方现代医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中医基础理论构建的重要方法。象思维在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界定与诠释,邢玉瑞[2]综合了各家学说,做出了较为中肯的定义:“是以客观事物自然整体显现于外的现象为依据,以物象或意象为工具,运用直觉、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以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把握对象世界的普遍联系乃至本原之象的思维方式。象思维是客观之象与心中之象的转化与互动过程,是将获取客观信息转化为‘意象’而产生的关联性思维”。
作为一种动态的思维模式,象思维遵循一定的路径和规律。王永炎等[3]将象思维的路径分为以下五个步骤:即观天地以察象、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依象而思虑与据象以辨证。这条路径概括了象思维活动的普遍规律。从象出发,总是开始于可感之象[4],即物象。象思维首先要观物,才能察象。《周易·系辞上》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下》曰:“象者,像也。”都说明物象始于形似。因此,象思维的第一步是从直观的具体现象或事物入手,观其形,察其物象。进而借助已知的外在物象,通过归纳、演绎、抽象等方式,获得意象,以阐明事物的内涵意义、功能、联系等抽象概念,即“立象以尽其意”。此处所立之“象”乃是意象。物象是具体化、形象化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在表现。而意象是抽象性的,超越性的,正如《黄帝内经》所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在得到多个意象的基础上,摆脱物象的束缚,在整体性和关联性的前提下进行理性的思考,发现联系和规律,进而构建完备的医学理论框架,是以称为“得意而忘象,依象而思虑”。以意象所构建的医学理论体系为指导,将意象体系与新的临床病症信息联系起来而进行诊断的实践活动,即据象以辨证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象思维路径中,第三步“得意而忘象”确切地说不能算作一个具体的程序或步骤,笔者认为它更像是获得意象后,要进一步“依象而思虑”的前提条件。具体来讲,在“依象而思虑”之前要抛开具体的物象,跳出物象的范围,摆脱物象对思维的束缚,寻求更抽象、更复杂的涵义和规律。邢玉瑞[5]在对象、象思维的概念及过程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象思维的基本模式有四种,更进一步地指出,据象辨证并非象思维的终极模式,“体象悟道”才是更深层次的目标,即在对某一物象或意象观察的基础上,体悟出相关的规律或大道。刘长林[6]也认为象思维的认识目标在“尽神”,即注意观察和确认事物在自然状态下的功能、信息联系,寻找自然过程本身的规律。
因此,象思维的过程或路径应包括对普遍规律的探寻,表现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据象而思—据象辨证—体象悟道。《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正是基于这样一条思维路径构建起来的。
2 象思维与六经辨证体系
象思维是《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及其临床实践过程的根本思维方式。六经辨证体系的构建过程,就是以象为基本元素,遵循上述象思维的路径,从观天地、察万物出发,取物象,得意象;再基于独立意象,构建多维疾病模型(据象而思),并探寻疾病发展和辨证施治的规律(体象悟道),最终再指导临床实践(据象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的实践过程既需要辨证规律和六经病模型理论的指导,又需要考虑具体的患者、病象、气候时令及地理环境。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反过来又会促进相关理论的发展,即据象辨证论治的反馈能够进一步完善六经病的理论模型(图1)。

图1 象思维与六经辨证体系构建
显然,六经辨证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实践经验→理论模型构建→临床实践→理论模型完善……”的不断循环反馈完善的过程。其核心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其构建过程是象思维及其路径的具体体现。
2.1 察天地万物以得物象——观物取象
《周易·系辞下》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观于天则察日月运行、昼夜交替;俯观于地则知寒热冷暖、生长收藏;近取诸身则明五脏六腑、咳喘肿痛;远取诸物则见根茎叶果、血肉有情。如此诸多具体的物象构成了古人对天地万物、时间、空间以及自身生理病理现象的最基本的感性认识,这种认识来源于直接的观察、体验、劳动实践经验以及临床经验,是意象体系构建的源泉。这些虽然未在《伤寒论》中明确提及,但却是所有意象以及六经病体系形成的认知基础。
2.2 从物象到意象——立象尽意
《周易·系辞上》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古人通过最直观的物象达到了对周围世界的初步认识,继而通过抽象、归纳等方法获得意象。意象不是直接反应具体事物的感性认识,亦非静态之象;而是通过分析、综合、抽象等方法概括而成的理性之象、动态之象,是反映事物运动、变化、功能、联系的全息之象。
《伤寒论》中的意象源于天地万物之物象,既涵盖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阴阳范畴,又包括了人体结构、功能之象,以及各种病象、证象、舌象、脉象等。
2.2.1 三阴三阳的意象后世医家将《伤寒论》的辨证体系概括为“六经辨证”。但在《伤寒论》中,每一类病的提纲并不冠以“经”字,亦未对“三阴三阳”给予任何阐释。因此,三阴三阳的本质问题历来颇有争议[7-11]。从《素问·阴阳离合论》来看,三阴三阳指足六脉。《素问·天元纪大论》又云:“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可见三阴三阳亦是阴阳之气盛衰之象。
《伤寒论》中六病的次序来源于《素问·热论》。《素问·热论》讲外感寒邪的发病及其传变,三阴三阳在这里仅仅指受邪的经络脏腑。张仲景对其做出了进一步的认识推演,从病位、症状、脉象等更多的物态之象中抽象出疾病各方面的属性,以三阴三阳为纲,属性相似的意象归纳整合,构建了六经病模型体系。因此,《伤寒论》中的六经病是疾病发展阶段的意象模型,每一经病都分别由一组或几组特定的、有内在联系和共同属性的、体现疾病本质的症状、体征所构成,是该类疾病的病位、病势、病性及病理变化的意象聚合。在这些意象模型中,疾病的空间属性应象于三阴三阳,体现在受邪部位,即经络脏腑,如太阳病的病位涉及足太阳膀胱经、足太阳膀胱腑、肌表营卫等。疾病的时间属性应象于三阴三阳,体现在疾病自愈日,六经病欲解时,疾病传变次序等。病性应象于三阴三阳,体现在六气之病、寒热表里之别等。
由此可见,象思维的“境遇性、常变性”特征[12]使三阴三阳的意象在《伤寒论》中有了多维度的衍生,最终形成了六经病意象模型。
2.2.2 “时”的意象《伤寒论》中关于六经病的排序、病因和“六经病欲解时”的论述,都体现了“时”的意象。六经病欲解之时,不仅应象于脏腑,更以一日之中阴阳消长的规律为依据。《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日月的规律运动引起了阴阳消长的周期变化,形成了人体生理病理的时间节律。这是“天人合一”理论的实际体现,也是“时”由日月运动的物象抽象为“周期”与“节律”的意象的认识过程。故《伤寒论》中六经病“欲解时”皆应象于阴阳消长的周期变化,如第9条言“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193条言“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是一日之中阳气渐虚的时段。此外,《伤寒论》中记载有伤寒、中风、温病、痉(燥)病、湿痹、中暍(中热)六气之病,此六气乃六季之气[10],由季节更替、阴阳消长而有盛衰,亦为“时”之意象。
2.2.3 人体脏腑功能意象《伤寒论》虽未详细论述人体脏腑功能,但脏腑功能之意象却常见于病机分析的条文中,是由症状分析病机的桥梁。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原序》中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五脏应象于五行,绝非解剖学意义上的脏器,而是综合了相关脏腑功能的系统意象。如《伤寒论》第180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第181条:“问曰: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此处的“胃”是整个消化功能的意象,包括胃、小肠和大肠的功能。第106条:“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膀胱为足太阳经之腑,太阳病不解,化热入里,与血相搏,结于膀胱,症见下腹部硬满,拘急不舒,小便自利,发热而不恶寒,神志如狂等。这里的膀胱却并不单指“膀胱腑”,而是指整个下焦部位,是整个下焦区域脏腑功能的意象。张仲景在《伤寒论》第124条中论述蓄血病机时,用的就是“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可见“膀胱”与此处的“下焦”含义相同,既指明了病位,又说明了病机。
2.2.4 病象辨病之“病”,应能反映某一疾病发生、发展、转归、预后的全过程,是对疾病在机体各方面发生异常变化而表现出来的象的总体认识。辨证之“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能反映机体在疾病某一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及正邪盛衰等综合情况[13]。《伤寒论》中的对疾病的论述都是先提病名,再分证型。因此《伤寒论》中的病象,包括不同的证象;而证象又反映在症状之象、舌象、脉象之中。例如:《伤寒论》第一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其中,“脉浮,头项强痛,恶寒”首先是脉象和症状之象,其次,三者构成了太阳病的病象。在这个病象的基础上,又分“无汗,脉浮紧”的麻黄汤证之证象,“汗出,脉浮缓”的桂枝汤证之证象。
同时,病象是关联的、动态的,并非孤立静止的。因此,《伤寒论》中亦可见合病与并病之象、疾病传变之象。如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以脉象(脉若静者、脉数急者)和症状之象(颇欲吐,若躁烦)作为传经与否的判断标准。又如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以阳明病和少阳病的病象是否出现作为排除太阳病传经可能性的条件。
2.3 从独立意象到六经病模型——据象而思
上文所述之意象,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随着认识的积累,独立的意象不断碰撞,不断被分析、联系、总结、归纳,最终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郝万山[14]认为:“六经病是人体感受外邪后,六大功能体系在和外邪作斗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症状和体征的综合,它既是外感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可以看成是既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证候。”六经病并不是孤立的病症,而是同一功能体系感邪后出现的疾病的综合,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每一经病都是一个小的意象体系,包括疾病发生、发展、转归、预后以及不同时期的病象(证象、舌象、脉象、症状)、治法方药等。六个意象体系相互关联、相互转化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维度六经病意象模型。六经病意象模型的构建是辨证论治的必要前提和纲领,是对人体结构、功能与大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与总结,是一种知识形态和认知结果,是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依据。
2.4 从意象模型到普遍规律——体象悟道
体象悟道,即在对某一物象或意象观察的基础上,体悟出相关的规律或大道[5]。这种规律可称之为道象,反映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或普遍规律。
六经辨证体系的核心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十二个字在《伤寒论》中虽是对变化多端的“变证、坏证”提出的施治方案,但也是整部《伤寒论》辨证施治的基本规律。郝万山[14]认为“这也是‘辨证论治’精神最明确的文字表述”。六经病体系内容庞杂而又相互关联,张仲景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体悟出这一普遍规律,对以象为媒介进行的辨证施治过程进行了高度概括。首先,“观其脉证”是通过“望、闻、问、切”等诊察方法收集临床病象;继而以六经病意象体系中的疾病模型为参照,分析新采集的病象,明确病因病机,是以“知犯何逆”,方能选择治法方药,“随证治之”。这一规律,是于纷繁复杂、变化无常的病象之中拨云见日,可谓辨证论治之精髓,乃“变中之常”,谓之大道。
2.5 从普遍规律与意象模型到临床实践——据象辨证
辨证施治的过程是六经辨证体系在临床中的具体应用与实践,是在普遍规律(道象)的指导下,通过分析新的病象与已有的疾病意象体系,来辨别施治的过程。人体感邪,在不同的病位产生千差万别的病象、证象,包括舌象、脉象及其他病理体征。但这些只是医生对该患者疾病的认知起点,通过“望、闻、问、切”获取这些信息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直接开方抓药,医家只有进一步将自己对患者舌、脉和其他病理体征的认知转化为意象,与脑海中已经建立的六经病意象体系中的相关意象进行对比分析,才能够按照普遍规律辨明证候及病因病机,“知犯何逆”,继而“随证治之”。这就是以“象”为媒介的“据象辨证”思维过程。
以脉象为例,患者自己也可以感受到脉的搏动,但患者感受到的仅仅是一种物理搏动,不能称为“脉象”。只有当医者将感受到的“脉的搏动”与大脑中“脉的意象体系”相联系,确定脉的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病象与病机,这种“脉的搏动”才能被称之为脉象,才能作为临床辨证施治的依据。王前等[15]认为:“医生手中感到的脉搏的具体形态称为‘脉’,它还不是‘象’;对脉深入体验后获得的‘象’才是‘脉象’。”此处所说的深入体验,即将脉的搏动的物象抽象为意象,并根据不同意象间的联系构建有关“脉”的意象体系的过程。《伤寒杂病论·平脉法》曰:“脉蔼蔼,如车盖者,名曰阳结也。脉累累,如循长竿者,名曰阴结也。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阳气微也。脉萦萦,如蜘蛛丝者,阳气衰也。脉绵绵,如泻漆之绝者,亡其血也。”这里的“蔼蔼如车盖、累累如循长竿、瞥瞥如羹上肥”等描述都是脉象,属于六经病模型中脉的意象体系,是脉诊知识和临床切脉的桥梁,也是脉诊的必要前提。只有深入体验后获得这些“脉之意象”,才能准确判别指下之脉是否心中脉象,而后结合其他病象,辨证施治。
同理,其他病理体征的判断也是从物象到意象的据象辨证过程。例如:“项背强几几”是张仲景根据经验总结出的太阳病的证象之一,而患者项背的感受,医生是无法感知的。因此,医家只有将患者描述“项背紧张不灵活”的语言采集、转化为意象,与大脑中“项背强几几”的意象加以对比分析,才能正确地辨证辨病,随证用方。
3 结语
六经辨证体系既包括经络、脏腑、病症、方药等较完备的知识内容,又包括辨病、辨证、辨误治、辨方药等重要思维方法。这个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皆是借助象思维方法,以象为媒介进行的。“象”是认识自然时空与人体生理病理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媒介,是构建六经辨证体系的基本元素。象思维的方法阐释了六经辨证体系的构建及应用过程。因此,六经辨证体系的实质是以“象”为媒介,以象思维为基本思维路径的解决人体多种病理问题的方法论体系。而六经病则是以意象为基本元素,阐释多种病理现象及其变化、联系和规律的多维度疾病模型。
象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模型化推理,模型的构建与推演当然离不开逻辑思维方法,六经辨证体系的建构也借助了逻辑思维的概念、命题、推理等思维形式;另一方面,由于象思维结果的或然性特征,依靠象思维所建构的六经辨证体系,还需要接受逻辑思维的审视和实践的检验。当代人们对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研究甚少,关于《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构建中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还有待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