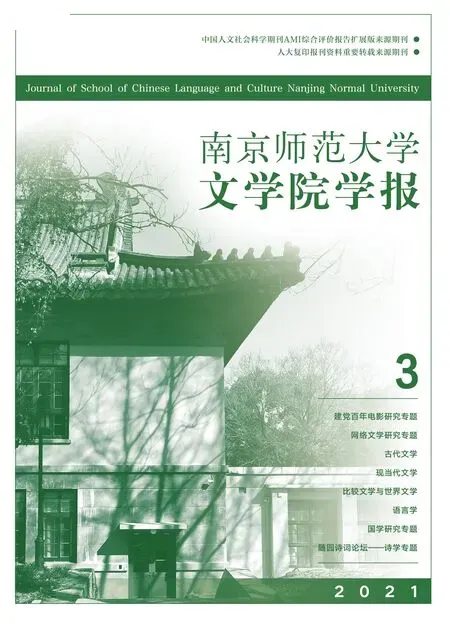宋人尺牍中的馈赠活动研究
——以北宋名家为例
付 梅
(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全宋文》中两宋私人尺牍有四万余篇,近年来各种文史资料中也不断有尺牍佚文出现,宋人尺牍数量之丰可见一斑。这些存世尺牍作品不仅包含丰富的史料价值,也有着深广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境界。褚斌杰先生《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说“一方面它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十分真实而有益的历史资料,大可以见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人情世态;小可以见一个人的思想、性格以及在正式传记中所不易了解到的一些细微方面;同时,也可以从那些书牍文的名篇中,学习语言的精妙和立言的得体等等”[1](P403),拥有巨大的文学研究价值。若我们走出纯文学的范畴,站在文化史、制度史、风俗史、礼仪文化的综合视角来看尺牍,它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的。尺牍之中往往包含着大量物质文化方面的历史信息,即伴书之“信”,这些信物以实际内容补充著书信的文字内容,构成书信交游完整的面貌:书以传情、信以致意,两者共同完成文人之间的各种交游活动。将书、信各自孤立,是无法看出它们的真实功用与效果的。
在宋世文明大辉煌、物质极大丰富的背景下,以及宋代“举世重交游”交游群体及覆盖面极度扩张的前提下,宋人尺牍数量空前,所包含的物质信息也空前丰富。存世宋人尺牍尤其是名人书简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涉及友人之间的馈赠往来。宋人尺牍之中这类内容更为丰富,以北宋三位尺牍大家兼文坛盟主为例,见下表:

表1.两宋尺牍大家礼赠物资往来简表(1)诸人尺牍总量以《全宋文》及各种最新辑佚成果为依据总结,如《欧苏手简》、天理本《欧阳文忠集》等。
欧、苏、黄是北宋士大夫最杰出也是最典型的代表,同时他们也是尺牍大家,在宋代已有尺牍单行本传世。同时他们的尺牍所涉人物之多、物资之丰富,是两宋尺牍的代表。存世尺牍涵盖了他们一生出处、情感、交游、生活诸多层面,是我们了解这些文坛盟主以及以他们为轴心的整个时代士人生活最真实细微处的第一手材料。欧、黄二人存世尺牍之中半数以上涉及礼赠往来。苏轼尺牍之中也有近两成涉及相关内容。可见宋人尺牍涉及礼赠物资往来内容的比率是相当高的,这些礼赠应酬所涉及的人员、内容、方式等,对于我们研究尺牍施受双方的社会关系、生活状况,乃至整个宋代社会风俗、人际交往、风土物产、生活水平、饮食日用、医疗保健等各个方面,都是可靠而直接的第一手材料。由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尺牍的功能除了传统的沟通、交流思想与情感之外,也承担着礼尚往来、维系人际关系的重任。尺牍本身就是结交礼仪的一个环节,又作为载体,承载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这些礼物往来与尺牍文字相结合讨论,才能真正复原宋代士大夫交游的完整画面以及尺牍在社交生活中的真实应用功能与价值所在。下面我们通过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将欧苏黄三人尺牍之中涉及的各种馈赠活动进行综合量化分析,力求对三人乃至宋人的经济消费生活作一个剖面观察。
一、欧阳修尺牍中的礼赠活动
一代名臣韩琦、范仲淹,宋代诗文革新领导者梅尧臣、石介等皆是欧的密友,宋六家其五皆是欧的门人,欧阳修自己的交游圈辅以他的门生三苏(苏门)、王安石的交游圈几乎网罗了北宋一代所有重要人物。作为一代文宗,“天下翕然效之”[2](P215),欧阳修的交际圈之大,涉及人物之多可想而知。而存世的欧阳修书简744通,从对象上看,囊括了同时代大部分名人;从时间上看,起于天圣六年(1028)入京求知,终于熙宁五年(1072)溘然长逝,这些书信比较均匀地覆盖了他的一生,详实记录了他一生履历与各种交游活动。对研究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交际活动是有直接参照价值的。
在欧阳修存世的744通书简中,有304通涉及物资往来,占全部尺牍数量的40%。可见礼尚往来、物资交流是欧阳修日常生活中相当重要的活动,也是其书简重要内容之一。这304通书简所涉物资大致可分为十类,内容涉及衣食住行、文化娱乐、日用器具等各方面,包含着北宋前、中期文人的主要交游娱乐活动、经济水平、日常生活、时代风尚等种种信息。具体而言,包括诗文、著作(自著、他著、前人文献)228种,书画(自书、他书、前人名家书)、金石、碑刻(自刻、他刻、前人名刻)67种,食物果品(粮食、生鲜肉类、肉干、蔬菜、酱料、熟食、干果、水果)28种,器具物资(生活用品、生活物资)35种,药物药方(药材、汤药、丸药、药剂)24种,茶17种,文房、器玩18种,酒9种、其它20种及不详(统称为土产、珍物)10类464种。其中诗文248种高居榜首,在所有的馈赠往来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可见这是欧阳修日常交游的主要方式,也可知书信往来也是宋人诗文作品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两百多种诗文,基本都是以文字方式伴随书简传递,但还有24种是以刻石及拓本的方式往来的。可见北宋士人不仅将诗文著作文本当作礼赠来与同仁互动,诗文的刻石拓印也蔚为时尚佳礼。这一点在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尺牍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金石碑刻在宋代的兴起离不开欧阳修的实践与倡导,这一点在他的尺牍之中时有体现。其存世书信随处可见他到处求碑:“县境有好碑,试为访之,别后所收必多也”(《与张职方三之三》)、“蜀中碑文,虽古碑断缺,仅有字者,皆打取来”(《与王懿敏公仲仪》十七之五)、“闻金陵有数厅梁、陈碑,及蒋山题名甚多,境内所有,幸为博采以为惠”(《与冯章靖公》八之六)。为了“投其所好”,亲友也纷纷为他找寻,这就形成了书简之中礼赠物资的第二大类:金石碑刻。这类投其所好的馈赠令欧阳修雀跃,如《与刘侍读(原父)》二十七之二十六(嘉祐七年):
某启。昨贤弟行,尝奉状。属合宫大礼,前后事丛,遂阙致问。昨日进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书,窃承动履清胜,兼复惠以古器铭文,发书,惊喜失声。群儿曹走问乃翁夜获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恶之异如此,安得不为世俗所憎邪!其穷达有命尔,求合世人以取悦,则难矣。自公之西,《集古》屡获异文,并来书集入录中,以为子孙之藏也。幸甚幸甚。岁律渐寒,惟为时自重。[3](P2429)
刘敞(1019-1068)字原父,是北宋著名经学家,欧阳修的忘年交,二人结交于皇祐年间欧阳修组织的聚星堂诗会中,此后往来频繁。欧集中存与刘敞书简27封,多涉及诗文唱和与金石碑刻,可知诗文与金石之好是他们之间共同爱好。欧阳修自言“故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集古录跋尾·伯囧敦》)、“最后成余志者,原甫也”(《集古录跋尾·韩城鼎》),《集古录》中有多种金石都是刘敞所送。两人之间往来物品有24种之多,涉及诗文、碑刻、食品、药物、书画等数种类型,往来可谓密切。
从欧阳修涉及礼赠内容的尺牍来统计,与欧阳修物资往来密切程度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1)挚友梅尧臣,41通86种;(2)挚友蔡襄20通37种;(3)好友刘敞24通36种;(4)好友韩琦20通35种;(5)僚友吕公著14通14种;(6)僚友王素13通17种;(7)长子欧阳发13通49种;(8)内兄薛仲儒10通9种;(9)僚友王益柔5通10种;(10)僚友张洞4通13种。其他绝大多数人与欧阳修的物资往来都在一两次之间。而这个排名之中无不是与欧阳修有密切过往甚至亲属关系的人,可知宋人物资往来虽多而丰富,但是所施对象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一点在其他各大家的书简之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其中排名第一的梅尧臣,是欧阳修的至交。自天圣九年(1031)在洛阳相识,至嘉祐五年(1059)梅尧臣去世,二人保持了数十年深厚的情谊,文学上共同支持诗文革新运动,政治上也始终站在同一阵营。欧阳修集中存与梅尧臣尺牍46通中41通皆有礼赠互动,其中往来最多的是二人唱和诗文,其中还包括如“与谢家书”“答苏轼书”“君贶家书”“问答之简”等书信内容的品评讨论,是宋人将书信当作传世文学作品品赏、探讨的一个开端,也是宋代书信地位不断提高的一个起点。著作类如梅尧臣《孙子兵法注》、欧阳修《新唐书》,可见二人也交流学术著作。此外,梅尧臣也为欧阳修搜集碑拓,二人也互赠食品如鲍鱼、鸭脚子、达头鱼等,欧阳修也分名茶、好酒与梅尧臣,还给他传授药方(2)失音可救,曾记得一方,只用新好槐花,寻常市中买来染物者,于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怀袖中,随行随坐卧,譬如闲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气味,久之,声自通。(《与梅圣禹》四十六之二十三)。作为真正的老友,二人的交流达到了随心所欲又无所不可的境地。
排名第二的蔡襄也是欧阳修的密友,二人同登天圣八年(1030)进士第,是同年、同僚兼金石书画同好。特别是政治上的同盟立场巩固了两人的友谊,欧阳修被贬夷陵途中所作《于役志》记载蔡襄参与送行活动多达六次,还曾在欧阳修家里留宿,二人关系可谓非常密切。这段友谊一直持续到治平四年(1067)蔡襄卒于家中。蔡襄逝前还遣人将为欧阳修亲书的《牡丹记》摹本送到亳州其居所。欧阳修也派专人吊唁蔡,并为他作祭文与埋铭,自称“与公之游而相知之最深者”。在二人往来尺牍中有20通涉及37种礼赠物资,其中也包括诗文、著作、书画、碑刻、文房、食品、茶等诸多类型。二人的馈赠活动也达到了脱略形迹、达意而已的程度。如《与蔡君谟帖》四中“以宣笔八十、铜绿笔格、花石盆各一、龙茶三饼、惠山泉三缶为饷”,文房器具、日用茶饮都是寻常物什,却承担了“润笔”的任务,据《归田录》卷二载:“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自序》刻石,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余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君谟大笑,以为太清而不俗。”[4](P27)此帖南宋时仍存世,刘克庄曾亲见并感叹曰:
右庐陵公五帖,皆与蔡公往复者……其五乃送写《集古录序》润笔。昔皇甫湜为裴公作记,自云字直三缣,蔡字比之湜文价当十倍,今仅以宣笔八十、铜緑笔格、花石盆各一、龙茶三饼、惠山泉八缶为饷。世固有持芜辞恶札而受人不赀之濡毫者,岂不有愧色哉
润笔之风由来已久,中唐古文家皇甫湜为裴公作记,要求裴家以一字三缣的价格付润笔费。蔡襄在当时已成名,书法价钱比皇甫湜高十倍,本不是宣笔、笔格、花石盆等微物可以报偿的。然而欧阳修坦然以此为酬,蔡襄也欣然接受,这充分证明了二人的友谊。这种不对等的“交换”正是“馈赠”活动的精髓所在。
与欧阳修馈赠活动往来频繁者,皆是他的亲友。往来的物资虽然丰富,却不以贵重见称,其中尤以诗文著作交流为多,金石碑刻的馈赠往来的普遍性更体现欧阳修交际圈基于兴趣爱好的个人特色。欧阳修虽然是一代文宗,交际广泛、作品众多,馈赠活动在书简之中也比较普遍,但是总体而言他的馈赠往来圈子要远远小于他的交际圈,可见宋人馈赠活动与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也是有关联的。
二、苏轼尺牍中的馈赠活动
如果说尺牍是一部古人私人社会生活史,宋人尺牍内容之丰富、牵涉面之广无逾苏轼。他的尺牍是最典型的宋代尺牍文学样本,不仅可以从中观察他个人的一生,更可以最为全面深入地观察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学、政治、经济诸方面,尤其是文人交际活动。存世尺牍1580篇,从初出峨眉的《与宝月大师》到建中靖国元年去世当年的《与钱济明》,清晰地勾勒出了他平生足迹与心路历程,更绘出了一幅宋代文人社交生活风情长卷。他“自来不受非亲旧之馈”(3)《答水陆通长老》九首之五:“且说与姚君勿疑讶,只为自来不受非亲旧之馈,恐他人却见怪也。”,又“平生不作墓志及碑”(4)《与元老侄孙》四首之三:“十九郎墓表……义当作,但以日近忧畏愈深,饮食语默,百虑而后动,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终当作耳。”《与范纯夫》十一首之七:“《忠文公碑》,固所愿托附,但平生本不为此,中间数公盖不得已,不欲卒负初心。”《书许敬宗砚》二首之一:“君懿死,其子沂归砚请志,而余不作墓志久矣,辞之。” 《答范蜀公》十一首之五:“不肖平生不作墓志及碑者,非特执守私意,盖有先戒也。”,少了大量相关润笔记载。尽管如此,其存世尺牍中仍有293则尺牍涉及礼赠应酬物资320种,占总数约20%。这些材料对我们研究苏轼的人际关系网络、交游圈、馈赠活动的性质大有价值。
苏轼尺牍礼赠所涉内容也极为丰富,包括金石、碑刻、书画、法帖85种,诗文著作45种,器具、日用39种,药物、药材27种,文房器玩23种,茶9种,酒8种,其他(花、苗木等)8种,不详8种等10类320种。与欧阳修尺牍之中礼赠物品的类型总体一致,尤其是以茶、花、书画为主的文人雅事相馈赠的一贯性,可见馈赠在营造宋人的艺术生活氛围中的功用,也可见宋人日常交往馈赠活动方式、频率、内容之大略。但是又与欧阳修尺牍所包含的物质内容相比各有侧重。主要表现在以书信传递诗文活动的急剧减少,与书画、法帖互赠、品题活动的丰富。这既有北宋后期社会艺术氛围浓厚、苏轼自身才艺及其艺术圈的密切交往等因素,也与党争酷烈文禁森严及文人的畏祸心理相关。苏轼屡遭贬谪,流落岭海,然其尺牍之中礼赠之风不减,只是更加私密,所涉及对象范围更加有限。
虽然苏轼尺牍礼赠活动在对象上全面覆盖了他的家属、姻亲、同僚、同年、门人、后学、方外等宋人生活交际圈中几乎所有人群,计136人,但大多数往来仅在1-2次之间。仅有十余人之间物质往来次数与种类超过十次/种,分别是:程正辅(之才)22次47种;朱康叔(寿昌)13次16种;钱穆父(勰)12次19种;滕达道(元发)12次15种;米元章(芾)11次16种;陈季常(慥)10次11种;林天和(忭)9次14种;程全父5次14种;南华辩老3次18种。分析这些礼赠对象,未必尽是“亲旧”,时间也多集中在晚年贬谪岭南以后。
如排在第一的表兄兼姐夫程之才,苏轼集中收《与程正辅》计71首,全部作于苏轼南迁之后。两人本是同乡,又世代为姻,但是由于苏轼姐姐嫁给程之才又被程家虐待致死,令两家交情断绝,至成世仇。直到绍圣二年(1095)正月程之才作为广南东路提刑巡视广州,主动托人转达和好之意,两人才一笑泯恩仇,此后尺牍馈赠不断。程之才在物质上给了身处绝境的苏轼极大的帮助。在他赠予或代为采买的众多物资中,涉及食物类18种、药物类7种、日用器具类3种,还有各种新茶、佳酿等,对贬居“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之地的苏轼而言,可谓雪中送炭。苏轼也对他有厚报,主要是自作诗文书画,如《松醪赋》、和陶四五十首一轴、碧落洞诗、《表忠观碑》装背作五大轴等,这些书画因苏轼之名自然价值不菲,同时又都是在苏轼誓不作诗文以求避祸的心境下写成的,自然包含了对程之才极大的信任。可惜绍圣三年(1096)程之才就被诏回京,苏轼也再贬儋州,两人再无往来记录。程之才作为地方长官主动解仇并与流落岭海的“罪人”苏轼和好,多有馈赠且殷勤为身在罪籍的苏轼充当与亲友故旧的信使,苏轼“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瑕疵”的感叹不可谓不真心。
排名第二是苏轼的僚友朱寿昌,此人与文同友好,苏轼与文同是姻亲、知交,是以元丰三年(1080)苏轼到黄州后,与时任鄂州知州的朱康叔往来甚密。两人多次书信往来,赠送物资如羊面、酒、果等,也应求为苏轼寻找药方、制作器物,并向苏轼求取书画作品。苏轼回赠以墨竹、书字、屏赞、砚铭、录《国史补》一纸、古木丛竹两纸、经藏碑等。两人这种物质交流,实是朱对编管待罪的苏轼的一种接济。
另一位文人陈慥与苏轼结交情境略似朱寿昌,他久居黄州,是苏轼僚友陈公弼之子,对流落至此的苏轼也多有帮助,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曾多次赠药、柴炭,借《史记索引正义》,送沙枋画笼、扶劣膏等给苏轼。苏轼也常请他代为采购生活物资如茶臼子并锥等,也曾戏谑讨要好处“知壁画已坏了,不须怏怅。但顿著润笔,新屋下不愁无好画也。”(《与友人》一)。
至于米芾,则是苏轼的书画密友,两人的往来主要是集中在同在京供职期间的鉴帖题画、雅集唱和。在两人11通书简所涉16种物资之中,大半都是书画,如“临古帖”“妙迹三本”等,也涉及各种古器物如“山砚”“古印”等,价值一般都比较高,苏轼一般是观赏之后即“却纳上”“题跋了奉还”。有时遇见心仪的器物,苏轼也坦然接受,予以回报,“山砚奇甚,便当割新得之好为润笔也”。苏轼晚年北归以后,两人仍然保持了联系,继续早期的金石文物赏玩活动。此外如滕元发,是名臣范仲淹之甥,与苏轼父子是再世交游。两人的往来涉及金石书画、诗文器物、食物、药品各种馈赠,苏轼还曾向他“求买朱红累子两卓二十四隔者”。在苏轼贬谪黄州期间,腾元发物质馈赠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与帮助。又如钱勰,是苏轼在杭州的僚友,两人之间的礼赠以日用、饮食、药物为多。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突破苏轼“不受非亲友之馈”的人,如广州推官程全父(天侔)、博罗县令林忭、韶州南华寺重辩(南华辩老)等。他们都是苏轼贬谪岭南时所识,且所赠皆非贵重物品,大多是如米、酱、姜、盐、荔枝、鹿肉、笋蕨等当地食物食材,这些日用品对处境艰难的苏轼而言可解燃眉之急。同时,这些人在众人对苏轼避之惟恐不及时坦然与之交往,对其施以援手,苏轼对他们也甚为感激,回赠各种自作书画,甚至伺机为民请命、出谋划策。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交往,在黄庭坚的尺牍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可谓党争之中流贬文人的常态。
三、黄庭坚尺牍之中的馈赠活动
黄庭坚是宋代仅次于苏轼的一座高峰,也是宋型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在宋代复合型士大夫中间,他是政治色彩最弱而文化气息最为浓厚的一家。尤其是在漫长的贬谪生涯中,他更是隐遁书画,远离政治人事。这些在他的一千两百多篇传世私人书简中有着清晰的记载。作为“小道”的书信并未被黄庭坚视为祸害之源,因而大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书信流传下来,记录了他的人生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详检黄庭坚尺牍,会发现其经济方面的信息丰富得惊人,其中有685通涉及到日常衣食住行、礼尚往来种种开销。这些资料为我们了解黄庭坚本人日常生活消费乃至宋代文人经济生活留下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无疑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
这685通涉及各种礼赠应酬买办活动,占其全部尺牍52%,也即黄庭坚所有书信中有半数以上伴随着各种物资赠送、回赠、求索、报谢活动。也可知礼物往来、日常生活物资的流动,是黄庭坚日常交际生活中重要活动之一。这六百余通尺牍之中所涉及的内容为北宋诸家之最,物品极为丰富,大致仍可以分为十类:诗文著作219种(文95、诗79、词9、不详8,书籍著作26);书画、金石、碑刻170种(书法95,碑刻43,绘画22,其他10,不详4);日用器具物资168种(器具103,服饰衣料46,物资19);食材、食物154种(主食55,酱料38,果品39,蔬菜28、肉类水产23,不详9);文房器玩100种(纸51,笔15,墨12,砚8,香9);药物、药材83种(药材31,成药32,药方16);茶63种(双井27,建茶17,其他15);酒22种(4种有名,18种不详);其他22(花7,船6);不详2(节物、土宜)等981种。名物之多、品类之盛居宋人尺牍之最,对这些物品、物资的精确统计与研究,对我们了解宋人日常经济、交际生活实况及其成本无疑是大有意义的。
这981种物资如欧苏二家一般,亦是极为分散,往来频繁、所涉物品多于十种者仅十余家,如檀敦礼32次/88种,王直方(立之)21次/32种,马中玉(瑊)20次/28种,党伯舟(涣)21次/20种,逢兴文20次/25种,王献可(补之)16次/26种,觉范(范上人)12次/17种,明叔少府9次/17种。元勋(不伐)7次/16种,武皇城5次/20种等。如上十人与黄庭坚往来物资达289种,已占全部馈赠物品29%,其余诸人也多在一两次往来两三种物资之间。这些人中与黄庭坚书信往来频繁莫过檀敦礼,二人往来书信32通(27通为答简),涉及物资包括诗文、书画、文房、器玩、食物、日用器具、药物、食物各种类型计88种之多。在黄庭坚集中尚存两篇为檀敦礼所作的文字《跋三伯祖宝之书》《檀敦礼研铭》[6](208册,P285),与他人简尺中也提及檀氏,可谓过从甚密。
檀敦礼名不详(5)从黄庭坚尺牍之中推断,檀敦礼似乎并无科第,也无官衔。尺牍中所云“秘校”并非实际官名。据《答敦礼秘校简》九“复损茶器四种,皆九江佳物也……公之归澧,亦是佳事,彩衣奉亲,兄弟同文字之乐,此人生最得意处也”推测,檀当为湖南人。居住湖北荊州。且当时还是少年(《与敦礼秘校帖》四“未有佳物奉答,辄以药石之言为报。谢去少年戏弄之习,以副父兄之愿,岂不美哉”),热衷书画鉴藏,黄庭坚劝他不要玩物丧志,应归心举业。则檀敦礼之生平,还需更多的资料来进一步考证。,祖籍澧州(今湖南常德市),居湖北荆州。好书画古玩,然不精择,常以器物、文房等为赠,求黄庭坚墨宝,并请求他鉴赏、题跋他所收藏的古今名家手迹与古物。建中靖国元年(1101)黄庭坚过荆州小住时相识,此时檀敦礼家于此,《答檀敦礼》一二有“病余苶然,殊不堪事。以翟漕到三四日,义当一入谒,已不胜委顿。适饭表弟家,因解衣就卧,俟小凉,复拏舟归卧沙尾,岂可复胜冠带相见”,与《跋行书》所谓“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乙亥,荆州沙尾水涨一丈,堤上泥深一尺,山谷老人病起书也,须发尽白”[6](第107册,P77)记载相合。则二人当于建中靖国元年五月间相识于荆州。查看三十余通书简,基本都作于荆州或离荆州时期,此前、后黄集中皆记载,可知二人并非维持了相当时间的交际之密友,而是在黄庭坚流落到此时因缘遇合下的短暂交游。这一点二人往来中所赠和回赠的内容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二人往来尺牍32通中可见一个明显的现象,即几乎每通皆涉及檀敦礼对黄庭坚的各种物质馈赠,内容覆盖食物、文房、古玩、器具、茶酒等各种类型,唯不涉及自作诗文书法作品。其中有22通的礼赠是附加诗文书法创作、古书画器玩鉴别题跋的请求,且催迫甚紧,以至黄庭坚不堪其扰,用杜诗的典故规劝他:“杜子美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蹙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收书者亦欲精耳,贪多不择,亦是一病。”(《答敦礼秘校简》一○)还恳求“文字万一得暇,或可了,然盛暑如此,己之所欲,乃以望人”(《答敦礼秘校简一一》)。但是黄庭坚基本满足了他的愿望,所回报的基本皆是自作书法、诗文手墨。则与檀敦礼这种礼赠行为实际上有“润笔”的性质,这一点在诸简中是有迹可循的:
端研亦佳,谩作数语其下,衰老阘惰,不成文也。尝有人作一大镜研见惠,下有足,因戏作铭,旦夕得暇,当谩写去。《砧研铭》了亦送。渐欲省去长物,不须惠贶也。(《答檀敦礼》九)
惠独体朱砂圆……三轴文字得暇当写。(《答敦礼秘校简》一〇)[6](105册,P314)
从文意推断,第一则的“惠贶”就是回报黄庭坚所予墨宝并诗文《端砚铭》《大镜砚铭》《砧砚铭》的润笔。第二则“独体朱砂圆”当是与“三轴文字”同来的预付的润笔。其他内容也大抵如此。
总之二人的相处模式是:后学少年檀敦礼以礼物并书画相赠,求书法鉴赏、题跋、相关诗文创作,而黄庭坚对他的礼物及请求基本来者不拒,但是也明确表达了对他“贪多”又急切的不满。虽然不满,但仍应求,因为此时黄庭坚正在南迁途中,生计维艰,也因政敌打击而孤独无友。
其他与黄庭坚馈赠频繁的士人除位列江西诗派属联络型人物、与元祐党人多有交游的王直方(字立之)、元勋(字不伐,同年元聿之子)外,诸如贬谪途中所结交的时任泸州知州王献可(字补之)、荆州知县马瑊(字中玉)、黔州军事判官逢兴文、东川路分钤辖武皇城、宜州知州之子党涣(字伯舟)等皆是如此。黄庭坚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尺牍往来活动,携带了大量的礼品,但是细看这些材料,在馈赠——回报形式外表下隐藏的其实是常规买办活动:
今年进奏吏遂不以历日见及,恐有分诸吏者,可买一本。(《答逢兴文判官》二十)
斤竹若早得数本封来,甚幸。摺叠卓子,必为留意。青白花通裙,试为寻数条,即纳直也。(《与东川路分武皇城》三)
买附子二两,若得四枚,以黄龙清禅师小中急,来求药,旦夕欲遣人回,故敢恼乱道友耳。(《与忠玉金部简》三)
附子不审已得之否。脚婆已就否?数夜脚冷,甚念之耳。欲便打一锡盂。(《与忠玉金部简》四)
奉烦指挥干者为买人参、附子,批谕其值,幸甚。见秦处度,为乞佳墨一丸。(《与农沔染院》二)[5](105册,P227-314)
如上这些都是黄庭坚干请托买之物,措辞与馈赠一致。可知黄庭坚尺牍之中丰富的物资往来,并不表明双方的亲密关系,只是表明对方是可以请托办事的人士。黄庭坚在回报这些人的劳务时,除了“纳直”外,还往往附赠诗文书法作品,这种“酬谢”的方式,显得双方也非纯粹商务往来,从而模糊了原本买办请托活动的边界。
由上述内容可知,无论是萍水相逢的士人还是知交好友,黄庭坚所收礼品内容丰富、复杂,无所不包,然其赠送的礼品中则以诗文书法为主。可见以诗文书法为赠,是黄庭坚维持交游的主要方式。这一点与欧阳修、苏轼等大部分宋代文人都有相通性的,即“富者赠人以财,仁者赠人以言”,以自己所长所有,投人所好所无,诗文书画的价值与作用在这种往来之中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人所赠的各类物资与黄庭坚的诗文书法题跋之间,往往还存在着交换关系,即宋人盛行的“润笔”现象。买办活动在黄庭坚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有较大的比重。檀敦礼等人与黄庭坚有密切尺牍及馈赠往来的诸人,并无长期交往的记录,似也算不得黄庭坚交际网络之中的重点人物。这是黄庭坚尺牍之中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这一点《乙酉日乘》也可为旁证。《日乘》所载229则日记中,涉及交游者134篇,涉及物资馈赠活动的有49条,涉及书信的34条包含尺牍67通。67通尺牍中有32通家书,其中仅4通携带生活物资。而35通与友人的书简中,则有11通携带物资,内容涉及物资31种之多。资料显示当地士人邵彦明、秦靖等数人在登门拜访之余,也以书信馈赠,与黄庭坚建立友好关系。在馈赠往来互动中,日志对邵彦明的称呼由邵君变成了彦明,这其中自然有情感的交流与加深。但是整体而言,黄庭坚尺牍之中的馈赠活动较之欧苏等文人有了明显的不同。欧阳修尺牍之中物质互动最多为其密友梅尧臣、蔡襄、刘敞等,密切度与馈赠频率正相关。与苏轼物质往来最多者为表兄程正辅、黄州好友陈慥(僚友之子)、朱寿昌(文同之友)等,虽互动多在苏轼困境中,有一定接济的性质,但是仍以交情为基础。而黄庭坚尺牍之中物质往来频繁的,大半是沿途所遇当地士人,互动方式多是当地士人以礼品馈赠求书画文物鉴定题跋及黄庭坚本人的书法诗文墨迹,或黄庭坚本人向当地文人求取买办各种生活物资,并以书法诗文为“报”。这种互动之中馈赠作为“润笔”“报酬”的交换性质要明显大于基于人情的礼尚往来,这一点让黄庭坚尺牍中的馈赠活动有独特的探讨价值。
四、宋人尺牍礼赠活动中的历史渊源及承载的历史信息
欧、苏、黄三人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宗主式人物,又热衷奖掖后进、开启来学。尺牍在他们的文集之中占据相当重要的比重,而馈赠又是尺牍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见馈赠在三人交游生活之中的地位。查两宋尺牍存世比较完整的诸家,情况大抵如此:孙觌存世尺牍1377通,有272通(19%)涉及礼赠物资375种;朱熹存世尺牍2097通,有297通(14%)涉及礼赠物资465种;周必大存世尺牍595通,有108通(18%)涉及礼赠物资265种;杨万里存世尺牍291通,有183通(62%)涉及礼赠物资346种。其他两宋诸人的尺牍之中,礼物馈赠现象也随处可见。足知尺牍往来之中礼赠活动在宋代社会之中是普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传统,二是宋代社会之新特色。
书与信联袂历史悠久。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秦朝士兵黑夫与惊的家书,是现存最早的尺牍实物,距今有两千多年。信中云:“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今书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禅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操钱来,黑夫自以布此。”此信为报平安,亦为索要日用物资。若有回信必会附上相关财物。居延汉简中也有诸多关于买卖生活物资、食物果品的内容[7]。《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录尺牍文中也多有礼赠应酬内容,比如《全晋文》卷二十六王羲之杂帖中有数十通礼物馈赠往来书简,涉及蚶、厉、橘、野鸭等食物,丝布单衣、邛竹杖、白石枕珠等日用器物。卷一百〇二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五首中也有十八通涉及礼物的馈赠,其中十六通皆是诗文往来切磋评定,所涉文章有《愁霖赋》《喜霁赋》《岁暮赋》等文章,其三五有“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讫一十,当黄之。书不工,纸又恶,恨不精”[8](P4090)更透露了这样的历史信息:在魏晋时期,文人已经有意识收集个人作品成集,用良纸佳书抄录以为礼物。可知自秦汉以来书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作为载体不仅可以传递消息、思想,还能传递包括财物、日用品、诗文等等各种物资。这些物资由信使携带,与书信同时到达收信人手中,功能互补。信作为书的附件,也是尺牍内容的一部分。
礼品馈赠的历史比书信还要悠久,在没有文字的原始社会,群体之间就通过这种特殊的“交换”维系生存,它是人际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学者莫斯认为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交换”的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个人化而且无私、无目的的“交换”,而是有一套“报称馈赠”系统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9]。这个系统可以归纳出几个原则:义务性(所有表面上看似自由而个人化的“交换”行为,其实是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平衡性(在社会规范约束下的人们,收下物品都有必须回报的义务,并且回报必须等值)、契约性(不断进行的赠与和回报的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维持关系,而组成团体或社会。所以表面上看是物质交换的经济现象,其实是在维护、制造或表现社会阶层关系的政治现象)、普遍性(这是所有人类社会普遍的行为)。数千年来,交际活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都占据着绝大比重。互动与馈赠成了人际无尽的过程。上至帝王,下至三家村民,都需要在这种持续的互动之中维系彼此的关系,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正如许平《馈赠礼俗》所言:馈赠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他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反映了人类对群体生活的依赖和对人际交往的需求”[10](P24)。
早在先秦时期,馈赠的内容、形式与规则就已形成,儒家典籍已将馈赠纳入交际礼仪之中,《礼记·表记》言:
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民之毋相亵也。”
孔颖达《正义》:
“无礼不相见者,礼谓贽币也。贽币所以示己情,若无贽币之礼,不得相见。所以然者,欲民之无相亵渎也。[11](P3557)
“无礼不相见”,表达人情,需要用礼物。宾主相见,要先有言辞相通(介绍人或书信)然后才能带着礼物相见传情。这样可以熄灭人们的贪利争夺之心也。馈赠原则是重意轻礼“用时物相礼而已”:
野外军中无挚,以缨、拾、矢可也。郑氏曰:非为礼之处,用时物相礼而已。缨,马繁缨也。拾,谓射鞴。孔氏曰:军在野无物,故用此为挚可也。[12](P161)
身在军中无别物相赠,赠送随身马缨、箭鞴即可。同时: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11](P2665)
以物易物不是馈赠的目的,“永以为好”才是。正如欧阳修所说“礼有来必往,木瓜报琅玕”(《送荥阳魏主簿》),也如宋人王希吕《普向院记》所谓“夫礼尚往来,事有施报,施而不报、往而不来者,世无是理也”[6](273册,P354)。往而不来,来而不往都是非礼的行为。礼品馈赠虽然是一种“交换”,但是目的却并非得到物质,而是在彼此交换之中巩固关系,建立关系网络。馈赠服务于人际关系的建构,且在非亲缘的朋友、师门、同僚之间尤为重要。由个人、家族、乡党、朋友、师门不断向外扩展而形成的社交网络,能够最大限度的对抗制度与灾祸,保全个体。同时个体通过关系网络,还可以获取各种社会资源。人际关系如此重要,却具有变动性,成员之间必须能够持续友好互动、互惠互利。馈赠就是维持关系网络的必要手段,通过彼此馈赠,关系被不断维护和延伸。
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馈赠规范也给古人带来精神压力,如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春秋时期名相公仪休拒收客所赠鱼的寓言故事[13](P3101)就揭示的当时一个人际关系的规则:非礼仪性的馈赠,往往期待着非礼仪性的回报。客赠鱼,期待的不是得到同等同类型的回报,而是期许得到公仪休宰相的权利、威望带来的好处。若公仪休不想因此破坏原则、失去地位,就必须断然拒绝。但是断然拒绝是违背礼制与人情因而并不常见的,因此往往作为美德被记载。这一规则在宋代仍然通行,如欧阳修《与梅都官》所谓“修平生不欲夺人奇物”[14]及苏轼的“不受非亲友之馈”,都是为了杜绝请托等非分的回报并避免破坏馈赠的习俗。黄庭坚与檀敦礼的馈赠交游也是如此,虽然他对檀敦礼不断索求题跋、书法的“贪得”有不满,但是他仍勉力应酬周旋。对檀敦礼的馈赠也总有诗文书法为报。
黄庭坚无法拒绝檀敦礼的馈赠结交还有另一层顾虑,即这种互动关系实质上是地方士子对过往“名流”的干谒与名流对后学新秀的“提携”的传统。这种“干谒”“投贽”是科举时代士人之间的新礼仪,它维护的是整个士大夫群体上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众人都不能免俗。兴起于唐的行卷、干谒活动,至宋更为繁盛,这也是宋代尺牍馈赠活动发展的新方向。
同时,宋代科举的进一步盛行、门生座主提携模式的发展,也给馈赠活动带来新的礼仪规范。这种规范下,馈赠活动尤其是以诗文为贽成为约定俗成的士大夫群体上下之间的交际模式,上位者尤其无法拒绝。籍籍无名的欧阳修以文投献长官胥偃,眉山三苏携文拜谒文宗欧阳修,包括黄庭坚等投文结交名满天下的苏轼,以及两宋文集中众多的投献书启,都是依赖于这一新传统而产生的。新礼仪下,“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并非值得鄙视的投机行为,而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表现,否定贫寒士子,拒绝援引,反而是没有气量与见识的表现。
此外,这一新传统的形成与宋代社会性质的变化也是有密切关联的。随着门阀解体、科举大兴,大量平民进入政治权利中心,宋代开始进入一个平民社会,群体的力量取代门阀大族的力量,成为士人立身的关键因素。“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群体意识也空前强烈,交游活动频繁且规模宏大开始成为宋代社会新的时代特色。新的时代背景下,交游互动成为士人进身的重要影响因素,无论是入仕之前的求名之举,还是入仕之后的转官之需;无论是在朝的相互臂助,还是在野的相互扶持,都离不开士人之间的自觉交游,形成同门、同僚、同乡、同年等各种同盟。同处于这一士人群体之中的文人们也逐渐有了共识,上位者提携奖掖后进,后进者在得势之后,也热衷提携后进,并紧密团结在恩师举主周围,形成政治、文学团体,壮大彼此声势,影响社会发展。下位者积极干谒名流,期待“名人印可”以一夜成名,踏上坦途[15]。一旦得志,也迅速融入群体之中,并积极充当“伯乐”博取识人之美名。这一新传统,让士人群体空前壮大与团结,更刺激了交游活动繁荣发展。
“举世重交游”的宋代社会,不仅各种形式的集会、唱和、游乐活动层出不穷,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都染上了交际的性质,直接承担交际互动功能的文体——尺牍更是全面繁荣。两宋传世文集中交游性质的诗词文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以黄庭坚为例,他的文章现存17类总计2602篇,其中1219篇是亲友往来尺牍,占总量的46%。欧阳修、苏轼诸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可见交际活动在宋人生活之中的地位及馈赠行为在交际活动中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宋人也建立了一套“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礼仪”[16](P195),这种礼仪之中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馈赠活动。
宋人的馈赠礼品中,也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如欧阳修与友人往来尺牍之中的金石碑拓,苏轼尺牍之中记载的各种名书、奇石、怪砚,黄庭坚尺牍之中流转传藏的各种案头笔墨纸砚、香药茶饮,都是典型的宋型文化代表物。尺牍之中文人频繁的馈赠,让我们看到宋代雅文化对宋人日常生活的渗透,也铺展了一幅近乎全景式的宋代士大夫日常生活图卷,体现了一个文学、艺术、学术、科技诸层面全面繁荣,文化艺术气息浓厚,社会稳定太平、物质丰富,人民整体文化素养、鉴赏水平提高,博物、金石诸多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文治社会的灿烂图景。联系宋代历史、文化多方面材料,我们又能发现,这些礼赠往来,并非简单的物资的罗列,它其实体现的是宋代新的社会礼仪、规则,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水平、喜好风俗、价值观念与情感流动。正如《宋代士人交游录》所说:“士大夫在家乡或任官所在地产茶者,往往寄新与相知,表达友谊。一般附以书信诗词,封缄后派专人或由驿递寄给对方。对方也回赠当地土特产。有答书、赠诗,成为一种高雅时尚。”[17](P113)这种馈赠本身既是高雅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还是维持宋人交游关系的一个手段。
五、小结:宋人尺牍礼赠活动的研究价值
如果以人类学角度来看文学,文学是诸多文化生产形式中的一种,如陈恬仪《论南北朝的“谢启”:以赐物谢启为观察中心》中论及谢启的起源时所说:
文学乃文化的结晶品,是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或生命特质,则不应轻视古代士人大量创作,且渗入其不同生活层面的应用文类,即使是表面上看来无意义或无价值的应酬文字。透过这类作品的文辞技巧,我们可以进一步体察到作者以及作者所属的社群、阶层的生活特质和价值观、情感样态。[18]
尺牍作为应用文体,虽然不乏大量“无意义或无价值的应酬文字”,但是它的价值是不应当被轻视的。因为这种应酬活动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尺牍不仅仅是应用文,还是社会礼仪与规则,是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系的工具,是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水平、喜好风俗、价值观念与情感流动的展示平台。尺牍之中的馈赠,也不应当仅仅将其视为无文学价值的礼品清单。在礼尚往来的场合,礼物用以“表意”“致意”,而书信则用来补充说明这些礼物的具体内容数量及功用。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礼物无法表达谢意或示好之意,没有书信则无法确定礼物往来的意图,也不能确保信使是否中饱私囊,礼物是否如数送达。
另一方面,宋人尺牍之中之所以保存着大量的馈赠信息,也是出于礼仪规范,用书的文雅冲淡“信”的交换性质,突出书信往来的情感交流而非物质交换价值。其客观的效果是给我们提供了精确因而无比珍贵的宋人礼尚往来的清单,便于研究馈赠活动所包含的礼仪、情感诸多信息,同时,通过馈赠的品类、价值的分析,还能进而了解当时物价、经济、衣食住行诸多方面实况。通过馈赠礼仪的研究,我们更能理解宋人积极修订“切于人伦日用之常”的居家礼仪标准,如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和朱熹《朱子家礼》等的实用价值。
尺牍作为应用文体,既是礼仪工具及诸多礼仪规范实施的必由之路,同时其自身也是传统士人结交礼仪规范中重要的一部分。馈赠活动,既是尺牍的文本内容,也是尺牍的物质补充;尺牍既是馈赠备注文本说明,又是馈赠的承载方式。两者统一,既可见文人日常交游活动的实况,又可知宋人交游活动的方式、规则,关系网络的建构与延伸等等方面的内容。尺牍之中大量馈赠内容,为我们研究宋人交游互动提供了丰富细致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材料连同尺牍本身,与宋人常规的唱和、集会活动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文化价值。将文人的直接交游(集会、宴饮)与间接交游(以尺牍相沟通、馈赠、唱和)相结合综合研究,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再现“举世重交游”的完整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