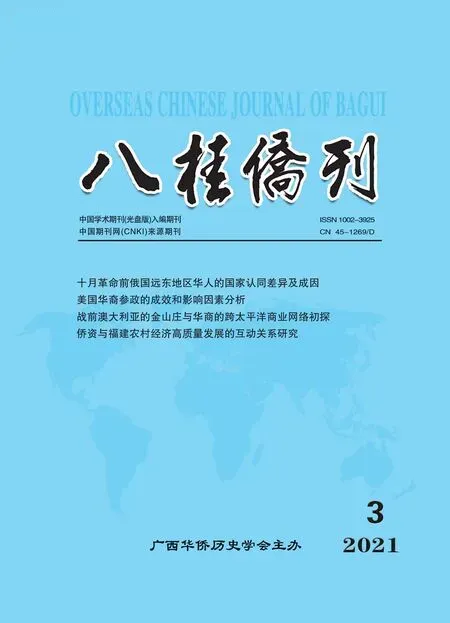泰国的潮州会馆与中华总商会的关系探析(1938—1945)
陈 攻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1855年,英国与暹罗①②1939年6月,“暹罗”的旧名改为“泰国”,此文暹罗将只用于引文或专有名称。政府签订了一份不平等条约《鲍林条约》,从此古老的暹罗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国门,加入了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当中。
1855年,暹罗②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鲍林条约》,自此之后,泰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独立于政府的小商人可以自由参与国际贸易,取代原先垄断国际贸易的包税商③这些包税商是吞武里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皇族华人”拥有处理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种种特权。。此种现象为泰国吸引了大量中国特别是潮汕地区的移民。根据美国施坚雅教授的估算,从19世纪晚期到1949年前,流入泰国的华侨人数多达约一百万人,华侨约占泰国总人口比例已超过10%④G.W.Skinner,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An Analytical Hist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7,p61.。大量的华人移民按地缘、血缘、职业等关系进行结合。因此,在泰国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多个华人社团。
这些社团大多建立在互帮互助为目的的基础上,从这方面看华人社团成立的原因和目的有着相似之处,其中泰国中华总商会逐渐脱颖而出,在处理外交、侨务等事宜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同时,以地缘关系发展起来的华人社团相继创设,尤其是以在泰华人祖籍地为主,例如潮州会馆、海南会馆、福建会馆等。
从1910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多数华人社团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秘密社团的性质,随着泰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华人社团逐渐转为经济服务组织。例如张映秋的《泰国华人社团模式的演变》⑤张映秋:《泰国华人社团模式的演变》,《潮学研究》1995年第1期。、范如松主编的《东南亚华侨华人》①范如松:《东南亚华侨华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张应龙主编的《海外潮团发展报告》②张应龙:《海外潮团发展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但是对于两者之间在人事、功能、性质等方面的关系则缺少详实研究。
杨锡铭的《泰华社团中家族传承现象初探》③杨锡铭:《泰华社团中家族传承现象初探》,《八桂侨刊》2017年第2期。中阐述了泰华社团大多是以潮州人为主体的社团,其中存在着潮籍华人家族传承现象。李慧芬的《试析泰国中华总商会的演变》④李慧芬:《试析泰国中华总商会的演变》,《八桂侨刊》2014年第3期。介绍了泰国中华总商会如何从一个小规模的社团发展到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黄素芳的《浅析曼谷王朝初期(1782—1910)泰国的华人方言群》和《泰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⑤黄素芳:《浅析曼谷王朝初期(1782—1910)泰国的华人方言群》,《八桂侨刊》2012年第3期;黄素芳:《泰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八桂侨刊》2007年第3期。介绍泰国华人的方言群体以及对华人社团发展的影响,对泰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做了详实的梳理。有鉴于此,本文以1938—1945年时间段内的两个组织为研究对象,试图深度解析两者合作及互动的基本情况,阐明在这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泰国中华总商会和潮州会馆在不同的历史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转变。
一、泰国中华总商会中潮州人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初,随着大量华人涌入以及泰国对外贸易迅速的扩张,泰国社会出现了深刻变化,泰国中华总商会正是这种社会巨变所带来的产物之一。泰国中华总商会与在泰华商的奋斗与发展史,都与当时的泰国、中国乃至亚洲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历史现状有着密切的联系。
泰国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10年,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是泰国历史悠久的华人商会之一。但是直到1938年,在泰国的潮州籍华人才组建了属于这一方言群体的潮州会馆,随着潮州会馆的诞生,标志着泰国华人社会已经按照现代组织的模式彻底建立起来了。潮州会馆和泰国中华总商会,被称为泰华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社团组织。
(一)大批潮州籍华人的涌入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殖民主义者开放东南沿海通商口岸。1858年6月27日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朝政府与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潮州(后改为汕头)被迫成为向西方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汕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港口城市以及华人漂洋过海移居海外的起点之一。
同时泰国与英国签署《鲍林条约》,开放通商,国门大开,西方资本大量涌入,在1850—1917年的这段时期中,经济飞速增长,热带种植业、手工业、矿场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此背景下,来自潮州的大批华人来到泰国。华人移民大批涌入,为泰国社会补充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进出口贸易、航运业和批发商业的快速发展日益需要买办商人,华人的到来同时也填补了泰国社会缺失的商人群体。因此,泰国王室及政府对华人移居泰国也持支持的态度。也可以说华人成了《鲍林条约》的受益群体,同时促进了泰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使得泰国快速融入了现代世界贸易。

表1 1882—1917年泰国各地华人出入境总人数统计表(每个时期统计)
(二)潮州籍华商的壮大和华人社区的出现
20世纪初,随着泰国对内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中国沿海城市陆续开埠,泰国出现了一批以华人为主与政府无关联的独立商人,也称为“头家”。这些华商在泰国的经济中能充分的自由竞争,而且泰国传统势力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做生意的头脑远远高于泰国本地人,有较强的公司运营和财务管理能力,懂得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计划,了解市场行情并且能够及时捕捉市场需求,对东亚、东南亚市场的理解和把握强于泰国贵族和上层阶级。逐渐壮大的华商群体凭借自身经商优势,开始在曼谷、汕头、新加坡和香港之间建立商业网络,特别是大米的贸易网络。
随着华人移民不断涌入并在泰国定居,泰国华人社区也不断扩大。靠岸登陆的华人大多定居在湄南河东岸的耀华力路、石龙军路和三聘街等区域,这个区域位于曼谷城西,占当时曼谷市区面积约五分之一。泰国国王拉玛五世在位期间,曾经御驾三聘街,为华人四面佛像献袈裟,接受华商和华人代表的朝拜,询问华人经商、生活等情况。
1911年法国作家加尼尔(Charles M.Gamier)来到曼谷时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刚开始的期待是想看见暹罗人,但是感到非常遗憾,因为直到快离开曼谷时都没有能看到暹罗人。”①Charles M.Gamier,Bangkok,colonie chinoise,ou le secret du colosse jaune,Revue du Mois9,1911,p232.由此可见,当时的曼谷是一个华人占比较高的城市。定居的华人不仅是商人,同时也是消费者,他们一方面源源不断运来中国的商品,另一方面又将泰国产品运回中国,因此泰国对华贸易也日趋活跃。1939年《华商》里也有一句话这样描述当时在泰国遍布的华商盛况:“在暹罗国内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人烟的地方,就有华商的存在。”②《暹罗中华中学校舍落成纪念刊》,曼谷:《华商》泰国中华总商会,1939年版,第23页。

表2 1882—1917年中国海关记录的由汕头前往曼谷的人数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泰国的华人中,从汕头出发的潮州籍人数很多,他们不仅都有独特的生活习俗,而且还拥有着传统的方言、民间信仰及农业技能。潮汕地区至今流传着一首民谣歌曲:“天顶天顶两只鹅,阿弟有亩阿兄无,阿弟生仔叫大伯,大伯听着无奈何,打个包裹过暹罗”。第一批登陆泰国的华人虽身在异乡,但情系桑梓。这些华人社区成为潮州人建立的庞大的海外宗亲网络的一部分,也有效组成和维护着以潮州人家族生意人脉为主的海外贸易网络。
然而,正是由于潮州籍华人人数过于庞大,要顺利成立一个团结全体潮汕籍华人的组织机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照下表其他地域性会馆成立的时间,潮州会馆直到1938年才成立。直到1975年秋,会馆馆址才最终选定,前后花了五年时间。从潮州会馆的建立以及馆址的选定都十分迟缓这个事实看出潮州会馆成立的困难程度。

表3 1910—1945年泰国华人地缘性社团成立时间表
二、潮州会馆和中华总商会的密切联系
19世纪末期,是契约华工大批移居泰国的时期,华人社区的庙宇往往也相当于同乡会馆。华人地缘性组织的职能、人员、组织结构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所变化。总的来说,直到二战前,地缘性组织带有明显的政治和秘密社团的色彩,随着泰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地缘性组织逐渐发展成华人社会服务组织。
在潮州会馆成立之前,在泰潮州人也曾成立过类似的组织,最早的潮人社团组织可追溯到潮人先侨登陆暹埠时所祭拜的“老本头古庙”、“三聘亚娘庙”及“新哒叻龙尾爷”①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到了1921年,潮人成立“潮安互助会”“潮安研究社”两个社团,目的是当地潮人能够“看守相助”“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由于两个社团规模较小,1927年两个社团合并成为“潮安辅益社”②《旅暹潮安同乡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曼谷:旅暹潮安同乡会,1987年版,第209页。。这些社团都带有浓厚的地缘性和秘密结社的色彩。
(一)泰国中华总商会加速潮州会馆的筹备过程
20世纪初,政府为了控制社团以及与社团相关的活动而出台社团法,华人秘密社团遭到政府打压,华人把地下结社活动设法转变为合法运作。特别是部分具有单纯的经济和社会服务为目的的社团,社团领导人按照西方社团的组织管理模式及经营方式来改造华人社团,由此在1910年,火砻公会的高学修、黉利业行的陈伦魁,以及澄海籍华人领袖廖葆珊等人努力下成立了“暹罗中华商总会”,其创立宗旨为“中华商总会即为泰华商与各界侨胞之大家庭,所有会务及大部分工作,遂不免涉及全体华侨的共同利益及负起全国性的领导作用”③《暹罗中华总商会纪念刊》,曼谷:泰国中华总商会,1930年版,第73页。。
在1930—1932年期间,在泰国中华总商会的努力下,不少地方性帮派解散或者改组成华人地缘性社团。在1936年潮州会馆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员例如陈景川、廖公圃等大多都是中华总商会的成员,筹备委员会的主席是同时也是中华总商会主席,著名华人领袖蚁光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潮汕地区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地处华南海防前线,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日本侵略者从日据台湾出动数艘军舰对潮汕地区发动了侵略战争④《在潮汕内地活动驻汕日领署举行表演紧急集合》,《申报》1937年7月23日,第9版。。战争造成了潮汕人民颠沛流离,农业生产严重受挫,导致粮荒发生,蚁光炎闻讯后,为了尽快购运米粮到潮汕赈灾,减轻当地粮荒,潮州会馆筹备委员会工作加速了会馆筹建的工作⑤《潮州旅暹侨胞进行平粜代赈第一批为一万包》,《申报》1938年6月11日,第4版。。
(二)潮州会馆参考中华总商会形成组织架构
到1938年2月14日⑥《四十年来的泰国潮州会馆》,《泰国潮州会馆成立40周年暨新馆落成揭幕纪念特刊》,曼谷:潮州会馆,1979年版,第1页。,潮州会馆正式完成政府方面的注册,潮州会馆的成立,泰国中华总商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馆根据当时中华总商会标准的制度来组织运行,具体为由潮汕籍华人领袖们组成一个执行委员会,秘书和司库由执行委员会提选正副主席各一人,秘书和司库(财务)各一人,常务委员一人,年迈且有一定威望的侨领组成一个监察委员会,监察和稽查委员共8人。潮州会馆成立几个月后,就成为泰国华人界仅次于中华总商会的最重要的华人组织。会馆的成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满足了潮汕籍华商们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缘性社团组织,能满足潮汕籍华人团结互助,帮助祖国抗日的需求。当时参加会馆的会员,在华人社会里都是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对泰国经济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在当时潮起潮涌的爱国主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潮州会馆与中华总商会的执事关联现象
施坚雅教授在其著作《泰国华人社会的领袖人物及其势力》中提到,泰国的华人社会按照不同的组织原则来组建社团,大致分为地缘性社团(方言会馆或乡团)、血缘性社团(宗亲会馆)、业缘性社团、慈善机构、宗教社团、善堂等。这些社团之间联系密切,形成互相渗透交织的多重网络,而且相同的一个华人精英群体在不同社团都担任职务,这个现象称作为“泰国华人社团执事关联现象”①Skinner G W,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pp109-112.。
(一)执事关联现象的成因
根据日本学者市川信爱的研究对比发现,在潮州会馆成立初期,会馆成员人数一半以上同时也隶属于中华总商会,在两个组织同时担任职务的人员比例高达81.3%②[日]市川信爱著,郭梁译:《泰国华侨社会的特点和各种华侨帮派形式》,《南洋资料译丛》1981年第3期。。在中华总商会永久会员的名单中,同乡会馆中只有潮州会馆是唯一的永久会员。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潮州会馆与中华总商会存在执事关联现象。
1.多数华人精英在多个社团身兼多职。泰国华人社团酝酿形成于17、18世纪,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泰国华人社会逐渐壮大和稳定,泰国华人社团也进入成长期。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中华总商会开始广泛整合和组建一批血缘性、地缘性、业缘性社团,使其合法化。在组建过程中,一批泰国华人精英在担任全侨性社团的中华总商会职务的同时也担任其归属的血缘性、地缘性、业缘性社团的职务。如潮州会馆的筹委会成员之一的张兰臣,曾任该会馆第三、四届主席,同时1942年起连任5届中华总商会主席。
2.泰华社团中普遍存在家族传承现象。华人社团不仅是泰国华人和衷共济、沟通情谊和辅助事业发展的平台,而且是维系华人族群文化和族群特征传承、推进华人社会发展的重要媒介,在华人社会中有一定威望的侨领担任不同社团的职务,不仅能较快推进华人社团数量增加,同时快速提升新建立社团的实力及影响力。如郑氏家族是华人社团中资历最老的家族之一。郑午楼的父亲郑子彬是潮州会馆筹委会成员之一,曾任该会馆第一届执监委会常务委员。郑子彬曾协助改组华侨报德善堂,并历任中华总商会常务委员、救国公债暹罗劝募委员会主席等职,在泰华社团中德高望重。
3.商会成员中的富商巨贾实际上维持着许多华人社团的运转。与政府关系较好且有较强经济实力基础的华商担任不同社团的职务,能够为社团的运作提供必要的资金资助,使得地缘、血缘、业缘社团形成了相互重合不能分离的特殊关系,因而更能够有效保护大多数的华人社团,促使华人社团有效抵御来自外部政治、经济、社会的压力,尤其是来自泰国国家民族主义政策影响。
(二)执事关联现象的特点
潮州会馆与中华总商会以及其他泰国华人社团之间的执事关联现象发展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
1.社团职能分工日趋明显。中华总商会将主要负责协调中泰两国政府间关系,处理商务、贸易方面事务,而潮州会馆及其他社团工作重点则转为主流社会提供公益服务。
2.华人社团之间联系逐渐强化。逐步建立覆盖广、多领域、区域性的社团组织,融合的思想成为社团精英的共识,社团活动中推进融合、服务主流社会的工作也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提升理论自觉,进而增强理论自信的最重要保障。
3.社团间的政治分歧明显淡化。缘于政治认同分歧的冲突缓解,华人社区出现了相对团结的局面。但是,泰国华人社团执事关联现象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尤其是名利之争和后继乏人问题最为严峻。
(三)执事关联影响下的华人社团职能分工
对任何一个华人社团来说,其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帮助华人适应与融入当地的生活。因此,潮汕会馆与中华总商会在成立时都有着相同的愿景和目标,且两个组织间人员高度重合,发生社团冲突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是,在二战结束前这段时期内,两个社团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博弈的过程,导致两个社团形成各自差异的职能分工。
受泰国移民政策以及中泰关系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华总商会逐渐成为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相比其他华人社团来说,中华总商会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当探讨潮州会馆与中华总商会的职能分工时,仍然不能忽略中国的影响。以中华总商会主席陈守明为例,在中泰建交之前,他作为国民政府驻泰国的商务专员,总商会承接了大部分的外交和领事工作。抗战胜利后,为帮助因战乱而流落异国他乡的侨胞回乡,国民政府在泰国清迈、宋卡、呵叻成立总领事馆,中华总商会均派出代表出席升旗典礼。此后,中华总商会是唯一一个全侨性社团,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具有固定接待场所,因而一直是接待中国来访官员的主要承办方。
二战后,潮州会馆则努力使华人能够更好融入泰国社会,积极响应配合泰国政府各种政策号召,救灾恤难,捐款慰劳军警,修建学校、医院、寺庙,对繁荣泰国经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均全力以赴①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
中华总商会和潮州会馆这两个组织成为泰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泰国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的历史情境下趋向本地化、公共化,两者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各自的职能分工和日常运作方式,不仅没有制造华人社团之间的冲突,反而形成了两者在日后的发展中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局面。
四、潮州会馆与中华总商会的联动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会馆与中华总商会的发展迎来了繁荣期。中华总商会在这一时期逐渐脱颖而出,扮演着令人瞩目的角色,在处理外交、侨务等事宜中发挥较大的能量。潮州会馆加紧团结旅泰潮侨的力量,促进泰华社会公益事业快速发展。
会馆与商会合作关系的事迹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来概述:
第一,商会与会馆用坚定的行动支持祖国抗日战争,但这也同时给商会带来了重大危机,泰国华人社会针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重新组合成立新组织,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组织上的高度统一。
第二,在经济情势剧烈变化的背景下,中华总商会与潮州会馆号召华商抵制日货及提倡国货的工作很有成效。
第三,抗战后期,潮州华侨各个慈善团体逐渐由分散归为统一,越来越凸显会馆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功能。
(一)商会和会馆合作成立“抗联”
1937年,日本侵略者开始入侵中国南方地区,而大部分南方地区正是旅泰华人的故乡,推动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和抗日热情。从1938年开始,在泰华商和华人开始了民族主义运动,目的是救亡图存,积极参与故土对侵略者的反抗,支援国内对日作战的各种政治组织,民众直接掀起民族主义的浪潮,发起募集活动并把所得捐款全部汇到中国作为抗战所需资金。
然而,泰国陆军銮披汶颂堪将军开始对泰国的华人采取严格的措施,要把华人的民族主义和社团活动控制在政府严格限定的范围之内。政府声明不论是中华总商会还是潮州会馆支援国内抗战的政治活动,或者募集资金都是属于非法活动,因此华人的爱国抗日组织必须转为地下活动②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
抗联就是由许一新、李华、黄耀寰、许侠、吴敬业(吴林满)等爱国潮侨筹建而成的,以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为主导,以“反抗侵略、全力救亡”为号召,在其他地缘性会馆的协助下,秘密成立的,下属学生、工人、妇女、工商界人士等分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活动。潮州会馆中的不少成员就是抗联的骨干分子。
潮州会馆为志愿回国参军报国的华人青年提供旅费支持,在抗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一些爱国青年华人,如欧阳惠、张庆川等7人,则直接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投身报效祖国的事业。次年又安排数百名潮籍爱国华人青年,组成“暹罗华侨抗日义勇军”,回国支援抗战①②陈骅等:《海外潮人爱国壮举》,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第54页。。抗联组织的回国人员,全部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韩江、琼崖纵队。抗联在全泰国设有40多个支部,将所筹集款项悉数送到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代表处。据统计,抗战时期广东籍华侨华人回国支援抗战人数约有4万人,其中有许多是潮汕籍华人②。
(二)商会和会馆共同号召“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在抗战合作取得丰厚成果的同时,中华总商会和潮州会馆在经济方面的合作也十分出色,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泰国的经济,致使泰国与日本进出口贸易额,从1937年9月的630万日元下降为1938年4月的270万日元③《日本统计书》,东京:国际日本协会,1942年版,第49页。。
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秘密组织暹华商界救国会,号召华商抵制日货,工作很有成效。商界救国会与大多数华商秘密议定,宁愿牺牲丰厚的利润,与日商断绝往来。与拒卸日货、抵制日货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商会联合会馆号召的提倡国货运动。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国货情况,1939年1月,潮州会馆成员林鸿兴、谢玉堂、梁永昌、廖真威等9人,组织“华侨祖国实业考察团”回国调查,不仅参观了上海工厂,而且转赴各地考察④《华侨考察团参观工厂国货联会设宴洗尘》,《申报》1939年3月5日,第3张,第10版。。1939年3月出版的《华商》中写到由于泰国华侨对国家遭受苦难感到十分痛心,所以大家都乐于支持购买国货的行动,根据泰国海关每个月的统计情况,日货进口量大幅减少,而中国进口持续增长⑤《暹罗中华中学校舍落成纪念刊》,曼谷:《华商》泰国中华总商会,1939年版,第29页。。中华总商会同时积极引导华商发展工商业,保护华商利益,得到了泰国国王的直接支持⑥《泰国中华总商会略历》,《星暹日报》编印,泰国:星暹日报社,1988年版,第11页。。
在泰潮侨在捐款方面也起了带头作用,带动了华人爱国捐款的大量募集,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泰国华人所募集的爱国捐款达到了240万泰铢,根据统计,抗战期间,爱国华人捐款总量超过了600万泰铢⑦蔡仁龙等:《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福建党史工作委员会,第522页。。在潮汕各地被日军占领之前,泰国潮州会馆组织运送泰国大米救济家乡灾荒,直到汕头被日军占领后,才被迫停止救灾工作。日本战败投降后,泰国潮州会馆及其所属同乡会立即成立“暹罗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推举爱国潮领郑午楼为理事长,筹集泰国大米约31000多包,运回到祖国以赈济灾民⑧《汕头文史》第10辑,汕头:政协汕头市文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75页。。
(三)商会和会馆共同保障华人权益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据泰国后,当时除潮州会馆主席陈景川外,会馆的绝大多数执行委员拒绝与日本合作后均被逮捕入狱⑨市川信爱,郭梁译:《泰国华侨社会的特点和各种华侨帮派形式》,《南洋资料译丛》1981年第3期。,其余爱国抗日华人分别转到泰国抗日义勇队或为避免逮捕而躲避到内地。中华总商会及潮州会馆为了保障广大华人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公开抗日活动进入了低谷期,商会与会馆的合作转到了对华人社会的服务。
1942年的秋天,泰国各地遭受罕见水灾,尤其曼谷及周边地区受灾严重,中华总商会及潮州会馆及时组织有效救济,受惠的灾民人数达到十六万多人。通过这次救济活动,潮州华侨各个慈善团体逐渐由分散归为统一。1943年,同盟国对曼谷进行轰炸时,商会与会馆组成了一个常务委员会,组织救济空难受害者①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页。
为避免受到銮披汶政府“大泰族沙文主义”的波及,潮州会馆在努力宣传潮州文化的同时,也努力将其与泰国本地文化相融合,使之成为泰国文化的一部分,促进了华人社区与周边泰人的和睦相处,有利于潮州人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华总商会提倡其成员与泰人通婚,促使这些具有经济实力和良好教育的华商转变成为华裔泰人,努力帮助华商群体成为泰国社会的中产阶级,最终成为泰国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泰国的拉玛七世国王(1925—1934年在位)就曾经表达过泰人和华人是兄弟民族②[泰]素攀·占塔哇匿:《泰国潮州人及其潮汕原籍研究计划》第二辑,曼谷: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1997年版,第3页。。
尽管当时的泰国政府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采取了一些同化政策,但从潮州会馆和中华总商会方面来说,文化融合并非配合政府的同化政策,而是泰国华人愿意融入当地社会。潮州会馆推动文化融合的成功,既和泰国文化的包容性有关,也与潮州会馆在政治上秉持不参与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因为在当时泰国政府看来华侨和平善良、无野心的性格,是不会产生任何政治上的危险的③邓水正:《19世纪中期以前泰国华人经济概述》,曼谷: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1997年版,第53页。。
五、结语
泰国中华总商会与潮州会馆关系发展过程中,泰国潮州人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泰国潮人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纽带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商会与会馆成员祖籍的亲缘和语言上的相同,使得两个组织在合作方面能更好地融合;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他们对于中泰两国的特殊感情,在抗战爆发的时候,祖国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了在泰潮人的爱国热情,使得他们紧紧团结在会馆或者商会周围,并且致力于成立新的救亡社团,积极开展爱国活动。可以说无论是中华总商会或者潮州会馆,都和泰国潮州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致力于促进中华总商会与潮州会馆关系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在泰潮人来说,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