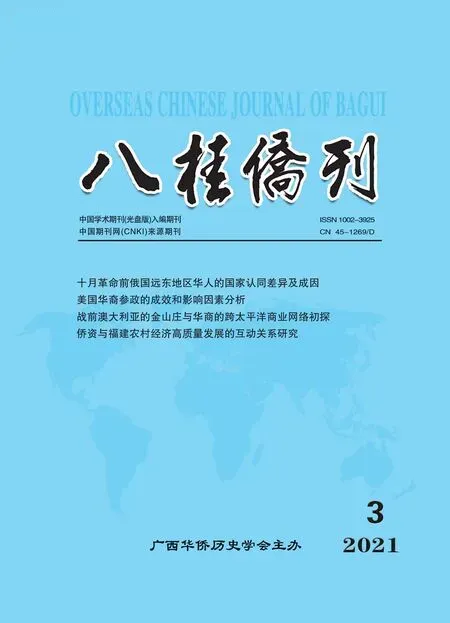十月革命前俄国远东地区华人的国家认同差异及成因
——以华商、华工和华农三大群体为研究对象
谢 倩 邵政达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
自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至十月革命爆发,俄国远东地区华人社会不断壮大,从职业上主要分为华商、华工和华农三大群体。他们为俄远东地区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沙俄不断扩张,而中国积贫积弱的不平等关系之下,华人内部不同群体在国家认同层面呈现出令人深思的差异性①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既包括旅居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华侨,也包括加入俄籍的华人,并将二者统称为“远东地区华人”。。学界对俄国远东地区华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华人移民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华人生存状况的考察②李永昌的《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论述了旅俄华工在帝俄时期的悲惨境遇及参加十月革命的情况;宁艳红的《旅俄华侨史》梳理了自“割地成侨”至当代的旅俄华人发展轨迹;俄国人格拉韦、纳达罗夫和翁特尔别格等的著作是研究早期远东地区华人生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参见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宁艳红:《旅俄华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俄]格拉韦:《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李春艳、吴春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俄]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相关研究鲜有关注远东地区华人的国家认同问题。本文拟就远东地区华人中的华商、华工和华农三大群体在中、俄两国国家认同上的差异性及其成因展开分析,以期深化学界对俄远东地区华人群体的认识。
一、俄国远东华人国家认同差异性的表现
19世纪中后期,因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及沙俄远东大开发的需要,除“割地为侨”产生的大批华人外,还有大批中国人进入俄据远东地区,为远东地区经济开发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由于地理上接近,俄远东地区的华人社会与祖居国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
早期前往远东地区的华人,多是由于在国内的处境艰难,生活得不到保障,才铤而走险,正如当时俚语所讲的——“死逼梁山下关东,走投无路上崴子”,意即前往远东地区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①方雄普、李斌斌:《俄罗斯及中亚东欧华侨华人史话》,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5页。。据统计,1910年以前,俄远东地区华人已达111446人,此外还有大量非法移民未计入。通过在远东地区的辛苦劳作与勤俭节约,华人纷纷将积攒的收入汇往国内。据俄方统计,19世纪后期,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乌苏里等地华人的资金汇兑额迅速增长,1889年滨海资金汇兑额为l579675卢布;1891年为2513918卢布;1893年已增至4010228卢布,1889—1893年间,华侨华人年平均汇款为2718869卢布②[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4页。。对于大多在俄远东地区经商或做工的华人来说,他们只是将这里作为谋生场所,而且多数在远东工作一个或几个季节后(最多不过3—4年),就会大批返乡。当然,仍有部分华人选择在当地扎根。华人中约有5%的人拥有固定住所,另有2%的人加入了俄国国籍③刘涛、卜君哲:《俄罗斯远东开发与华人华侨(1860—1941年)》,《延边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根据这一时期华人经济特点,可将远东地区的华人分为从事贸易活动的华商、赴俄佣工的华工和从事农业劳动的华农三个主要群体。三者虽同属于华人社会文化圈,但在国家认同的强烈程序和认同指向上表现出一定差异。
华商群体在整体上有着比较强烈的国家认同倾向,但群体内部对中、俄两国的认同指向存在差异。远东地区华商群体的贸易行为具有跨国主义性质,他们往往从中国进货,再前往俄国境内进行贩卖,与中俄两国都有经济联系,同两国民众交往也都比较密切。据《烟台贸易年报》记载:“山东地方,向称人民输出货物往西伯利亚,为有名之地。每年由此人民寄归金额甚多。烟台市场,现存俄币约称4万元。”④徐万民:《东帮华商在俄国远东》,《黑河学刊》1993年第2期。作为旅俄归国华商的代表,邵宗礼回国兴办实业的事迹一直为人传颂。1909年,由于俄国政府的打压,邵宗礼一家回国发展,凭借雄厚的资金,投资两处戏院,兴办金矿,并开设商号——“广聚公”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黑河文史资料·第8辑》,引自《旅俄华侨史料选》,黑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1991年,第93页。。邵宗礼本人乐善好施、秉性慈祥,被推举为“黑河慈善会”会长,之后更是大力劝导地方兴办教育⑥宁艳红:《黑水为证:旅俄华侨的历史记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4页。。富贵还乡后回报祖居国正是这一时期旅俄华商的普遍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部分华商为便于在俄国远东地区更好地开展贸易,选择加入俄国国籍或者皈依东正教,这在客观上推动部分华商产生了对俄国的国家认同或双重认同。著名旅俄华人纪凤台即是典型。他于1893年正式加入俄国国籍和东正教,并取俄文名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他乐于帮助传教士,自认是一个亲俄分子⑦[俄]尤·奥希波夫:《俄籍华商纪凤台》,《长白论丛》1996年第2期。。中俄通婚也是旅俄华人对俄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表征。华商凭借自身经济实力成为华人与俄国本地人联姻中的主力军。早期赴俄华人多为男性,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部分单身男性华人在具备一定经济能力后选择与俄国当地女性结婚。据统计,1880年,在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沿岸的6628名华人中,有99人与当地俄国人结婚。俄国法律规定,入境华侨需皈依东正教,方可与俄国女性通婚⑧宁艳红:《旅俄华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通婚的行为不仅使旅俄华人得以长期合法居留俄国,也推动他们加入俄国国籍,进而产生对俄国的国家认同。
就华工群体而言,他们在国家认同层面普遍保持了对祖居国的强烈认同感。旅俄华工饱受俄国资本家及官僚的剥削与压迫,生活十分困苦,为此,他们不断掀起反奴役和反压迫的斗争,仅在1916年就发生了6起较大规模的华工反抗斗争事件①宁艳红:《旅俄华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3页。。由于在俄国的生活困苦,华工寄希望于中国政府能提供一定的保护。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正值中国剧变之际,清政府及之后的北洋政府都面临内忧外患,但仍设法通过一些措施保护旅俄华工群体。例如,驻俄公使刘镜人于1916年拟定《华工赴外工作章程》、《地方官关于华工出境应尽事务章程》和《通商事务员管理华工规则》,以规范招工行为,避免同胞惨遭凌虐②李志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时期的赴俄华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5期。。尽管中国政府的保护举措并未对旅俄华工处境的改善起到实质性作用,但在客观上有效增强了华工对祖国的认同感。
正是对中国强烈的认同使得他们时刻不忘中国的革命事业,远东地区的华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特殊作用。旅俄华工接触革命思想较早,部分华工还参加了远东地区的工人赤卫队,投入到创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③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83页。。1916年5月,旅俄华工华鸿图在上海创办“中华农工联合会”,为广东农工会的上海支部。该组织一面宣传马列主义,一面联合农工组织罢工运动,其目标是“破坏资本主义,铲除人类剥削人类之恶习,实行社会主义,无阶级之分,无国家强迫之苦。”④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35页。华工通过创建工会向国内传播先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关心国内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对国内的无产阶级运动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就华农群体而言,虽然绝大多数仍延续传统上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但这种认同的程度相对较低。不同于华商和华工群体普遍存在的、鲜明的国家认同观念,华农的国家认同观念较为淡漠。华农在经济上具有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形成了较小的华农社会圈,对于中俄两国的认同都不明显。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时,较少考虑到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一时期华农较多从事鸦片种植,鸦片的主要去向就是中国。据统计,1906年,滨海省罂粟播种面积是200俄亩,1910年,滨海省罂粟播种面积是306俄亩。另据俄人统计,1897年滨海省销往中国的鸦片达200普特⑤[俄]索洛维耶夫:《资本主义时代的旅俄华工在远东(1861—1917)》,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0页。。
总之,早期的俄远东地区华人大多认同“中国人”身份,不仅积极往国内汇款、投资建厂,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还促进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无产阶级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华人内部不同群体在国家认同层面上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华商中有少部分通过加入俄国国籍、信仰东正教及与当地女子通婚等方式,在远东地区落地生根,逐渐产生了对俄国的国家认同。相较而言,华工群体普遍保持着对祖居国的强烈认同,而华农群体在国家认同感上普遍较淡薄。这种国家认同层面的差异是由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
二、经济地位的高低影响民族认同的差异
经济地位是反映个人社会阶层的重要指标,也深刻影响着个人思想观念的形成。一般来讲,某一群体在某一地域经济地位愈高,该群体同该地区的利益联系也愈发密切,也易对该地区产生认同。华商、华工和华农三大群体在俄远东地区不同的经济地位深刻影响着各自在国家认同上的差异。
其一,这一时期远东地区华人中人数最多的华工群体经济地位极其低下,成为塑造该群体国家认同观念的重要原因。受俄国远东大开发政策的影响,华工作为最早进入远东地区的华侨群体,成为远东地区经济开发的主导力量。驻海参崴商务专员致外务部函表明,1907年,从山东烟台前往海参崴的华工已达六七万,而仅在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间,到海参崴华工已有四千余名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99页。。大量华工进入远东,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且多从事俄国工人以及外国工人不愿做的,最为辛苦、脏乱和危险的工作,如修筑铁路、开采矿业等。据1910年俄国政府官方统计资料表明,从事公务劳动的外国人共有26443人(其中阿穆尔省3 467人,滨海省为22976人);从事金矿劳动的有20022人;乌苏里铁路工人4939人,总计51404人,而在这些外国工人中华工占81%以上②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9页,第21页。。
华工所受待遇与其经济贡献不成正比。工资层面上,191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管理局俄国工人的日工资是1卢布到1卢布80戈比,而华工工资则仅为60戈比到1卢布,在私人企业中受雇的华工工资还要低得多③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9页,第21页。。华工不仅在工资待遇上远低于同种工作的俄国工人,基本人身权益也得不到保障。华工不仅工作强度大,而且经常忍饥挨饿,受到雇主各种名目的盘剥、控制和歧视。有俄国老板建立警察部队专门用来监管华工,甚至导致一些人不堪折磨而自杀④Gregor Benton and Frank N.Pieke eds,The Chinese in Europ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p.284—285.。远东地区华工饱受俄国资本家和官僚压榨,处于当地社会的最底层,经济地位十分低下。
正是由于低下的经济地位和遭到不公平对待等客观因素,远东地区华工不仅难以对俄产生国家认同,反而易激发反俄情绪和对祖居国的强烈认同。1916年,哈尔滨包工头林程(音译)招聘580名华工到库页岛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铁路第712块里程碑处的一个伐木场做工。忍饥挨饿、疾病缠身、痛苦不堪的华工每天天不亮就被赶到工地做工。在未得到任何工钱,还被通知继续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的华工手持斧头冲向管理所进行反抗,最终被哥萨克警察持枪无情射杀,同样发起反抗的还有铁路线718块里程碑处的华工。在铁路工人的激发下,更多的华工投身于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运动,构成远东地区无产阶级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⑤[苏]H·A·波波夫:《中国无产者在沙皇俄国》,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70—72页。。
其二,华商群体在俄据远东地区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远东地区生产力落后,加之俄国大力推行开发政策,为华商群体提供了机遇。卓越的经商能力使他们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地位,俄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具有卓越的经商才能”⑥[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9页。。华商经营种类繁多,销售途径广泛且方式灵活,通过广建中小店铺的方式在与俄商的竞争中占据先机。不仅如此,据阿穆尔地区著名商业顾问塔达统计,俄商开办企业的成本远高于华商。俄企的经营开支包括:员工工资、食宿、奖金、租用商场和货栈及照明、取暖、店铺和商品保险等,还有一些小项支出,总计占到营业额的15%—20%。与之相比,同等规模的华商企业开支则不超过其营业额的5%—8%⑦[俄]格拉韦:《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李春艳、吴春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2—43页。。主要原因在于华商吃苦耐劳,更擅长节约成本、缩减开支,因此不但能够赢得竞争优势,还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另外,就资金规模来说,1908年海参崴20万资本以上华商商号共有16号,2万资本以上有100多号,而千元、百元以上者高达400—500号⑧宁艳红:《浅析早期旅俄华商的经贸活动及其作用》,《西伯利亚研究》2014年第5期。。华商在远东地区的发展规模虽以中小企业为主,但因其数量之多,仍对远东地区的商业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华商在远东地区创办的大型商行,虽数量不多,但其资金充足,能够发放贷款甚至资助中小华商企业,在事实上主导着远东地区的华商网络,经济地位自然不言而喻。
较高的经济地位也给部分华商在俄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赴俄华商多值青壮年,且有一定经济实力,不仅能够支撑家庭开销,也能让女性免于外出劳顿,对于男女比例失调的俄国女性来说,是极佳的择偶对象。据统计,在沿额尔古纳河的村落中有33对华商与俄国女子结合的婚姻。此外,在黑龙江边境一带,瑷珲兵备道所辖关卡还有许多华商与俄国女子通婚后回国定居①宁艳红:《旅俄华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婚姻关系是远东地区华商国家认同的重要导向,同俄国女子结婚可获得俄国国籍,进而达到长期在俄国经商的目的,这部分华商易对俄产生国家认同。对于同俄国女子通婚后选择回国定居的华商,其对祖居国的国家认同更为强烈。总之,较高的经济地位是华商拥有较强国家认同观念的基础,也是部分远东地区华商转向对俄认同,或对中俄双重认同的重要因素。
其三,华农群体经济地位相对较低。早期华农多是根据《北京条约》条款留在远东地区的当地居民,数量庞大,光阿穆尔省就有10646名②[俄]索洛维耶夫:《资本主义时代的旅俄华工在远东(1861—1917)》,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9页。。随着俄对远东地区的大开发,华农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1879年,华农在南乌苏里边区耕种5791俄亩土地,其中在兴凯湖区耕种2034俄亩,在苏城区耕种2567俄亩,在绥芬河耕种497俄亩,在阿瓦库莫夫区耕种693俄亩③[俄]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3页。。因华农的生产技术先进,粮食产量较高,因此备受好评。英国人沃特·杰拉里在1902年参观远东地区时曾说:“中国农民可以在1俄亩的土地上种植出比俄国农民在1英亩土地上所种植出更多的东西来。”④1俄亩约等于2.7英亩。参见陈碧笙编:《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02页。
相较于华工和华商在远东经济中的突出特点,华农群体较少被人关注,但其在推进远东地区大开发进程中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但自19世纪80年代起,由于从欧俄前来的农业移民数量不断增多,华农被迫从占用的土地上迁移出去,这种强制迁移一直持续到1906—1907年⑤[俄]亚历山大·拉林:《中国移民在俄罗斯:历史与现状》,刘禹、刘同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割地成侨”的华农逐渐丧失了对祖居土地的所有权,只能向俄国移民租赁土地,如在绥芬河和济木河流域就有200余名土地主将土地租佃给中国人和朝鲜人⑥[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1页。。在这一过程中,华农经济地位持续下降,大多以佃户或雇佣农的身份过活,在远东地区华人社会中处于中下地位。由于经济地位低下,自身利益又得不到保障,华农较难对俄国产生认同,同时因为权益也无法得到中国政府的维护,传统上也对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淡漠。
总之,十月革命前,远东地区华人经济地位因职业分工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华工作为远东地区华人的最大群体,虽为远东地区经济开发做出巨大贡献,但处境艰难,经济地位处于最底层。远东华商经济地位较高,在远东华人社会中处于中上阶层。华农主要是租佃户或雇佣农,经济地位普遍低下。经济地位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不同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地位低下的华工对中国的认同更为强烈;经济地位较高的华商国家认同感也较强,但部分华商已经形成对俄认同或双重认同;华农群体则对中俄两国的认同都较为薄弱。
三、社会交往程度影响民族认同的差异
作为跨国群体,华人的社会交往指其同祖居国和现居国的社会交往。由于职业特点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远东地区华人内部不同群体对中俄两国社会交往的程度呈现显著差异,从而影响了各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异。
首先,华商的社会交往活动最为频繁,同两国社会的双向联系较为密切。华商主要在远东地区从事贸易活动,且多以中小型贸易为主,因而较多采取走街串巷的行商经营方式进行货物交换。“自三姓贩运货物,通行松花江至东北海口,行乌苏里江至穆棱河口以上,以货物易物,分售伯利、三姓等处”是华商的主要贸易路线之一⑦丛佩远、赵鸣歧:《曹廷杰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6页。。行商经营不仅可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华商深入远东地区社会内部,强化与当地居民的联系。华商与当地居民的贸易主要采取以货易货或赊账的方式,通常是用生活必需品、猎具和酒精换取当地人打猎而来的毛皮①[俄]格拉韦:《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李春艳、吴春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0—51页,第78—79页。。
除行商经营外,远东地区华商还在当地开设店铺,扎根当地社会。以滨海省为例,华商经营面广泛,不仅有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还有各种售卖小商品的货摊,省内各城市和乡村都开设有商店②[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90页。。经营场所的固定化有利于顾客群体的稳定化,为华商与当地居民深入交往提供了便利。此外,一些开设大型商行的华商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能够接触到俄国社会上层,甚至担当俄当局的中介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华商刘福,被清朝官员称“华貌俄心”,“内地苟有举动,俱一一为俄人言之”③丛佩远、赵鸣歧:《曹廷杰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7页。;华商纪凤台因精通俄语和过人的经济头脑,在俄国社会积累了大量人脉。1891年纪凤台还被当时的皇储尼古拉接见,随后与俄国人合作开辟了哈巴罗夫斯克至松花江的货运航线,借此垄断该条航线的贸易。日俄战争期间,纪凤台积极为俄军服务,为此付出多年积累的财富④潘晓伟:《十月革命前俄罗斯远东地区华人商业活动》,《西伯利亚研究》2017年第5期。。深入而频繁的社会交往在客观上使部分华商逐渐产生了对俄的国家认同。
与此同时,华商同中国社会的交往活动也十分频繁。往国内汇款是华商同中国国内最普遍的联系方式,特别是山东省成为远东华商钱款的主要去向⑤徐万民:《东帮华商在俄国远东》,《黑河学刊》1993年第2期。。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远东地区华商籍贯多是山东省。此外,远东地区华商还凭借雄厚的实力在国内投资建厂,大力发展工商业。例如远东地区华商中的翘楚——张廷阁,从1912年开始,先后将其经营的大型百货商行“双合盛”的资产陆续转移到国内,之后于1914年在北京创办啤酒汽水厂,1915年在哈尔滨设立双合盛制粉厂等,并积极担任社会职务,响应国内实业救国的热潮⑥张宗海、张临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华商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形成和发展》,《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2期。。华商在国内投资建厂,将资本和国内社会相结合,不但创造较多就业机会,还促进当地实业发展。远东地区华商与中国社会的密切交往是与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相互促进的。
其次,华农扎根远东地区,同中国社会交往程度最低,同时受农业经营方式影响,其同当地社会的交往也并不密切。早期远东地区华农大多是“割地成侨”,仍主要从事农业耕作和农副业种植。虽然华农为远东地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需求,但因华农负责种植生产而非销售活动,与当地社会的交往并不密切,仍徘徊于当地居民生活圈之外。自给自足和依附于土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之缺乏国家认同观念。
最后,华工在俄生活闭塞,但多数能够定期往返中俄,与中国社会保持着紧密联系。一方面,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限制了华工的生活圈。华工多从事采矿、修路以及伐木等条件艰苦的体力劳动工作,工作时间长,大多集中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的工棚,生活环境闭塞,除资本家老板和包工头外,华工较少能接触俄国当地社会。据远东华工刘福回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赶修摩尔曼斯克铁路,他们得在零下40至60度的天气中日夜三班工作,伐木、铲土、铺石子,许多人甚至冻掉了脚趾头、耳朵和鼻子⑦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红旗飘飘第4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45页。。19世纪80年代的采金华工,工作时间为清晨5点至晚上8点,只在下午2点时有半个小时的用餐时间。他们以10至12人为一团,住在又脏又窄的小工棚里⑧张宗海:《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1—122页。。
华工消费能力低,且大多出身社会底层,识字率低,又不会俄语,这些因素也大大限制了他们同当地社会的交往。据1909年滨海省驻军司令的奏折记载,在海参崴,一个俄国工人每月的消费额为19卢布37戈比,而一个华工的月消费额仅为5卢布10戈比;在伯力,一个俄国工人的月消费额为22卢布38戈比,而华工仅为4卢布97戈比。表1中阿穆尔省谢列姆热公司矿工的月消费情况直观地反映了华工的消费能力⑨[俄]格拉韦:《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李春艳、吴春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0—51页,第78—79页。。

表1 阿穆尔省谢列姆热公司矿工的月消费情况
因此,相比在远东地区社会中处于半隔绝状态的华农,华工多像候鸟一样,定期往返中俄两国。以较多的烟台籍华工为例,他们大多为18—30岁之间的青壮男子,在每年的三四月份离开烟台,当年十一或十二月份由海参崴返回①张宗海:《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就此而言,华工和中国社会的情感联系更为强烈,渴望“看到故乡的太阳、亲人、家祠和祖坟”②[苏]诺沃格鲁茨基,T·杜纳耶夫斯基:《中国战士同志》,纪家俊等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第14页。。密切的社会交往与情感归宿强化了华工群体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综上,远东地区华人各群体与中俄社会的交往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华商同两国社会皆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华农扎根当地,但受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与当地交往并不密切;华工定期往返中俄,在俄国主要限定在工作地狭小的生活圈,而与国内的联系较为密切。由此,华商与华工群体多数都保留对中国强烈的国家认同,部分华商也产生了对俄的认同感,而华农鲜有这种现象。
四、中俄政府政策影响国家认同的差异
对于具有典型跨国主义性质的远东地区华人来说,祖居国与住在国对其的认可、保护或压迫、排斥都会直接作用于其国家认同的心理。因此,中俄两国政府对远东地区华人的政策也深刻地影响着华人的国家认同。
就俄方而言,俄国政府对远东地区华人的态度大致呈现出由初期的积极包容到后期的消极排华这一转变。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政府以政治恐吓和武力威胁的方式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确立对远东地区的统治。为紧急开发远东地区以巩固政权,俄国政府颁布移民法令,加快开发速度。1861年俄国移民法规定,阿穆尔地区对俄国和外国移居者开放,且额外规定每户移民的每个人可按每俄亩3个卢布的价格最多占有100俄亩的土地,并免除10年兵役和20年赋税;1866年,俄国政府又在远东地区开放47万俄亩的优质土地,并免除赋税24年③[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11页,第13页。。受俄国政府早期移民政策的影响,华人可以享受同俄国本土移民同等的待遇,由此远东华人数量迅速增长。19世纪70年代,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沿岸每年有500多名华人前往俄国境内,至1885年时,乌苏里地区登记在册的华人已达10353人④[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11页,第13页。。俄国政府对远东地区实行积极的移民政策,以吸引人口的大量增长,为华商提供市场资源,为华工提供工作机会,优惠的土地政策也满足了华农的生存需要。
19世纪末,伴随着远东地区华人的不断增多及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影响力的日增,俄国政府感到威胁,转而开始限制和排挤华人。1886年,沙俄政府禁止中国人在同中国相邻的俄边界地区居住,以限制远东华人数量①③⑧[俄]格拉韦:《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李春艳、吴春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页,第112页,第54—55页。。此后,俄当局又实施一系列排华、限华活动。相对而言,对华人内部群体而言,俄国政策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华工首当其冲成为俄国政府的打压对象。华工吃苦耐劳,所求工资低,因此雇佣率极高,在某种程度上抢占了俄国本土工人的就业机会。从1906年起,俄当局严查海参崴等地的华工护照,并每年押解无照华工返回烟台。1907年春,一千多名从山东前往海参崴的华工被遣返②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00页。。俄当局不仅实行严格的护照审查制度控制华工数量,还限制俄企雇佣华工。1910年6月21日的法令规定,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禁止在国家部门所需要的工程提供或雇佣外国人,并禁止将工程承包给外国人③。另外,俄国政府还借满洲里疫情之名,大肆排挤华工,禁止华工入境。1911年2月6日,西伯利亚总督宣称,为控制鼠疫流入俄境,禁止华工进入阿穆尔省④管书合、杨翠红:《防疫还是排华?——1911年俄国远东地区大规模驱逐华侨事件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不仅如此,1912年5月,俄国杜马还递交《保护远东地区的俄国劳动力、抵制中国劳动力》议案,全面限制远东地区对华工的雇佣⑤宁艳红:《旅俄华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法令颁布后,华工群体遭到毁灭性打击,就业机会锐减,多数只能回国。由于俄当局对华工的打压,使华工难以在俄境内生存和发展,反而激发了他们反抗俄政府的情绪,遑论对俄产生国家认同。
华农同样深受俄政府打压。自1882年起,俄政府规定远东地区的外国人不再享受1861年移民法令中有关免除赋税及购买土地的优惠政策,之后更是禁止华人购置土地⑥孟昭慧:《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俄国远东地区华人探讨》,《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第3期。。不仅如此,俄政府还勒令华农将早年拥有的土地转让给移民至此的俄国人。在西伯利亚总督于1883年呈送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曾间接汇报此事,“鉴于重要原因要将新移民顺利安置到中国人所占土地上,恳请您悉数恩准中国人自行取走已经种植的粮食和蔬菜,方可使其离开。”⑦[俄]亚历山大·拉林:《中国移民在俄罗斯:历史与现状》,刘禹、刘同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在俄国政府的打压下,华农大多沦为佃户或雇佣农,由此华农群体尽管植根当地,遵纪守法,但难以真正获得归属感,也很难形成对俄的国家认同。
华商虽也受到俄政府的限制,但相较于华工和华农较为宽松。1893年,滨海省驻军召开由地方杜马以及富商大贾参加的会议,拟对华商实施加大征税、建立稽查团体、三次逃避规定即驱逐出境以及限期关闭店铺等限制措施,但遭到驻军司令翁特尔别格的否决,其理由是“为了消费者利益,不应采取过激措施。”⑧之后,俄当局的限制主要限于对华商商品加税⑨张宗海、张临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华商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形成和发展》,《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2期。。在出入境管制方面,华商受到的限制比之华工轻微。1911年东北爆发鼠疫期间,俄当局虽然严格禁止华工入境,但对华商的限制并不苛刻,如阿穆尔地区的华商只需留验五日未发现疾病,即可正常通行⑩管书合、杨翠红:《防疫还是排华?——1911年俄国远东地区大规模驱逐华侨事件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华商在俄远东地区经济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以至于俄国政府很难在不影响市场的前提下严加打压,因此,较为温和的限制措施成为这一时期华商在国家认同方面区别于华工与华农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内忧外患下,仍能出台部分保护政策,维护远东地区华人权益。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采取中国封建王朝传统上对华人的排斥态度,将之视为“弃民”“莠民”“贱民”,或斥为“不肖子孙”,甚至还下过“康熙五十六年以后入洋者不许归国”之类严格禁令[11]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页。。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攻占北京,民族危机加剧,迫使清政府改变内政外交政策,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海外华人成为清政府开眼向洋的重要媒介,符合振兴商务和巩固海防的需求①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8页,第203—204页。。1860年的《北京条约》包含“允许华人出国”的条款,推动远东华人数量急剧增长。清政府也很快转变观念,对海外华人实行保护政策。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人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民国政府延续了对华人的保护政策。
特别是海外华人中最易受侵害的华工群体,中国政府出台了相应政策尝试加以保护。1865年,恭亲王奕讠斤发布招工章程22款,规范华工出国流程,减少诱拐坑骗行为,主要内容有:严禁贩卖人口,违者处死;招工的商人需由中国地方官核查,出洋时需由地方官员会同领事按契约核对人数等②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8页,第203—204页。。另外,为改善华工在外处境,中国政府曾一度要求俄国远东地区的工厂在合同终止或工人生病时将工人运回家,而不是简单地解雇他们;要求减少对旷工的罚款;明确规定受伤时应支付的赔偿金数额;减少承办商的佣金;在寒冷的季节,为华工提供柴火;要求华工享有与俄罗斯工人同样的工作条件和权利③Gregor Benton and Frank N.Pieke eds,The Chinese in Europ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282.。尽管这些政策在实践中收效甚微,但其为保护华工人权做出了努力与尝试,给身处惨境中的华工以慰藉,加深了华工与中国的情感联系,强化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总之,远东地区华人的国家认同受中俄两国政策的影响。俄国政府限制华工入境,削减华工就业机会,剥夺华农土地,打压政策较为严苛,但对华商的限制较为温和,这在客观上造成华人各群体在国家认同中的差异。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俄远东地区的华人,特别是华工的保护和声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华人对祖居国的国家认同。
五、结语
19世纪中后期至十月革命前,尽管绝大多数远东地区华人延续传统上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但内部差异明显,这同各华人群体的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程度以及中俄两国政策密切相关。相较而言,由于经济地位较高、与俄社会交往较密切等原因,华商群体中的部分已形成对俄国家认同或对中俄的双重认同。华工群体经济地位较低,与俄社会交往也非常有限,且受俄政府打压沉重,加之中国政府为其权利发声等因素,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最为强烈。华农群体因其生产生活方式的自给自足性质,国家认同感普遍较低。但无论如何,在十月革命前,俄远东地区的华人社会已经初具规模,无论是华商、华工还是华农,各群体都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认同层面的差异是这一地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相互交织。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远东地区也很快受到革命洗礼,华人社会面临新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