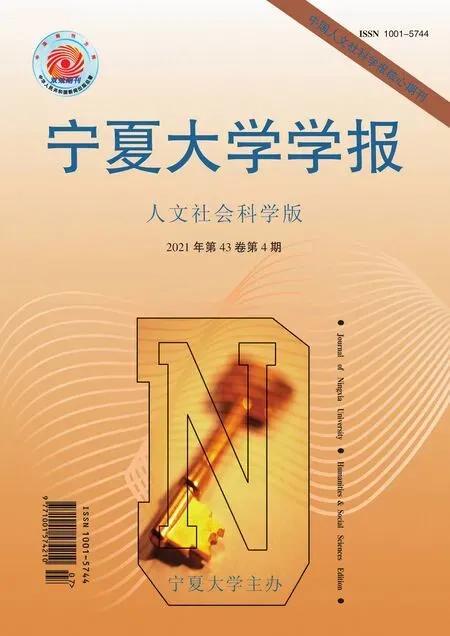商代教育史研究中的概念辨析与反思
——由甲骨文中的“教”和“学”说起
徐锦博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商代教育史研究既属于教育史研究范畴,同时处于殷商史研究时段,而殷商史距今年代久远,研究资料较少,且涉及以甲骨卜辞为核心的出土材料,具有一定难度,这客观限制了我们对于商代教育史的研究。推进商代教育史研究,要敢于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进行创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尤其要重视基础性的材料考证和概念辨析,从史料研究中寻得突破,夯实研究基础。学界已有教育史研究者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初步探讨了利用甲骨史料研究教育史的展开方向,强调了出土材料的重要价值[1]。将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切实运用在对具体问题的探究中,会进一步推进商代教育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在鼓励利用出土材料开展研究的同时,利用甲骨材料对商代教育研究进行阐释,应当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部分商代教育史研究成果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资料的运用和解读存在偏差,有关商代教育中的基本概念还需进一步辨析。本文在尝试进行商代教育史研究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深度解读涉及商代教育史研究的部分甲骨材料,对商代教育史研究中“教”与“学”的基本概念进行辨析,探讨商代教育的特性,以期为更好地推动商代教育史研究提供基础。
一 有关商代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反思
近年来,不少教育史研究专家提出有关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问题,对于教育史性质、范围、边界划分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提出回归历史研究的本性和教育史学科的本来面貌[2]。从教育史概念上讲,“教育史是教育的发展历程,即关于教育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3]。从学科属性上讲,“教育史学是历史学科与教育学科交叉而成的一门学科,具有双重的学科属性”[4]。教育史研究要在新时代有所突破,势必要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有新的探索。教育史研究应当多从历史学、教育学等其他相关学科中借鉴理论方法,并且能够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对以往的研究内容在史料和研究角度上有新的突破。在多学科结合探究的过程中,对于新理论、新史料的利用,要遵循学科特点,明确适用范围。关于古代教育史研究,有一个理论认识方面的基本点,就是要充分认识到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教育思想、教育状况、教育制度等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烙印。要回归到历史情境中,不能脱离时代看问题。
我们经常将历史比作一条河流,可以溯源而上,探究历史长河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但却不能轻易地将下游的一朵浪花与上游的一串水珠直接对应,这种简单的对应,割裂了事物在漫长时序中的变化与联系。百川归海和今胜于昔的观点并不能直接套用去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却部分存在这种线性的历史观,认为“中国古代教育的特性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不断发展和日益丰富的”[5]。这种观点为众多研究者所接受,但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在教育学理论中,对于广义教育与狭义教育的区分不仅仅是对事实的概括,实际上隐含着一种价值的判断,即正规的教育必然优越于非正规的教育,制度化的教育必然优越于非制度化或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教育。正因为如此,现代教育必然优越于此前一切时代的教育”[6]。这种线性的、机械的历史观,制约了教育史研究,掩盖了教育发展的时代特性,对研究者探讨教育历史的积极性和必要性是一种削弱。如果先入为主地采取这种价值判断,势必影响研究者对于历史上教育状况的分析把握,很可能会出现削足适履般的简单对应和错误解读,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历史发展的状况。
就商代教育史研究而言,在线性历史观的影响下,不少研究者将视野局限于讨论正规学校教育的变迁,试图将后世的教育思想、教育机构、教育制度等在商代就要找到所谓“雏形”和“根据”。为了找出前代与后代教育内容的“跨时空”交流,梳理所谓清晰的“发展路径”,难免会出现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的问题。部分学者在未完全掌握和理解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急于对商代教育性质下定义,离开特有的历史环境阐发其中的教育思想,甚至倒推发展脉络,这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学校教育是最有代表性甚至是唯一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在学校教育的框架中去理解商代教育,那么,这就曲解了教育史本质,有关商代教育史研究必然会陷于研究领域狭窄的窘境。
利用甲骨材料研究商代教育史,这从研究思路和材料发掘方面无疑都具有创新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甲骨材料自身具有特殊性,一些甲骨片中虽然刻写有少量文字,但是整体却残损,仅有的几个字很可能使我们无法准确理解材料的全部信息。大量甲骨材料本身呈现出“断章”的特性,贸然强行“取义”,势必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真实性的整体把握。甲骨材料中还有不少单字现在学界还无法准确释读,即便能够释读的文字仍然有很多争议。不少甲骨文专家对文字的解读各持己见,一位专家考证某字为地名,另一位专家可能将其释为行为动词,无意义的修饰语或者也可释为祭祀礼仪,此类情形在古文字学界是常见的。就学术研究的层面而言,这样的学术争鸣会拓展研究深度,使得专项研究更加贴近历史真实。但由于各家释义不同,一条卜辞中某个单字的释读可能使得整条材料性质都发生变化,材料表意会截然不同。这也造成了我们利用甲骨材料展开具体研究必然会面临一定的学术风险,所以在利用出土材料的过程中要格外谨慎。
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长”的理论,认为“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组、不断改造和不断转化的过程”[7]。人作为教育活动即“生长”的核心,必然同时扮演者施教者和受教者两个角色。回顾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从教育的角度考虑,一直伴随着“教”和“学”这两方面的内容。“教”和“学”的推进是非常复杂的,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即使是在商代,“教”和“学”也绝不是单一地在课堂里完成,涉及的内容也不只是“六艺”,其目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技能习得。从甲骨材料看,部分卜辞中的“教”和“学”有着特定的含义,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定义有一定差距。商代的教育模式是否可以称之为“学校教育”,这也是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
二 甲骨文中的“教”与商代教育基本概念辨析
商代虽距今已有三千余年,有关商代教育史的内容却并未湮灭,我们仍可以从部分传世文献中一探究竟。根据文献记载,上古三代时期似已出现了专门的官方教学机构,《礼记·王制》云: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8]。
郑氏注云:“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礼制要义》卷五《王制下》云:“以下文云:‘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则左学小,右学大。此经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故知殷制也”[9]。从文献资料来看,商代已经出现了“庠”“序“”左学”“右学”“大学”等教育机构设施,有关商代的教育制度已经初见端倪。商史专家宋镇豪先生就认为“这些机构设施均属于贵族子弟就教场所,反映着虞夏商周的学校教学制度”[10],不少专家学者也基本持有同样的观点。
有教育史研究专家提出过质疑,陈青之先生的《中国教育史》从审查史料的角度认为,《礼记》《白虎通义》等文献中记载的上古教育制度,全属汉人作品,“此处所谓上古教育制度,完全由他们捕风捉影,假托古制以见己意”,属于后人臆造的史料。所以“商代以上,虽有教育事实,绝无教育制度”[11]。就文本资料的成书过程而言,《礼记》成书于西汉,是戴圣辑录战国以来学者们对于古代礼制的著述汇编而成。书中各篇章成书年代不同,经过了漫长的流传过程,难免会有佚失和伪窜;且创作年代距离商代已远,资料的来源成疑;汉儒崇尚三代制度,个人的历史观念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在其历史著述中,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其未必能够真实地反映商代的教育状况。研究商代教育,仅凭传世文献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图一 《甲骨文合集》5617号卜辞
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部分教育史研究者开始关注甲骨文,并尝试运用相关材料试图还原当时的教育状况。在不少古代教育史研究著作和教材中,都涉及有关商代的教育状况,但是细究其中部分涉及甲骨材料的内容,却存在一些问题。在研究商代贵族教育状况时,有著作引用了甲骨卜辞论证:“乎多伊·教王族”[12]。笔者仔细翻查了这条材料,实际上是《甲骨文合集》(下文均简称《合集》)中的5617号卜辞[13(]见图1)。教育史丛书中对于这条卜辞的释读存在很大的错误,直接曲解了原本材料中的内容。这块卜骨中间有一条比较清晰的界划,表明这片卜骨中的文字实际上是两条卜辞而非一条。其卜辞云:
呼多朿尹次于教。
王族。(《合集》5617)
同样,在《从殷墟甲骨文论古代学校教育》这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了一条卜辞“癸巳卜,其呼戍?……其教戍”,并将“教”理解为教谕人员,“就是占问商王要不要教谕人员出征、戍守、田猎和训练车马”[14]。细查该文作者所引甲骨材料,是无名组的一版卜辞:
癸巳卜:其乎戍……
弗利。
丁酉卜:其乎·多方蠢小臣。
其教戍。
亚立,其于右利。
其于左利。(《合集》28008)
这版卜辞郭沫若先生在一开始释读时仅仅看到的是未经缀合的残辞,误以为只有一条卜辞,错释为“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他当时认为“多方,多国也…据此,可知殷时邻国,多派遣子弟游学于殷”[15],其解释在今天看来显然也不符合卜辞原意。这块卜骨后经缀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材料,是有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占问军事戍守和布阵的相关事宜。“戍”指戍守,“教戍”可与“乎戍”对应,意思是戍守于教地,而非“教戒”,当与教育无关。
文章作者虽已经将“戍”释为“戍守”,却把“教”理解为“教谕”。商代教育史学者章小谦先生对这条材料也进行了辨析,介绍了相关卜辞最新缀合的研究成果,认为“‘教’和‘戍’合在一起,是‘训练部队戍卫边陲’的意思”[16]。“教”在卜辞中除个别由于甲骨残损造成语句字词缺失,无法准确释意的情况外,多指代地名和占卜的贞人名:
戊戌卜:雀人刍于教。(《合集》20500)
前一条卜辞旨在于戊戌日占卜有关雀人在教地从事农业活动的情况,“教”指代地名。屈万里先生针对这条卜辞也认为“于此为地名”[17]。后一条则是由“教”这位贞人在庚戌日占卜今天是否会有灾祸,“教”在“贞”前,无疑是指代贞人。所以将上述甲骨卜辞中的“教”理解为一种行为动词,进而假想其已具有现代语意中“教育”“教学”的含义,词义词性偏离了材料原意,而在此基础上对有关商代教育的解读也就不能成立了。
三 甲骨文中的“学”与“大学”
韩愈在《师说》中讲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也是古人对于教育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理解。现今教育工作中经常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师”和“生”都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教师不是仅仅承担“教”,学生也不仅仅是“学”,教和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教学相长,正是这种关联的真实写照。
“学”作为重要的教育概念,很多教育史研究者自然也希望在商代教育史研究中能够发掘出相关内容。传世文献中反映出的商代教育,其受众为贵族子弟,带有商王室“官方”教育背景,并且记载有类似学校的机构。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商代教育当以学校教育为主,在著作中自然也要从商代的学校和学校教育谈起。在《中国教育通史》系列丛书的先秦卷中,有关“商代的教育”一节便首先探讨了商代的学校。其中引用了甲骨材料,“丁酉卜:今(旦,有释作‘日’)万其学?于来丁乃学?与乙学?若丙学?”并称“是关于送子弟上学时间的问辞,是丁日还是下一个丁日,或者乙日、丙日才宜于上学呢?这条卜辞已经是证明商代已设学校的典型实例[18]。”书中虽未注明资料来源,但应当是下面这版卜辞:
丁酉卜:今旦万其学。吉
于来丁乃学
丛书作者所引卜辞在释读上存在问题,在甲骨文中“又”的字形确实与“乙”字接近。但是经过仔细分辨,可以发现该字在上述卜辞中其上部有呈弯曲向内钩的形态,符合“手”形,应当释为“又”。我们将“”字形定为“”,包括后一条卜辞中的“”字,从字形上讲都存在“”这个结构,它表示宫殿庙堂一类的建筑物。那么既然“”和“”都代表建筑,是否意味着上文所举卜辞是在占卜有关上学地点的事项,甲骨文中“学”的含义是否与今天相同呢?
在现有探讨商代教育史的著作和论文中,几乎都将甲骨文中的“学”字理解为“学习”这一种含义。然而从卜辞《屯南》662中可以发现,这几条卜辞出现了多处礼仪场所,这使我们不得不猜想这些卜辞可能与祭祀相关,“学”或许是祭名,指代某种祭礼。
对于“学”在甲骨文中的释义,前人多将其与“学习”“学校”相对应,少有从祭礼的角度探究过此问题。翻查有关卜辞祭名的研究著述,李立新先生的《甲骨文中所见祭名研究》[19]将卜辞所见祭名分“新派、旧派、旧派新派共有”三类进行专文探讨,收入了207种祭名,未见学祭。徐中舒先生的《甲骨文字典》中收入卜辞祭名279种,并未包括学祭,但也提出“疑为祭祀活动”[20]。章小谦先生的研究推进了这种猜想,认为学祭可能是祭伊尹,其仪式包括在室外举行的大型舞蹈,而且要避开雨天[21]。“学”是否可能为一种祭礼,我们还是要从第一手材料即甲骨文中找寻答案,确有卜辞可以证实我们的猜想:
(1)甲寅卜:乙卯子其学商,丁侃。用。子臀。
甲寅卜:丁侃于子学商,用。
(2)甲申:子其学羌,若侃。用。(《花东》473)
癸巳,岁妣癸一牢,龟祝。(《花东》280)
(4)…其(延)学…(《屯南》4035)
仔细分析这几条卜辞,(1)中“学商”可与“奏商”对应,“奏”是祭名,甲骨文中作“”形。《说文解字》:“奏,奏进也。”段注云:“登歌,堂上歌也。礼经或言歌,或言乐,或言奏,实皆奏也。”陈梦家先生指出:“奏是奏乐,奏舞或是乐舞”[22]。岛邦男也认为:“即登歌舞雩之义,用作祭仪的‘’即登歌。因此,‘’的字形象两手拿管乐器状”[23]。“奏”应当是指一种以歌舞音乐为主要内容的祭礼,奏祭主要是为了祈雨,并且常常有其他祭礼相伴:
(5)…酉卜,今日勿奏,其雨。(《合集》12825)
(6)叀嘉奏,又大雨。吉。
叀商奏,又正,又大雨。(《合集》30032)
(7)叀美奏。
叀祇奏。
叀商奏。(《合集》33128)
上举(5)(6)两条卜辞都记录了有关祈雨的事项,并且使用了不同的祭礼反复贞问。(6)(7)中的“商”“嘉”包括“美“”祈”等是商代歌乐之曲名[24],“与奏祭相伴的祭名相当多,有舞、伐、用、岁、循……等,其中与舞祭相伴举行的辞例最多,乐舞、歌舞相属,这也是奏祭为登歌舞以祭的证据”[25]。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1)中与“奏商”相对应的“学商”也是一种有关于祈雨的祭礼,并且其具体内容很可能也含有歌舞音乐,“学”或为一种祭名。(4)中同时出现了“延”与“学”,延祭常有伴祭:
另外还有一条卜辞也常见于探讨商代教育史的论著中:“庚寅卜,争贞:王其学,不冓〔雨〕”(《合集》39822),各家都将其解释为“子弟们上学回来,会不会遇到下雨”[26]。实际上或可解释为:争这位贞人于庚寅日占卜,商王进行学祭,是否不会遇到雨?
甲骨中的“学”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即与“戊”相连,组成一个人名。徐中舒先生已经关注到有关“学”字的释义中有“人名:学戊”[27]这样的含义,甲骨文有云:
(13)贞:隹祖庚。
贞:不隹祖庚。
贞:隹学戊。
贞:不隹学戊。(《合集》1822)
辛卯卜贞:今日其雨。八月。(《合集》6)
除上述材料外,甲骨文中有关“学”的资料最引人关注的,当是有关商代“大学”的记载。说起商代学校教育中的“大学”那就不得不提一条“明星卜辞”,即“于大学寻”(《屯南》60)。称其为“明星卜辞”,原因在于该卜辞被教育史研究者反复地在各种探讨古代教育史,尤其是古代学校教育方面多次引用,不外乎是其中的“大学”吸引住了学者们目光。是否在商代就有大学了?我们不妨深入探究甲骨文中的“大学”,看看其究竟具有怎样的功能。
《屯南》60是经整理者缀合后的一块卜骨[29],其上有六处记载,虽未有明确刻画的界划,但每一处都与其他部分前后空开约两个字的距离,可以清晰地辨别。这些卜辞都围绕着同一主题,即为是否需要进行寻祭而占卜:
(15)弜寻。
王惠癸寻。
于甲寻。
于祖丁旦寻。
于庭旦寻。
于大学寻。(《屯南》60)
从图二这片卜骨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占问了是否要进行寻祭,并且涉及进行寻祭的具体细节。试图通过占卜挑选出癸日和甲日中更为合适的时日,同时也占卜了是在祖丁旦、庭旦还是大学进行寻祭。寻祭在甲骨材料中较为常见,祭祀对象有祖先神和自然神,伴有人牲和动物牲,多与祈求农业丰收有关。

图二 《屯南》60
(16)壬戌卜,宾贞:寻燎于岳。(《合集》14474)
(17)壬寅卜,寻侑祖辛,伐一,卯一牢。(《合集》32221)
(18)王其寻二方伯于阜辟。
壬戌卜,王其寻二方伯,大吉。(《合集》28086)
(19)贞:庚申寻,禾于咒。(《屯南》705)
在《屯南》60这片卜骨中,占卜者连续贞问了选取寻祭地点的事项,其中“大学”与卜辞中的“祖丁旦”和“庭旦”可以相对应。“旦”指的是宗庙建筑的组成部分,陈梦家先生认为“旦”疑假作“坛”[30],于省吾先生肯定了陈梦家先生的观点,并且认为“旦”多与占卜狩猎和征伐之事有关[31]。从甲骨文例上看,“大学”也应当是指某一建筑或场所,而且其功能应与祭祀相关联。探究“大学”的具体功用,我们在甲骨文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线索:
(21)王其飨,在庭。(《合集》31672)
甲骨文的‘大’字有不同的形体,“‘大’字又分化为‘大’、‘太’两字”,这里记载的“大室”实际上就是“太室”。《尚书·洛诰》记载:“王入太室祼”。孔传:“太室,清庙”。孔颖达疏:“太室,室之大者,故为清庙。庙有五室,中央曰‘太室’”[32]。大学与太室都属于宗庙建筑的范畴,可以进行祭祖活动,这也符合寻祭的祭祀礼仪。而在《屯南》60中与大学并举的“庭”,根据卜辞我们知道商王在庭进行飨食之祭,可见其为等级较高的祭祀性建筑。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大学很可能是进行祭祀的场所,并且其规格等级相对较高。
现有的甲骨材料中仅出现一次有关“大学”的记载,暂无其他出土材料可以确证商代“大学”的性质职能。如果仅凭卜辞材料中存在“大学”二字,与现代教育机构名称相同,就认定其承担有教学职能,这仅仅是一种推论。《礼记》中的确记载有关于“明堂”“瞽宗”“庠”“序”等类似学校的机构,也有不少古人注疏附于其后。但是其成书年代距殷商时期跨度已然很大,汉儒及后世儒家学者限于时代以及学术理念的限制,对文本的再次解读正确与否仍要打上一个问号,还需得到多方面材料的支持。贸然将商代卜辞中的“大学”与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直接对应,进而认为商代具有成熟的学校教育体系,这种论断恐怕还需谨慎再三。
四 对商代“学校教育”的再讨论
对于商代教育性质的界定问题,不少学者先入为主地认为是一种学校教育。须知在教育学研究中,学校教育具有特定含义,部分学者在进行商代教育研究中不假思索地使用学校教育这一概念,实际上并不妥帖。学校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的专门教育形式,它有别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其他教育形式,属于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子系统。在学校教育的框架中,学校是一种公共机构,伴随着学校诞生的还有教师和学生群体、学校教学制度、教材等。商代存在教育史实,且对教育本身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认识,这是肯定的。但是否存在学校,在没有完全得到出土材料证实的情况下,很难作出肯定的判断。
在原始社会中,教育发生只需直接参加生产生活的劳动者将其经验口耳相传给受教者。但是在学校教育中,教育发生需要多次转换,将积累的知识经验通过筛选,形成相对固定且以文字资料为主的教学材料,教师和学生将围绕这些材料进行教学活动。商代已经出现成熟的文字,但商代教学是否还停留在原始阶段,授课形式是怎样的,是否具有完备的学校教学制度,当时教育活动采用的教学材料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地梳理和解决。
根据传世文献再结合出土材料分析,商代教育在教育方法上更偏向于体验式的实践性教育。商人实践性教学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在射猎方面。《礼记·射义》中记载:“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人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33]。射猎是一种礼义,射礼是中国古代军事训练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就有“己亥卜,在澭,子其射,若。不用。”(《花东》467)贞问在澭地射礼进行的状况如何?在射猎的过程中,卜辞中还记载有学射的具体过程:“戊申卜,叀疾弓用射鹳。用。”(《花东》37)商人在学射的过程中用疾弓射猎鹳鸟,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弓射技艺。根据韩江苏的研究,花东卜辞重新排谱后,可见“射”字形前后发生变化,“甲午日,是此次射箭活动的初期,其射字作‘’形,象两手抱弓箭之形。经历十日后,到己巳日‘,子’用‘恒弓’射时,其射作‘’形”[34]。从“射”的字形变化,正反映出子从开始学射到逐步掌握射箭技能的过程。
另外这种实践性教育还体现在有关甲骨卜辞刻写技艺教授方面。甲骨卜辞刻写在龟甲兽骨上,再通过钻凿烧灼来进行占卜。甲骨卜辞的刻写和占卜只能由特定人员进行,对于这些专业人员,研究者们将其称为贞人。对于贞人的教育培养是非常严格的,在新手合格“上岗”之前,往往需要做大量的练习,这种练习是在技艺成熟的贞人引导下完成的。例如《合集》38058这版卜辞(见图三)[35],其中既有贞人刻写的范例,又有研习者的仿刻。从右至左的第三和第四列应当是范刻,字体成熟,没有错误;而第五和第六行当是学习者的仿刻,字体稚嫩,且出现了错刻、缺笔等问题。以“丙”字为例,范刻没有错误,但是第五行仿刻缺少了横画,第六行仿刻内部笔画方向倒转。除此之外,从“子”“戊”“戌”等字的刻写情况也可看出商代对于学徒贞人的教育过程。这种情景非常类似后世习字的过程,由教师传授,写下范例,学生进行模仿学习。学生再通过练习,巩固学习成果。在商代贞人要在龟甲骨板上刻写,书写材料十分特殊,大量的实践练习是必不可少的。甲骨材料中有关习刻的内容,正是这种实践性教育的真实写照。

图三 《合集》38058
商代对于贵族子弟的教育,除知识传授外,德育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商代的德育教育同样具有实践性教育的特点,不仅仅是说教,而是切实深入日常生活中,通过特有的礼仪和行为方式来进行教育。《诗·小雅·绵蛮》有“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的记载,给人以饮食,人在饮食的过程中去体会和学习礼仪规范,这就是实践教育的雏形。文献中记载还可以在甲骨材料中得以证实,卜辞中就有“甲寅卜,彭贞:其飨多子”(《合集》27649),多子进行飨食之礼,目的并不在于饮食本身,重要的是学习观摩礼仪。卜辞中还有“壬子卜:弗,小学”(《合集》30827)“”是一种利用酒水进行祭祀的礼仪,参与者也在进行模仿学习。这种“体验式”的德育教育目的何在?《诗·大雅·公刘》中提到“饮之食之,君之宗之”,实际上就反映出商人实践教育的教育思想。借助于日常生活里的种种礼仪,在实践中使受教者切实地体会到礼所带来的秩序,深切地感受到王室的权威,产生一种向心力和荣誉感。既达到了教育子弟学礼明义的目的,商王室又可借以巩固宗法制和礼乐制度。德育对于人的教育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也不能忽视有关商代历史德育的内容。
学校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学校教育具有社会化和选择两项基本功能,个体在接受学校教育后能获得社会适应的基本素质,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36]。从这个角度来讲,现有资料所反映的商代教育是具备这样功能的。但是商代的教育模式或者教育体系,很难定义为学校教育。从教育培养对象方面讲,甲骨文及传世文献中有关教育受众的身份都是商王朝的贵族子弟。从教育方法上讲,商代教育具有实践性教育的特点,更多地保有了教育早期发展阶段中“言传身教”的质朴方式。以血缘纽带为内核的宗法制度是商王朝制度的核心,其教育虽是在“国”,其性质却是在商王室之“家”。很难将其定义为广义上的家庭教育,但冠以宗族教育,或许更为贴切商代的教育状况。
总体而言,在研究商代教育史的过程中,现有的针对商代“教”和“学”的学界研究成果尚有不足,这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部分古代教育史研究者已经在对既往研究做补正纠谬的工作,还需要广大教育史研究者更加细致全面地深度探究。我们也应当秉持传统史家“传信阙疑”的态度,对于可以得到史料充分证明的研究结果,自然要积极发掘,广而告之;而对于史料支撑相对缺乏的一些观点和推论,更应该格外谨慎。在商代教育史研究中,利用甲骨材料对有关商代教育基本概念进行辨析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地下材料的解读和运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