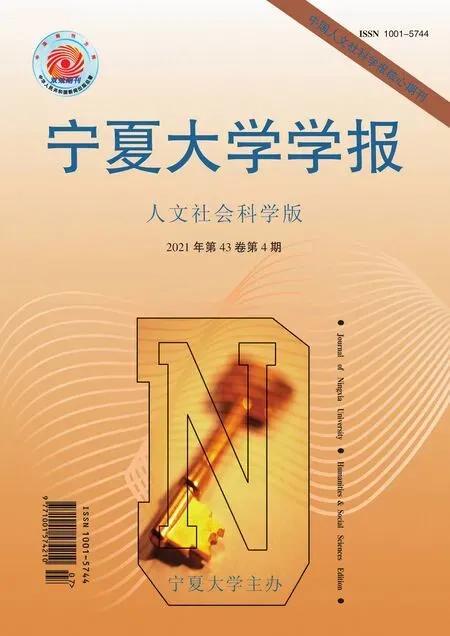林译小说的诗文翻译与古文论“共鸣”现象
赵 凯
(兰州交通大学 党委校长办公室,甘肃 兰州 730030)
古文与翻译的联通是近代文学的特有现象,文言翻译作为林纾翻译小说(以下简称“林译”)最醒目的标识,在相关研究中长期受到关注,这是由近代文学翻译的整体环境决定的,但就个人而言,诗人与古文家的身份才是林纾以文言翻译名世的基础。“译界之王”林纾早年便是卓有成就的诗文名家,在古文论方面亦有建树。林译里的诗文在承担翻译任务基础上,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显示不同领域的文学交融,呈现林纾文论对翻译的影响。从翻译效果来看,古诗文的运用显著提升了林译小说的文学品质,使原作“改头换面”进入近代中国的小说市场,是林纾赋予译作地道的中国文学标签。这些“标签”使他的文论与翻译形成交集,产生创作上的联通与共鸣,而《春觉斋论文》和其他文论著作,是解读林译小说诗文密码的钥匙,亦是探要他文论对翻译影响的重要参照。
一 骚体诗翻译的“情韵”特质
林纾一生诗作数量丰富,体裁主要是七律、七绝和五古,他的《闽中新乐府》和《畏庐诗存》是近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诗集,此外还作有《讽谕新乐府》130余首及《劝世白话新乐府》《劝孝白话道情》等44首旧体诗。林纾写诗同时注重诗歌理论研究,他对《楚辞》颇为重视,编著古文读本《左孟庄骚精华录》专门对《九章》进行评点,而《春觉斋论文》作为林纾诗文论的集大成者,原是于京师大学堂任教时的讲义,1913年在《平报》连载,名为《春觉生论文》,1916年由都门印书局首次出版,后多次再版,皆遵照都门印书局版本,内容由《述旨》《流别论》《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和《用字四法》组成,其中《流别论》与《应知八则》都包含对楚辞音韵和形式特征的研究。事实上,林纾的楚辞研究虽然丰富,但相应的创作却少,对比数量众多的叹世诗和题画诗,他的骚体诗所受关注不多,但其在林译小说中的出现却值得重视,因为这是在翻译影响下进行的诗歌创作。
(一)骚体的相思与哀情
骚体的本质是抒情,《九章·惜诵》首句“惜诵以致愍兮,发奋以抒情”便直言骚体的抒情特质。相较《诗经》之庄雅,骚体窈窕多变,更加适宜情感的抒发,而屈原为之注入的一腔哀情也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传统。骚体重哀情之抒发,无论《离骚》之悲思还是《九歌》之缠绵,始终贯穿着丰沛而深邃的诗情。林纾在《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中提到:“乃知骚经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1]。这无疑是将情感真实作为骚体诗的创作核心,高度肯定了作诗起意的情感,而这一主张也被延伸至林译小说中。
从《巴黎茶花女遗事》起,林译便以真挚充沛的情感影响当时的阅读风潮,林纾能将骚体诗成功移植到域外小说中,是因为其实现了诗歌情感与原作的贴合,这是骚体诗在翻译中获得“二次生命”的基础。在林译《魔侠传》(《唐吉坷德》)中,奎沙达(堂吉诃德)带着山差邦(桑丘)到牧羊的地方,听到一首情诗,林纾很有创见地用骚体翻译了这首诗:“最难忍者唯相思兮,吾无首之可搔。嗟情愫之难逐兮,将舍死其焉逃?愿既绝而影息兮,谁慰我之忉忉。但有悲而无乐兮,惟否运之相遭。吾死其又奚悔兮,愿余人之鉴我,果彼美能察吾心兮,吾虽逝而亦可”[2]。原诗篇幅很长,译为骚体后仍有近四百字,这里引述的是节选。诗的作者是一位相思而死的男子,但他所爱女子毫不知情。男子的赤诚和愁苦近乎痴狂,这给翻译提供了足够的情感强度,为展现骚体写情的感染力奠定了基础。骚体诗迂回的内部节奏足以契合相思的千回百转。节选诗歌每两句构成一个层次,言说一种相思情状,从第一层对相思的刻骨难忍,到最后一层表明女子在心中的至高地位。情感强度在诗句的往复中递进加强,精准传达了原作的真挚、热烈和悲切,也显示了林纾“情韵说”的影响。
关于“情韵”,林纾在《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提道:“凡情之深者,流韵始远”[3]。认为只有足够深切的情感才会产生绵远悠长的感染力,而情之深的基础是情之真,过度矫饰则会使作品情感失真,连带丧失“情韵”,故诗情讲求源于自然和本心。对此他复又提道:“有是情,即有是韵。体会之,知其恳挚处发乎心本,绵远处纯以自然,此才名为真情韵”[4]。林纾在这里提到“情”先于“韵”的创作前提,重视创作者对内心真实的探索,将发乎本心的自然作为鉴定真“情韵”的标准。《魔侠传》中的骚体诗虽极力描摹男子相思情状,但诗歌情感却无过度矫饰,以保留和再现原作相思之情为目的,译文绵远自然,富有中国古典气韵,恰如屈原之“九死未悔”投于情爱,因而这首长诗在完成翻译任务的同时也成为“情韵”丰满的诗歌创作。
(二)楚歌的奇崛与复沓
《文心雕龙·辩骚》言骚体:“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说明骚体诗不仅注重情感真实,还兼具意象华丽,形式奇崛的特点,对此林纾提道“枚、贾得其丽,马、扬得其奇”[5],认为汉代辞赋家承袭了骚体诗的奇丽特征。诚然骚体的诗歌形式需要充分的情感契合,但意象的华丽与诗歌空间的辽阔也至关重要。从《离骚》的“香草美人”到《九歌》的神话意象,再到《天问》开创性的诗歌空间,决定骚体诗抒情层次的不仅有深邃的诗情,还包括丰富华丽的意象与驰骋想象的诗歌空间。
林纾在《吟边燕语》中翻译的歌谣展现了楚歌的形式和音韵特征:“尔趣五仞之渊觅父尸兮,尸面交横珊瑚枝兮。珠蚌呴光眼位迷兮,腐朽之身今乃沃泽如生时兮。宝气腾上光陆离兮,天吴奏乐媚彼以声诗兮”[6]。这首歌谣翻译自莎翁名作《暴风雨》,由其中的小精灵所吟唱:“Full fathom five thy father lies;Of his bones are coral made;Those are pearls that were his eyes;Nothing of him that doth fade;But doth suffer a sea-change;Into something rich and strange;Sea-nymphs hourly ring his knell;Hark!Now I hear them,Ding-dong,bell.”[7]歌谣带有强烈的奇幻色彩:珊瑚、珍珠在翻译后成为华丽的诗歌意象,第六句“宝气腾上光陆离兮”则明显受到骚体诗的影响。“陆离”一词在楚辞中多有出现:《离骚》有“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招魂》有“长发曼鬋,艳陆离些”;《涉江》有“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林纾将原诗第六句的“richand strange”译为“陆离”,对应诗里的珊瑚和珍珠,不仅还原了灿烂绚丽的景象,也突出了骚体诗色彩繁丽、意象斑斓的特点。诗中最后出现的海妖(Sea-nymphs)被翻译为“天吴”,《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在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黄”[8]。由于楚歌与骚体同出一脉,故二者在艺术上颇多相似。屈原承袭“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传统,在《九歌》中保留众多原始神话意象,奠定了骚体诗的神话写作传统。林纾以“天吴”翻译原作中的海妖,更易触发中国读者的神话想象,联想到中国传统的水神,契合楚歌的神话传统。

图1 天吴(明)蒋应镐绘图本

图2 天吴(清)吴任臣近文堂图本
除了具有神话特质的意象,骚体在音韵上的主要特征是复沓,以独特的衬字“兮”为代表。林纾在《左孟庄骚精华录》里提道“读九章尝不厌其沓,文字犯一沓字,便令人索然无味,独于楚辞则否”[9]。直言骚体最独特之处便是复沓,这与其他文类全然不同,其内部的韵律音声回环往复,皆用以渲染、强化诗情,将冗沓升华为笼驭作品的艺术技巧。林纾对此解释:“由情本于衷,虽言之又言,而人感其诚恳,故不以为冗复”[10]。又以《离骚》《九章》为例:“观离骚中拳拳于怀王,言之又言,不能招人厌倦者,情深而语悲。九章中无数叠床架屋语,读者何会斥其絮絮不休?”[11]林纾通过屈原的作品指出骚体“言之又言”的复沓都是为了支撑作品中深邃而悲切的情感。《吟边燕语》里的楚歌是一首荒诞的挽歌,不仅神话色彩鲜明,还包含着浓重的悲伤气息:五英寻深的冰冷海水里,隐匿着逝去的国王,面对他沉落的尸体,海妖正在敲响丧钟。原作通过句尾词的押韵来传达悲情:“lies与eyes”;“made与fade”;“change与strange”;“knell与bell”采用交错押韵的形式,每隔一句进行押韵,不仅在吟唱时更加上口,也能通过音韵重复来加强情感。林纾的翻译则以衬字“兮”来反复吟咏,不断渲染和强化诗里的哀情,“兮”字同时可以拉长音调,使作品弥漫着华丽、哀伤又奇异的氛围。
二 写景翻译的古文特征
林译是“不忠实的美人”,参看多篇林译小说,很容易发现林纾对原作的删减,但他却将作品的景物描写翻译得很完整,不仅保留原本内容,甚至偶有增补。相对小说的叙事和对话部分,林纾的写景翻译对原作整合程度更高,再创作特征也更明显,紧密关联着他本人的古文创作。
(一)四字句的行文单位
在翻译环境描写时,林纾常以四字句行文。参看他对柳宗元《剑门铭》的研究,包含对四字句的精要评价:“其用四字为句,非取其短悍也。叙事能缩繁为简,鳞比而下则气聚而不散。响彻而难枵,尤足泽以古雅之词”[12]。林纾认为使用四字句的重点在于叙事精炼简洁,呈现结构紧凑、文气流畅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要兼顾音韵,以古雅之词来润句。关于林纾行文的洗练特征,可联系《春觉斋论文·论文十六忌》里的“忌庸絮”一说:“庸”指凡俗,“絮”指拖沓,古文写作不仅立意不能落俗,简洁原则也必须兼顾,因而文中不可有冗章、冗句和冗语。秉承这样的创作原则,林译小说的环境描写多是先拆解原文,再重新整合译文,句法形态上以四字句为单位,将原句化繁为简。
“时夜色沉沉,月痕逾午,人间万声都寂,虽名园胜概,咸无游赏之人,而豺虎恒以此时出猎禽兽”[13]。这段文字出自《吟边燕语》的《蛊征》一篇,原是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对《麦克白》的缩写:“Now was the middle of night,when over half the world nature seems dead,and wicked dreams abuse man’minds asleep,and none but the wolf and the murderer is abroad.”[14]译文采用四字句辅以六字句的结构行文,林纾首先用“月痕逾午”来翻译午夜,将原作中“死一般的寂静”译为“万声都寂”。值得注意的是,他删去了原文关于梦的描写,却添加了“名园胜概,咸无游赏之人”的四六句,同时将狼译为豺虎,对译文中的景物配置作了改变,但依然保留了《麦克白》中暗夜凶杀的诡异氛围,与原作十分契合。在《黑奴吁天录》中,主人公乘车去庄园的路上,也有对周遭环境的精彩描写:“一路景物荒悄,似久无人行。两行怪树,状若鬼魅离立,苔纹绣满树身,如盘绿蛇。瘴气弥水,水腥臊作深紫之色”[15]。这里依然以四字句行文,但林纾减去了部分内容,不再保留原作关于风吹长堤的描写,同时增译了“瘴气”一词,为腐水增译了深紫的色彩,从而补足细节,增强了画面感。原文中关于蛇的描写使用了较长的嵌套句:“Now and then a snake might be seen sliding among broken stumps and branches that lay here and there,rotting in the water.”[16]译成白话难免冗长,结构失衡。林译本删去长定语,译为“如盘绿蛇”,原文中这里并非比喻,因而是一处误译,但林纾采用了读者熟悉的四字句,寥寥数笔便刻画出原文阴森恐怖的场景,成功保留了原本的环境特征,在气氛渲染上近似古代的小说话本。
(二)“意境说”对“译境”的影响
林译小说的环境描写多呈现风格独特的“译境”,这源于林纾在古文创作中践行的“意境说”。“意境”作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经典的创作美学概念,可溯至《周易》的“立象尽意”之说,而“意境”能成为中国诗歌创作和审美的重要标准,在于其内容的不断变化和丰富:从唐代皎然的《诗式》,王昌龄的《诗格》,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到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都包含对“意境”的系统诠释,及至近代出现王国维的“境界说”,“意境”对中国诗歌的创作评价体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林纾在《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中开设专章强调“意境”的重要性,将其影响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意境者,文之母也,一切奇正之格,皆出于是闻。不讲意境,是自塞其途,终身无进道之日矣”[17]。他在这里直接将意境作为古文创作的核心标准,也是学习古文最重要的门径。
意境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囊括诗文中所有难以言说的审美细节和感受,这些内容的诠释都通过“境”来实现,“境”对诗歌的艺术水准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其并非凭空架构,而是由“意”建筑成的艺术空间。林纾“意境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对“意”“境”关系的思考,他在承袭前人观念的基础上,对“意”的来源和影响有相对独立的看法:“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18]。这便指出了“意”对“境”的统摄作用,在此基础上林纾又分析了“意”和“境”的来源,认为“意者,心之所造;境者,又意之所造也”[19]。直观说明“意”对“境”的建构作用。“境”产生在创作者的审美立意上,因而无法脱开“意”的影响,“意”则来源于创作者的学养,包括所阅诗书、所习仁义和世间阅历。
“意境”在林译小说里最终呈现为一种疏淡自然的审美心胸,转化为小说中独特的“译境”。参看林译中关于风景描写的段落:“思极仰卧地上。观天际飞云,片片相逐,直至海上,与水云合,蔚蓝一色,气极清明。自念骤归见窘于阿姨,不知偷间斯须,以吸清空之气,较为幽静。时草虫嘶咽,野碟群飞,仰见古塔之上,老鸦哺儿声牙牙然”[20]。这段译文出自林译《迦茵小传》,译作在当时引起“现象级”的阅读风潮,但原作(《Joan Haste》)只是一部无甚新意的罗曼史,作者哈葛德(Haggard)在西方世界也非一流作家,之所以呈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接受态势,不仅因为契合了当时中国的文化需求,更在于林纾译笔起到的催化作用。景物翻译是《迦茵小传》的神来之笔,节选的译文用语凝练,形式工整,所用四字句很符合传统山水文的行文特点。由于林纾对学养的注重,这段译文在审美上呈现出疏淡自然的文人特质,通过和原文段落的对比,其意境特点呈现得更加明显。
“Thus thought Joan;then,weary of the subject,she dismissed it from her mind for a while,and,lying back upon the grass in idle contentment,watched the little clouds float across the sky till,far out to sea,they melted into the blue of the horizon.It was a perfect afternoon,and she would enjoy what was left of it before she returned to Bradmouth to face Samuel Rock and all other worries.Grasshoppers chirped in the flowers at her feet,a beautiful butterfly flitted from tombstone to grey tombstone,sunning itself on each,and high over her head flew the jackdaws,taking food to their young in the crumbing tower above.”[21]哈葛德的原文混合着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语法,句中有较多插入语和补语,会使译文流畅性有所欠缺,但林译本中这样的情况并未出现。原作描写的“天”“云”“水”在翻译后具备了意象功能,通过疏淡的色彩成功建构出悠远的画面空间。林纾在“片片相逐”和“与水云合”两句中,增译的两个动词(逐、合)具有明显的提炼特征,不仅使景物具备灵动的姿态,更增添了整幅画面的动感,文中的“气极清明”一句成为这段景物描写的审美核心,这在林纾的文论中亦有迹可循。
关于什么是理想意境以及如何形成的问题,林纾解释道:“须知意境中有海阔天空气象,有清风明月胸襟。须讲究在未临文之前,心胸朗彻,名理充备,偶一着想,文字自出正宗”[22]。前一句解释了关于意境的审美理想,强调诗文创作应讲求清朗与开阔;后一句指明学养是创作前的主要准备,学识积累对理想意境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林纾在景物翻译中所展现的文艺观念,主要是个人学养衍生出的审美心胸。他在译文中突出了景观的“清”“空”特质,使翻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描摹,而是建构出舒朗明澈的艺术空间,呈现中国式的风格画面:文中的迦茵不再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伦淑女,更像一位“偃仰啸歌,冥然兀坐”的女居士。林纾的“意境说”包含他对文章意境的理解和建构方式,呈现天然的文人审美趣味,是林译小说中古典“译境”的重要来源。
三 “以画入文”的景观描写
景观描写带有天然的画面特质,经译者处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多呈现翻译影响,这种跨越文化的语境差异可能导致蒙娜丽莎被临摹成唐仕女图。林译的景观描写十分注重画面呈现,这和林纾的山水文创作密不可分。近年出现不少关于林纾山水文的研究,但未与他的翻译产生联系。林译的景观描写结构完整、画面鲜明,相较白话翻译别有韵味,是具备独立研究价值的文学小品。从画面特质来看,其无论在布景、设色还是光影捕捉方面均有过人之处,显示了译者在翻译中的艺术融合。
(一)山水文与“词中有画”
《林琴南文集》收录70篇记体文,题材丰富,成就最高的是山水游记。林纾的山水文整体清新自然,重视景物描摹,突出山水主体,鲜有议论抒情,在当时独树一帜。他的《游栖霞山紫云洞记》《记九溪十八涧》和《明湖泛雨记》等作品充分显示出写景状物之造诣,不仅描摹精细,在布景次序、配色和质地搭配上也表现出独到眼光,具备较强的“可视性”。林纾关于艺术交叉的观点可溯至《春觉斋论画》提到的“词中有画”论:“诗中有画,指右丞也,余谓词中亦有画”[23]。之后他列举宋代七位词人名句,认为可取其中意境入画。“林纾所列举玉田、碧山、梦窗、草窗、清真、梅溪、白石等南宋七位词人的词,大都是有意境、有颜色、有构图、有视角,能够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可以根据欣赏者的想象变换为具象的画面”[24]。可以说“词中有画”的观点和山水文的“可视性”奠定了林纾“以画入文”的创作基础,同时将影响延伸到他的翻译中。
(二)画面色彩与景物质地
《魔侠传》中有一段林纾增译的景观描写,是他在翻译中创作的山水小品:“则细草芊绵如铺茵。其上有蔚蓝之天,阳光焕射,前有密林,绿荫如织。鸟声上下,翠羽朱喙,一一如画。林下有小溪,穿树而过,夹岸皆醲花芬郁。水清见底,细石可数。其旁有仰泉,以白玉叠而成之,复有一泉,则以贝为之,照眼晶莹。二泉所砌之物,白玉朱贝,杂以宝石,如出天然”[25]。这段译文本是用来讲解骑士小说的“妙处”,却被增译出一派自然优美的景致,译文基本采用四字句,行文特点近似传统山水文,采用移步换景的手法。从“以画入文”的角度看,具备鲜明的色彩和质地特征。
首先,林纾在翻译中表现出对色彩的敏锐捕捉,通过丰富的配色和层次对比来彰显译文的视觉特质。文中的细草、蓝天和密林构成画面的基础配色,缀以鸟雀,鲜亮清新。鸟雀“翠羽朱喙”,外观细节丰富,翠绿与朱红是高饱和度的对比色,可以进一步丰富画面配色,提亮色彩对比。“阳光焕射”一句显示了整幅画面的基础亮度,之后画面视角随着“穿树而过”的溪流继续延展,展开对水景的描摹,进行山水游记的“移步换景”。溪水颜色清澈,画面因此具备了通透感,对河底细石的描写则提升了细致程度。与此同时,两岸繁花充实了画面的景物配置,同时令色彩更加明艳。
其次,林纾在译文里添加了两处关于“泉”的描写。“二泉”虽然宛若天成,却是由白玉、朱贝和宝石构成。两处泉水对画面的影响不仅在于玉石、贝壳和宝石所提供的明艳色彩,还在于它们各自的质地。译文的视觉画面主要由色彩构成,但影响阅读体验的还包括景物质地。色彩有明暗搭配,景物的质地亦有刚柔对比。译文中的水和石本身就带有质地对比,而白玉、朱贝、宝石的坚硬质地与周围的花草再次形成对比,从而对景观起到整体性的“刚化”作用,避免画面意境流于单一俗艳。更重要的是,质地名词可以引发读者的感官体验,激发更多的官能想象:诸如玉石、贝壳和宝石的堆砌,再配合水的质地,可以带来坚硬、冰凉的触感,形成更丰富的艺术体验。这是林纾有意识的选择,因为他在其他译作中也会用到质地坚硬,外表华丽的物象:《吟边燕语》的《铸情》(《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篇,林纾称周丽叶(朱丽叶)“皎白如玉”,替换了原作将她称为太阳的比喻。这一方面契合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传统,引发读者对“玉人”形象的联想,同时使周丽叶和清冷、冰凉的玉石联系在一起,融入皎洁的月色中,使整体画面呈现出冷、艳、雅、香的风格特质。
四 结论
《春觉斋论文》和《左孟庄骚精华录》等文论著作是林纾在长期的诗文创作中所作的文艺总结,“情韵说”和“意境说”作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将影响延伸到了林译小说中,使传统诗文和域外小说在翻译中产生了深层接触。林纾的“情韵说”注重情感真实和诗体的奇幻瑰丽,成就了译作中骚体诗的深情与华美,“意境说”则通过工整古雅的四字句建筑起舒朗明澈的小说“译境”,是译文中古典韵致的重要来源。林译的景观描写在色彩搭配和质地选择上亦有创见,联系林纾的山水游记和“词中有画”论,可以认为其具备“以画入文”的创作特征。林译中的诗文小品是翻译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因而呈现相对特殊的文学形态。林纾将诗文创作融入域外小说翻译中,较为成功地实践了他的诗文理论,深层联结了传统诗文和域外小说,虽在今天看来有一定的局限与“隔膜”,却契合了当时的阅读需求与文化语境,显示出不同领域文学成果在翻译中的联通与共鸣,这是林译小说乃至整个近代文学翻译中值得重视的创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