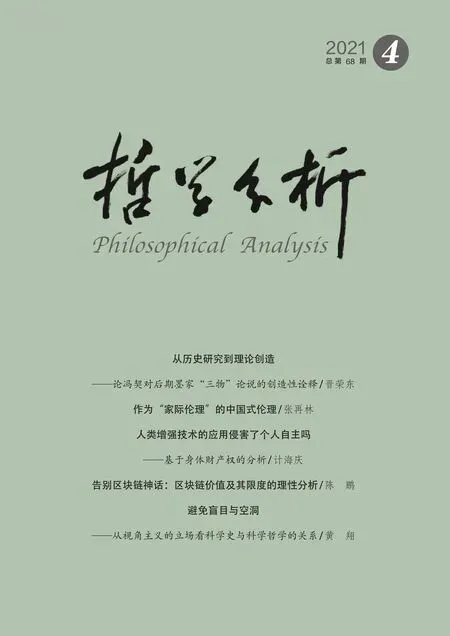从历史研究到理论创造
——论冯契对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
晋荣东
冯契的哲学创获主要反映在“智慧说三篇”之中,而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则可称作“哲学史两种”。a“智慧说三篇”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哲学史两种”指《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从总体上看,“冯契先生对当代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以中国哲学史研究为通达‘智慧说’的中介,体现出其哲学研究之‘思’与‘史’的高度融合,从而使得其哲学体系既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又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过,“作为辩证法意义上的中介,它(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引者)不仅是时间或形式上的中间环节,而且与其关联端之间存在着由此及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a参见高瑞泉:《在历史深处通达智慧之道——略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创作》,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6 期。。鉴于长时段的哲学史是由众多的哲学家、派别、著作和论争等构成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独创性也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理论创获体现出来的,本文拟采取个案研究的进路,以冯契对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为例,具体说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哲学创作之间“由此及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
一、关于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的主流解释
1919 年,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开创了通史形态的中国哲学史著述的第一个范例。按其后来的自述,“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b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9—160 页。1929 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纳入“万有文库”丛书第一集出版。。胡适认为,后期墨家的“《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而《小取》篇“有条理有格局”“最为完全可读”c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152、154 页。《墨辩》包括现存《墨子》一书的《经上》 《经下》 《经说上》 《经说下》 《大取》 《小取》六篇,其中《经》 《说》四篇通常又称《墨经》。。他把《小取》篇分为九节,认为总论“辩”的第一节尤为重要: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d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63 页;亦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15 页。“焉”字,孙诒让属下句,其余诸本多属上读。
胡适立足《小取》篇的结构与内容从“辩”的界说、辩的用处及辩的根本方法、故、法、辩的七法等方面对后期墨家逻辑思想进行了说明,并重点考察了有关“类”“故”“法”的论述。不过,相较于对《小取》及《经》 《说》四篇的重视,他鲜有提及《大取》篇,尤其是其中关于“故”“理”“类”三物的论说: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a原文无“夫辞”二字,“者也”倒为“也者”,今从孙诒让补移。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第413 页。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b据孙诒让,“此下疑当接后‘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句。”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第406—407 页。孙说不确。张纯一移此句接“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之后,前后文义贯通,今从之。参见张纯一:《墨子集解》,上海:世界书局1936 年版,第396 页。又,原文无“辞”字,据谭戒甫补,参见谭戒甫:《墨辩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449 页。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c“妄”,原作“忘”,据孙诒让引顾广圻之说校改。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第413 页。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当然,鲜有提及并不是未曾提及。事实上,胡适在解释何为“以类取,以类予”时就曾对“三物”论说有所引用:“一切推论无论是归纳,是演绎,都把一个‘类’字做根本。所以《大取》篇说:‘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一切论证的谬误,都只是一个‘立辞而不明于其类’。”d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65 页。不难发现,他只是引用了“三物”论说中有关“类”的部分内容,并未将这一论说从整体上加以主题化,更遑论阐明其逻辑意义。
冯友兰1934 年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堪称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述的又一范例。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家多未竭全力以立言,故除一起即灭之所谓名家者外,亦少人有意识地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故……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e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载《三松堂全集》第二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51 页。下引《三松堂全集》各卷不再一一注明出版社与出版时间。又,此书1931 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4 年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哲学史(下)》同时出版,内容有修改。。具体到后期墨家,冯友兰也是立足《小取》篇来说明其逻辑思想,其间对胡适的相关解释多有采用。与胡适不同,在解释完《小取》篇的相关文本后,他说《大取》篇有所谓“语经”,然后便全文引用了“三物”论说。冯友兰似乎认为“三物”论说就是“语经”,但对其理论内涵则并未给予具体说明,仅说“此与《小取篇》所说大意相同,惜其详不可知矣”f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载《三松堂全集》第二卷,第487—488 页。。
在1982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中,冯友兰明确把“三物”论说与“语经”等同起来,认为这一论说揭示了“辩论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只有几十个字,可是把墨经所已达到的逻辑学上的成就,简要而精确地总结起来”g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载《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491、492 页。此书最初于1982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这个规律,他进一步指出:
在一个演绎的推论中,“理”就是大前提,“故”就是小前提,“辞”就是由大前提、小前提推出来的结论……结论是直接依靠小前提,所以“辞”是“以故生”。再加上大前提,结论的可靠性就增长了,所以是“以理长”。再加上附加的举例,更有说服力,这就是“以类行”。a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载《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491—492 页。
这里,冯友兰似乎把辩论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具体化为辩论所使用的演绎推理应当遵循的程序或形式,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他援引印度因明“宗—因—喻”的三支论式来说明“三物”论说揭示了“辞—故/理—类”的推理程序或形式。
在胡适、冯友兰范例性的中国哲学通史著述之外,1979 年出版的由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也是一部影响甚广、特点鲜明的中国哲学史教材。b该书前三卷首版于1963 年,1979 年出版全四卷时对前三卷进行了改写和增补。此后,又不断再版,并在2003 年出版了修订版。为行文方便,下文将此书作者径自省作“任继愈”。任继愈基本上也是立足《小取》篇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并在考察有关“辞”(判断)的论述时提到了“三物”论说:“要达到判断正确,必须遵守逻辑思维规律。它说:‘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大取》)……这些都是形成判断的不可缺少的因素。”c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修订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210 页。同样是认为“三物”论说揭示了思维必须遵守的规律,冯友兰将其理解为辩论所使用的演绎推理必须遵守的程序或形式,而任继愈则将其归结为形成正确判断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1983 年,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出版。该书坚持《小取》篇是“墨经逻辑学的总论”的看法,但对“三物”论说的解释则有所调整,“故”“理”“类”三物不再被认为是形成正确判断所不可缺少的因素,而是推理过程必须具有的三个基本范畴。d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555 页。更具体地说,这一论说揭示了推理所必须满足的两项基本要求和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环节:
后期墨家的逻辑学并没有形式上固定化的推理论式,但仍然有关于推理的基本论式,它由“辞”“故”“理”“类”四个环节组成,这就是:首先立辞,接着提出论据,然后用统一标准加以衡量,最后连类相推证明结论。这四个环节体现推理的两项基本要求:事实和理论上的根据要充分,类的异同处理要得当。e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563 页。
此外,一些中国逻辑史领域的研究也对“三物”论说多有关注,并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理解:其一,“三物”论说是对推理形式的刻画。例如,张纯一、章士钊、汪奠基、温公颐、孙中原、周云之等就对比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印度因明的三支论式来说明所谓“三物论式”a参见张纯一:《墨子集解》,第396—397 页;章士钊:《逻辑指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年版,第92、276 页;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112 页;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15—117 页;孙中原:《印度逻辑与中国、希腊逻辑的比较研究》,载《南亚研究》,1984 年第4 期;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154—156 页;周云之:《后期墨家已经提出了相当于三段论的推理形式——论“故”“理”“类”与“三物论式”》,载《哲学研究》,1989 年第4 期。,或强调三者之同,或突出三者之异。其二,“三物”论说是对逻辑规律、原则的揭示。例如,詹剑峰、沈有鼎、崔清田、孙中原、刘培育等就主张这一论说揭示了在形成判断或进行推理时必须遵守的逻辑规律、原则。b参见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汉口: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76 页;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版,第41—42 页;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05—106 页;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44 页;刘培育:《中国名辩学》,载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25—128 页。
要言之,中国哲学史、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的主流做法是立足《小取》篇的结构与内容来诠释《墨辩》的相关文本以重构后期墨家逻辑思想,他们多把“三物”论说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特定形式上,将这一论说的本质勘定为对推理形式的刻画或对逻辑规律、原则的揭示。
二、冯契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
历史地看,冯契很可能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就对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进行了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他勾画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后文或简作《逻辑发展》)一书的轮廓、书稿、写作准备材料等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至今下落不明。c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六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375 页。下引《冯契文集(增订版)》各卷,不再一一注明出版社与出版时间。现存最早的相关研究是写于1977 年的《先秦哲学笔记》中有关墨辩的5 页笔记。d《先秦哲学笔记》写于一本硬面抄上。该硬面抄共写有70 页笔记,分为“先秦哲学笔记”和“中国古代哲学(秦汉至清代)笔记”两部分,其中先秦部分明确标有时间“1977 年”,包括关于子产、史墨、墨子、《老子》、《管子》和《商君书》、墨辩、荀子、韩非的笔记八则,共29 页。在他看来:
墨辩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逻辑思想,明确地提出:“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大取》)这就是所谓“三物必具”,即正确地进行逻辑思维和辩说的必要条件。a参见冯契:《先秦哲学笔记》,手稿,1977 年,第20 页。
所谓“以故生”,是指立论要有根据;“以理长”,是指论证和辩驳要遵守逻辑规律和逻辑规则来展开;“以类行”,是指按“以类取,以类予”的原则或事物的种属包含关系来进行推理。粗略地看,冯契对“三物”论说文本的理解同主流解释似无明显区别,不过就其适用范围与本质勘定而言,区别的端倪已经显现:不同于主流解释多把“三物”论说限定在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特定形式,冯契通过“逻辑思维和辩说”这一表述似在表明这一论说的适用范围更广,关乎整个逻辑思维;不同于主流解释把“三物”论说的本质勘定为对推理形式的刻画或对逻辑规律、原则的揭示,冯契认为这一论说提出了“正确地进行逻辑思维和辩说的必要条件”。
《先秦哲学笔记》实际上是冯契1978—1980 年为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所写的准备材料。b现存《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记录稿)》上下两册封面均印有“1978—79”。不过据《致董易》(1980年1 月2 日):“我一年半来每两周讲一次‘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最近可以结束”,可知冯契实际讲授的时间当始于1978 年秋季学期,结束于1980 年初。参见冯契:《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第279 页。从讲课记录稿看,在说明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时,冯契指出:
人们采用概念、判断、推理这些思维形式时,总是要运用类、故、理这样一些逻辑范畴。《大取》篇讲到:“三物必具,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讲了正确思维的三个必要条件。c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记录稿)》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海师大中国哲学研究室1978—79 年版,第80 页。
这些文字与《先秦哲学笔记》中的提法基本一致,但若仔细辨析,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就“三物”论说的适用范围说,冯契在此更为明确地强调它普遍适用于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形式。第二,就如何理解“三物”论说所揭示的“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看,冯契在此似乎有意把这些必要条件与思维必须运用的“类”“故”“理”等逻辑范畴关联起来。第三,就“三物”论说提出的逻辑范畴说,冯契在此不再拘泥于这一论说本身所表述的“故—理—类”的顺序,转而开始按照“类—故—理”的次序来讲逻辑范畴。
前文业已指出,学术界的主流做法是立足《小取》篇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虽然冯契也全文引用并解释了《小取》篇总论“辩”的第一节,但鉴于“三物”论说关乎整个逻辑思维,他在讲课中开始尝试从“类”“故”“理”三个方面来诠释《墨辩》相关文本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a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记录稿)》上册,第80—84 页。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三物”论说的诠释再一次显示出不同于主流解释的独特个性。
1980 年1 月2 日,冯契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回顾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研究,“感到还是比较粗糙”,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能提出自己的看法。b参见冯契1980 年1 月2 日致邓艾民、董易的信,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第235、280 页。1982 年3 月,他开始修改《逻辑发展》的记录稿。c据《致邓艾民》(1982 年3 月28 日):“这个月我已动手修改稿子,孔、墨、老、管等已基本修改好了。”参见《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第249 页。他把“三物”论说的本质从“讲了正确思维的三个必要条件”修改为“明确地提出了‘类’‘故’‘理’三个范畴是逻辑思维所必具的学说”,并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虽然“类”“故”“理”是墨子在不同地方提出的,“只是到后期墨家,才第一次把‘类’‘故’‘理’联系起来,明确地将它们作为逻辑思维形式的基本范畴来阐述,从而建立起形式逻辑的科学体系”。基于此,他进一步确立了以“类”“故”“理”的范畴架构来把握后期墨家逻辑思想的研究方法。相较于记录稿,1983 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用更为清晰的语言写道:“下面我们分别就‘类’‘故’‘理’三个方面来说明《墨经》的逻辑思想。”d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四卷,第215—216 页。有时冯契也把“三物”论说称作“形式逻辑基本原理”(第333 页)。
按冯契之见,后期墨家首先在“类”范畴下对同和异、个别和一般、部分和整体、质和量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他们不仅对同异的多种表现进行了分析,而且着重考察了“类同”与“不类”、“体同”与“不体”;按类属关系将名(概念)分为达名、类名和私名三种,并根据种属包含关系批判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点;提出了“异类不比”的原则,意识到逻辑思维不能违背质决定量的原则,只有同类事物才有共同的度量标准;赋予“类”以“法”(标准、法式)的含义,“效”之为论证方式就是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建立公式、模型进行推导的演绎法,而所效之“法”则反映了所考察的类的本质。在后期墨家所考察的或、假、效、辟、侔、援、推等论辩方式中,如果说“效”揭示了演绎推理的本质,那么“推”所代表的归谬式类比,虽然是从个别到个别,其实也是以“类”为中介,“以类取”而又“以类予”,体现了归纳与演绎的统一。
其次,在对“故”范畴的考察中,后期墨家把根据或条件区分为“小故”(必要而不充足的条件)和“大故”(充足而必要的条件),而“以说出故”就是说推理要提出“故”来作为立论的根据。
再次,针对“理”范畴,后期墨家不仅探讨了许多推理形式,而且接触到了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所强调的名实对应关系正是同一律的基础和实质,与坚持同一律相联系,后期墨家反对“两可”之说,包含着排中律的思想;而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不能“俱当”,又包含着矛盾律的思想。
虽然后期墨家主要还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考察“类”“故”“理”这些基本的逻辑范畴,但冯契认为,某些论述其实已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界限,如用“异”来定义“同”,提出“同异交得”的思想,已经揭示出即便是在最普通的逻辑思维中也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a详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四卷,第216—224 页。
总起来看,相较于立足《小取》篇的结构与内容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这一主流做法,冯契创造性地把《大取》篇的“三物”论说所提出的“类”“故”“理”的范畴架构作为诠释与重构的基础;相较于主流解释多把“三物”论说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特定形式,冯契认为这一论说关乎整个逻辑思维,普遍适用于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形式;相较于主流解释把“三物”论说的本质勘定为对推理形式的刻画或对逻辑规律、原则的揭示,冯契强调这一论说提出了“类”“故”“理”三个范畴是逻辑思维所必具的学说;相较于主流解释基本依据“三物”论说本身所表述的“故—理—类”的顺序来进行文本诠释,冯契则是按照“类—故—理”的次序来讲逻辑范畴和后期墨家逻辑思想。
三、创造性诠释何以可能?
冯契之所以能对“三物”论说作出不同于主流解释的创造性诠释,在很大程度上跟他把自觉的哲学创作意识注入哲学史研究有关。当然,这绝不是说胡适、冯友兰、任继愈等人的哲学史著述就完全没有渗透他们各自的文化观念和哲学成见。以胡适为例,有见于自唐代以来缺乏恰当的逻辑方法已严重妨碍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着眼于“再造文明”,他提出“非儒学派的复兴是绝对需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些学派中我们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尤其如此”a参见胡适:《先秦名学史》,《先秦名学史》翻译组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年版,第7—9 页。译文有所 修 改,见Hu Shih: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Shanghai: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1922,pp.6—8。。基于此,他把名学方法(逻辑方法)视为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对包括后期墨家在内的非儒学派的逻辑思想给予了极大关注。此外,他强调在校勘、训诂哲学史料的基础上还必须贯通,而“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这样才能互相印证、相互发明。b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21—22 页。
一般而言,哲学史研究总是需要以某种理论思考或者说元哲学的自觉为前提,但在不同的哲学史著述中,元哲学自觉的表现形态与强烈程度不尽相同。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深受其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念的影响,他基于历史主义的态度也期待在中西文化的汇合中创造一种新的中国哲学,但囿于把哲学史的目的规定为明变、求因和评判,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并未被赋予为创作新的中国哲学作准备的功能。而冯友兰在哲学史研究中虽尽可能悬置其“正统”派的个人主见,对传统哲学思想作客观化的系统论述,但他明确把“照着讲”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视为哲学创作的准备,而其《贞元六书》所代表的“新理学”则是对宋明道学的一种“接着讲”。
需要注意的是,长时段的哲学史研究与元哲学自觉之间的关系未必能处处妥帖地反映在对哲学史个案的研究之中。就对后期墨家逻辑思想的研究来说,主流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只是在提供关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的历史知识,而不是旨在提出新的逻辑理论。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墨辩》研究主要展开于“名辩逻辑化”的范式之下,即运用西学东渐而来的传统逻辑(以及逻辑的其他分支)的术语、理论和方法,来梳理名辩的主要内容,勘定其理论本质,评判其历史地位。c参见晋荣东:《中国近现代名辩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20 页。鉴于《小取》篇的结构在《墨辩》六篇中相对完整,内容上能整合统摄其余五篇,其中论及的“名”“辞”“说”又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逻辑学所说的“概念”“判断”“推理”,于是研究者们纷纷以《小取》篇为基础,把传统逻辑作为“解释演述的工具”来贯通《墨辩》的相关文本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在这一范式下,“三物”论说或依附于对“辞”(判断)的说明,或依附于对“说”(推理)的解释,自然难以成为诠释和重构后期墨家逻辑思想的基础。
作为中国哲学史著述的第三个范例,“冯契所做的不是作为普通教材而作的哲学史,而是作为哲学创造的准备和哲学理论的长时段历史论证而著述的哲学史。”a参见高瑞泉:《在历史深处通达智慧之道——略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创作》,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6 期。这就是说,他的哲学史研究始终展开于自觉的哲学创作意识的指引之下。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元哲学自觉,冯契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研究了自先秦直至近代的整个中国哲学史,创造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具体到对后期墨家逻辑思想的研究,冯契之所以能对“三物”论说作出不同于主流解释的创造性诠释,可以说直接受益于他在辩证逻辑研究中对逻辑范畴问题的长期思考。
在1985 年4 月4 日的一次谈话中,冯契曾说:“从50 年代以来,我是围绕认识论搞研究的。一是逻辑和方法论,一是人的自由和真善美。”b冯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和内容的一些设想》,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第220 页。而逻辑范畴正是逻辑和方法论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从幸存下来的“文革”前讲课记录看,冯契在1956—57 年的《辩证唯物主义讲授记录稿》(后文或简作《辩唯记录稿》)中已考察了七组范畴,即:(1)单一、特殊和一般,(2)现象和本质,(3)规律、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4)根据和条件,(5)内容和形式,(6)现实和可能性,(7)必然性和偶然性,并对这些范畴之间的辩证联系进行了初步说明,但他并未讨论为什么是这七组范畴以及为什么按这样的次序来讲范畴等问题。c参见冯契:《辩证唯物主义讲授记录稿(铅印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办公室1956—57 年,第94—125 页。据讲授记录稿,在讲完范畴后,曾有学员提问:“斯大林讲辩证法的四个特征,恩格斯讲三个基本规律,而我们这里又讲了七组范畴,这中间的关系如何?为什么我们要按照这样一个次序来讲?”冯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但未回答第二个问题(第127—128 页)。关于这本讲授记录稿,可参见晋荣东:《冯契未刊〈辩证唯物主义讲授记录稿〉的考辨与解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3 期。
稍后不久,冯契又在1957 年12 月的《〈哲学笔记〉的辅导报告》(后文或简称《哲笔辅导》)中用了一讲来专论“逻辑范畴的体系问题”。在他看来,范畴体系主要包含三组范畴,第一组范畴“从单一和一般的考察开始,从现象深入到本质的研究,这是与认识发展的第一个规律相适应的。其次,从对事物本质矛盾的揭露来把握事物的内在必然的联系,因此第二组范畴就是如何通过关于因果关系的揭露达到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与认识发展的第二个规律相应。第三组的范畴是从必然向自由的飞跃,这与认识发展的第三个规律相应”d冯契:《〈哲学笔记〉的辅导报告(记录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1957 年,第21 页。关于认识发展的三个规律,详见《辩唯记录稿》第四部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或前引晋荣东《冯契未刊〈辩证唯物主义讲授记录稿〉的考辨与解读》一文。。冯契从认识发展规律的角度提出的范畴体系基本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辩唯记录稿》未能很好解决的范畴次序安排的问题,不过在这次辅导中,他尚未找到合适的名称来称呼这三组范畴,也没有具体说明这三组范畴究竟包含哪些范畴。a在讲完范畴体系的线索后,冯契结合《哲学笔记》讲了肯定与否定(有与无)、整体与部分(一与多)、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四对范畴,但并未说明这四对范畴与范畴体系应该包括的三组范畴之间的关系。参见冯契:《〈哲学笔记〉的辅导报告(记录稿)》,第22—44 页。
“文革”结束后,冯契从1977 年10 月开始再一次为哲学教师讲《哲学笔记》,讲课内容被记录整理为《辩证逻辑问题——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辅导报告》(后文或简作《辩逻问题》)。在专论“逻辑范畴”的第五讲,很可能就是受到《先秦哲学笔记》中有关墨辩、荀子的笔记的影响,他开始把恩格斯所说的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三对主要逻辑范畴与“类”“故”“理”对应起来。b冯契:《辩证逻辑问题——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辅导报告(记录稿)》,上海:上海师大哲学教研室1977—78 年版,第63 页。在此基础上,他坚持逻辑范畴体系的展开与认识深化扩展进程的一致,按照知其然(察类)、知其所以然(明故)、知其必然与当然(达理)的认识深化扩展进程,初步考察了关于“类”(一般)、关于“故”(根据)和关于“理”(规律)的三组范畴。冯契这一时期的研究已呈现出“史”与“思”有机融合、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造相互生成的特点。他不仅用“三物”论说系统提出的“类”“故”“理”来称呼反映认识深化扩展进程的三组范畴,而且开始联系中国哲学史的材料来具体说明这三组范畴及其辩证推移。
就对“三物”论说本身的诠释而言,冯契在《先秦哲学笔记》中已提出这一论说关乎整个逻辑思维,揭示了正确进行逻辑思维和辩说的必要条件。受益于对逻辑范畴问题的长期思考,尤其是发现了恩格斯所说的三对主要逻辑范畴与“类”“故”“理”之间的对应关系,他在《辩逻问题》中对“三物”论说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强调“类”“故”“理”三物的逻辑范畴本性,提出“类”“故”“理”指的是三组逻辑范畴,认为“类—故—理”的范畴顺序体现了认识深化扩展的进程,等等。
如果说这些新认识在《辩逻问题》中还依附于对逻辑范畴问题的思考,那么在《逻辑发展(记录稿)》中,这些新认识作为元哲学自觉的产物,直接促成了冯契对“三物”论说的独特诠释。
首先,由于强调“类”“故”“理”三物的逻辑范畴本性,而逻辑范畴是逻辑思维的基本环节,冯契没有像主流解释那样把“三物”论说的适用范围限制在逻辑思维的特定形式,而是认为它普遍适用于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多种形式。
其次,基于相同的理由,冯契开始把“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这些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之所以成立的根据与思维必须运用“故”“理”“类”这些逻辑范畴关联起来。
最后,由于“类”“故”“理”对应于恩格斯所说的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三对范畴,而这三对范畴的辩证推移体现了知其然(察类)、知其所以然(明故)、知其必然与当然(达理)的认识深化扩展进程,冯契不再拘泥于“三物”论说本身所表述的“故—理—类”的顺序,转而按照“类—故—理”的次序来讲逻辑范畴和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
在讲完《逻辑发展》后,冯契从1980 年9 月到1981 年6 月又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其中讲课记录稿的第八章专论“逻辑范畴”。a冯契曾设想作为“智慧说三篇”之一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其主旨是讲“化理论为方法”,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但是,现收入《冯契文集》的该书实际上是他在1980—81 年的讲课记录稿,不仅论述了上述主旨,还较详细地论述了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并把后者贯彻于价值领域,考察了理想与现实、人格等问题,即论述了部分“化理论为德性”的问题。冯契生前曾重新审读了讲课记录稿,拟就了修改计划,但该计划因他的遽然去世而未能实现。参见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383—384 页。在范畴本质的问题上,他坚持其一贯看法,强调“范畴是客观存在的一般形式的反映,是认识过程的一些阶段,又是逻辑思维的一些基本环节”b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42 页。,主张从客观辩证法、认识论或逻辑的不同侧面去研究范畴,但反对把范畴割裂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个部分。从逻辑侧面看,逻辑范畴是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中概括出来的,是认识史的总结和现实矛盾的反映,是流动的、灵活的、在对立中统一的;逻辑范畴的推移体现了正确思维的结构和运动法则,科学方法的正确使用总是蕴涵着逻辑范畴的运用。
相较于《辩逻问题》,冯契此时对逻辑范畴所涉诸论题的思考已臻成熟,为修改《逻辑发展》记录稿的相关内容提供了可能,并最终成就了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冯契对“三物”论说文本的理解与主流解释并无二致,即立论要有根据、理由(故),论证和辩驳要遵守逻辑规律和规则(理),推理要根据事物的种属包含关系(类)来进行。不过,他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追问了这些要求(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之所以成立的根据,并将其归结为人们在逻辑思维时必须运用“类”“故”“理”这些逻辑范畴。由此出发,他不再满足于把“三物”论说的本质表述为“讲了正确思维的三个必要条件”,而是将其勘定为“明确地提出了‘类’‘故’‘理’三个范畴是逻辑思维所必具的学说”。另一方面,冯契认为后期墨家明确把“类”“故”“理”作为逻辑思维形式的基本范畴加以系统考察,建立了形式逻辑的科学体系,因此相异于立足《小取》篇的结构与内容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的主流做法,他坚持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深化过程的统一,在按照“类—故—理”的次序来讲逻辑范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以“类”“故”“理”的范畴架构来诠释和重构后期墨家逻辑思想。
四、从“三物”论说的诠释到逻辑范畴体系的建构
冯契对逻辑范畴问题的思考最终成就了他对后期墨家“三物”论说作出了不同于主流解释的创造性诠释,而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又进一步为他建构逻辑范畴体系提供了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基本架构,由此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作之间那种“由此及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下文主要根据《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相关论述略作说明。

冯契后期墨家“三物”论说诠释与逻辑范畴研究相互影响示意图
是否需要给逻辑范畴安排一个体系?如果需要,又如何建构这个体系?这些都是冯契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思考的重要问题。关于体系的必要性,诚如恩格斯所说,“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a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页;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48页。,一切体系或迟或早都会被克服(保留其合理环节),被超过(达到更高层次),但冯契认为,既然逻辑思维能把握具体真理,哲学和科学的理论能够客观全面地把握一定层次上的实在,那么这样的理论就一定是体系化的,相应地,逻辑范畴也必须体系化,否则就难以把握具体。
至于如何建构逻辑范畴体系,冯契将其分解为两个子问题来加以考察:首先,范畴体系从哪里开始?他坚持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的辩证运动的统一,认识从哪里开始,逻辑就应该从那里开始。由于知识开始于对当前的呈现(“这个”)有所知觉和作出判断,形形色色的呈现总是依附于客观实在,而呈现既是实有的又是非实有的,因此作为认识从现象深入到本质的基本环节,逻辑范畴体系应该从客观实在出发,把实在理解为现象与本质的统一。b更详细的论证,参见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48—250 页。
其次,范畴体系如何展开?冯契对此的探索实际上也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主要的逻辑范畴有哪些?二是这些范畴如何联系、推移?关于第一个方面,冯契在“文革”前的探索集中于对西方哲学史上康德、黑格尔以及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述进行批判总结。在他看来,康德从判断分类中概括出关于量、质、关系和模态的四组范畴,除去关于质的范畴,剩下三组其实就是关于个别与一般、因果联系、必然与偶然的范畴。c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71—72 页。冯契把关于质的范畴所涉及的肯定与否定,解释为判断的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运动,参见《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53—254 页。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讨论“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组范畴d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下,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45—246 页。,恩格斯从黑格尔“概念论”的判断分类中概括出个别、特殊、普遍等一组范畴,又把“本质论”中的范畴概括为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这三个主要的对立。e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925—928、913 页;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52 页。“文革”结束后,冯契的逻辑范畴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日趋合流。正是受益于对逻辑范畴问题的长期研究,他在诠释“三物”论说时才能把“类”“故”“理”解释为逻辑范畴,并创造性地立足“类”“故”“理”的范畴架构来把握后期墨家逻辑思想;而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又使他在逻辑范畴研究中能充分利用中国哲学史的材料,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主要的逻辑范畴就是“类”“故”“理”三组,康德、黑格尔、恩格斯所说的三组范畴均对应于并可归结为这三者: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主要的逻辑范畴是三组或三个,就是“类”“故”“理”。《墨经·大取》提出:“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恩格斯所讲的个别和一般、同一和差异实际上是关于“类”的范畴,原因和结果是关于“故”的范畴,必然和偶然是关于“理”的范畴。a参见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53—254 页。
上述结论既是对有关后期墨家“三物”论说创造性诠释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中西哲学史上有关主要逻辑范畴的相关论述的批判总结,充分体现了其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作的高度融合与相互生成。对于这一极具原创性的观点,冯契明确表达了其在理论上的充分自信:“范畴的体系,我按照中国哲学的历史总结,按照‘类’‘故’‘理’三者来讲。‘类’‘故’‘理’这范畴的分类是中西哲学的共同结论。”b冯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和内容的一些设想》,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第225 页。
关于第二个方面,即这些范畴是如何联系、推移的?冯契认为,康德的“二律背反”虽揭示了范畴的矛盾,但没有认识到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范畴的辩证本性c参见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42 页。,因此他所提出的几组范畴仅仅是静态的分类,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和转化,不能反映认识的辩证运动。而根据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合理内核的概括,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体系体现了人类认识从现象揭露本质的一般过程,但这个范畴体系没有以客观实在作为出发点,并且是独断的。d同上书,第245—247 页。就冯契本人的探索来说,他坚持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认为“辩证逻辑的范畴是现实存在的本质联系方式、认识运动的基本环节和逻辑思维的普遍形式的统一”e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41 页。。因此,要回答逻辑范畴是如何联系、推移的这一问题,就必须阐明“类”“故”“理”这些范畴究竟体现了哪些认识辩证运动的基本环节?他指出:
从认识论来说,察类、明故、达理,是认识过程的必经环节。察类就是知其然,明故是知其所以然,达理则是知其必然与当然。“类”“故”“理”……这三组范畴是人们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并对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扩大所必经的一些环节。由然到所以然,再到必然和当然,是一个认识深化扩展的进程。a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54 页。
将“类”“故”“理”的内涵进一步解释为察类、明故、达理,这是冯契在逻辑范畴的内涵理解和认识基本环节的阐明方面所取得的又一理论创获。以此为前提,逻辑范畴的联系、推移自然就应该按照“(察)类—(明)故—(达)理”的次序来展开。
在解决了范畴体系从哪里开始、范畴体系如何展开等问题之后,冯契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为基础,对中西哲学史上逻辑范畴研究的积极成果予以辩证综合,用“三物”论说所提出的“类”“故”“理”为骨架建构了一个辩证思维的范畴体系:
总起来说,我们这样来安排范畴体系:从客观实在出发,把实在了解为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以及对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扩展的前进运动,也就是逻辑思维通过“类”“故”“理”等主要范畴的矛盾运动来把握性与天道的过程。b同上书,第256 页。
这个体系按照“类”(包括同一和差异,个别、特殊和一般,质和量,类和关系等)、“故”(包括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条件和根据,实体和作用,内容和形式,客观根据和人的目的等)、“理”(包括现实、可能与必然,必然与偶然,目的、手段和当然,必然和自由等)的次序来展开,反映了认识从知其然(察类)到知其所以然(明故),再到知其必然与当然(达理)的认识深化扩展进程,体现了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辩证运动的统一。
冯契强调,这个范畴体系不是封闭的、独断的,而是发展的、开放的,即范畴的数目会增加,范畴的内涵会深化,范畴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丰富。这一方面是因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都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总有许多逻辑范畴还没有把握(自然现象之网是无限丰富的),而且已经揭露的逻辑范畴总有待于研究再研究”a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47 页。冯契生前曾在讲课记录稿的目录页第八章第二、三节标题前加了“系统论”三字,可能是想把系统论的相关思想甚至“系统”这个范畴补充进关于“类”的范畴及其解释之中(第385 页)。此外,他在介绍《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时所提到的关于“类”“故”“理”的具体范畴已与讲课记录稿的表述有所不同。参见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41 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冯契在建构体系时重在“揭示出一组组范畴的矛盾运动,并对整个的范畴体系有一个安排,这样就能给人们提供观点和方法。如果这组范畴和那组范畴之间的联系讲不清楚,我们就不说,以后的人会超过我们,他们会提出更好的见解,会克服我们的弱点,超过我们的体系”b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55 页。。就范畴体系的整体而言,对立统一、矛盾发展原理是其核心。正是通过“类”“故”“理”这些范畴的辩证推移并进行思辨的综合,人们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地揭示具体真理,把握性与天道,亦即运用逻辑思维从相对中把握绝对、从有限中揭示无限,而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运动便表现为无止境的前进发展过程。c参见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42 页。对冯契的逻辑范畴体系更为深入的研究,可参见彭漪涟:《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20—256 页。
冯契所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是“逻辑范畴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突破和新进展。这无论对于哲学、逻辑学还是对于其他一切具体科学关于范畴和范畴体系的研究与建构来说,都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理论意义的”a参见彭漪涟:《对智慧探索历程的逻辑概括——论冯契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2 期。。相较于同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种种范畴体系,这个体系独树一帜,不仅体现了马、中、西的深度融合b参见童世骏:《现代性的哲学思考》,载杨国荣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哲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346—348 页。,而且以后期墨家“三物”论说提出的“类”“故”“理”作为逻辑范畴的骨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个范畴体系也是构成“智慧说”哲学体系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理论创获。“古人既然已提出‘类’‘故’‘理’的范畴,说明古人也已经具体而微地把握了逻辑范畴的体系。……我们用‘类’‘故’‘理’作为逻辑范畴的骨架,这好像也是出发点的复归。”c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54 页。从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到建构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冯契以其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作的高度融合和相互生成,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从历史研究走向理论创造的宝贵范例。

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
- 哲学分析的其它文章
- 知识和真命题的关系
——回到金岳霖的《知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