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意义
枣红马
就像白昼需要黑夜一样,黑夜也需要白昼,因此意义需要荒谬,荒谬也需要意义。(荣格)
——题记
引 论
继幻象摄影集《空之像》、梦幻叙事作品集《寐语》之后,张鲜明凭借他那极具魔幻色彩的《暗风景》系列诗歌作品,在深度意象时代的诗坛闪亮登场,以其闪耀着荒诞性美学光芒的幻象诗学风貌,强力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如果说顾城的《鬼进城》是中国新诗进入深度意象时代的引领性作品,那么张鲜明的《暗风景》系列则可视作深度意象时代的持续性、促进性作品。
《暗风景》系列作品整体上就是一部幻象的诗学结构,尤其是以荒诞性幻象构建的精神世界。文本里平静的意象覆盖着心理学级别的狂奔,幻象在诗人心理的锅灶里已经燃烧到了极点。也只有到了极点,心理的火焰才呈现出极度的夸张变形,从中有人看到它是一种极光,有人看到它正在飞雪狂舞,甚至有人看到那火焰竟是一丛鬼火。因为诗人对于内心世界以至于灵魂世界的表达,唤起了人们深入骨髓的想象,这让我们惊异地发现,张鲜明极致的幻象在《暗风景》里产生了刻骨铭心的诗学力量。
幻象,既是一种心理学现象的呈现,又是诗的意象状态,而且是意象的极致状态。
幻象诗学的虚幻美、神秘美以及荒诞美增加了诗学的表现力。正如现代主义心理学家荣格所说:“幻象时刻的美和情感的强烈,是无法言传的。”[1]所以,从柏拉圖开始,哲学家、心理学家、文艺评论家、诗人逐渐认识到了幻象的诗学理念。尤其是在现代主义诗人那里,幻象从诗人最隐秘、最深邃的灵魂世界里幻化,作为深度意象而普遍显现,形成了诗学的自觉。中国新诗进入深度意象时代之后,意象的表达已经与世界诗坛同步发展,幻象诗学可以说标志着中国新诗诗学进入了深度成熟期。
幻象,它的本质在于“幻”。“幻”的创造性心理学表现,是一种极致的心理活动和呈现,因为一般的心理活动的呈现只是创造一般的意象状态,达不到“幻”的心理学级别和美学级别。在现代主义诗学那里,诗人的意象创造必然会呈现出幻象状态,因为幻象是在诗人深度意识里孕育,在诗人强烈的心理活动中成长。于是问题就来了,对于幻象诗学,读者该表现出怎样的阅读心理。作为诗的文本,幻象向来不是孤立地存在,有时候虽然是孤独的,但它的存在必须有阅读心理的支撑。具体到张鲜明的《暗风景》系列,如果从表层的意象阅读心理来审视,幻象的演绎似乎是一种“荒谬”的呈现,但这种审视有可能会阻碍对幻象诗学精神的探寻和理解。那么,以深层的意象阅读心理去审视幻象的“荒谬”,荒谬却不再是“荒谬”,它已经升华到了美学的意义。正如荣格所理解的,这种意义并不是一概的中规中矩,它需要“荒谬”的呈现,这样才能进入深度精神状态。所以,要理解张鲜明幻象诗学的精神蓄蕴,一定要用深度的甚至是极致的阅读心理,就是要从深度精神的角度去审视。这时候就会发现,那看似虚妄的“荒谬”的幻象,实则是拥有了灵魂的隐喻,甚至是一种超越性的真实,即深度的真实。
所以,张鲜明幻象诗学的“荒谬”状态,其意义就在于诗人的灵魂用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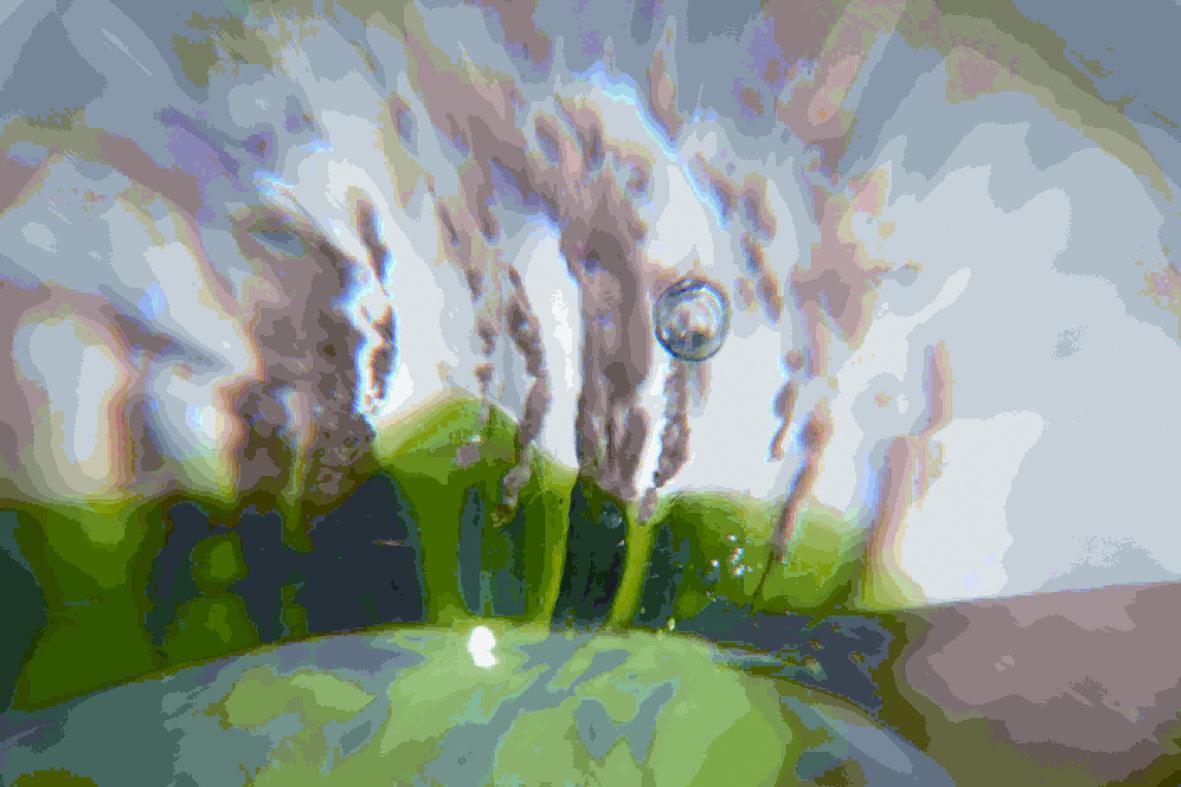
一.幻象状态下的精神结构,现实和灵魂的两重世界的“悖谬”构成。荒诞性幻象的表达更真实也更有深度和力度。
张鲜明最崇拜的作家是卡夫卡,创作上也最受卡夫卡的影响。他直言不讳地说:“莫非这个时代仍然需要一个卡夫卡,上帝就派我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莫非我是卡夫卡转世,是活着的卡夫卡?”[2]诗人不仅崇拜卡夫卡的荒诞性表达,更崇拜卡夫卡的创作态度,即卡夫卡说的要重新审察世界一遍。好的作家不会去重复别人的观察,而且在审察世界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灵魂用意,即建立自己的精神结构。张鲜明体会到了卡夫卡的灵魂用意,那就是用“悖谬”的哲学思维创建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卡夫卡建立的精神结构中,是正和负的撕裂而共存的状态,“负”让他感到自己存在的悲剧感,“正”让他感到自己存在的创造力。
诗人创建的精神世界不应是空中楼阁,当是由意象和意象的联结而构成,张鲜明学习到了小说家的本事。“卡夫卡常常是从日常生活入手的,正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提取出怪异事件来,让大家惊诧。”[3]怪异的事件看似是荒谬的,但它出现在诗里就不再是单纯的荒谬事件,而是成了诗人精神世界的构成要件。张鲜明在日常生活和幻象的交融中,建立了双重的精神结构:一重是世俗的我和精神的我,再一重是我(世俗和精神)与世界的关系。“荒谬”的幻象不是诗人的强制,而是灵魂世界里自然生成的精神现象。当悖谬思维产生荒诞的美学效果,那些冲撞而又融合的各种意象,在张鲜明诗的幻象里面,就蓄蕴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灵魂的撕裂、抗争和创造。按他自己的话就是由于“人与人关系的疏离感,因而产生了灵魂的分裂感、孤独感等等”[4]。
当然,在西方现代派诗人那里,这种创作态度司空见惯,在中国现代主义诗人那里,也比比皆是,因为现代主义艺术的美学思潮的精神倾向就是深度而强劲的内心表达。张鲜明是这种思潮的独立实践者,他以自己惯用的荒诞性的幻象强化自己的感觉世界,以现实和精神的融合深度建造诗人自己的精神炼狱。《谁在敲门》:“门/自己响了”。《只要你答应把状子递上去》:“门开了/没有人,没有风,没有脚步声/只有一声/重重的/叹息//门再次开了/黑暗中传来一声低语:‘我是从这屋子飞下去的,但我不是蛾人。//门第三次开了/一根细细的青藤爬进窗棂:‘只要你答应把状子递上去,我就不打扰了。//我点点头//门/慢慢地关上了/礼貌而谦卑地响了一声。”世界本来是真实地存在,而在张鲜明幻象的感觉里,它却是“荒谬”地存在,“荒谬”的意象似乎是看不到摸不着,把诗人捉弄得异常地无奈和屈服。《子弹已经射出》:“他们说我有罪/今天执行死刑//监刑的人/在人群中//子弹已经射出//妈呀——/要是没有脑袋就好了!//四处都是/枪声。”从无奈到惊悚,现实世界幻化出来的子弹的幻象进入了诗人的灵魂世界。想象是脱缰的野马,它任由人们的思维在不着边际、没有边界的精神世界里遨游,而现实世界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身边并与我们纠缠。现世与我们形影不离,即使躲进无人的房间里,现世也会以各种信息的面目渗透进来,我们很难摆脱它的纠缠。因为现世饱含着世俗的力量,并且时时以缠斗的方式向人们攻击。这种缠斗的致命处在于攻心,几乎每个人都会无奈地败下阵来。张鲜明的体会真切而深邃。《凌迟》:“不见柱子,不见绳子,不见刀子/我在接受一场凌迟/而刽子手/正是我自己//不见血,不疼痛,只有嗖嗖的切割声/从头发到脚趾/我的每一个器官/化作羽毛/在飞//我分崩,我离析,我身轻如燕/直至成为一粒/虚拟的/尘埃//我依然活着,却已经没有肉体/连我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当然也就不知道/我/跟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关系//好啊,彼此都轻松了——/不用说再见/也无须跟任何人汇报/我在哪里。”精神的“我”被现世撕裂了,陷入一片迷茫,这是深入到精神世界的悲剧,此为“负”。《浑身的毛孔正在裂开》:“我的眼睛软塌塌地/闭着/已经没有力气睁开//而你——/我的神啊/却把眼睛越瞪越大/就像宇宙大爆炸//你是担心谁把这个世界偷走/还是有更深的想法?/你大概是横下了一条心——/只要这个世界还在/你就会强行借我的身体/朝着人间/瞪下去,瞪下去//如今,我只剩下一张皮/我的神啊/看你怎么借我的眼睛?//哎呀,我浑身的毛孔/正在裂开。”世俗的“我”已经形同虚设,此为“负”,而精神的“我”犹如宇宙爆炸,让世俗的“我”毛孔裂开,精神生命的力量在爆发,此为“正”。虽然,“正”和“负”都是人的深度精神的正常的生命状态,但细细体会,张鲜明诗中精神世界的力量对世俗世界的力量的抗争,已经呈现出了压倒性的强势,精神的“我”已经创造出了生命的力量。西方很多现代主义诗人都强调诗学精神是世界的精神财富,可能就在于这种诗学创造了充满力量的精神生命。
由于精神世界里“正”和“负”的缠斗,由于这种缠斗使精神世界发生了变形,张鲜明的荒诞性的幻象表达产生了奇异的诗学效果,正如著名诗评家耿占春所评价的,“《暗风景》如同荒诞而精彩纷呈的不连续的惊悚片”。惊悚,让读者感受到了诗人最隐秘、最深度的心理活动。诗人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受苦,因为世俗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诗人用幻象来表达折磨产生的隐秘的痛苦,于是就透出了灵魂的真实。诗人的灵魂在撕裂,在受难,也在奋争。然而,即使奋争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灵魂世界的兴奋情势也摆脱不了隐秘的痛苦,因为世俗世界的魔性总是不依不饶地与人的灵魂世界缠斗,灵魂世界和世俗世界一直并会永远处于这样的存在状态。灵魂,是人的自性,是生命的力量之源。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是由灵魂建造的,是形而上的,灵魂属于一个更高的精神世界。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生命的本源,而且渗透在宇宙中。荣格以自己的原始意象理论认为灵魂是生命的气息,是生命的原动力,是生命力量的标志。生命的精神力量永远不会向世俗的魔性屈服,所以,“灵魂,是鲜活的深邃的不朽的人的本質和精神力量”[5]。而且,灵魂世界里的缠斗愈激烈,那么,“荒谬”的意义就会愈强烈。
显然,张鲜明荒诞美学的表达不是停留在修辞的技术层面上,而是诗人作为人的最为本性的精神力量的表达。诗人的精神力量的创造不是抒情模式,也不是田园诗态势,而是在灵魂深处。灵魂深处的幻象看似荒谬,却是诗人深度精神创造的深度意象。这样的深度意象,不仅挖掘出了诗人精神冻土下的灵魂世界,不仅沉重地敲击着读者深层的阅读心理,也表达出文本状态下灵魂世界的深度存在。因为,“梦是灵魂发出的具有引导性的话语”[6]。
张鲜明这种诗的表达不仅进入了深层的心理世界,“荒谬”也具有了哲学层面的意义。正如尼采说的,“如果你长时间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7]。所以荣格说,“走向地狱就意味着变成地狱”[8]。诗人寻找灵魂世界,去天堂很难找到它的入口处,他必须走向精神的地狱,因为灵魂世界的入口处就在深层的精神世界。当诗人寻找到深度自我的时候,他也建造了自己的精神炼狱。所以,精神炼狱的两种力量既撕裂而又交织地存在,缠斗性的存在必然会有“荒谬”的意象呈现出来,因为只有这种意象才是真实的灵魂表达。诗的意象就这样在灵魂境域里以悖谬的思维酿造着张鲜明的幻象诗学,正和负、世俗的我和精神的我融合的精神力量鲜活而深邃,并且不停地创造着。
二.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的“荒谬性”,创造出幻象情境。强化意象是幻象诗学创造的机理。
诗作为诗,从中国诗学的角度来看,一定是要创造出诗的情境和诗的意境,而现代主义诗则更强化了诗人的心理创造功能,情境创造的意象时时被提升至幻象的级别。探讨张鲜明的幻象诗学,笔者借用了计算机科学的术语VR和AR。
在张鲜明的诗集《暗风景》里,几乎每一首诗中的意象都呈现为幻象的状态,都是典型的幻象营造的深度意象。读他的诗,想象他诗中荒诞的意象,犹如戴上了VR眼镜,满眼都是虚拟现实。《只要你答应把状子递上去》(见上述摘引)这首诗有情节、有细节,甚至是故事性的,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个现实情境。可细看时,这情境无疑是虚拟的现实,因为诗人已经把现实情境通过虚拟而幻象化了。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3D的现实世界里,但现实世界被作家写在纸上的时候,就成为了平面,失去了3D世界的真实性。难怪美国的一位作家无奈地感叹,在脑子里想的是那样地真实,而一旦写到纸上,就感到没有了真实性。这位美国作家开出的处方是写内心世界的真实。但内心世界的表达应该是创造性的、多角度的、千姿百态的创作,在内心世界以至于灵魂世界里幻化出意象来虚拟现实,其实就是张鲜明寻找出的一种真实表达内心世界的创作方法。因为虚拟现实不仅保持了真实的3D世界,还保持了现实世界的侵浸性。侵浸性,即“我”仍然处于幻象状态下的真实的场景中。不仅诗人自己享受着侵浸性,读者也享受着侵浸性,在诗的情境里,诗人和读者都作为意象“在场”。意象的“在场”,这是现代主义诗学的基本原则。
AR就是增强现实。现实很多时候是平实的状态,虽然有时候现实是那样地激动人心,甚至还能超越人们的想象力,然而,人们还是不满意现实场景里世俗的黏性,不满意世俗黏性的刺激,于是,在现实的场景中,就增加了诸多的非现实的意象,如虚幻的细节以及动作,让现实的场景变得丰富了,被提升了。增强现实就是增强刺激性,刺激性的增强,无疑强化了人们的想象力量。这是张鲜明的诗《陀螺与鞭子》:“鞭子抽着/陀螺转着//鞭子/从上头来/从下头来/从左边来/从右边来/鞭子,像网一样/撒过来//谁看见鞭子/谁就是陀螺//陀螺不想成为陀螺/它呜呜地哭着/而鞭子却脆生生地说:‘这是对你的信任,你哭个什么!//终于有一天/晕头转向的陀螺/转成了鞭子/朝着自身/不停地/抽着/就像一个人的肉搏。”鞭子抽陀螺,陀螺旋转,这是基本的现实场景。接着,网一样的鞭子开始幻化出一连串“荒谬”的意象,这些非现实的场景在现实场景里出现,就成了诗的幻象。毋庸置疑,诗的幻象增强了现实场景的表达。强化表达,是诗人的天职。诗人不可能啰里啰唆地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他要在有限的情境里传达出无限的意境。有限表达无限,就必然要去强化表达,不仅要强化意象的浓缩表达,还要强化诗人的心理创造,不论是浓缩还是创造,意象的幻象化都是一种诗学表现,而张鲜明的强化表达则达到了幻象诗学的层级。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在张鲜明幻象诗学里的运用,涉及两种美学的效果,即有意味的形式和荒诞性。
“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论断是20世纪初英国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美学理念,虽然是针对视觉艺术而言,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艺术,因为只有具有“有意味的形式”的作品才会使人产生审美感情。这种美学理念对于塞尚以来的后期印象派以及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等现代派艺术的出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诗的意象尤其是幻象是诗人的心理活动产生的内视影像,从这个角度来看,诗可以说是心灵的视觉艺术,所以“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学理念也适用于现代主义诗学。
荒诞性表现形式虽然古已有之,而到了现代主义诗人那里,则表现得普遍而十足。因为20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狂潮异军突起,揭开了反叛美学思潮的世纪,文学的意识流、表现主义、荒诞派、超现实主义,从外界到内心、从理智到荒诞,冲破了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学的藩篱,尤其是二战劫难之后,荒诞派在西方竟形成了一个文学运动。荒诞派美学的内涵让世界看到一个反抗绝望的意象英雄,一个痛苦挣扎的意象灵魂,而在表现形式上却是那样地极端化地夸张变形,象征和暗喻显示了深入骨髓的表现效果。由此可言,荒诞性美学是“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学的升级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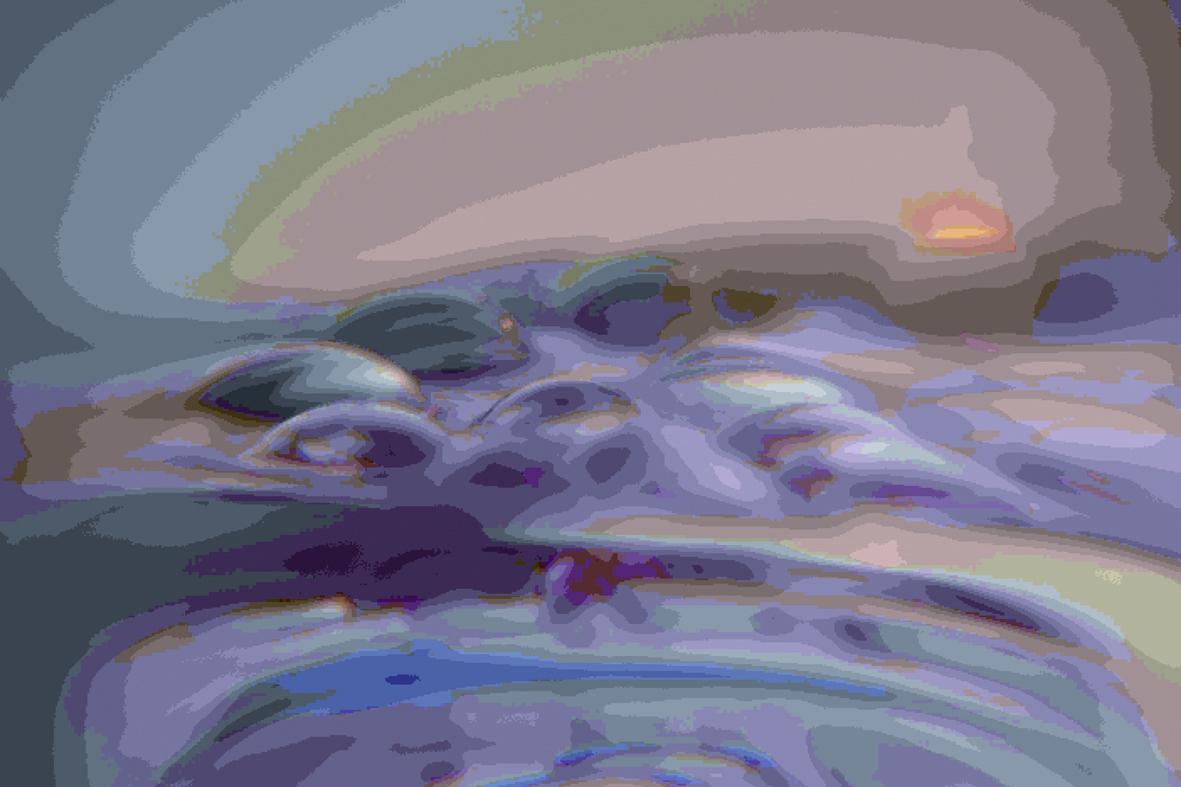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的计算机科学的表现形式一经面世,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受到青年人的热捧。因为,他们受到了超越往常的刺激。其实,人自从成为人之后,就开始不断寻求各种新的力量刺激感觉、意识、情感和思维。叔本华等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人的生存是以快乐为原则,生理的和心理的刺激往往增强了快乐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寻求新的刺激的历程,因为生命的创造一刻也离不开精神的刺激。刺激尤其是精神的刺激上升到美学的层面,就萌发和蕴含了精神生命的力量,诗也就蕴涵了诗学的力量。
张鲜明的诗以“有意味的形式”和荒诞性的美学原理创造的幻象,既是诗人和读者作为人的心理需求,也是现代主义诗学的需求。反过来,这种需求又刺激诗人深度创造更有意味的形式、更具美学的诗的幻象。这种互文的诉求,是诗学不断创造的一种动力。“荒谬”的意象,就成为了张鲜明幻象诗学的发酵剂。
三.诗学幻象的两种创设形态,梦幻和魔幻。天然感觉和天然积淀的诗学意义。
正如本文开始说的那样,幻象是人的心理活动达到极致而幻化的意象,具体来说,是梦幻和魔幻两种心理活动幻化的意象。
1.梦幻
梦幻是诗人原生态的创造性的心理活动,往往呈现出无意識状态。
著名法国诗学理论家雅克·马利坦认为,诗人的直觉是“创造性直觉”或“诗性直觉”,它“产生于精神无意识中”[9]。他赞同弗洛伊德的意识结构理论,认为人的意识分为自动无意识、精神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诗性认识以无意识或前意识的方式产生”[10],诗性直觉“是人的精神本性的一种基本表现,也是浸泡在意象和情感中的精神之创造性的根本要求”[11]。
创造性直觉或诗性直觉的发生机理,是从天然直觉到创造性直觉,也就是从自然梦幻到诗学梦幻,这是一个既是天然又是诗学的精神幻化和提升的过程。很奇特,很奇妙,弗洛伊德按照自己的体系解释了这个心理创造过程;又很诗学,马利坦按照弗氏理论解释了这个诗学发生过程。无疑,马利坦的诗学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基础之上。弗氏理论过去虽然让人们疑惑,以致被诺奖委员会提名三十三次却始终无缘,但现在它已经实实在在地被现代主义作家普遍接受,具有了世界性意义。
并非所有的诗人都具有梦幻直觉的本事,但张鲜明有,而且是天生的本事。这种天生的本事是独具的,每一个诗人的无意识心理状态都不可能与他人重复,所以,张鲜明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诗学幻象。具体阅读张鲜明的诗,尤其是写梦而且是纯写梦境的诗。《吃梦》:“早上起来/我的枕头胖了许多//枕头叽叽哇哇地叫着/梦/在里头乱作一团//此刻,枕头的一角/叼着一个梦/就像巨蜥在吞食青蛙//我正要逃跑/枕头突然拽住我:/‘哪里去?你就是一个梦!”《总是在深夜到来》:“你总是在深夜到来/坐在我的心尖上/吃我的梦,啜饮夜色//你占用我的嘴巴/拧我的脸,揪我的头发/把往事抛洒得/满天满地//你瞪着眼/看我/我闭起眼/看你/就像天花板和地板/在对峙//知道你不会轻易走开/我骂骂咧咧地/走到阳光里/看你还敢不敢/追上来。”《抱住我的腿》:“梦/又追上来了//我的每根头发每根汗毛/都颤悠悠地/站着梦/它们拥挤,争吵,撕咬/它们肥胖,好动/我的身体已经盛不下它们//我正在为每一个梦安排房间/突然听见叽哇一声——/一个梦没有站稳/从我舌尖上/摔了下来//梦是自己跌倒的/却哭叫着/抱住我的腿。”
有人可能会问,这写的是什么?没错,写的就是梦。那么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这是人们阅读时的一种求解性的习惯性思维。可是在这里,诗人并不是去刻意表达什么意思,他就是去写梦境。可是细细揣摩起来,也很有意思。这些梦幻的意象就是诗人的天然感觉。无意识是诗人灵魂世界的天然呈现,这种呈现只属于天然感觉,而这种感觉则表达出了诗人最为隐秘的地方——灵魂世界幻化出的意象,既是天然的幻象,又是诗学的幻象。所以,幻象的创造就是诗人精神的创造,幻象的世界就是诗人精神的世界,诗人的感觉、意识、思维、情感和精神尽在幻象的蓄蕴之中。这就是梦幻的最大意思,也是张鲜明幻象诗学的重要意思。诗人的创造心理学过程是从天然直觉到创造性(诗学)直觉,从天然梦幻到诗学梦幻,而这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其源泉就是天然感觉。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就是内在欲望冲动的挣扎外在化。内在冲突和外在表现的统一就是梦幻的幻化过程,这个过程是诗人创造的思维过程,也是诗学酿造的过程。
2.魔幻
仔细比较一下,魔幻和梦幻的存在状态具有一定的差别性。梦幻是从天然的感觉产生出来,是一种不自觉、下意识产生状态。而魔幻,则是由魔法幻化出的幻象。既然是魔法,那就应该是一种方法;既然是一种方法,那就是后天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解,“经由魔法的方式,人类可以与灵魂交通,同时,魔法的概念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就如我们所认为的,灵化自然的过程尚未完成等例子里”[12]。他说的“魔法的方式”,就是笔者所理解的张鲜明魔幻性幻象诗学的一种表达手段。
弗氏的这段话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与灵魂交通,一个是灵化自然。这两个关键点都涉及人的最隐秘、最深层的东西,而且只能靠感觉来体会这个灵化的过程。如果说梦幻是“天然感觉”,那么,魔幻应该是“返还天然感觉”。
“返还天然感觉”在诗的创作心理过程中极为重要。因为,诗人创作不一定都是由梦开始,往往很多时候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他的灵感有各种各样的现实刺激和想象刺激,甚至是理念的、主题先行的。但是,诗人在灵感的刺激下,必须丢掉那些刺激灵感的元素,返还到天然感觉。这就是“白日梦”创造的开始,从清醒到魔幻。
“返还天然感觉”,读者在张鲜明的诗里能够体会到。《脚窝》:“我的脚窝很深//我在我的脚窝里尖叫。”《冷汗》:“你冒充钟馗/在我熟睡的时候,偷走我的宝剑/就像悄然出门的城防队员//你走遍城市,穿行于数不清的梦境/黎明时分/你一身征尘,回到我的枕边/手中的剑已经卷刃/红缨上/挂着冷汗//可否借你的见闻/拍一部恐怖片?”在自己的脚窝里尖叫,就是魔幻诗艺幻化的幻象;红缨上挂着冷汗,也是魔幻诗艺幻化的幻象。从诗中可以感觉到,诗人在清醒时看到脚窝,看到冷汗,灵感便来了,感觉返还到天然,用魔幻的诗艺创造出了幻象。这种诗的存在状态表明,诗人是清醒的,而幻象是魔幻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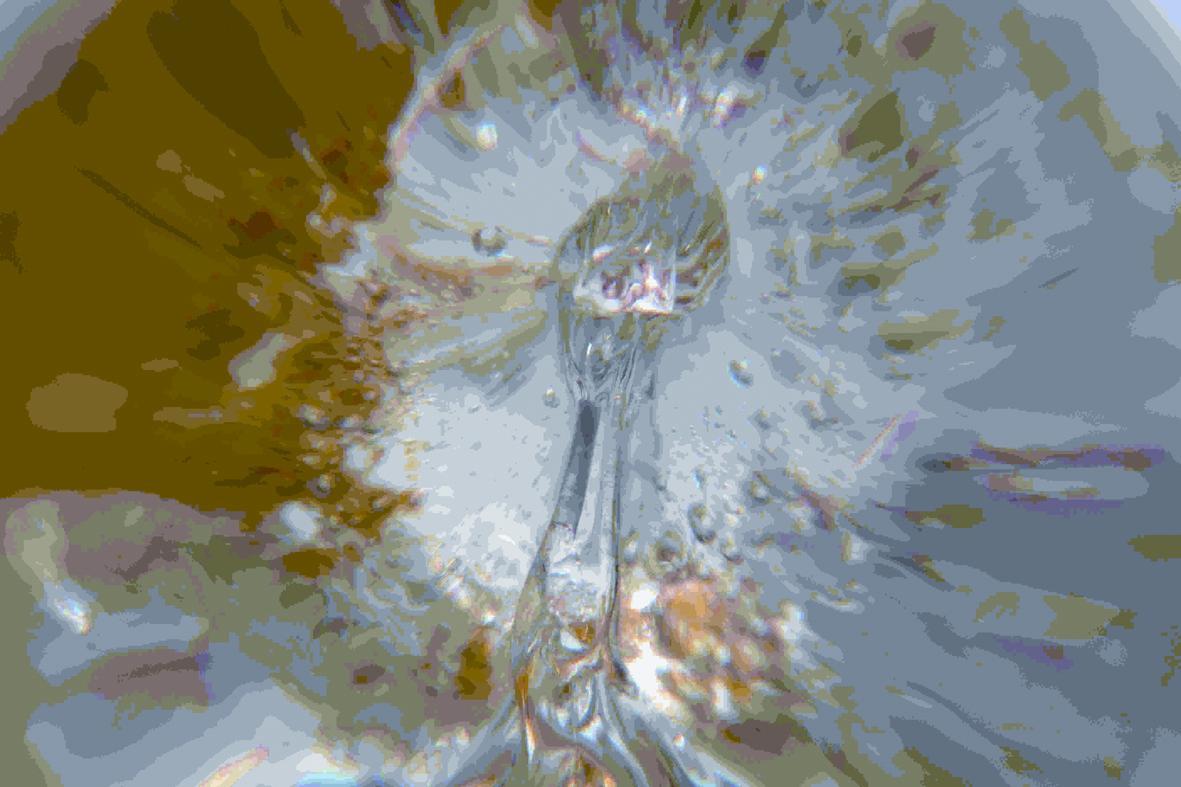
不论是梦幻的幻象,还是魔幻的幻象,诗人都必须具有最隐秘的、最本性的感觉,或者说是创造性直觉即诗性直觉。这种感觉既是人的本性,又是诗学的特性。没有这种感觉,诗人不会创造出诗的幻象。不论是天然感觉还是返还天然感觉,都是现代主义诗学的本源。诗人用想象看见了看不见的世界,而这个想象眼睛的瞳孔就是感觉。诗人创造的是一个不曾有的世界,诗人用感觉的瞳孔看到了那个不存在的世界,用意象表现出来,就构成了诗的世界。天然感觉来了,一切生命都在跟诗人对话,自然、社会、历史以及思潮,也都会成为活的意象,生命创造的意象,都蕴含着能够被诗人感受的力量。被诗人感受之后,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幻化为幻象,这就是精神生命力量的內在意蕴,一切都从天然的感觉中幻出。诗人的天然感觉能让冰冷的石头说出温柔的话语,能让冰冷的石头长出青青嫩叶,开出散发着芬芳的花朵,冰冷的石头在天然感觉的无意识作用下,正在迸发出生命的力量。
这些梦幻或魔幻的诱惑力,是一种想象的力量,一般的感觉听不到也看不到,要能感受到这种想象的力量,只有靠天然感觉,即诗性的感觉。所以,诗性感觉是灵魂深处的感觉,密而不透风,深而不可测。它在现代主义诗学里,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在很早的时候,启蒙时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洛克就用感觉起源说创造了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世界观。他把这个源泉流向的通道称为感官和内部感官(反省),他说:“这两种东西,就是作为感觉对象的外界的、物质的东西,和作为反省对象的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内部活动,在我看来乃是产生我们全部观念的仅有的来源。”[13]
如果借用洛克的哲学感觉起源说用到诗学上,那么,诗学上的感觉就是想象力的源头,尤其是现代主义诗学,最为隐秘的感觉就是天然感觉,它决定了一个诗人想象的隐秘性和深邃性,也决定了意象的深度形态。天然感觉,是人性最隐秘、最纯净的感觉,也是人的精神积淀所渗透的感觉。精神积淀同样应该是不受污染的积淀,环境的影响、知识的获得、观念的培养在诗人的意识里都会有积淀,这种天然感觉支持下的积淀在诗人的潜意识里必定会产生精神活动,这种活动是内视,是意象的胚胎。于是也就不难理解,马利坦为什么把创造性直觉称为诗性直觉,因为那是天然感觉和天然积淀的融合。而且,天然感觉和天然积淀往往是自发地以梦的形式出现。
张鲜明具有做梦的潜质和特质。他曾说:“我记得,从1997年7月开始,连续好长时间我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譬如,波德莱尔变成了一头公牛闯进我的房间,用尖利的犄角划开了我的腹腔,从我体内流出来的不是内脏而是一堆甜腻腻的铅字,那些铅字化作苍蝇飞走了。那个阶段,我时常在梦中作诗,那是我在清醒的时候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诗歌。出于好奇,我顺手把这些梦境和诗句记下来。从那以后,我的床头总是放着纸和笔,还有笔记本电脑,以便随时记录梦境。后来,我就把梦境当作素材,写了一批超现实主义诗歌。”[14]梦是无意识的,但并非无端的;梦是“荒谬”的,但不是没有意义的。梦深入并唤醒诗人天然的感觉和天然的积淀,就会奇迹般地幻化出诗的幻象。于是,张鲜明的创作实践给了人们思索的灵感,天然感觉和天然积淀作为诗的创造心理学,或许应该成为现代主义诗学的一个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瑞士]荣格.刘国彬,杨德友译.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483.
[2][3][4][14]张鲜明.我是活着的卡夫卡?(未刊文).
[5]李传申.深邃的世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46.
[6][7][8][瑞士]荣格.周党伟译.红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111,136,136.
[9][10][11][法]雅克·马利坦.克冰译.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27,131,128.
[12][奥]弗洛伊德.杨庸一译.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101.
[1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51.
美编 敏子 编辑 王晓杰 165334926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