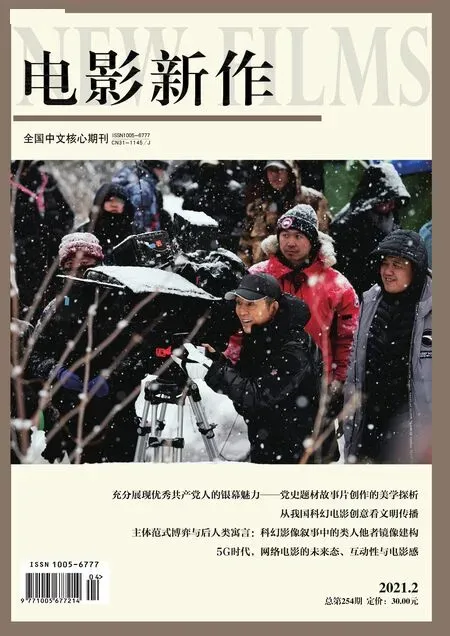论“互动电影”主体共生关系的构建
陈 玮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看来,一切事物的关系,究其根本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不同主体间的交互关系;随着这种关系的不断交流、转化,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交融、相互塑造。依据这一论断,电影创作者与观影者是平列对举的两个主体,电影是他们构筑的“共同世界”,两个主体交互活动不断丰富电影世界的内涵,双方形成了互相促进“共生关系”。
“共生”本为生物学领域的概念,最早由生物学家德贝里提出,是指生态系统中两种不同生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互利关系。这一理论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成为各个领域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将电影比作一个生态系统,创作者和观影者就是这个系统中的核心要素,两者通过观影活动完成信息的流转和思想的对话。数字技术催生的“互动电影”,使电影生态系统中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电影艺术从关注导演的创作空间转向关注观影者的选择空间,走向了创作者与观影者共生、共建,和谐发展的方向。目前为止,以主体共生为核心理念的互动电影创作观念体系尚未有效构建,本文以此为目的,深入探讨创作主体与观影主体在互动电影构建主义观影环境中的多层次对话机制,辨析互动电影的观赏性、体验性如何在非线性传播中实现创新熵增。
一、电影创作者与观影者共生关系的演变
在电影诞生之初的默片时代,由于技术限制,电影创作者通过演员的肢体语言、单画面的字幕以及电影现场配乐,使观众解读剧情。恰恰是这种没有对白的缺憾,成了电影艺术的“留白”。创作者给观众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揣摩演员的表演意图,代入角色的内心,进而自行解读电影的思想和主题。默片的这一特性,促使观众将不完整的视听素材,按照自身经验,组织成有意义的完形整体。进而,观影主体与创作主体形成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有声电影诞生以后,电影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电影声音与画面的表达日臻完美。1964年,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中提出:电影作为高清晰度的媒介,具有观影时间长、观影环境密闭等特点,会减少观影观影模仿、触觉和动觉的协同作用;电影创作主体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总是被动接受电影的内容与思想。麦克卢汉认为,电影所传达的信息清晰而饱满,并未留下空白让观众自行补充,无需观影者深度参与。由此可见,电影拍摄技术的成熟,反而对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交互关系产生了反作用,主体间丰富而灵动的共生关系,转为无生气的支配关系。
20世纪60年代,蒙特利尔世博会放映了世界第一部互动电影:《自动电影:一个男人和它的房子》(Radúz Cincera
,1967)。导演在影院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了红绿两个按钮,观众通过按下按钮进行投票决定剧情走向。此后,电影产业逐渐开始了互动电影的尝试。21世纪,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电影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基于数字交互技术的互动电影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语言。无论是在影院还是在私人观影空间,互动电影的功能和设备都能让观众着手讲故事,并主动地推动情节发展。互动电影通过分支选项技术、游戏引擎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提供给观影者剧情选择的自由度和深度参与的体验感。互动电影的发展,使得电影摆脱了为技术所累的宿命,新的交互技术打破了电影屏幕次元壁垒,形成新的交互场域,使创作主体与观影主体重归对等的共生关系。二、互动电影共生关系的基本形态
数字交互技术促进了创作主体与观影主体间相互理解、相互成就,为两者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场景与模式。发生在创作者与观影者间的共生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
(一)创作者与观影者之间的共生关系
传统电影的观影带有强烈的仪式感,毫无交集的陌生人并肩坐在黑暗的影院,共同体验另一种人生。而电影的创作者,则栖息于电影的构建、消费等活动之上,通过银幕的遮蔽,产生一种神秘感。观影活动的仪式感和神秘感,造就了电影创作者的权威性。观众对电影的感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电影创作者意志的“认知呈现”。数字化及网络技术所支撑的互动电影,需要观众拿着遥控器、鼠标,去决定剧情的走向,解锁电影的结局,观影场所也不再局限于院线,这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观众对创作者的依从关系。围绕电影叙事创制的互动,互动电影又使得观众由“被动的旁观者”,摇身一变成为电影“共同的创造者”。与观众地位上升相对的是电影创作者权威性的大幅下降,电影创作者与观影者之间的界限变得相对模糊。
值得一提的是,互动电影创作方试图通过给予观众选择权,让观众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选择都是自己做出的,影片的结局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有意思的是,从第一部互动电影《自动电影:一个男人和他的房子》开始,选择权往往是观众自以为是的错觉,无论作何选择,所有的结局走向都是创作者设定的。互动电影的创作者提供了一套建筑组件,观影者则需要动脑动手,将各个模块组合起来完成个人设计蓝图。然而无论组合方式如何变化,其结果都难以超出创作者所设计的建筑框架。为满足观影主体对互动电影主导权的诉求,创作主体不断拓宽互动设计的想象力边界。国内首部探险互动剧《古董局中局之佛头起源》(袁菲,2019)同时为观众设置了十余种分支剧情及六个操作关卡。分支剧情的选择,会导致三种不同的结局。而游戏关卡的设置则推动故事的进程:操作成功,故事继续;操作失败,主角死亡,故事重新开始。在操作关卡,观众处于第一视角,能够看到自己眼前或者是探出的物体,就像自己在亲身经历一样(如图1)。观众如果连续三次操作失误,画面将会从第一视角跳转到第三视角,观众操纵的人物“许一城”就会跳出画面,面向镜头无奈调侃:“兄弟,你行不行啊?Are you OK?”(如图2)。电影主创通常是在电影以外的场所与观众交流,此举打破了观众的常识,突如其来的语言和眼神交流,让观众有一种发现隐藏彩蛋的惊奇感。这种恶搞式的镜头,颠覆了正剧的严肃性,大大增强了观影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图1.《古董局中局之佛头起源》第一视角

图2.《古董局中局之佛头起源》第三视角
(二)不同观影者之间的共生关系
电影创作者不断提升电影科技以求增加观影的现场感和互动感,却忽视了观影者与观影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构建。国内3D动画电影《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沈乐平,2014)在点映场首次启用了“弹幕”观影模式,这种互动观影新模式引发了热议。弹幕观影模式的出现,满足了“粉丝社群”分享观影体验,表达自我主张的需求,也使得观影者之间的社交活动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数字化及网络技术对人们的行为习惯、人际交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观众会因为相同的价值观或者审美取向而聚集在一起“抱团”观看,形成无形的“粉丝社群”。“弹幕社交”使观众的关注力从电影本身,转移到搜寻精彩评论,以及发表自我看法的层面上来。孤立的个体在群体性的互动中连接为思想的共同体,观影者与观影者之间形成精神层面的共生关系。
观看弹幕电影的乐趣在于个体意识的集中表达,而院线互动电影的乐趣则在于观影个体能实时感知个体选择与群体决策的差异性。2020年8月,北京电影节引进了全球首部互动院线电影《夜班》(托比亚斯·韦伯,2016),中国观众首次在电影院观看互动电影。《夜班》设定了“不可回放”的机制,任何选择都将影响电影结局且不可回头重来。剧情的选择由现场所有观众投票决定,个人没有办法主宰角色的命运。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在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下,电影剧情的走向,甚至是观影个人的选择都不再重要,人们沉浸于整体决策的强大力量带来的专横感。整场电影大概做了六十余次投票选择,在这期间看观众的反馈比电影本身还要精彩。每当全体做出心照不宣的投票时,全场的观众会爆发大笑。在《夜班》的观影过程中,多数观众的选择特点其实就是尽可能直接、刺激,还有满足自身恶趣味的自私。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似观念互相联合,形成群体性的“同感”。电影经过两轮的放映,现场观众的投票选择的结局却完全一致,使得悬疑电影竟然出现了喜剧色彩。院线互动电影不同于网络互动电影的观看形式,它大大提高了观众的参与热情,成为院线专属的群体性社交体验。

图3. B站热播互动剧

图4. B站自制互动剧《逃离10月25日》
(三)不同创作者之间的共生关系
从电影表达的主题来看,大多数互动电影都有浓厚的“宿命论”思想。《自动电影:一个男人和他的房子》的创作者设定了,无论观众怎么选择,都无法避免房屋着火;《黑镜:潘达斯奈基》(大卫·斯雷德,2018)的创作者设定了观众无论如何都难以避免悲剧的结局;互动电影游戏《隐形守护者》(帝王金,2019)的创作者设定了观众无论如何选择,注定要“为了更重要的人而选择牺牲同志或亲友”。此类互动电影的创作者似乎达成了共识:结局可以由观众掌控,但是电影的主题和基调,都取决于电影创作者意志。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的操控自由度,但是避免了电影意识的“人格分裂”。
从交互内容的角度来看,互动电影的创作者之间开启了剧情分支“军备竞赛”,不断拓展观众的自由选择空间,如《黑镜:潘达斯奈基》拥有70多个剧情选项,5种结局;《夜班》设置了180个剧情选项和7个不同的结局;《超凡双生》(大卫·凯奇,2018)更是提供了370个剧情选项,35种结局。此类互动作品在保证主线故事完整且支线剧情足够丰富的基础上,赋予观众规划剧情走向和决定人物命运的主动权,为后来的互动电影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样本。互动电影的创作者不断尝试用更多、更密集的互动节点,构建多线程的复杂性电影叙事,刺激观众的好奇心,鼓励观众自我编织情节,解锁多重结局。
创作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正来源于上述观众角色的转换。2019年7月,视频网站Bilibili(以下简称B站)热推“互动视频”功能,Up主可以自制带有选项功能的互动视频,观众可以通过B站播放器,做出不同的选择决定剧情的走向。B站将互动视频制作工具下放给用户,打造互动视频创作社区。虽然目前B站自制互动视频素材来源存在版权问题,视频内容也明显过于生硬(如图3),但是这种模式为互动剧的快速推广提供了新的思路。B站自制互动剧《逃离10月25日》(GoldenEggs,2019)(如图4),视频素材来源于游戏《我的世界》,结合电影《恐怖游轮》叙事特性改编,具有三重叙事循环和真假结局,目前为止收获840万次播放和62条万弹幕。用户对影视作品的二次创作,打破原作故事设定组成新的剧情,其身份也从观影者转化为创作者。原创者和二次创作者均从这种模式中获取新一波的流量,双方互惠互利,彼此成就。
三、互动电影主体间共生关系实现路径
(一)以感知为基础构建共生关系
感知是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反映。观影者通过对电影声音、影像的感知来了解电影的主题思想。互动电影制作与放映的变革对观众感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互动电影的创作思路来源于游戏,它与游戏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叙事性,游戏在关卡中设置过场动画,而互动电影则是在叙事中插入互动环节。电影视听语言为观影者建立起感知剧情的渠道。互动电影的多线程叙事,使得观影者感知影片内容和主旨的渠道产生了多条支流,如何在完成电影连贯的叙事线的前提下提供互动性的体验,是当下互动电影面临的重要课题。互动电影《黑镜:潘达斯奈基》的创作者为了给予观众操控人物的主宰感,全然不顾人物性格塑造的一致性和关联性,使电影主角沦为观众解锁剧情的傀儡。而观众为了通关,必须不断重复观看相同的剧情,剧情重复的次数越多,越不利于观众感知电影的思想。这个时候,观众也沦为了创作者傀儡。相较于流于表面的互动形式,观众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个连贯的故事,而不是无谓地解锁结局的数量。站在互动娱乐性的角度,《黑镜:潘达斯奈基》是一部成功的开拓性电影,但是站在观影体验的角度,却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如何平衡观众的感知体验与互动体验,《龙穴历险记》(Don Bluth
,1983)给出的答案是采用单线叙事的创作方式。当遇到危险时,玩家只有给出正确的选项或者正确的发动才能让故事继续。虽然作品的互动性被弱化,《龙穴历险记》仍收获了用户的好评,并在现代游戏主机上成功推出了续作。而今,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给出了强化观影流畅感更好的解决方法。美国互动电影《愤怒的河流》(阿门·佩里安,2018年)利用眼球追踪技术,判断出观众的目光停留在电影屏幕的区域,并反馈给控制故事线的计算机,最后投其所好给出观众期待的结局。《愤怒的河流》规避了互动电影转场生硬,叙事不连贯的弊端,观众在感知电影的同时也作出了选择,完美地平衡了电影的互动性和观影的流畅感。(二)以通感为导向构建共生关系
钱钟书曾经给通感下过定义:“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动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在电影中,通感可以理解为“主体的统觉”,主体既可能是创作者,也可能是观影者。通感是电影艺术惯用的创作手法。在传统电影中,影像是触发通感的首选,它具有实物展示的作用,通过视觉的刺激,调动出观众触觉、嗅觉、味觉等方面的联想;其次是电影音乐,它具有联觉效应,使观众形成视觉、听觉同步,展现多样的情绪氛围。而在互动电影中,交互动作是触发通感效应的首选元素。在观影过程中,观众通过点击、滑动等交互动作来改变屏幕所展示的虚拟空间中物体的性状。这种虚拟的触觉连接被反馈到观影者大脑,引发多感官联动。真人秀互动剧《你的荒野求生》(本·西姆斯,2019)中,观影者通过支配“贝尔”参与野外冒险。创作者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感觉进行联合,触控式的互动体验,连接了观众的五感,使得观众在操纵“贝尔”行动时,不自觉的联想到白蚁或者蛆虫肥腻的口感,锯齿状野草粗糙的触感,降落伞俯冲时的坠落感。实际上,这些感官暗示都来自于观影者本身的生活经验,是沉浸式体验带给观众记忆和联想,再反馈给感官。互动电影的创作者建立起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合理映射,利用感官之间的结合传达信息,带给观影者沉浸式体验。

图5.《隐形守护者》“方老师”牺牲时画面

图6.《暴雨》切指救子画面
(三)以共情为支撑构建共生关系
著名影评人罗杰·艾伯特将电影描述为,“所有艺术中最强大的共情机器。”传统电影具有“不在现场”的属性,隔着银幕,观众以旁观者的身份,窥探他人的喜怒哀乐,这种创作者强加的被动共致的剧情处理以及精致的画情,导致了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深入角色。互动电影则破开银幕的隔阂,消弭了观众与创作者的隔离状态,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代替电影角色作出种种选择,加深了观影的沉浸感,观众得以暂时脱离现实世界,在创作者设定的情境中产生情感共鸣。
互动电影中最能体现“共情”特点的设定,在于互动选项的两难性。《隐形守护者》逼迫观众主动作出“求生”或“求仁”的痛苦抉择,使观影者深深地陷入“他人因我而死的”负罪感中。当“方老师”为了保护“我”而牺牲时,电影的主创利用静态画面的优势,放大了面部表情的细节,延长了哀伤反应时间。“方老师”坚定的目光带来直击灵魂的拷问,观众的道德防线瞬间被击溃(如图5)。电影细致的剧情处理以及精致的画面,使选择带来让人信服的“共情”体验。而与《隐形的守护者》相对含蓄的情感表达不同的是,美国游戏公司Quantic Dream于2010年制作发行的互动电影游戏《暴雨》,其共情更加强调“临场感”。“伊森”救子心切被迫切掉手指的桥段,对观影者造成剧烈的情感震撼。观影者扮演着“伊森”,经历几番挣扎,终于狠心切掉自己的手指,撕心裂肺的惨叫令观影者有了强烈的真实感(如图6)。这种真实感让共情变为主动,观影者自觉融入创作者构筑的世界,体会不一样的人生。
结语
互动电影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创作者与观影者作为互动电影生态系统中的两个主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双方需要竭诚合作,在信息的交流、感官的交融、情感的共鸣中创建共生关系。促进互动电影共生关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保证创作主体和观影主体均能获得收益。对于创作主体来说,需要将观影主体的需求转化为共生合作的驱动力。融媒体时代,多样化的媒介组合形式为互动电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互动电影可以实现多领域综合互动,更好地满足观众的互动需求,并将其需求转化为购买力。在此基础上,创作主体取得良好的发展收益,观影主体也能获得更好的回报,享受更加新奇有趣的观影体验。其次要提升主体共生质量。高质量的共生关系,是主体间相互理解、相互促进的关系。互动技术较为完善的《黑镜:潘达斯奈基》,目前为止豆瓣评分仅6.8分,很多观众给出“内容无趣,形式远大于内容”的评价。该电影的某些选项设计毫无意义,为互动而互动,观众沦为选择的机器,电影自然无法得到观众的认可。优质的互动选项应当在每次选择时,促成观众对电影内容进行新的创作,使观众沉浸于故事;高明的互动操作设计,应当能与剧中人物“通感”或“共情”。观影主体对互动电影的评价与反馈,推动创作主体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互动电影主体间高质量的共生关系,对促进互动电影技术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奥]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M].张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5-155.
② Heinrich Anton de Bary,Charles C.Gillispie.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0:611-612③ [美]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69-78.
④ 潘芊芊.叙事的乌托邦——数字媒体时代互动电影的心灵治愈[J].电影新作,2020(05):145-149.
⑤ Glorianna Davenport.“Interactive Cinema”, in Marie-Laure Ryan, Lori Emerson & Benjamin Robertson.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Digital Media,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278.
⑥[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4.
⑦ 谭智秀、张艳婉.电车难题中的道德选择问题——权利与情感中潜藏的功利主义[M]宜宾学院学报,2018(08):32-38.
⑧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425.
⑨ 钱钟书.七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65.
⑩刘姝彤.电影音乐的视听联觉效应——浅析音乐在电影中的作用[J].电影新作,201(05):119-122.
⑪ 详见罗杰·艾伯特个人主页[EB/OL].https://www.rogerebert.com/roger-ebert/eberts-walk-offame-rema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