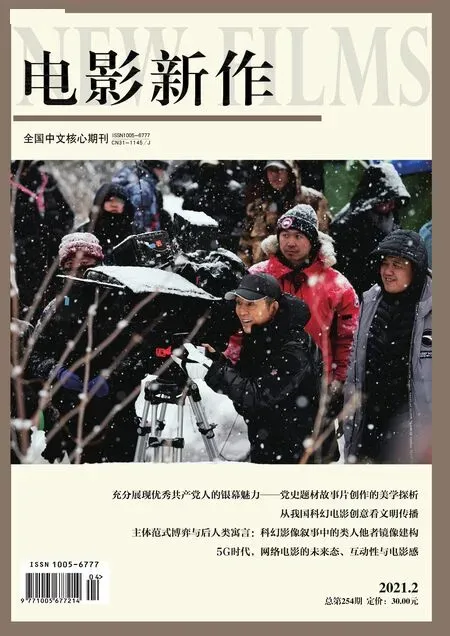“十七年”越剧电影美学初探
龚玉娇
越剧诞生于浙东乡村,成熟于三十年代的上海。借助于上海这座城市人口密集、商贸发达,文化交流密切和娱乐业发达的土壤,越剧逐渐完成了从绍兴文戏到都市越剧的转型,同时也形成了全女班表演的独特文化现象。四十年代初,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家着手进行越剧改革运动,提出“新越剧”的口号,主动向话剧、电影、昆曲、绍剧等兄弟剧种和兄弟艺术汲取养分,以精进打磨越剧之特色。从文学、音乐、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出发,对越剧进行了全方位的提高。1946年,越剧家袁雪芬领衔的雪声剧团,将鲁迅小说《祝福》改编成为越剧新戏,并于1948年拍摄完成了第一部越剧电影《祥林嫂》,这部作品也成为 “新越剧的一座里程碑”。若越剧《祥林嫂》的“触电”仅是电影对新越剧突破自我的一次重要见证,随后的“十七年”时期,越剧和电影相互交织,产生了更为密切深远的双向影响与作用。电影艺术特性和技术手段开拓了越剧人的表演方式,越剧艺术宝库也为民族电影创作增添色彩。越剧和电影仿佛是天作之合的相遇,于是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一批经典越剧电影的诞生。
“十七年”时期是戏曲电影的创作高峰期,纵观“十七年”时期戏曲电影创作,根据剧种、流派、剧目和艺术家的不同,在艺术呈现上也体现出不同的特色。而针对十七年戏曲电影的相关研究,大多以题材(传统戏、新编古装戏、现代戏)和空间(北派与南派,“北”指以崔嵬、陈怀皑为代表的北影厂系列作品,“南”指以桑弧、徐苏灵等人为代表的上影厂系列作品)两条路径入手,以剧种角度切入戏曲电影的个案研究甚少。戏曲剧种的概念于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确立,并在随后的“戏改”运动中得到发扬。而“十七年戏改”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以剧种为切入点将“戏改”政策推行到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浙沪地方大剧种的越剧积极响应,并主动与电影联姻,在自身剧目改造和戏曲电影拍摄的改编中探索“如何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戏曲”的路径,从而“实现越剧的新定位”。同时,越剧音乐、唱腔、表演风格都与京剧区别甚远。在谈到剧种与电影拍摄手法的关系时,导演崔嵬曾直言:“我以为不同的剧种,不同的内容,就必须采取不同的拍摄方式,保持并突出剧种和剧目特有的风格,才有可能创造出民族电影独有的新样式。”面对越剧电影创作,彼时多拍摄京剧电影的影人们需要打破定式,重新探索符合越剧特色的银幕表达方式。
在“十七年”上影厂拍摄的戏曲电影中,拍摄最多的剧种分别为越剧、锡剧、京剧和黄梅戏。在这一时期拍摄的百余部戏曲电影中,越剧拍摄的影片共有16部。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桑弧、黄沙导演,袁雪芬、范瑞娟主演,1953年),《情探》(黄祖模导演,傅全香、敫桂英主演,1958年),《追鱼》(应云卫导演,徐玉兰、王文娟主演,1959年),《红楼梦》(岑范导演,徐玉兰、王文娟主演,1962年),以及《碧玉簪》(吴永刚导演,金采风、陈少春主演,1962年)则是这一时期越剧电影中公认的优质作品。

图1.越剧电影《红楼梦》剧照
越剧“轻程式、重人物”的艺术风格和“柔美、秀美”的美学品格,不仅在剧种特点上规范了其细腻、典雅的气质,也允许更丰富的电影表现手段与更复杂的摄影机调度发生。同时,女子越剧演剧所包含的女性意识、文学诗意、爱情叙事与身体表演,也在影人们镜头语言的改造下,呈现出更加显著的风格特点。本文旨以“十七年”时期代表性越剧电影为例,从越剧人与电影人的合作入手,探寻女子越剧表演美学与电影媒介相遇后,如何进行改编与再创造,并力求归纳由此诞生的繁盛时期越剧电影的叙事特征、文化内涵和美学样态。
一、女性意识与民族爱情叙事
爱情故事是越剧最根本的主题。著名越剧女小生尹桂芳曾在文章中写道:“越剧吸引大众的鉴赏,儿女私情,永远地占领每部剧本的大部分。”表现爱情,也自然是越剧的剧种优势。这样的特质放到影片中本不为奇,但在十七年时期多数电影以革命情、战友情、同志情为叙事主调的情况下,越剧电影中刻画的爱情则显得格外生动有趣。《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一文如此概括中国电影对爱情主题的刻画描写:“新中国电影中的男女角色通常是战友、同志或是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共同的斗争生活中,他们建立起牢固的革命情谊。”例如,在影片《渡江侦察记》中,连长与赵四姐之间借一束山花传情达意,以含蓄遮掩的互动沟通彼此的情感。与西方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直白地拥抱和接吻定情不同,遮掩、含蓄的爱情表达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但这种总以“男女主人公告别结束”的革命爱情的归宿,并不能满足我国观众对团圆美满式爱情结局的向往。
对比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所刻画的爱情,则是一位主动、重情的大女子形象,配上一位温驯、憨厚、不善表达的书生形象。在从戏曲到电影的改编中,影片主创更加强化了梁山伯人物形象的温润、被动。导演桑弧在谈到《梁祝》电影改编时便提到,“梁祝”故事的戏曲演绎本有川剧《柳荫记》与越剧《梁祝》两个版本。越剧在“楼台会”一场,梁山伯在知晓英台已被许予马文才时曾有三番大骂“言而无信祝英台……果然负心祝英台……无情无义祝英台”的唱词。这样的唱词虽对戏剧冲突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因有损于梁山伯的忠厚、纯朴,对祝英台一往情深的舞台形象”。最终,导演桑弧决定删去这一段原剧本中梁山伯声讨祝英台的唱词。文本上改编后,经过越剧家范瑞娟的表演,梁山伯的形象则显得更加真情憨厚。
从表演上看,女子越剧中的男性形象是由女性扮演,经由女性视角过滤后的理想化男性形象。从电影文本上看,影片中梁山伯的形象,一改传统越剧文本中的色情迷信因素,建构了符合女性审美的,一位宠爱英台的大哥哥形象,是女性心中的大英雄。同时,桑弧、岑范、应云卫等影人的男性知识分子身份,也在影片创作中不自觉置入男性凝视的审美因素。一方面,电影镜头将越剧女子演剧的特色放大,尤其是在女性艺人扮演的女小生角色的刻画上,难免有不像、不适的间离之感。这种来自男性影人导演的“介入”大大“中和”了女子越剧表演中尖锐和不适的部分。另一方面,男性影人与女子越剧家的“集体创作”,不单单是戏人与影人的艺术合作。其创作背后的“十七年”政治话语作为一股隐性力量,推动完成了戏人、影人们在新中国文艺规范中的自我改造和规训。
如何在革命话语和经典戏曲文本中找到越剧电影二度创作的切入点,是“十七年”时期越剧电影创作中影人与戏人们面临的挑战。在“十七年”早期戏曲电影创作时,也有因“以戏就影”或“以影就戏”而争执不下导致合作失败的案例。反观越剧人和电影创作者们在合作时,均需或多或少地走出自己既有的安全区,以开放的姿态完成戏曲电影的集体创作。例如,由吴永刚改编、导演的越剧电影《碧玉簪》,便体现了导演吴永刚与演员金采风的密切合作。金采风的表演精髓在于“手”的表演,其手部表演特色细致入微,丰富了其塑造的大家闺秀形象的婉约和绝美。在花园对联传情一场中,当丫头们告诉他王公子特意写作对联向她表达心意,得知此情此意的她外表娇羞、内心却喜悦不已。为了表现李秀英这个人物矜持又真挚的人物性格,金采风设计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动作——“转扇”,这一神仙般的“转扇”动作动人俏皮,含羞带怯,淋漓尽致,加上表情的一颦一笑都是点睛之笔。导演吴永刚也特在此刻以中近景追上李秀英的手部表演,让艺术家的精妙演绎被影像永远记录下来。此外,越剧电影《碧玉簪》开头和结尾的新编,也让这段源自旧社会的爱情故事颇具现代意识和女性视角的巧思,体现了越剧与电影人合作的深入。全片以秀英待嫁镜中梳妆为开始,彼时镜中秀英的表情是婉约娇羞,不谙世事,在经历了冤屈、伸张、和解以后,全剧末时的最后一个镜头同样以秀英镜中帖花黄结尾,而此时的秀英表情变了,不再是成亲时唯唯诺诺的温柔气,眼神和表情中多了坚毅和刚强。紧扣主人公秀英的变化成长,以一组此时和彼时对镜贴花黄的镜中表情,展示了主人公在全剧终时巨大的改变,昭示女子自强自爱自重的意义。这组镜头不仅在当时的时代颇有创新意义,就是放在今天看,也颇有当代性。将传统故事置入当代人的看法和观点,也是优秀创作的核心,这一点是越剧电影《碧玉簪》带给我们当下戏曲电影创作者的重要启示。
不论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双双化蝶的“梦中团圆”,或是《碧玉簪》最终“送凤冠”后秀英的接纳与觉醒,都体现出“十七年”越剧电影创作者在新中国政治话语下对传统爱情题材叙事变形和改造的决心。影片努力祛除传统才子佳人戏剧叙事里宿命论、因果论等封建思想糟粕,借助家庭、亲情等日常生活环境,柔和巧妙地将“人民”话语织入民族爱情叙事,从而刻画出符合时代语境,并蕴含高度人伦道德与女性意识的新时代民族爱情故事。这也正是越剧电影《梁祝》一度创下票房奇迹,全面俘获观众的根本原因。
二、越剧电影文学性特点与表征
在“十七年”越剧电影中,《红楼梦》具有无法撼动的地位。越剧电影《红楼梦》是1962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出品,上海越剧院演出的戏曲电影作品,其舞台版、电影版均受到观众的喜爱。由徐玉兰、王文娟饰演的贾宝玉、林黛玉也成为观众心中的至尊经典角色。电影版基于1958年上演于共舞台的舞台版本,由编导演俱佳的岑范执导拍摄,朱石麟担任艺术指导。1978年至1982年间,越剧电影《红楼梦》票房达2亿人民币,观众人次超过12亿,观看人数至今难以突破。
越剧电影《红楼梦》首次开启了戏曲片作为文学电影的叙事方式和美学样态。正如西方类型电影模式无法对我国戏曲电影这一类型进行概括。在《电影的文学性与“文学电影”》一文中,作者提出同样无法用西方类型电影理论概括的中国电影形态——“文学电影”。关于“文学电影”的定义,文中将之称为“改编自或表现文学为主题,文化底蕴较高,具有浓厚历史感和民族趣味的影片”。
之所以认为越剧电影《红楼梦》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叙事特征,源于对我国新时期电影理论界有关电影“文学性”问题大讨论的回望与反思。这场在中国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讨论,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张骏祥为代表,认为“电影是另一种由电影手法表现的文学”。另一派则以张卫、钟惦棐等人为代表,反对电影依附文学或戏剧,主张“电影是一门独立艺术”的观点。而在《从误读到正解:1980年代电影“文学性”论争的再考察》一文中,作者则通过文献比较“复原”当时论证的时代语境与原文,还原了张骏祥提出“电影文学性”的立场。基于文中推论,张骏祥的观点“更多是以重回‘十七年’时期确立的文学为电影创作提供思想保障”为前提,并对80年代“过分强调电影表现形式,忽略文学性和思想性”的现象提出不满。
在谈到有经典文学做基础的电影改编创作时,张骏祥提出在影片的主题思想上要融合文学作品的核心思想和主题。并特意提到越剧电影《红楼梦》在思想内容上高度体现“文学性”的特征。他认为,由戏曲或文学改编成电影也要关注情节和思想的主线,“越剧《红楼梦》就只能搞了贾宝玉和黛玉宝钗的婚姻关系这段纠纷,别的只好割爱。”时至今日,越剧《红楼梦》的剧目排演仍以岑范导演的电影版为基准,以宝黛钗爱情为主线。这也佐证了越剧电影《红楼梦》在编创时重“文学性”特点,正是其成为后世经典的重要原因。
从戏曲电影本体来看,戏曲进入电影这一载体后,“本体被融化,艺术元素融合后产生了新的质”。而从叙事与视听策略来看,越剧电影《红楼梦》与“十七年”戏曲片主流叙事不尽相同,从思想内容、形象塑造、视听元素三方面都体现了其“文学性电影”的特征。
首先,在思想内容上,编剧徐进从小说世界庞杂的人物关系中拎出了宝黛爱情这一主线。尽管这一探索取舍的过程非常艰难,但最终仍决定“围绕着这一爱情悲剧,适当地扩大一些生活描写,歌颂他们叛逆的性格,由此揭露封建势力对新生一代的束缚和摧残”。这既是从戏剧和电影观演角度考虑,“立主脑”必不可少。同时围绕宝黛爱情开展叙事也利于越剧表演艺术之长——情感戏的呈现。
其次,在影片形象塑造上,徐玉兰与王文娟的宝黛形象深入人心。在访谈中,扮演贾宝玉的徐玉兰多次谈到熟读《红楼梦》原著对她塑造宝玉的帮助。在表演理论中,常强调人物出场是全片最重要的时刻,出场亟须在观众心中立刻立住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宝玉的出场更是让徐玉兰颇费脑筋。困难之一是其演出时年龄已至34岁,而宝玉出场时才14岁。困难之二是诸多兄弟剧种都演“红楼戏”。正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当时的观众对“红楼”故事与宝玉这一角色也颇为熟悉,若没有巧思,她演绎的宝玉也无法让人信服。最终是原著中的情节启发了徐玉兰对宝玉出场的设计,“原著中宝玉有次和王熙凤出游,庙里的师傅喊宝玉带一串檀香给老祖宗”。于是便有了影片中宝玉摇晃着香串的登场方式。可见,对文学和原著的重视,给电影版《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再次,影片视听元素的特点体现在其运镜的细腻讲究,镜头的“动”与越剧音乐的抒情节奏高度契合,也让角色情感的表达贯穿流动,体现了镜头语言的“诗性”特征。如“黛玉葬花”一场时,当黛玉唱罢专为电影版编创的唱词“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此处宝玉代替黛玉哭出声来,借此倾诉衷肠。而当黛玉于右下斜角出画后,岑范并不跳镜,而是将镜头自然推向宝玉的特写。这样的运镜方式在影片中有多次重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表意效用。又如,“黛玉焚稿”一幕,在一组空镜与黛玉“忆往昔”的唱段呼应后,黛玉到达情感的高潮。当黛玉最终叹出“洞房花烛夜,魂断天涯时”,镜头松紧合宜,既不过分宣泄代入,又不冷漠旁观,情感流淌的自然且节制,让观众充分感受到悲剧的感染力。而在“宝玉哭灵”一场,景别和画面选择也十分丰富,窗前、灵前、奉牌位,不论从何角度,镜头总能很准确地刻画捕捉人物关系。最鲜明地体现影片文学化叙事特征的段落是全片开头,即从“黛玉出场”到人物悉数登场,大全景中黛玉一行人以对角线前进,黛玉出场哀怨舒缓的音乐主题奠定了人物性格,“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心理动作以声音和影像跃然银幕之上。这些细节都体现了导演岑范如文字般书写影像的文学意识,对戏曲文本本身的深刻研读和独具匠心的导演处理。
三、基于舞台美学的银幕美学拓展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在五十年代创造出上映“31401场,22425176人次观演,平均每场人数714人”的轰动奇观。在1957年的全国优秀影片授奖大会上,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发言中总结到优秀戏曲片受到喜爱的原因是,故事上有“强烈的传奇性,歌颂了忠贞的爱情和人间的正义”,风格上“富于浪漫主义、乐观主义的色彩”,剧目选择上“选取了有丰富民族色彩和民族风格的地方优秀剧目”,表演上“演员都有长期剧目实践,能创造美好生动的艺术形象”,在拍摄上“导演有一定的创造性加工”。可以看出,编、导、演、摄、景等各艺术环节的紧密配合和从舞台到银幕的技术与艺术突破,是“十七年”戏曲电影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其一,是在戏曲与电影表演美学方面的突破。
越剧电影中的演员以诗意的身体仪式,开创了自如展露内心欲望和情感意志的越剧银幕表演。越剧塑造的花旦与小生形象,与京剧重程式的特性相比,更加自然化和生活化。而不经面具、脸谱遮挡的身体,更让演员的自然身体与面部表情直接展露予观众。在这一点上,越剧电影与其他剧种的戏曲电影相比,更易被普通的、并非有许多‘看戏’经验的电影观众所接受,有更加亲民的特性。
这种自如展露内心的银幕表演,在“十七年”电影表演风格中,显得格外耳目一新,塑造了故事片中都找不到的人物和美感。1955年1月的《戏剧报》曾刊登了一则消息,即牡丹江京剧团演员们在观看学习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后的反响情况。文中提到,“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影片之后,大家都感到:人家(越剧)的长处太多了,自己的缺点也太多了。最明显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影片的演员不受程式的束缚,从生活出发。’二是,‘影片入情入理地处理了祝公远(张桂凤饰)和祝英台的这对父女关系’。”并进一步尖锐自省,“人家演出来的父女真像父女,我们演出来的父女就像敌人。”最后总结到,“我们以往舞台上的许多人物的处理是概念化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物,而越剧《梁祝》的演员让观众看见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越剧做功细腻,表演上不受程式的束缚,善于刻画入情入理的人物关系,而越剧电影真正做到了让观众看见人物的内心。如徐玉兰在总结扮演贾宝玉的心得时言道:“越剧是很生活化的,小生分官生、锦生、穷生。贾宝玉衣食无忧,他的动作就要自在,明快,无忧无虑。”与以往剧场观演始终处于“远观”感不同,电影语言、镜头运动和景别交换让观众得以“远观”也可“近赏”,这让越剧家们的细节性创作得以最大化地展露给观众,这也是越剧与电影合作取得的开拓。

图2.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同时,越剧对“美”的追求,在越剧电影的表演呈现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例如,《红楼梦》中黛玉“葬花”一场,原本在剧场版本中王文娟有花锄、扫帚等诸多工具,而原本的舞台动作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不再行得通。“导演说我太生活化,愁眉苦脸,后来看剧照,我吓了一跳,哪里是黛玉?完全就是个园林工人。”扮演黛玉的王文娟看到原先剧场版本的身段动作在银幕上“太实”,便立即设计了一系列舞蹈动作。“虽然很美,但动作太跳也不好”,最终影片中留下的仅是黛玉扛着花锄演绎的几个清新的水袖动作。这段生动的“葬花”表演的改造,体现了尽管越剧在剧种的表演特色上已更有轻程式化、生活化的特征,更易与电影相融。但在具体的银幕呈现片段中,还应从人物和情境出发,为银幕呈现寻找最适宜的表演方式。
其二,是在布景设计上的突破。
越剧电影善于纳用越剧舞台美术的精华,并巧用过变形、挪移等手段,将之融入电影场景的设计中,产生了独特的具有舞台艺术美的越剧电影布景。拍摄于1958年的《情探》是由黄祖模导演,傅全香、敫桂英主演的一部黑白越剧电影。影片场景设计富有新意,既有舞台艺术美又有电影场景美。布景灯光向舞台设计借鉴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在造景上坚持前景原则,多在前景置放廊柱、书斋用品,增加影片纵深和层次。其次,影片善于在内景引入外景环境光,如敫桂英收到休书一场,当读毕休书内容震惊不已时,导演从近景跳入大全镜头,中景处的弦窗月影正好投到敫桂英身上,远景处一道平行的月光也投过门廊照在玄关处,这个画面巧用舞台定点光效果,让敫桂英的孤独、凄冷、悲怨的境遇由景传达。蕴含舞台艺术美的电影场景设计,巧妙表现了敫桂英的孑然与悲苦。又如,海神庙一场中,引入门口的月光与近景处的烛光对映,“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经典唱词与此番景象呼应,映照出敫桂英从此孤单一身、孤苦伶仃的绝望处境。而在外景拍摄时,则采用中国画取景章法打造自然景观,完成了“民族装饰风格”打造。如《红楼梦》黛玉潇湘管的竹林外景,便是以竹子画黛玉,竹林布局和造型空灵洗练,体现出黛玉清净孤傲的人物性格。

图3.越剧电影《追鱼》剧照
其三,是电影特效运用上的突破。
由应云卫导演,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追鱼》,讲述了家道中落的书生张珍,寄居于幼年订下婚约的牡丹家却饱受岳父数落的故事。烦闷时,对湖水中鲤鱼对话,却引鲤鱼精化做牡丹模样,与张珍相恋的故事。本片因故事中的奇观、奇幻情节,导演在实景中引入了电影特效,既增加电影语言的丰富性,也帮助了戏曲叙事向电影叙事节奏转化。此外,本片坚持“中轴美学”原则,一是体现在将人物置于居中位置,二是体现在双牡丹、双包公等重点场景中。如“双牡丹”一场便运用了对轴特效,父母抱女儿向外转的镜头接背靠内转镜头,这样的特效设计符合表演调度和剧情。而当真假包公审问真假牡丹时,对称结构的运用也突出了戏剧场景的诙谐,帮助了剧情推进。又如《情探》中王魁中状元后,紧接着敫桂英“千里魂飞”一场。判官引路让敫桂英鬼魂去到京城,让她当面与王魁对峙。此处导演黄祖模将敫桂英与判官、小鬼的跑路画面,与鸟瞰地面的空镜穿插,体现了电影蒙太奇的特性和影视语言独具性,戏剧冲突集中,丝毫不拖泥带水。遗憾的是,此时三位演员的舞蹈仍然以舞台版本示众,未能前瞻地考虑到电影特效的成果与其表演的贴合,而做出更适宜银幕呈现的调整和改变。在电影特效的衬托下,戏曲假定之特性则从优势变成了劣势,暴露出戏曲假定性与电影写实性的矛盾。
结语
越剧和电影都是年轻的艺术类型。越剧在发展成长中勇于跨界,积极探索,其剧种基因里就带有创新的使命和色彩。作为我国第二大剧种,越剧在话剧和电影等艺术的影响下,以大写意为前提,着重写实和心理表演的提高,形成了典雅、细腻的剧种气质。在越剧电影创作中,越剧虚拟性与程式性并存,富有自然之趣和生活之感,较少受到戏曲程式束缚的剧种优势,让越剧与电影的融合跨界显得更加和睦而深远。
纵观新中国“十七年”越剧电影创作,电影人与越剧人努力跳出“以影就戏”或“以戏就影”的桎梏,追求时代精神与戏曲美学神韵的共振,开拓了越剧之“真”与“美”在银幕内外的书写和表达,形成了兼具传统性和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越剧电影美学,是中国电影民族化探索之路上的重要成果。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在新时代书写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创作目标下,“十七年”越剧电影的创作经验和美学价值,值得当下戏曲电影创作者参考和重拾。
【注释】
① 田钟洛.“祥林嫂”——新越剧的里程碑[N].时事新报,1946.10.20.
② 郝宇骢、盛亦惠.戏曲的三种身体:“戏改”中的跨媒介化与再媒介化[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5):58.
③ 张艳梅.新中国“戏改”与当代越剧生态[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68.
④ 崔嵬.戏曲艺术片的探索——电影《杨门女将》导演杂谈[N].文汇报,1960.10.
⑤ 龚艳.承续与蜕变——“十七年”上海戏曲电影掠影[J].上海艺术评论,2020(10):23-24.
⑥ 根据《中国戏曲电影史》(高小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 与《十七年越剧电影与沪港两地电影交流》(许元,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文中统计数据,重新整理而来。十六部越剧影片分别为《越剧精华》(1949)、《相思树》(1950)、《石榴红》(1950)、《梁山伯与祝英台》(1953)、《情探》(1958)、《追鱼》(1959)、《斗诗亭》(1960)、《云中落绣鞋》(1961)、《西厢记》(1961)、《柳毅传书》(1962)、《红楼梦》(1962)、《碧玉簪》(1962)、《三看御妹刘金定》(1962)、《毛子佩闯宫》(1963)、《金枝玉叶》(1964)、《烽火姻缘》(1965)。
⑦ 姜进.诗与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30;原引自尹桂芳[N].芳华剧刊,1947.
⑧ 黄会林、王宜文.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J].当代电影,1999(5):68.
⑨ 陈荒煤.于在京编剧座谈会上的发言[A].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C].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363.
⑩同8.
⑪桑弧.桑弧导演文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22.
⑫万伯翱.周恩来总理与戏剧轶事二则[N].新民晚报,2014.10.12(B7).
⑬钟菁、黎风.电影的文学性与“文学电影”[J].当代文坛,201:97-98.
⑭同13.
⑮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根据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片第二次导演总结学习会上的发言整理)[J].电影通讯,1980.
⑯张卫.“电影的文学价值”——与张骏祥同志商榷[A].电影的文学性讨论论文选[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71.
⑰齐伟.从误读到正解:1980年代电影“文学性”论争的再考察[J].东南学术,2015(2):218.
⑱同15.
⑲王忠全.“电影作为文学”异议[A].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C].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164.
⑳信芳.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越剧红楼梦搬上银幕的前前后后[J].上海采风,2008(7):29.
㉑同20,36.
㉒摘录自部分国产影片的几个统计数字[J].中国电影,1956.
㉓沈雁冰.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电影[J].中国电影,1957.
㉔ 丁卒.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给我们的启发[N].戏剧报,1955.1.16.
㉕董煜.人生如玉戏如兰 徐玉兰传[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2013:13.
㉖同20,33.
㉗同26.
㉘韩尚义.戏曲影片的布景形式[N].中国电影,1956.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