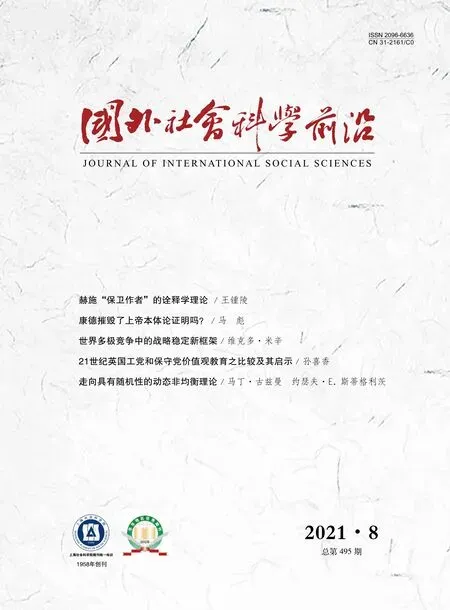康德摧毁了上帝本体论证明吗?*
马 彪
通常来说,人们大多认定是康德摧毁了传统神学中的上帝或上帝存在的证明。例如,杨一之先生在《康德摧毁了上帝本体论的证明》一文中就直言不讳地认为,康德的功绩在于他破除了由圣·安瑟伦(Saint Anselm)以来“绵亘七百年的上帝本体论证明”。1杨一之:《康德摧毁了上帝本体论的证明》,《学习与思考》1983 年第6 期。与此相应,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亦曾指出:“康德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现在再也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报了。”1[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116 页。不过,与杨一之先生看法略有不同的是,海涅虽然断言康德攻击了上帝存在的三种主要证明方式,即本体论的、宇宙论的与自然神学的证明,但是他认为,康德“只能打倒后两种,不能打倒最初的一种”。2[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112 ~113 页。而我们都知道,在康德哲学中,后两种证明显然是以第一种为基础的,因此当海涅说康德没有打倒本体论证明,这也即是说,康德并没有摧毁关于上帝存在的任何证明。可见,虽说同是面对康德上帝本体论证明批判这一事实,中外学者的认知还是有所差别的,而这种差别在某种层面上无疑彰显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就本文主旨而言,笔者试图结合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联系近年来康德的研究,评议一下康德对上帝本体论证明所作的批判,看看其中有哪些症结值得我们注意。鉴于此,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由外部比对安瑟伦和康德关于上帝本体论证明之议题的不同之处,重点辨析安瑟伦对上帝的证明与康德批驳上帝存在所用论证工具的根本差别;其次,从康德哲学体系内部刻画康德对上帝本体论证明所作批判的疑难问题,着重阐述“一百个塔勒”和“两种谓词”之论据本身所引发的争议;最后,立足于21 世纪康德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考察“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生发出来的思想碰撞,以及由此碰撞而引起的有关康德哲学的深层思考;文末,归纳和总结了上述论题之彼此勾连、紧密相扣的关系。
一
如所周知,“上帝的本体论证明”这一名号始自康德,在此之前,虽有类似证明但显然没有如此地称谓,例如安瑟论就曾把这一类对上帝的论证称之为meum argumentum,而非本体论证明。3Jean-Luc Marion, Is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Ontological? The Argument According to Anselm and Its 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Kant,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30, no. 2, 1992, pp. 201-218.那么,何为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呢?康德认为,凡是抽调一切经验并“完全先天地从单纯概念中推出一个最高原因的存有(gänzlich a priori aus bossen Begriffen auf das Dasein einer höchsten Ursache)”的证明就叫上帝的本体论证明。4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56, s. 566.与其他的上帝证明不同,康德所认定的上帝本体论证明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特征:其一,对上帝是否存在的证明与经验没有任何关系;其二,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只能出自单纯的概念。
后世不少学者认为,安瑟伦在《宣讲》(Proslogion)中对上帝的论证是完全契合康德关于本体论证明的界定,原因在于安瑟伦相信,人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命题,即上帝是“无法设想有比之更大的存在者”(aliquid quo nihil maius cogitari possit),上帝是人们(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怀疑论者)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存在;由于存在又可以分为观念的存在与现实的存在,因此若是上帝只存在于观念(in intellectu)中,则不符合最大存在的要求,只有上帝同时也存在于现实(in re)中,它才是最大的,所以上帝必然是现实的存在,毕竟一个人若是有了大的上帝观念而又否认其现实的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诚然,安瑟伦在该命题中所表述的“更大”不是在时空或现象中的“更大”,而是“更完满、更完美”的意思。对此,约翰·希克在《宗教哲学》中早已指出过:“十分明显,安瑟伦所说的‘更大’,意思是更完善,而不是指在空间上更巨大。”1[英] 约翰·希克:《宗教哲学》,何光沪译,高师宁校,三联书店,1988 年,第37 页。就安瑟伦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来看,他无疑是从“完满的”上帝概念出发以导出上帝的存在,貌似完全符合康德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界定。2笛卡尔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亦有类似之处,他断言:“即单从我存在和我心里有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也就是说上帝)的观念这个事实,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参见[法] 勒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52 页。然而,深究之,当不难发现两者还是存在着根本地差别的。的确,安瑟伦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与经验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完全符合康德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第一个界定。不过,对于第二点,即由单纯概念推导出上帝来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概念,双方的认知则有较大出入。
与康德眼中的那种推理概念即理性不同,安瑟伦所说的概念为“信仰的理性”(ratio fidei),它与信仰密切相关。从信仰与理解的关系来看,安瑟伦主张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而不是理解之后再去信仰。他曾明确指出:“我不是寻求理解以便我信仰,相反,我是相信以便我理解,因为我深信:除非我信仰了,否则,我无法理解(Neque enim quaero intelligere ut credam,sed credo ut intelligere. Nam et hoc credo: quia nisi credidero, non intelligere)。”3[意] 安瑟伦:《信仰寻求理解》,溥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204 页。之所以如此,与他证明上帝存在的目的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安瑟伦证明上帝存在的目的旨在帮助信徒们理解他们信仰的对象,并不是让那些无神论者因其论证而成为基督徒。对于这一点,他也并不讳言,在《宣言》的“序言”中他把自己的写作意图交代的甚为清楚:“我写下了下面这部小作品,试着让一个人振奋他的心灵去静观上帝,让他寻求理解他所信仰的。”4[意] 安瑟伦:《信仰寻求理解》,溥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98 页。由于在安瑟伦的时代,信徒对自己所信仰的上帝虽然深信不疑,但是对这位无处不在的主还是充满着困惑的。比如,他们尚未亲眼目睹过上帝的“亲临”,也不知道如何“寻觅”他的存有;他们渴慕上帝的圣容,却并知道他的所在等等。正是为了解答圣徒们类似的问题,安瑟伦才写下了《独白》(Monologion)与《宣讲》(Proslogion)等解疑答惑的著述。5就安瑟伦的论著而言,Proslogion 倾向于为信徒而作,而Monologion 虽其名义上是为基督徒而写就的,但他宣称,任何粗具理性的读者——无论是否认可《圣经》——都会欣然接受他所给出的哲学论证。同时,安瑟伦也承认,前者比后者写的更简洁,论辩也更为统一。诚然,在后来的作品中,安瑟伦也毫不讳言,他之所以写作Monologion 与Proslogion,目的还是在于单是依凭理性来说服那些从不信靠《圣经》的人信仰上帝与道成肉身(Incarnation)。
那么,安瑟伦何以非要选择由信仰到理解,而不是相反的路数呢?按照让·卢克·马里奥(Jean-Luc Marion)的说法:“理解之所以由信仰开启,是因为理性只有在信仰中才能识别思维的不变的和根本的条件,正是基于此,理解不仅需要信仰,并且由此才能详细地说明信仰,进而确信:理性必须先信仰才能实现理解。”6Jean-Luc Marion, Is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Ontological? The Argument According to Anselm and Its 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Kant,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30, no. 2, 1992, p. 207.对安瑟伦而言,理解的根本前提不是我们的理性,而是信仰,相对于人的理性而言,信仰更为基础,因而也尤为重要,它是理解得以展开的基础。1安瑟伦(1033—1109)的这一观点与数百年之后的笛卡尔(1596—1650)的主张大致是一致的。在笛卡尔看来,上帝“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这是每个人都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白”的观念。既然这个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白”的观念告诉我们“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即“上帝是我的存在的作者”,那么我们人所具备的认知工具即理性自然也是源于上帝的。参见[法] 勒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45 ~50 页;也可以参见:Lawrence Pasternack, Predication and Morality in Kant’s Critique of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Kant Yearbook, vol. 10, no. 1, 2018, p. 164。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安瑟伦认为,存在一种“信仰的理性”,它包括“信仰的理性基础”(the rational basis of faith)与“信仰的逻辑”(the logic of faith)两个层面。前者“指向外部的面向,它为某个具有辩护或规劝目标的学理提供论证支持”。2Sandra Visser and Thomas Williams, Ansl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14.而后者涉及内部的方面,它指的是“信仰学理中的一致性,并在逻辑上把一切要点归并为一”。3Sandra Visser and Thomas Williams, Ansl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4.在安瑟伦看来,基督教恰好具备上述特点,其教义无论是外在的“信仰的理性基础”方面,还是内在的“信仰的逻辑”方面,都是个完整的合理体系。作为信仰的基督教教义之所以是符合理性的,是因为它的学理所关涉的就是终极理性,即把至上智慧贯穿于万事万物之中(包括人在内)的上帝,正是“对这位终极智慧,并将其至高理性贯穿于万有之中的上帝的信仰,才使得人成为理性的”。4Sandra Visser and Thomas Williams, Ansl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7.换句话说,安瑟伦眼中的上帝就是终极理性或终极智慧的化身,而人之所以有理解能力就在于他对终极理性即上帝的信仰。
在某种层面上,由于安瑟伦所说的“信仰的理性”关涉的是服从某种至上意志的精神,因此我们要想理解世间万物,那么我们的心灵一定要谦卑,要像晚辈听从长辈的教诲一样去顺从上帝的指示。正如安瑟伦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首先应该成为孩子、顺服上帝,并接纳上帝给所予的智慧……因为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以顺服的态度从《圣经》中汲取的营养愈多,我们对事情的理解也就愈精准。”5Thomas Williams (ed.), Saint Anselm, Basic Writing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 216.问题是,何以从《圣经》中吸收的越多,我们的理解就越好呢?对于这一点,安瑟伦断言:“没有信仰的人就没有经历(experior),而没有经历就绝不可能认知。就像经历某件事优位于听说某件事一样,一个经历过某件事的人,其知识肯定比那些仅仅听说那件事的人要多。”6Thomas Williams (ed.), Saint Anselm, Basic Writing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p. 216-217.此处,暂且撇开安瑟伦论证信仰与理解关系的神学外衣与宗教色彩不说,仅就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而言,安瑟伦主张信仰无疑是先于认知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信仰与认知之间隔着经历(experior)这一层关系,而且还在于信仰可以通过三条路径保证理性认知少走弯路,即谦卑(humility)、顺服(obedience)与精神规训(spiritural discipline)。安瑟伦认为:“就谦卑而言,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心灵的卑微和神圣真理的崇高,这一认识有助于防范我们的推理,并使我们由顽固且盲目的自我辩护中抽身而出;于顺服方面,一旦我们接纳了《圣经》及其教义,它就能为我们的运思指示明确的方向,使理性免于混乱的摸索;最后,借由精神规训,我们可以清除心灵中物质层面的东西,辨明哪些应该是理性自身能够思考的,哪些不是。”1Sandra Visser and Thomas Williams, Ansl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0-21.总之,正是由于信仰有着理性所没有的这些优点,所以信仰必然要先于理解,没有信仰,我们虽有些事情可以得到说明,但有些事情则根本无法理解。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安瑟伦眼中“信仰的理性”的内容及其可能的条件,与康德用以批驳上帝存在与否的理性概念是有差异的。与安瑟伦的信仰高于理性的看法相左,对康德而言,理性是人所独具的推理能力,它是我们运思的根基,也是我们最高和终极的认知源泉。与作为规则能力的知性不同,理性是种原则(Prinzipien)能力,其目的在于为知性有条件的知识提供无条件的基础。美国知名康德专家亨利·阿里森(Henry Allison)曾经指出:“正如知性的功能在于通过把那些在感性直观中所与的原始材料带向统觉的客观统一性中,使它们统一起来一样,理性的功能是通过把知性的那些分离的产物(判断)带入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系统),使它们统一起来。因此,理性的工作位于知识事业的顶峰,如果我们达到了这个顶峰,那么理性所追求的这种统一就完成了整个知识体系”,2Henry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09.也就是说,理性是确保一切认知(Erkenntnisse)的终极要件与最终根源。那么,作为原则能力的理性何以具有如此高的功能,其权柄从何而来呢?康德认为这是个超验的问题,它越出了我们的认知能力之外,我们对此无法给出回答。换句话说,这个原则“与逻辑公理不同,它包含着一个形而上学的预设(assumption),即对每个有条件者之完备集合条件的现实性预设,而此集合本身必须被视为无条件的,因为按照假设(ex hypothesi),不可能有什么更进一步的东西作为它的条件了”。3Henry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12.至此,康德的立场十分明显,作为无条件的理性是理解任何别的东西的基础,世间万有之存在的最后根据不在神灵的庇佑,而只在于它们是否能够经得住理性的批判(分析、考察),任何脱离理性批判的事物都没有合法性的基础,因而都是可以质疑的。康德曾自道曰:“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4[德]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3 页。
就我们的论旨而言,如若康德所批判的“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就是指“完全先天地从单纯概念”(gänzlich a priori aus bossen Begriffen)中推导出上帝存在的证明,而这个可以纳入广义“理性”(Vernunft)5关于理性与知性的区分,杨祖陶与邓晓芒认为:“广义的理性,它泛指以先天原理为依据的一般认识能力,因而是指一切认识能力(感性、知性、狭义的理性)的先天原理的根源……理性一词有时被用来泛指包括知性和狭义的理性在内的思维的自发性能力,有时又被当作知性的同义词使用。”参见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30 页。中的所谓“概念”之所指不过是理性存在者的一种认知能力,那么康德就没有真正驳倒安瑟伦对上帝的本体论证明。虽说在本体论证明界定的第一个方面,即与经验了无关涉方面,安瑟伦与康德有相似的认识,然而在第二个方面,即对单纯概念方面,两者的理解有着根本不同。毕竟,在安瑟伦看来,他对上帝之存在的论证仰赖的是“信仰的理性”,而非康德哲学意涵上、理性存在者(人)所独具的原则能力的理性,两者的论证手段或工具的差别之大,是不能以道里计的。更何况,就康德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批判本身而言,其所运用的例证或理据也存在着极大的疑点,争议很大。
二
前面我们是从论证上帝存在与否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进路,即由证明所使用的工具方面来质疑康德的,如果据此而仓促地断言康德没有驳倒传统的本体论证明未免太过武断,也难逃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毕竟,由《圣经》到人以证明上帝存在与从人到《圣经》以驳斥上帝存在之间,两者本来没有什么可比性。现在,我们就从康德哲学体系的外围切入其学理内部,看一看康德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批驳在其学理内部中有哪些问题值得考虑。
我们知道,康德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上帝的存有之本体论证明的不可能性”这一节中。康德指出:“‘是’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即不是有关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种东西的一个概念。它只不过是对一物或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用在逻辑上,它只是一个判断的系词。‘上帝是全能的’这个命题包含有两个概念,它们拥有自己的对象‘上帝’和‘全能’;小词‘是’并非又是一个另外的谓词,而只是把谓词设定在与主词的关系中的东西。现在,如果我把主词(上帝)和它的一切谓词(其中也包含‘全能的’)总结起来说:‘上帝存在’或者‘有一个上帝’,那么我对于上帝的概念并没有设定什么新的谓词,而只是把主词本身连同它的一切谓词、也就是把对象设定在与我的概念的关系中。概念和对象两者所包含的必然完全相等,因此不可能因为我将概念的对象思考为绝对被给予的(通过‘它存在’这种表达方式),而有更多的东西添加到这个仅仅表达可能性的概念上去。所以,现实的东西所包含的决不会比单纯可能的东西更多。一百个现实的塔勒所包含的丝毫也不比一百个可能的塔勒更多。”1[德]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476 页。康德的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值得我们在此详加征引,其核心要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存在”与“上帝”没有必然的关联;二是“存在”是个“逻辑的谓词”,而非“实在的谓词”。2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逻辑的谓词”与“实在的谓词”之区分的探讨成果亦颇丰硕,仅在2020 年就出现了5 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如舒远招、韩广平:《论康德Sein 论题中的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从二项解读模式到三项解读模式》,《哲学动态》2020 年第9 期;李伟:《康德“存在不是实在谓词”论题诠证》,《哲学动态》2020 年第9 期;李科政:《拨开“存在”谓词的迷雾:康德存在论题的第三种诠释》,《哲学动态》2020 年第9 期;彭志君:《被遮蔽的逻辑谓词——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现代哲学》2020 年第9 期;以及,舒远招:《实在谓词一定是综合命题的谓词吗?——就Sein 论题中的实在谓词的理解与胡好商榷》,《现代哲学》2020 年第7 期。康德认为,传统本体论证明中所津津乐道的“上帝存在”或者“有一个上帝”的命题,进而由上帝的概念推导出上帝的存在,就在于他们误将“存在”这一本为“逻辑的谓词”视作了“实在的谓词”,继而把上帝的可能性存在误解为了实在性的存在。
对于康德的第一个论点,我们先看看来自神学思想家的回应。美国神学家埃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认为,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驳未得其要。他指出:“本体论证明的主要特征是上帝的‘存在’是必然的,康德显然认为‘非存在’的命题也是必然成立的,其理由是,我们否定‘存在’并不会造成矛盾。”1Alvin Plantinga, God Freedom and Evil, William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p. 92-93.对此,普兰丁格举例说,康德对“上帝存在”的反驳,和“单身汉是男的、25 岁以上的、未婚的人”类似,而这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因为这两个命题有本质的差异。普兰丁格指出,谓词“男的、25 岁以上的、未婚的人”对于主词“单身汉”而言是偶然的,而“上帝”与“存在”的关系与此全然不同。我们在思维“上帝”与思维“单身汉”时,是在做着绝然不同的两件事。通常来说,我们都会把“男的、25 岁以上的、未婚的人”等等特征附属于“单身汉”之下,但也可以去掉某些属性,如“25 岁以上”等特征,但当我们思维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时,绝对不能不包含“存在”,就是说,“存在”与上帝之间有着必然地关联。
表面上看,普兰丁格的反驳深具浓厚的宗教背景,貌似一位神学家对一位哲学家的批判。其实,此乃不必要的误解,因为普兰丁格的批驳完全是依照康德论证理路进行的,它是对康德理性概念和经验概念的正确运用。与此相对,康德本人以“一百个塔勒”为例来反驳上帝存在的论证却有欠妥当。我们知道,就康德的哲学体系而言,“上帝”概念与“一百个塔勒”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范畴。对康德而言,广义的理性认知及其对象可分为三个层面:感性认知,涉及直观的知识;知性范畴,关涉以概念整理感性经验材料,以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最后理性理念,指涉上帝、灵魂不朽,以及自由意志等侠义的理性知识。就康德对认知领域的划分来看,“一百个塔勒”(或单身汉)与“上帝”决然不在一个认知领域,因为在康德看来,上帝不是我们直观的“经验对象”,也不是我们的知性范畴所把握的“概念客体”,它是“理性的理念”。相对而言,“一百个塔勒”(或单身汉)只是个“经验概念”,它们与作为“理想(Ideal)”的上帝不在同一个认知层阶。因此,当康德拿“一百个现实的塔勒所包含的丝毫也不比一百个可能的塔勒更多”等经验概念来说明“上帝”这一理性的理念对象时,他无疑犯了一个概念误用的过错,毕竟“一百个塔勒”(或单身汉)与“上帝”的实际差距是不能以道里计的。康德曾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指出,上帝“与自然的人的距离……无限大,以至那个神性的人对于自然的人来说,再也不能被当作榜样”。2[德] 伊曼努尔·康德:《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338 页。作为自然的人与上帝都没有可比性,何况“一百个塔勒”这一经验概念呢?正是基于这一点,普兰丁格指出,假如本体论证明“仅仅是把‘存在’这一偶然的属性附加在上帝的概念之上,那么其论证当然理应受到康德的批判,但是它不是”。3Alvin Plantinga, God Freedom and Evil, William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98.“上帝存在”和“单身汉是男的、25 岁以上的、未婚的人”绝然不同的两个命题,分属截然不同的两个论域,上帝就是“上帝”,上帝不是没有结婚的“单身汉”。
在阐述了康德批判“上帝存在”这一议题上对概念(经验概念和理性理念)的淆乱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康德最为核心、也最具争议的一对范畴:“逻辑的谓词”与“实在的谓词”。4英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最新关注,可以参见:Lawrence Pasternack, Predication and Morality in Kant’s Critique of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Kant Yearbook, vol. 10, no. 1, 2018, pp. 149-170。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康德的论点。对康德而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东西用作逻辑的谓词,甚至主词也可以被自己所谓述,因为逻辑抽掉了一切内容”1[德]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475 页。不会对主词增添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所以根本不会影响人们对主词的理解。相反,“实在的谓词”则完全不同,它在对主词加以规定时增加了内容,为主词赋予了其本身所没有的新信息。当我们说“上帝存在”或者“有一个上帝”时,这里面的“ist”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而只是个“逻辑”的谓词,传统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之所以由“上帝的概念”推导出“上帝的实存”,就在于他们把两类在质上完全迥异的谓词混为了一谈,此其一。
其二,就存在作为“实在的谓词”来说,在“上帝存在”这一命题中,主词与谓词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上帝”与“存在”之间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不会有别的可能了。“分析判断”也叫“说明性的判断”,“综合判断”也叫“扩展性的判断”。前一类判断指的是“通过谓词并未给主词概念增加任何东西,而只是通过分析把主词概念分解为它的分概念,这些分概念在主词中已经(虽然是模糊的)被想到过了”。2[德]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8 页。因此,如果你所主张的“上帝存在”是个分析判断,那么你通过“存在”没有为“上帝”增添任何东西,因为此时你心中的观念要么是“该物本身,要么你就预设了一个存有是属于可能性的,然后就以这个借口从内部的可能性中推出这一存有,而这无非是一种可怜同义反复”。3[德]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475 页。反之,如果“上帝存在”是个综合判断,那么谓词“存在”就不是绝对的与主词“上帝”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上帝不存在”也是有可能的,毕竟谓词并未如分析判断那样内在的属于主词之中,所以上帝不存在是有其可行性的。康德自信地断言,只要人们“发现了混淆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即一物的规定性)的这种幻觉”,4[德]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475 页。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摧毁借由“存在”来证明上帝实存的一切“挖空心思的论证”。诚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思维一物,不管我通过什么谓词和通过多少谓词(哪怕在完全的规定中)来思维它,那么就凭我再加上‘该物存在’,也并未对该物有丝毫的增加。因为否则的话,所实存的就并不恰好是该物,而是比我在概念中所想到的更多的东西了,而我也不能说实存着的正好是我的概念的对象了。”5[德]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477 页。
针对康德以“存在”是个“逻辑的谓词”而非“实在的谓词”来否定上帝存在的这一主张,艾伦·伍德(Allen Wood)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当康德断言,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否则它就增添了主词中所没有的东西,这时他的意思无非是说当我们假设一个具有除了“存在”实体之外的“几乎完满的存在者”(almost perfect being)时,如果“存在”被我们纳入到了“几乎完满的存在者”之中,那么它就不再是“几乎完满的存在者”,而是个“彻底完满的存在者”(wholly perfect being),6Allen Wood, Kant’s Rational The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08.而这与我们所思考的那个“几乎完满的存在者”的假设是相矛盾的,因而是荒谬的。对此,伍德认为,如果“存在”不能充当“实在的谓词”,那么其他的语词也无法充当“实在的谓词”。他举例说:“这次我们假定‘万能’(或者其他无可争议的实在的谓词)是‘几乎完满的存在者’所缺失的实体。在此情况下,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果‘几乎完满的存在者’是万能的,它就拥有了这个缺失的实体,并由此变成了‘彻底完满的存在者’了,而这依然与我们原初的假设,即‘几乎完满的存在者’这一前提矛盾。因此,如果康德的论证成功地表明了存在不是个实在的谓词,那么它也将成功的表明没有什么会是实在的谓词。”1Allen Wood, Kant’s Rational The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08-109.如此一来,康德所作的关于“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之区分就失去了应有价值,成为语词之争的游戏。退一步来说,即使“实在的谓词”是有意义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主词,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主词就不再是原来的同一个东西了吗?例如,如果我说某物是红的或全能的,那么我是把这个谓词加在该物的概念上了,但它依然是同一个东西,虽然我以前思考它时没有想到那个性质。然而,如果这对明显实在的谓词——例如,‘红’、‘全能’——是成立的,那么它对‘存在’为什么就不能成立呢?2Henry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15.
因此,正如伍德所总结的那样,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康德对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的区分,以及基于这一区分所作的论证,都不足以表明‘存在’不是一个实在、完满性或者真正的谓词。的确,康德试图在“存在”与“谓词”之间给予更为精细的界分,如果“他是正确的话,他就能够一劳永逸地去除逻辑上必然存在的概念,并且去除本体论证明,但是他没有提供充足的理由,让我们认定他的观点就是正确的”。3Allen Wood, Kant’s Rational The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09-110.
三
不可否认,伍德对康德的质疑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的,这一点可以从21 世纪以来关于此一问题所一再生发出的众多文献中窥出端倪。4例如,William Forgie 就认为,当哲学家们在对“存在是不是个谓词”并进行争论时,他们忽略了“存在”所拥有的多重涵义:一、对象所具有的一阶(first-level)内涵,如马、石头、你我等;二、概念所具有的二阶(second-level)内涵,即可以例示化的(instantiate)概念的属性。康德哲学中的“存在”指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可见William Forgie,How Is the Question ‘Is Existence a Predicate?’ Relevant to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Philosophical Religion, vol. 64, 2008,pp. 117-133。比如,庞思奋(Stephen Palmquist)教授就认为,伍德对康德解读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看到视角原则(the principle of perspective)在康德哲学论证中的重要作用”。5Stephen Palmquist, Kant’s Critical Religi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 420.而错失这一点将很难在整体把握康德哲学的品格,因为本质上来说,康德的整个立论或论证方式都源于这些原则在其思想中的应用,也正是这些原则统一构成了其颇具“建筑术”特色的哲学体系。
庞思奋指出,康德关于传统上帝证明的批判是基于“最实在的存在”这一阐述之上的,其实,这一点伍德也并不是没有看出来了,1可以参见[美]艾伦·伍德:《康德的理性神学》,邱文元译,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112 ~116 页。但是伍德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将此与后面的本体论、宇宙论,以及自然神学证明勾连起来加以系统考察:从某种层面上,可以说康德关于“最实在的存在”的论证已为破除传统的上帝证明做好了准备,其后的三种神学批判皆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具体推进。基于康德哲学,由于对任何一个对象的把握必须在对其通盘的(durchgängig)规定中来加以说明,而所谓通盘的规定,就是指为了完全认识某一物,我们必须认识一切可能的东西,并由此而不论是肯定性地还是否定性地对它加以规定。就此而言,一切事物的谓词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规定,这个基底就是关于一切实在性的大全的理念(omnitudo realitatis)或一切可能概念的总和(Inbegriffaller möglichen Prädicate),而所有的否定只是对该大全的限制而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最实在的存在”概念并非就是经验的实在性,因为现实事物对原始存在者,即最高实在性的限制并不是现实的分割,而只是将它作为逻辑上的必要前提。换句话说,作为理性的思维之物,我们不能由“最实在的存在”这一概念推导出其经验实在的存在,而一旦我们混淆上述区别,把最实在的存在这个理念实体化,同时将该概念的原始存在者视为绝对唯一的、单纯的、甚至看作完满的与永恒的话,就会形成传统宗教中的上帝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有关于上帝的证明方式,即本体论、宇宙论和自然神学的证明方式。
在庞思奋看来,康德对上述三种上帝证明方式的批判,正是基于“最实在的存在”这一概念之上的分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对传统上帝证明采取的批判视角并不相同:对应于本体论证明的是逻辑的视角(logical perspective),对应于宇宙论证明的是先验的视角(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而对应于自然神学证明的是经验的视角(empirical perspective)。2Stephen Palmquist, Kant’s Critical Religi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 420.由于康德在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运用的是逻辑的视角,因此这里的“是”或“存在”只能用于分析判断,它仅具有逻辑功能,只能充当“逻辑的谓词”,永远不能充当“实在的谓词”,也不能要求它对现实本身有所传达。3Stephen Palmquist, Kant’s Critical Religi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 424.因为“逻辑的视角”本身的应有之义就在于它抽离了一切其他的内容,单是对知识给予先天的分析。4Stephen Palmquist, Kant’s System of Perspective: An Architecton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pp. 138-139.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或者说当康德的视角原则被充分解释之后,我们再断言一个逻辑上的存在可以作为一个实在的谓词,这无异于把逻辑的视角与先验的视角混为一谈。5Stephen Palmquist, Kant’s Critical Religi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 430.
毋庸置疑,庞思奋教授对伍德教授的批驳较有力度,也较为中肯,但也并不因此就是没有问题的。为了澄清这一点,我们还须对分析判断、逻辑的谓词,以及实在的谓词之间的复杂关系给予进一步的考察,在这方面,劳伦斯·帕斯特纳克(Lawrence Pasternack)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我们不应忽视的重要理论资源。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康德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充当逻辑的谓词,因为“逻辑抽掉了一切内容”,它与主词关联,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命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逻辑的谓词反映的是一个完整命题中两个必要元素的句法区别。在这里,内容之所以被抽离,并不是因为充当逻辑的谓词的概念没有内容,而是因为它体现只是这一概念的句法功能(syntactic function)而已。与此相对,实在的谓词反映的一个命题的语义功能(semantic function),涉及的是一个完整命题中概念的含义和关系。由于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两者并不相互排斥。1Lawrence Pasternack, Predication and Morality in Kant’s Critique of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Kant Yearbook, vol.10, no. 1, 2018, p. 150.比如,在“拉布拉多猎犬是友好的”(Labrador Retrievers are friendly)这一命题,其中“友好的”一身兼二职,它既是一个逻辑的谓词,也是一个实在的谓词。说它是逻辑的谓词,不为别的,乃是因它在这一命题中构成要素来说的,即它仅凭借其句法功能而是一个逻辑的谓词;说它是实在的谓词,是因为它涉及了句法之外的语义内容。正是基于这一分梳,帕斯特奈克指出,实在的谓词一定是逻辑的谓词,而逻辑的谓词未必就一定是实在的谓词;逻辑的谓词在某些情况下是实在的谓词,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未必。据此,若是人们得出,康德之所以批判上帝本体论证明,是因为他认定存在是一个逻辑的谓词,由此而必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存在诚然是一个逻辑的谓词,但它是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仍然是有待确定的。2Lawrence Pasternack, Predication and Morality in Kant’s Critique of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Kant Yearbook, vol.10, no. 1, 2018, p. 151.举例来说,在“三角形有三个角”这一命题中,这里的谓词虽然不是实在的谓词,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仍然具有内容,这一内容体现在它作为逻辑的谓词之句法作用上。另一方面,逻辑的谓词在语义功能上有没有内容,以及有哪些内容主要取决于它对主词特征(Merkmale)的选择上。
那么,什么是特征呢?在由其学生Jäshce 整理编辑、康德审定出版的《逻辑学》(Logik)3注:Jäshce Logik 在中文里被译为《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2010 年。一书中,康德指出,人的认知都是经由表象而发生的,表象构成了人们认知的基础,由于认知都是由作为表象之特征构成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特征来认识事物或理解概念,而所谓特征指的就是“事物中构成该事物认知部分的那种东西,或者说——这是一回事——表象,只要这种表象被视为全部表象认知的基础。因此,我们的一切概念都是些特征,而一切思维无非是由特征而来表象的”。4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X, Berlin: Walter de Grunter & Co, 1924, s. 58;也可参见[德] 伊曼努尔·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57 页。其中,笔者对中文译文略有改动,由于习而不察的原因,大多中译本没有对Erkenntnis(认知)和Wissen(知识)给予区分,两者其实并不完全一致。由于概念都是些特征,所以对概念的把握无非就是对其特征的理解。在对特征作出如此刻画以后,康德又对概念(主词或谓词)具有的各种特征给予了详细的分类,它们包括分析的和综合的特征、同位的和隶属的特征、肯定的和否定的特征、重要而富有成果的和空洞而不重要的特征,以及充分必然的和不充分的偶然的特征,等等。5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X, Berlin: Walter de Grunter & Co, 1924, ss. 59-60.
对康德而言,当我们反思概念的语义内容时,我们其实是在考察构成概念的那些特征,概念之间的比对说到底就是特征之间的比对,对同一概念的分析就是构成同一概念之特征的分析。在此意义上,我们作出的分析判断,也只不过是对包含在主词这一概念中的特征进行选择,换句话说,逻辑的谓词之所指,也不过是在主词这一概念中识别一个或多个特征,从而呈现主词的不同面向。就此而言,下面的这两个命题即“所有单身汉都没有结婚的人”和“所有单身汉都是男人”,虽然同为分析判断,但句中作为逻辑的谓词的“没有结婚的人”和“男人”则拥有完全不同的语义内容,因为在这里,谓词对主词之特征的指涉,并不完全一致,其语义内容取决于它们和主词之间的关系。同样的道理,同一个特征既可以用来指涉实在的谓词,也可以用来指涉逻辑的谓词,在“所有单身汉都是没有结婚的男人”这一命题中,“没有结婚的人”就是逻辑的谓词,因为它关涉的是主词中充分必然的特征;与此不同,在“所有80 后都是没结婚的男人”这一命题中,“没有结婚的男人”则显然是一个实在的谓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庞思奋教授和康德一样在论证实在的谓词、逻辑的谓词,以及分析判断之间没有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他对康德辩护是有待商榷的。正如帕斯特纳克所指出的那样,要想理解康德的两类谓词,我们不仅要结合他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来把握,还要结合它们的句法和语义功能来查勘。因为在康德那里,同一个特征是否是逻辑的和实在的,以及是否是说明性的和扩展性的,完全取决于它与主词之间的复杂关联。例如,同一个特征在此一命题或场合中有可能是“同位的”“重要而富有成果的”,以及“充分必然的”特征,而在另一命题或场合中则极有可能是“隶属的”“空洞而不重要的”,以及“不充分的偶然的”特征。在此意义上,康德面临的挑战是,即使存在某一种情况下不是实在的谓词,但他也不能由此得出存在于所有情况下都不是实在的谓词这一结论。再者,与逻辑的和实在的谓词之截然二分相反,非实在的谓词并不是毫无价值的,它在语义方面也不是空无一物的。最后,一旦认识到逻辑的和实在的谓词之区分并不是详尽无遗的,那么“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可能就不再对本体论证明具有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把存在作为上帝这一概念之内部特征的证明版本,更是如此。1Lawrence Pasternack, Predication and Morality in Kant’s Critique of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Kant Yearbook, vol.10, no. 1, 2018, p. 153.
四
综括前文,之所以试图揭示康德在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存在着种种值得商讨的疑难,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轻率地断言,康德的批判是彻底错的,传统的上帝本体论证明是完全对的这么简单,我们也无心在众多证实或证伪上帝存在的证明中加一无足轻重的论述。不过,针对那种动辄“康德摧毁了传统上帝本体论证明”的论调,我们只想指出,当我们评议康德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批判时,不仅要从外部区分证明上帝进路的差异,还要从康德哲学体系内部解读其错综复杂的理论预设。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与康德的批判进路不同,安瑟伦虽说是从理性出发来论证上帝及其属性的,但是他所使用的说理工具“信仰的理性”与康德动用的作为原则能力的“理性”还是有不少距离的。当然,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作为教徒的安瑟伦证明上帝存在的运思模式是由上帝到人的过程,而康德则是从人走向上帝的过程。如若我们的这一断言是成立的,那么康德对传统上帝存在证明的批驳应该打些折扣,毕竟两者的介入与论说手段没有太多的交集。就康德哲学体系内部的运思而言,他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批判是否就取得了如他所认为的那种效果呢?这也是见仁见智的。比如,深谙神学思想的埃尔文·普兰丁格就认为,康德混淆了理性理念和经验概念之间的区别。我们诚然不能错以为在“经验概念”的账户上增添“一百个塔勒”就真的增加了实际的经济收入,但康德以此为例反驳“上帝存在”这一命题确实有欠公允,因为它们在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范畴。毫无疑问,对康德最有力的反驳来自艾伦·伍德和劳伦斯·帕斯特纳克。伍德主张,若是“存在”不是“实在谓词”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有实在谓词,试图破解康德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核心观点,即存在是逻辑的谓词,而不是实在的谓词。针对伍德的反驳,庞思奋则认为他没有充分理解康德在批判上帝本体论证明时所使用的视角原则,因而其驳斥是不充分。然而,在帕斯特纳克看来,即便康德采用的是逻辑的视角原则,但只要其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的区分还没有穷尽谓词的所有可能性,那么“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这一说法就不再具有本体论证明的核心意义,而康德对此所作的批判也将不再具有终极价值。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康德仅仅以“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这一论据来试图破除上帝本体论证明的做法还是值得商榷的,而那些试图维护康德这一思想的学人,要想为康德的这一立场给予辩护,他们面临的困难亦不可谓不多。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