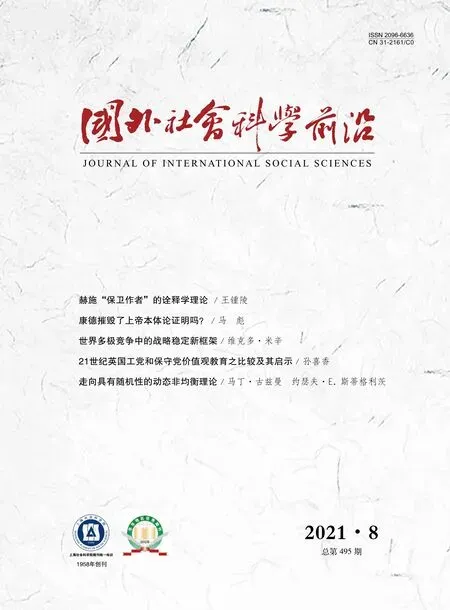赫施“保卫作者”的诠释学理论
王锺陵
一
在第二版序言中,伽达默尔说他的《真理与方法》一书,“赢得了读者,同时也找到了它的批评者”,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第2 版序言》,《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1 页。该书正文页码与序言分开排列,在序言中,第3 版序言又复单立,第2 版序言与导言的页码连排。——作者注在第三版序言中,他又说到该书引起了争论的事。在其晚年的《自述》中,伽达默尔说:“我写这本书几乎用了10 年时间”,“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真理与方法》这个书名还是在该书印刷的时候想出来的——我自已都不清楚这本书是否出得太晚了,真正过时了。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新的一代理论工作者,他们有的对技术充满了期待,有的则受到意识形态批判的影响,这是可以料到的。”2[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自述(截止于1975 年)》,《真理与方法·附录》(下卷),洪汉鼎译,第800 页。[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洪汉鼎主编的《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与其所译《真理与方法》,人名用字前者为“伽达默尔”,后者为“加达默尔”。——作者注由于伽达默尔的诠释理论自身存在的缺点,也由于学术环境的变化,该书1960 年出版,1962 年就遭到贝蒂的批评,1965 年被赫施重炮抨击,而哈贝马斯所发表的尖锐的批评意见,则激起了他与伽达默尔的引人注目的辩论。当然也有起而为之辩护的,如霍埃。从诠释学的角度最值得注意的是,赫施在对伽达默尔的诠释理论的批判中,鲜明地打出“保卫作者”的旗帜。赫施1965 年刊出《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的长文,在消除作者、视域融合及前判断等问题上,对伽达默尔的理论予以了尖锐的批评,1967 年又出版了《解释的有效性》一书,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一个与伽达默尔迥乎相异的诠释理论。他的理论尚不为我国学界所关注,因此,有值得加以介绍与评论的必要。
二
“保卫作者”,是《解释的有效性》的第一章章名。这个标题,并非仅针对伽达默尔,而是针对“前此四十年中”中对于“一件本文(Text)的意义应是该本文作者意欲表达的意义”的“激烈而富有成效的攻击”。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9 页。“文学研究家们在此往往提出这样的论据:作者无关紧要的思想对文学批评和广泛的文献学考察是极其有益的,因为,这种思想把人们的注意中心由作者转移到了他的作品上。由这样的思想出发,当代文学批评家为了寻找本文独立自足的含义,而不是作者生平先期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就怀着忠实于作品的原则,小心谨慎地去考察作者的本文,只有很少一些研究者反对这种把重点转向释义的努力。”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0~11 页。与此同时,“晚期浪漫派的那种从作者的习俗、情感和经历出发去解释作品状况的方法,遭到了有力的抨击。”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1 页。我们可以看出,赫施所说的文学研究家、批评家们,是新批评派。所谓“作者无关紧要的思想”,是说的新批评派所认为的在理解作品上,对有关作者传记及某篇作品写作意图之类知识的了解是无关紧要的。
赫施说,这种理论“是那种怀疑一切客观地正确解释之可能的怀疑主义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1 页。也就是说,消除作者的倾向是对正确释义之可能的怀疑得以产生的一个根源。它的演化过程如下:“正是作者作为本文含义的决定性要素被彻底否定之后,人们才渐渐觉察到了,没有任何一个评判解释之正确性的合适原则存在。随着这个意识发展的内在必然,‘一件本文表明了什么’的问题就演变成了一件本文对某个批评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样,人们就时兴去谈论一个批评家‘理解本文’的活动。阅读活动这个词现在开始在许多著作的标题中得到了体现,这个词还蕴含了这样的意味,即作者被消除了,而读者却被保存了下来。”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1~12 页。“这样一来,读者就取代了原来的作者。”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4 页。赫施这段话中含有一个前提,即评判解释之正确性的合适原则是作者赋予作品的含义。这显然是狭隘的。然而,他对于从重视本文到“阅读活动”一词的时兴,以至读者代替了作者的说明,正是不期然地说出了西方文论的一脉发展。
在赫施看来,读者取代了作者,就会产生理论混乱:“在原先只存在一个作者的地方,现在就出现了许多作者,而且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一样具有同等的权威性。”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4 页。这样,赫施的结论是:“一个理论家如果要拯救正确性的原则,那么,他也就同样必须拯救作者。”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4 页。
赫施拯救作者的方法是区分本文的含义、意味与意义,并对或出于心理学的、或出于历史主义的许多意见给予驳斥。
“本文含义就是作者意指含义”,“作者意指的含义不仅是确定的,而且是可复制的。”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5、37 页。这是赫施的中心论点。为此,他驳斥了诸如“对作者来说,本文含义是处于变化中的”,“重要的并不是作者要表达什么,而是本文陈述了什么”,“‘作者意指的含义’是无法揭示的”,“作者本人并不清楚,他要表达怎样的含义”7[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4、19、23、29 页。这四项说法。
对第一项意见,他说:“象所有其他人一样,在时间行程中作者的态度、感情、观点和价值标准都会发生变化,因此,他经常是在一个新的视野中去看待其作品的。”所以,“对作者来说发生变化的并不是作品的含义,而是作者对作品含义的关系。因此,意义总是包含着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个固定的、不会发生变化的极点就是本文含义。”8[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7 页。这里说到了含义与意义的区分。从赫施所说“即使作者改变了他对语词所表达之含义的评价,但他还是没有做到改变原来的含义”9[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7 页。一语中,可以看出,此处之“意义”表示评价之意。
对第二项意见,赫施一句话就予以了否定:“对意图和意图实际实现之间的区分,对确定语词含义来说不具有任何意义。”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1 页。
第三项意见稍微复杂些:“由于我们所有人与作者都不是全然相同的”,“我们也就无法复制作者意指的含义”。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3 页。“即便是作者本人也无法复述他原初的意向,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唤回他原初对含义的体验。”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6 页。这是两条心理学的理由:一条是说读者无法达到作者的心理,一条是说作者也无法回到原初的体验。
归纳起来,赫施对第一点的驳斥举了四条理由:一、“如果解释者坚信他已完成了解释,那么,含义也就成了能为某个广泛的公众圈所达到的东西。”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4 页。这是说解释者解释的并非是纯属作者个人的含义。二、赫施认为:“这个观点把含义与精神活动的过程混在了一起。”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42 页。这是说读者领会的是本文的含义,不必阑入其心理过程。三、赫施说:“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点上能够始终产生同样的精神活动,就象完全不同的精神活动能够达到共同的含义一样。”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43 页。这是反对只强调作者与读者及不同时段的作者本人的心理差异的偏向。四、“现象学最严格地对精神对象和精神活动作了区分”,正如“无数各不相同的意向性行为能够求得同样的意向性客体”一样,“无数各不相同的意向性行为都能达到同样的词义。”7[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49 页。这是对上一条理由作了现象学的理论论证。
我们还记得,施莱尔马赫曾说:“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而进入作者的意识。”8[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1805—1810)》,《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 年,第23 页。这一要求因被论者们攻击为不可能,现在已为赫施放弃了。赫施对施莱尔马赫相当尊崇,赞扬说:“他就解释所说的一系列格言,对解释学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9[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04 页。但仍然放弃了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认识话语如何是精神的事实(灵魂的产物)”的“主观的历史的重构”10洪汉鼎主编:《诠释学讲演·1819 年讲演纲要》,《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 年,第61 页。这一任务。
赫施对第二点的驳斥,举了两条理由: 一、“每个作者都知道,他用语言所制作的表达形式只能表达由语词构成的含义”。“我在创作中所想到的所有东西,并不是都能通过我的用词而传达给他人的。同样,可共有的含义中,有许多在当时的想法中根本不存在,这里就涉及了所谓无意识含义。”1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7 页。这是说,回到那未曾被表达出来的原初的体验,对于解释来说,是没有必要的,需要的是理解由语词构成的含义。二、赫施说,“极端历史主义”主张“只有我们自身的文化给定性才拥有对我们来说‘真正的’直接性,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不能‘真正地’理解过去之本文的原因所在,‘真正的’理解只适用于同时代的本文,对过去的每一个理解都具有‘抽象’和‘构想’的特点。殊不知,对文化给定性的每一种理解,不管这文化给定性属于过去还是现在,实际上都摆脱不了‘构想’的特点”。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54~55 页。这是以“构想”的普遍性来反对历史主义,然而,赫施这里便暴露出一个漏洞,他忽视了构想的难易程度,毕竟在对文化给定性的构想中,现在易于历史,现在有许多直接的感受与见闻可以依凭。
对理解的历史性的强调,是自狄尔泰、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观点,赫施与这一观点明显对立。与心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两面作战,是坚持解释客观性的赫施在诠释理论中自我设立的新座标。
赫施对含义所作的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这一区分,直接形成了赫施对第四项意见的回答:“要表达人们不想表达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而要表达人们并未意识到要表达的东西便是很有可能的。”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1 页。
由于“本文的含义正是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保卫作者》,《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3 页。,因此,赫施致力于对词义作出界定:“词义不仅是一位作者用他的语言符号表达的意欲类型,而且也是他人能凭借这种符号去理解的东西。”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61 页。赫施并说:“强调‘类型’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类型’这个概念才可能把词义视为受到确定的意识对象,而这个意识对象同时是大于意识内容的。”“类型就是一个具有界限的整体。”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61 页。什么是“意欲类型”?赫施曾举过一个例子:“再没有什么会象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那样使我喜爱了”这句话,“实际是指,再没有什么艺术品会象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那样使我喜爱了”,而“洗海水浴”就“不属于我用‘使我喜爱的东西’所指的事物”。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60 页。显然,“意欲类型”即所欲表达的类型,在这个例子中,就是艺术品,它大于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能由一个以上的事物去再现”,7[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61 页。但它仍然有一个界限。这样,词义就既是确定的,又是读者“可分有的”8[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62 页。了。
词义的确定性,表达有意识的含义;那么,无意识的含义呢?赫施说:“一位作者所表达出的含义几乎总比他意识到的含义来得多,因为他不可能顾及到其含义的所有方面。”9[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59 页。这种“未被察觉的含义”10[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60 页。也构成含义整体的一部分。对此,赫施使用了一个概念:“迹象性含义”1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75 页。。赫施说:“一个语言迹象”,“是某个他物的非任意的标记。”1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64 页。他举例说:“这种词义就象一座海上冰山,它的绝大部分是隐藏在海水之中的,但它必定有一些部分是露出水面可目遇的。”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65 页。露出水面可目遇的,是有意识的含义;隐藏在海水之中的,是未被察觉的含义。赫施将“迹象性含义”归入意义:“迹象性的非自愿含义就是本文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68 页。这一归类与他的整个理论是矛盾的、不恰当的。按他的理论,应归入意味。
赫施自己说得很明白:“意味始终是被隐匿着的”,“存在于含义整体中而且被界定含义的界限包围着”,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75~76 页。“我把这些潜在含义或特征称为‘意味’。”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范型概念》,《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83 页。而“意义永远是含义与某事物的关系”。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74 页。“迹象性含义”作为一种“隐含义”“‘未表达’含义”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73 页。就只能是意味,而不是意义。
这样,本文就有含义、意味及意义这样三种涵义了,而意味仍是含义之一种。因此,就大类说来,词义表达的是含义,读者对含义的不同领悟是意义。
据此,赫施对心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解释论,再次加以了驳斥:“在持怀疑论态度的解释者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心理主义往往来源于对词义和意义的混淆”。“解释者的反应,也就是他赋予词义的或多或少地具有个人特质的意义。”7[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49~50 页。“每个极端历史主义的信条是:每个时代对过去本文的看法都是各有所异的,而且没有一个时代会象它所说的那样真正地理解了过去的本文,因为,‘重新作出的解释’就象一个‘新的见解’一样,是与原来的东西不同的。谁这样认为,谁也就把对一件本文的……领会的状况与阐述的状况混淆了起来。”8[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53~54 页。领会的是含义,阐述的是意义。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感到,赫施对于含义与意义的区划过于截然。一个词往往多义,这些词义有时还有其相应的色彩,某一义项及其色彩,会开启对某一种意义的悟解,亦即它与某一种意义是密切联系着的,如何能够截然划开呢?
三
赫施说:“理解、解释和批评在实践中是多么紧密地联在一起的,而在理论上又多么需要把这三者区分开来。”9[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60 页。上一节说到,赫施将本文的涵义区别为含义、意味及意义三种,他也将理解活动区分为三种:理解、解释和批评,但并不与涵义的三种类型相对应。
赫施说:“把词义限定在作者所指的内容上,并把理解界定为对这种词义的揭示。”10[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61 页。所谓“把词义限定在作者所指的内容上”,是指作者有意识表达的含义。对有意识的含义的揭示,构成理解。赫施所说“理解就是对含义”的“揭示”,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57 页。就是这个意思。与此相对:“解释就是对含义的一种阐述。”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57 页。赫施说,解释“几乎总是被与批评混淆在一起”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57 页。。其实,不仅如此,解释也会与理解相混淆。赫施说:“‘理解’这个概念……不仅仅意味着对作者意指含义的把握,而且也意味着,对含义是如何与作者的世界或我们自身的世界相吻合的这个事实的把握。”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64 页。含义与作者或我们世界的吻合问题,难道不是解释?赫施说:“把意义界定为所揭示的词义与某些其它事物之间的某种随意的关系”,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57、161 页。这就是解释。
含义限定于词语中,意义则是含义与其它事物的关系,而“指向意义、论及意义、描述意义”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65 页。,则是批评。这似乎是三个递次扩大的概念。赫施举例说:“例如,在传记中,解释就是与对某人生活的理解相应的,即他的生活如何,经历如何,而批评则是与把他的生活放入到某个更广泛的有关系中去看相关的。”7[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63页。译文不通顺,然原文如此。——作者注在这个例子中,赫施既将理解与解释相混了:“解释就是与对某人生活的理解相应的”;又将解释与批评相混了:“他的生活如何,经历如何”与“把他的生活放入到某个更广泛的有关系中去看”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后一相混的情况还更多一些。赫施说:“批评所努力的就是,描述本文和广泛的与之相联的现实及价值的关系。”8[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66 页。这一说法,就似乎将解释也包括在批评之中了。赫施自己的话可以为证:“批评比单纯的解释更有价值,尤其是当批评包含着解释之时,那就更是如此。”9[美]埃瑞克· 唐纳德· 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66 页。这样一种混淆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是必然的:“在英语地区,人们把有关本文的所有论说都视为‘批评’。”10[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65 页。
由上所述,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含义与理解相对应,解释、批评则与意义相对应。前者为领会,后者为阐述。与含义、意味、意义可以合并为含义与意义一样,理解、解释、批评也可以合并为理解与解释。将解释一词换成阐述、批评、论说都可以。
赫施对理解与解释之间关系,作了三点说明:一、“对意义的说明是以先对含义的揭示为前提条件的,而对含义的揭示并不以某种关联,也就是说,并不以某种意义为前提条件。”1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63 页。这说得有些绝对,一般说来,先要理解本文的含义为何,才能对之作出意义的解释;然而,也时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有知道了本文的“某种关联”,本文的某种含义才能被揭示出来,或被揭示得更深入。二、“每一个听众群都需要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方法,一切解释都具有历史性”,“但是,这一点绝不意味着,本文的含义也因时代而发生变化。”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58 页。这是讲的解释的可变性与含义的不变性,这是赫施所坚持的核心观点。三、“在某种程度上,一个解释有时会深化我们的理解,但是,一个解释有时又会根本地改变我们的理解。”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51 页。这是说解释对于理解有或深化或改变的两种功能。这一点显然与第二点有矛盾,如果含义不随时代变化,而解释则是有历史性的,那么解释如何能够导致理解的改变呢?只有承认了上文所说,有时我们只有知道了本文的“某种关联”,其某种含义才能被揭示出来,或被揭示得更深入,所谓解释导致理解的深化与改变的情况才能发生。证之以赫施所说“一切理解必然地而且在根本上是隶属于本文实质的,而一切解释则必然地是易逝的和历史的”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59 页。话,赫施的上述矛盾就更清楚了:易逝的和历史的解释,如何能够改变隶属于本文实质的理解?之所以产生这一矛盾,同赫施对解释的轻视有关。他心中念兹在兹的是,强调本文作者意指的含义的确定性。
其实,解释也并不都是易逝的。我在拙著《文学史新方法论》中曾举过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例子:“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大力推赞东方虬的《咏孤桐篇》,其曰:‘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然而,《咏孤桐篇》却佚失了,而陈子昂藉之倡导汉魏风骨的这篇《序》却成为历久弥新的名文。文本和读解来了个转换,陈子昂的读解流传而为文本,而原有的文本却只留下了陈子昂的读解。”4王锺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215 页;文史哲出版社,2003 年,第210 页。换用赫施的概念,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对东方虬的《咏孤桐篇》的解释,更准确地用他的概念说是批评。它并不易逝,而是长久地保存了下来。缺乏文学史实际研究的纯理论探索之易于出错误,由此可见。
对于理解活动,赫施还阐述了“范型”概念。这个概念源自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在历史上第一个指出了范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这是对解释学的一个重大贡献。”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04 页。范型概念,“是一种内在的解释本文的方法。”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05 页。赫施对这个概念涵义的说明比较多样,不太确定。
他说:“对‘雨点’没有理解的人,也无法理解‘这个特殊的雨点’,如果我们抛弃了对‘雨点’的范型构想,这也就必然意味着,我们同样抛弃了‘这个特殊的雨点’。”7[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范型概念》,《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94~95 页。这里的范型指的是类。句中所谓“范型构想”指的是对概念的概括。用到本文的理解上,赫施说:“如果解释者没有预先推定语词所从属的表达类型或语句系列,他何以能理解他正在感受的那个语词的作用呢?”8[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范型概念》,《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96 页。所谓“预先推定”,也是“范型构想”,不过不是对概念的概括,而是对表达类型或语句系列的判断。语词的作用要放在类型与系列中理解,仍然是在类中理解个别。
赫施又说:“一个解释者几乎总是入手于某个类型构想,这个类型构想要比表述的真正方案来得含糊和宽泛,而且他在紧接着的解释过程中只会去限制和更准确地构造这个类型构想。”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范型概念》,《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02~103 页。这段话中所说的“类型构想”,是对于所要解释的本文的一个模糊的总的猜想,因而才会在紧接着的解释过程中被限制和更准确地构造。对上述理解,赫施的这样一句话可以为证:“一个不真实的范型就是一个错误的推测,而一个真正的范型就是一个正确的推测。”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范型概念》,《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03 页。推测即猜想。
赫施赋予“范型”的第三种涵义是文体:“同样的词语,当它作为诗和作为散文印出来时,其效果是不一样的。当然,散文和诗是极其宽泛的范型构想。”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范型概念》,《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10 页。
“范型”涵义的多样,使得赫施作出了一个抽象的界定:“我已把真正范型界定为一个构成并决定含义的被传达的类型。”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范型概念》,《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20 页。简言之,就是用类型来界定范型。
这种宽泛的“范型”概念导致了赫施对文体本质的否定:“什么是诗之为诗的独特本质,人们却很少达到统一的认识,而且,这种状况还会延续下去”。“我的论点,诗不具有特定的本质,而只具有某个含糊的真正范型。”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72 页。“象‘文学’和‘诗’……除了具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变动不居的种类系统外,不具有任何确定的本质。”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73 页。这种文体观显然是错误的,它表明缺乏文学史实际研究的纯理论探索对于实际论题之无能。
赫施的解释理论,还有一项内容:对理解有效性的验证。《解释的有效性》一书的最后一章即第五章就是阐述此项内容的。赫施这本书后有三篇附录,其一题为《客观的解释》(1962),此文中对于验证问题有一个简洁的说明。他列出了四条标准:第一条是合法性标准:“解释必须得到本文于其中被把握的公共语言规范的认可。”7[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72 页。第二条是相应性标准:“解释必须阐明本文的每一个语言成分。”8[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72 页。第三条是范型合适性标准:“如果一件本文是按科学论文的方式写成的,那么,于其中揭示出某种影射含义就是不合适的。”9[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72 页。第四条是连贯性标准:这条标准是核心。赫施说,前面三个标准,“使得人们能对某个难解的本文在根本上意味什么,作出多种解释。假如解释者于此要作出选择,那么,他就会选择最符合连贯性标准的解释。”10[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72~273 页。
赫施又说:“验证的过程虽然是相当复杂和艰难的,但是,验证的最终原则却是很简单的,即想象性地去重建陈述主体。”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79~280 页。陈述主体“是指整个作者主体性中的某个特定的、专门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陈述主体就是指作者的那些规定词义的部分”。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80 页。用《解释的有效性》第五章末尾的话说:“解释尽管具有实践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但是,解释的基本问题却是一致的——推测作者原意是什么。”“有关解释之学科的目的就在于,不断提高我们所作推测正确的或然性。”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有效性验定及其原则》,《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35 页。这样,从结构上说,整本书的论述,就完成了第一章所提出的保卫作者的任务。
四
关于赫施的解释理论,我们还应说到他对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批评。在《解释的有效性》的附录中,第二篇即为《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此文对伽达默尔的理论的一些主要论点作了批驳。
赫施说,伽达默尔理论的独特之处,并不在解释者的历史性这个主要命题,而在于他“对这个老命题启用了一些新概念,并且赋予了旧名词以新的含义,例如,在伽达默尔那里,‘前判断’就不是一个需要否定的词,而是一个需要认可的词。解释不需要解释者对其个人视界采取中立态度,解释而是一种‘视界融合’,解释的历史是一种‘效果历史’”。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83~284 页。他的新解释学“呈现出与‘新批评派’以及更新的‘原型批评’的相似之处,这三者都对作者决定本文含义的特权提出了怀疑,但是,伽达默尔是部分地把他的反意向论观点建立在审美沉思基础上(这一点与新批评派相似),而根本没有建立在集体无意识基础上(这一点与原型批评不同),但是,伽达默尔主要是把他的反意向论观点建立在马丁·海德格尔的极端历史主义基础上的”。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85 页。上引这两段话,前者说明了伽达默尔理论的特点,后者说明了伽达默尔理论与其它两个西方文论流派的异同。
在《解释的有效性》第四章中,赫施对伽达默尔的理论有一个概括的说明:“伽达默尔对正确性问题并不怎么感兴趣,他所探讨的是另一个问题,即理解的历史性如何影响了解释的实现。”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76 页。这一说明对于《真理与方法》的第二部分所体现的总的理论立场的概括,是正确的。
在《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一文中,赫施对伽达默尔理论的第一项批评,便是关于解释的正确性问题。
赫施说:“当伽达默尔去否定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潜在地把精神活动与含义混为一体时,他的阐述似乎也潜在地包含着这一看法:本文含义无论如何都能独立于某个个人的意识而存在。”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87 页。这是说伽达默尔在反对诠释的心理学倾向时,也使本文含义独立了。赫施又说:“伽达默尔在书面语言的实质中发现了这种含义独立性的依据”。“本文独立于某个具体的人的意识,也就达到了语言本身的自主存在。”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87 页。从赫施接着所引述的海德格尔的话来看,赫施这是指的伽达默尔追随海德格尔“语言说”的思想,而将语言视为一种自主的存在。
赫施设问道:依照伽达默尔,理解是一个再创造活动,领会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的观点,本文含义乃是一个无穷的可能含义的系列,这个无穷系列就需要无数的解释者去解释。解释者的分歧如何解决呢?赫施代为回答说:“对伽达默尔来说,传统这个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概念暗示了这样一个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人们就能去调解处于相同时代的读者之间所发生的意见分歧。哪位读者依循着传统,他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哪位读者离开了传统,他也就失去了合理性。”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89 页。赫施又对这一回答批评说:“传统概念严格地是作为对本文解释的历史而运用到某个本文上去的,每个新的解释都鉴于其单纯的前在而从属于这个传统并改变着这个传统,因此,传统不能被作为固定的、规范的概念去看待”,从而,“伽达默尔引进传统这个概念仍然是徒劳的。”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0 页。
继之,针对伽达默尔所说阅读中的理解并不是对一些以往事物的复现,而是对某个现时含义的参与的观点,赫施评论说:“复现其实不是复现”,那么,“我们提出这个简单的问题:一个正确的解释存在于何处?”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2 页。
以上共三层意思:含义的非个人化;传统并非是个固定的、规范的概念,因此无法解释不同理解间的分歧;复现其实不是复现,那么正确的解释存在于何处?这是赫施在理解的正确性问题上对伽达默尔的批评。
赫施对伽达默尔理论的第二项驳斥,指向其“视域融合”论。赫施说:“只要某个解释者不管怎样尚未把握本文原初的观点,尚未与自身的观点相结合时,他何以能去融合两种观点——其自身的观点和本文的观点——呢?如果有待融合的要素尚未具体化,也就是说,如果本文的原初含义尚未被理解之时,这样一种融合何以会发生呢?”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4 页。赫施又说:“如果解释者真正地固守其自身的历史性,那么,他就不会离开其自身的历史性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处于过去和现在相交融的中间地带”。“如果人们承认,解释能获得来自于某种融合的观点”,“那么,人们在原则上也就承认了,解释者能离开其自身的观点。假如这一点能成立的话,那么,伽达默尔的理论基石也就瓦解了。”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4 页。赫施以上的反驳,虽然有简单化的不足,但还是击中了要害。
视域融合是以理解的历史性为前提的。针对“过去对现在来说,在本体上是疏异的,过去含义的存在无法演变成现在含义的存在,因为,存在是有时间性的,而且,时间的差异也就是存在的差异”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6 页。这一理由,赫施反驳说:“如果这一点就是伽达默尔有关历史性学说所立足的依据,那么,伽达默尔就应承认:这一点不仅仅否认不同时代间的融通,而且也根本地否认文字上的交往。”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6 页。赫施所叙述的理解的历史性的那条理由有些含糊,何谓含义的存在?过去时代作者意指的含义难道不在伽达默尔所爱说的那个流传到现在的“流传物”中存在?本文中的有意识与无意识两种含义,是含义的过去的存在,还是含义的现在的存在?“演变”是什么意思?如果所谓“无法演变”,是指读者无法理解在流传物中的上述两种含义,那么赫施的这一诘问才是正确的。
赫施又说:“如果时间不是区分时代的最重要标准,那么,由不同时代的人无法彼此理解这个论断就可推出结论:生活于根本地不同境遇中和拥有不同人生观的人同样也无法彼此理解。”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7 页。赫施是用这个推论来反驳伽达默尔的,然而它恰恰是正确的。人群与人群,甚至人与人之间是隔膜的。但赫施所说“由于人一般是各有所异的,因而,人也就无法理解他的同类所表达的含义。‘同在’和‘传统’这种拯救性的概念只是莫须有的幻想”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8 页。的话,则又走向了极端。
在《客观的解释》一文中,赫施也有一套“视界”理论,将它与伽达默尔的“视域”理论相比较,对于辨清他们理论上的差异是必要的。赫施是这样来解释“视界”的:“照胡塞尔看来,那些未意识之含义就是以‘视界’的方式存在于眼前的。”“人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类型期待和或然性系统”,“它是对整体的一种不明确的构想。”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54 页。这是说视界是未意识的含义与范型构想,这样两层意思为伽达默尔的“视域”概念所没有。
我们还记得,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是这样说明的:“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东西,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去观看。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391 页。伽达默尔的“视域”概念有区域或曰范围的意思。赫施的“视界”概念虽然也有区域、范围的意思,却加了限制:“这种视界规定了作为整体的作者意向”,“视界概念的意义在于,它原则上规定了适用于本文所表达含义的规范和界限。”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54 页、256 页。赫施的“视界”概念一和作者意向相关,二和本文相关。然而,伽达默尔的“视域”概念本质上“属于处境概念”3[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391 页。,因此他说:“在历史理解的范围内我们也喜欢讲到视域”,4[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391 页。“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5[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393 页。而赫施则说:“解释者的目的就在于假设性地去竖起作者的视界并谨慎地去涤除自身的、随机的联想。”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54 页。“解释者通过把本文归类于某个特定的范型,他也就自然地确定了一个宽泛的含义视界。范型代表着对整体、对类型化含义成分的一种构想”。“这个范型化的归类只提供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它只是对某个特定含义视界的大致构想,解释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准确地去界定这种视界。”7[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55 页。不过,赫施自己并没有能够将他与伽达默尔的上述不同讲清楚。
在赫施的解释理论中,也有两种视界:“对本文含义作出界定和说明的视界就是本文的‘内在视界’,它是超时间的而且是与自我同一的,每一个含义除了具有这种内在视界”,“还具有一种‘外在视界’”,“每个含义都是与另一些其它含义发生关联的”,“这个外在视界是批评的领地,它不仅仅未得到限定而且也是发展变化的。”8[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57 页。简洁地说,内在视界是本文的含义,外在视界是与其它含义发生关联的批评,但两者之间没有也不能融合。
赫施的这一套视界理论本也自成一说,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在《解释的有效性》的第四章却写下了这样一个注:“含义本身是取决于当时的看法的,而且,解释者如果要在其所处时代去理解某个时代的词义,他就必须依循某种双重透视,他既要保持其自身的立场,同时又要设想陈述者的立场,这就是所有俗定传达的一个特征。”9[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57页注1。在这句驳斥他所谓“极端历史学”10[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57页注1。的话中,已然有对理解的历史性的承认,所谓“双重透视”,其实就是两种视域。虽然赫施强调了陈述者即作者的立场,虽然他没有说到双重透视的叠合或交融,但仍然背离了他的上述“视界”理论,而向着他所批判的伽达默尔的意见大大地走近了。
在《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一文中,赫施对伽达默尔理论的第三项驳斥,是关于“前判断的学说”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8~299 页。。赫施说:“伽达默尔在攻击解释之客观性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最坚固的观点和最有力的武器并不是有关历史性的学说,而是有关前判断的学说。”2[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8~299 页。赫施驳斥道:“暂时性的解释学假设(前期待)与前判断并不是一回事”,“没有一个人会完全清楚,新的假设是如何诞生的。把新的假设与前认识相提并论,也就是说,把一切有关材料的新思想都归因于旧的前判断。”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02 页。“由于前理解是一个有助于理解的模糊的假设,由于理解据此是部分地取决于前理解的,因此,对本文获得准确的前期待,对解释来说就具有决定性意义。”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03 页。“在解释过程中对本文的暂时性推测或前期待,实际上就是对该本文所从属范型的推测。”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04 页。
以上引文表明,赫施是要区别前判断与前理解或前期待。他说得很明白:“用‘前认识’或‘前判断’去取代‘前理解’这个词,是一种不能成立的错误的混淆,‘前认识’和‘前判断’这两个词具有着有偏爱的或合惯例的态度这种含义成分,因此,上述这个混淆也就潜在地意味着:一个解释者实际上无法改变他通常的态度。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人们知道:解释者事实上是会改变其对本文含义的认识的。”6[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01 页。此外,前判断学说的错误还在于它将一切新思想“都归因于旧的前判断”。7[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02 页。
赫施对“前理解”的定义是“一个有助于理解的模糊的假设”,8[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03 页。他对“前期待”的定义是“对该本文所从属范型的推测”。9[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04 页。这两个答案其实是一样的:有助于理解的模糊的假设,就是对其范型的推测。这样,赫施就以其“范型”概念取代了“前判断”概念。
现在,我们可以对赫施解释学的整体框架作一个总的概括了:保卫作为陈述主体的作者是他的《解释的有效性》一书的宗旨,这一宗旨所要求的是从本文推测作者的原意,亦即重建陈述主体。本文的涵义被区分为含义、意味、意义三种, 可归并为含义与意义两种。理解活动被区分为理解、解释、批评三类,也可归并为理解与解释两类。含义与理解相对应,解释与意义相对应。作者意指的含义是确定的,而意义是变动的。“范型”概念是含义被传达的类型,解释者入手于某个类型构想,并在解释过程中去限制和更准确地构造这个类型。合法性、相应性、范型合适性及连贯性则是解释有效性的四条验证标准。前判断与前理解、前期待不能混淆,“视域融合”论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然而,可以反问赫施的是,如果作者不加说明,你怎么知道他意指的内容?虽然可以从本文的表达中加以推测,但要“重建陈述主体”,因为含义时有的模糊性及其与意义的联结关系,往往做不到,特别是对博大精深的著作,更是这样。
五
为了对赫施的理论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我们还应该述及为伽达默尔的理论作了全面的辩护,并对赫施对伽达默尔的批评予以了反驳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教授大卫·库森斯·霍埃的意见。
霍埃在《批评的循环·英文版前言》中说:“若不是与卡斯顿·海利斯(Karsten Harris)及H.G. 伽达默尔进行了讨论,从而激发了我的灵感,那么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1[美] D. C. 霍埃:《英文版前言》,《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0~11 页。此书将《译者前言》与原作者的《英文版前言》两篇合并排列页码,《西方解释学现状——原作者中译本序言》及正文则各自另排页码。——作者注由于伽达默尔的参与讨论,因此霍埃这本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是伽达默尔对于包括赫施在内的批评的回答,因而值得注意。本文因为论题的原因,只叙述与评论霍埃对赫施的反驳。
霍埃对赫施的许多批驳并不能站住脚。他说,赫施“还原了心理学重建的原则”2[美] D. C. 霍埃:《妥当性与作者意图》,《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4 页。,其根据是赫施说了这样一段话:“解释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自身去重建作者的‘逻辑’、他的态度、他的文化给定性,简言之,也就是去重建作者的世界。”3[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79 页。然而,如本章第三节所引,赫施随即说明是要“想象性地去重建陈述主体”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80 页。,并专门作了区分:“陈述主体与作者的主体性并不是一回事。作者的主体性是在其实际的历史的个人中呈现出来的,而陈述主体则是指整个作者主体性中的某个特定的、专门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陈述主体就是指作者的那些规定词义的部分。”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80 页。[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7 页。霍埃对赫施的原话是一直引用到了“想象性地去重建陈述主体”之处的,但他还做出了上述指责,这是不顾事实在讲话。
赫施说:“理解是默默地发生的,而解释则是见诸于言说的。”1[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理解、解释和批评》,《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157 页。霍埃评论说:“这样,理解便不是以实际评论的行为而实际写下来的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唯有释义。”2[美] D. C. 霍埃:《妥当性与作者意图》,《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9 页。此处的“释义”即“解释”。理解作为领会,自然可以是默默的;解释作为阐述,则必须见诸言说;当然,理解也可以见诸言说。霍埃的评论,是在钻牛角尖。
霍埃说,赫施“坚持认为含义是实际人的意识问题,这若不是对心理因素的过于注重,那便只是一种多余的话”。3[美] D. C. 霍埃:《妥当性与作者意图》,《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9 页。所谓“含义是实际人的意识问题”,应该是指本章第二节已引赫施的主要观点:“本文含义就是作者意指含义。”4[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5 页。赫施正是由此而肯定含义的确定性的:“作者意指的含义不仅是确定的,而且是可复制的。”5[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客观的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80 页。[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含义和意味》,《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37 页。这不可以单纯归之为心理因素;并且,对于赫施的理论来说,这恰恰是非常重要的话。
霍埃在书中多次说:赫施“关于作者意图即是确定正确释义的唯一基础的观点是哲学的而不是实践的观点”。6[美] D. C. 霍埃:《妥当性与作者意图》,《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41 页。他又说,赫施的理论“有一个包袱,其重要部分在于他认为含义是实际上确定的、不变的。不幸得很,这些结论都来自于他的术语,而不是来自于可观察到的经验”。7[美] D. C. 霍埃:《妥当性与作者意图》,《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0 页。我可以代赫施辩护说:如果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都从某篇(部)作品中读出某种含义,那么你就不能说它不是确定的。恰恰与霍埃所说相反,这样的阅读经验普遍存在。
霍埃又将认识与理解分别开来,他说:“知识往往归入对于事实的断定,而理解所指的则‘更多’。”“这些方面包括了整体的意义,包括了带有无数个暗示的总体观,包括了联想以及滞留在背景里但又确定着本文的重点及内容是否被恰当掌握的内涵。”“客观主义者也许仍然会认为,强调了这种‘更多’的理解,便使得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成为非认识的、主观主义的了。”8[美] D. C. 霍埃:《理解的特征》,《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60 页。这一段话有两个错误,第一,所谓“理解所指的则‘更多’”,这些“更多”并非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所关心的内容。伽达默尔说得很清楚:“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Sein)。”9[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第2 版序言》,《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6 页。第二,这些更多的内容,赫施也同样重视,这些内容存在于他的“意味”“意义”与“范型”的概念里。看来,自认为伽达默尔辩护并对赫施加以反驳的这位哲学教授,对于这两者的理论都不大懂得。
依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如果把握不当,确存在着相对主义的可能。伽达默尔有句经典的话:“我们只消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就够了。”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383 页。此语自然有相当的正确性,但如果走过头,走到否定理解中有确定的、一般的成分的地步,那就是相对主义了。我曾说:如果在一千个李白研究者的心目中就有一千个李白,那么任何研讨会都不必开了,也无法开,因为只有各说各话了,甚至彼此都听不懂其他人的话。总得大家对李白的认识有同有异,这个会才有开的可能。在各异的解释中,通过比较,通过对解释与本文及历史语境符合程度的比较,我们是能够从众多的解释中,找出比较好的解释的。
赫施理论的缺点,霍埃并不能抓住。比如,读者如何区别有意识的含义与无意识的含义,赫施就没有说到,这在他理论中,涉及含义与意味之别。赫施反对将前判断与前理解、前期待混淆起来,这是对的,但他将前理解、前期待落实为范型,也过于狭隘了。这些比较重要的理论缺点,霍埃都没有看出来。
不过,霍埃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抓对了的,即伽达默尔与赫施代表了两种对立的解释学观念。霍埃说,赫施“把与本文的关系看成是‘认知的’关系”,2[美] D. C. 霍埃:《理解的特征》,《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57 页。伽达默尔则“注重了对于理解特征的描述”。3[美] D. C. 霍埃:《理解的特征》,《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57 页。霍埃认为,《真理与方法》是一个“讽刺性书名”4[美] D. C. 霍埃:《本文与语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16 页。,他说:“这种反语是故意的,因为解释学已经洞察到,真理并不能由方法来加以保证。”5[美] D. C. 霍埃:《本文与语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16 页。霍埃并称伽达默尔最初计划把他的书名定为《理解与发生》6[美] D. C. 霍埃:《本文与语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16~117 页。。我们记得,伽达默尔在他的《自述》中曾这样说到过书名的事:“我的国内外同行都期待着把这本书作为一种哲学诠释学。但当我建议用哲学诠释学作书名的时候,出版商就反问我:什么叫哲学诠释学?看来更好的做法还是把这个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名词作为副标题的好。”7[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附录》,《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自述(截止于1975 年)》,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800 页。虽然伽达默尔自述如此,但只要加上一个限制,不要把“发生”理解为发生学上的发生,而是理解为一种运动的构成,那么,霍埃所说的这个书名还是揭示了《真理与方法》一书的主旨的。自然,这一书名未能显示出伽达默尔思想来自于海德格尔的根由。
霍埃就“那种认为释义即是与一个对象之间的认知的关系的见解”8[美] D. C. 霍埃:《理解的特征》,《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58 页。中的“关系”一词议论说,它“指的是把两个‘事物’引到一起来,它已经表明了本文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和差别;本文便被指定为一种‘对象’,它与必须达到它的主观意识有着一段距离。然而从现象学来看,这样一种描述并不符合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的实际过程。更确切地说,直接经验却更加接近于读者与本文的融合”。1[美] D. C. 霍埃:《理解的特征》,《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58~59 页。霍埃这是说,在赫施的解释理论中,本文是读者的对象,两者是分离的,而非融合的。
对于伽达默尔的理论,霍埃说:“解释学传统是从海德格尔对于那种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问题的重新阐述出发的。我们必须原则上不再认为我们自己是纯理性的存在、独立的自我,或者是站在世界之对立面或世界之外的独立的意志。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内了。”2[美] D. C. 霍埃:《英文版前言》,《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9 页。此书将《译者前言》与原作者的《英文版前言》两篇合并排列页码,《西方解释学现状——原作者中译本序言》及正文则各自另排页码。——作者注“伽达默尔理论是以海德格尔把Dasein 看成‘已然在世上’的分析为前提的。在解释学经验中,正在分析的是交流的行为,参加者存在于先前被分享的含义的世界中,那就是说,他们共享着一种语言。”3[美] D. C. 霍埃:《理解的特征》,《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78 页。“伽达默尔的‘语言转向’——他转向了语言,而背离了传统的主客体心理学。”4[美] D. C. 霍埃:《理解的特征》,《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81 页。“Dasein”,此在。“已然在世上”,是指的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5[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 年,第65 页。的思路。但霍埃所说“交流的行为”一语,对伽达默尔思想的概括并不准确,伽达默尔说:“理解不是心灵之间的神秘交流,而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377 页。说伽达默尔转向了语言,这是对的,伽达默尔曾说:“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过程。”7[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真理与方法》(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496 页。说伽达默尔“背离了传统的主客体心理学”,也是对的,伽达默尔视理解活动如同游戏,或者如上所说是一种运动的构成,但这是一种无主体或者准确地说是漠视主体的运动构成,自然不存在主客体问题。伽达默尔自己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中就明确说:“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Dasein)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本书中的‘诠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8[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第2 版序言》,《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4 页。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存在论的解释学。
追随着这一思路,却是走得更远,如同赫施所批评的“解释者真正地固守其自身的历史性”9[美]埃瑞克·唐纳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附录:伽达默尔有关解释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年,第294 页。那样,霍埃说:“人类包含在一个前进着的历史之中,他无法超然于历史之外去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10[美]D. C. 霍埃:《理解的特征》,《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89 页。这样说来,人们便无法认识历史了。所谓整体是什么含义?求全求备的整体历史把握,是永远没有人能够达到的;具有总体性的、近似的历史把握则是可达到的,并不因为我们生活于历史的延续之中,就整个融合在其中了。阅读是一种开拓、提升,因而也是一种超越。人对于自身的历史存在,在阅读、理解中是能够有所超越的。为什么人们能够从前代作品中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作者的原意,就在于这种超越性,伽达默尔正是不明白这种超越性,所以他所说的“视域融合”,其实是视域化入,是历史视域化入现在视域。
伽达默尔与赫施的理论各有其优长,也各有其明显的不足,我们审视围绕着解释的客观性的争论,所应得出的结论是:诠释学应该是存在论与认识论的统一、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