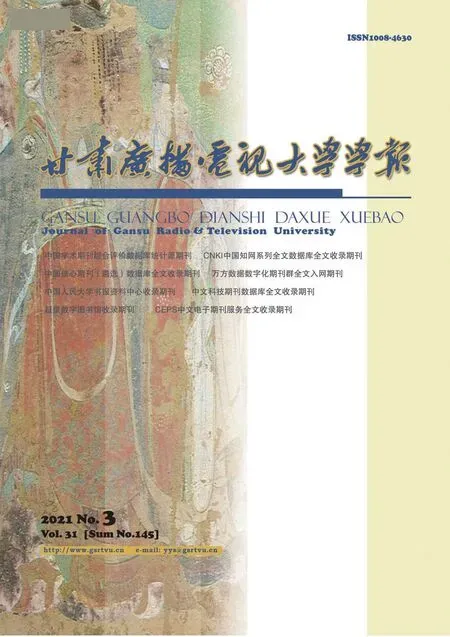刘勰文章润色观刍议
徐庆玲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文章的润色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从情感到句法、辞采到音律,无不可作为装点文章的要素。从先秦到魏晋,关于文章的润色的论述要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论述最为折中、系统。
一、“泽”的含义与“悦泽”论
从字形上看,金文“泽”字的部首为水,整个字形如羊在饮水。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水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以水为部的字自然也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先秦典籍中,“泽”字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在《诗经》《周易》《庄子》《孟子》中也屡见不鲜。据《广韵》,“泽”字本义与水有关。
《周易·说卦传》云:“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1]434由于水是泽之所以存在的因素之一,故后“泽”常与“润”相结合成为一个词语。西汉刘向《说苑》云:“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2]即“泽”的作用是滋养万物,使万物达于一种“说(悦)”的状态。后“泽”又常与“悦”连用,如汉代焦延寿的《焦氏易林》:“凫得水没,喜笑自啄。毛羽悦泽,利以攻玉。”[3]形容鸟身上羽毛的光鲜亮丽,而其原因正是得益于水的润色。
“悦泽”一词由自然界转而进入文学家的视野,始于晋。陆云《与平原书》:“久不作文,多不悦泽,兄为小润色之,可成佳物。”[4]陆云并未指明“悦泽”具体指的是哪些方面的内容,只是暗含与“润色”有相近或相似含义。
自先秦至汉魏六朝,“悦泽”论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介于有意识与无意识的状态之间。一方面,作家们都注重文章的润色,在声律、采藻、修辞等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加工;另一方面,这种自发的行为由于缺乏文学理论的节制,逐渐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繁缛。至齐梁,刘勰作《文心雕龙》方重申“悦泽”的含义与使用原则。
二、刘勰“悦泽”论的内涵与原则
刘勰的“悦泽”论主要反映在《文心雕龙》中,其《铭箴》《诔碑》《杂文》《诸子》《定势》等篇都有对“泽”的论述。尤其在《定势》篇中,刘勰称赞陆云“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5]531。并因此提出“势实须泽”的主张。
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刘勰提出了鉴赏作品的六要素:“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5]715“置辞”“奇正”“事义”“宫商”都与文章的润色有关。另外,《镕裁》篇也规定写文章的三个步骤,即“设情以位体”“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5]543,把“舒华布实”作为写文章的程序之一。在刘勰看来,“悦泽”与否关乎文章的成败,文章的润色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声律的使用一定要谨慎。诗歌文章依声律而作并非刘勰首倡,早在先秦时期,《诗经》的采集者对韵的使用就已经十分清楚,注重用雅正的声音去歌唱,这是因为文学在产生之初与音乐、舞蹈的结合十分密切,其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礼乐,追求的是一种“和”或者说“合”的状态。此后的很多文学作品,在韵方面有意或无意地追求和谐,而严格的声律论直到齐梁时期才由沈约、谢朓等人提出,即“四声八病”说。“四声八病”指“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和“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毛病。其原则是“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6]在此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篇提出“声有飞沈,响有双叠”[5]552,即声韵分平仄,又分双声与叠韵,作文章时声与韵要“辘轳交往,逆鳞相比”[5]553,反之,文章的声律就会不和谐。刘勰的声律论是文章润色的要素之一,一篇文章的风貌在于韵律的和谐。在声律的运用过程中需要变换韵脚声调,但换韵不能太勤,也不能太少,须秉承节制的原则,反复斟酌,“比音切近”,方能产生调和的音律。
其次,重视比兴。“比”与“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7]在《毛诗序》中这六项又称“六义”。刘勰对“比”与“兴”的解释见于《文心雕龙·比兴》篇。“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5]601刘勰把比与兴推崇为诗人表情达意的两种方法。然而,纵观先秦至汉魏六朝的文学,自《诗经》以后,作家大多重视“比”而忽略“兴”,尤其是汉赋大力使用铺陈排比的手法,譬喻多而兴义少,这种取向直到西晋仍十分盛行,刘勰对此十分不满。在《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部分,刘勰表达了对儒家传统的遵循。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深刻影响了他对文学作品风格的认识,《定势》篇中云:“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5]531文章的势不一定要依靠豪言壮语、慷慨意气,而是要做到“文质彬彬”,情感与文辞协调一致。如此,就算是言辞委婉的文章也可以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就要依靠“比兴”手法,尤其是“兴”,以达到美刺的目的。在使用比兴手法时,刘勰认为追求的效果也应当贴切,要使文章达于“和”的状态。虽然文学到了魏晋已经进入自觉的阶段,但刘勰对于“比兴”的认识还在朝着“有益政教”的方向发展。
再次,夸张、对偶、用典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文心雕龙》的《夸饰》《丽辞》《事类》三篇专论文章的夸张、对偶与用典,《谐隐》等篇在写作过程中也大量使用《周易》《尚书》《尔雅》《礼记》《左传》《汉书》等中的典故。可见,刘勰对文章的修饰润色十分重视,并且在写作中一直践行。他所追求的是用技巧却不着痕迹,达于自然之效。如《夸饰》篇中,刘勰推崇《诗经》《尚书》的夸张技巧,不认同司马相如、扬雄等汉赋家的辞赋,指出夸张一定要合于情理,不能违背事实,理想的效果是“夸而有节,饰而不诬”[5]609。
在具体的文章润泽过程之中,刘勰认为要“重熔裁,明隐秀”,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的写作技巧堆砌在一起。《丽辞》篇称:“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5]589技巧的运用要追求自然的效果,也即“和”的状态,这与道家的“无为”思想达到了高度的契合。老子云“无为而无所不为”[8],其目的不是要人“不为”,而是要因势利导,做到“善为”。《文心雕龙》开篇便讲“原道”,追求文章写作的自然状态,以贴近“道”之本原。这看似是要求作家“无术”,实则要求他们“善术”。《总术》篇云:“执术驭篇,似善奕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5]656言明不能“弃术”,而要“执术”,注意掌握作文之大体,因时乘机,动不失正。总之是要在创作文章时做到润泽而有节制。
三、刘勰“悦泽”论的时代背景与渊源
刘勰生活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那时中国文学的创作已经进入自觉状态,同时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渐趋成熟。文学思潮方面,齐梁时主要有“新变”与“复古”两大阵营。以裴子野为首的复古派主张文学要师法儒家经典,而以沈约、萧纲等为首的新变派则表现出对声律、辞藻等的关注。在文学理论方面,刘勰之前,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不同体裁的文章应该有各异的风格,“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9]158。陆机在曹丕的基础上对文体及其风格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9]171。陆机在文章的立意与润色方面主张巧妙妍丽,“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9]172。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虞、夏、商、周到南朝的文学风貌及其产生的原因均有总结评论。他的这些评论集中见于《时序》《才略》二篇,其他篇目亦有提及。在《宗经》篇中刘勰评楚辞和汉赋的特点是“楚艳汉侈”。在《通变》中说:“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5]520在刘勰看来,正是楚辞汉赋造成的“流弊”被魏晋南朝的作家所吸收,才使他们创作的骈体文对形式美的要求极高。
刘勰生活的时代,“文笔之辨”正当热潮,《文心雕龙·总术》篇中提出的区分“文”与“笔”的原则是:“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5]655这与萧统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10]在表述上虽有差别,但在内蕴上却达到了一致,他们都强调文章的加工润色。可见,刘勰所处的时代,偏好文章辞采的华美,作家们对文章的修饰甚至到了繁缛的程度,即便是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难以避免这种风气的影响。
虽然刘勰与同时代的作家在文章的是否润色上持有相同的选择,但刘勰的润泽观却别有一番清丽的风貌。《文心雕龙·宗经》篇中,刘勰主张作文宗经,以达到“情深不诡”“风清不杂”“事信不诞”“义贞不回”“体约不芜”“文丽不淫”[5]23的效果,以此来正末归本。刘勰反对的并非是润色本身,而是要改革自楚骚、汉赋开始形成的艳丽侈靡的文风,以及晋宋以来文人为追求新奇而使用的颠倒字句的方法。他力图把文学拉回正轨,达于自然的状态,其润色观的特点是取向中和,强调润泽而有节制。
《物色》篇是《文心雕龙》杂论中的一篇,兼谈写作的方法。全篇论述的是如何用文学来描述自然景色,文章认为《诗经》、楚辞、汉赋都对自然景色有所描摹,《诗经》的语言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5]693,十分简约形象;楚辞的语言如“嵯峨”“葳蕤”等开始铺陈,到了汉赋,辞句则发展到了繁芜的程度。辞句繁便不珍,抓不住重点,反失了最初的写作动机,辜负了作者的情志。刘勰的这一主张深受《周易》的影响,《序卦传》云:“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1]450此处“饰”通“饬”,含整顿之意。《说文解字注》说:“凡人物皆得云饬。饬人而筋骸束矣,饬物而器用精良矣。”[11]同理,文章需要整饬、加工,但到达极致之后其效果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所以刘勰对“泽”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节》卦卦义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节》卦卦象为“泽上有水”,本应处于十分和谐的状态,但如果水过多,就会溢出,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需要加以节制,“安节”则亨,但节制过头又可能会走向穷途末路,是以“苦节”不可。
《周易》之后,先秦儒家和墨家都对《周易》的“节制”思想进行了深入阐发。孔子及其门生作《十翼》阐释《易》理,认为《节》卦的根本在于“当位以节,中正以通”[1]346。孔子把天地的“节”引申到社会秩序中,再将之延伸到诗教中,即“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而墨家对“节”的阐释则更注重于其“节俭”的含义。刘勰的在文学作品的润色上所持有的节制原则正是受到了儒家之“节”的影响,既不否认与摒弃艺术形式,同时又对齐梁时期诗文润泽的“讹势”进行节制改造,表现出对深郁厚笃的艺术风格的追求。《文心雕龙》中有关文章润色的论述,始终贯穿节制的思想。《情采》篇:“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5]538辞采是辅助表明情理的手段,是文章之“末”而非“本”,文章的“本”应该是情理,滥用辞藻的结果是舍本逐末,弄巧成拙。如此一来,润泽的关键一步就正在于“知止”,要“斟酌乎质文之间,隐括乎雅俗之际”[5]520,以求“文而不侈”。
四、结语
魏晋时期,关于文学应有之样貌的争论十分激烈,诸多文学家在文学理论和写作实践中都不遗余力地传播和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或完全走向复古的极端,或为求新而变,以至讹势。而刘勰因其深厚的儒学功底使得他能兼众家之理而中庸,结虑司契,垂帷制胜,故而其润色理论对同时代的裴子野、萧纲以及后世文学家、理论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