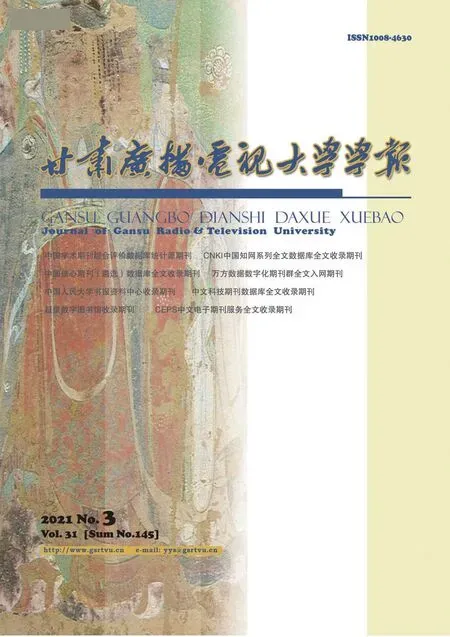吴子林的诗性批评
——以《批评档案》为例
张宏伟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吴子林是当代中国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批评档案——文学症候的多重阐释》可以作为吴子林文学批评的范本。吴子林在本书的《跋》里说:“这部文集收录的批评、论争的文章基本按撰写、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时间跨度二十年左右。它们记载了我不断尝试、探索的思想与学术历程,当然,也呈现了我的文学批评之梦。”[1]所以,悉心观照《批评档案》中的论文,大致可以把握吴子林文学批评的特征和风貌。
一、现实关切与问题意识
吴子林的文学批评有几个突出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切实的当代问题意识。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面临巨大的困境,迫于西方文论的压力,大多要么沉醉于对西方理论的接受、解读与阐释,要么用西方理论来套中国的文学文本,或者拿中国文学文本去印证西方理论。这样做的结果,都使得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相当程度脱离了自己的语境,缺乏应有的现实关切。因此,吴子林的研究都从现实问题出发,具有浓厚的时代感和深沉的使命感。
《批评档案》中选取的篇目无不显示这样的特点。《诗人:人间的“安泰”——杨骚诗论蠡测》一文希图借杨骚诗论“纠正近年审美思维重心片面转向表现模式,忽略文学的普及,忽视诗人与时代、与人民的联系等诸多偏颇,重新积淀于生活的灵肉之上的诗美。”[2]10《对话:金圣叹评点与英美新批评》一文认为,“金圣叹的评点在走向本文、文本的‘细读’上,与‘新批评’有某些惊人的相通之处,而凸显出现代的价值”;故可作为我们建构现代诗学的“本土资源”[3]21-25。而《症候阅读——金圣叹“独恶宋江”与“腰斩”〈水浒〉新论》一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借助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的批评方法对中国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金圣叹“独恶宋江”与“腰斩”《水浒》现象做了鞭辟入里、令人信服的阐释。《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则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俨然成为一道重要的文学风景”的“身体写作”的冷静审视和尖锐批判。
《“文学终结论”刍议》和《图像时代文学的命运》是对视觉文化或图像文化兴盛背景下“文学终结”的一片喧闹声的分辨与探究。《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一文对目前国内文艺界流行的“文学性扩张”的说法进行了针砭。《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可能向度——以文学批评家胡河清为例》面对的是当代中国还是很缺乏真正知识的现状,希望通过对作为“中国文学的守灵人”的胡河清的文学批评的例证式评论对此问题进行“探求”,目的在于“启示”和“扭转”我们“早已迷失传统、与西方亦步亦趋的文艺学研究之颓势”[4]155。《“菲洛克忒忒斯的神弓”——当代文学批评的歧途与未来》一文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在知识与思想退出公共领域的情况下,退避进了自己的专业领域,“知识本来所具有的超越性被切断了,不再向社会提供现实意义”,“当代文学批评逐渐演变成为各种方法论和可用科学方法予以验证的公式。”,“制造各种繁荣假象,掩盖尖锐的现实问题,漠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价值”[5]188-189。《“菲洛克忒忒斯的神弓”》一文便是对当代文学批评“歧途”的校正。
或许有人说,任何文学批评都有自己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所探讨的问题本身是否针对急切的现实。就普遍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来讲,正如吴子林所说,相当程度上已经沦为西方话语的仆从,业已转变为漠视现实问题的所谓纯粹的“学问”或“知识生产”。这样的批评显然要在西方的概念、判断或论证中找寻问题,与当代中国的实际在很大程度上脱节了。不仅如此,吴子林着力批判并要努力“扭转”的恰恰是这种局面。吴子林斩钉截铁地说:“文艺学的研究必须正视文学所面对的‘迫切问题’——人的现实生存境况”[6]。吴子林对胡河清的热情肯定事实上也基于这一点,因为胡河清最终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对当代社会生活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以及一种异乎寻常的生活激情,而在文学中寻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4]157。带着这样急切的“用世之心”,吴子林的文笔必然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学院风格,而是显得至诚至性,寄寓着深深的关切与忧虑,于是,文字便拥有了感染人、警策人和说服人的力量。
二、人文关怀与文学本位
吴子林文学批评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并始终坚持文学本位。文学本来是人学,有着现实关切的文学批评必然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
文学对人的意义是吴子林文学批评始终坚持的着眼点。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诺曼·N.霍兰德的一段话深入其心:“文学之独特而又奇妙的力量在于:它以一种强烈而又高度浓缩的形式,为我们完成了随着我们自己的成熟必须要做的事情——它把我们原始的、幼稚的幻想转化成成年的、文明的意义。”于是,吴子林便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个性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论述,抓住了文学的真义:“文学显示了人类实现自己精神与审美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即如何‘做人’的漫长历史。”[2]1,2杨骚的诗歌创作正是基于“对祖国、人民的挚爱”,谋求自身和祖国人民精神的自由、发展与解放的不懈努力。以文学的这种“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的眼光来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后流行的“身体写作”,会发现其偏颇和缺失是非常严重的、不容忽视的。因为“身体写作”实际变成了“享乐主义的消费时尚”,偏离了其照亮读者心灵、并为已有中国文学增添女性质素的终极目的。至于网络时代的玄幻小说,虽然它满足了年轻一代,也可以说是人类追求自由、渴望自由的天性,但是受制于消费文化逻辑,缺乏文学里最为宝贵的东西——真正的自由精神与想象力,无法使人的无穷生命潜力得以呈现。出于对现实不离不弃的作为“行动的精灵、战斗的精灵”的作家的倾心,吴子林批判了余华的“空白之心”,认为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价值偏移,实际是不为正义之情所激发的琐屑艺术。吴子林也不满意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因为“批评家仅是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研究者,而不是文学世界的一个介入者、行动者”,而“只有行动着的人才可能从历史走向未来”[5]185。
对文学意义的追寻使吴子林在面对“文学终结论”“文学扩张论”的时候显得颇为谨慎。通过深入辨析,吴子林认为西方理论界持续言说的“文学终结论”不过是西方文化和思维的“死结”,并不能概括全球,而且危机总意味着“发展的契机”。由此可见,吴子林对“文学终结论”是不以为然的,这在他对“文学性扩张”的质疑中得到了印证。面对国内流行的“文学性扩张”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调,吴子林紧紧抓住文学的本质进行申述。文学应该包括“审美”和“语言”两个维度,“审美”在精神向度上要引人向上而不是向下,而语言作为文学不变的栖居之地,则以其诗性言说唤醒生命,应该“成为人们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的本真显现”。显然,对吴子林来说,只要人类的生活继续着,情感表达的需要存在,文学就活着,因而文学是不死的。不妨直接引述吴子林自己的话,他说:“世上只要有读者,只要人们的情感生活不至于枯竭,文学就永远不会寂寞,更不会走向所谓的‘终结’”[7]。
正是基于对文学不死的信心,吴子林展开了对文学世界不息的探究,“文学本位”遂成为其事业的不易法则。有的人是以别的身份和动机来研究文学的,比如,明朝的李贽;他笃信阳明心学,本“童心”而论“文”,其评点是“高屋建瓴式的赏析”,给中国文学批评史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但是,他是以“一个思想家的身份惠顾小说”的,“美文意识不足”,“对于至文之所以为至文的文本依据,语焉不详”[3]13。这种着眼于“文学之外”的批评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可谓司空见惯。但是这种做法并非吴子林的本心。吴子林坚持的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方式。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文学批评就应该以文学文本为依据,自觉到文学的形式特征,在批评层次上转向作品的“体格声调”。因此他推崇金圣叹。真正理解“文字之三味”的金圣叹的评点与英美新批评在实践上颇为接近,都在对文学文本的“细细详察”“精切读之”中品味分析,又能对作品的整体艺术予以高度重视,在“文文相生”中把握其文学的价值。显然,在吴子林看来,这样的精切阅读才能得文学之神髓奥妙,也就是说,吴子林是坚持“文学本体论”的。因此,他尖锐批评现代那些习惯于“闭门造车”和“高空作业”的文艺理论家,“他们往往将中国的文学作品变成西方的或中国传统的某个理论、概念正确性的一个实证,成了自己得心应手地构筑模式、摆弄材料的智力游戏……严重忽视了对文学形式和审美的研究,导致文学本性的基本丧失”[4]139。不过,吴子林在明确主张“回到事物本身”、回到文学文本本身的同时,又不囿于英美新批评的樊篱,走向了金圣叹张扬“读者精神”的开放的结构。这个时候,那些重要的哲学理论、文化理论等都成为吴子林深挖文学文本内涵的有效助力。这便成就了吴子林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三、读者精神与中西会通
重视读者精神是吴子林文学批评关注的重点,是吴子林文学批评的基础。“读者精神”是吴子林从金圣叹文学评点中概括和提炼的观点。金圣叹认为:“读书尚论古人,须将自己眼光直射千百年上,与当日古人提笔一刹那倾精神融成水乳,方能有得”[3]21-23。可见,完整理解“读者精神”,须先重视金圣叹所强调的类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能力。金圣叹的评点着眼文本的一句一字一节一篇,“晰毛辨发,穷幽晰微”,“精切读之”,以发掘文本的多义或“含混”、悖论、反讽等特性,而且也像英美新批评一样重视文学的意象和整体艺术性。但是,不同于英美新批评对作者意图和读者感受的拒斥,“金圣叹的评点以文本为中心的同时,张扬‘读者精神’,作者、文本、读者和诠释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关系:(作者—文本—读者)——诠释者”[3]25。吴子林如此详细论说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在方法论上可谓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吴子林的文学文本批评都在一方面洞幽烛微,另一方面又积极发扬“读者精神”,以期与作者精神水乳交融。其关于杨骚的诗论、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评论、对胡河清文论的评论以及对余华创作的批评都在生动践行这一方法。其实,吴子林的任何文学批评都贯穿和渗透着这种精神。他那些针对“文学终结论”或“文学扩张论”的文字也是辨微晰幽,又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洞察着人们的复杂社会心理。于是,在细读“文本”前提下大量借用和调动相关理论知识来深入挖掘文本内涵也就成为吴子林文学批评的必然选择。
吴子林文学批评的信息量极大,中西文化(包括文论)的知识在他那里信手拈来、汇聚激荡,融和在一个论题中。在《诗人:人间的“安泰”》中,吴子林调动了霍兰德、王国维、鲁迅、郁达夫、别林斯基、黑格尔、克罗齐等人的有关话语,来扎实开掘杨骚的诗论。《对话:金圣叹评点与英美新批评》一文在谙熟金圣叹评点的基础上,与英美新批评进行了内在的沟通和比较。《“症候阅读”》主要结合金圣叹的人格和生活的社会环境,自如运用阿尔都塞的“症候批评”方法来开塞清障,又运用维特根斯坦、布尔迪厄、伊瑟尔等人的有关理论和李贽、鲁迅、钱钟书、聂绀弩、陈洪、胡万川、罗尔纲、周岭、张国光等人的相关研究来立论和驳诘。《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则通过西美尔、伊格尔顿、舍勒、埃莱娜·西苏、科林伍德以及刘小枫、徐坤、郑敏等人的眼光,在广泛的文化视域中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身体写作”。《“文学终结论”刍议》一文对图像时代甚嚣尘上的“文学终结论”展开冷静思索。但是吴子林始终立足中国现实来谈论这一问题,于是李衍柱、童庆炳、金慧敏等学者的态度和观点就成为着重比照与考量的对象。《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一文也在思考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的命运,同样在伊格尔顿、马泰·卡林斯库、乔纳森·卡勒、巴拉兹、波普尔、黑格尔、张隆溪、D.佛马克、E.蚁布思、奥克塔维奥·帕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萨义德、利维斯等人的理论间自由出入。吴子林《批评档案》中的其他论文都具有这样的鲜明特色,着眼于重要的现实文艺理论问题,自由出入于中外文论之间,以文化的大视野深入探讨所立论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故意炫耀知识、掉书袋,而是透彻明晰与切实解决问题的内在需要。从运用的自如和阐发的有机性来看,这绝不是写作过程中的死命拼凑,而是长期的勤奋阅读、积累与持久的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这是一种中西会通的大境界,在全球化时代应有的全球性视野,然而却始终瞄准自己的问题,又绝不轻视自己的传统和研究成果,体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一直回响着在中西互辨、互通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文艺理论道路的心声。
四、美学创造与诗性批评
吴子林的文学批评有效沟通了我们民族的批评方式,属于性灵文字,着眼于美学创造,在构建一种诗性批评。
吴子林文学批评的天平始终在彰显文学的魅力和价值,因而是出于责任心的严肃的审美活动。里尔克说,“世界在人身上分崩离析,唯有诗人才将它加以统一”。所以,“文学既不是生活的‘描红’或‘佐料’,也不是生活的‘安乐椅’或‘按摩榻’,其生命在于质疑、冒险和拯救。”[5]182-183批评家的责任就在于通过精切阅读,有效介入文本世界,以反思性的审美体验发现和解说作品中的人生启示,提升作家的艺术敏感度。这就要求批评家出于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和虔敬,作为作家的深切同情者,和作家站在同一层面来考察和理解作品。又能将一般读者排斥和不解的艺术作品成功引领到普通读者的视野和关注之中,有效充当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中介调停人”。符合这样要求的批评文字显然不是史料的堆积和逻辑的推演,而是“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的用“心”的主体性批评,是属于“生命的学问”。也就是那种“批评家在作品里找到了某种贴心贴肉的东西,一定是‘恋人絮语’般的有效沟通、交流”[5]194。以是之故,批评家便以“回归生活、回归现实”的崇高责任感“把自己的血写进了自己的书”。中国历史上的李贽、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无不如此,他们这样的“小说评点不啻是批评分析,更是一种美学创造”[5]187。
吴子林的文学批评也是这样。他的批评实践总在捕捉作品的灵魂与精髓,是灌注了灵魂质地和精神气息的批评。对于杨骚的诗论,他捕捉的是杨骚那“满骨子里嫉恶如仇、桀骜不驯,刚强的性格和正直的心胸。”针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评论,他通过“症候阅读”透视了金圣叹心目中的理想国,发现了金圣叹美学思想与意识形态之间冲突的某种妥协或平衡。他也以切身的体验彰显了“身体写作”、玄幻小说、余华的文学创作作用于人的灵魂的意义和效果问题。吴子林发现,这些文学创作没有给我们提供解除现实心灵困境的钥匙。吴子林对胡河清文论却完全持另一种态度。胡河清对于文学有非同寻常的热爱,他在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用胡河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做了一个“中国文学的寂寞的守灵人”。因此,胡河清的文学批评是出于对文学以至对生命与存在的激情,以“追体验”的方式进入形象和情感的世界,与作者的精神相往来,完全冲破了文学评论套语的陈旧、呆滞和猥琐,用独特的审美观照呈现了作品的神奇,从而真正把握了文学艺术的本质。这是能触摸到批评者跃动不止的生命脉搏,感受到源于其切身体验的扑面而来的具有生命气息的文字,因此往往超越了持论之文而进入另有创新的天地。这也是带着体温和热血的灵动的批评文字,极具个性魅力,形成了一种玄妙灵动的中国式生命精神体验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必然是拥有文学气息的文学批评,是诗意的批评。而且,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胡河清有效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论结合起来,用它来指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创作,从而沟通了中西,打通了现代与传统,“以现代情绪和感悟开启逼近传统文化的沉积层面,激活历史,以惊人的想象综合力和异禀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作为价值的纯正源头,凝聚成宏大的形而上精神,以匡正当代人文化精神上的失血苍白和生命、生存的羸弱、动荡、虚飘,以张扬生命的坚韧、绚烂和庄严”[4]137。因而,胡河清的文学批评为中国文艺研究开辟了一种民族的可能的向度,肩负起了重建中国文化的大任。当吴子林用这些曼妙的文字评论胡河清的文学批评时,其实是引其为同道的,或者以其为楷模的。因为吴子林的文学批评或多或少都具有胡河清文论的特点。不妨引用一段吴子林评论杨骚诗论的开场白文字来表明他文论的这种诗性特质,吴子林这样讲:“诗论,是诗人创作路途中停息驻足之所。当他将目光沉静莹澈地栖息在造化万物时,就开始了异乎直觉的理性思索,伴着挥洒汗水和纷至沓来的阵痛之后的惶惑……”[2]1
五、结语
清末学者邱炜萱说:“天地间有那一种文字,便有那一种评赞。”[3]12真正文学的评论就应该体现文学的特点。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的忠告也在表达同样的意思,他说,“诗是需要分析的,但要像诗人那样来分析,不要失去诗的气息”[5]201。曾几何时,我们的文学批评变得日益枯燥和干瘪,实际成为阻隔文学文本与读者的厚障壁,这其实是对文学本质的背叛,实际变成“文学终结论”的帮凶。所以,文学批评本身迫切需要自我反省,从概念推演和知识游戏中走出来,回到文学本身。以是观之,吴子林那有着厚实的积淀和睿智、表达透彻、优雅、总能给人以文学审美享受的批评就显得难能可贵。基于年轻时的特殊经历,吴子林在人人遗忘别林斯基的年代仍然立志做“中国的别林斯基”,本质是对时代的、责任的、文学的、诗性的文学批评的执守,这何尝不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论传统的忠诚与担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