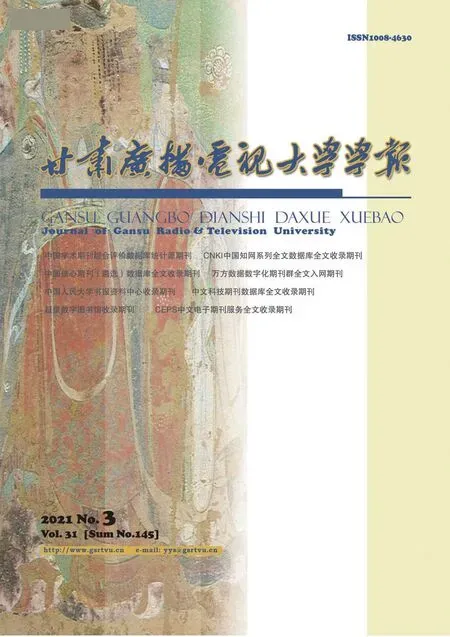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的节料
徐秀玲
(河南大学 文献信息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20世纪早期出土的敦煌文献中有关于节料的记载。对此,高启安先生解释说,有时也叫“节粮”,多出现在饮食文献中的节日食物原料支出中,不惟寺院节日支出的饮食原料称为“节料”,归义军衙内节日支出的食品原料也叫作“节料”,因此可以判断出它是“专为节日支出的饮食原料”[1]。关于敦煌文献中的节料研究,赵红、高启安曾提到敦煌寺院一般为诸色人等发放的节料是麦、粟、油等粮食或酒之外[2],并未对敦煌寺院领取节料人员的构成、节料的等级性进行探讨。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敦煌寺院的节料作进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从敦煌寺院领取节料的附属人员
从敦煌寺院领取节料的附属人员,从名字上看有黑女、安三娘、五娘、六娘子、员住、恩子、再儿等人,但是他们的身份又各不相同,试析如下。
(一)黑女、安三娘、五娘、六娘子
黑女、安三娘、六娘子出现的文书仅S.6233lv《年代不明(9世纪前期)付诸色斛斗破历》,转录文如下:
廿八日,付天养麻子□麦肆斗,溥。五月四日,付麦伍斗与黑(女)□充节粮,(溥)。同日,付黑女酥壹升,折麦贰斗,溥。十日,付面叁斗,付黑女,折麦贰斗,溥。十一日,付黑女豆贰斗,粮食,溥。十三日,付黑女麦贰斗,充粮食,溥。同日,付黑女豆贰斗,充粮食,溥。十九日,付黑女粟伍斗,充粮食,溥。廿四日,付黑女麦两斗,粟贰斗,充粮食,溥。廿五日,付黑女粟叁斗,对付……溥。六月三日,付安三娘粟贰斗,麦壹斗,溥。五日,付安三娘……溥。十六日,付安三娘青麦伍斗,廿三日,付安三娘青麦贰硕,……□月四日,付黑女五娘青……溥。七日,付黑女及六娘子青麦共陆硕,溥。[3]174
本件文书记载了黑女等三人从寺院领取斛斗的记录。在整个五月份黑女计领取麦9斗、面3斗、酥1升(折麦2斗)、豆4斗、粟8斗,小计麦粟面豆等斛斗2硕6斗。六月没有黑女领取粮食的记录,但是六月安三娘从寺院领取粮食粟2斗,麦2硕6斗,计2硕8斗。七月,黑女两次领取粮食,第一次数目不明。第二次是七月七日与六娘子两人领取青麦6硕。按人均计算黑女两次领取粮食总数至少3硕以上。从黑女、安三娘、六娘子三人领取粮食的数目来看,人均每月领取粮食至少麦粟2硕8斗5升。
李正宇指出,唐宋时期敦煌人对女子往往按其排行,称之为“一娘子”“二娘子”“三娘子”“四娘子”等。莫高窟第107窟女供养人题名见有“二十一娘”。呼之既久,约定俗成。于是“厶娘子”也就成了该女名号。贵族女子,取有雅名,则以名行,但仍习惯在名前冠以“厶娘子”,以示行辈,如莫高窟第98窟女供养人题名有“第十一小娘子延胜”“第十二小娘子延荫”[4]。S.6233lv文书中的安三娘、六娘子、五娘等人与黑女一起领取粮食。如黑女五月、七月两个月内领取粮食5硕6斗以上,也高于一般庄头人的食粮,极有可能是她们也如“某头”一样作为某项活动的负责人,从寺院领取粮食。可见黑女等人的身份应高于一般的当寺女人。
(二)员住、再儿等人与恩子的身份比较研究
员住是人名,但是在敦煌文书中,有叫李员住、安员住、令狐员住、康员住者多人,唯独有名无姓叫员住的人仅出现在S.1398v《壬午年(982)酒破历》[3]227与S.4642v1-8《年代不明(10世纪)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3]548两件文书中。前者出现在酒破历的后面杂写两行,后者出现员住之名较多,一起出现的还有再儿、任婆等人。在后件文书中员住与任婆、再儿等人一起从寺院领取月粮、节料,甚至员住与妻子治病、再儿妻子祈祷平安都是寺院出资。为明白起见,转S.4642v1-8《年代不明(10世纪)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部分录文如下。
麦壹硕,付员住月粮用。麦壹硕,董和通月粮用。麦伍斗,任婆月粮用。粟两硕捌斗,付员住再儿月粮用。(大岁)面叁斗,付员住、任婆节料用。面伍斗,员住妻将病用。(寒食)面贰斗,付员住、任婆节料用。(冬至)面捌斗,员住、再儿节料用。连麸面叁斗,员住、再儿节料用。连麸面叁斗,员住、任婆、和通节料用。(大岁)油贰胜,再儿、员住节料用。油壹胜,员住将病用。(寒食)油壹胜,员住、再儿节料用。油贰胜,再儿妻平安用。(冬至)油壹胜,员住、再儿节料用。[3]548-554
由本件文书可知,员住、再儿、任婆等人在敦煌某寺领取月粮、节料以及家人费用麦粟连麸面油等物品。如员住领取月粮麦1硕,另一次是与再儿两人领取粟2硕8斗,人均1硕4斗。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某段时期,麦粟比例为1:1.4,员住领取月粮麦1硕即相当于粟1.4硕,可知员住常年月粮为麦1硕,全年为12硕。此外,员住从寺院领取节料,本人及妻子生病,寺院又支出面及油等1硕6斗5升,员住全年收入可达13硕6斗5升。
再儿月粮如员住一样同为折合麦1硕或是粟1硕4斗。全年月粮12硕,再儿妻平安以及再儿节料还从寺院领取连麸面、油等,寺院支给再儿一家的斛斗也超过12硕。
董和通从寺院领取月粮及节料的资料仅有三条,董和通的月粮为麦1硕,节料是与员住、任婆领取一起的连麸面3斗,人均1斗;和通还从寺院领取面6斗,可知董和通一年从寺院支取的粮食也超过12硕。
任婆的月粮每月麦5斗,全年6硕,任婆从寺院领取节料有3斗5升。全年收入6硕3斗6升,远远低于员住、和通以及再儿等人。
可见,敦煌寺院支付给黑女、义员、恩子、再儿、任婆、员住等人在大岁日、寒食、端午、冬至等节日的节料有麦、油、面、连麸面等。麦的数量一般较少,仅黑女在端午节前夕得麦5斗,其他的人的节料一般是面或油,其中掺杂着连麸面。如员住、再儿任婆、和通、恩子等人都得到过连麸面。
关于他们的身份。如恩子,谢和耐将之称为难以解明的恩子,可能是奴隶阶级[5]。池田温认为恩子是人名[6],北原薰认为恩子不见于净土寺以外,恩子不表示身份[7]。姜伯勤从寺院供给恩子年粮、节料,家庭特殊用途、住房,以及恩子在寺院长役等几个方面认为恩子确是一个人名,地位是当寺厮儿,身份相当于寺奴婢[8]182-183。黄英认为恩子可能是“僧奴”的别名,不同寺院对僧奴的称呼不同,是供养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一类人的总称。寺院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每逢节岁时还有额外的补贴[9]。笔者以为,黄英指出恩子为敦煌寺院某一类人的别称,其观点有误。其一是姜伯勤认为恩子从净土寺领取的粮食:春秋粮、节料以及其他收入每年最多9.4硕[8]180-181,按照唐宋时期人均每年食粮最少7硕2升计算,恩子每年的食粮总数仅够一人吃用。若恩子是某一类人的总称,净土寺关于恩子食粮的支出断不能每年不到10硕。从这角度来看,黄英把“僧奴”这个群体等同于恩子并非正确。
唐代官奴婢给粮,“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厨膳,乃甄为三等之差,以给其衣粮也。(注:四岁已上为小,十一已上为中,二十已上为丁。春衣每岁一给,冬衣二岁一给,其粮则季一给。丁奴头巾一,布衫、袴各一,牛皮靴一量并毡。官婢春给裙、衫各一,绢裈一,鞵二量;冬给襦、複袴各一,牛皮靴一量并毡。十岁已下男春给布衫一、鞋一量,女给布衫一、布裙一、鞵一量;冬,男女各给布襦一、鞵袜一量。官户长上者准此。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三升五合,中男给三升)。凡居作各有课程。(注:丁奴三当二役,中奴若丁婢二当一役;中婢,三当一役)[10]。“其粮则季一给”,很显然,恩子属于奴婢。但是员住等人与恩子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按月领取粮食。张弓指出,寺奴婢的月粮标准没有明确记载。唐代官奴口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寺奴婢与此相差不多。作者以“僧奴”为例,说明僧奴的取粮方式似乎反映着某种常规:凡称“牧羊人僧奴”取者,所取有粟,有面,品种较好;所取凡称“月粮”或仅署“僧奴”而不称“牧羊人”者,品种则以粗劣的连麸面为多,细粮较少。这表明:(1)有的僧奴每年仅在春、夏、秋放牧季节充做收羊人;(2)在僧奴做牧羊人时,寺院供给的口粮品种有时稍好;若不放羊则仍取一般寺奴所受的月粮,品种亦粗劣[11]。但是仅从某月节料员住、再儿、任婆、董和通人均1斗连麸面,属于粗粮外,其他时间里,员住、再儿和通等人领取的月粮、节料以及自身、妻子生病或祈求平安时领取的麦粟面油等均属于细粮可知,敦煌寺院中的劳动者以领取月粮质量的好坏作为评判他们是否属于一般寺奴婢的标准不准确。我们从寺院员住等人领取全年的粮食高于恩子等人领取的春秋冬粮推测员住等人的身份应该高于寺院奴婢,或者他们即使属于寺院奴婢,其身份也应归属于寺院奴婢中的上层。
综上所述,黑女、安三娘、六娘子、员住、再儿、和通以及任婆等人,他们从寺院领取粮食、节料,生病、祈祷平安时可从寺院支取粮食。他们的身份有的属于寺院某项劳动时的“某头”,负责劳动时从寺院支取粮食,有的是寺院的附属人员,在寺院中承担各项具体的劳动,领取春秋粮、冬粮以及节料等,身份等同于或高于奴婢。
二、领取寺院节料的僧官、众僧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的僧官、众僧在节日期间也会获得节料。寺院支出的节料有白面、油、麦、粟等,其中麦、粟一般用于卧酒。
S.3074v《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某寺白面破历》第42行载“廿四日,出白面叁硕,付利珍,充冬至众僧节料”[3]171。S.1519(1)《辛亥年(891或951)某寺诸色斛斗破历》第9行载“十九日,麦酒壹瓮、粟酒两瓮,僧录僧政节料用”[3]177。S.1519(2)《辛亥年(891或951)十二月七日后某寺直岁法胜所破油面等历》第12行载“(大岁日)又酒肆瓮,诸和尚节料用”[3]178。P.2049v《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第175行载“麦玖斗,冬至卧酒僧官节料及徒众等用”。第176至177行载“麦玖斗,岁卧酒僧官节料及众僧等用”。第318至319行载“油贰斗伍胜,岁付众僧节料用”[3]377,383。P.2032v《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第236行载“麦九斗、粟壹硕二斗,冬至节料及众僧等用”。第247行载“粟壹硕贰斗,和上众僧法律等岁(付)节料用”。第251行载“油肆斗陆胜,岁付众僧节料用”[3]467-468。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乙巳年正月已后)第308行记载“油五升,岁付众僧节料用”[3]419。
上述文书记载了敦煌诸寺领取或享用节料的僧人,有众僧或徒众、僧录、僧正、法律、诸和尚等人。众僧或徒众一般属于本寺僧人。僧录、僧正、法律及诸和尚的身份可能比较复杂,有的可能属于敦煌佛教教团的成员,如僧录或僧正等,有的可能是本寺的僧官。当冬至、大岁日等节日期间时,这些僧官也从寺院领取一部分节料。但是相对于一般的僧众,僧官从寺院领取的节料,基本上都有酒,而普通的僧众,仅有麦、粟、白面等。可知敦煌寺院僧官与普通僧众领取或享用的节料具有等级性。
三、敦煌寺院中酒户的节料
在唐宋时期的中原地区买官曲的酒户一直存在,即“明年(崇宁四年),改令磨户承岁课视酒户纳曲钱法”中提到的酒户[12]。但是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被称为酒户的有两种:一是官酒户,二是寺院中的酒户。
(一)敦煌的官酒户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的官酒户,如P.3569v《唐光启三年(887)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附判词》记载:
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去三月廿二日已后,两件请本粟三拾伍驮,合纳酒捌拾柒瓮半。至今月廿二日,计卅一日,伏缘使客西庭、扌祭微、及凉州、肃州、蕃使繁多,日供酒两瓮半已上,今准本数欠三五瓮,中间缘有四五月艰难之(乏)济,本省全绝,家贫无可吹食坐,朝忧败阙。伏乞仁恩,支本少多,充供客使。伏请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光启三年四月日龙县丞牒。付阴季丰算过。廿二日、准深押衙阴季丰。右奉判令算会,官酒户马三娘、龙粪堆,从三月廿二日于官仓请本贰拾驮,又四月九日请酒本粟壹拾伍驮,两件共请粟叁拾伍驮,准粟数合纳酒捌拾柒瓮半,诸处供给使客及设会赛神,一一逐件算会如后(后略)。[3]622-623
本件文书是唐光启三年(887)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二人上书归义军府衙要求支付酒本的状凭。作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二人需要为归义军出使西庭、扌祭微,以及来自凉州、肃州、蕃等地的使者提供酒水。但由于归义军提供给二人的酒本较少,酿酒的原料入不敷出,故二人向归义军府衙提出补充酒本,以此充供使者。从归义军支付给他们的酒本35驮,即归义军府衙需要向官酒户支付大量的酒本,可知归义军时期确实存在着官酒户。
(二)敦煌寺院中的酒户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寺院中的酒户。如沙州寺院有隶属的酒户,S.0542《戌年诸寺丁口车牛役部》第44旱记载:“(大云寺)安宝德:煮酒一日。”第146行:“(灵修寺)何伏颠:酒户。”[13]可知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寺院有酒户,他们隶属于寺院,是寺户的一部分,但是也承担官府的劳役。
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统治下敦煌寺院的酒户。如S.1519(1)《辛亥年(891或951)某寺诸色斛斗破历》第9行载:“油贰升,酒户郭没支节料用。”[3]177P.4906《年代不明(10世纪)某寺诸色破用历》第6至7行记载:“油壹升,与酒户安富子寒食节料用。”[3]233寒食节时,寺院的酒户郭没、安富子各从寺院支取节料油2升、1升。对于二人的性质,姜伯勤指出,他们已经摆脱了对寺院的隶属性,从寺户酒户转到以领取寺院酒本为寺院供酒的酒户。作为小生产者和小商品生产者,他们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作为当时开店投榷的酒户,在买官榷或交榷钱后取得卖酒资格,并以零售的形式向寺院发售,这种经营方式属于封建社会商品生产性质;另一方面寺院以预付酒本的方式向酒户发放安家酒本,这种酒本在酒户经营困难时有某种贷款式的性质,酒户按照寺院的要求酿酒、供酒,从而形成了在一定时期对寺院的依赖,并使寺院得到低于时价水平的供酒,对酒户形成某种超额的剥削[8]255。姜先生依据的是《通典》的记载:“广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定量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8]254广德二年是764年,唐代宗的第二个年号,但是到吐蕃统治敦煌时,由于吐蕃的制度与中原王朝不同,吐蕃统治下的敦煌是否也实行酒榷制度,作者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说明。
对于归义军政权下的官酒户,冯培红指出,官府榷酒制度下有“官酒户”的称呼,既冠有官字,相对应的应该有寺院酒户的存在。冯培红对姜伯勤提到的“敦煌诸寺供酒的酒户又称为酒司”这一说法,他认为姜先生误解了酒司的含义,“既混淆了酒司的性质,否认酒司是归义军官府的酒业管理机构,而认为其属于寺院性质;同时又混淆了酒司与酒户之间的关系,否认两者是互为从属的关系,而认为彼此等同”[14]。张议潮建立归义军政权以后,曾经对部分寺户进行放免,但是张议潮死后,其政策被改变。当时的寺院为了保护财产,“千方百计地把寺院对地产和人户的占有保存下来”[8]128,如寺户被以“常住百姓”的名义保护下来,寺田被称为“厨田”,等等。在此情况下,吐蕃时期出现在敦煌寺院中的寺户酒户,或寺户酒户的一部分应该也是以常住百姓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因此,笔者同意冯先生的意见并认为归义军时期隶属于寺院的酒户继续存在。而被保存下来的这部分酒户,他们作为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隶属人户,在节日期间也从寺院领取节料。
由此可推测酒户安富子、郭没两人与其他在寺院领取酒本的经营者如马家、寒苦家、罗家店、丑子店等不同:酒户安富子、郭没完全是隶属于寺院,从寺院领取节料,而马家、寒苦家、罗家店、丑子店等酒店应该是姜伯勤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的从寺院领取酒本,依附于寺院,但是又向官府交纳酒榷的酒户、小生产者或者小商品生产者。同时,笔者也在敦煌文书中多次发现寺院从以上酒店沽酒的记载①,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后者虽然与寺院联系密切,但是他们并不隶属于寺院,他们与寺院应该是一种合作关系。
从敦煌寺院支付给郭没、安富子二人的节料可看出,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寺院继续存在着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寺户酒户转化而来改称为常住百姓并与之身份相差不多的寺院隶属酒户。这些酒户同寺院常住百姓或寺奴婢一样,过节时从寺院领取节料,而且还极有可能从寺院领取月粮或春秋粮。
四、敦煌寺院领取节料人员的特点
晚唐五代宋初从敦煌寺院领取节料人员的身份有以下特点。
其一,附属于寺院的人员,他们的身份略等同于寺院的奴婢,但是却比一般的奴婢身份要高,如恩子、黑女等人,他们在节日期间从寺院领取的节料是麦、粟、面、油等。此外,领取节料的人员还有隶属于寺院的酒户,他们从寺院领取节料以及酒本,所酿造的酒归属于寺院,基本上不能对外出售。这与那些独立开店的酒户不同。
其二,敦煌佛教教团的僧官以及寺院的僧众也在节日期间领取节料,如僧录、法律以及寺院的众僧、诸和尚或徒众等。他们领取或享用的节料有酒、麦、粟、白面等。
其三,从敦煌寺院领取节料人员的身份看,寺院的附属人员几乎很少有酒,然而敦煌寺院或佛教教团的僧官或诸和尚等人从寺院领取的节料里有酒。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寺院在发放节料时的等级性。
唐代佛教繁荣,中间虽然经武宗灭佛影响,但是佛教仍然深入人心。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虽然处于当时中西交通的要道之上,然而它并没有受到武宗灭佛的打击,佛教仍然在此地流行,寺院的僧人除了参加一些必须的生产劳动外,还经常参加或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在宗教活动中获得外界的布施。与中原地区佛教寺院不同的是,敦煌寺院平时并不提供本寺僧人的日常饮食,但是在节日期间,僧人可从寺院领取或享用节料:酒、麦、粟、面、油等食品。此外,寺院的隶属人口也可在节日期间获得寺院下发的节料。但是他们的节料与僧官、普通僧人相比,仍然存在着等级性。
注释:
①敦煌诸寺马家、寒苦家、罗家店、丑子店等酒店沽酒记录:S.4649+S.4657拚合《庚午年(970)二月十日沿寺破历》S.4657第7行“□月十七日,粟壹硕贰豆斗,员昌店沽酒石众井……”(第215页);S.6452(1)《某年(981—982)净土寺诸色斛斗破历》第1—2行载“十四日,粟壹豆斗,就氾家店沽酒”(第222页);S.5039《年代不明(10世纪)诸色斛斗破用历》第26—27行“麦陆斗,就丑子店沽酒沋都头亡看都官用”,第29—30行“麦陆斗,扵史盈子店沽酒屈曹僧正阴都头用”(第229页);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让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第234—235行“粟柒斗,寒苦及马家沽酒三日交库用”(第360页)。S.5050《年代不明(10世纪)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稿残卷》第14—15行“粟伍斗,赵家店沽酒迎磑车师僧用”(第535页)。以上均来自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印中心出版,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