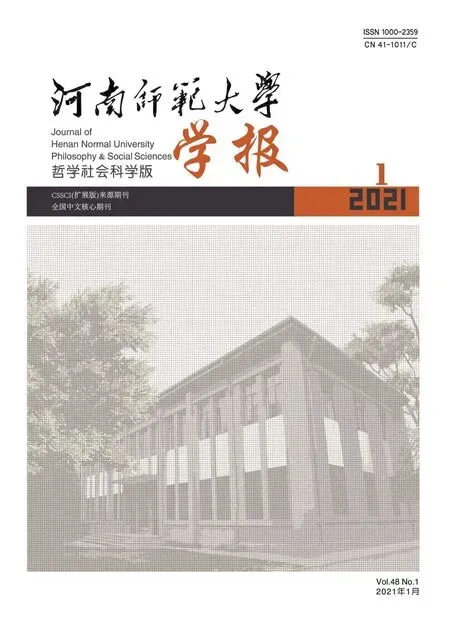加速化社会的治理方案:从固化模式到灵活行动
周 军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已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激烈变化和加速化过程进入到平稳发展的阶段。这既是社会的总体特征,也是社会的现实条件,因为社会及其治理都呈现为这样的特征,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条件。而如今,我们已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砥砺前行数十年,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流动性的迅速增强,以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急剧增长,正改变着社会总体特征,改变着治理的社会现实条件,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努力思考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现实。对此,我们将提出怎样的治理方案才能适合于这个以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为总体特征和现实条件的时代呢?
一、科层制对固化治理行动模式的积极建构
作为工业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理性化的结果,官僚制组织的基本结构是科层结构,其在结构化工业社会及其治理的过程中使得整个社会都同样地呈现出科层结构特点,并基于这种结构来运行和治理社会。通过科层结构,官僚制组织寻求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控制低速流动性、化简低度复杂性、排除低度不确定性。在科层结构不断取得良好治理效果的过程中,官僚制组织高度依赖这种结构形式进行社会治理,因而形成了固化治理行动模式。可以说,用固化治理行动模式来规范和约束行动者,其原初的目的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这种行动模式在规避人的非理性行为和政策自上而下执行方面有着以往任何行动模式所不具备的“技术优越性”(1)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但它却在透过这种技术优越性尝得“甜头”之后逐渐走向了对这种固化模式的过度依赖,而遭到日益加速的流动性、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反噬,使行动者变得行动固化,缺乏灵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此,在承认固化治理行动模式以往的积极功能的同时,我们也要在当前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批判地认识它,而其中的关键点则在于:一是固化,二是模式。
就治理行动固化的发生原理而言,固化可以概括为两种主要情形。一种是预设。面对低速流动性、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治理任务,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在分解治理任务、设计治理流程时,预先假设了可能出现的问题情形,假设了可能的问题解决方案,以及每种方案可能出现的后果。决策者会根据预期所想要达到的治理结果,建立唯一朝向这一结果的通道,排除其他不在预设范围的任何可能性,甚至将这些可能性视作错误。如此,每个人、每个环节、每个机构都要照着预设好的标准和规则运行在通道内,不得出现偏离预期目标和预设轨迹的任何“差错”。这样,科层结构也就通过这种预设方案固化了治理行动。而其后的治理实践则帮助验证了这种预设的固化行动是高效的,是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的,事实上,越是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决策者就越有足够的动机去强化它,执行者就更乐意接受它。
而另一种则是经验。行动者根据以往行动者或自身的历史经验,习得问题解决的方案,这种经验的习得既可是成功经验,亦可是失败经验。行动者在成功和失败经验中进行多方面比较,形成个体特定的行动习惯,并在每次遭遇类似问题情境或条件时采取相同或相似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经验固化是思维定式引发的行动定式。相比较而言,组织的经验固化过程比个体的情况要相对复杂些,因为经由历史的经验知识而逐渐形成组织行动习惯,会经历比个体行为选择更加复杂的筛选过程。如果说个体往往更乐意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偏好而形成习惯,那么,对于组织而言,筛选过程则要综合历史和当前、个体和集体、自我和他者等各方面的经验知识进行决策,而筛选结果则往往会被内化为组织及其成员行动习惯。这实际上是一种行动依赖,或者说,组织及其成员在采取行动时,更愿相信这种固化的经验和习惯,因为它们通常可能是正确的行为选择,即便它们是错误的,也可能是不需要个体去承担责任或后果的。
与固化类似,模式也是科层结构的重要观察点,但在这一观察点上,模式更倾向于模仿系统的运行,即从已知条件的输入,经系统运行后,输出结果来。一方面,在模式化运行中,该行动者总是能够或希望能够从已知条件出发,获得未知的结果。可以说,“工业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社会行动都可以归类到模式化行动的范畴之中,行动大多建立在理性知识的基础上”(2)张康之:《模式化行动与合作行动中的知识类型及其比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如果行动者掌握了系统“暗箱”部分的运行,那么,在输入条件已知、系统运行已知的双重前提下,输出结果也便由未知转化为已知了。模式也就是如此运作的,即行动者利用已掌握的理性知识科学地设计出了模式的系统运行部分,并设定好所要输入的条件,当条件满足时,便会自然而然地输出所想要的结果来。另一方面,在模式运行中,它将已知理性知识进行可视化处理(如各种模型),当行动者采用这类模式开展具体治理行动时,便能够照着这种模式或模型的运行规则而获得相应的结果。例如,在行政审批运行中,输入必要材料之后,才会产生相应结果,一项行政审批内容是否能够得到通过取决于输入必要材料的完备性,结果是从要件到结果的审批过程脱离了具体行政内容,或者说,对于行动者而言,具体行政内容已与行政审批程序无关了。当今技术条件的迅速发展更使得模式化运行变得更加便利,促使行动者更加依赖它,因为它所建构的输入—运行—输出的逻辑关系,使行动者能够清楚地把握和预测行动产生的实际结果,并因而依赖模式化运行的可预测、确定性方案。
通过固化治理行动模式,科层结构将行动者限定在了一整套条条框框之中,这些条框以预先设计好的行为规则和行动轨迹来规范和约束行动者及其行动。按照科层结构的设计初衷,固化治理行动模式原本可以通过控制、化简、排除来应对低速流动性、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然而,这种成功却在流动性加速、复杂性增长和不确定性集聚的社会变迁中逐渐暴露出其内在缺陷,进而失去了原有的效用,变成了束缚行动、消磨积极性、抵消自觉性的无形枷锁。在现实和逻辑两个层面上,在科层结构强化对行动者及其行动进行控制的同时,行动者自身也依照相应的规则和轨迹做出同样的策略选择,或者说,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建构达成控制与被控制的共同结果。
一方面,面对流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问题时,科层结构开始组织开展治理行动时,最大的担忧便是行动者不能按照预设好的行动方式和轨迹行事而导致行动失败,因而,它寻求固化行动模式来对行动者及其行动实施有效控制,以达到决策者设定的预期目标。即便实际情况并没有按照预设路径进行,科层结构也不会因此就放弃固化行动模式,反而会在对其进行修补式改革中扭转不利局面,进而达到决策者所希望的“最优”或“满意”结果。事实上,这种方式越是好用,行动者就越是依赖它,而决策者或规则设计者就越是要强化它。在不断强化这种行动模式的主动设计过程中,决策者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却忘记了什么是预期目标,以及为何设定这样的目标等根本性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这种固化行动模式是合理合法的、经过科学设计的,它就能够达成预期目标,他们在乎的是过程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果这样的话,结果也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了。如此下去,便在不断强化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异化”现象,固化行动模式超出了实现原初目标的范畴,而成为限制和约束行动者及其行动的工具性策略,其结果则是建构了一种控制导向的结构化方案。
另一方面,在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中,行动者被镶嵌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并且他们也并非将治理作为一项崇高的正义事业,而更多的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在谋生职业的意义上,行动者便会进行理性的“计算”。表面上看,科层结构是一种奖罚分明的结构,但实际上,对于行动者而言,奖励并不如惩罚来得直接,奖励或者是金钱的,或者是职务晋升的,但在科层结构运行实际中,这种奖励往往并不能很好地调动行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种奖励兑现起来是很难的,甚至还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主观判断。而惩罚则相对直接,经济惩罚会很快反映在行动者的工薪收入上,而职业前景惩罚则可能导致行动者直至退休都无法得到应有的晋升。特别是在获得奖励尚未兑现的情况下,又因犯错而遭到惩罚,导致行动者曾经为奖励而付出的努力“前功尽弃”。为此,在科层结构中开展治理行动,行动者最大的担忧是承担责任,因过错或失误而受罚。因而,在科层结构日益滋长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氛围中,行动者在采取行动时,面对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已明确规定的情形,不敢僭越雷池半步,既怕犯错,又想规避或推脱责任。而在面对那些新出现的、没有明确指导的情形时,则无所适从。这时,科层结构则会通过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进行逐级上报、逐级审批的方式来提供新的行为指导意见,处于底层的行动者需要在获得明确审批结论以后才能采取实际行动。在面对低速流动性、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问题时,或者还能够勉强应付,而一旦面对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问题时,它就捉襟见肘了,而这恰恰又是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常态”。
因而,不论是科层结构上述任何一个方面,都明确地告诉我们,科层结构在应对确定、简单问题情形时,其固化模式的表现是优异的,而当面对流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这种固化行动模式的弱点也就暴露无遗了。为此,我们要对固化治理行动模式进行解构,建构灵活的治理行动方案。
二、加速化社会对固化治理行动模式的解构
如果说在低速流动性、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具有结构主义特性的固化治理行动模式能够胜任对那些尚不算太复杂的社会问题的积极有效回应,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流动性的急剧增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急剧增长所构成的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事实已然宣判固化治理行动模式导致的政府治理失灵。更为重要的是,在后期出现针对政府治理失灵的可选择替代方案中,学者们发现,不仅市场和政府会失灵,即便是志愿组织、慈善机构等“第三方政府”(3)Salamon L M,The New Governance and the Tools of Public Action:An Introduction. In The Tools of Government,edited by Lester M.Salamon,1-47,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也会出现所谓的“志愿行动失灵”或“慈善失灵”(4)Salamon L M,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而按照波兹曼的观点,当这些部门都处于“失灵”状态时,也就意味着“公共价值失灵”(5)Bozeman B,Public-Value Failure: When Efficient Markets May Not Do,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2(2).。在当前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尽管我们并不经常看到各部门全面失灵的极端情形,但事实上,当两种及以上的多重失灵频繁、交叠、循环出现并作为一种治理新常态时,我们便不难想象,既有社会治理的固化行动模式及其修补式改革方案正面临着趋向于公共价值失灵的危险境地。
这种治理失灵是社会现实与社会运行的急剧变化对政治、法律、治理造成影响的直接或间接表现。我们看到,罗萨等人提出的“社会加速理论”(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不仅对此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且给社会治理创新方向和理论建构方案带来了重要启示。按照这一理论观点,“现代化的经验就是加速化的经验”(6)Rosa H,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Jonathan Trejo-Mathy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21.。可以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学者观察并关注到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他们从时空压缩、交通、沟通交流、社会节奏(日常生活)、生产和效率、社会文化变化率等诸多领域对此发表各自见解。这些研究所提供的例证,使我们很容易从这个时代中找到大量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是一个日益加速化的社会,并且事实上它已经呈现出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特征。但同样地,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例证或领域,它们并没有加速,甚至还呈现为减速的状态。这种“反例”给人们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误解,即社会并没有像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加速化了。这就涉及社会加速的两个关键问题,即社会的加速还是社会中的加速。事实上,我们能够从当今社会中找出各种形式的加速状态,因而我们认为,加速化是这个社会极为重要的特征,同样,当我们看到大量减速的或者说放缓的情形时,也同样能够得出结论,即社会是减速的。而就社会加速而言,其内部却显然存在着加速与减速并存的局面。最为典型的减速情形,如文化、结构、社会排斥等呈现为一种相对稳定性,甚至在有关政治文明和历史的研究中,学者断言,它不仅没有加速,反而走向了“终结”,如福山所讲的“历史的终结”。实际上,在现有制度安排和治理体系中,如果我们的治理安排失当,那么,它不仅不会促进文明的进步,反而可能导致“文明的终结”(7)张康之:《论风险社会中的治理变革》,《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在加速化的社会里,高速流动性对政治、法律、治理的影响也基本呈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加速,二是减速。我们知道,速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就社会加速和减速的相对性而言,当我们看到社会的某部分领域在加速,而另一部分没有加速或者加速度并没有跟上时,那么,另一部分则呈现为相对减速的情形。而这部分领域并没有加速,只是另一部分在降速,也会表现为这部分的加速情形。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来看,我们面对的社会加速化,显然是相对复杂多变、多种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即我们所观察的部分在加速,而相对的另一些部分或者在加速,或者加速度不足,或者在降速。在这种复杂的加速化社会中,高速流动性对治理的影响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不论是既有治理模式还是正在生成中的治理模式,都将面对加速的考验。因而,加速是这个时代走向成功最为重要的行动策略。对于既有的、老旧的、固化的治理行动模式而言,它并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要想方设法在社会中谋求生存之道,因而,我们看到大量修补式改革方案的出现,其主要特征基本可以概括为寻求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同步的加速度。然而,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成功。并非加速行动策略失败了,而是能够支撑其加速的“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组件失败了。当固化治理行动模式及其修补式改革方案想要进行加速以求跟上时代步伐时,它们残破而落后的核心组件并不能承担起这样超负荷的劳动。因而,继续加速不仅不会跟上步伐,反而会加速其走向“终结”。因此,我们看到,固化治理行动模式试图通过外围加持方式进行加速的思路失败了,等待它的则是我们时代新的理论命题,即寻求全新的替代治理方案。这一方案必须是和高度流动性、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相匹配的,其产生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并且是具有很强前瞻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豪华版”治理方案。如果我们用“轿车”来比喻现有治理模式,那么,我们则不能继续采用“轿车”来命名这一全新治理方案,因为在核心组件上它已经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轿车”了。
可以说,在行动逻辑、规则体系、运行程序、价值实现等这些核心组件上,固化治理行动模式是一种制度主义框架下的结构化承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它努力通过官僚制组织及其“条块化”的科层结构去实现这种“结构化承诺”(8)Colebatch H K,Polic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9,p15.。在具体治理关系上,这种结构化承诺通常又表现为具有稳定性、规律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的科学设计流程、结构-功能方式、控制技术手段等,帮助治理主体回避流动性、复杂性、不确定性造成的治理客体无法准确定位、控制、预测的难题。这是低度流动性、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社会现实条件下,人们在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建构起来的确定性追求路径。也就是说,固化治理行动的制度主义结构化承诺在控制流动性、化简复杂性、预测不确定性上是具有积极效果的。而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带来的各种治理挑战使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灵活性、创造性、流动性之于社会治理的实质性意义,并因而提出要求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具有灵活性、创造性、流动性的强烈诉求,这一诉求与结构化承诺所追求的稳定性、规律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是相矛盾的,甚至可以说,结构化承诺追求的是拒绝灵活性、扼杀创造性、控制流动性的制度安排和治理体系。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进程中,尽管我们能够清楚地预料到固化治理行动模式即将瓦解的必然结果,然而,流动性的增强及其对灵活性、创造性的强烈诉求并没有立即“终结”固化治理行动模式,这可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努力通过各种技术改进和结构优化维持着这种对重要资源的结构化承诺,并力图从其对低速流动性、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问题的积极有效回应中维系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谋求更多的合理性资源。在特定意义上,它做到了并且是成功逃避了被终结的厄运。就官僚如何回应行政改革而言,“态度与行动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反映了官僚们是如何能够自由地形塑其官僚部门以便获得工作任务中所期望的平衡的程度”(9)Gains F. and John P,What Do Bureaucrats Like Doing? Bureaucratic Preferences in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Refor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0(3).。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于官僚制组织、科层结构、固化治理模式的批判和解构总是无法彻底进行的原因所在,因为它还具有很有说服力的合法性基础,并因而拥有着勉强令其继续存活下去的合理性资源。在固化治理行动模式力图通过回应性加速谋划生存下去的合法性基础和合理性资源时,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失灵”不断“打脸”这种治理行动模式及其修补改革方案。
另一方面,面对不可回避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固化治理行动模式也力图通过加速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通过加速的方式并没有使其走出“失灵”的困境,反而加速了其走向“终结”。需要指出的是,在控制流动性的问题上,固化治理行动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特别是其经过科学设计的流程。因而,在对自身进行加速以期跟上社会加速化的步伐时,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流程再造的方式来优化结构—功能、改进控制技术手段、加速组织运行流程来实现的。然而,表面上看,这种流程再造能够保持组织运行的流动性——它确实加速了,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并不能突破其是经过科学设计来控制流动性的本质。因而,当固化治理行动模式加速时,其早期效果是明显的,但随着加速所要求的前置条件越来越高,其效果式微了,甚至在不重构其核心组件的前提下,持续加速的必然结果则是这种行动模式走向“终结”。
因而,对于固化治理行动模式而言,前者是其勠力谋划的修补式改革方案,而后者则是自取灭亡但总想尝试的加速选项。但不论是何种方案,都无法带着它逃脱终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困局,合作治理研究的早期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给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公私合作(10)Linder S H,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 Grammar of Multiple Meaning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9(1).(11)Lund-Thomsen P,The Global Sourcing and Codes of Conduct Debate: Five Myths and Five Recommendation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8(6).、跨部门合作(12)Bryson J M., Crosby B C., and Stone M M,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 Propositions from the Literatur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S).(13)Bryson J M., Crosby B C., and Stone M M,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Needed and Challenging.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5(5).等。逻辑上,政府治理失灵引发的变革逻辑很自然地指向了部门比较优势重组,即在看到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公民等治理力量自身都存在缺陷并可能导致治理失灵的同时,也看到了它们各自具有的独特比较优势,因而进行优势重组才是避免陷入“公共价值失灵”的可能路径。事实上,这一逻辑引导着社会治理创新朝向建构多元治理力量合作的格局。在认识论上,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我们会有这样的冲动和意图,即创造一个近乎完美的存在。而在当前特定的社会现实条件下,我们看到了治理主体在有各自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内在缺陷,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毁灭掉所有这些部门而重造全新的、被认为是完美的部门。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它并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现实是社会建构的(14)Berger P L. and Luckmann 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1.,而我们正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治理体系建构了当前的现实。我们知道,当前的现实不可重塑,但却可以改造,并将影响和创造未来的现实。面对当前的现实条件和未来的治理方向,我们的任务是对固化治理行动模式进行解构,而这一解构任务就是解构其制度主义的结构化承诺。当然,解构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重新建构一个全新的治理行动方案才是我们最终要走的正确道路和要解答的时代命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建构的应当是不屈就于现实,面向人类社会未来的治理创新方案。
三、灵活性治理行动方案的生成与建构理路
可以说,我们对全新治理行动方案的建构思路,是基于对固化治理行动模式的解构而得以展开的。概括而言,固化治理行动模式在其结构、行动、思维上分别具有僵化、固化和定式的核心特征,这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社会流动性迅速增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急剧增长的社会现实条件所要求的治理的弹性化结构、流动性行动、创造性思维是不相匹配甚至背道而驰的。因而,在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总体特征下,当我们努力为社会治理创新寻求一种全新的治理行动方案时,必须首先在行动主义框架下对固化治理行动模式的这三个核心特征进行解构,才能最终完成建构全新治理行动方案的目标。总体而言,从结构、行动、思维三个维度进行考虑,我们所要建构的,是一种灵活的方案,而不是固化的模式,为此,我们称之为灵活性治理行动方案(见表1)。

表1 固化治理行动模式与灵活性治理行动方案比较
第一,弹性化的结构,而非僵化的结构。在结构-功能的意义上,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排斥流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抗拒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冲突,被动适应复杂的治理环境(G),通过各种控制导向的技术手段对已被条块分割的组织单元或社会部门进行功能整合(I),对不符合组织目标实现意图的内外部行为实施强有力的控制,创制和维持组织内外秩序和运行稳定(L),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机构的急剧膨胀来换取组织目标的微弱实现(A)。因而,从固化治理行动模式的生成与发展路径来看,它基本符合了帕森斯对基于目标达成、适应、整合、模式维护等四项基本功能(AGIL)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子系统所进行的总体社会系统的表征。基于这一观点,如果说稳定的秩序是固化治理行动模式最为本质的结构问题,那么,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上,结构依赖于地位—角色的分析单元,在帕森斯看来,“在地位-角色社会体系中,最重要的互动过程包含了个体之间关系的结构……也是行动模式化互动关系中的参与,是最重要的社会体系单位”(15)Parsons T,The Social System,Free Press,1951,p25.。不难发现,固化治理行动模式在通过角色预设建构行为期待和行为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作为相对稳定的、模式化的制度规范的结构。因而,官僚制组织在通过一系列价值模式、角色互动以及规范体系建构了其科层结构。如果说在低速流动性、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回应了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对稳定秩序、共同价值和行为期待的诉求,并显然具有强烈的结构和功能整合意图,那么,在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我们却发现这种稳定秩序的追求和制度安排的整合意图,在约束行动者行为边界和规范组织成员的社会性共识上,因过分强调秩序和稳定、变量控制,以及行为约束而导致了治理行动结构的僵化。因此,在建构固化治理行动模式的过程中,我们将要破解的便是这种僵化的结构,而建构起弹性化的结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弹性化的结构,不如说它是一种无结构的结构。也就是说,弹性化的结构包含着两层基本内涵:一是结构的弹性。这说明的是,我们所要建构的治理方案具有某种可观察到、可表征、可模型化的结构形态,但这种结构可以随着社会环境、治理条件、行动目的而发生适应性改变,这种改变使组织及其目标实现对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二是弹性的结构。这说明的是,它并不具有某种特定的结构形态,或者说,我们拥有一个类似于结构“百宝箱”的存在,当治理行动需要何种结构来提供支持时,行动者便从中选取何种结构或多种结构的混合。为此,行动与结构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行动者不依赖或受制于固定的某种或某类结构开展行动,而是由特定的行动来决定采取何种结构形态。我们可以说,弹性的结构是行动中的结构、流动中的结构。为此,基于上述两点,我们认为,“行动者网络”更适合来表征这种无结构的结构状态。
这里,我们并不主张将“行动者网络”视作某种特定的结构形态,但事实上,我们却可以把它当作某种结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积极投身治理行动中的行动者都是网络的节点,它们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又构成了网络的“链”,并使由其构成的网络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弹性。而之所以不将其视作结构形态,主要是因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行动者网络”超出了特定时空限制,或者说,它具有很强的时空延伸特征。在时间上,作为节点的治理行动者既是现在的,也是过去的和未来的,不论是身在何时的行动者,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代际和当代)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治理行动,因而可以说,它们都在这样的治理网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且在时间维度上形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向互动和多维呈现。在空间上,行动者既是“在场”的,也是“不在场”的,因为信息技术等创造性技术已使所谓的“存在场景”(16)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Polity Press, 1984,p61.式微了,不论其是否在场,网络中的行动者及其行动都将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行动者发生互动。而在这样的互动中,行动者便已然超脱了科层制的僵化结构,不论其身处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虚拟世界中的何处,身处何种社会或组织层级,身处组织内部还是外部,都不能排斥和抗拒其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以及对合作治理行动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不排除消极影响)。因而,在“行动者网络”建构上,我们力图促使其朝着松散、灵活、流动的构成方式发展。在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条件下,也只有这样的网络才能够为灵活性治理行动方案提供足够的组织、交往、行动支持。而正是如此,我们才能发现,区别僵化结构所造成的行动者及其行动的消极、迟缓、被动,弹性化结构能够为行动者及其行动——特别是积极的、主动的、自觉的行动——提供足够的支持性资源。
第二,流动性的行动,而非固化的行动。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17)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Polity Press, 1984,p377.。在吉登斯看来,规则和资源共同构成了结构,并通过二者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结构形态。其中,规则是结构中相对稳定的知识,对行动者及其行动起到制约和规范作用,而资源则是积极变动的能量,是行动者及其行动的外在条件。因而,吉登斯才会认为结构“既有制约性又有能动性”(18)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Polity Press, 1984,p170.。而当我们去思考结构与行动二者关系时就会发现,结构中规则和资源两种要素对行动者及其行动构成了不同影响。作为行动者的知识和理解,规则通过行动者对知识的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而内化为影响行动的内在因素,而一系列相互联系、彼此交错的规则群,又通过与实践活动的建构性联系而成为行动者及其行动界域。“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记忆)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19)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Polity Press, 1984,p17.。结构中的规则往往会因行动者的知识局限和理解偏差而产生意外后果,而在规则设定上,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是惧怕并反对“意外情形”的,因为这会引发不情愿的结构变迁。因而,我们看到,尽管作为一种知识和理解,规则需要得到行动者的内化才可对行动产生作用,但官僚制组织则是强行将规则灌输到组织的每一个角落和组织中的每一个人的,其科层结构更多地表现为追求稳定秩序的限制性规则。实际上,它不仅忽略了资源的积极变动能力,更以拥有和控制组织运行的内外部资源而寻求确定性和安全感。
如果我们需要继续在结构的意义上去理解“行动者网络”,并获得其建构思路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在科层结构中,规则的稳定性及其对行动的限制性远胜于资源的变动性及其对行动的支持。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择从限制性规则和支持性资源去重构结构。与科层结构高度依赖限制性规则不同的是,“行动者网络”更倾向于获得资源的广泛支持,而不是规则的过度限制。也就是说,在资源稀缺性假设前提下,行动者的策略是充分整合各种优势资源来开展合作治理行动,因而,它们更加需要资源的广泛支持,并围绕支持性资源在持续的合作行动中建构流动性的规则,替代预设的各类设计性规则对行动的过度限制。从支持性资源角度去观察“行动者网络”及其结构方案,我们看到,基于“行动者网络”的行动不同于基于科层结构的固化行动,而是流动性的行动。这种流动性来源于资源的流动特性。如果资源仅被特定行动者所控制或者根本不被任何行动者所拥有,不能在行动者之间自由流动和有效分享,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行动者及其行动得不到足够资源的支持而无法克服资源稀缺性的约束条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为了获得或拥有资源的竞争模式只能短暂地促进共同福利的增长,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公共支付以及对资源的有效共享才能保证共同福利增长的可持续性。因而,对于“行动者网络”的建构,我们主张用支持性资源取代限制性规则在合作网络中的关键地位,并进而在合作治理中建构一种流动性的行动体系,而非固化的行动。
第三,创造性的思维,而非定式的思维。对于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而言,受行动者“自由意志”决定的行动选择是与组织所追求的确定性相违背的。按照近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进程,官僚制组织的一切设计都朝向祛除充满不确定性的“价值巫魅”的方向发展,并千方百计通过控制的技术手段来改变行动者的自由意志、结构化其知识、定式化其思维,使其理所当然地认为按照经过科学设计的规则行事是最优解、最合理的方式、最符合组织目标(公共利益)实现的路径,从而达到控制行动者意志和行动的目的。对于正义的行动者而言,自由意志是他们能够作出正确行动选择的基础,而不同选择标准和价值偏好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行动者对行动选择的理解和决策。一般来说,行动者会选择三种基本标准:一是社会公平正义。正义和非正义是一组普遍的、社会性的判断标准,它更多地来源于法律认知和道德认知;二是公共利益实现,这是公共生活领域特定的职业或行业标准,属于角色认知;三是官僚制组织的目标,这是最贴近行动者及其行动选择的要求和规范,属于组织认知。但人们最担忧的是,当这三种标准相互冲突时,行动者应当按照何种标准来进行行动选择,这其实也是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最为担忧却也很容易解决的难题,即通过在三者之间建立统一性来结构化行动者的思维。也就是说,官僚制组织的目标设定以及为了这些目标而制定的各种规则被宣称是与公共利益实现完全一致的,或者说,组织目标的实现是公共利益实现的途径,而公共利益实现则又是与社会公平正义保持高度一致的。基于三者之间的统一性,行动者及其努力实现的组织目标就是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然而,这种统一性却事实地掩盖了三种标准之间可能,使行动者围绕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所设定的规则行事,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其行动选择既是其自由意志,又是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
其实,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也并不简单地将设计性规则强加给行动者进而限制行动者选择的思维,而是将规则结构化为影响行动选择的经验性惯例和常识性知识。就经验性的惯例而言,官僚制组织将通过实践经验积累而来的知识结构化为一系列的惯例,那么,行动者作出了违反这种惯例的行动选择之后,就会被视作组织中的“异类”,并因而在社会交往关系中遭到排斥,甚至是打击。为了这种社会交往需求的满足,即便行动者认为自己的行动选择是正确的、正义的,也会因担忧违反了组织内约定俗成的惯例而放弃这种选择,因而在组织中表现为“随大流”“依惯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得过且过”的组织亚文化氛围。就常识性的知识而言,按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规则便是结构中相对稳定的知识。在知识结构化的意义上,如果惯例属于非正式知识的范畴,那么,规则就应当属于正式知识的范畴。尽管我们说行动者对知识的结构化通常是带有反思性的自我认知,但事实上,这种自我认知往往是对法律认知、道德认知、角色认知、组织认知的映射。官僚制组织也正是通过这种认知映射使行动者潜移默化地接受知识及其结构化,并形成定式思维。在确定性和稳定秩序的追求中,定式思维引导行动者按照组织的规则和要求采取行动,祛除“价值巫魅”,从而实现行动的理性化。
在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条件下,建构“行动者网络”需要打破依赖结构化知识的定式思维,建构基于无限想象力的创造性思维。在人类理性化过程中,知识结构化和思维定式化导致了人类创造力的流失。在合作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建构中,我们主张寻求理性和想象力的双重支持,并更多地依靠人类无限的想象力在各种奇思妙想中寻求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实现创造力的回归。但是,我们自然会追问,什么是奇思?什么是妙想?我们无法回答它们,因为任何有限的回答都可能限制了它们的内在张力以及可能激发的想象力。事实上,对于想象力的过多理论论证是徒劳的,任何指导性的、预设性的思考,都似乎源自我们已然被结构化的知识和定式化的思维。尽管想象力常以结构化知识、理性化思维为基础,但与之不同的是,想象力是实践的、流动的、无拘无束的,更没有任何结构可言。或许我们不能用任何形式化的语言来框定它,但它独有的那些特性却预示着我们的合作治理理论建构是开放的、包容的,任何有益合作的成分都应当被这一开放体系所认可和接受,反过来,想象力也要求我们的理论建构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如果借用吉登斯关于结构和规则的理解,我们可以说,想象力源于行动者的知识不完备,这种不完备使我们缺乏被完全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和定式化的思维方式,因而才可能在面对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治理问题时,找到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实现这样的良好意图,那么,便实现了通过想象力回归创造力的美好愿景。
总而言之,当去思考加速化社会的治理问题时,我们发现,低速社会的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通过固化模式开展治理行动时会陷入“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的双重困境。在破解这一治理难题的创新中,我们要以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总体特征和现实条件为历史方位,积极寻求超越固化治理行动模式的灵活性治理行动方案,以突破固化治理行动模式的僵化结构、固化行动和定式思维,最终建构一种具有弹性化结构、流动性行动以及创造性思维的行动方案。对于这一行动方案的建构,我们采取的是不同于制度主义逻辑的行动主义建构方案,当然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合作的。可以说,就实现合作治理理论建构的目标而言,我们目前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它需要不断吸纳更多的积极合作成分,将这一建构方案延伸至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行动者,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行动者网络”平台,积极开展合作的话语体系和行动方案的建构。
——基于马克思和韦伯文本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