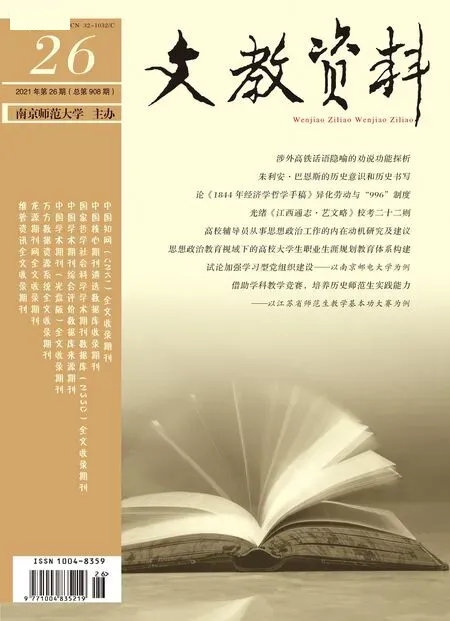庄子美学中的理想人格塑造及其现实意义
谢 姣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庄子哲学具有深厚的美学意蕴。李泽厚曾提出“庄子的哲学即美学”的观点。他说:“从所谓宇宙观、认识论去说明理解庄子,似不如从美学上才能真正把握住庄子哲学的整体实质。”[1]庄子的哲学与老子的哲学对宇宙的关注不同,虽然也关注天地、自然,但最终回到人存在的意义。虽然同为人生哲学,但庄子哲学与儒家哲学对人生现世功用的关注不同,更偏重人格的塑造和精神的自由,希望人能“不物于物”,超越现世人生,最终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庄子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有特定的时空环境和现实土壤,但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既受惠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又因为沉迷感官的物质刺激陷入异化,“房奴、车奴、孩奴”等流行词汇,体现出人类为物所役的现状;“丧”“佛系”等生存状态,展现出现代人精神的迷惘、焦虑和失重。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千年,但庄子在宗法社会崩溃时期的人生哲学思考,对于当下仍旧显得历久弥新而颇具现实意义。
一、人生困境
庄子哲学产生在氏族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早期宗法社会崩溃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物质文明迅速发展,财富和欲望不断积累,压迫和剥削日益激烈。正如《庄子·盗跖》所写的:“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2]无耻的人富有,自夸的人显达,无耻又自夸的人反而名利双收。在这种背景之下,庄子一方面抨击社会不公、人心丑恶,发出“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2](《庄子·盗跖》)这样深刻的批判、直指人心的诘责。另一方面指出人日益为外物所奴役,被自己的贪欲、野心、权势、财富所统治的现实,抗议和批判“人为物役”。《庄子·骈拇》中写道:“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在庄子眼里,天下的人无不为外在目的疲于奔命,疲惫不堪,“小人”“士”“大夫”“圣人”,为了“利”“名”“家”或“天下”,皆是如此。庄子第一次“意识到人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与作为某一群体(家、国……)的社会存在以及作为某种目的(名、利……)的手段存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3],这成为庄子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我们可以将这看作庄子面临的第一重困境:人追求自由的本性与外在物质、环境、条件桎梏之间的矛盾。
在受到外物桎梏的同时,人也受到自身局限性的束缚。“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2](《庄子·养生主》)探寻知识是人认知世界的重要途径,但生而有涯,知而无涯;试图以有生之涯徜徉漫无边际的无涯的知识之海,只会扭曲人的天性,让人疲惫不堪。再者,人会因为对自身局限的无知,争强好胜,勾心斗角,“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2](《庄子·齐物论》)。心机深沉、相互算计,斤斤计较、勾心斗角,提心吊胆、失魂落魄;只会失去生机、老朽枯竭,成为“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2](《庄子·齐物论》)。对于人过于追求智巧,坑蒙拐骗、勾心斗角、颠倒错乱、诡词强辩,庄子甚至发出“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2](《庄子·胠箧》)的感慨。这是庄子提出的第二重人生困境:知识与智慧之无穷与人的内在局限性之间的矛盾。
与儒家对人的力量推崇不同,庄子多能直面人的渺小和脆弱。“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2](《庄子·秋水》)相对于浩渺的宇宙而言,人何其渺小,就好像小石头、小树木存在大山之中一样。不但人,而且“四海”“中国”,在无限的空间之内,也同样微渺。庄子说:“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2](《庄子·秋水》)又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xiào)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2](《庄子·知北游》)人所知道的比不上不知道的,人活着的时间比不上没有活着的时间;人在天地之间活一场,就好像一只白马掠过,不过一刹那而已。可见,人除了以自己的渺小面对空间的浩大外,还要以短暂的生命面对亘古而永恒的时间,人的迷乱、哀伤、悲痛都来源于此。这是庄子提出的第三个人生困境:空间和时间的浩渺与生命短暂、渺小之间的矛盾。
二、理想人格塑造
人既受到外物的限制,又受到内在的局限,还以渺小而有限的肉身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无垠里。庄子仿佛在告诉我们,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但庄子并没有停留在人生的困境上,而是试图唤醒人们,从这种悲剧中超脱出来,实现精神的自由、人格的超越。
如何实现人生的超越?最重要的方法是“悟道”。道是指什么呢?这个概念看起来十分复杂,有人认为它是精神,有人认为它是物质,也有人认为它是上帝。庄子认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2](《庄子·大宗师》)“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2](《庄子·知北游》)由此可见,“道”是一个玄妙、超越的概念,道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问无应,但同时,道又有真实有验证,可以心传,可以体悟。与别的事务被时空局限不同,“道”是超越于一切的,它在天地之前已经存在,造就了鬼神、上地,产生了天地,是一直存在、无所不存又无所不能的。但与老子宇宙论不同,庄子的“道”是借宇宙论人生的。明“道”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至人”“真人”“神人”,他获得了绝对自由,可以“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他“无所待”,不受任何外在事务的约束。他是“神人”,“肌肤若冰雪,淖(chuò)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2](《庄子·逍遥游》)。由此可见,庄子想要塑造的是一个超越万物、绝对自由、自然而然、毫不做作的理想人格。
既然“道”顺应自然,那么人要怎么达到这个和“道”同一的理想人格?庄子提出了“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2]《庄子·逍遥游》,即消除了对个人生死、贫富、得失、毁誉等一切事务的计较。庄子还提出了“坐忘”——“堕肢体,黜(chù)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2](《庄子·大宗师》),忘记形体、废黜聪明、摆脱束缚,与道同一。庄子借用孔子和颜回的谈话,告诉我们什么叫“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庄子·人间世》)。孔子要求颜回不用耳听,而要用心听;不要用心听,而要用气听。因为耳只能听到声音,心只能了解现象,气是空虚准备响应万物的,要用“虚”达到境界的超越,展现“道”,达到一种心的斋戒。“无”“外”“坐忘”“心斋”,都是指对人生的一种超越状态。放下名利得失、排除心思巧智、顺应万物变化,庄子以此作为实现精神自由的途径。
虽然庄子似乎看透了一切,但他并非寡情。他没有把世界和人生看成是虚妄的,“与人为善,与物为春”(《庄子·德充符》)、“万物复情”(《庄子·天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讲究对人对物的温暖和善,提倡复归万物本源,号召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中得到快乐,体现他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眷恋与温暖。
三、现实意义
在科技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庄子当时所揭示的这些人生困境并未得到充分解决。
一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弗洛姆认为:“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在这种体验中,个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或者说,个人在这种体验中变得使自己疏远起来。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成了他的主人,他只能服从甚而崇拜它们。”[4]这一概念的核心,也就是人主体性的丧失,与庄子提到的“以物易其性”的判断非常相似。三次科技革命的成功推进了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但同时出现了“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人开始成为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的奴隶,成为与此关联的权力、金钱、名望的奴隶。人们把生活中的他者作为获取金钱、权力与名望的工具,人的主体性与人和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丧失了,“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使人陷入孤独和疏离之中,既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又无法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信任和温暖。
二是个体与自身关系的异化。“超越性是人的一种本质属性,这种本性促使人不断地突破现存的状态、超越自身,永不停息地追求自身的完美。”[6]由此,物欲化的现实世界和张扬主体精神的诉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一边在物欲中沉沦,一边渴望精神的反叛与挣脱。但现实对人生价值的评价错位,显然很难让人超脱于“物”;人被自己所创造的财富束缚和捆绑,在白热化竞争中的内卷压力下,快速迭代的时代与认知局限之间的矛盾,增进了“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分裂感和焦虑感。个体与自身关系的异化,使人常常处于焦躁和惶恐的状态,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
三是意义困惑带来的精神焦虑。在消费的大网之下,人们沦为劳动的机器,膨胀的物质欲望带来精神的困惑和目标感的缺失。“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的意义诘问在青年群体中十分常见。目标丧失后,人们被欲望裹挟、被焦虑包围,内心的澄明和平静变得不可追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速度减缓,阶层固化和上升通道关闭,以及科技进步与媒介发展下信息传递的便捷与迅速,都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失落和不平衡,引发“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的信仰危机。
庄子美学中对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为现代人类异化困境的渡越提供了可能:一是控制欲望。放弃对诸多身外之物的过分倚重,超越对于金钱、权利、名望的追求,返璞归真,与“道”同一,也就是回归人的本源,才能获得身心的真正自由。低欲望生活方式的倡导,主动降级消费等,都是年轻人对此的尝试性实践。二是放慢速度。顺应自然和生命发展的规律,放慢生活的步伐,放弃心思巧智,让灵魂能够跟上身体的脚步,如此才能求得生命的协调和圆满。三是回归生命本身。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将个体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超越个人的局限性和生命的有限性,寻找内心的使命所在,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人的深度链接中得到内心的平和与快乐,找到精神的安顿之所,在对生命本源的回归中,获得生命的舒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