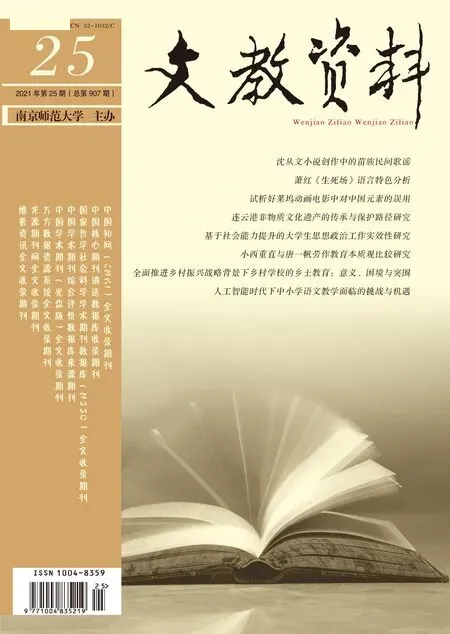从《活着》到《文城》
——审视余华的“苦难书写”
吴豪杰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000)
一、苦难的呈现:苦难人生
在余华的文学世界中,人生处处有苦难,受苦仿佛是一种原罪。余华笔下两个最经典的人物——《活着》里的徐福贵和《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一个是顺从苦难的潮流活着,一个是靠卖血填充苦难活着。
《活着》主人公徐福贵的生命历程可以说是一部“受难”史。福贵一生经历了嗜赌成性、一贫如洗、被抓壮丁、妻子重病、儿子被抽光血致死、女儿生病致聋而后生产致死、晚年丧妻、女婿惨死,就连唯一的外孙小苦根也因为吃多了豆子而撑死等一系列的痛苦,直至最后老了只得一头老牛相伴左右。福贵在旁观了周围亲人的死亡,受尽了生命的苦难后仍然能够活着,是余华的“苦难书写”为读者保留的一块“蜜糖”——生命的韧性。
那福贵的经历为何能称作温情的受难?在余华笔下,每个人在命运面前都毫无反抗之力,虽然想极力挣脱死亡之网,但最终都只能做个顺应天命者,更加增添文本探讨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悲哀。苦难总是在福贵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高危并在努力抗争的时候下达死亡通知,例如福贵的母亲重病,他在给母亲抓药时被抓了壮丁,老人在贫病交加和对儿子的思念中走向了死亡,一切抗争只能半强制半将就地戴上了“温情受难”的帽子。
与福贵“温情受难”相比,许三观一生都在“被迫受难”。《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的不断挣扎。小说中许三观总共卖了12次血,一家人依靠许三观渡过了各种厄运,其中的9次卖血是为了儿子。由此看来,卖血的行为实际上是许三观在践行作为父亲的责任,许三观作为父亲的威严和权利在卖血中体现,然而在体现深沉浓厚的父爱的另一面,卖血行为是苦难的重复,许三观成了卖血的机器。余华让小人物承受无边的苦难,又让他们在苦难的深渊中寻找自我安慰。于是卖血之后吃一盘炒猪肝,喝黄酒,黄酒要温一温便是许三观在苦难中的自我安慰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乐趣。当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靠卖血就能渡过难关,让许三观进入“自我受难”的阶段并不断循环。当许三观被告知自己老了,没办法再卖血的时候,他内心的苦闷与凄楚源于“人生无用论”,这当中流露着他的存在失去价值的悲凉。卖血的苦难结束了,许三观却要承受存在失去价值的内心的苦难,生活之难和存在之重的关系呈现西西弗斯式的难局,苦难永远无法消解,它将永远追寻生存着的人。许三观用卖血丈量苦难的长度,以此考量自己承受苦难的力度。
二、苦难的意义何在?
余华被誉为一位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作家。他在文学作品中展开对生命的沉思,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和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他发表了大量富有先锋品格的小说,努力关注生存与死亡,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困境,如《死亡叙述》《偶然事件》《现实一种》等。他对一系列“苦难”问题的提出,不禁让我们思考“苦难”背后的意义何在?对此亦有不少理解,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忍受的人生哲学。何为活着?余华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这样解释:“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1]
面对人生的种种苦难,福贵找到了缓解苦难的有效方法——忍受。忍受父母的离世,忍受妻子的死亡,忍受后辈的夭折,以一种“顺天知命”的生活态度,与苦难和死亡不断进行抗争。余华曾说过,福贵是“我见到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还活着。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2]。
第二,对凡人直面苦难的礼赞。余华一次又一次描写着死亡,死亡的结局仿佛踩着命运不可抗拒的脚步一步步逼来,死亡成了人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但当小说中的人物面临巨大苦难时,他们没有呼天抢地,更多的是默默地流泪,在沉默中展现个体力量,同时让读者完全投入进去,感受他们所经历的悲痛。例如《活着》中有庆死后余华这样写道:“他一遍一遍想着儿子中午上学时的情形,疼得都哭不出来,直到天亮才不得不埋。”[1]
第三,对生命的人文关怀。余华对生与死有独特的感悟,这与他的童年记忆和成长体验有关,也跟他对人性和这个世界的看法有关。余华在很多场合谈到他的作品都是源于自己和现实的紧张关系,甚至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他后来转向现实主义,个人情绪由早期的愤怒、冷漠转为温和、深沉。他的小说世界带给我们太多的阴郁、压抑、冷酷和残暴,让我们行走于暗夜并听见他在细雨中孤独而无助地呼喊。
三、苦难的再思考:不幸者
回到现实生活,特别是当全人类正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苦难”时,不得不再一次思考余华的“苦难书写”。这并不是想要否定余华的小说创作,而是要对“苦难”再一次挖掘与思考——“苦难”更深的姿态及更深的书写应该如何呈现?
余华是一位极富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的当代作家,其笔下的作品大多都细腻地描绘人类的生存苦痛和人间悲苦。特别是在余华的新作《文城》问世之后,更有文学批评家和书评将其视为余华的重返巅峰之作,这巅峰便是《活着》。暂且不论《活着》是否真为“巅峰”之作,但从《活着》到《文城》,余华一直是在“苦难书写”的道路上“徘徊”。
《文城》讲述了主人公林祥福带着女儿千里寻母,最终来到一个叫溪镇的地方,认定这儿就是纪小美口中的“文城”,便带着女儿在这里生活下来。与《活着》相比,《文城》在谋篇布局上切实展现出不俗的技巧,但叙述内容上仍然没能脱离“苦难书写”的场域。主人公林祥福在寻找“文城”的过程中同样经历种种困难:被小美欺骗丢失金条、初到溪镇遇暴雪险些丧命、在溪镇安居的生活又被军阀和匪祸打破最终惨死。余华同样将故事置于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以雪灾和匪祸构成艰难的生存环境。小说除了主人公林祥福外,其他人物如陈百良、顾益民及作为童养媳的纪小美等无不面临生活的苦难。但是,这样一种“苦难”只能属于个人的“歼灭”而非群体的“歼灭”,只能属于个人的“苦难”而非群体的“不幸”。
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时刻都是对不幸的记忆,都是对不幸者的哀悼。苦难可以学习,可以汲取教训,但不幸能汲取什么教训?正因如此不幸突破苦难的个人场域,沦为一种集体的骇然之物。
在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是不幸者。他从小便被亲生父母抛弃,侥幸存活之后听到福玻斯的预言,出于对神示的信任和对父母的敬爱,他只身一人逃往外地。在三岔路口遭遇强权挑衅之时,他奋起反抗。在忒拜城击败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体现了他的智慧。可以说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乃能文善武、勤政爱民的英明国君,他是英雄主义的化身。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旷世英雄也逃脱不了残酷命运的束缚,无奈徒劳的屡次反抗既体现了俄狄浦斯的英雄形象,又反衬了命运魔爪的强劲残酷,为全剧的悲惨氛围增添了一份壮美。故事的高潮,即俄狄浦斯刺瞎双眼后大呼:“看在天神的面上,快把我藏在远处,或是把我杀死,或是把我丢到海里。”与结尾具有深远意味的评论互相照应:“在一个凡人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不要说他是幸福的。”[3]俄狄浦斯的关键在于:这地方没有他存在的可能,他是一个不幸者,他没有资格存活,没有资格看世界,没有资格拥有他的墓地,这个人不配在地上活着。
反观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对“不幸者”的理解与阐释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如阿Q、孔乙己。在《阿Q正传》的第一章中,作者叙述了四点为阿Q作传的难处。第一,是文章的名目,作者写道:“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这里用“文体卑下”表明阿Q身份的卑贱。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但作者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最开始考据“他似乎是姓赵”,但又被赵老太爷否定。第三,作者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第四,作者不知道阿Q的籍贯。这种种难处暗示阿Q不幸者的身份。因为不幸者是没有语言,没有意义的存在,他们带有奴役的印记,奴役又意味着不可逃脱,有某种咒诅的意味。
同为“不幸者”的孔乙己也是如此。
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4]
对于他人而言,孔乙己成为一个玩笑,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物”,因为他已经失去他的生命形式、社会组织,但却没有死亡,是等待死亡的非生命状态。
然而,不幸者的结局更不幸。赵老太爷一家被抢空,阿Q直接被抓当作替罪羊。“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鲁迅并没有描写阿Q被抓后如何受到刑法拷打,仅仅通过语言和动作描写就将阿Q“不幸者”的姿态展露无遗。第一,阿Q是个不识字的人,这说明他一直被排除在“文明”状态。第二,由签字变成画圈,但阿Q还是失败。第三,阿Q并不知道画圈意味着认罪,是无知地接受他人宣判的死亡。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阿Q成为替罪羊,正是他对于未庄而言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物”,他的牺牲不具有任何意义,不会对未庄产生任何影响。
孔乙己的结局亦是如此。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4]
这种刻画“不幸者”虚无的状态与他者的漠然,使得鲁迅笔下的“苦难”更深刻与虔诚,这恰恰是余华笔下“苦难书写”所未能够探索到的地方。
四、结语
《文城》的问世可以说是余华想要对原有“苦难书写”的突围。余华坦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便开始写这个故事,中间经历了数次中断。那时他刚写完《活着》,希望再写一部《活着》之前时代的故事。他将这归因于这代作家一种“挥之不去的抱负”——希望在作品中搭建出一部百年史的版图。但遗憾的是,这次突围仍算不上成功。尽管在形象上刻画的林祥福这样一个“至善的人、被命运撕扯的人”是成功的,但对“苦难”的叙述还是在原来的老路上徘徊,未能拓展到更深邃的领域。